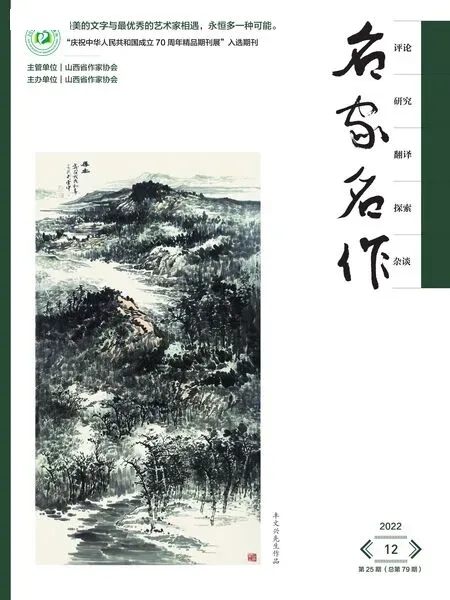民俗文化视角下二人台与日本狂言的对比研究
赵晓春
一、二人台的起源与特点
(一)二人台的起源
二人台是移民活动的精神文化产物。一种艺术形式的诞生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会受时代、历史环境的制约,而移民活动产生的外来人口则通过口口相传,将秦腔、晋剧、道情、社火、秧歌、打坐腔等艺术形式,通过民谣和其他文艺节目的形式传播出去,不但对长城北部、河北坝上和内蒙地区的发展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使蒙、汉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形成了一种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在农忙时可以放声歌唱,到了假日,可以在大街上、戏院里踩着简单的高跷,玩得不亦乐乎,这就是二人台的产生。二人台流行的地域范围很广,东起大同、张家口,西边是阿拉善旗,南部是河曲和榆林,北部是武川和固阳北部。在发展的过程中,二人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大致分为东、西两路,由“东口”张家口迁入的外来人口,在乌兰察布、锡林浩特、河北坝、山西雁北一带,而由“西口”迁入者,在内蒙古西部和河套一带、陕西榆林和忻州一带形成了双人台。
(二)二人台的特点
二人台的演唱形式分为硬码戏、带鞭戏、对唱戏三大类。硬码戏注重“唱、念、做”;带鞭戏为载歌载舞,更多地注重舞 ;对唱戏主要是男女和对,俗称“掏牙句子”,是典型的“敕勒川情歌”。细细品味三种形式,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两个地区、两个民族共同打造的艺术融合韵味十分浓厚。分析来看,二人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唱腔的融合
二人台的唱腔既有晋、陕民歌之音符,又有“敕勒川情歌”的元素。如《走西口》小戏中,男角太春上场前幕后有一声亮调,既似陕北信天游,又像蒙古长调。
2.舞蹈的融合
二人台带鞭戏的舞蹈中既有晋陕社火、秧歌表演动作,又有草原舞蹈动作,特别是男角手中的“霸王鞭”,可以看出游牧民族的影子。
3.语言的融合
蒙、汉两个民族的语言糅合在台词之中,被喻为“风搅雪”。如云双羊的代表戏《阿勒奔花》,汉意为“十朵花”,运用了蒙、汉两种语言,叙唱了蒙古族青年与汉族姑娘相爱的故事,使蒙、汉民众之间的语言自然沟通,促进了民族间的认同,增强了两个民族的关系。
4.曲艺的融合
二人台小戏中加入了敕勒川方言中的串话与呱嘴,幽默、风趣、合辙、押韵、流畅上口,类似快板、快书,有着浓郁的地区特色。
5.牌子曲的融合
二人台在小戏开演之前,必有一段牌子曲演奏,可视为二人台的序曲。演奏的四大件乐器中,丝竹乐器由两件增加到四件,现代人又加入了三弦、笙、唢呐等民族乐器。牌子曲有百首之多,由蒙古族民歌、汉族民歌、蒙元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四个部分构成,演奏分为慢板、流水板、快板等板式,起初舒缓,继而流畅,然后越奏越快,与民间劳动生产生活的节奏大体合拍,美妙动听,雅俗共赏。
二、日本狂言的起源与特点
(一)日本狂言的起源
狂言是日本的传统曲艺类型,与“能”一起并称为“能乐”,也就是说能乐是包括两种戏剧舞台形式的能剧与狂言。狂言和能剧差不多同时出现,中国唐代的散乐(杂技)在奈良时期就传入了日本。平安时期,民间艺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模仿人像的滑稽动作,逐渐发展成为“猿乐”,即狂言的前身。在镰仓时期,狂言逐渐与能剧有了区别,直到室町时期,在王公贵族的帮助下,狂言才逐渐显露出来。狂言和能剧在江户时期就开始了发展,而且速度很快,整体剧目也很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狂言脱离了长久以来只能充当能剧附属的角色,开始走向独立发展。如今,专业的狂言艺人,既可以自己表演,又可以和能剧合作。
(二)日本狂言的特点
日本狂言的创作主题大多来源于日本民间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对上层阶级、权力者的反叛,以及对底层民众的怜悯。它以喜剧的形式、有趣的故事、生动的表情和动作、幽默的方式表达人类的喜怒哀乐。早期的狂言有三种类型:和泉流、大藏流、鹭流。后来,鹭流在逐渐演变中消失,余下的和泉流与大藏流都有各自的特色,其中和泉流共有254种,大藏流共有180种。在内容、语言和服饰等方面,都严格保留了原有的演出形式。两个派系虽有相似的戏剧,却又有着各自的演出特色,同时还具备了日本关东、关西的特色。
三、民俗文化视角下二人台与日本狂言的异同分析
(一)相似性
1.具备喜剧性与生活性
二人台“姓喜不姓悲”,这是整个剧种的特色。从道白到演唱、从走场到台步、从舞蹈到身段、从抬手抬脚到眉目传情,演员用夸张的动作、滑稽的表演、丰富的表情以及种种特技,将观众逗乐逗笑,将“丑角”这一行当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二人台的喜剧性。同时二人台剧目反映的大多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就决定了它具备明显的生活性。尽管演员在表演过程中要对生活中的一些动作进行提炼、加工,以便使之舞蹈化、节奏化,但总体来看仍旧接近生活的原生态,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如在《捏软糕》中,担水、淘米、捏面、箩面、拌面、蒸糕、捏糕、炸糕等一系列动作,都十分细腻、真实。再如在《走西口》中,玉莲给太春梳头、《探病》中刘干妈的台步等均具有生活性。
而日本狂言同样具备这两个特征, 狂言的题材主要取自民间的现实生活,讴歌底层民众,比如农民、仆人、下级武士等的勤劳、勇敢和机智幽默,非常容易引起底层民众的共鸣。日本狂言在喜剧性的塑造上也具有强烈的特色,如《夷·毗沙门》中的有德人为招女婿向西宫的夷和鞍马的毗沙门二神祈求。夷和毗沙门二神都想当有德人的女婿,他们先后来到有德人家,向有德人夸耀自己,互相争夺,还给有德人赠宝,在喜庆中,以双人舞的形式翩翩起舞直至曲终。剧情浅显易懂,具有强烈的滑稽感。
2.表现形式多样化
二人台艺术在完善过程中,已具备了唱、舞、道白、表演、乐器伴奏,不仅有“文场”的丝竹乐,还有“武场”的打击乐,并吸收了晋剧、道情戏等的特点,剧情有了拓展,可以称得上“戏”了,但这个戏程式化程度较低,演员自我发挥的空间大,自由度宽,有西路、东路二人台之分,风格特色体现为多样化。
日本的能剧和狂言起源于8世纪,其后的发展与杂技、歌曲、舞蹈等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融合在一起。如今,这是日本最重要的一部民间戏剧。这一类型的戏剧以日本的文学文本为主,在演出方式上辅以面具、服装、道具、舞蹈等,已经从最初的简单表演变为多样化的表演形式。
3.受众相似
二人台的用语简单明了,多使用本地农民所熟知的词汇,其意象鲜明、逼真、质朴、热烈、豪放、真情流露,充满了浓厚的乡土风情和深沉的人生趣味,且内容多数都反映了劳动人民最熟悉、最关切的生活实践,因而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长时间流传于广阔的农村,演员大多是业余性质的农民和手工艺者,他们有极为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能够准确真实地刻画剧中人物的性格,表达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表演自然逼真、朴实亲切,使二人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从一开始,狂言就是平民百姓和底层武士们生活的产物。在狂言中,最能体现时代特点的是大名·小名类和出家·座头类等。那时,“下克上”盛行,下层反抗上层,例如下级反抗大名,下层僧人反抗上层僧人等,试图破坏旧有的社会制度。有些狂言嘲弄和讽刺大名和高僧,使平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脱感,因此深受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强烈拥护,这是有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的。
(二)差异性
1.表演目的不同
从中国剧种和西方剧种来看,戏剧的目的是娱乐和教育。本·琼生曾说过:“给听众带来欢乐,并给他们带来知识。”如果把这个目标运用到一部戏剧中,就会有四种情形:一是纯粹为了取乐;二是娱乐与教育并举;三是注重教育,同时兼顾娱乐;四是注重娱乐,并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教育。很明显,狂言就属于第一种情形,主要是为了消遣和让人开怀大笑。比如讽刺寄生阶级,一个僧侣在施主家念经,对着一位忘了给钱的师父,百般劝说。而师父想起给予的时候,僧侣却婉拒了,故作清高(《没有布施》)。又比如主题是乡间的生活,岳父和女婿因干旱而彼此争水(《争水的女婿》)。可以说,在狂言的一系列剧中,并没有流露出作者自己的感情和喜好,而是纯粹为了娱乐。
而二人台的传统戏剧则多是描写劳动生产,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歌唱婚姻爱情,具有浓厚的人生趣味,还有一些传说和历史故事。与狂言不同,二人台在愉悦观众的同时,多多少少也表达了创作者的一些个人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特色剧目,西路二人台有《打金钱》《打樱桃》《打后套》《转山头》《阿拉奔花》等剧目,东路二人台有《回关南》《拉毛驴》《摘花椒》《卖麻糖》《兰州城》等。
2.展现形式、侧重点不同
狂言作为能戏的补充,扮演的是辅助者的角色。这就规定其剧本篇幅不宜太长,一般演出时长在30分钟左右,当然也有个别的“狂言”大戏。需要指出的是,狂言是科白剧,即以对白和动作为主。狂言最主要的文本叙事手段是独白性质的语句与段落。在如此简短的剧情中,狂言文本中还常常有演员的大段叙述,这在世界戏剧史上也很罕见。比如《爱哭的尼姑》中,有一位平日爱哭的尼姑,随住持前往信徒家做法事。住持手中摇铃,用佛家俗讲的方式连续讲述了几个古代孝行。哪知道,尼姑竟然呼呼大睡,任凭住持怎样摇铃提醒也无济于事。最后法事无法收场,两人灰溜溜地逃走。在戏剧文本中,住持所讲的佛教故事占去不少篇幅,作用是,他的故事讲得越精彩,观众越会被尼姑的憨态逗笑,越能产生喜剧效应。所以,尽管扮演住持的演员在台上念念有词,但有经验的观众却不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他所讲的故事上,演员的姿态、动作、身段和表情中所蕴含的“花”,才是观众注目之所在。文本故事通过人物直接叙述的方式存在,成为艺能展现的依托。还有一类独白叙述段落是由人物交代事情的背景或来龙去脉,有时出现在人物刚一上场的时候,有时则是在剧本中间。
而二人台更具有明显的“唱”的特征,二人台的演唱,都是一场剧一首独奏,一曲一调。按照情节的不同,用慢、中、快三个节奏进行歌唱。二人台演唱的曲式较为多样,大多是以民间曲目为依托而形成的。最基础的是“爬山调”“烂席片”,并吸纳其他地方的曲谱及其他地方的曲牌,以增加它的表现形式。在二人台东、西两路中,唱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3.戏剧审美不同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狂言呈现的是一种具有“喧嚣”的艺术层次,是它“出神入化”而取得的最高艺术成就。在能乐演出中,与狂言互动进行,在主观上,从美学需求方面,把悲剧和喜剧一分为二,完全割裂开来,狂言为喜,能剧为悲,相辅相成,共同成就。而中国戏剧偏爱各种形式的喧嚣和美学形式与技巧,以营造出一种悲壮的气氛,使观众的心灵受到冲击,并以诙谐的插科打诨嵌入,使其自然和谐,中和了悲剧中过于消极的情感表现。因此,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中国戏剧都具有“中和”美学的至高境界。以二人台为例,我们不能把它界定为纯粹的悲剧或者喜剧,它可以在《卖碗》中揭示出封建制度剥削妇女的丑陋面目,也可以欣赏《打连城》里的少男少女们在灯会上赏灯的热闹景象。
四、结语
作为一种重要的戏剧形式,二人台与日本狂言都具有特别的意义。由于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两类戏剧的表演往往牵扯到神灵信仰、岁时节令等民间习俗,戏剧表演遍布寺庙、神祠、庭院厅堂、会馆茶馆、舟楫河岸等。此外,在表演中,宗教、禁忌等一些具体内容也会受民俗文化的制约。在民俗文化的影响下,日本狂言同二人台相比,虽然在形式、内容等方面多有雷同,但它们的美学和功能性表达方式截然不同,日本狂言的幽默总是与能剧的庄严相结合,两者互补,在音乐中成为一个整体,而二人台无论是手法还是风格,其更为独立及完整,更易于被百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