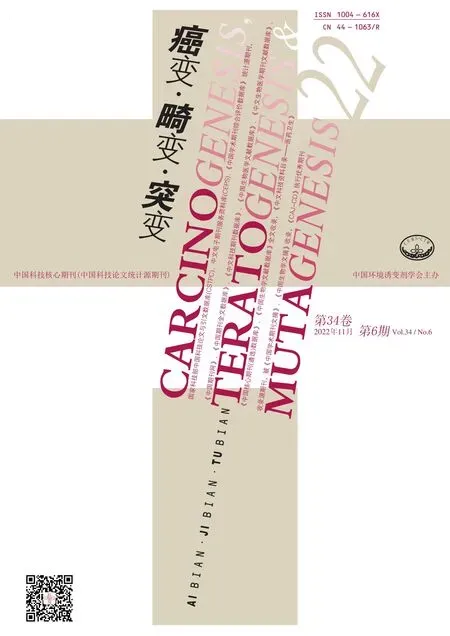调节性T细胞在抗肿瘤免疫及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梁 敏,肖艳红,刘艳灵,王伟岩,刘芹芹,滕清良,
(1.青岛大学附属泰安市中心医院血液病诊疗中心,山东 泰安 271000;2.青岛大学附属泰安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山东 泰安 271000)
肿瘤是机体在各种致癌因素作用下,由细胞异常克隆性增生而形成的新生物,是人类的重大疾病之一。国家癌症中心陈万青教授团队根据2020年全球癌症负担数据和联合国人口数据以及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估算了2022年癌症新增病例和新增死亡人数,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新发各类癌症共计482万余例,死亡近321万例[1]。目前除了传统的手术、放疗、化疗外,肿瘤靶向治疗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是CD4+T细胞的一个亚群,具有调节免疫反应维持免疫稳态的作用,于1995年首次被发现并命名为CD4+CD25+T细胞[2],也称其为调节性T细胞。Tregs因独特的免疫作用成为免疫学研究的热点,一方面Tregs通过抑制免疫应答维持免疫稳态来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另一方面Tregs可通过抑制适应性免疫反应的方式抑制机体抗肿瘤免疫细胞的活性,促进肿瘤发生免疫逃逸。
Tregs在肿瘤免疫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据Tregs可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这一特性,认为抑制Tregs的功能是一种治疗肿瘤疾病的新策略[3]。本文将对Tregs在抗肿瘤免疫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Tregs的起源
1970年,Gershon等[4]发现胸腺源性的T细胞可抑制某些抗体反应,首次提出了Tregs作为抑制性T细胞的概念,但是由于缺乏特异性T细胞的标记物,未能成功引入Tregs;直到20世纪90年代,Sakaguehi等[2]首次在小鼠外周血CD4+T细胞中发现一群高表达IL-2受体a链(CD25)的细胞群体,这群细胞具有免疫调节和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命名为CD4+CD25+调节性T细胞。研究发现CD25除高表达于CD4+T细胞之外,在CD8+T细胞中也有表达,由此说明CD25分子在Tregs中的表达并不是特异性的,因此,将CD25作为Tregs的标志物并不完全准确。直到21世纪初,Sakaguchi等[5]学者发现在CD4+CD25+T细胞中转录因子叉头盒蛋白3(forkhead-box Protein 3,Foxp3)分子呈特异表达,该分子是Tregs的关键转录因子,与Tregs的发育和发挥免疫抑制与调节功能密切相关[6]。
2 Tregs的分类及亚群
体内Tregs按其来源可分为胸腺源性Tregs(thymic-derived Tregs,tTregs)和外周诱导性Tregs(peripheral Tregs,pTregs)[7]。tTregs可直接从胸腺中发育而来,而pTregs是外周淋巴组织或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中在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存在及炎性细胞因子(如IFN-γ、IL-4、IL-6)缺失的情况下由CD4+CD62L-Foxp3-的T细胞诱导而来[8]。
Tregs可以分为如下几个亚群:源自CD4+T细胞的亚群如调节性T细胞1(Tr1)、辅助性T细胞3(Th3)和CD25+Tregs,以及CD8+T亚群如CD8+Tregs。其中Tr1可分泌大量细胞因子IL-10;Th3可高表达细胞因子TGF-β;CD25+Tregs可表达多种功能分子,如Foxp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CD25、糖皮质激素诱导的TNF受体家族相关蛋白(glucocorticoidinduced TNF receptor family-related protein,GITR)和诱导型共刺激分子(inducible co-stimulator,ICOS)等,这些功能分子可以稳定Tregs的表型并调节免疫系统[6];此外,已有文献报道了CD8+Tregs具有免疫抑制功能,可通过分泌细胞因子IL-10及TGF-β抑制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cells,CTLs)及NK细胞的抗肿瘤活性[9]。综上所述,Tregs不同亚群具有抑制免疫系统的不同机制。
3 Tregs抗肿瘤免疫的机制
Tregs通过促进ATP水解来抑制TME,从而实现抗肿瘤免疫。Tregs可表达两种酶:CD39和CD73,CD39是一种细胞表面酶,是ATP水解和腺苷生成的关键酶;CD73是一种将AMP转化为腺苷的外酶[10]。在TME内,ATP被激活后可增强抗肿瘤免疫细胞的活性,而腺苷可抑制TME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及NK细胞对肿瘤的杀伤功能,从而促进肿瘤免疫逃逸。在癌症患者中,大多数临床数据表明CD73/CD39高表达与预后不良及疾病进展密切相关[11-12]。
Tregs可通过分泌IL-10、IL-35、TGF-β等抑制性细胞因子直接抑制免疫应答。研究表明:在恶性肿瘤晚期,TGF-β通过促进骨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增殖[13]、抑制NK细胞活性[14]以及降低CTLs活化[15]来降低机体抗肿瘤免疫。
此外,Tregs还可以通过FasL/Fas及颗粒酶/穿孔素途径介导CD8+T细胞凋亡,以及通过与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s)间的相互作用来影响DCs的功能,从而抑制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Tregs表面免疫抑制因子CTLA-4和T细胞表面的协同刺激受体CD28竞争性的与CD80/CD86结合产生抑制性信号,导致T细胞活化降低[16]。IL-2是促进T细胞活化与分化的重要细胞因子之一,而Tregs高表达CD25,与DCs分泌的IL-2有更强的亲和力,CD25与IL-2结合会抑制效应T细胞的活化、增殖与分化[17]。
4 肿瘤微环境中靶向Tregs的策略
Tregs利用多种机制参与肿瘤免疫反应,促进肿瘤生长和发展,通过破坏Tregs的功能、降低Tregs的活性、限制Tregs进入肿瘤组织以及靶向肿瘤代谢等免疫治疗的方法,可有效抑制肿瘤的发生与发展。
4.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Tregs表面高表达免疫检查点分子(如PD-1、CTLA-4),靶向这些分子可能是抑制Tregs功能较理想的方法。研究表明,在荷瘤小鼠CT26结肠癌模型中,小鼠腹腔注射抗CTLA-4抗体后可降低小鼠肿瘤进展、提高生存期,但与抗PD-1抗体联合用药时抗肿瘤作用并未起到协同效果[18];而在三阴性乳腺癌细胞模型中联合上述用药后抗肿瘤作用显著增强[18];此外,在某些晚期癌症患者中,抗PD-1抗体使用后,患者血清中会高表达犬尿氨酸(kynurenine,Kyn),导致患者预后不良[19]。由此可见联合用药可能是治疗某些侵袭性肿瘤耐药性的新途径。
4.2 清除Tregs
消除Tregs的免疫抑制作用是肿瘤免疫治疗的关键[20],CD25在Tregs中高表达,是实现Tregs耗竭的一个潜在靶点。抗CD25免疫毒素(denileukin diftitox,DAB-IL-2,Ontak)最早用于治疗T细胞淋巴瘤,但因会造成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而在临床应用受限[21]。Cheung等[22]研究出第二代靶向CD25的白喉融合毒素s-DAB-IL-2(V6A)能够降低B16黑色素瘤荷瘤小鼠瘤内Tregs数量,抑制肿瘤生长同时减少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发生。虽然该药物在动物试验中取得了良好疗效,但临床应用极其少见,其安全性尚需进一步研究。
4.3 抑制Tregs衍生的细胞因子
Tregs可通过分泌抑制性细胞因子如IL-10、TGF-β、IL-35等抑制免疫应答。研究表明,在卵巢癌患者中IL-10表达明显上调[23]。此外,在前列腺癌荷瘤小鼠模型中,TME内IL-35+Tregs及MDSCs比例显著增加且促进肿瘤组织血管生成,当IL-35被中和抗体清除后,小鼠肿瘤生长受到抑制且TME中CD4+T及CD8+T细胞数量增加,抗肿瘤作用增强[24]。这为治疗前列腺癌提供了新靶点。
4.4 IDO/TDO抑制剂
在TME中,IFN-γ一方面作用于肿瘤细胞使之发生凋亡,另一方面可促进肿瘤细胞分泌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及色氨酸2,3-双加氧酶(tryptophan 2,3-dioxygenase,TDO)[25],TME中存在大量色氨酸(tryptophan,Trp),Trp在IDO/TDO的作用下分解成Kyn,Kyn作为多环芳香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的配体可激活AhR,AhR既可诱导Tregs的增殖[26],又能促进CD8+T细胞中PD-1的表达,进而影响CD8+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促进肿瘤免疫逃逸[27]。研究表明,抑制肿瘤细胞中IDO的表达可抑制小鼠结肠癌的进展[26],此外将IDO1/2抑制剂与抗PD-1抗体联合使用时抗肿瘤效应增强[28]。这些结果为未来临床试验中使用AhR抑制剂、IDO1/2抑制剂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癌症提供了理论依据。
4.5 抑制Tregs进入TME
TME中的癌细胞通过产生各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趋化因子28及其受体10(CCL28/CCR10)、趋化因子1及其受体8(CCL1/CCR8)和趋化因子17及其受体4(CCL17/CCR4)等来增强Tregs对TME的浸润,因此,阻断趋化因子或趋化因子受体可阻止Tregs进入肿瘤组织,是降低肿瘤生长的机制之一[29-31]。
胰腺癌是一种高度恶性的腺癌,临床常将吉西他滨、氟尿嘧啶和叶酸作为辅助疗法来改善患者术后总生存期[32-33],但效果不佳且会产生副作用和耐药性。研究发现,胰腺癌患者中CCL28和CCR10表达均升高[34],Yan等[35]发现CCL28的表达与胰腺癌患者低生存率相关。在胰腺癌荷瘤小鼠模型中,敲除CCL28后可阻止CCR10与CCL28的结合,小鼠肿瘤生长受到抑制、Tregs数量降低同时MDSCs数量降低。表明CCL28是一个潜在治疗胰腺癌的新靶点。
在癌症患者中,肿瘤浸润性Tregs表达的CCR4比外周Tregs更高,且由肿瘤细胞释放的CCL17招募CCR4+Tregs到肿瘤部位抑制抗肿瘤特异性免疫,促进肿瘤发展,导致预后不良[36]。研究表明,抗CCR4单克隆抗体(莫格利珠单抗)用于治疗难治复发性成人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ATLL)[37]及皮肤T细胞淋巴瘤(CTCLs)[38],多数患者完全缓解。此外在乳腺癌及B16黑色素瘤荷瘤小鼠模型中,减少CCR4的表达后,小鼠肿瘤生长受到抑制、肿瘤浸润性Tregs数量降低[36]。表明CCR4是一个潜在治疗乳腺癌及黑色素瘤的新靶点。
此外,CCR8在肿瘤浸润的Tregs中高表达,其趋化因子CCL1在炎症发生部位表达上调,会招募CCR8+Foxp3+Tregs浸润到肿瘤组织中抑制抗肿瘤免疫功能,使机体对肿瘤产生耐受[39-40];而且在TME中,当CCR8上调后可诱导Tregs中Foxp3、IL-10、CD39等抑制性分子的表达增加,从而增强肿瘤浸润性Tregs的免疫抑制活性[39]。通过对结肠癌、肺癌以及黑色素瘤患者实体瘤及血液分析发现,CCR8在肿瘤组织中高表达、血液中低表达,表明CCR8是一个潜在的高选择性治疗肿瘤的新靶点[41]。
4.6 靶向肿瘤代谢
氧化应激引起的肿瘤组织中Tregs凋亡是一种新的肿瘤免疫逃逸机制,在TME中,凋亡的Tregs释放ATP,通过CD39、CD73代谢为腺苷,并通过与腺苷和腺苷A2A受体的相互作用来抑制抗肿瘤免疫,增强机体对免疫抑制剂的耐药性[11,42]。研究表明,在荷瘤小鼠模型中使用A2A受体或CD73抑制剂后,小鼠肿瘤生长受到抑制且逆转抗PD-L1抗体的耐药性[42]。因此靶向肿瘤代谢可能是肿瘤治疗的潜在策略。
5 Tregs作为肿瘤治疗靶点的不足
目前已证明多种针对Tregs的免疫治疗方法在促进肿瘤杀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有些方法有时会导致机体释放自身抗原和肿瘤相关抗原引起局部产生炎症,从而刺激和激活肿瘤浸润性Tregs,进一步导致抗肿瘤反应受到抑制[43]。有研究显示:某些肿瘤抗原可特异性诱导产生Tregs,癌症患者接种针对肿瘤特异性抗原的疫苗可以有效阻断肿瘤诱导性Tregs的产生,抑制癌症进展的同时也可导致机体感染[44]。另外,卡介苗(BCG)治疗过程中高表达PD-L1的Tregs增多,会显著降低其治疗效果[45]。Tregs是机体维持免疫稳态的重要免疫抑制细胞,盲目清除并不可取,易造成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些结果揭示了Tregs作为治疗肿瘤靶点的不足之处。
6 小结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Tregs的起源、分类、抗肿瘤机制以及TME中靶向Tregs的策略,同时也提出了目前Tregs在临床抗肿瘤应用中的不足之处。清除肿瘤浸润性Tregs是目前治疗肿瘤的重要方法,针对Tregs新靶点的研究成为当前治疗肿瘤的突破点和热点,寻找减少或阻断肿瘤浸润性Tregs和抑制其活性的免疫疗法与其他治疗方法联合应用,是目前临床上提高各种癌症治疗效率和降低耐药率的有效手段。
- 癌变·畸变·突变的其它文章
- 《癌变·畸变·突变》2022年第34卷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