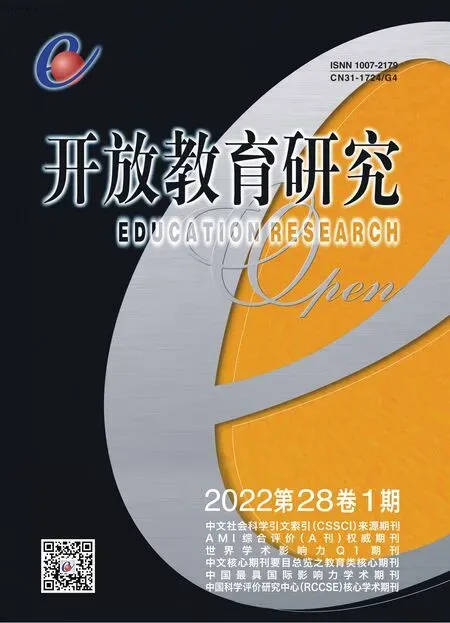“休眠”的主体:在线教学的主体性困境与反思
——基于县城A中学的调查
方程煜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2020年春季学期全国大中小学校以在线方式开展网上教学活动。虽然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提升显著,但仍然存在地域和机构内部的特殊性,即使在统一的政策建议下,各学校线上教学安排与实践仍面临地方性问题和个体化差异。此次在线教育实践,是对县域初中教育系统的教师、学生以及家庭教育的直接挑战。就疫情期间的反馈看,学生缺乏学习自主性问题常受诟病,而家长难以应对相应的家庭矛盾,部分教师面对线上教学环境的不适甚至焦虑,也反映出教师在线教学自主性的困境。因此,作为主体性的核心意涵之一(刘志军等,2005),自主性成为教育主体性考察的重要切口。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虚拟民族志方法考察学校线上教育活动。选择场域是某县城A中学,调查对象是该中学的各科教师、初一年级的学生和家长,使用民族志方法收集田野调查资料,具体方法包括对教师、学生、家长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见表一),收集的实物资料包括老师的教学日志、学生周记、与学生闲谈整理而成的文本材料等。

表一 受访者信息
在此次线上教学开展前,即2019年秋季学期始,研究者已经参与观察该中学的课堂教学实践,与初一年级部分班级教师和学校管理层进行了初步沟通和半结构化访谈,也开放式访谈了部分学生的学校和家庭生活。这些前期调研因为疫情受到了影响,而疫情阶段的在线教育考察也为对比和反思常态化课堂教育教学提供了契机。A中学①2020年4月26日恢复春季学期线下教学,研究者在遵守疫情防控规范的前提下,参与学校的线下教育教学工作,期间主要跟踪调研前期访谈的初一M班,面对面深度访谈老师,追问线上教学阶段的教学适应以及与线下教学的衔接状况,同时也跟随M班的老师对部分同学进行了家访,还加入班级QQ群和教师QQ群,间接观察和参与教师和学生的讨论,直观了解一线教师线上教育的态度、观点、行动及其转变。
二、文献综述
(一)主体性的内涵与外延
已有学校教育的主体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参与主体的学生和教师。本研究讨论的学习主体性,更接近学习自主性研究,主要包括两条进路:一是针对学生自主性内涵及提升策略的讨论。如有研究(熊川武等,2013)结合学生自主性的特征和特殊属性,指出学生的自主性有很强的可塑性;也有研究(刘天,2016)认为不能因为给予学生自主性而忽略教师的自主性;还有研究者(顾建军,2000)认为应兼顾教师与学生两个主体的能动性,以教育“双主体性说”强调两者的“主体性协同”,或是从过程哲学的视角出发,关注师生合作的过程性和共生关系(魏善春,2019)。另有研究(叶小耀,2014)建议分学科建立主体性课堂,或就具体科目②讨论提升学生学习自主性的策略。张丽敏(2020)指出,学生面对教师背后的制度化力量,主体性地位会受到教师权威的压制,导致师生关系异化,因而学校教育改革,应着力强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并适当限制传统教师权威。还有研究突破学校教育范围,将学习的自主性置于更基础和宽泛的成人学习中加以思考。大卫·利特尔等(2009)将自主学习定义为具有独立性的人能够作出批判性反思、敢于决策和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
二是对学生主体性的测量。研究的差异集中在不同量表。心理学研究者(陈丽君等,2001)测量了西南、华南、华中、华北四个地区的4320名中学生的主体性,指出学生的主体性存在着随年级升高而下降的趋势,对学习的兴趣较直接地影响他们学习的主体性。此后的研究可能使用的测度指标不同③,但总体维持了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学习自主性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田澜等,2011)。上述两条路径对学生和老师的主体性进行了必要探讨,但线上教育更凸显出学习主体性的重要性。
(二)线上教育的主体性考察
线上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研究在线教学实施的现状和特征。有研究者将“停课不停学”期间在线教学的典型案例归纳为“网络在线课程、网络直播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电视空中课堂”(焦建利等,2020)。其中,网络资源所提供的选择性,对学习者的自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还有研究将这一时期的在线教育视为正在发展中的“全球最大的信息化教学社会实验和一次开放教育资源运动”(黄荣怀等,2020)。此类研究意在通过检视在线教学实践,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指引。二是分析和反思在线教育各参与主体面临问题的成因。有研究讨论了高校英语学习者的技术接受和在线自我调控学习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技术支持的语言学习能够提升学习者的自我调控能力,且更有可能帮助学习者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郑春萍等,2020)。有研究者指出影响在线教育实施效果的多重影响因素,如基础设施、课堂实践和个人使用的数字鸿沟,以及家长扮演的角色与困境等(罗梦雨等,2020)。李凌艳等(2020)指出学生的自主性对居家学习至关重要。有研究通过斯蒂芬森的Q方法,依据学习者的主体性分析在线学习者的动机(Lee et al.,2020)。另有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澳大利亚五所大学的教师指出,理解教师教育者如何通过教学信念和方法构建学习者和教师主体性,对未来在线高等教育至关重要(Saltmarsh et al.,2010)。三是提出在线教育的应对策略。有研究者基于霍姆伯格的远程教育思想,指出需要在学习支持和服务、教育主体交互两大方面提升教学系统的应对能力(唐燕儿等,2020)。上述研究能够帮助教育参与者形成在线教育的直观感知,但因为传统课堂教育忽视对主体性的培养,因此在在线学习环境中,教师、学生、家长等都会面临深层次的、系统性的主体不适应。本研究通过考察县城A中学的线上教学活动,讨论其中的主体性问题的生成机制。
三、线上教学主体性困境的现实表征
(一)教师个体的冲突与调适
1.教育技术个体探索的不适
对于县域初中而言,推进线上教育本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强制性政策,但政策本身也为教师个体实践留有探索空间。不同教师个体的认识、理解、行动成为关注的重点,因为它关涉传统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的衔接,直接关系到在线教学目标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转化程度。
A中学的线上教学更多地依据上级政策要求开展。教师需要不断摸索方法和挖掘工具,满足班级管理的新需要。“从听说人传人后,(教师)群里每天信息就炸了,自己也关注疫情变化,(确诊)人数上升很快,加上学校一直发防控要求,整个人的精神也比较焦虑。”(L-20200225)A中学多数班级都建立了QQ群,但使用率不高,疫情让班级QQ群重新“活”了起来。王杉老师对疫情阶段的工作每天都有详细记录:“寒假期间,我给班上的孩子布置了诵读作业,要求家长把作业发到群里,后来改在线上学习,增加了上传学生日常锻炼图片的项目。”QQ群组成为了家校沟通的重要平台。
不过,疫情倒逼技术赋能在线教育,对不同年龄层次的教师提出了教学和管理的挑战。七年级数学老师吴白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他认为:“老师年龄不一,接受的东西也不一,有的老师习惯课堂教学的方式,接受新东西不太适应,就很抵触。”(WB-20200411)。笔者也观察到,有些教师会积极地分享社交软件针对疫情开发的网课功能⑤使用方法。例如,有老师发现新上线的社交软件“老师助手”比较好用,在家长群中建议建立线上班级群,方便作业收发、批改和通知等,但未得到其他教师响应。不同科目的教师很难线上实现有效的联动和配合。班级教学空间突然缺位后,不同科目的教师更专注于摸索对于自身更方便和适应的教学方式。同时,教务管理部门对线上教学没有具体规定,教育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班级教学和管理的松散,从另一个侧面为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可能。这意味着,线上教学对教师个体的主动性提出了要求,但年龄并不足以解释教师对应用技术产生的抵触情绪。
2.线上教学开展的松散与曲折
“停课不停学”铺开后,初一和初二年级学生利用地级市智慧教育应用平台开展课程学习,但这一线上教育平台面对大规模的学生和教师流量时,几度陷入崩溃。L老师用“打仗”形容使用平台初期的情形:“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也不认真看群里的操作手册,系统本身也有问题。”(L-20200413)。3月2日,省空中课堂开放,教育资源平台进入问题基本解决。部分老师开始采取其他方式安排教学,同时也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身的学习资料。尚樱老师教授初一和初三年级的政治课程,最初采用QQ群直播或钉钉软件线上授课,她觉得“有点慌,有点焦虑……总觉得自己不自在”(SY-20200410)。后来她找到一些质量不错的名师课程,便督促学生按照网上发布的课程安排上课。此外,尚老师也主动在网络上寻找优质的教学资源,观察其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教培机构的课程颇有哗众取宠之嫌,老师的语言、妆容、装束啊,特别更注重趣味性,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因为从教师的角度看,上课时这些东西太多,会干扰和分散孩子的注意力。”(SY-20200410)谈及线上教学,尚老师注意到这些网上课程更关注课程内容本身,可能无法满足应试需要,对此,她将课程重点笔记和知识点做成课件发到班级群供学生下载学习。初三毕业班有升学压力,且没有网络课程,需要老师自己录制课程,“虽然一节课45分钟,但是你不能录45分钟吧,中间有时可能会暂停,学生还要记笔记或者什么的,我大概录20-25分钟”(SY-20200410)。一段时间后,尚老师从最初的不适转变为适应,也从居家线上学习与自身工作方式的“转型”中找到了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心态。 对于线上教学而言,这种转变是教学资源、教学工具、教学方式与教师心态之间的冲突、妥协、调适和对接的过程,它不是单方面的教育资源供给所能实现的变化,而是教师根据现实情境,在具体教学中作出的行动选择。
3.线上教学的学情隐匿与失控
教师们最担忧的问题是线上学习隐匿了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王继新等,2020)。A中学线上教学采用“双师制”,网上录课教师统一授课,本校教师进行网上辅导,做好线上答疑、作业批改、反馈、辅导等工作。但线上课程实施初期,学生还没有纸质版教材和辅导作业,老师们为了让学生能够及时巩固教学内容,并为疫情后的复学做准备,根据课程进度在群内布置作业。学生不需要抄写题目,只需要将作答内容发送到家长群中。但事实上,课程作业完成情况并不乐观。在线上学习期间,笔者调查班级的45名同学语文作业的提交状况见图1。

图1 疫情期间A中学七年级某班语文作业完成情况
从上图可见,4名同学完成作业0-10次之间,有位同学没有交过作业。完成作业11-20次之间的2名,21-30次之间的4名,31-40次之间的2名,41-50次之间的6名。剩下27名同学完成作业51-60次,占60%。这意味着,40%的学生不能随着课程进行巩固练习。班主任王杉表示,相比于线下授课,这一作业完成情况非常不乐观。“我每周日都会在群里总结一周的作业情况,让家长知晓孩子的作业完成情况。有些孩子作业不完成,我单独打电话给家长,但没有效果,作业要么做得马马虎虎,要么不做。”(WS-20200323)但对学生来说,他们不能像课堂上那样直观地感受到老师评价中所包含的情感和意味。对于特别依赖教师评价的学生来说,课堂表扬所包含的在整个班级层面的“人际情绪”(张泽民等,2020)失去了效果,尚老师曾点明师生互动缺失的潜在问题:“平常上课老师会引导学生提问,说说不同的意见,但是在线上课就很难实行。像语文课,有些东西是用情感去感染(他人),在网课情况下是没有的。”(SY-20200411)另外,老师们使用批评也非常谨慎。出于顾及家长和孩子的尊严,教师在很大程度上会“牺牲”班级管理的主动权。吴白老师检查作业时发现,有同学抄袭作业,在群内指出了这一问题:“每天的作业请同学们务必自己独立完成,老师才能准确地判断你的学习状况,才能更好地辅导你!”(WB-20200325)这其中,不仅是学生独立自主完成作业反映出的学情能够为课堂教师提供教学指导,更重要的是,学生需要对自身的学习状况和态度有清晰的认知和把握。而抄袭所带来的道德影响,这可能会对学生人格教育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家庭教育的“失灵”
1.亲子关系的冲突
居家学习打破了原先家校之间协调的教育“节奏”,要求家长抽出更多时间参与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家长的计划,并可能由此产生不满情绪。这种不满会成为亲子矛盾的“导火索”,直接影响家长对孩子的评价,很难对孩子学习起到有效的监督。吴白老师就自己与上小学六年级的孩子相处的经历指出,缺乏距离的亲子关系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时间长了就会缺乏耐心,看到孩子做得不好就会批评,鼓励太少,(以)毫无顾忌的情绪或者语言打击伤害孩子。”(WB-20200417)
在居家学习中,如果家长不能以身作则,也难以对子女作出行为规范的要求。紫怡在家学习期间常因小事与母亲口角:“我妈脾气很大,从来不听我说完就打断我,她让我不要玩手机,自己一回来就开始玩手机,看抖音。”(ZY-20200419)。吴白老师对此深有感触:“我觉得孩子在家里的习惯和大人的习惯是相互映射的,孩子身上的习惯,大多都是跟大人学的。”(WB-20200411)就县域初中而言,教师强调家庭在子女教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而在居家学习阶段,学校教育都让位给家庭后,家长在其中的突出位置加重了教师对学生家庭的关切。
此外,新技术使传统亲子关系发生倒置,加剧了亲子教育的紧张关系。对于21世纪后出生的孩子来说,他们被称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对新技术具有很强的接受能力。相对而言,他们的父母在技术上可能处在一种“技术无知”的状态。从访谈可知,很多家长对自己与孩子之间的技术鸿沟存在预设,认为孩子在技术上的灵活与适应是自己不能及的,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转化为家庭教育的不和谐,而是强化了家长试图在亲子关系中寻找作为监护者的优越感,这让家庭教育因为技术知识的差别而产生的矛盾变得更频繁,也削弱代际沟通的意愿。上述矛盾更多地表现为家庭教养问题,而非隐藏在其背后的技术鸿沟。技术的初衷是开放地提供给每个人平等地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进入人类社会后,却成为了分割人群的工具。
2.学生自主学习习惯与能力的缺失
学生缺少自主学习能力和习惯,而家庭教养只以刻板和单一的方式回应,居家学习让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缺乏问题更突显。教师们尽管没法像课堂教学那样观察和评估学生的课堂表现,无法就学生违反学习要求和纪律进行指正,但能够基于经验、学生作业和家长反馈了解学生居家学习可能存在的问题。教师的监督机制退为家庭管理的策略,即以教师对学生学习表现和品格的把握,对家庭教育提供可能的指导,但这些指导相对于家庭内部既有的教养而言仍显得脆弱。学生阿土,初一上半学期就不怎么完成作业,在家学习时,各科作业都没有提交过。班主任嘱咐阿土母亲要监督孩子的学习,但阿土母亲强调自身受教育水平有限,对班主任“叫苦不迭”:“老师啊,我真是管不住他,他拿了手机,就把房门反锁,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TM-20200315)“诉苦”成为无力应对子女教育的家长与教师沟通的惯性表达。
电子产品使用的分歧暴露了亲子关系中的“隐疾”,很多家长采用强制方式加剧了家庭成员的紧张关系。鲍腾很喜欢玩游戏“王者荣耀”,他母亲陈梅看在眼里,但线上学习阶段,提交作业和查阅资料需要用手机,所以只在自己在场时给鲍腾使用,并不定时查探。“这孩子很不自觉,他说要上网课,查作业,查百度,我中间去他房间检查,看他在打游戏,火气上来就把手机摔了。”(CM-20200316)鲍腾对母亲的暴躁也颇有意见,母子间常言语争吵,有时也采用“武力”,让鲍腾感到很委屈:“她脾气很大,每次都不听我把话说完就在那儿教训,从来都不听我说。”(BT-20200318)。有研究者援引中国青少年网络使用状况的调查结果指出,孩子们渴望得到使用网络的帮助和指导⑥,但很多时候家长对孩子文明上网缺乏指导,更多地诉诸“一刀切”的强力措施,这对于亲子关系而言,无疑是加深了双方的隔阂。
在线上学习阶段,班级学习的物理空间让位于学生居家学习,家长需要将学校规制在家庭情境中做出转化。这要求家长也具有教师那样的可信任的道德权威。但这种转化挑战了家庭生活的秩序,而重建秩序的过程又缺乏必要的方法。家长需要考量自身的行为避免失去对子女教育的正当性,这也意味着他们自身的放松空间和方式受到限制,而这种限制可能让家长自身容易产生被剥夺感。
总之,家长想要以长辈的姿态对孩子的技术优越表达反对,但他们也会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至放弃“抗争”,以更暴力的方式切断孩子与技术或信息世界的关联。两代人之间的技术鸿沟扰动了传统意义上的亲子关系,而如果父母刻意地回避和对抗这种技术差距,两者之间的冲突会影响沟通和理解。这些冲突的后果便容易让家庭教育陷入彼此“看不见”和各自“改不了”的沉默当中。
四、“失踪”的主体:主体隐匿的原因
(一)教师自主学习和技术运用的缺陷
在这场线上教学中,教师们的教学活动和心理应对存在个体差异,暴露出教师终身学习能力和习惯的缺失。就A中学而言,很多教师对教学方式的变化感到不适应,甚至产生对抗教育技术应用的心理,即一些老师不乐意利用新技术手段进行班级管理和教学,表现出对传统线下课堂教育更强的依赖性。但这些不适应也反映出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话语与教学实践之间的割裂。因为老师对教育技术使用的逆反心理可能与部分教师缺乏技术应用经验密切相关,而这种技术“缺席”让他们在观念层面上,始终对技术运用抱怀疑态度,且视学生使用电子产品为“洪水猛兽”。
这次疫情对很多教师形成了倒逼压力,迫使他们对技术保持开放包容和积极尝试的态度,更好地将教育信息技术运用到教学实践中。
(二)从“经师”到“人师”角色调整的迟滞
就县城A中学而言,部分教师对线上教育的态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技术“僭越”课堂给他们带来的暂时不适,但深层次来看,这种不适突显出知识性内容的讲授更容易被替代或通过技术手段得到优化呈现的现实。对于多数老师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教育技术的介入往往使教学内容得到更具吸引力的展现,老师们通过更加生动和形象的形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没有从根本上使教师更新教育观念。疫情初期,教育政策话语中的线上教学模式表现出给予教师最大程度的技术使用自由,但事实上,教师们对技术的深度介入往往很难有亲近感,因为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人与人相处的亲和性。当知识性内容被网络课程取代后,学校生活被简化为教师通知家长、家长督促学生的信息传达。教师权威失去了“展演”的空间,从班级管理的权威蜕变为信息员,身份的挑战加深了他们的不适。
此外,教育部门部署的线上教学与线下辅导结合的“双师制”模式,并非确切意义上的教学方式变革,两位教师之间的角色关系没有做明确规定。这种看似全面而周到的安排,暗含了对教师角色认识的二分化倾向,即作为知识性内容的传递者与作为品格德行的培养者。但事实上,对于初中教学来说,育人工作往往围绕着基础知识教学展开和延伸,二者彼此融合,互相推进。做符合专业标准的“经师”是教师的职分,而胜任“人师”则需要更强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然而,“经师”的角色内容因为绩效考评制度的约束变得更突出,当“经师”的角色从传统教师角色中被剥离时,教师作为“人师”的意义获得了被重新审视的机会。
缺乏常规班级集体生活的环境,学生学习品质的形塑和健康人格的养成,需要教师更强的班级管理能力。因而,在“双师制”中,教师需要面对学生居家学习条件的复杂性,也要对家庭教育的差异可能加剧学生分化的后果有所预判。疫情再次将信息化推到教育的前台。教师有必要借此机会重新确立“教育”育人要旨这一时代要求。正如有研究者所言,这次疫情让线上教学资源得到开发,此所谓“经师易得”,但学生成人成才更重要的是“人师”难求⑦。
(三)学校管控模式“移植”家庭中的失败
疫情之下,教育部门力主开展“双师制”线上教学。“双师制”在基础教育中主要还是一种词语借用,而非一种触及教学方式改革的创新策略。在职业教育领域,“双师制”指的是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学习的特点而实施的职业教育模式(马桂芳等,2012),该模式的核心目标在于让技术实践能力与理论知识水平融汇在教师和学生培养过程中。
A中学的“双师制”指线上授课与线下教学之间的配合与辅助模式(见图2),并未实现两者的融通与结合。线上教师是单向的资源提供者。与学生没有互动,线上教学内容与线下教学安排之间的衔接更多地依靠对课堂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课堂教师是多主体之间的协调者,需要更高程度的自身能动性才能实现对学情的把握。学校要求课堂教师同步学习网络课程内容,预判学情。但学生运用网络学习软件存在偏差,学习效果也有差异,通过作业反映学情未必可靠,这意味着学生线上学习可能存在隐性问题。课堂教师试图扮演学生居家学习的幕后指导者,但纯粹的指导又可能会让课堂教师变为课程任务的传达者和劝说者。对此,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家长对学生的监督成为关键,重拾家庭教育的角色,成为了线上教育发展极为紧要的启示。

图2 A中学疫情期间的“双师制”教学模式
但不少家庭“移植”学校的管控手段监督孩子学习遇到了阻碍。“双师制”仍然是线下教育思维,即通过时间和程序管理尽可能地在家庭教育中“复制”学校管控体系,这事实上回避了学校与家庭的时空装置无法置换的现实。阿利埃斯(2013)指出,在旧制度下,家庭更关心孩子对家庭建设方面的共担责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道德和社会性的联系,但是对于现代家庭而言,父母与子女之间更多的是情感连接,这其中学校扮演了重要角色。桑格利(2012)认为,学校创造了现代社会对儿童的特殊认知,即孩子是天真和脆弱的,成人有责任保护他们,同时学校在地理空间上隔开了孩子与家庭,却因此加深了双方的感情。因而,以纪律和规范对学生行为作出界定的学校特征很难直接介入。当学校的管控模式转移到家庭情境时,家长作为父母的角色与他们试图扮演的学校监管者角色产生了冲突,家长教育职能的“空白”难以对孩子的角色做出妥善。这也从反面说明学校对学生全方位的管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自主性,后果可能是学生只有“寄生”于管控之下才能感受到主体的存在,而这种主体具有虚假性,过度依赖外部规则的刺激而更松散和脆弱。
(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习惯的缺失
传统教育中,班级的学习环境不仅是同辈之间相互影响而构成的制度和空间约束,也是学校对学生个体生活进行统一规划和安顿的权力场域。福柯对现代社会的权力与支配体系的核心关注中,将学校视为当代规训与监督的典型场所。譬如,在学校场景或空间中,学生在强制性的序列体系中被锚定在不同的等级中,且在不同空间中的等级位置也在发生变化。福柯(2012)将这种系列空间的组织形式视为基础教育当中,学校对学生实行个体监控和整体上对权力驯服的重要手段,这其中涉及权力对人的直接控制。具体而言,规训通过对人体运作的精细掌控并加以规范化和规则化,将人体训练为符合权力拥有者期待的肉体。人体对这些规范要求的不断操练,能够“让个体和全体的操作都达到最大效益”(谭光鼎等,2008)。在福柯(2012)看来,在肉体层面,规训强制构建了“能力增强”和“支配加剧”之前的限定关系。就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能力训练而言,这意味着学生愈接近于一个规范、理想和优秀的标准,即相应地拥有能够转化为某种经济收益的能力和才干,那么也就越可能服从于权力的规训,同时很可能只有在更强大的权力控制下,才能感受到主体的存在,但这种主体性在生成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消失。
此外,学校密集化的教学管理环境,并没有给学生自主成长“呼吸”的必要空间。就A中学而言,多数教师仍然扮演主导角色,但学生也并非没有主动性的瞬间或者意识,只是在课程安排中,留给学生自主思想、反思和探究的空间较“逼仄”,而课外学习时间又被各种市场教育机构侵占,对学校管控的适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他们在弹性空间稀缺的环境中的实用性策略,因为依循学校规范管理不会让自身遭到惩戒,同时又能够在安全范围内得到学习的导引。在这个意义上,学校管理所提供的安全制度转化为学生自主性“寄居”的稳定结构,学生在其中不需要为结构内容的安排、组织和计划作出调适,而是只需服从于标准化的课程进度、行为规范、任务要求,就能够取得与服从程度相匹配的成绩评价结果。在此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失去了自我暴露的动力而进入自我保护式的“休眠”状态,因为突破规制的行动可能打破业已适应的安全环境而让自身无法再拥有稳定结构的庇护。
总之,县域教育如何应对线上教学持续的影响,家庭教育需怎样重构实践亲子关系,学校教育如何回应现代社会知识学习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都是研究者需要关注和反思的。
[注释]
①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出现的地名和人名均已匿名化处理。
② 中学阶段的科目,如语文、英语、数学、历史等,都有针对性的研究从学科特点出发,提出发挥和提升学生主体性的教学对策。参见朱婧(2014).主体性教学可以实现吗——对传统初中美术课的反思[J].上海教育科研,(10):61-63+40.
③ 有研究在查阅国内外有关学生自主性测量的相关量表后,结合自身的定义确定了特定的自主性初始问卷。参见熊川武,柴军应,董守生(2017).我国中学生学习自主性研究[J].教育研究,38(5):106-112.
④ 桑新民(2020).疫情中的教育反思与文化觉醒:教育者应该有一种面向未来的远见与胸怀[EB/OL].[2020-08-10].https://mp.weixin.qq.com/s/Utzzbaeyp9F2jlAvZ31vDw.
⑤ 腾讯公司QQ团队在2020年2月20日对电脑和手机端版本进行了更新,新增了“群课堂”“作业红笔批改”“家校群快捷栏”“群接龙”等,方便教师进行线上教学和班级管理的支持功能。
⑥ 可参见《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09-2010)》。一项家长对孩子网络使用态度的调查显示,家长对孩子上网的支持程度均分为4.2分(1至10分,从“完全不支持”到“完全支持”),就此分数而言,支持程度并不高;标准差较大,说明家长之间的态度差别较大。参见金盛华,周宗奎,雷雳,方晓义等(2015).中国青少年网络生活状况调查研究(全国报告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32-233.
⑦ 文东茅(2020).战“疫”之后,更呼唤“人师”[EB/OL].[2020-08-10].https://mp.weixin.qq.com/s/w3_Meblo26KkhyINDhw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