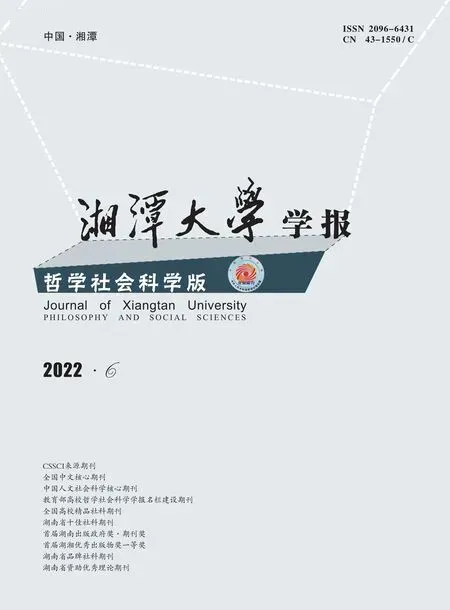1990年以来英国“长18世纪”妇女小说批评趋势与特色*
潘 建,刘亚群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 长沙 410205)
一、引言
英国现代小说兴盛于18世纪,传统小说史常视笛福(D. Defoe)、理查逊(S. Richardson)、菲尔丁(H. Fielding)等作家为小说之父,但实际上,与其并肩作战的还有许多妇女小说家,有些甚至与小说之父们齐名。例如,罗伊(E. Rowe)的《死亡中的友谊》(1728)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比理查逊的《克拉丽莎》(1748)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卖得更好,海伍德(E. Haywood)是言情小说、女性教养小说(bildungsroman)和家庭小说等小说亚类的开拓者。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将小说上溯至贝恩(A.Behn)的《奥鲁诺克》(1688),称其为该国第一部小说。它比《鲁滨逊漂流记》、菲尔丁的《帕米拉》(1740)、《莎米拉》(1741)和《约瑟夫·安德鲁斯》(1742)等小说早了30—50年不等。《帕米拉》之前,《奥鲁诺克》已再版了7次[1]16。有了17世纪的基础,18世纪涌现出众多妇女小说家似乎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从事英国18世纪研究的英美学者常因顾及文学连续性而以“长18世纪”(the long 18th century)断代(1)为了尊重历史事件的“自然”进展,英美学者将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至1815年滑铁卢战争结束之间约130年时间定义为“长18世纪”,也有学者将1662年的王室复辟到1832年的天主教徒解放运动约170年时间划为“长18世纪”时段(https://en. wikipedia.org/wiki/Long_ eighteenth_century.)。,该时期的妇女小说批评主要伴随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来,并历经20世纪初期、中期以及末期至今三次批评热潮。第一、二次批评热潮时,虽然最重要的妇女小说家已经亮相,例如,奥斯汀(J. Austen)、伯尼(F. Burney)、拉德克里夫(A. Radcliffe)、艾奇渥斯(M. Edgeworth)、海伍德、英奇伯德(E. Inchbald)等,但是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比较有限。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批评热潮才真正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长盛时期,几乎所有“长18世纪”妇女小说家都被挖掘出来,个案和主题研究成果上千种。个案研究不仅延续了第一、二次批评热潮中的研究重点,即重要小说家获得最多关注,例如奥斯汀(261)、伯尼 (22部)、拉德克里夫 (13部)、艾奇渥斯 (8部)等,而且,“查漏补缺”也做得非常全面:有些小说家虽然已经在前两次批评热潮中“亮相”,但重视程度不够,此次或保持平稳发展,或得以快速升温;以前未能“亮相”的,此次也都被发掘出来;那些未成为独立个案的小说家也频繁出现在作家群或专题论述中①,呈现出一个庞大的妇女小说家群像。同时,专题研究也迅速发展,由最初的单一主题探讨发展到了主题包罗万象,而且形成了许多特色鲜明的主题系列研究,最突出的系列有:妇女小说写作传统、哥特小说、革命小说以及言情小说等。(2)虽然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Wollstonecraft) 写过两部小说——《玛丽:一部小说》(1788)和《玛丽:女人罪》(1798),但后世研究都集中在其政论和教育著述上,很少针对其小说。因此,本文未将其纳入妇女小说批评述评中。
相应的,中国学术界关于该时期的批评始于20世纪80年代,散见于文学史和各类学术刊物。“中国知网”之“核心期刊”检索结果显示,关于奥斯汀的论文有326篇(至本文写作日期),可见其受欢迎程度,接下来就只有拉德克里夫(3篇)了。国家图书馆检索结果显示,关于奥斯汀的论著有7部,未找到其他小说家专论。与英美本土相比,国内研究远未铺开。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视角,以英美学术界1990年以来关于英国“长18世纪”妇女小说研究论著为对象,系统解读该领域的学术成就,探寻其发展趋势与特色,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二、应运而生的妇女小说史论
早在20世纪初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时期,英美学者即已开始整体考察“长18世纪”妇女小说家,不过以推介为主。再次出现妇女小说史论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以斯宾塞(J. Spencer, 1986)、托德(J. Todd, 1989)、斐济斯(E. Figes, 1989)等学者为代表的史论直接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批评基础。真正意义上的批评热潮始于妇女运动第三次浪潮的20世纪90年代。整体上,这些史论可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种类型,不过,由于通史时间跨度长,18世纪妇女小说批评的分量很轻,在此略过。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以18世纪为主的断代史,已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有威廉姆森(M. Williamson)的《提高声音:英国女作家,1650—1750》(1990)、特纳(C. Turner)的《以笔为生:18世纪女作家》(1992)、琼斯(V. Jones)的《英国妇女与文学,1700—1800》(2000)、斯特伍斯(S. Staves)的《英国妇女写作史,1660—1789》(2006)、巴拉斯特(R. Ballaster)的《英国妇女写作史,1690—1750》(2010)和拉布(J. Labbe)的《英国妇女写作史,1750—1830》(2010)等。它们都是以史为纲,从写作传统和特色、写作背景与条件、小说文本本身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于写作传统与发展特色,威廉姆森、巴拉斯特和拉布三位学者的观点如出一辙,都认为,英国妇女小说应该要上溯至贝恩。威廉姆森和巴拉斯特指出,17世纪末形成了分别以菲利普斯(K. Philips)和贝恩为榜样的两股写作力量:菲利普斯追随者以诗歌创作为主,偶有戏剧和小说等,后来成为道德标杆;贝恩追随者以小说创作为主,兼有诗歌和喜剧,却被视为放荡典型,17至18世纪就是一部“连续的女性主义史”[2]5。至18世纪80年代,英国妇女写作已发展成稳定事业。拉布视1750—1830年为英国妇女写作第一次全面开花阶段,不仅影响了小说性质,还改变了“虚构”与“真实”的表述方式,“将小说提高到了一个新层面[3]16。特纳和琼斯归纳了妇女可能“以笔为生”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成本很低,只需纸笔,而且当红女作家的稿费最高可与菲尔丁等男作家媲美,从5英镑到800英镑不等[4]78-79,这说明她们要以笔为生是可能的;二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妇女识字率的快速上升[5]4,这给妇女写作也带来了契机,成就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斯特伍斯也指出,女作家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各特殊时期的文学氛围进行创作。而且,妇女写作史需要“评价性批评”(evaluative criticism),必须聚焦文本本身而非那些外部条件,因为“文学史中,我们评判的是作品而非作家,不能因为她们受到了父权制的压迫或厌女症的批评而同情她们。”[6]1相反的,我们应该将该时期所有女作家纳入视野,赋予其文学地位和美学价值,对其史学意义做出鲜明评判。
实际上,除了上述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以外,还有一些小说亚类史论,突出表现在女性哥特小说史论,即克莱瑞(E. Clery)的《从里夫到雪莱的女性哥特》(1999)、海兰德(D. Heiland)的《哥特与性别导论》(2004)、戴维逊(C. Davison)的《哥特史:1764—1824年间的哥特文学》(2009)以及华莱士(D. Wallace)的《女性哥特史:性别、历史与哥特》(2013)等。由于下面有哥特小说专题批评论述,为方便起见,并入下面的专题批评述评一起讨论。
至此,虽然尚未有英国“长18世纪”妇女小说专史面世,但涵括各文类的写作史研究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系列,可以反映出英美学者为建构妇女小说史所做出的努力。
三、独树一帜的妇女哥特小说专论
哥特小说是英国“长18世纪”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瓦尔普(H.Walpole) 1765年出版了第一部英国哥特小说《奥特兰托堡》,至18世纪90年代形成高潮,特别是以拉德克里夫为代表的妇女哥特小说家,更是大出风头,形成了鲜明的妇女哥特小说传统,影响延续至今。莫尔斯(E. Moers)的《文学妇女》将妇女哥特小说定义为“女性哥特”(female Gothic):“自18世纪产生哥特一词以来,我们就将妇女以文学形式创作的该类作品称为女性哥特。”[7]90旨在区分男女作家创作的哥特小说,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追捧,“女性哥特”小说批评因此而受到青睐。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趁势而为,又产生了许多新成果。整体上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上文已经列出的克莱瑞、海兰德、戴维逊、华莱士等学者的史论,第二组是侧重哥特主题的研究,例如,哥特女性主义与女性气质、女性哥特小说表述以及妇女与哥特之关系等,以沃尔斯腾霍姆(S. Wolstenholme)的《哥特再探》(1993)、霍维勒(D. Hoeveler)的《哥特女性主义》(1998)、普维斯(M. Purves)的《妇女与哥特》(2014)、霍纳和兹罗斯尼克(A. Horner & S. Zlosnik)的《妇女与哥特爱丁堡指南》(2016)、登特(J. Dent)的《邪恶历史》(2016)、华莱士的《挥之不去的想法:女性哥特隐喻和女性主义理论》等为代表。最后一组是关于拉德克里夫的个案系列研究。
首先是女性哥特小说史论。莫尔斯“女性哥特”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克莱瑞和戴维逊都以该概念为基础展开讨论,只是路径稍有不同,前者重男女哥特小说模式异同之对比研究,称刘易斯(M. Lewis)等男作家重在外部惊悚环境描述,为“恐怖哥特”(horror Gothic),而女作家重在内心恐惧感受,为“恐惧哥特”(terror Gothic)[8]9;后者从重新定义莫尔斯概念出发,将哥特作为批评历史意识的革命模式而嵌入文化、知识和政治语境中[9]51,列出了该亚类最先传递紧张政治气氛的各个方面,称拉德克里夫点燃了一场“元女性主义/中产阶级文化革命”(proto-feminist/middle-class cultural revolution)[9]81。海兰德同样看重女性哥特模式的形成,将其进一步分化,认为不同的女作家继承了不同模式,例如,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母女继承了拉德克里夫模式,即利用哥特小说来呈现社会不公;布朗特姐妹重在“家庭哥特”(domestic Gothic)的诡异气氛使“家”的功能失去作用;而史密斯(C. Smith)则聚焦民族与殖民身份故事等。因此,女性哥特小说都是“基于情感与崇高主体现实的审美来探索父权政治的运作方式”[10]5;华莱士追踪这一模式的发展历程及其原因,认为女作家之所以转向哥特小说创作,是因为她们要利用它重新进入传统历史叙事,从而将历史小说起源上溯至索菲亚·李(S. Lee),称它是远早于斯科特(W. Scott)的“女性谱系”(female genealogy)[11]5。
其次是女性哥特创作主题研究。英国18世纪时期,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形成,各种社会思潮迭起,但另一面,公/私领域的划分却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使其地位得不到保障,这些无不反映在小说创作中,于是更多学者们聚焦于此。霍维勒针对哥特女性主义与女性气质主题,提出了“受害者女性主义”(victim feminism)新概念,即女性哥特在帮助创造资产阶级新秩序时产生了妇女职业受害者的新身份,亦即新模式,旨在颠覆父权制的同时让妇女能够享受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相对舒适[12]10。普维斯以及霍纳和兹罗思尼克等学者主要关注女性哥特文本的表达方式。普维斯研究女作家巧妙利用哥特制造政治立场或批评其文化、探索个性的各个方面,提出,对于许多女作家来说,没有比哥特这一媒介更好的表达方式了[13]1。霍纳和兹罗思尼克二位学者则指出,早期女性哥特文本发展出一种“新女性主义能量”(new feminist energy)的精准表述,要么“模仿西方社会的妇女极化,要么寻求挑战具破坏性的老套故事和局限性的实践活动,有时同一文本中两者兼有。”[14]2哥特使女作家们赢得了一个协调自己作为作者和读者双重身份的特殊手段,建立起了一个发散的多角度文本空间。此外,哥特小说与历史小说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后者影响和构建了自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的哥特小说。
最后也是最具特色的一组是拉德克里夫个案研究。虽然女性哥特模式研究已经涉及拉德克里夫,但其个案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18世纪90年代,以拉德克里夫为代表的女性哥特小说家大出风头,被称为拉德克里夫模式,“哥特小说,尤其是拉德克里夫创作的那种,已经被女性主宰:女性写、女性读、女主人公”[6]114。实际上,拉氏个案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快速发展,出版了不少成果。例如,美国阿诺出版社(Arno Press) 1980年就曾推出过一套名为“哥特研究和学位论文”的系列著作,其中相当部分是关于拉氏哥特小说研究的。1990年以来,拉氏哥特小说研究仍然活跃,这不仅包括两部传记作品——迈尔斯的(R. Miles)的《大巫婆拉德克里夫》(1995)和诺顿的(R. Norton)的《尤多福之谜》(1999),还有五部主题专论:逻各斯(D. Rogers)的《拉德克里夫批评反响》(1994)和《拉德克里夫书目文献》(1996)、戴克(G. Dekker)的《浪漫主义游记小说》(2005)、马克苏德(S. Maqsood)的《拉德克里夫和坡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理想反乌托邦》(2012)以及汤森德和赖特(D. Townshend & A. Wright)的《拉德克里夫、浪漫主义与特哥》(2014)等。关于拉氏传记,共同特点是缺乏直接有效的信息,作者只能利用各种间接渠道,再结合其生活进行解读,观众最终得到的印象就可能不太一样。因此,这两部传记的共同之处在于:一是都强调拉氏生活背景对创作的影响;二是都在尽力寻找和甄别关于传主的真实信息;三是都充分肯定她对哥特文学的贡献。迈尔斯重在拉氏的早期小说和三部重要作品,认为她是创建哥特文类的关键人物,是“18世纪90年代作品被阅读、被引用最多,最畅销的作家”[15]8。诺顿的拉氏传记,内容最全面,详尽记录了拉氏的童年和家庭生活,对传言中的疯癫和隐世直至最终精神崩溃等特殊事件进行了细究,构成了一部文学妇女的“文化史”,将其地位提升至亨利·菲尔丁级别。
关于拉氏主题专论,各位学者考察的内容也不尽相同。逻各斯的两部编著都是拉氏批评汇编,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全面信息。戴克、汤森德和赖特三位学者的研究都指向拉氏哥特和浪漫主义互动过程。戴克分析了拉氏游记中宗教、文学和政治等方面的主题,认为《森林传奇》(1791)是“吸收浪漫主义游记小说话语并对虚构叙事做出贡献的突破性作品”[16]96。汤森德和赖特二位学者提出,拉氏使用地理和历史距离作为民族主义形式,体现的是其政治意识。马克苏德将拉氏与艾伦·坡(E. A. Poe)并置,考察其浪漫主义理想的倒置或反乌托邦书写,认为她表现出了一种反浪漫主义潮流的张力,可怕的黑色超自然世界侵占了预言家诗人崇尚甜美牧歌式的浪漫主义世界,这与浪漫主义者将诗人誉为通过描写自然美而找到生活意义的天才形成了鲜明对照。
英美学术界的研究让我们了解到,英国哥特小说兴起于18世纪中期,并在短短几十年中得到迅速发展,达到高峰,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既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受到学术界的青睐。
四、备受关注的革命小说专论
法国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英国知识分子关于民权社会和国家政治性质的大辩论,激进者拥护或同情革命,并期待革命在英国发生,保守者则恐惧并反对它。包括小说家在内的许多妇女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大辩论,其态度同样分为支持/同情和反对两种,文学创作与出版因此达到空前高度。这一情况终于在1990年以后得到了英美学术界的重视。例如,沃森(N. Watson)的《革命与1790—1825年间的英国小说形式》(1994)、郎-普拉塔(L. Lang-Peralta)的《妇女、革命与1790年代小说》(1999)、克莱西恩和乐克(A. Craciun & K. Lokke)的《反叛之心:英国女作家与法国革命》(2001)、伍德(L. Wood)的《法国大革命后的妇女、保守主义和小说》(2003)、克莱西恩的《英国女作家与法国大革命:世界公民》(2005)、马努(L. Maunu)的《妇女书写民族:民族身份、女性社会和英法联接,1770—1820》(2007)、伍德沃思(M. Woodworth)的《18世纪女作家与绅士解放运动》(2011)以及哈文斯(H. Havens)的《说教小说与英国妇女写作,1790—1820》(2017)等都对此展开讨论。这些研究大多围绕法国大革命引发的主题:大辩论、公/私领域、国际主义、妇女文学与大众文化关系、小说结构重构、角色塑造等。
妇女积极参与政治大辩论和大众文化建设,不可避免地要与大众发生互动,这实际打破了既定的公/私领域界线,赢得了在公共领域发声的机会。因此,上述大多数学者——伍德沃思、郎-普拉塔、克莱西恩和乐克等——都聚焦于此,只是视角不同而已。克莱西恩和乐克两位学者的共同研究是英美学术界首部关于妇女参与革命大论辩的全面考察。针对女作家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反应及其围绕这些问题而参与大辩论的情况,引导读者关注革命和战争引发的跨国联系和价值观,质疑公民和民族话语中的宗教和政治。郎-普拉塔从妇女文学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关系出发,归纳出妇女探讨反映社会性别的七个文化模式:厌女症自由思想(misogynist libertine)、骑士式和堂·吉诃德式(chivalric & quixotic)、传统家长式、时尚家长式、改良家长式以及女性主义模式等,从最少逻辑(least logical)到接近理想化(ideal)[17]ix。换言之,是法国大革命加快了妇女进入公共领域的步伐。哈文斯揭示了妇女小说家利用说教小说(didactic novel)来参与政治论辩的方式,认为她们巧妙地利用该文类的传统结构,支持、弱化、质疑或书写社会认可的礼仪和价值观,这也是妇女得以参与公共政治事务和模糊政治思想边界的少数可接受方式之一。伍德沃思围绕绅士品质的“本性/养成”(nature/nurture)之争,“革命性地修改了‘彬彬有礼’(gentility) ”概念的涵义[18]212,重构了公/私领域。
探讨国际主义或世界大同主义 (cosmopolitanism)主题的学者是克莱西恩和马努等。克莱西恩借助世界大同主义概念总结出妇女介入公共政治的两种形式——“对抗型”(oppositional category) 的“无性征女性”(unsexed female)和自定义型的“女哲学家”[19]5,认为在应对欧洲革命危机时,女作家们形成了明显的反民族主义(anti-nationalism)或女性主义的世界大同主义思想。马努也指出,英国女作家表达了反英法关系背景的社会性别焦虑,设置了想象中的“女性社会”[20]18。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仅是英国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大变革,还有英国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巨变。通过考察那些视革命思想为“毒药”并利用小说形式作为“解药”(antidote)的女作家之相互关系及其与反革命同行的关系,伍德发现,她们在保守的印刷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另一种女性(非女性主义的)话语,意外帮助革新了英国小说形式。最后是沃森的研究,她探索的是浪漫主义时期书信体历史与哥特小说向权威第三人称叙事模式转变的原因,认为它是法国革命引起的焦虑所致,同时也是个人与社会舆论关系更广泛意义的重构。
以上主题专论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法国大革命为英国女作家提供了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的契机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日新月异的言情小说专论
英国“长18世纪”妇女小说的最主要亚类是言情小说。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它被称为“情感小说”(sentimental novel),18世纪中期时叫“感性小说”(novel of sensibility),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又发展出浪漫主义小说。虽然浪漫主义小说与情感/感性小说已经有较大差异,但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为它保留了许多情感/感性小说的因素。本文基于英美学者对情感/感性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重在情感探讨而将其放在一起进行论述。研究也大致分为两组,一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的情感/感性小说研究,一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小说研究。情感/感性小说批评以下列学者为代表:格林(K. Green)的《求爱小说,1740—1820》(1991)、巴拉斯特的《诱惑形式》(1992)、贡达(C. Gonda)的《阅读女儿们的小说,1709—1834》(1996)、哈戈提(G. Haggerty)的《非自然情感》(1998)、班内特(E. Bannet)的《家庭革命》(2000)、维克伯格(E. Wikborg)的《18世纪妇女小说中作为父亲形象的恋人》(2002)、克拉夫特(E. Kraft)的《妇女小说家与欲望伦理,1684—1814》(2008)、鲍尔斯(T. Bowers)的《强暴还是诱惑》(2011)、格莱特利(J. Golightly)的《1790年代英国妇女小说中的家庭、婚姻与激进主义》(2012)、斯塔尔(J. Stahl)的《18世纪妇女怎样利用写作和言说避免性侵》(2014)等。而浪漫主义小说批评主要来自以下学者:菲伊(E. Fay)的《浪漫主义的女性主义导论》(1991)、梅勒(A. Mellor)的《浪漫主义与社会性别》(1992)、海耶夫纳和威尔逊(J. Haefner & C. Wilson)编辑的《重温浪漫主义》(1994)、费尔德曼和克雷(P. Feldman & T. Kelley)的《浪漫女作家》(1995)、华兹华斯(J. Wordsworth)的《辉煌成就》(1997)、贾诺威茨(A. Janowitz)与梅勒著作同名的《浪漫主义与社会性别》(1998)、吉恩(A. Keane)的《女作家与1790年代的英国民族》(2001)、格林菲尔德(S. Greenfield)的《哺育女儿》(2002)、克莱西恩(A. Craciun)的《浪漫主义中的堕落女》(2003)以及卢塞(D. Looser)的《浪漫主义时期的妇女写作剑桥指南》(2015)等。
对于情感/感性小说的批评,始于巴拉斯特和格林等学者的宏观考察,贡达、哈戈提、班内特、维克伯格、克拉夫特、斯塔尔、格莱特利、鲍尔斯等则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主题研究。巴拉斯特和格林首先从给妇女言情小说定性着手,而且二人的研究正好形成了一个时间上的连贯整体。前者对性别与文类、言情小说与女性读者等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妇女言情小说以亚文化形式服务于日趋退化的大众品味[21]2,被冠以“女性形式”(female form)特征的妇女小说在17、18世纪之交得到了女作家的提炼,去掉了不利因素,为后来的女作家树立了榜样。格林挑战理查逊《帕米拉》为英国言情小说开端并为该文类树立最好典范的传统观点,提出,18世纪言情小说“既是女性所写,也是为女性而写”[22]2。妇女言情小说是女性权力的肯定符号,是“妇女的文本解放”[22]18。换言之,妇女小说家在表达中产阶级妇女价值观和存在问题的过程中“女性化了这一文类”[22]13。该观点呈现的是被瓦特(I. Watt)等男作家所忽视的他者经典。
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莫过于夫妻及其与子女的关系,这是家庭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夫妻关系、父女关系、母女关系、非正常情感、欲望伦理、女性角色塑造等成为其他学者的主要主题。班内特、格莱特利、贡达和维克伯格四位学者主要考察夫妻和父女关系主题。前两位学者侧重夫妻关系,班内特将从曼利(D. Manly)到伯尼的妇女小说分为两类:一为女家长(matriarch)式的,她们不挑战现行等级制度,而是认为妇女的理智和美德优于男性,可采取行为策略超越丈夫来掌控家庭;一为平等主义(egalitarian)式的,她们攻击现行社会制度,构建社会和性别关系的创新机制,拉平等级制度。两种类型都寻求提升妇女地位,可谓殊途同归。格莱特利发现,18世纪末的妇女小说家一反早期乌托邦式的理想婚姻——合作、个人自主和平等,发展出婚姻为男性社会责任之概念。就是说,两个理智人的婚姻,应该达成平等共处、分担家庭责任的共识,这才是促使社会改变的理想。后两位学者——贡达和维克伯格——探索的是父女关系。贡达先定义“女儿们的小说”,即指“以女主人公为中心的关于家庭生活、求爱和婚姻的小说”[23]xvi。在分析了哥特恐惧、乱伦色情、孝顺和服从等主题后指出,父亲形象由早期的暴君式发展到后来的“温和权威”式,正好契合了18世纪人们对父亲态度的变化[23]xvi。维克伯格瞄准成为女儿恋人的父亲形象,认为她们试图将父亲形象改造为婚后会承认妻子人格的理想追求者。
另四位学者——哈戈提、克拉夫特、鲍尔斯和斯塔尔——则侧重家庭其他成员之间或与家庭外人员间的情感纠葛。哈戈提和克拉夫特聚焦女性间情感。哈氏考察“非正常情感”(unnatural affection) /“禁忌欲望”(transgressive desire)叙述,发现18世纪妇女言情小说中充斥着各种激烈情感甚至禁忌情感刻画。小说家们蔑视家庭思想的文化规则,描绘了浪漫朋友、“娘娘腔”男伴侣、忠诚姐妹情、畸形女主人公、悲情男主人公、可怜父亲的痴情以及女同性恋等文化禁忌关系,反映出社会性别角色和女性欲望表达的复杂性,完成了一般文学史所不曾允许的事情[24]100。克拉夫特关注各种形式的欲望伦理,提出女性欲望和女作家书写欲望与性概念,认为她们“一直都有发声、有欲望、有主体性……有能力去爱、伤害、愈合、回应和要求”[25]30。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对强暴、诱惑和性关系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这也明显体现在妇女小说中。鲍尔斯和斯塔尔两位学者的研究就是针对诱惑故事(seduction stories)中的女性受害者。前者基于海伍德等早期言情小说开拓者们在成为畅销作家的同时又丑闻缠身备受争议的情况,发现强暴和诱奸概念是根据女性受害者所采取的反抗或默许措施来区分的。“诱惑故事的主要焦点不是性关系本身,而是当时两个最扰人的思想问题,即难以将抵制权威和美德传统措施相结合,尤其是在屈从者的服从和不平等身份者的相关力量和责任方面。”[26]11后者着重探究受害女性保护自己免受男性侵害的策略或措施,认为女性在受到男性的暴力、“侵犯”(aggression)和“霸凌”(abuse)时,她们除了尽量用言语和文字劝服施害者以外,别无他法。故事女主人公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有的死时爱上了施暴者,有的避开父权监控,成功掌控了自己的命运,取得了事业成功。
关于妇女浪漫主小说批评,虽然也围绕情感主线,例如,母职和母女关系等,但也考察浪漫主义女作家的写作条件、写作传统、国家和民族命运、女性角色塑造等主题。据统计,1770—1835年浪漫主义运动期间,英国至少有500位妇女出版过诗歌[27]xvi,可见妇女作家数目之庞大。但在1980年之前,她们几乎都被忽略,即使到了1985年吉尔伯特和古巴(S. Gilbert & S. Gubar)的《诺顿妇女文学选集》,也只收录了20位浪漫主义女作家。众多女作家终于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英美学术界的兴趣。梅勒和菲伊两位学者首先提出“女性浪漫主义”新概念。梅勒认为,有男性和女性两个“浪漫主义”并行,并归纳出后者的四个主要特征:理性爱和夫妻平等、“家庭政治”或在父母双方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充满爱育而非恐惧的家庭崇高和女性美以及在与他者相关和自身和谐的关系中形成的主体性[28]199。菲伊则指出,从批评角度看,存在多个浪漫主义而非一个浪漫主义。她将该词的历史范畴延长至“长浪漫主义世纪”(long romantic century):1750—1850年。从而推翻了传统文学史关于英国浪漫主义的概念和内涵。接下来,华兹华斯对全体浪漫主义女作家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出四个群体:诗人,论辩家和政论文家,教育论家,小说家和散文家。第四个群体中,奥斯汀、伯尼、海斯(M. Hays)、英奇伯德、拉德克利夫等都成为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字。华兹华斯提出,一方面,如此众多浪漫主义女作家之文学创作见证了社会对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态度的巨变,另一方面,她们的文学作品又促进了传统政治和社会看法的改变。这是对浪漫主义时期女作家的全面介绍和评判,是关于妇女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上乘之作。
因为性别关系,女作家从事创作有许多天然劣势,会不自觉陷入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困境。海耶夫纳和威尔逊两位学者认为,她们明显被差别对待,如果是异见女作家,则会陷入“双重局外人身份”(double-outsidership)[29]199,所受束缚也是双重的,例如威尔士加尔文教派女作家。公/私领域的划分是另一束缚,她们不仅受到相夫教子等家庭羁绊及其无保障的法律地位约束(3)1870年,英国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案》,确立了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在此之前,妇女及其财产都属于丈夫所有。1882年,该法案的修订案才确立妇女的财产处置权。,其读者群和流通范围也会因此受到限制,难以在男性定义的文类规则中建立起自己的风格、权威和合法性等。费尔德曼和克雷也指出,为了使自己的声音合法化,她们只能在女性的“素描”(sketch)与男性的文学中挣扎[30]80。
作为承担起相夫教子重任的家庭主妇,女作家探讨最多的主题还是母职和母女关系,这自然也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格林菲尔德以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学方法阐释了众多女作家关于母女关系的描述,认为许多描述母亲缺失的妇女小说,主要特征是不在场母亲和遭罪女儿,“母亲的缺失突出了她的不可或缺性”[31]13。这为18—19世纪妇女小说中的“贤母”形象提供了一个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吉恩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宏大主题出发分析了拉德克里夫等五位小说家质疑被置于国家话语体系中的母职及其后果,指出她们的小说呈现出商业化、进步、审美以及尊重个性等男作家才会涉及的浪漫主义思想[32]3。克莱西恩着重分析了“放荡女”(fatal women) 形象,认为纵欲和暴力的“放荡女”颠覆了自然、仁慈和被动的传统女性形象,它在浪漫主义女作家诗性身份发展过程中以及探索身体、性和政治等问题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是劳乌的研究。她基于男女浪漫主义作家有“亲缘关系”的认知[33]93,将男女浪漫主义作家同行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发现罗宾逊(M. Robinson)和柯勒律治、史密斯和华兹华斯、奥斯汀与同时代人、赫门兹(F. Hemans)和雪莱等不仅相遇相交,而且相互影响。例如,罗宾逊视柯勒律治为“志同道合的心灵”(associating mind)。劳乌还指出,“男诗人一直以天赋创造性想象力著称,但是奥斯汀却是以理性、常识和经验现实的倡导者而闻名。”[33]93我们因此而了解到,浪漫主义运动不仅产生了男性诗人,也产生了女性诗人、小说家等。他们相互影响,并肩作战,而且,女作家所取得的成就同样不容忽视。
众多言情小说主题研究不仅重现了18世纪妇女小说流行的事实,而且展现了英美妇女小说批评的兴盛和特色。
六、结语
英美学术界三十年来关于英国“长18世纪”妇女小说批评与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发展方向。实际上,还有更多次要主题系列,例如,乌托邦与科幻、游记、社会性别、教养等,限于篇幅,未能一一论述。不过,以上研究情况足以让我们知悉英国“长18世纪”妇女小说家群像及其小说创作的多彩画卷。它不仅让我们了解到该时期涌现出了像奥斯汀、伯尼、艾奇渥斯、拉德克里夫等许多可与“小说之父”比肩的“小说之母”,同时,这三十年来的批评与研究也让我们看到了该世纪妇女小说批评与研究的盛况及其发展趋势和特色。越往后发展,用来阐释的理论工具就越多,主题就越多样化,形成的系列研究就越多,研究也就越深化。众多研究在不知不觉中复活了沉寂的女作家,创造了新作家,矫正了传统文学史的偏颇,肯定了妇女小说家在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实乃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