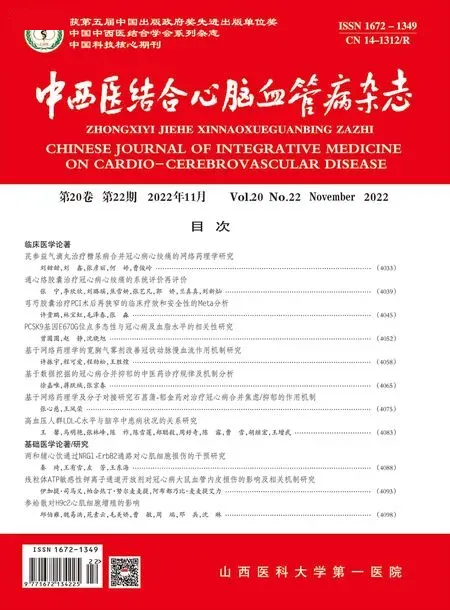从“子盗母气”理论探讨肠道菌群与冠心病的关联
王雅琴,张 艳
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作为一种普遍的心血管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较高的发病率。在我国,冠心病的患病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8》显示,2017 年国内冠心病死亡率为237.36/10 万[1],并且以老年人为主要发病群体,中青年群体发病率在逐步增高,冠心病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重大健康问题,对冠心病防治迫在眉睫。尽管对于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如吸烟、高血糖、高血压、脂代谢紊乱等进行控制[2],冠心病的发病率与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因此,寻找冠心病新的治疗靶点日益紧迫。对肠道菌群的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对宿主消化、内分泌、神经、运动等多系统产生广泛影响[3],其对心血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肠道菌群可归属于中医脾胃系统,与心系统存在五行母子关系。本研究旨在从“子盗母气”理论探讨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对冠心病的作用及其机制,并将肠道菌群作为治疗冠心病的一个新突破口,为冠心病的防治提供更多思路。
1 肠道菌群与中医脾胃的关系
肠道菌群,即人体肠道内寄生物的微生物。人肠道内微生物的数量为每平方米100 亿,在人体防御、消化、感染、免疫应答、内环境稳态、抑制肿瘤细胞等多方面起重要作用,被喻为“超级生物体”。中医并无肠道菌群这一概念,但肠道菌群生态系统与中医脾胃系统不谋而合。《内经》云:“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食从口入,于胃中腐熟发酵,其中精微营养物质由脾过滤,输布心肺,奉心化赤为血,濡养四肢百骸,此为“脾气散精”“谷气通于脾”。饮从口入,胃阳蒸腾,化成津液,由脾为中轴转输,化为“泪、汗、涎、涕、唾”,可见脾是人体能量的转化器,为人体源源不断地供应营养物质。与之对应,张成岗教授[4]在2013 年曾提出“菌心说”的概念。“饥饿源于菌群”是菌心说的理论要旨。菌心说认为,人体饥饿基因由肠道菌群编码并通过由肠道菌群构成的第二大脑释放出摄食的信号,驱动人体从食物中获得能量,与中医所说的“脾为气血生化之源”相互印证。
诺贝尔奖获得者Lederberg[5]揭示了人体微生物(尤其肠道菌群)与人体是相互寄生的关系,即“人菌共生”的概念。动物实验证明,无菌条件下,小鼠难以存活于外部环境。对肠道基因组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可以在人类婴儿阶段帮助大肠发育,开发智力,参与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并维护免疫系统稳定,可以说肠道菌群为人体“后天之本”。病理上,大量研究表明,脾虚与肠道微生态失衡关系密切。动物实验显示,脾虚的小鼠模型存在显著的肠道菌群失衡,而肠道菌群生态紊乱的小鼠普遍存在脾虚的证候[6]。脾虚会出现纳呆、四肢疲乏无力、便溏等症状。而基于肠道菌群比例改变所引起的炎性肠病(IBD)同样也会出现上述腹泻、四肢疲乏无力、厌食等症状。脾主肌肉,脾病则肌肉腠理不固,卫气不充,则对外邪防御能力下降。相同地,肠道菌群与机体免疫也密切相关。泄泻病人肠道有害菌分泌的抗原会刺激肠道黏膜,使肠道局部免疫加速,使得血清中免疫球蛋白(Ig)A、IgG、IgD 的含量低于对照组[7]。
2 “母子相生”——肠道菌群稳态对稳定心脏功能至关重要
《素问》云:“心生血,血生脾”。五行上心属火,脾为土,火生土,心脾二者为母子相生关系。《素问·玉机真脏论》曾论述过疾病的传变:“受病气于其所生之脏”“气舍于其所生”,五脏的病气来源于“我生”的子行脏气,心所受的病气来源于脾;反过来,病气常常会停留在“生我”的母脏,脾病日久累及心。在经络上,太阴脾之脉,别络于胃,上行过膈,注入心中,于小指末交于手少阴心经。脾之大络,于腋下出,散布胸胁。由此可见,心与脾以气血为载体,以经络为通路,在诸多功能上相互协同,一言以蔽之,即为“母子相生”关系。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脾胃阴阳气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肠道菌群生态的变化,因而,肠道菌群与心功能息息相关,即心、脾胃、肠道菌群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形成“心-脾-肠轴”。比如,肠道菌群代谢物短链脂肪酸具有降压效果[8];肠道菌群分泌物可以作用于肠道S 细胞,促进S 细胞分泌促胰液素,增加心排血量。肠壁细胞对物质的通透性会随着肠道菌群的代谢物的改变而变化,影响包括心排血量、心脏前负荷、免疫蛋白等在内的与心血管息息相关的因素。国外研究者在研究心力衰竭小鼠肠道菌群的变化过程中提出“肠假说[9]”,即当心输出量下降时会导致肠道低灌注,引发肠缺血水肿,肠道通透性、肠道菌群结构数量随之改变,而继发的肠道生态改变和血浆内毒素升高会引发全身慢性低度炎症反应,处于激活状态下的炎症细胞会加快心力衰竭的进展。
3 “子盗母气”—— “心-脾-肠轴”失调在冠心病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3.1 脾虚生痰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病理基础 《证治汇补·痰证》云:“脾为生痰之源”;《诸病源候论·虚劳痰饮候》指出:“劳伤之人,脾胃虚弱,不能更消水浆,故为痰也”;《内经》言:“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现代人由于素体脾胃虚弱,又嗜食肥甘厚味,或久居潮湿之地,亦或思虑过度,伤及脾胃,导致脾的运化失司,影响正常水液代谢,水液聚集不散形成痰饮。痰饮留滞心脉,脉道不利,不通则痛,则发为胸痹心痛。中医所说的痰则可对应为西医上的血脂[10]。现代医学认为,冠心病是冠状动脉壁斑块累积日久导致管腔狭窄,完全或不完全的血流阻断引起心肌供血不足所导致。而血脂代谢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其中,以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HDL)和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相关性最大。HDL 与LDL 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过程中是互相拮抗的。HDL 分为多个亚型,HDL 小颗粒型在变为成熟的大颗粒型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吸收胆固醇,实现胆固醇的逆向转运,即HDL 为“好的脂蛋白”[11]。而LDL 会在血液中被氧自由基氧化,形成氧修饰的低密度脂蛋白(ox-LDL),其可使胆固醇蓄积于血管壁上,加快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即LDL 为“坏的脂蛋白”。
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可以影响脂类的消化吸收代谢,调节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Fu 等[12]认为肠道菌群主要通过影响血脂成分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的生成,从而影响心血管疾病的预后。Thomas 等[13]发现胆汁酸在部分肠道细菌的参与生成下进入血液循环,通过G 蛋白偶联受体(GPCRS)调节LDL 的代谢。傅颖等[14]发现肠道微生物可以调节与HDL 成熟相关的血清SRB-1 和LCAT 的表达。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可以影响与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sd-LDL)生成相关的三酰甘油(TG)和脂蛋白脂酶的表达,间接地调控动脉斑块的形成[15]。
3.2 脾“升清降浊”功能失调加重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 中医上,“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指脾升发清阳之气,即饮食水谷中的精微,在菌群生态系统中,泛指对人体有利的益生菌。胃主降浊指胃沉降晦浊之气,即饮食水谷中的糟粕,在肠道菌群生态系统中泛指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西医研究表明,肠道代谢的情况取决于肠道微生物的组成,每日摄入的营养物质、机体分泌排泄的有机成分,在不同肠道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化成不同的物质,对人体生理、病理产生不同的效应。脾胃升清降浊功能障碍会引起菌群生态平衡失调,这种失调可通过产生各种代谢产物直接或间接地引起心脏功能障碍[16]。
有关研究表明,与健康人相比,罹患冠心病病人肠道致病菌数量比例较多,益生菌数量较少。健康人群肠道内真杆菌属(Eubacterium)和罗氏菌属(Roseburia)丰富,而动脉粥样硬化病人耶尔森氏菌属(Yersinia)和柯林斯菌属(Collinsella)大量增殖。Toya等[17]选取晚期冠心病病人组与健康人群组进行对比,分析比较两组肠道微生物的组成,结果表明,冠心病病人的香农-威纳指数和菌群丰富度指数Chaol 明显下降。对动脉粥样硬化病人从肠道菌群基因组层面的研究发现,其中的某些微生物含有编码肽聚糖基因,肽聚糖是细菌细胞壁的糖肽化合物,作为抗原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促使巨噬细胞释放调节因子、炎性细胞释放炎性因子,促进血管慢性炎症化和动脉斑块形成,从而促进冠心病的进展。部分有害菌在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时,可直接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循环,引起血管平滑肌和心肌的慢性低度炎症,使心功能下降。
王玉珍等[18]建立高脂饲喂小鼠模型与正常饲喂小鼠组进行对比,检测两组血清中三甲胺(TMA)、氧化三甲胺(TMAO)、总胆固醇(TC)、TG 的水平,并运用16s rDNA 高通量检测两组肠道菌群结构改变。结果显示,高脂饲喂小鼠TMA、TMAO、TC、TG 水平明显增高,并伴随肠道菌群的结构和数量的明显改变,表现为某些益生菌如乳酸杆菌的数量显著减少及大肠杆菌、链球菌、梭状芽孢杆菌等有害菌和条件致病菌数量升高,进一步揭示了肠道菌群失衡,可以显著增加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从而促进冠心病的发展。
4 “补土益火”——以肠道菌群为靶点防治冠心病
随着各国科学家对肠道菌群与冠心病相关性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以肠道菌群为靶点防治冠心病。在中医上则以补土益火为治,重在通过调整脾胃稳定肠道生态来恢复心脏功能。
4.1 中药 运用作用于肠道菌群靶点的药物,比如大黄,入胃、大肠经,有泻热通便、解毒消痈的作用,药理学上其含有的大黄素对肠道具有抑菌、清除氧自由基、消炎和保护胃肠道黏膜的功能。研究发现,给心肌梗死小鼠灌大黄水煎剂,小鼠心功能提高,心肌梗死面积减少,从而对调整肠道生态治疗冠心病的方法得到证实[19]。
丹参活血消痈,清心凉血,除烦,用于心痛、不寐、疮疡肿毒等。药理作用上对心血管方面研究较多。在研究丹参酮对心血管保护作用机制的过程中发现,调整肠道内环境是其改善心功能的途径之一。丹参可以增加肠道物种丰富度,在增加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有益菌数量的同时减少肠球菌等有害菌的数量。对心血管术后病人其可减少血栓素生成,降低血黏度,修复肠黏膜受损细胞,阻碍有害物质吸收入血,从而降低心血管危险因素,保护心功能[20]。
很多中药在人体的利用率较低,但可以通过在肠道内调节肠道菌群的生态,间接来调控人体代谢而发挥作用,比如中药白藜芦中的白藜芦醇可抑制TMA 合成酶;姜黄中的姜黄素可以恢复肠道屏障功能,减少脂多糖进入血液循环;葫芦巴碱可降低TMAO;茶多酚可促进双歧杆菌的增生;薏苡仁多酚提取物可保护肠道黏膜屏障等。
4.2 方剂 用“健脾”“运脾”“补脾”的方剂。孙媛提出“治脾以安五脏”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以“培土益气,活血养心”为治则,比如用四君子汤加桃仁、赤芍,治疗脾虚推动乏力导致血滞心中所引起之胸痹[21];用瓜蒌薤白半夏汤运脾化痰、宽中散结,治疗脾运不健,湿聚成痰,阻遏心阳而成之胸痹[21]。李七一教授从脾胃论治冠心病八法中提出用人参汤温中散寒、振奋心阳,治疗脾阳虚衰、阴寒内盛所致之胸痹;而对于因久虑久思所致之胸痹,因其耗心伤脾,湿盛阳微,则用逍遥散加味[22]。国医大师邓铁涛治疗冠心病,重在运脾化痰,常用方剂为温胆汤加人参,以除痰利气,条达气机[23]。
4.3 饮食 基于中医药医药同源的理念,改变饮食结构是防治冠心病的有效措施之一。粗粮中含有的β-葡聚糖及植物甾醇可增加32 种益生菌的活性,尤其促进如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的生长,促进肠道蠕动并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24]。低脂饮食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结构,增加肠道有益菌,如拟杆菌,减少肠道有害菌,从而改善肥胖和代谢紊乱的症状[25]。
4.4 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 粪菌移植作为一项新兴的治疗手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粪菌移植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菌群,移植到病人胃肠道内,重建新的肠道菌群,实现肠道及肠道外疾病的治疗。中医早在公元4 世纪就开始用“金汁”(古人曾将屎比作黄金)治疗严重腹泻和高烧不退。东晋医学家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中就有鸡矢白、稀牛粪、雄鼠屎等以排泄物组方治疗疾病的记载[26]。中药还有诸如夜明砂(蝙蝠屎)、人中白(人粪)、白丁香(麻雀粪)、左盘龙(鸽子屎)、龙涎香(鲸鱼屎)、五灵脂(老鼠屎)、望月砂(兔子屎)等干燥粪便药材。现代的粪菌移植技术目前在复发性难辨梭菌感染、炎性肠病、肠易激综合征[27]、便秘[28]、代谢综合征[29]等疾病的治疗上疗效肯定。其他疾病如帕金森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自闭症、病毒性肝炎等肠外疾病也有个别报道。肠道菌群在冠心病的治疗上多局限于动物实验,且受限于粪菌移植方法学的水平,其安全性和稳定性也在研究中[30]。但目前对肠道菌群的研究让人们意识到肠道菌群的研究潜能巨大,相信随着科学技术以及国家粪菌数据标本库的成立,粪菌移植有望成为治疗冠心病的一个新的手段。
5 总结与展望
冠心病作为世界性医学问题让无数科学家为之倾注心血。近些年来,西方医学掀起了肠道菌群的研究热潮。随着对肠道菌群这个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研究的深入,其与冠心病的关系慢慢被揭开。西医占据主流的海外国家逐渐认识到肠道菌群失调与冠心病的发生有重大关系。而中医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认识到肠道菌群的治病潜能,从最原始的菌群移植“金汁”,到五行藏象理论,再到理法方药,中医学在华夏大地上熠熠生辉。中医治病强调“整体观念”“治病求本”。针对冠心病,不单单要从“心”论治,更要基于五行生克制化,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进行辨证论治。基于心脾母子相生理论,以肠道菌群为靶点调节肠道生态为冠心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广阔的前景。虽然目前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但对于中药调节菌群生态的分子机制研究尚少,动物实验也缺乏有效的证据,对于运用肠道菌群来治疗冠心病仍处于探索状态。但是相信随着分子微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肠道菌群有望成为治疗冠心病的新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