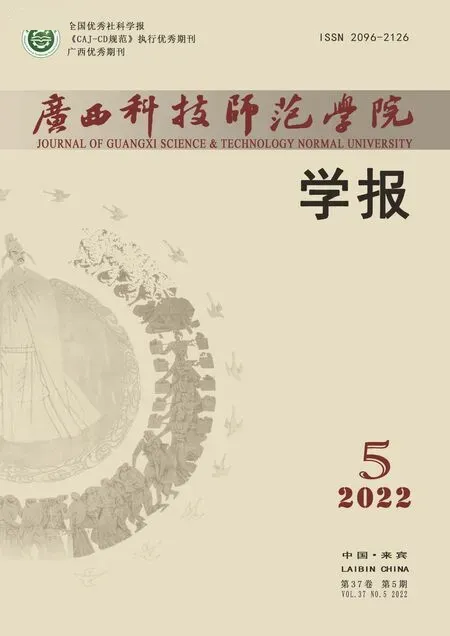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与路径选择
——基于广西部分民族村落调查
王丽云,孙庆彬,郭传燕,徐 标,潘兰芳
(1.玉林师范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2.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 来宾 546199)
本研究所言“内生动力”,特指由民间社会内部生发出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动力。关于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学者们研究指出,文化的内生动力源于利益需求[1]、文化认同[2-3]、文化自信[4]等。学者周永广认为,“内生”有三条路径:强化内部生长动力;当地人成为主要参与者;建立体现当地人意志的有效基层组织[5]。虽然体育学界也有学者聚焦体育文化的“内生”问题,如体育的内生动力[6]、内生增长[7]等,但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对象的“内生”研究较为鲜见。
自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算起,由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17个年头。综观以往保护工作,“基本上是循着从上级政府、专家到地方政府再到基层社区的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模式展开的”[8]。有学者指出,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而言,若要使“非遗”保护成为可持续的长久事业,则应该“民间的事情民间办”[9]。循着上述学者思路,以民间视角探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与路径,就成为一项紧迫而有意义的工作。
本研究调查的民族村落,大多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少数民族数量、人口众多,居住着汉族、壮族、苗族、侗族、瑶族等民族,流传的民族体育文化项目(如打榔、打扁担、跳蚂拐、抢花炮、多耶、芦笙踩堂、舞狮、猴鼓舞等)绚丽多彩,蕴藏着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智慧,具有研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和访谈法,以广西部分民族村落为研究对象,探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持续传承提供依据。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从中国知网、超星等电子文献资源以及部分地区的图书馆、县志办等地方文史资源中,收集、查阅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面的资料,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
(二)实地调查法
课题组成员对表1中的8个村落进行了实地走访,收集了大量案例材料。这些案例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项目在生发逻辑、传承手段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具有一定的跨地域代表性。
(三)访谈法
课题组成员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马山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与融水苗族自治县、河池市东兰县与天峨县等地,走访当地有关部门,访谈相关专家,了解广西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历史与现状,深入当地民族村落,访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探寻其传承的内生动力与运行机制。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系统
任何动力都是有源头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亦是如此。系统论认为,“系统、要素、环境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系统之所以运动并具有整体属性就在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10]。我国学者林福永用数学方法证明,一个有机系统在环境、结构和行为要素之间存在着固有关系及规律[11]。根据系统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滋生于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如图1)。

图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系统
我们探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可根据系统论,从传承主体(传承者)、传承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传承客体(体育文化本体)等多个源头追寻。从传承主体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源于传承者的族群需求、文化自觉等;从传承环境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源于民间信仰、宗族关系、传统节庆等;从传承客体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源于文化创新、文化融合等。上述三个维度的动力源,分别滋生出三维动力要素,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构建出一个结构性、关联性、开放性、整体性的三维内生动力系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生动力系统是开放的,而不是终极、周延、穷尽的。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段、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实际情况,不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源会有所不同。
(一)源自传承主体的内生动力要素
1.需求内驱力。族群内部需求是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之一。如打榔(又称打舂榔、打舂堂、打砻等),其传承的一个重要动力便是当地族群的娱乐需求。打榔的源头可上溯至唐代的打舂堂[12]。但后来,壮族村民用于制作“舂堂”的大口径木材逐渐匮乏。为满足族群的精神文化需求,壮族村民遂以“木板+木凳”替代“舂堂”,创造出富有壮族稻作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打扁担”。在娱乐需求的驱动下,“打扁担”这一壮族民间体育活动得以不断发展。再如纳洞村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跳蚂拐”①跳蚂拐是一项模拟青蛙动作的壮族民间体育活动。有些资料称为“蚂拐舞”,《广西通志·体育志》(1988年版)则称“跳蚂拐”。,其传承的内生动力源于壮族人民对蚂拐的崇拜②“蚂拐”是壮族人民对青蛙的称谓,是壮族的传统崇拜物。。再如三合村的猴鼓舞,其是瑶族人民在丧葬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猴鼓舞的传承内生动力是祖先崇拜需求。综上,族群需求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生的内生驱动力。
2.文化自觉力。文化自觉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持续传承的动力源泉之一。根据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觉的形成基础可概括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根”有清晰认知;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容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规律能够准确把握。文化自觉是强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主动力。例如,三合村的猴鼓舞原为祝著节举办的祭祀性原始舞蹈,动作简单,节奏单一。近年来,以蒙胜文为代表的三合村瑶民挖掘创造出十余种不同的舞蹈动作:既有展示祖先打仗、耕种奋斗场景的,也有表现瑶民现代生活故事情节的。这些活动既有古朴韵味,又富现代气息。类似的活动还有加方村的打扁担、高定村的多耶、整垛村的芦笙踩堂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传承至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拥有牢固的历史文化根基,传承者能够自觉珍视其所传承的体育“活宝”,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二)源自传承环境的内生动力要素
1.信仰吸引力。爱弥尔·涂尔干在论述图腾信仰时指出,在族群之外“存在着支配他们同时又支持他们的力”[13]。民间信仰作为构筑民族传统体育心态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具有“根”文化、“元”精神的意义,它不仅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体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还与文化象征体系构成微妙的互补关系,其所蕴含的精神力量不可低估。这样的精神力量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村的抢花炮场地得以展现。富禄村抢花炮是一项“烧钱”的民间体育活动,单单举办“迎炮”“送炮”“游炮”等仪式,“炮主”就得开宴数十桌,以飨寨民,费用常远超参赛者赢得的奖金。然而是何种动力推动着富禄村民年复一年乐此不疲地“抢”呢?其奥妙就在于所争夺的三个花炮中分别包含着“财”“子”“福”等“好运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民间信仰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民间信仰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应充分发挥其精神动力作用。
2.宗族凝聚力。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差序格局”[14]。在“差序格局”框架下,中国传统社会孕育出了宗族性体育组织,它们有着基于血缘、亲情的凝聚力。例如,侗寨高定村就由吴、杨、李、卢、莫、黄等6个姓氏族群组成,各个宗族分片聚居,每个片区都建有一座姓氏鼓楼。多耶、芦笙舞等宗族内举办的体育活动一般都在本宗族鼓楼坪举行,体育组织也以宗族关系为主要格局(如图2),凸显宗族的凝聚力[19]。纵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过程,宗族关系与体育组织相互交织,强化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凝聚力。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变迁,宗族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力逐渐衰退,而民间协会、理事会等新型民间组织开始浮现。在当代经济浪潮冲击下,中国社会传统的乡土逻辑正在发生改变,由以“血缘—宗族”为核心的传统乡土逻辑向以“市场—消费”为核心的新乡土逻辑嬗变。

图2 以宗族关系为主要格局的体育组织
3.节庆推动力。传统节庆是一个包含着神话传说、饮食娱乐、祭祀庆典等众多民俗事象的“文化丛”,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极强的群众参与性。根据人类学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理论,传统节庆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性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记忆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源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往往交织镶嵌在传统节庆框架当中,与节庆活动共用文化符号系统。例如,跳蚂拐、多耶、芦笙踩堂、猴鼓舞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别在蚂拐节、侗年、坡会节、盘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举办,它们分别使用蚂拐、鼓楼、芦笙、长鼓等符号。传统节庆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提供强大推动力。
(三)源自体育文化本体的内生动力要素
1.创新拉动力。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内生力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史就是一个渐进创新的发展过程[16]。例如,“打榔”向“打扁担”的演化,就是一个创新拉动发展的典型例证。再如,整垛村传统的芦笙踩堂,步法简单,节奏缓慢,逐渐不适应当代苗族人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后经整垛村民创新改编,新推出的芦笙踩堂已开始呈现出新气象:舞步多变,节奏加快,再配以花束、花扇、花伞等艳丽道具,现代感十足,深受当地苗族年轻人的喜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具有一定规律性。只有尊重文化规律的创新,才具有传承拉动力;而逆文化规律而作出的所谓“创新”,则会引发文化损毁。
2.文化融合力。文化融合是指“民族文化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其传统文化为基础,根据需要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促进自身发展的过程”[17]。就当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而言,文化融合所展示出的传承动力不容小觑。例如,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睦村的一心堂舞狮队,在2004年成立之初推出的技艺是传统的地狮和台狮,后来以兰贵孟为代表的艺人主动引入广东梅花桩狮艺,强化了动作的可观赏性。但他们并未完全照搬,而是在传统狮艺基础上自觉融入苗族文化要素:在表演情景中置入苗族传统故事,伴奏乐器选用被誉为苗族文化符号的芦笙,表演服饰也采取蕴含苗族神话寓意、以羽毛作边饰的百鸟衣。一心堂舞狮队的融合创新卓有成效:2018年一心堂舞狮队荣获广西狮王争霸赛冠军。文化融合有着自身规律:首先要积极接触外来文化;其次要主动接受文化碰撞,并在碰撞中选择、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元素;最后进行文化整合。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路径
从系统论角度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思考:诸动力要素的强化、不同参与方的协同、不同层次传承内容的兼顾。下面以融水苗族自治县整垛村的民族体育活动——芦笙踩堂舞为例,来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可借鉴的三条路径。
(一)从源头出发,强化三维动力要素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包括三维内生动力源和诸多动力要素——需求内驱力、文化自觉力、信仰吸引力、宗族凝聚力、节庆推动力、文化创新力、文化融合力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最基本路径,就是强化上述诸动力要素。首先,芦笙踩堂之所以在整垛村经久不衰,最根本的动力是它能够满足村民节庆娱乐、婚恋择偶、村寨交际等需求。其次,民间信仰为芦笙踩堂传承提供强大动力。芦笙踩堂中蕴含着神话传说与信仰崇拜的元素。民间信仰是芦笙踩堂传承的重要精神力量,这从芦笙踩堂场地中央高高耸立的布满苗族图腾的芦笙柱①芦笙柱布满苗族文化图腾。柱身绘龙画凤,雕刻水牛角。水牛角是友谊和睦、相亲相爱的象征。柱顶部雕有孔雀、野鸡、白鸽或混合型神鸟。苗族人将姑娘比作鸟,因为鸟不仅美丽,而且善于歌唱,是人类歌颂的对象。就可看出。另外,传统节庆为芦笙踩堂传承提供了重要动力。坡会节是融水苗族自治县春节后的族群集会形式,几乎每个乡镇都会组织。芦笙踩堂是坡会节最重要的活动内容。以2020年为例,大型的坡会节就有19个,为芦笙踩堂传承注入强劲的动力。综上,芦笙踩堂传承的一个最基本路径,是强化其各个动力要素。
(二)以民间为主,凝聚多方力量
从文化传承主体角度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需要民间、政府相关部门、学者、商家等的参与,需要协同、凝聚多方传承力量。其中,民间力量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关键一方,这是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间性所决定的。“民间事情民间办”,其他参与者只起“辅”的作用,这是我国民间事务管理的历史惯例[9]。以民间为主体,积极调动民间各参与方的积极性,同时协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学者、商家等多方力量,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又一条路径。我们遍览融水苗族自治县2020年的19个坡会节芦笙踩堂活动,发现基层群众才是其真正的主人,学者、商家等在芦笙踩堂活动中只起“辅”的作用。以芦笙柱为核心的芦笙踩堂场地——芦笙坪上,就像一个大舞台,在学者、商家等多方力量的辅助下,苗族基层群众“奏响”了芦笙踩堂文化传承的“交响曲”。
(三)内外兼顾,传承多层文化内容
从文化的四层次结构理论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包括器物、制度、行为和心态等四个层次的文化内容,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要兼顾上述四个层次的文化内容。例如,整垛村的芦笙踩堂就体现了器物、制度、行为、心态等四个层次的文化内容。芦笙踩堂活动现场呈现着形态各异的器物文化,如芦笙坪、芦笙柱、大小芦笙、表演服饰等;包含着纷繁复杂的非正式制度文化,如器物制作、动作编排等;展示着丰富多彩的行为文化,如动作技术、套路风格、行为符号等;还蕴含着底蕴深厚的心态文化,包括观念、意识、信仰、思维方式等。芦笙踩堂就是循着这种多层次文化内容兼顾的方式世代相传的。
结语
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应从“民间依从”向“民间自主”过渡转型[18]。中国各地流传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都源自民间社会,民间自主本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正常、本然的存续状态。虽然我国政府对传统文化采取立法、资助和分级保护等干预措施,但这并不妨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回归民间自主传承之道。由“民间依从”向“民间自主”过渡,这符合“民间的事情民间办”的惯例。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都诞生于乡土社会,在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乡土逻辑正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以“血缘—宗族”为核心的传统乡土逻辑向以“市场—消费”为核心的新乡土逻辑嬗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文化堕距”现象,从而易造成传承动力系统的紊乱失衡。因此,学界还应加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的重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