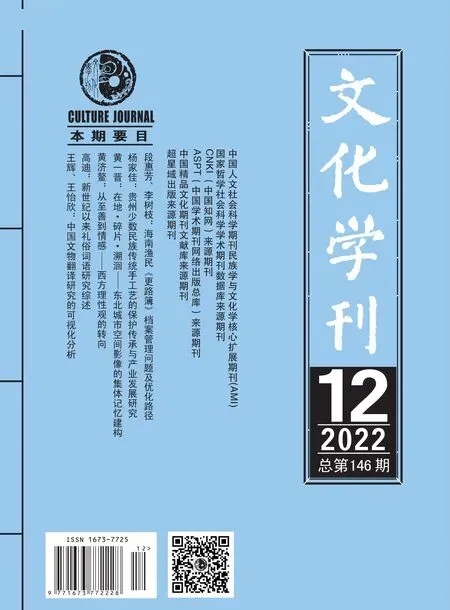贺麟“新心学”思想研究
李 晓 吴 锋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新心学”的创建者,“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之一”[1]。他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和理学熏陶,所以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他说过:“我从小深受儒学熏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2]“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他凭借着对中华传统儒学的挚爱,力求通过恢复儒家传统来挽救当时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现实危机。在国内,他像还海绵一样充满激情地吸收总结梁启超、梁漱溟、吴宓等学者的儒家思想;在海外,他又如饥似渴地学习黑格尔、斯宾诺莎等哲学家的思想;在爱国主义情怀的激荡下,他于1934年发表了《近代唯心论简释》,之后又发表了《宋儒的思想方法》《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一系列的论文,从而构建起“新心学”的思想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一面“旗帜”。“他之提倡新心学,就是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鼓励人们本着自立自强的精神,勇于实践,开创事功。”[3]这在当时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贺麟“新心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有我”“有渊源”“吸收西洋思想”是贺麟在《文化与人生》一书的序言中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总结。所谓“有渊源”者,即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他以传统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思想为主体,并汲取各学派的思想文化。所谓“吸收西洋思想”,顾名思义,指吸收西方哲学思想之精华,他对黑格尔、斯宾诺莎、康德等西方近代哲学家的思想,进行融会贯通,吸取哲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思想和方法,以资中华民族复兴。
(一)国学功底:宋明儒学为贺麟“新心学”活水源头
贺麟哲学既然称为“新心学”,那它必然是“有渊源”的,也就是“它确实采取了心学的基本立场”[1]。张学智认为,贺麟先生是“以心物合一、心理合一、心性合一、体用合一、知行合一为特点”[3]的,这很有道理,基本概括了贺麟先生“新心学”的核心内容。这也说明了贺麟在创建其“新心学”时,必然既有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也直接继承了宋明心学的思想,将“旧”陆王心学的精华与20世纪民族危亡的现实、所接受的西方哲学相融合,终而阐发自己的“新”的心学思想体系。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重儒家之外其他诸子的重要意义”[4],贺麟不只对孔孟程朱有同情的解释,而且“对老庄杨墨亦有同情的新评价”[5]。所以,他在创建“新心学”的过程中,努力将宋明儒学中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调解融合,做到无党无偏,而非厚此薄彼。
(二)西学之思:西方哲学思想为贺麟“新心学”助力加持
贺麟于1926年留学美国,在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心理等相关课程;1928年又去芝加哥大学学习黑格尔哲学、伯格森、怀特海等哲学的思想;1930年夏,贺麟加入柏林大学学习黑格尔、斯宾诺莎等哲学家的思想。西方哲学对贺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斯宾诺莎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等。这才有了回国后的“新心学”创建。当然,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假设,贺麟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设法找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集合的交会之处,旨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消化西方哲学的成果来构筑自身的哲学体系。
首先,斯宾诺莎哲学对贺麟“新心学”在思想和方法上都有所启发: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思想启发了贺麟提出了“知与行为同一生理心理活动的两面”“知与行永远在一起,知与行永远陪伴着”[6]的创见;对于斯宾诺莎的“认识真理即是自由”的观点,贺麟从更高的视角加以理解,并在中国思想的根基上加以阐发。可以说斯宾诺莎哲学贯串贺麟“新心学”的始终。其次,贺麟“新心学”也继承了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是哲学研究的主题,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自然成为认识的客体。贺麟在接受康德哲学的基础上,通过融入陆王心学“心即理”“心外无理”的理论,强调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界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自然知识和自然行为所以可能的心中之理或标准”[7]。再次,他提出“不能知亦不能行”的知行观。这是他吸收了谢林哲学的直觉哲学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学界对贺麟“新心学”的肇始点的问题,一般是归结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因为贺麟的“向外格物穷理即向内明心见性”这一观点便来源于此,而且在“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思想的形成中,新黑格尔主义的“绝对唯心主义”也是其“新心学”的来源之一。
(三)推陈出新:现代新儒家思想为贺麟“新心学”锦上添花
“新心学”的形成不只有传统之源、西学之资,实际上早期现代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等的思想对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思想的开拓者,被新儒家“尊为他们的开山人”[8],其“新孔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贺麟“新心学”思想。贺麟面对“新孔学”思想,秉承“扬弃”的理念,一方面吸收其中有价值的“直觉问题”,通过改造和创新,使其成为“新心学”思想体系构建的重要方法论;另一方面,贺麟还克服了“新孔学”思想中的理论的缺陷,并将本体论和宇宙论作为“新心学”的研究重点。对于 “新唯识论”,贺麟认为熊十力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本心即仁”“本心即性”方面,而对于“本心即理”“心者理也”方面的关注度则稍低。
除此之外,现代新儒家的其他代表如冯友兰的新理学、马一浮的新经学、方东美关于生命理想的思想、唐君毅对人文精神的追寻等新儒家的思想也对贺麟“新心学”都有助益。贺麟在看待分析这些现代新儒家的人物思想时,都带着“滤镜”,取其精华,以资其创建的“新心学”更日臻完美、更稳定成熟、更系统完整。
二、贺麟“新心学”的主要内容
贺麟“新心学”思想集百家之长,对中西方哲学进行比较,找出两者集合的交融之处,吸收、借鉴现代新儒家思想中有益的部分,因此内容体系涵盖颇多,主要包括等文化、知行等多领域。
(一)“心即理”
“心”是贺麟“新心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最主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心即理”思想是贺麟在康德哲学和传统心学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借鉴、继承和发展而来。
贺麟以康德哲学为基础,提出“逻辑意义的心”的创新观点。贺麟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一方面是心理意义的心;另一方面是逻辑意义的心。而逻辑意义的心是所谓的‘理’。心理的心是物,如心理经验中的感觉、幻想、梦吃、思虑、营为,以及喜怒哀乐等情绪,都可以用几何方法当作点线面积等实物去研究。”[9]由此可见,贺麟的“二理”为“心理”和“道理”,这个基础上得出了他的所谓的“心即理”。实际上,心理之心为“物”,就是我们的生理器官,这是形而下的具体之心;而所谓的逻辑之心的“理”,是哲学意义的、形而上的抽象的心。
与传统心学家们提出的“心即理”思想不同的是,贺麟所谓“心即是理”意在表明理是心的本质,故“心”与“理”并不完全等价。如此,若要得到对“理”的认识,只需向内求于心,而非向外诉求。总而言之,贺麟认为“心即理”,若是“离心而言物”不仅使物没有条理,更没有价值可言。
(二)知行观
贺麟关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知行关系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在坚持“知行合一”的观念。在《知行合一新论》一文中,贺麟认为“新心学”的研究重点是知行问题。他首先对“知”“行”做出了清晰的定义:“‘知’指一切意识的活动。‘行’指一切生理的活动。”[10]他将诸如感觉、记忆、逻辑思辨等精神层面的活动都归纳为“知”;将四肢五官的运动及神经系统的活动都归结为“行”。“知”与“行”皆为活动,因此不可以简单以动、静来作为区分依据,他坚持认为“知有动静,行也有动静”[11]。
贺麟还吸收和消化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知和行观点,创造性诠释了知行相关的观念。贺麟吸收了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和格林的知行合一观,提出知和行如影随形,始终齐行并进。这是一种自然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行合一”思想。同时,贺麟在继承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提出了以知为主,行为从的论点。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他还区分了“自然的知行合一”和“价值的或理想的知行合一”; 他甚至还从“主从”关系的角度讨论知行的关系;对于知行难易问题,贺麟与中山先生达成一致,认为“知难行易”。所谓“知难”,即从行为、实践到获得真知是很困难的;而“行易”,即指将知识运用在现实生活中,则更加容易。由此可见,贺麟“对知行问题的探讨及建立知行问题的近代哲学理论的尝试”[12]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三)文化观
文化观是贺麟“新心学”思想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关键就是“华化西洋文化”[13]。贺麟自认为研究文化观有两个“必要性”:一是建立唯心主义体系,二是学术建国。
贺麟将唯心主义思想称之为“精神哲学”,这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就是心与理。贺麟认为,这是建立唯心主义体系的必要性原因。而所谓的学术建国的必要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贺麟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到西方列强的侵害、饱受战乱和蹂躏之苦,主要根源在于中国当时的学术文化不及西方。故而,他得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在于民族文化的复兴”这一结论,从而提出了“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助用”新文化观。
在文化观上,贺麟还承袭了朱熹“道之显者谓之文”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推促文化载于道,道同样也是万物、自然的载体这一观点。故而文化具有真善美的特性,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的结合体。
对于体与用相互关系的问题,贺麟提出了“文化的体用观”。他反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当时流行的观点,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能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西方文化,能不能把西方文化中国化,儒家思想的复兴就是要用儒家思想去融合西方文化中的哲学、宗教、艺术等。他认为,当这些文化被引进至中国之后,能不能将其作为中国文化之用,这才是关键。同样,对于科学、技术等处于西方文化中用之地位之物,也不可变成中国文化之体。即体用不可混淆。为此,贺麟“在文化学术上倡导援西学入儒学,充实并发挥儒家思想,使之在现代有新的开展。”[14]这是一种体用合一为用,体用平行发展的思想。
(四)直觉论
贺麟“新心学”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互磨合、融汇的产物。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皆使用“直觉法”,然侧重不同。程朱理学注重读书穷理,向外透视;而陆王心学则重视回复本心,向内省察。贺麟将二者的不同融合统一,提出了自己的“直觉法”。贺麟的直觉观实际是从方法论的视角去发扬儒家的诗教传统,他将直觉法分为两面,一面是向外观认,一面是向内省察。这正是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各执一面的直觉法作了糅合。
贺麟认为“过去儒家因乐经轶失,乐教中衰,诗教亦式微。”[15]所以他从艺术的直觉视角来思考理论的建构,认为直觉是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对于“直觉”,贺麟说,“经过很久的考虑,我现时的意思仍以为直觉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方法。所谓直觉是一种经验,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它包括生活的态度,灵感的启发,精神的境界,神契的经验,知识方面突然的、当下的顿悟或触机”[16]等等。 由此可见,贺麟的直觉观既包括了其人生哲学的思想,也是一种研究真理的方法论。贺麟对“直觉”的重视并不是他夸大其作用的理由,因为直觉只是一种洞见,他并没有舍弃理智的分析,所以他面对“直觉”,依然保持客观的态度。
三、贺麟“新心学”思想的理论特色——“新”之所在
每一个思想都有其特有的理论特点,“新心学”是在传统心学的基础上,继承与发扬而来,两种学术思想孕育的时代背景不同,蕴含的含义不同,产生的方式不同。贺麟“新心学”是基于中国传统儒学,融合西方哲学思想,综合现代新儒家思想所创造的理论体系,同样也具有其特有的理论特色,即“新心学”的“新”之所在。
(一)“新心学”所处时代之“新”
每一种理论从孕育到最终的成型必然有其特殊的使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贺麟“新心学”思想也不例外,产生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采用了扬弃的发展方式、孕育出新时代需要的心学思想。
“新”总是与“旧”相对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七十余年,中华民族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欧风美雨席卷而来,西方各种思潮和文化充斥着中国文化的市场,“中国本土文化向何处去?”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社会课题。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踏上了奋力追求民族文化复兴之路,由此催生了现代新儒家思想。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主题,每一代人总有一代人各自的使命。现代新儒家思想诞生于救亡图存的时代,贺麟“新心学”亦不例外,他打破了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壁垒,对心学有了创新性发展,同时更是将中学与西学相融合,使得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协调统一、融合发展成为可能。在近代文化失衡、民族危亡之际,贺麟的“新心学”思想为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发展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并力图寻找一个能够使中国文化恢复辉煌的新方法,寄托了他希望恢复民族文化以达振兴中华民族之目的。
(二)“新心学”所蕴内涵之“新”
“新心学”承袭并发扬了传统心学,虽有继承,但仍存异处,如在“心与理”“知与行”概念与关系上,两者之间的含义却并不相同,贺麟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以变动,于是“新心学”诞生了。
陆王心学的“心”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范畴;“心即理”中的“心”和“理”都是封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贺麟在“新心学”思想中对“心”进行了重新的构造和深入的发掘。他将心作二义:其一是“心理意义的心”,指感觉、幻想、情绪等物;其二是“逻辑意义的心”,指“心即理也”中之理,是行为、知识、经验、评价的主体,以及理想的精神原则。由此可见,贺麟所认为的“心”的含义与心学中是有所差别的。贺氏所谓之“理”,即“心即理也”,是从心中推演出来的,其中包含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以及其他许多意义,这显然是与陆王的“心学”体系完全不同。
同心和理存在差别一样,“新心学”体系中的知与行的概念也不同。传统心学中,如王阳明所认为的知行合一,即知与行并重,不分彼此,说明道德意识和道德修养是同等重要。贺麟在“新心学”思想体系中阐释了知与行的概念,“知”是指所有的意识活动,包括感觉、直觉、记忆等;“行”是指所有的生理活动,如四肢、神经系统的运动等。由此看来,知与行在心学和“新心学”中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新心学”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行观。
(三)“新心学”所呈方式之“新”
在新儒家思想各流派中,贺麟的“新心学”提出较晚,但其在新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不仅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还因为“新心学”是贺麟不偏不倚、不偏不党,对其他的相关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诞生的。
传统儒家文化在新文化以及“五四运动”前是没有生机的,为了民族振兴,有志之士提出重塑传统、复兴儒学。贺麟在中西文化的对撞中,提出要具备时代节律,善于学习西方文化,掌握西方哲学的精髓,并将其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如此才是作有用功。而面对中国文化的有体无用和西洋文明的有用无体的差别,贺麟亦指出应该抱着将二者合一的态度,即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
贺麟的“新心学”自然也是调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产物,这也是“新心学”思想的显著特征和独特风格。贺麟一方面重视儒学,另一方面重视其他诸子之学的积极意义,一视同仁地进行扬弃。
不管怎么说,“新心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仍然是以心学为立场,只是在强调传统文化和民族复兴的背景下,贺麟想调和心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还以中国哲学为本,借鉴西方文化以重铸民族文化,使其极具民族性,以达复兴民族文化之目的。总之,贺麟的“新心学”在以儒学为宗的基础上,兼采他山之石,赋予了现代新儒学新的价值和意义。
四、贺麟“新心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新心学”思想的产生是20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最后一派新儒家思想,它既有对早期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吸收和总结,也对后来者的现代新儒家思想发展产生了指明方向的影响。
现代新儒学体系中的“新心学”思想与现代新儒学的其他流派一样,都是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和中国文化危亡的紧迫情景下产生,其肩负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旨在通过复兴儒学,来拯救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现实命运。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方主流思想的沟通与交融,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新心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在打通先验逻辑方法和直觉法的问题上开展了有创见的工作,这对中国当代哲学体系的重构和建设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一方面,“新心学”思想跟现代新儒学的其他学派一样都在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寻求对提升民族的文化素养和哲学素质的优秀传统。这在20世纪的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新心学”和现代新儒家的各家各派一样,在探索文化哲学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其对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等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也是不可缺少的。
贺麟对哲学充满了智慧,他一生致力于改变儒学传统发展的走向,对新儒学思想建设有着重要贡献,然而贺氏也存在不足之处,他本人的思想过于分散,缺少理论的自觉,且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使得贺氏并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儒学传统发展的走向。瑕不掩瑜,贺麟的“新心学”思想对儒学走向的发展具有时代意义。
总之,每一种理论从孕育到最终的成型必然有其特殊的使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贺麟“新心学”思想也不例外,产生于救亡图存的时代、来源于扬弃的发展方式、孕育于大众的心学思想,其对新时代中国哲学的双创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哲学的未来重建中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