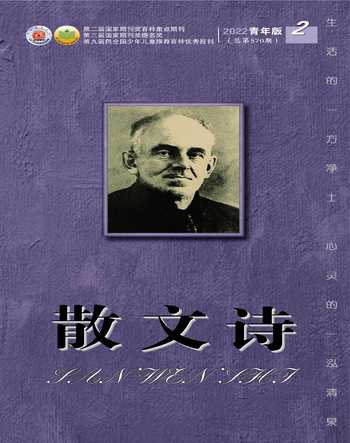以麦子为序
弋吾
在这场大雪之前
叶子还绿着,野草还青着,冬麦还在尝试着撑起秋天最后的颜面,正如我试图用一句话,让一首诗站起来。
没淬过火的骨头没有硬度。
田野看上去一派祥和,万物还散漫地活着,还不知道明天可能是最后一天。我还在肆意地浪费着孤独,全然不知明天可能就在孤独的悬崖。
生命大都有特殊的感知能力,比如卸下落叶的枝条,比如控干水分的野草,比如佝偻身子的父亲最智慧。
北风阵阵,只为提醒,这场大雪之后,春天正走在来路上。
春天的希望是一枚嫩芽的蜕变
冬麦在大雪中褪下披挂。
看似熄灭的灯盏,恰恰是在保存火种,这春天的希望,的确需要一枚嫩芽蜕变。确实与人有相同之处。
蜕下恶意,他就成了一个家唯一的希望,太阳一样承载着所有的温暖。
我们是发小。冰雪的铁窗并未熄灭他心上的火焰,春风一吹,春天遍野烧着绿色火焰,冬麦一样。
他扛起生活的锄头,铲去留在泥土中的残冰,成就丰硕的秋天。不是遥远不可及,只需解开命运的绳索。
大雪后想起春天
的确应该想起。春风一声号令,万物争相复苏,成就春天的美丽。
的确应该感恩。多少雪花舍身,才让那些眼睛睁开来欣赏这美好的人间。
的确是如此的美好,花草重新装扮了母亲的家园。
相对于雪花的美,春天更为繁杂一些,虽然我知道雪花更为纯洁,更为清透,但多一种选择,就多一分希望。
朝着一种事实飞去,感恩母亲为我铺下的路,用生命换来,雪地一样平整,舍不得留下一个脚印。
可惜,想要长出翅膀,需要等冬雪融化,种子发芽。
春天来时,并不会那么巧合。
雪融时草芽纷纷举起挥别的手
穿过黑暗的甬道,钻出泥土的勇士,一试寒风,也探取新路。
不必辩驳,草芽是最初的春天。
正如我们是母亲的光明一样,也是她最初的惊喜,雪融时,母亲在人间的路也走到了尽头。
无论怎样,我们都要生活下去,为了母亲的付出。
再也没有像雪花爱人间一样的爱,落在我们头上。从此,未来的路,我们自己走。
举起手就是挥别,探出头就是新的世界。
顶在额头上还未化的雪,是母亲留在这人间最后的吻。
像一个警醒,未来的路必将泥泞。
若想突破命运,深根向下,抬头向上,把天空看成最后的疆场。
亲 人
狗蹄花儿举起来的天空。
与喇叭花举起来的天空有什么不同。都是春天的肯定者肯定春天,都是天空的梦想家梦想天空,都是村子的守护者守护村子。
粮食丰收的那些年,喇叭花攀援麦秸,甚至高过了粮食本身,养活人的五谷毫无怨言地任由它缠绕,任由它举着喇叭高喊:黄了就收咯。
这几年,田地荒芜了,喇叭花匍匐着,也不忘举起天空,晴朗也好,阴霾也罢。
父亲弯下腰身,狗蹄花挺起胸膛,三个从不离弃的亲人,在旷野上撑开越来越低的天空。
枯荣照旧,四季如常。
招 数
既然能开,一定有独特技能,每一种花开,都有不同的亮光照着人间。
花开没有套路,也没有定律可遵循。
麦子开花一串串,胡麻开花蓝茵茵,向日葵开花黄灿灿,它们活着,却要一种花开。
父亲的汗水,每一滴都是一份信仰。
悬在空中,就意味着接受了挑战。
不论孤独,不论艰难,父亲从未让一粒粮食失望过,也从未让任何一朵花失望过,即便一滴汗水,也得到了相应的肯定信任。
相信阳光一样,种子相信开花的汗水,也相信父亲的为人。
不可否认,在这方面,父亲有太多招数,让每一粒不同的想要开花的粮食饱满、丰硕。
而对我们这几株刺槐,他用尽了浑身招数,依然没法让我们长成獨有的风景。
苜蓿的立场
站起来,就是春天。
这多年生草本,没人见过它的根到底深入到哪里,能不能贯穿这蓝色星球,只有同它有着同样倔强性格的父亲最懂。
一生硬骨头就不必说话。苜蓿对抗干旱的方式太简单,长出嫩芽。父亲也有着同样简单的方式,直起腰身。
捍卫信仰的天空,一切多余的动作都显得毫无意义。
活下去,就是唯一的立场。
若是能绿了春天,若是能让田野生出一些想象,这深长的意味,最真实。
春天更懂生命的忠诚,在于不离不弃。
春风有意推开万物的心门
冰雪勒着万物的脖子太久,春风会结束这将要窒息的日子。
阳光稍微有点暖和,便觉得有了春天。
灿烂,有时候是一场春风,伸出手推开万物久闭的心门,正是冰雪献身的机会。
在北风大作的夜晚,突然有了一次错位的感觉,像一场错位的相认,像草木偏爱大火,像高粱偏爱浓霜,像耕种者偏爱双脚深埋泥土。
不必质疑,不必争辩。
在可见的世界里,冰霜最纯粹,春风最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