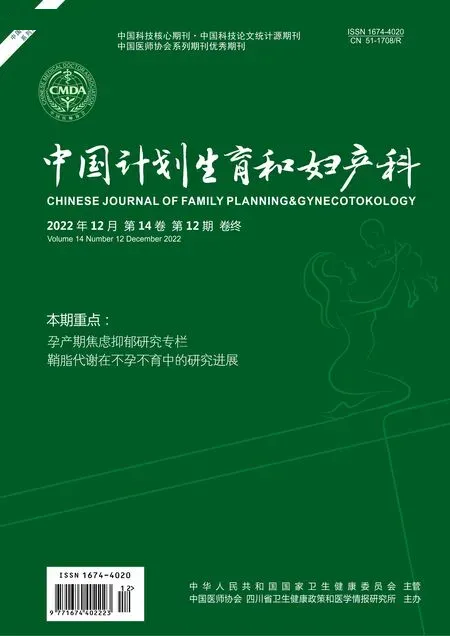产后抑郁的中医药治疗研究进展
孙国娟,李东霖,王学梅,谢萍
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PPD)又称为产褥期精神综合征,最早由Pitt B[1]于1968年提出,是指产妇在分娩之后出现的以情感持续低落为基础特征的一组临床表现,包括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障碍、精力下降、无价值感等,严重时甚至产生自杀念头。新生儿亦可能出现发育迟缓甚至可能在认知发展、社会情感发展和行为方面发生障碍[2]。PPD多于产后2周内发病,4~6周达到发病率高峰。不同国家的产后抑郁发生率各异,国外关于产后抑郁的一项系统性评价报道其发病率约在8%~26%[3]。我国发生率约为6.8%~23.6%,有研究表明这可能与传统生育观念及对科学孕育认知有偏差有关[4]。PPD严重影响产妇及新生儿的身心健康,鉴于目前临床上治疗轻中度产后抑郁最常用的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重度产后抑郁则主要采用药物治疗,包括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三环类抗抑郁药 (TCAs)、5-HT/NE 再摄取抑制剂 (SNRIs)等[5],但由于产妇的特殊生理因素及产后用药的诸多障碍,替代治疗的应用在临床上越来越广泛,中医药治疗产后抑郁具有独特的优势,现将其进展综述如下。
1 产后抑郁的中医认识
古医籍无“产后抑郁”病名记载,根据产后抑郁的临床表现,祖国医学将其归属于中医“郁证”“癫狂”等产后情志异常范畴[6]。与现代医学“产后抑郁症”定义相比,范围更为广泛。患者素体脾气虚弱,或气血不足,或肾阴不足,或肝气郁结,或瘀血内停,分娩过程中气血丢失,致气血亏虚、瘀血阻滞更甚;产后气血亏虚,血不养心,心神失养;产后气虚推动无力,血滞成瘀,瘀闭心窍;加之产后所愿未遂,或因家庭、社会、工作等因素重伤情志,发为本病。在大量古医籍的查阅中发现,数千年来,祖国医学对产后情志异常的临床表现、病因及治疗的记载丰富。如宋代医家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产后不语”“产后癫狂”“产后狂言谵语如有神灵”“产后乍见鬼神”等产后情志异常的临床表现。而针对产后抑郁的病因,《赤水玄珠》汇集明代以前诸家之粹,指出本病多因元气亏虚、心血不足、外邪所侵等原因所致。《陈素庵妇科补解·产后恍惚方论》也指出心血虚为本病的主要病因:“产后恍惚,由心血虚而惶惶无定也。心在方寸之中,有神守焉,失血则神不守舍,故恍惚无主,似惊非惊,似悸非悸,欲安而忽烦,欲静而反忧,甚或头旋目眩,坐卧不安……”历代医家强调由于产后特殊的生理状态,此期致病尤易而重。故清代著名中医大家傅山所著《傅青主女科》明确提出“凡病起于血气之衰,脾胃之虚,而产后尤甚”。综上,中医认为产后抑郁的病因病机多为素体气血不足,脾胃虚弱,加之产时失血耗气过多,气随血脱、阴血亏虚、心失濡养,气血瘀滞,因虚因瘀致郁。强调应重视产后将养调治。
2 产后抑郁的中医治疗
针对产后抑郁的中医治疗,古代医家记载丰富而详尽,主要针对病因及临床表现,辨证选方用药。宋代《陈素庵妇科补解·产后发狂方论》中指出:“产后发狂,其故有三:有因气虚心神失守,有因败血冲心,有因惊恐,遂致心神颠倒。其脉左寸浮而大,外症昏不知人,或歌呼骂詈,持刀杀人。因血虚者,辰砂石菖蒲散。败血冲心者,蒲黄黑荆芥散。因惊者,枣仁温胆汤。总以安神养血为主。”明代《万氏妇人科》表明:“心主血,去血太多,心神恍惚,睡眠不安,言语失度,如见鬼神,俗医不知以为邪祟,误人多矣。茯神散主之。”又指出“产后虚弱,败血停积,闭于心窍,神志不能明了,故多昏愦。又心气通于舌,心气闭则舌强不语也。七珍散主之。”清代《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论述:“产后血虚,心气不守,神志怯弱,故令惊悸,恍惚不宁也。宜用茯神散,其方乃人参,黄芪,熟地,白芍,桂心,茯神,琥珀,龙齿,当归,牛膝也。若因忧愁思虑,伤心脾者,宜归脾汤加朱砂、龙齿治之。”现代医家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创新,强调补虚化瘀,并进行深入的基础及临床研究,以印证古代医家治疗方药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为产后抑郁中医治疗的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了客观依据。现将历代医家对产后抑郁的研究及治疗进展总结如下。
3 中医内治法
3.1 气虚血瘀证治以补虚化瘀
金元医家朱丹溪认为:“产后无得令虚,当大补气血为先。虽有杂证,以末治之。”首提“产后多虚说”,而后明清医家在理论上不断完善,总结出产后“多虚多瘀”,基本奠定了中医对产后疾病的认识。在产后抑郁一病中,气血亏虚为本,瘀血阻滞为标,认为气虚血瘀是产后抑郁发病的关键病机,因而治疗时首重益气养血,活血化瘀。
基于产后抑郁的这一特殊生理特点和发病机制,成都中医药大学谢萍教授研究团队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了“补虚化瘀”的治疗方法,创制了“参归仁合剂”用于产后抑郁的治疗[7-8],开展了一系列临床研究,证实了其临床疗效,并进一步探索其治疗产后抑郁的分子机制。研究团队对108例产后抑郁患者进行临床研究,发现参归仁合剂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分,并改善患者产后抑郁中医证候[9]。郑利茶[10]、呼改琴等[11]也先后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临床研究证实了参归仁合剂的临床疗效。此后,多位学者运用参归仁合剂对补虚化瘀法治疗产后抑郁的分子机制进行了探索,先后证实了参归仁合剂可通过提高额叶p-CREB、p-ERK1/2蛋白表达水平[12-13]、诱导ERα、ERβ、BDNF、TrkB、RSK1、MEK1等基因表达上调[14-18]、调控ERK1/2信号通路[19-20]等方式改善产后抑郁模型大鼠的抑郁样行为。此外,参归仁合剂还可通过对PI3K通路的调节改善产后抑郁模型大鼠海马DG区神经元的数量、形态和凋亡情况[21]。从临床和基础研究证实了补虚化瘀法治疗产后抑郁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分子机制。
3.2 脾虚肝郁证治以疏肝理脾
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司条达,肝气之郁滞与郁证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在朱丹溪之“六郁”论中首重气郁,而气郁多因肝失疏泄,如《医贯》所云:“凡郁皆肝病也。”《太平圣惠方》言:“夫思虑烦多则损心,心虚故邪乘之。”《医宗金鉴》中则有“产后血虚,心气不守,神志怯弱,故令惊悸,恍惚不宁也”的论述。心主神明,统属五脏,心在情志疾病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而脾统血、肝藏血,肝、脾二脏在气血运行中均起着重要作用,联系紧密。《景岳全书》载:“思则气结,结于心而伤于脾也……”由此可见脾在郁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史亚飞等[22]的研究初步探讨了肝失疏泄与精神障碍类疾病,尤其是抑郁等疾病的密切关系,为从肝论治郁证提供了新的依据。杨欣文等[23]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心、肝二脏在产后抑郁中的重要地位,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许芳[24]、丁渊等[25]均认为“脾虚肝郁、心神失养”是产后抑郁发病的关键病机,而许琳洁等[26]通过对产后抑郁中医证型的总结,同样发现心、肝、脾的气血阴阳失调是产后抑郁发病的重要环节。
越鞠丸具有疏肝理脾、调畅气机之用,可解“六郁”;甘麦大枣汤功擅养心安神,和中缓急,可治妇人脏躁。此二方为文献报道临床上治疗产后抑郁的常用方剂,两方合用,则可从心、肝、脾三脏治疗产后抑郁。夏宝妹等[27]对越鞠甘麦大枣汤(越鞠丸、甘麦大枣汤合方)进行了动物试验,其研究结果显示越鞠甘麦大枣汤表现出与西药氯胺酮一致的快速抗抑郁作用。随后,该团队继续对越鞠甘麦大枣汤治疗产后抑郁的分子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越鞠甘麦大枣汤可以改善Balb/c母鼠的产后抑郁样症状,其作用可能与下调海马Akt/mTOR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28-29]、激活前额叶BDNF-TrkB通路[30]、上调海马SIRT1-ERK1/2信号通路[31]有关。此外,他们还发现产后抑郁小鼠的子代小鼠更容易表现出抑郁行为[32],而越鞠甘麦大枣汤同样可以通过对Akt/mTOR信号通路的调控来改善其抑郁症状[33]。
逍遥丸具有疏肝解郁,健脾养血的功效。在治疗PPD的现代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文献报道临床疗效肯定。许琳洁等[34]对1996~2016年中医治疗PPD临床研究文献的方药规律进行探究,发现逍遥散出现频次最高,占比15.49%。高耀等[35]研究发现逍遥散抗抑郁代谢表型包含97个代谢物和48条通路;逍遥散可以在转录层次调节106个基因,在蛋白层次调节11个蛋白发挥抗抑郁作用。转录组学和蛋白组学整合分析发现逍遥散通过调节CUMS抑郁大鼠氧化磷酸化通路、谷氨酸能突触通路发挥抗抑郁作用。其中6-姜酚、芍药苷、阿魏酸、藁本内酯、柴胡皂苷a、柴胡皂苷c和甘草素,这7个活性成分可能通过调节谷氨酸能突触通路发挥抗抑郁作用。
王敦建等[36]采用加味疏肝解郁汤(百合、生地、桃仁、红花、合欢皮、香附、川芎、茯苓、郁金、白芍、当归、柴胡) 联合醒脑开窍针法联合抗抑郁剂治疗与单用抗抑郁剂比较,均可有效缓解患者抑郁症状,且可降低疾病复发率,安全性较高。张翔昱等[37]对产后抑郁患者加用解郁安神汤作为观察组,结果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HAMD、EPDS、PSQI评分改善显著,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得出结论:解郁安神汤辅治产后抑郁肝气郁结证可提高临床疗效。王含彦等[38]研究表明舒肝解郁胶囊可能通过调节ERK1/2通路增加BDNF mRNA表达从而发挥改善抑郁症状的作用。一项纳入3项随机临床试验(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RCT)的研究显示单用舒肝解郁胶囊治疗6周对比SSRI类抗抑郁药治疗产后轻中度抑郁在降低HAMD评分上相当;舒肝解郁胶囊[39]治疗轻中度抑郁障碍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中指出其治疗轻中度产后抑郁证据级别: D;推荐强度为强推荐。
3.3 心脾两虚证治以补益心脾
中医认为,心主血脉,脾既是气机之枢纽,又是后天生化之源,心脾二脏是气血运行的关键所在,故心脾两虚常导致气血之亏虚,心神失养、脑神失司,从而引发产后抑郁。
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基于自评量表的研究报告相继出现,认为治疗PPD“支持性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均属必须”,特别提到可辅以归脾丸等中药治疗。崔艳超等[40]研究表明归脾汤对产后抑郁模型大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相关激素及 5-羟色胺具有调节作用,从而改善产后抑郁症状。唐启盛教授认为气血亏虚,瘀浊闭阻,脑神失司是产后抑郁的关键病机,因此提出了“补益心脾法”,并拟定“参芪解郁方”(黄芪、党参、酸枣仁、郁金、陈皮等)用以治疗产后抑郁。王丹等[41-43]先后进行了多次临床试验,证实了参芪解郁方对产后抑郁的临床疗效,能够改善产后抑郁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和EPDS评分,降低血清孕酮水平并提升血清雌二醇水平。有关参芪解郁方治疗产后抑郁的动物试验也在不断开展,证实了参芪解郁方能够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相关激素水平、脑内ER表达及单胺递质与代谢产物含量改善模型大鼠的抑郁样行为[44-47],同时可以促进产后抑郁模型大鼠脑组织病理损伤的恢复[48]。此后的研究还发现其抗产后抑郁作用与调控Treg/Th17的失衡状态[49-50]、提升脑内5-HT、NE含量[51]、改善脑前额皮质和海马DA的功能并调节DOPAC的紊乱失衡状态及D2R表达障碍[52]、调节Th1/Th2的失衡状态[53]等机制有关,并能够修复模型大鼠受损神经元,促进神经重塑,调节谷氨酸能系统及膜磷脂代谢,从而对产后抑郁发挥治疗作用[54]。
3.4 肾虚肝郁证治以益肾调气
《灵枢·本神》言:“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肾盛怒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言。”初步论述了“肾藏志”在情志疾病中的重要性。而肾所藏之真阴为一身阴精之根本,肾阴亏虚,一则不能滋养肝木,易致肝失疏泄,二则不能上济心火,易致心火亢盛,如此则情志失调。近年来,从肾虚肝郁论治产后抑郁逐渐受到重视,汪金涛[55]认为从肾虚肝郁论治是产后抑郁治疗的重要方向,付雨等[56]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唐启盛教授[57]在科研和临床工作中发现肾虚肝郁是产后抑郁症常见的病理因素,由此提出了“益肾补虚,调气安神”的治疗大法,命名为“益肾调气法”,并拟定了颐脑解郁方(刺五加、郁金、栀子等)。许芳等[58]基于益肾调气法的理论,运用颐脑解郁方联合针灸治疗产后抑郁,结果显示该治疗方法能够调节血清雌二醇和孕酮水平,改善产后抑郁患者的中医证候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分。吕凯等[58]则使用颐脑解郁方对产后抑郁大鼠模型进行干预,并与氟西汀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该方对产后抑郁大鼠模型表现出了明显的抗抑郁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调节海马5-HT、5-HT1AR的表达有关。
4 中医特色治疗方法
4.1 针刺及耳穴治疗
《医旨绪余》云:“夫人身之有任督,犹天地之有子午也。人身之任督,以腹背言,天地之子午;以南北言,可以分,可以合者也。分之以见阴阳之不杂,合之以见浑沦之无间,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任主阴精而督主阳气,阴精引导阳气下潜,阳气促进阴精上承,阳降阴升,循环灌注,水火既济。任督二脉气血不畅,则一身阴阳均流转不畅,脏腑阴阳由此失衡,阴盛阳衰则萎靡低落,阳盛阴衰则烦躁易怒,因此任督二脉不调在情志疾病的发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杨卓欣教授通过对其临床和科研经验的总结,创立了“调任通督法”,以阴阳调和为主要原则,强调补益及调理气血,临床治疗采用辨证选穴,通过对任督二脉的平衡性进行协调,疏经通络以及补虚泻实,以实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苏苇等[60]通过临床研究发现调任通督法能够影响产后抑郁患者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简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的评分,并提高患者血清花生四烯酸、二十碳五烯酸、二十碳六烯酸水平,降低血清维生素D、雌二醇和孕激素水平。杨育林[61]的研究则显示调任通督法的抗抑郁作用可能和调节肠道菌群,增加益生菌丰度有关。此后闫兵等[62]的真实世界研究则发现调任通督法对产后抑郁的疗效与疗程密切相关。
曹悦等[63]纳入13个RCTs,包括899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手针治疗与盐酸氟西汀在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临床有效率、临床痊愈率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P<0.05)。手针与心理治疗在患者临床有效率和痊愈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刘思聪等[64]、苏谨程等[65]对针灸治疗产后抑郁进行了理论探析、疗效研究和选穴规律研究,认为针刺治疗产后抑郁的可能机制是针刺可调节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激素生成,调节血浆中E2的含量,也可能与针刺可通过提高外周5-HT和NE水平等单胺类物质的释放和代谢达到抗抑郁作用有关。袁坤等[66]在通过使用耳穴治疗PPD患者研究中发现,耳穴干预能明显改善产后抑郁患者生活质量,可能机制在于耳廓内有迷走神经耳支分布,舌咽-迷走神经感觉纤维分布区域对应耳甲部的内脏反射区,通过刺激耳穴相应部位来调理相应内脏功能。
4.2 五行音乐疗法
音乐疗法(music therapy)指音乐治疗师、护士、医生、言语治疗师等利用音乐体验的各种形式,制订音乐治疗计划以促进患者康复。黄帝内经《灵枢·邪客》篇五行音乐疗法的记载:“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欧阳修在《送杨寘序》中言:“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记述了自己习琴治疗抑郁。五行音乐疗法是基于中医基础理论,在阴阳五行生克上根据宫、商、角、徵、羽等音调与肝、心、脾、肺、肾五脏及怒、喜、思、悲、恐五志对应关系进行辨证选乐,在情志类疾病的干预中多有应用。韦求艳等[67]、孙静怡等[68]、汪成书等[69]均对五行音乐疗法治疗产后抑郁进行了研究,表明了五行音乐疗法治疗产后抑郁的有效性,且研究指出中医五行音乐疗法治疗产后抑郁在降低HAMD、EPDS评分,改善5-羟色胺、孤啡肽、E2水平,提高总有效率等方面优于对照组。
4.3 情志疗法
传统中医学中常用的心理疗法包括情志相胜疗法、移精变气疗法、顺情随缘疗法、言语开导疗法、暗示疗法等[70]。中医情志干预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情志干预改善患者不良情绪,达到治疗疾病目的。五志与五脏相对应,根据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实施情志疗法治疗情志疾病,例如“思胜恐(土克水),怒胜思(木克土),哀胜怒(金克木),喜胜哀(火克金),恐胜喜(水克火)”。符艳艳等[71]、邓琼涛等[72]予情志相胜法、移情易性法、调神养心法干预产后抑郁,在提高产后抑郁总有效率方面优于对照组。
4.4 综合治疗
产后抑郁患者不仅表现为情绪抑郁,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躯体症状,治疗时应采取心身同治法。朱淳等[73]将采取情志疗法结合穴位按摩干预的产妇纳入观察组,认为情志疗法结合穴位按摩能够有效改善产妇产后心理状况,减少患者产后抑郁的风险,提升生活质量,对产妇的身心健康都能起到积极影响。曾博等[74]将产后抑郁患者在西医治疗基础上联合中医治疗(针灸、中药汤剂解郁安神汤、穴位按摩)。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有效改善机体性激素水平及血清Hcy、5-HT水平,减轻产后轻抑郁程度。高可新等[75]研究“自拟益气养血安神方”联合“三步推拿法”能有效降低心脾两虚型产后抑郁患者的抑郁程度,且不良反应较小,安全性较高。唐顺姣等[76]将产后焦虑及抑郁症倾向的产妇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对照心理疗法,给予常规的心理干预及心理疏导,观察组采用坤泰胶囊联合认知行为疗法,研究结果显示产后焦虑及抑郁患者采用坤泰胶囊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改善患者焦虑及抑郁情绪。
综上,产后抑郁的中医治疗,主要有有补虚化瘀法、疏肝理脾养心法、补益心脾法、益肾调气法等。中药内服配合中医外治法可增强疗效。
5 展望
产后抑郁因其增加产后母婴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涉及多学科相互协同,需要加强临床医生对产后抑郁的早期认识和判断。既往有过产后抑郁症病史的妇女再次妊娠时,其发生产后抑郁的可能性会较前升高,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临床医生应更加重视并加强防范。
中医药治疗产后抑郁在中医基础理论整体观思想指导下辨证选药,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内服中药与外治法相结合,在产后这一特殊时期、特殊人群的使用中具有特色优势。我们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产后抑郁的中医药基础及临床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中医药治疗产后抑郁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雌激素介导的ERK及PI3K通路发挥抗抑郁作用,为产后抑郁的中医药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相信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治疗方式的不断完善,产后抑郁的中医治疗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为保护母婴安全和健康,维护家庭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