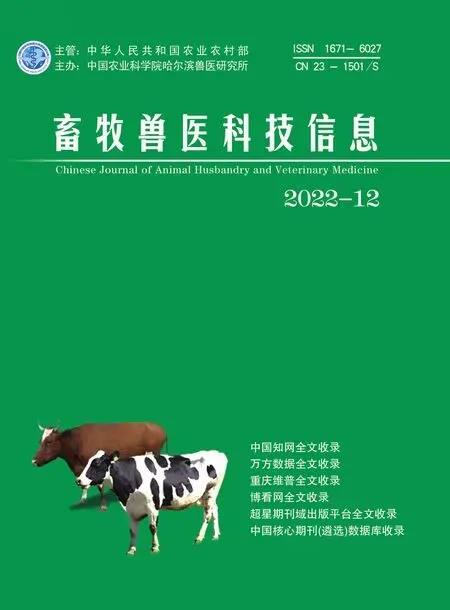非洲猪瘟疫苗的研究进展
鄂秋煦,杨婧怡
(沈阳工学院生命工程学院,辽宁 抚顺 113122)
非洲猪瘟(ASF)的病原是非洲猪瘟病毒(ASFV),该病是严重影响家猪与野猪的出血、热性高度致死性传染病,ASF 的流行对全球养猪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市场贸易与流动性,导致ASFV 很容易在家猪之间传播。ASF 严重威胁猪的健康、食品安全、国民经济和生产环境。考虑到目前还没有理想的治疗手段和有效疫苗,ASF 控制主要基于严格的卫生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减少接触感染动物的数量和限制出口,但这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可以说ASF 是目前全球养猪业面临的最大威胁。
1 非洲猪瘟病毒与疫苗研究背景
ASFV 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双链线性DNA 病毒,基因组的大小约为170~190kb。ASFV 可编码约200种蛋白质,其中近1/3 为结构蛋白,重要的结构蛋白p30、p54、p72 等是当前研究的热点。ASFV 主要对单核细胞与巨噬细胞形成威胁,其中病毒对巨噬细胞功能的调节对致病与免疫逃避机制方面尤为重要。ASFV 根据毒力的强弱可分为高致病性、中致病性、低致病性和无症状感染毒株。临床上遇到的ASF 病例大多数来自高致病性病毒的感染,高发病率与高死亡率是其典型的特点。ASFV 是一种重要的跨界病原体,从东欧传播到亚洲,进而增加了对其他养猪生产中心的风险。特别是从2018 年8 月从辽宁省沈阳市传入后,ASF 开始在中国多个省份流行,为了防控该病,截至目前已经屠宰超过百万头猪。
虽然非洲猪瘟病毒早在上世纪初就被发现,但是对于非洲猪瘟的疫苗研究却落后了近半个世纪,这可能与ASFV 庞大且复杂的基因组所带来的明显的遗传多样性有关联。到目前为止,宿主保护性反应的机制还未完全确定,保护性抗原也有待确定,这对非洲猪瘟疫苗的深入研究形成阻力。缺乏针对ASF 的有效治疗或疫苗使得国内国际ASF 的防控变得复杂。而一直以来关于ASF 疫苗研究从未间断,研制出适合猪免疫的疫苗是疫苗研发的重点,目前在科研人员不间断的努力下,一些试验性的疫苗开始表现出效果。此外,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将目光锁定在蜱用疫苗的研制上,目的是切断软蜱造成的ASFV 感染。关于非洲猪瘟的疫苗研究大体上可分为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基因工程疫苗,其中基因工程疫苗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具体又可分为基因缺失疫苗、亚单位疫苗、DNA 疫苗等。
2 非洲猪瘟灭活疫苗
灭活ASF 疫苗是研究较早的疫苗,开始于20世纪60 年代,但大量的研究表明灭活ASFV 作为疫苗基本上是不可行的策略。灭活疫苗虽具有抗原性,但缺乏刺激机体产生完整细胞免疫反应的能力,这可能是灭活疫苗无法提供免疫保护的原因之一。
3 非洲猪瘟减毒活疫苗
连续传代减毒的ASFV 可诱导针对亲本毒株的保护性免疫应答。20 世纪60 年代,减毒株开始研究,但由于ASF 的慢性感染症状而被放弃,这种症状广泛出现在接种疫苗的猪身上。在后续研究中,接种ASFV 自然减毒株NH/P68 的猪对毒力株ASFV L60 具有耐药性,而NK 细胞活性增加,表明NK细胞活性与ASFV 的保护性免疫成正相关。此外,接种自然减毒毒株OURT88/3 可诱导交叉保护性免疫,以抵抗非同源ASFV 毒株的攻击,这与接种猪淋巴细胞分泌IFN-γ 的能力有关。同样也提示了ASFV 活疫苗免疫的特殊性。
4 非洲猪瘟基因工程疫苗
大多数疫苗在接种后能够抵抗同源亲本毒株的攻击。但也有部分接种过疫苗的猪产生一定的病毒血症和副作用。因此,基因缺失疫苗仍有一些不确定性值得考虑。不同毒株中相同的基因缺失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结果,原因在于对ASFV 的抑制和保护作用可能取决于毒株。2016 年,O” Donnell 团队在ASFV Georgia 2007/1 的基础上进一步删除了MGF360/505-△9GL,虽然删除的菌株高度减毒,但对同源毒株的感染没有保护作用,当Ramirez Medina 等人同时删除Georgia/2007 菌株的9GL、UK 和NL 基因时,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目前,对有关机制的探索还远远不够,研究人员还需在进一步的工作中优化可删除的基因组合,以填补相关毒力或免疫逃逸基因研究的空白。
绝大部分没有ASFV 相关毒力基因的基因缺失疫苗可以提供完全保护,且由于剩余毒力的存在,容易引起毒力恢复的潜在风险。近期的研究表明,通过删除中国HLJ/2018 菌株的多基因家族MGF360/505 的6 个基因获得的减毒菌株HLJ/18-6 GD 可以保护猪免受亲本毒株的攻击。但是进一步的评估数据表明,该疫苗可能存在形成强毒株的高风险。该研究团队的最新的实验表明,将CD2v 基因删除而设计的HLJ/-18-7GD 浮出水面,目的是最大限度消除前述所带风险,并提供足够的保护。
当前,以亚单位疫苗等为代表的ASF 基因工程疫苗,在围绕副作用以及安全性方面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一些ASFV 蛋白(p30、p54、p72、CD2v、pp62 等)是ASF 疫苗研究在主要靶点的热门选择。Gomez-Puertas 等人发现病毒重要的结构蛋白p72、p54 和p30 等在中和抗体中起到关键作用,其中的原因在于p72 与p54 可抑制病毒吸附,而p72和p30 可激活细胞毒性T 淋巴细胞(CTL)反应,研究人员利用表达ASFV p30 和p54 的重组杆状病毒对猪进行疫苗接种,可刺激机体产生中和抗体,对ASFV-E75 株具有一定的免疫保护作用。随后,重组杆状病毒表达的嵌合蛋白p54/30 接种猪也发生了类似的结果。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那就是中和抗体对以上蛋白在抗体介导的保护方面并不完全。因此,这也引起了人们对p30、p54和p72 在免疫保护中的相关性的怀疑。
同时DNA 蛋白免疫可能有助于识别病毒抗原特异性应答,这可以为开发更高效、更安全的ASFV亚单位疫苗提供更多潜在信息。2019 年,ASFV 重组蛋白(p15、p35、p30、p54、CD2v-E)与pcDNA3 的结合。选择编码ASFV 基因(CD2v、p30、p72、CP312R)的猪,用ISA25 佐剂免疫猪。结果表明,接种ASFV DNA+蛋白的猪可以激活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其中p72 是IFN-γ 的主要诱导剂。在目前的研究中,特异性ASFV 蛋白和编码ASFV 基因的pcDNAs 之间协同作用的机制尚不清楚,并且pcDNAs 可能触发一些非特异性免疫反应,从而增强对这些蛋白的特异性反应。影响免疫介导的ASFV 感染和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抗体依赖性增强(ADE)影响中和抗体的产生。
近年来,为了能够在抗体与细胞介导的ASFV免疫反应中间达到均衡,对猪进行了复合ASFV 抗原制剂的免疫接种。2017 年,Lopera Madrid 等人发现,接种HEK 293 纯化重组ASFV 蛋白(p72、p54、p12)可促进ASFV 特异性抗体的产生,但并没有增强细胞免疫。然而用改良痘苗病毒Ankara(MVA)载体抗原(p72、EP153R 和CD2v)增强免疫可补充前者,并通过细胞免疫促进IFN-γ 的产生。在DNA疫苗的基础上,提出了DNA 原代和重组痘苗病毒(V ACV)增强策略,以使编码抗原定向到特定的抗原表达途径,以增强对保护反应的诱导,并广泛应用于ASFV 的免疫原性和潜在的保护性抗原的筛选。Jancovich 等人在2018 年通过筛选47 个病毒基因,鉴定出一个ASFV 抗原的亚群,包括p30、p72 和D117L,通过筛选47 个病毒基因,可以有效地刺激体液和细胞免疫。尽管接种猪血液和淋巴组织中的病毒负荷显著下降,但所有接种过疫苗的猪都出现急性ASF,并观察到更严重的临床和病理征象。
5 总 结
ASFV 的传播迅速,养殖形式的多元化与密度高、养殖人员缺乏足够的生物安全意识,诸多原因使我国ASF 整体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由于目前还没有商用疫苗,国内的ASF 防控在很大程度上还需依靠严格的生物安全体系。基于前述ASF 疫苗研究现状分析,利用ASFV 毒力基因敲除减毒株开发的重组疫苗作为未来中短期候选疫苗具有比较乐观的前景。ASF 基因工程疫苗也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些疫苗是否能实现对致命ASFV 株起到完全的免疫保护。保护性潜力的抗原是需要发现和深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