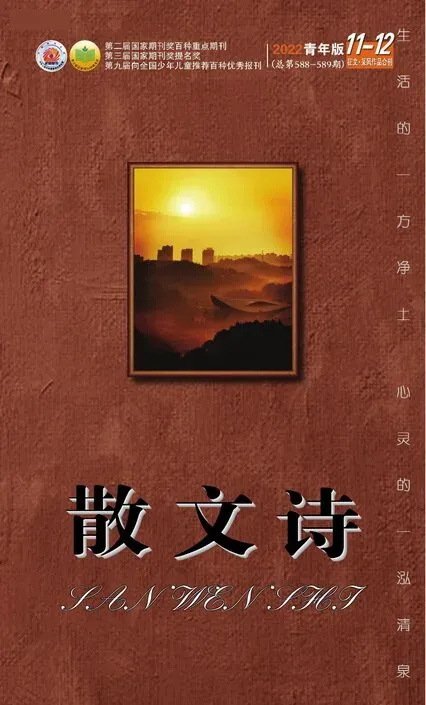益阳采风四题
蒋立波
塔吊司机
从洞庭湖洲岛渔夫,到渔民新村建筑工地的
一名塔吊司机,这身份的变换足够让人惊讶
或许他仍然是在垂钓,区别仅仅在于
以前他痴迷于从一片熟悉的水域
捕获那些莽撞的鱼虾,而现在
他凭借一支吊臂,钓起砖块、水泥和钢筋
那些沉重而坚硬的事物,通过他而到达
与云朵平起平坐的位置,如同方言中艰涩的
词和发音,通过力矩原理绷紧的公式
转译给浙江诗人王自亮和余刚
或许他仍需要面对深渊,但他已熟谙于一种
举重若轻的技艺,那从鱼肚白里获取的
新的一天的启示录,那无边的现实主义
从此在他和世界之间,他可以使用一种新的语言
进行交谈,他和那些庞然大物之间
获得了一种有力的对称,他仍然是卑微的
但他欣喜于每天可以将一轮旭日垂钓
清溪田野音乐诗会
穿过一片荷塘,去看一个人的故居
我们通过入口,接受一道慈祥目光的扫码
一支测温枪伸过来,仿佛历史仍在低烧
这里是立波清溪书屋,书架上的书可随意取阅
概不出售,就像乡村的虫鸣和星光
也不标价,我在幼年时读过其中的两本
里面的内容我都忘了,只依稀记得暴风、骤雨
阶级、土地,这些曾经激烈的词汇
在今夜的琴弓下变得安静,“干旱的月亮
扑向泥土深处沉睡的人民”。事实上
只有墙上挂着的笠帽与一穗稻粱,还能证明
他曾在这里居住,他曾用此地的俚语写下
一种陌生的叙事,那过于浓重的湘语发音
一种失传的现实主义,像嘹亮的朗诵
在耳膜里形成的嗡鸣。荷塘里的淤泥
沉默,藕孔的音箱,回响经过改造的口型
在舞台下我再次和他笔下的人物相逢
他的乡亲,那些在复数里隐身的人民
因此对于无处不在的彼此混淆与偶然的
重名,我的探究,常常显得徒劳
注:2022 年9 月28 日晚,由散文诗杂志社与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人社情 人民心” 清溪田野音乐诗会,在作家周立波故乡清溪村的立波清溪书屋前坪举行。
去高新区的路上
从人社局乘大巴去高新区,中间有一小段
司机走的是一条小路,轻微的颠簸
在手机上震出一串乱码,这不可破译
适度的荒僻,恰好暗合这些做白日梦的诗人
梦同样不可破译,包括梦中掠过的那些
云朵,旗帜,村庄,稻田,栎树
电子元件厂,礼花加工作坊,寿材行
车辙一根筋,孩子们跳的是另一根
橡皮筋:他们跳得比自己还要高
这条短短几公里的小路边,我同时遇到
一场婚礼和一场丧事,就像同一根枝条上
喜鹊和乌鸦相安无事,鸟类的立法院
不妨吵翻天,唯生死可让它们达成共识
冷气吹得诗人们昏昏欲睡,无人留意
刚收割过的稻田,新鲜的稻茬上
镰刀细齿的牙印。小路尽头是数字产业园
流水线上,是同一双握过镰刀的手
熟练地装配着政府最新绘制的图纸
那密集、无名的芯片,电流疾驰的电路
在资江边散步
跟其他地方没有两样,需要绕过妖娆广场舞
高分贝舞曲,眩目的霓虹,才能找到
一座矮小的塔,和它深埋在淤泥里的倒影
那些磨损的膝盖,游荡的幽灵
找到禁渔期的鲟鱼,它微微上翘的嘴
“一颗行星的尖脸?” 或许。但无疑已经错失
一种小小的傲慢与反讽,波纹般织出的
细密鱼鳞,隐秘的刺,喉音里拔出的欸乃
需要绕过高新区新栽的行道树,佳宁娜酒店
不放假的喷泉,腥甜舌尖弹出的方言
才能找到江边滩涂上醉酒的打工妹
她的抽泣,她呕出的食物,幸福的胆汁
像一条禁欲的江,在我们关于文明与野蛮
现代与前现代的争论中,悄然降下水位
它压低我们的音量,压低吹过城垛的风声
如餐桌上为我们减去的一个省的辣度
或许仍汹涌,而航标灯给出的航道
已悄然改变,语速里的一个浪,罔顾险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