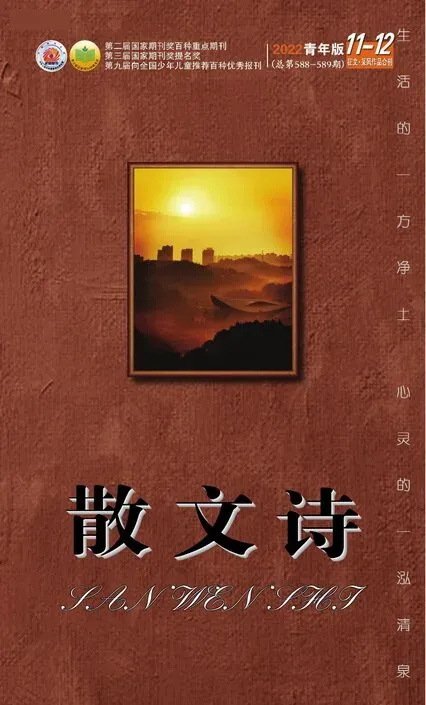写给父亲的散文诗
2022-02-25 06:29:01肖柴胡
散文诗 2022年22期
肖柴胡
在隧道里
太阳给予皮肤黑色,高山给予隧道黑色,父亲,你把你给予黑色——头上戴着一颗明亮的灯。
在蜀地的日子,会遇见李白吗?
在隧道,会遇见过世的爷爷吗?
你从不考虑那些与日子关系不大的事。将黑色的皮肤、花白的头发,融入至更深层次的黑;而这种黑,比深绿色的高山,更沉稳,只有沿着铁轨,才能抵达……
只有抵达隧道,才能抵达高山的心,这里冬暖夏凉,这里昼夜不分。
在隧道里看隧道外,火车从白色的光的那边驶过来,隧道上的裂缝,需要去补,像女娲,补天。
在工地上
父亲,母亲不懂你,儿子也不懂你,只有泥土懂你。
父亲,在红土上耕耘,在混凝土上砌墙;让玉米比你高,让砖头比你宽。
半辈子与泥土打交道,只有泥土懂你的沉默和汗水。
你说,你从泥土中来,也会回到泥土中去。
父亲,铁铲在你的手中那么温顺,扬起的河沙,从铁网中,筛出碎石和凄白的贝壳,这是一个需要动用听觉的过程。
你听,你筛出了,除沙与铁网撞击以外的声音。
水泥搅动,如此顺滑——
这深蓝色的丝绸,顺得那么凝滞,滑得那么厚重。
这深蓝色的丝绸,从早穿到晚。父亲,你的脚下,铺着一整块蓝天。
在火车上
从小辍学的你,知识来自大地、河流、竹林,经验来自厚茧。半辈子,坐着绿皮火车到西双版纳,到广州,又到松潘,你走成了一个南方地理学老师。
后来,坐着高铁,遗忘的速度越来越难把握,你贴近铁轨,贴近橡胶树,贴近水泥和砖块,贴近油漆厂——
疏远故乡,和我。
电话里,我听到了你的愧疚,也听到了你的衰老。
在那些无力的话语和额头上渐深的皱纹面前,我们——
一双手稚嫩;
一双手苍老。
猜你喜欢
英语文摘(2019年1期)2019-03-21 07:44:18
人大建设(2018年9期)2018-11-13 01:10:06
风采童装(2018年1期)2018-04-12 02:05:06
小学阅读指南·低年级版(2017年1期)2017-03-13 20:10:52
风采童装(2016年1期)2016-12-25 11:54:30
文学港(2016年7期)2016-07-06 15:26:46
英语学习(2016年6期)2016-05-14 16:16:16
Coco薇(2015年12期)2015-12-10 02:45:28
小资CHIC!ELEGANCE(2014年9期)2015-03-16 09:44:18
儿童时代·幸福宝宝(2012年5期)2012-08-21 02:5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