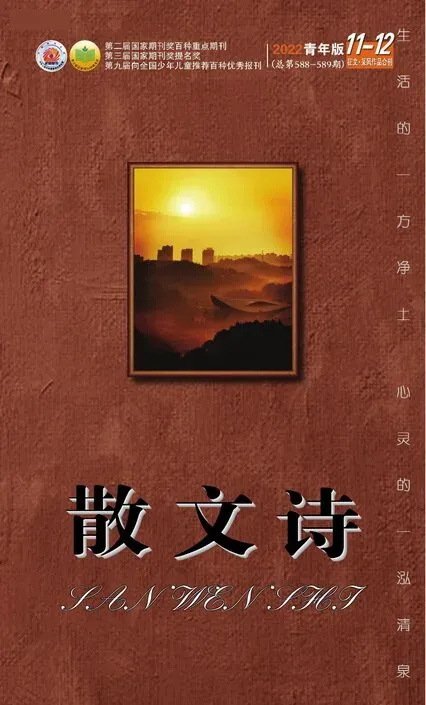给亲人书
金小杰
种光的父亲
他们用安抚完大地的双手,安抚着城市。
房前摇曳的野花,深秋挂霜的黄柿,牛棚里绵长低沉的哞叫,几件与水纠缠过上千次的旧衣裳,打包成了他们离乡后扛在肩上的四季。
工地里,他们用刮板,把图纸上的砖瓦,归位。建楼和栽树一样,一点一滴地,耐着性子与时间对峙。
烈阳下,他们爬上脚手架,爬上塔吊,像当年爬上自家门前的苹果树,轻车熟路。
阳光不遗余力地照下来,和水泥的父亲想起夏末院子里挖的地窖,土壤新鲜,几条圆滚滚的蚯蚓沾了满身潮湿的土粒。
捆扎钢筋的父亲弯着腰,捆得久了,手里的钢筋就变成家乡的麦穗,沉甸甸,带着太阳烫手的炽热。
搭架子的父亲固定好每一根钢管,很多年前的夏天,他就是这样搭建好门前小院的扁豆架。
卖力气的父亲们站在工地,高楼在他们身后长成森林。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方方正正,是他们开辟的一块又一块的农田、果园。他们用尽气力在每个窗口都埋下一粒光,黑暗里,这些光长成了万家灯火。
汲水的母亲
到处都能见到她们,饭店、工地、超市……离乡前,她们的身后往往有个小孩子,花苞一样,长在身上。一步三回首,对于故乡,她们有着更深的挂念。
一切都在生长,树影变短,又变长了几次。
城市里,做家政的母亲哄睡了一个孩子,却哄睡不了留守老家的另一个孩子。山重路远,每一次想念,都开成老屋窗外的石榴花,夜风坐上花枝,摇曳的侧影印上窗户,也能逗笑未满周岁的孩子。
农贸市场,母亲与母亲碰面,摊位上摆出凌晨两三点摘的西红柿,摆出头顶嫩花带刺的黄瓜,摆出起早贪黑浑身上下火辣的酸疼。碰面,聊几句家乡话,故乡就回到了脚下。
她们都是在城市里汲水的母亲,一遍遍地,打水。比闻鸡起舞更早,汲水的铁桶撞响井沿,几千年前的乡村醒了,几千年后的城市,也醒了。
摆渡的兄弟
很多城市都没有船,车便成了船。戴上头盔,紧了紧配送箱的带子,手机就成了地图。从一家店到另一家店,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战斗。
停不下来了,配送箱里装着的,可能是一家三口晚餐的果蔬配菜,可能是某位老人速心救急的药丸,可能是年轻人之间的一场浪漫……没有帆,但风是最好的伙伴。月亮爬过高楼,电动车立在旁边,这短暂的靠岸,水壶和饼干藏匿着另一弯月亮。给饥渴以琼汁,给病痛以药石,给期待以答案,我撑船摆渡的兄弟,在城市的河流中,穿梭往返。偶尔,有夜鸟惊飞,打翻了配送箱深处的秘密:成家立业,是他出发的原因;扇枕温衾,也可能成为他终生的遗憾。这简单的配送箱,装着他的生计,也装得下整座城市的沸腾。
拨通号码,一根缆绳在月光下出现。电话的两头,一头劝返,一头苦苦坚持。家乡的风顺着缆绳吹拂,撩拨着耳朵里的荠荠菜、蚂蚱花齐刷刷地长高。这条月光下横于河面上的船,一边渡着万物,一边渡着自己。远处,矮小的码头,在等着船,靠岸。
熬夜的姐姐
离乡前,姐姐们挽起长发,像是挽起一截柔软的月光,这一挽,还挽起了山涧的叮咚,满坡的野花。
进厂,套上灰蓝色的工服,走进灰白色的车间。噪声,击得人往后退了三退。一些刚来的姐姐,会把绣花小褂穿在里面,会把阿哥送的银项链捂在胸前。流水线前站了三天,已经被月亮眷顾。深夜的窗口,姐姐们站成了另一道生产线,机器飞转,产品在传送带上排列得整齐。家乡山川的轮廓,在梳棉机的运转中,纺织成线。敲敲打打,每一片电子元件里,都藏上几抹青绿。一想到这些苦撑苦熬的夜晚,便对身边每一片布、每一块糖、每一件日用百货,都起了敬意。
下班,夜空是她们的头纱,星星是她们的发卡。从工厂到宿舍,姐姐们将起点和终点扯直,偶尔休班,会绕路去商业街看看。橱窗里,模特穿着成衣,鲜亮成美丽的春天。前襟的纽扣,缝合的针脚,领口的花边……可能都与姐姐有关,却也似都与姐姐无关。
我亲爱的姐姐,她们是城市里笨拙的造物师,流水线上的复制粘贴,给生活以礼物,给众生以安慰。
给亲人书
秋风乍凉,想写信,却找不到地址。
第一封应该写给太阳。阳光太烈,家乡的苞谷一个劲地疯长。外出的父亲们还没有回乡,他们弓着身子,与钢筋水泥较量,脊背发烫。还有的父亲弯着腰在大街小巷,把清晨扫成了黄昏,把白天扫成了夜晚。太累了,就找棵树靠一靠,两个老伙计互相照拂。如果可以,请阳光照亮父亲们租住的工房,照亮城中村挨挨挤挤的小房间。他们是从故乡移居到城市的辣椒、蒜苗,和公园里争奇斗艳的花朵一样,都需要泥土,都需要阳光。
第二封应当寄给水。这千变万化的水,这流淌在鬓角的水,这从眼里汹涌而出带着盐分的水,请绕过莽莽如草芥的亲人们,不需要急湍,不需要深潭,他们很多人的命里,已经打满了补丁。
吃五谷活命的人,命里早有了青草的底色。再回信,应当寄给我们每一个人。“农民工” 三个字,像铁,太过生硬。城市里,车间的劳作工人,忙碌的小商小贩,东奔西跑的快递兄弟,连轴转的保姆、厨师……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