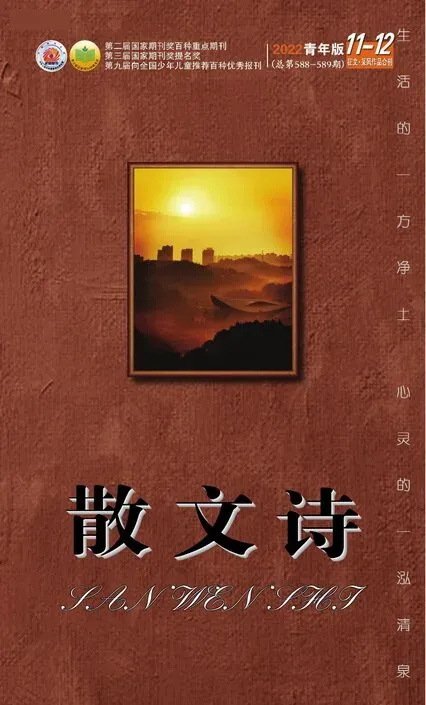盐的结晶是这样炼成的
青青小离
录音机里的拉丝厂
轰隆隆的机器声萦绕着拉丝厂,它像一台有高分贝噪音的录音机,回旋着亢奋的耳鸣。
从炉膛穿过的筋骨有着怎样的韧性?你们回想着自己的成人礼,是它们变调前的洗礼——一段励志的前奏曲。
它们穿过模具的调值,走出清一色的工号,你们也是流水线上的替代者。我听见磁带周而复始,旋转着太阳和月亮的班次。
青涩在褪变,肥皂泡明灭无常。梦想热气腾腾穿过机器加速的64 分贝音符,时有疼痛的呻吟在走调中崩断。
重新焊接打磨的筋骨继续经受抻拉的质变,继续经受千分尺苛刻的掐算。谁的指头被一段小插曲带进了漩涡,再也没有接上?
一捆捆消瘦的钢丝,是嘹亮的青春之歌,成为捕捉命运的渔网,成为轮胎里疲惫的闪电。
如今,录音机被DVD 和数码取代,唯有那时的歌声依旧年轻。
她的工作是一部繁琐的哑剧
她的工作是一部繁琐的哑剧,快节奏的旋律在她身体流淌。
微屈的身体、微跛的腿和变形粗大的指关节,是她长年磨砺的特写。我想到了那棵长年负重的歪脖子树。
她是被时间催赶的陀螺,旋转在高楼大厦的幽深处。她愿意化成阴影,擦亮阳光。尘土无穷无尽,拭去了,又从她的臂膀和脸上斑斑点点长出来。
褪色的服饰为她折旧的身体贴上了职业的标签,一个以小时计价的机器人,重复着时间的轮回。
她成了一块调色的方糖,速溶在优雅人士搅动的苦咖啡里。微薄的薪水只是富豪挥霍的一记高尔夫球。
她说话时缺失的牙齿,像机器体内掉落的一颗螺丝钉,随时都会散架。我闻到汗水发酵的酸咸菜味,就着一锅用辛劳煎熬的小米粥,吞咽着朴实无华的味道。
一团火焰照亮城市的街道
当大地还在沉睡中,她仿佛一根火柴划亮晨曦,划破城市的寂静。
到处是灰色高楼和灰色街道,她最先看到季节的颜色,和落叶飞花一样漂泊不定。
她比同龄人显老,有多少不能言说的秘密,在缺齿中漏风。一根扫帚支撑着简单的生活。
烈日里,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工作服告白:盐的结晶是这样炼成的。风雪中,老寒腿一锹锹铲去坚冰,要消耗多少力气才能除去打滑的前车之鉴!
她躲避着车流,一路汽笛的摇滚乐,敲打心跳。红灯下,为流淌的暮色清理残渣碎片。
街道和烦恼一样扫除不尽。不知何时,镜中增添了新的尘斑、沟壑……
她知道,自己也是大地的一粒微尘,使命就是与大地亲近、交融。没有华丽的服饰,却像一团火焰照亮城市的街道。
黄记酒酿
三十年了,从小伙子到老头子,他还是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载着几坛用一生酿制,取之不竭的心血。
一碗白花花的酒酿,泛着栀子的沁香,顺着氤氲热气回到了淳朴的初心。恍惚中,我又回到了童年时光,嗅出了妈妈的味道。平淡的日子,它是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仿佛微笑中的酒涡。
酒曲的发散性思维是魔术的秘方,在热情中发酵,让粮食升华成有浓度的温情。三分的醉意可以柔化空中坚硬的线条,柔化刻板的说教。
高楼疯长的城市,简谱的遗风正慢慢消失,他穿梭在五线谱的街道,高音喇叭依旧唱着不变的老歌:甜酒酿……如今,黄师傅成了网红,没有华丽的门面,动态的名片似信鸽一样捎去甜蜜。
修理铺
收放自如的塑料大篷,在无雨的天气绽放简单的快乐。
他是聋哑人,外面世界的声音他听不见,一双灵巧的手感触着时间的律动。
他负责修理鞋子、雨伞、补衣服和换拉链。父亲帮他收款,与顾客沟通。彼此像影子一样扶持照应着。
他比划着哑语,犹如在黑暗中打开了那扇通向月亮的天窗,通向灵魂的隐喻。一声“师傅” 是人们对他的尊称,也是救赎他的良药。
微薄的收入,让修鞋匠越来越少,只有他依然坚守岗位,修鞋机在他手中“咿咿呀呀” 唱着矢志不渝的歌谣。
修理了大半辈子,已到知天命的年龄,他知道自己就像这些微不足道的破旧物什,缝补着它们,就像缝补自己的命运。
快递员黑牡丹
仓库网点,你搬运堆积如山的邮件,将它们像星星一样撒向各自的轨道。
每天早出晚归,在鼓声敲打的节奏中,紧扣时间的脉搏。不敢喝水,一顿简易快餐或压缩饼干,拉长了奔跑的时间。
面对长龙淤堵,更多时候只好拐入狭仄颠簸的捷径。你不断寻找着远方,不断登上高梯,突破一个个新的记录。
顾客的脸,时而如奖章带来温暖,时而如红灯亮出罚单。时刻提醒自己要学信鸽守时,生活宛如一根绷紧的弦,自己就是射出去的箭矢。
锁骨和小腿骨开裂过,春天在石膏中静止。你的体内有不锈钢拧紧的坚韧,奔跑是你的宿命。
历经了烈日煎熬,风雨敲打,你被炼铸成隐忍的女汉子。
取之不竭的物流,移动在一张网的脉动里。被带动的消费,血液一样循环着。
没有停止的驿站,黑牡丹是你的外号,是闪电的过客。
一页孤独的叙事
园林是他一生绕不开的主题。太阳帽下,一张虚实相间的脸,在半露半隐中与世人若即若离。
在尘土和落叶中,他翻过一页页风雨,一页页败笔,一杆扫把在撇捺中反复练习“人” 字的中庸之道。
剪刀操着美学的圭臬,削落了灌木丛多余的巧言,修辞。它们多像纯抒情的空头支票。
肩上的打草机沉重,在嗡嗡声中割舍柔软的青春,迸溅的飞石划破暮色的夕阳。
内向寡言的他与大地保持着肢体语言,难以抗拒花草自然的向心引力,落下了颈椎病。微驼的身体,弯成了对生活无尽探究的问号。
他在枝丫的细节嫁接远方,期待着更多沉甸甸的花朵,果实落入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