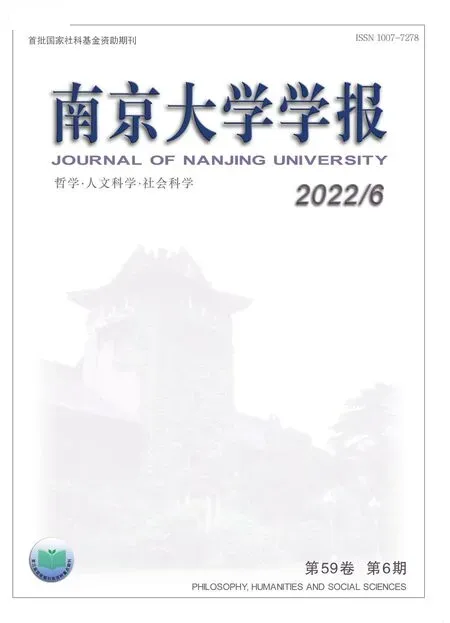论“情动”转向的剧场可能
——以《开心的日子》为样本
周仰子
(华威大学 戏剧与表演研究系, 英国 CV4 7EQ)
一、引 言
布莱恩·马苏米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情动的自主性》中提出:“在媒介、文学与艺术理论中似乎有一种愈发兴起的感觉:情动对于理解以信息和图像为基础、当中宏大叙事被认为已经分崩离析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至关重要……情感的溢出是我们当下状况的表征。”(1)Brian Massumi,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7.同伊芙·科索夫斯基·赛吉维克与亚当·弗兰克在同年合作发表的《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解读汤姆金斯》一文相呼应(2)这两篇文章之后分别被收入马苏米的《虚拟的寓言》和塞吉维克的《触碰感情: 情动、教学和表演性》当中,且均在2002年出版。,马苏米对“情动”(affect)关键性的感知触发成为欧美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多个学科领域联动的“情动转向”(the affective turn)。
马苏米通过“情动”发起理论重新定向的重要诉求是,与阐释和话语主导下的结构—后结构主义拉开距离。(3)Brian Massumi,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p.70.与媒介、文学、艺术这三者相比,根植于身体和感受的剧场,无论作为文化现象还是研究对象,皆关注不同身体间相互作用对其行动力和情感的影响,与自斯宾诺莎《伦理学》以来形成的“情动”传统更具有一脉相承的连贯性。正如戏剧学者艾林·赫利所概括的那样,“通过感觉行动”构成了剧场存在和目的的二位一体(4)Erin Hurley,Theatre & Feeling,London: Red Globe Press, 2010, p.4.,对情感在剧场中效力与意义的讨论贯穿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到后布莱希特感知力的戏剧理论与实践。在戏剧与情感内在亲密关系的映衬下,“情动”转向在逐渐发展后表现出的对自身伦理限度的自反性思考,以及不断拓展的跨学科、跨媒介理论网络中戏剧的不在场显得愈加明显。(5)在丽塔·菲尔斯基对其《批判的限度》进行延伸的新作《勾住:艺术与吸引》中,她屡次提及将绘画、电影和音乐纳入以出于喜爱的吸引为基础的后批判美学体验范畴。Rita Felski,Hooked: Art and Attachment,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吉尔·贝内特在讨论后“9·11”媒介时代美学感知的社会性论著《实践主义美学:“9·11”之后的事件、情感与艺术》中,涵盖了摄影、装置艺术、体育比赛等媒介和艺术形式。Jill Bennett,Practical Aesthetics: Events, Affects and Art after 9/11,London: I.B. Tauris, 2012.而根据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在《表演性美学》中的论述,剧场艺术和戏剧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经历“表演性转向”(the performative turn),在“情动”转向刚刚开始的20 世纪90年代已完成对演员—观众以及观众之间深远且持续的关系的新定义。(6)Erika Fischer-Lichte,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Performance: A New Aesthetics,London: Routledge, 2008, p.49.那么,在“情动”转向中是否存在与剧场/表演在理论层面经历的流变中类似的元素?观照两者间已有和潜在的互动,对于当代剧场有怎样的启示?
本文将首先着重阐述“情动”转向与戏剧剧场性展开对话的可能性,将现当代剧场观演关系放置于非认知与认知“情动—情感”交织的阈限处。面对作为方法的“情动”在认识主体所处环境时陷入的僵局,本文将以贝克特于1979年在英国伦敦皇家宫廷剧院(Royal Court Theatre)导演其剧作《开心的日子》(HappyDays)为主要样本进行分析,兼有介绍欧美剧场近年来对“情动”转向的其他实践性呼应,意在理解剧场空间中演员与观众身体所承载意识的多重性和混沌性如何在文本—表演生成过程中,表达“再现”的裂缝中流露的“次要情动—情感”(minor affects)。这一类“情动—情感”呈现的微妙强度或许与针对“情动”转向规避当下公共危机的批评形成对话,从而探索剧场与“情动”构建“人类纪”(Anthropocene)后危机时伦理—政治前景的开放性可能。
二、再现即终结:从“情动”的剧场性到“情动”剧场
“情动”一词与在使用中更加习惯化的“情感”和“感觉”间的联系可谓错综复杂。英语中“情感”(emotion)一词可以追溯到拉丁文中的“ēmovēre”和法语的“émotion”:前者意指从某处迁出、离开(7)“ē”与“ex”前缀代表与离开趋势有关,“movēre”则特指离开的行为。,后者在历史上常被用来形容受到刺激而兴奋的心理状态。考虑到作为哲学概念的“情动”一般特指身体和身体间的潜在力量,“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样的能力提供了进入表达、认知领域的渠道。戏剧学者马丁·威尔顿就指出,在剧场内外,“感受”(feeling)都结合并反映出情感、理智和身体这三个维度对感知的塑造。(8)Martin Weldon,Feeling Theatre,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5.“情动”与“情感”这两个关键词之间既对立又联通的关系,无论是对于理解分支众多的“情动”转向,还是剧场中的情感状态都尤为重要。情感与认知、语言间的粘着性解释了马苏米为何将“情动”定义为发生于表面的非自主反应。这样一种“强度”尽管脱离意义和叙述,但语言与“情动”并不是毫无瓜葛的对立概念,它们恰恰通过各自不同的机理产生联系。(9)Brian Massumi,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pp.25-28.
马苏米的“情动”理论,部分缘起于对20 世纪60年代开始的语言学转向并统治理论30余年后其自身效力的疑问。他十分关注以语言表达为基础的“情感”作为“情动”目的与终结的双重属性。作为媒介的语言在再现过程中无法完全捕捉“情动”潜在的开放性,因此作为量化了的“强度”的情感在表达“情动”的同时,也宣判了“情动”不复存在。(10)Brian Massumi,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p.35.尽管以马苏米为代表的“情动”理论研究者从根本上不认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之一概括为“情感的消逝”(the wanning of affect),但在这里,马苏米意外地与詹姆逊达成一致。后者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同样宣称“情动”由于强调身体感受的特性,必然抵抗认知情感施加的语言介入的桎梏。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詹姆逊指出“情动”对文学创作提出一个全新的再现任务,即试图去“抓住‘情动’稍纵即逝的本质,迫使它显现”(11)Fredric Jameson,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London: Verso, 2015, p.31.。上述观点可以看作是詹姆逊对其之前的著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情感消逝”说的修正:漂浮在言语之外、等待被激发的“情动”本身并没有减弱;“情动”需要的是去描述、表达,使它的“强度”重新进入感知领域的形式或媒介。
在马苏米和詹姆逊建构的语境中一步步走向再现/消亡这一双螺旋式终点的“情动”,与戏剧理论向剧场和表演转移后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在以界定剧场独特性为目的的阐释中,剧场几乎与“稍纵即逝”(ephemerality)、“消逝”(disappearance)等概念融为一体。(12)在剧场和表演研究中强调剧场的独特本体无法离开与其他媒介和艺术形式,特别是当代大众媒体的区分。如美国戏剧学者佩吉·费兰在其重要著作《无标记:表演的政治性》中,从根本上否定了表演能够被重新表现和生产的可能性。Peggy Phelan,Unmarked: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London: Routledge, 1993.本文选择将“情动”与剧场在“表现即消逝”层面进行类比,对围绕剧场开展的现场性辩论不作展开。类似地,德国戏剧理论家汉斯—蒂斯·雷曼在《后戏剧剧场》中,将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情感宣泄理解为通过逻各斯的框架来“驯服”诸如遗憾与恐惧等暴烈情动。在构建一种不同于再现框架下情感规训的剧场理论的尝试中,雷曼引入了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设想的“能量剧场”(energetic theater)。尽管雷曼认为能量剧场不能在名称上直观体现出戏剧传统发展的流变,但他依然肯定了利奥塔的观点所勾勒的充满“力量、强度、现时的情动”剧场想象与后戏剧剧场的紧密关联。(13)Hans-Thies Lehmann,Postdramatic Theatre,London: Routledge, 2006, pp.160,37-38.这样一条审视逻各斯—文字—意义的线索所暗示的已经不止是文学领域寻找新的话语的策略,而是一种与文本,或是以发源于文本的视听感知为主导的戏剧决裂的诉求。
不过,将剧场中的“情动”转向绝对地与反文本联系在一起显然是有缺陷的。雷曼并没有对在脱离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后留下的社会效用方面的空白作出有效的补充;后戏剧美学的自治性在面对从柏拉图《理想国》起就根深蒂固的“反戏剧偏见”(14)关于“反戏剧偏见”,见Jonas Barish,The Anti-theatrical Prejudice,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时,也难以为剧场辩护。当学术话语中的“批评距离”(critical distance)已经以批判性参与的形式成为当代戏剧构作的宗旨和对剧场观众的要求时(15)海伦·弗来希沃特在《剧场与观众》中对戏剧学者、剧评人和普通观众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三者对观剧行为产生的愉悦的不同看法进行了思考。Helen Freshwater,Theatre & Audience,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游离在认知之外的剧场“情动”如果拒绝任何形式的再现或感知,则注定会徘徊在被动的美学空洞边缘。
相比之下,塞吉维克则沿袭美国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形成的“情动”在极富戏剧化的论述中表达出情感深刻的社会属性。如果说以马苏米为代表的“情动”思想与剧场共有的“死亡冲动”尚是需要挖掘的隐喻的话,塞吉维克则在《触碰感情:情动、教学和表演性》中阐释了明确的“世界剧场”观(theatrum mundi),即趋向濒临反常和越界的表演行为在现实生活与现实主义叙事中普遍存在。不过,与她对“剧场性”一词的直接使用(即该著作第一章《羞耻、戏剧性和酷儿表演: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相比,塞吉维克的理论剧场性更多表现在她随后由空间视角建立的“边缘表演性”(periperformativity)中对不同主体间权力关系的揭示。这一概念力图解构的是J. L. 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中被“第一人称单数主动态直陈现在时”掩盖的异性恋本位思想。塞吉维克沿用了奥斯汀的婚礼誓词交换的案例,但她关注的重点不是在镜框式舞台上一般的婚礼情境中的演出的言者—演员,而是在舞台的“第四堵墙”边缘之外被“我愿意”这样的“施事话语”作用并作出(不仅仅是言语)反应的听者—观众的实体存在。相较该情境中被外部权威机构限定的言语的单一和僵化,塞吉维克认为反而是缄默的存在蕴含的非自主的、趋向否定面的潜能更具有活力和意义。(16)Eve Kosofsky Sedgwick,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71, 72.
通过引入“观众”的主体性及其携带的观演关系,“边缘表演性”拓展了汤姆金斯基于“情感场景”(affective scenes)归纳的“情动脚本”(affect scripts)。汤姆金斯尤其强调,“脚本”产生于“注意系统”,被该系统设定为自我管理的规则,当中包括了管控认知与情感指令的附属规则集合,好比对一个文本的理解预设了语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规则。(17)Silvan S.Tomkins,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 The Complete Edition,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985.虽然汤姆金斯回归了“脚本”在阐释过程中体现的文本性而非在演绎情境下的剧场性,但他借此强调了“情动”能够在认识与非认知间流动,并且浸润在历史因素和社会影响中(即规则是“预设”好的)。这在理论上为帕塔·泰特提出的剧场中情感表达的模型提供了支持。泰特认为,情感“由感受和当下的身体感觉(‘情动’)组成;从前体验过的自主和非自主的各种模式化反应,以及理解这些反应的认知系统,与两个组成部分都有关联”(18)Erin Hurley,Theatre & Feeling,p.19.。在这样的“情感—情动”不断联动、转换的剧场情境中,戏剧和后戏剧剧场间关乎文学或话语的区别不像在雷曼构建的戏剧形式的语境中那么重要,也因此展现出由剧场本体向剧场内关系的转移。
与此同时,这一在总体情境中关注参与主体的多重性、重视主体间关系的趋势顺应了将表演看作反映和构想现实社会的一种范式,因而肯定再现框架在某些方面对表演生命维系积极作用的认识。例如,基于对斯里兰卡海啸、卢旺达大屠杀等自然、政治因素造成的创伤进行的戏剧治疗的观察,詹姆斯·汤姆森更是提出了应用戏剧以“情动”终结“效用”的大胆设想。具体到如何另辟一条不同于将表演理解为效力的指标和简单化的诊断的研究路径时,汤姆森借用了美国理论学者克莱尔·科尔布鲁克在《德勒兹研究》中阐述的观点,认为“让艺术成为艺术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通过感官力量或风格创造内容的情动”(19)James Thompson,Performance Affects: Applied Theatre and the End of Effect,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117.。“表演情动”试图通过唤醒在应用戏剧实践中一度被抛弃的感官体验,使表演能够承载“以情感描绘世界会怎样变得更好的愿景”(20)Jill Dolan,Utopia in Performance: Finding Hope at the Theater,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6.,践行吉尔·道兰笔下的乌托邦理想。
虽然这样的论述详实展示了表演乌托邦如何能够在表达不同政治文化诉求的戏剧类别中实现具体的社会美学,但它们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文化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引出了这种乌托邦思想隐含的矛盾。夹杂在后殖民语境与创伤话语之中的“更好的世界”,依然没有脱离西方现代性主导下无法抵抗、不可倒退的线性时间观和对正向进步必然性的坚守。(21)Amitav Ghosh,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70.特别是在面对诸如环境危机这类远超人类感知习惯的时间维度上酝酿的悲剧时,它的普适性恐怕会像布鲁诺·拉图尔设想的那样,“让我们通过地球工程和再现代化将灾难推迟到下个世纪”(22)Heather Davis and Etienne Turpin,Art in the Anthropocene: Encounters among Aesthetics, Politics, Environments and Epistemologies,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5, p.52.,将萌发出离心趋势的乌托邦推回那个在当下认知时间限度内满足自洽的中心主体。如果说“人类纪”不断涌现的例外、断层、延宕造成不确定性给所有艺术叙事带来了挑战,那么剧场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是:“情动”的乌托邦中表演与现实的即时情感共振,是否还能为未来想象提供范式?
三、“情动”转向及其不满:趋向剧场(性)的次要“情动—情感”
出于类似对人为建构的时间历史中现代性的疑虑,科尔布鲁克在《过去与未来的人类:在幸福与灭绝之间》一文中对“情动狂热”(affect-mania)进行了批评,也反思了她曾经支持的“艺术即情动”的观点。有趣的是,正是在对当代大众科学和流行文化的观察中,科尔布鲁克发觉被马苏米等人高度理论化的非认知“情动”,早已由认知捕捉并披上了叙事的外衣。她认为,既然“情动”理论认为对主体的感知必须通过与外界刺激联系所产生的效力得以实现,那么构建自我的过程其实也是主体将外部联系解读为与自身一致的过程,主体的生命因此呈现一种不断发展、繁荣、丰富的“幸福”状态。(23)Claire Colebrook,“The Once and Future Humans: Between Happiness and Extinction,”Alastair Hunt and Stephanie Youngblood,Against Life,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64-69.而对这种幸福感觉的普遍追求——它甚至在后末日叙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反映出幸福已然成为管理约束其他所有情感的基石。或者用前文提到的汤姆金斯的话说,它是那个指导一切“情感场景”的“情动脚本”。
对科尔布鲁克而言,这一倾向的危险之处在于,“情动”依然在用人类中心主义的标准去有选择地定义外部刺激的来源,将世界描绘为另一个不断自我生成、自我指涉的有机整体。人类主体于是抵达了在历史上一直在场也不会消逝的虚构乌托邦状态。以幸福为基础的目的“情动”将自然世界一切无法通过情感联系的异质元素推向认知以外的黑洞中,虽然在认识层面如拉图尔所言的那样推迟了灾难的来临,却无法避免地在现实中走向灭亡的终点。对此,科尔布鲁克提出了颇为激进的思想变革:她所提倡的已经不是后人类角度的延续共生,而是在一种能够直面人类灭绝可能的非人类立场上的理论凝视中,想象不可估量、没有感情、无法自洽的未来,从而在“情动”的缺失中迎接“真挚伦理”(genuine ethics)的到来。(24)Claire Colebrook,“The Once and Future Humans: Between Happiness and Extinction,”Alastair Hunt and Stephanie Youngblood,Against Life,pp.70-71.
这一设想对于美学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包括剧场在内的艺术需要找到的不仅是摆脱用意义维系的、建立在反思、连续、秩序、整体和价值观上的叙事(25)Claire Colebrook,“The Once and Future Humans: Between Happiness and Extinction,”Alastair Hunt and Stephanie Youngblood,Against Life,p.67.,同时还要避开在理论叙述中同样存在于这类叙事之外的“情动”的陷阱。不过,要使剧场与科尔布鲁克描述的无感情状况的全局展开对话,我们不妨先回到她对“幸福—情动”批判的源头。不难发现,以幸福为目的的情感管理机制与作为亚里士多德悲剧观核心的“情感宣泄”有不少可以类比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看似没有给经历遗憾和恐惧洗礼后的观众的心理状态贴上标签,但在情感净化进行的保留和过滤之后,被雷曼描述为“暴烈”的这两种情感(遗憾与恐惧)已经能与观众主体稳定共处。以此观照即可推测,科尔布鲁克总结的“幸福—情动”存在着两个预设立场:一是多样的、可能是负面的情感向单一正向情感的收缩;二是前者应该存在较为明显的强度,以致它们干扰到了追求幸福的主体的自治,招致主体明确果断地采取转化或过滤的净化行动。除此之外,科尔布鲁克提出的以“无情动”凝视救赎“幸福—情动”引发的后果也仅在时间维度上开展:要么回到从前对西方现代性之外的持有自然—人类历史一体观念的文化中进行考古(26)Claire Colebrook,“The Once and Future Humans: Between Happiness and Extinction,”Alastair Hunt and Stephanie Youngblood,Against Life,p.81.,要么快进至尝试表现人类灭绝后的“原末日”(proto-apocalyptic)情境中。在这样的前提下,科尔布鲁克对“情动狂热”的诊断忽视了处于对立的强烈“情动”和“无情动”之间可能存在的情感或情动种类,也没有对它们因为难以被宣泄掉而与主体长期共处可能带来的影响和意义进行探究。
美国理论家西安尼·魏的著作《丑情感》所研究的正是在道德判断和情感宣泄范围之外,因不够“戏剧化”(dramatic)而维持更久的弱强度情感。具体到它们所涉及的情境中,弱强度情感没有明确的意向和对象,更像是基于无行动原则的判断姿态,而非趋向行动的策略。在处理“情动”与情感的关系时,西安尼·魏并未以认知为标准将它们对立,而是把两者的不同作为一定范围内程度和结构上差异的表现。因此,她分析的“次要情动”更适合被理解为中间态的“情动—情感”。在两者集成内部动态、双向的关系中,主体难以将其情感作用的对象完全同化,所以会一直处于类似不安或困惑的“元情感”(mata-feeling)状态,即对自身到底在经历怎样的情感感到困惑。(27)Sianne Ngai,Ugly Feeling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6-7, 22, 14.相比于主要情感所指的固定性,次要“情动—情感”给在人际与社会关系中受阻的主体带来的困境正是其尚未定型的政治意义所在。
《丑情感》描述的在模糊不定中无法自洽的主体困境让人不禁联想到观众、角色、演员三者间的戏剧关系。在这个角度下,次要“情动—情感”的剧场性并非源自它在强度上对日常认知接受范围的超出,而是体现在它隐射的多主体复杂空间的关系中。尼古拉斯·里多特对剧场中意外事件的讨论便突出了资本主义语境下剧场中的“情感劳动”(feeling work)。巧合的是,“次要化”贯穿了他所关注的表演转向之前戏剧剧场中的情感议题。如果说演出中犯的大错放到现实世界中不过是一场小型灾难的话,那么,可以说剧场将前来娱乐的观众主体和正在工作的演员客体吊诡并置,给前者带来的不安和尴尬则是弱化了的、浮于表面的耻感——或者说是剧场般的耻感。(28)Nicholas Ridout,Stage Fright, Animals, and Other Theatrical Problem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85, 149.从演员对观众回以非角色的凝视,到演出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这些问题迫使观众意识到所属空间中的复杂关系,再次展示在出现的裂痕中暴露了其试图掩盖的真实社会关系。观众的美学情感体验在剧场这个“情动机器”(affect machine)运转不当的模糊瞬间被次要化和剧场化,随之进入伦理—政治领域。
诚然,上文提到的观点均根植于人类主导的美学体验和社会关系中,前者赋予了阐释框架下愈加容易被忽略的几类情感以理论的重量,后者则从反向的角度再现的意义上,挑战表演转向作为戏剧救世主和替代者的话语。不过两者关注领域的局限性不应阻碍我们尝试沿用类似的思维模式,研究剧场情境对现实危机的寓意。现当代西方剧场史中最接近后末日状况的段落之一,莫过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威胁、工业污染、健康危机背景下的荒诞戏剧。(29)有关荒诞戏剧创作的生态环境背景,见Carl Lavery and Clare Finburgh,Rethinking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Ecology,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Greening of the Modern Stage,London: Bloomsbury, 2015.例如,1967年英国康沃尔发生严重游轮漏油事件后,当贝克特于1971年在柏林导演《开心的日子》时,他将女主角温妮形容为“羽毛里浸着油的鸟儿”(30)Carl Lavery,“Ecology in Beckett’s Theatre Garden: Or How to Cultivate the Oikos,”Contemporary Theatre Review,28(1),2018.。而《开心的日子》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舞台呈现的末日情境与当中角色的身体语言的机械性重复,以及言语之间被抑止却从未消逝的情感传递。这一状态给科尔布鲁克提倡的“无情感”指出了不同的角度。在言语、动作、环境和意义之间的循环断裂后,被弱化的、看似不兼容的“情动—情感”对观看行为的主体有怎样的影响?贝克特1979年在英国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导演《开心的日子》过程中流露的构作理念,可以说浓缩了次要、负面的情动与情感在戏剧中的美学与社会意义,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四、剧场情感演习中的“次要情动—情感”
1961年1月13日,还在创作《开心的日子》剧本的贝克特在给美国导演阿兰·施耐德的信中写道:“我快要写到第一幕的结尾了,这仅是一版非常粗糙的初稿。我肯定会继续写下去,但不能确定它能否成为剧场。”(31)Samuel Beckett, Alan Schneider,No Author Better Serv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Samuel Beckett & Alan Schneider,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8.贝克特对剧本(戏剧)和剧场间关系的考虑在两个层面得以展现:首先,贝克特对剧场的态度显然不同于一些现代主义剧作家,认为剧场中的观演关系贬低了剧本—文本在美学上的自主性(32)Martin Puchner,Stage Fright: Modernism, Anti-Theatricality, and Drama,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p.10.;反而,他认为缺少了“在剧场中的实际工作”,根本无法确定“剧本的最终形态”。其次,在强调剧场时空特点的必要性之基础上,贝克特寻求的是测试、挑战剧场再现边界的构作方法,以此确立一种远离自然主义戏剧的、在文本—剧场生成过程中得以显现的剧场性。贡塔尔斯基指出,剔除了剧场叙事中多余的部分之后,贝克特戏剧通过“展现一幅极简而又难忘的图景,唤起观众的感觉”(33)S. E.Gontarski,“Samuel Beckett and the ‘Idea’ of Theatre: Performance through Artaud and Deleuze,”Dirk Van Hulle,The New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Becket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26,138.。在观赏《开心的日子》这样的作品时,观众体会到的更可能是与舞台上传递出的情感的割裂,是无法宣泄掉的异质感受,或者说是在贝克特写作该剧时“困扰”他的那一种“奇特但必要的错位感”(34)Samuel Beckett,The Letters of Samuel Beckett,vol. II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93.。
1979年版的《开心的日子》在英国皇家宫廷剧院的舞台上创造了一个未知灾难过境后苍白而瑰丽的世界。与贝克特保持长期合作的舞台设计师约瑟琳·休伯特使用了大量的帆布、网纱和干花黏在埋住温妮的土丘底部(35)Martha Fehsenfeld,Unpublished Rehearsal Diary Notes Taken during May 1979 Rehearsals of Happy Days, Royal Court Theatre, London. Directed by Samuel Beckett, UoR MS 2102, University of Reading Library, Reading, United Kingdom, p.9.,土丘与1961年纽约版相比“更加松散,好像有许多零碎的部分要脱落下来”(36)Jocelyn Herbert,A Theatre Workbook,London: Art Books International, 1993, p.55.,也更接近贝克特剧本中描写的枯焦草地的干燥破碎。与原剧本中舞台提示不同的是,休伯特将温妮从土丘的正中央稍微向左挪动了一点。从观众的视角来看,舞台中央的焦点从温妮一人变成了温妮与威利两人,刻意对称环境造成的不自然感反而因此有所减弱。不过,舞台上看起来被烧灼过的、禁锢着两个角色的“自然”与现实经验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呈现出的是末日式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暗恐”景象。
在1979年版的表演中,不少地方都暗示,温妮意识到了她所处的世界中最明显的危机便是维持她一天生活的资源即将耗尽,从她身旁的黑色手提包里取出的牙膏管已经扁平,红色的药水剩下不多,口红也快要用完,她也两次警示自己“不要滥用手提包”(37)Samuel Beckett,Happy Days: A Play in Two Acts,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p.19.。贝克特在导演笔记中也特别留意到,温妮在翻找手提包里的东西会时不时“突然停止她的动作,仿佛是意识到她不应该随意浪费包里的资源”(38)Samuel Beckett,Happy Days: The Production Notebook of Samuel Beckett,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5, p.134.。令人不安的是,温妮不断地把与这样的意识相对应的行为延后,最终完全推离自身。温妮在土丘上寻找牙刷和梳子的过程交织在她“这才合乎人情……合乎人性……合乎人的弱点……合乎人性的弱点”的自言自语中,这种并置无意之中给她丢弃东西的行为下了宿命式的定义。她随后承认“通常我用完东西后是不收进包里的”,又立即保证“这天结束的时候,我会把它们都放回去”。第一幕即将结束时,温妮把一面镜子扔到了身后,并且告诉自己“明天镜子会完好无损地回到包里,帮我度过一天”(39)Samuel Beckett,Happy Days: A Play in Two Acts,pp.13, 23.。但第二幕开始时,温妮脖子以下的身体都已被埋入土中,无法动弹;那些物品还四散在土堆上,并没有神奇地回到手提包中。1979年伦敦演出的灯光设计师杰克·拉比为了达到贝克特对刺眼灯光的要求,在舞台上安装了14盏1千瓦、供飞机使用的64帕聚光灯,集中打在饰演温妮的演员比利·怀特劳身上。(40)Martha Fehsenfeld,Unpublished Rehearsal Diary Notes Taken during May 1979 Rehearsals of Happy Days, Royal Court Theatre, London. Directed by Samuel Beckett,UoR MS 2102, p.10.强烈的光照让温妮之外的舞台元素大多处于过度曝光的状态下,与土堆在颜色上融为一体,仿佛消失了。《开心的日子》舞台上的物品在观众视线中从有到无的路径隐隐呼应了定义“人类纪”的环境危机:被浪费的、丢弃的资源已经不足以回到自然循环中去维持它的自我更新。这样的舞台情境也非常接近科尔布鲁克描绘的后末日状况:温妮和威利与其说是身处趋向结局的阈限时空,不如说是陷入了先前思维不复存在的“后终结”认知困境中。温妮对“结束”的错位认识使得她对“开心的日子”的重复执念无法唤起观众间接但相应的情感体验。值得注意的是,温妮说出“开心的日子”时,她的面部动作常与她提到“老一套”时一样,经历打开—关闭的公式化过程;两个词组分别夹在“(幸福的表情)……(收起幸福的表情)”和“(微笑)……(收起笑容)”这样的舞台提示——也可以说是“情动—情感”脚本之间。而让温妮发出“老一套”感慨的,一般都是她刚刚提到的与“一天的结束”“夜晚的降临”和“死去”等相关的词句。(41)Samuel Beckett,Happy Days: A Play in Two Acts,pp.11-33.比较之下,尽管她一直用将来时的状态想象开心的日子,但它们听上去更像是陷入对过去规律而又周期性的时间的过时怀旧中。温妮的幸福无法成为自带氛围的、有传染力的情感并传递出去,只能不断闭合归复至她无表情的自我和历史叙述中。
西安尼·魏的次要“情动—情感”分类中的“惊倦”(stuplimity),是观众对温妮一遍遍排演幸福行为时可能产生的情感反应。“惊倦”结合了震惊与无聊这两种强度和持续时间上截然不同的情感,与崇高理论中个人因意识到自身体验能力局限性而产生的负面情感不同,“惊倦”这种被阈限化了的次要崇高感来自于一些宏大美学体验中令人疲乏的重复,导致震惊与无聊这两种情感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被对方同化。西安尼·魏以贝克特和斯泰因等人的散文和现当代大型艺术作品为例,指出它们在重复中持续维系着无趣感与吸引力间的张力,迫使读者在想放弃的同时又不得不继续。(42)Sianne Ngai,Ugly Feelings,pp.261-272.不过与贝克特在完成小说三部曲(《莫罗瓦》《马龙正在死去》《无名者》)后形容“黑洞般”的小说叙事不同,剧场“有限的形态和时间”或许不仅为作家本人提供了更为“明亮”的创作方式(43)Jocelyn Herbert,A Theatre Workbook,p.219.,也让观众进入了更加微妙的时空领域。贝克特对《开心的日子》结尾的调整则进一步触碰了剧场限度的边缘。温妮对爬向她的威利的台词由“你是在找手枪,还是在找我”(44)S. E.Gontarski,The Intent of Undoing in Samuel Beckett’s Dramatic Texts,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p.77.,变为了悲剧性更弱的“你是找我来的,还是找其他东西”(45)S. E.Gontarski,The Intent of Undoing in Samuel Beckett’s Dramatic Texts,p.77.。1979年演出的排练日记中,记录了贝克特曾亲自为扮演威利的演员演示,指出他的手放置的最后位置应该位于温妮和手枪之间。(46)Martha Fehsenfeld,Unpublished Rehearsal Diary Notes Taken during May 1979 Rehearsals of Happy Days, Royal Court Theatre, London. Directed by Samuel Beckett,UoR MS 2102,p.28.灯光熄灭前的最后场景定格留下了超越作为时间标志的结尾的悬念——威利是要拿枪还是去触摸温妮?如果是拿枪的话,他要杀死温妮还是他自己?与明确的尾声一起被剥夺的,还有获得稳定意义的满足感;观众虽然和温妮体会着不同的“情感—情动”,却同样陷入了(后)终局的困境之中。
在斯泰因和德勒兹的启发下,“惊倦”的政治意义被总结为它作为“开放情感”对宏大叙事/系统规训过后应有反应的幽默颠覆。(47)Sianne Ngai,Ugly Feelings,pp.284-297.在剧场中,它则有可能演化为次要化羞耻,即尴尬或“不安”。在这一点上,里多特反复提到的演员—角色对观众伦理意识产生的双重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排练《开心的日子》开场时,贝克特要求演员怀特劳以“一种痉挛性抽搐的方式移动右手”(48)Martha Fehsenfeld,Unpublished Rehearsal Diary Notes Taken during May 1979 Rehearsals of Happy Days, Royal Court Theatre, London. Directed by Samuel Beckett,UoR MS 2102, p.11.,这一对演员身体携带的额外意义的刻意强调,打破了温妮开场动作中那一套木偶般行为的机械性,也预示着怀特劳扮演的温妮在随后演出中关于幸福的言行操演即便是重复的,也始终无法摆脱一种脱离控制脚本的风险。与此同时,过于明亮的舞台本身也阻止了导演和观众将演员仅仅视作木偶般模仿的载体。14盏大功率聚光灯带来的热量呼应了剧中“愈加酷热”的环境,但演员怀特劳无法像角色温妮那样“出汗减少了许多”(49)Samuel Beckett,Happy Days: A Play in Two Acts,p.20.。剧组必须在土丘下放置一台电扇,以防怀特劳因出汗过度而晕倒。(50)Martha Fehsenfeld,Unpublished Rehearsal Diary Notes Taken during May 1979 Rehearsals of Happy Days, Royal Court Theatre, London. Directed by Samuel Beckett,UoR MS 2102, p.10.表演环境为演员带来的不适为舞台和观众空间里的情感流动施加了一个道德困境:身处黑暗之中的观众既有着凝视演员—角色客体的权力,也不得不意识到观演关系正是将使他人不适的表演合理、合法化的原因。因为观众的存在,被环境禁锢住的“怀特劳—温妮”同样想要停止,却又不得不继续。
从第一幕的后半段开始,观众主体藏于台下所带来的安全感被进一步破坏。贝克特引入了肖瓦(Shower)或库克(Cooker)这个并未实际出现的含混身份作为观众在舞台上的替身(51)在解答施耐德对“Shower”应怎样发音的问题时,贝克特回复道:“应该念做‘肖瓦’(下雨的意思)。‘Shower’和 ‘Cooker’来自于德语中的‘看’(‘schauen’和‘kuchen’),他们代表了想要弄清事物意义的观众。”Samuel Beckett,Alan Schneider,No Author Better Serv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Samuel Beckett & Alan Schneider,p.95.,并借温妮之口,质问他们为何执迷于她行为的意义,最终却又违背要救出她的承诺而一走了之。如果说之前观众不过是在黑暗中的座位上无法脱身,他们现在则是在刺眼燥热的舞台上被温妮回以凝视的“最后的人类”(52)Samuel Beckett,Happy Days: A Play in Two Acts,p.25.,他们的存在与动机都无法隐藏。《开心的日子》在此将科尔布鲁克对依恋“幸福—情动”中意义的批评进行了巧妙的现实化和改编;在剧场空间中,观众追寻意义的过程不仅没有使其在认识上高于被客体化的角色,反而将他们拉入了演员—角色遭受的后灾难末日情境中——他们感觉体验经历了由(期待的)愉悦到“惊倦”再到“不安”的次要化的“情感—情动”演习。
结 语
西奥多·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将贝克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写作誉为对废墟中的世界为数不多值得推崇的美学回应。否定的价值在于,它“拒绝参与创造绝对的邪恶”,因此提供了“朝向还未到来的另一个世界的机会”(53)Theodor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London: Continuum, 1973, p.381.。在贝克特之后,当代表演中的次要“情感—情动”所指涉的公共讨论愈发多样化。例如,英国强制娱乐剧团的《明日派对》(Tomorrow’sParties)则与《开心的日子》同样呈现了极简的舞台设计和一男一女两位演员。全剧由不同的未来叙事碎片拼接而成,演员以介于好奇与困惑间的语调道出或美好,或荒谬,或灾难性的可能情境,时不时引人发笑。然而独白/对白中辅以不断延长的刻意停顿、演员身后逐渐暗淡的装饰灯光,一起将表演的批判性反思内核推出诙谐谈话的外壳。在演出后期,剧场内的氛围被厚重但涌动的沉默取代。该演出协同鼓励直面演员的观众在展开平行的未来想象的同时,去碰触现有经验和认知的限度。对于观众而言,这些表演中混沌模糊的不确定流露出的不仅是开放了的意义和情感,同时也是一种可能会饱含对自我之外空间的感知和伦理—政治警觉、反思的希冀。
本文在梳理“情动”转向和现当代剧场理论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时同样发现,一些次要的、负面的“情动—情感”为观演关系注入了不同于主流情感的灵活意义延展,在由舞台与观众空间共同组成的总体环境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剧场生态的反馈圈。如果说“后末日”早已应被当作现实而非未来想象的话,我们或许,也需要去寻找无情刺眼的白色聚光中各具色泽的微小“情动”,在被它们触动的不和谐音调中拒绝回到那个虚幻自洽的从前世界。由此,难以脱离人和人类情感而存在的剧场提供了为环境等方面危机进行情感演习的场所,这便是“情动—情感”与剧场互动后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