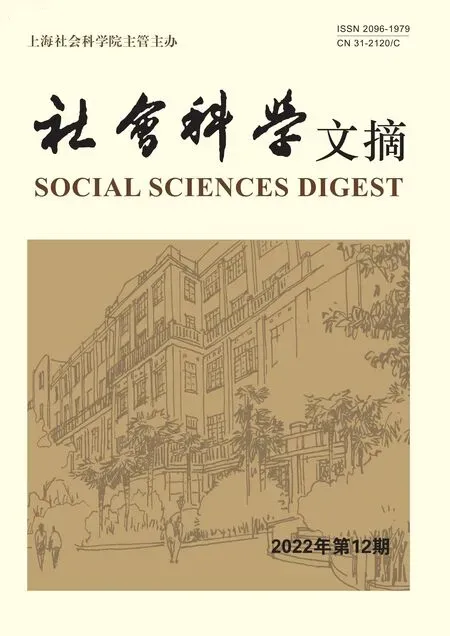“权力”视角下的工作场所侵害
——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郑路 刘梦玲 陈宗仕
当下,“工作场所侵害”(workplace bullying)这一屡见于职场的现象逐渐走入公众视界。其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普遍性,且受害者涉及各个社会阶层、种族、性别、年龄、职业人群。大量文献揭示工作场所侵害的根源是权力问题,通常发生在施害者和受害方存在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但既有研究尚未围绕权力这一核心概念提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社会学经典理论中对“权力”概念的讨论为出发点,考察影响工作场所侵害的重要因素和作用机制。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工作场所侵害的定义与权力不平衡实质
从国外兴起的对于工作场所侵害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北欧,本研究使用的工作场所侵害的定义由爱纳森等人提出,即“工作场所侵害是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出现的施加于目标对象并且令其难以防卫的消极行为(包括言语羞辱、责骂或者肢体威胁等)”。工作场所侵害不仅是“侵害者—受害者”双方反复出现的互动行为,还凸显了受害者处于弱势一方,与侵害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二)“权力”概念的三个维度
要针对工作场所侵害问题构建“权力”视角的分析框架,首先须回溯“权力”的内涵,并从中提炼出可操作化的概念维度。基于社会学对权力概念和关系的经典理论,我们把权力分解为三个维度。
权力的“依赖性”维度来自埃默森的“权力-依赖”理论。埃默森提出,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关系之中,弱势一方对于强势一方所拥有资源的依赖性:这个资源越重要,后者对前者就拥有越大的权力。权力的“强制性”维度来自韦伯,他认为,权力是人在某种社会关系行为中哪怕遇到其他参加者的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即有权力的一方对弱势一方能够任意实行支配和控制的能力,我们将其称为“强制性”。权力的“可替代性”维度同样受启于埃默森对权力关系的进一步阐述,他提到:“当B在A-B关系之外实现目标或取得资源的可能越大,B受制于A的可能性越小。”“权力-依赖”关系理论启发菲佛和萨兰西克提出“资源依赖理论”,他们将权力分析运用到组织社会学领域,提出组织对外界的资源依赖导致了组织间权力与依赖关系的不平衡。该理论指出组织降低权力不对称和依赖性的策略之一,就是开发和维持获取资源的其他渠道,即提高所需资源的可替代性。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对权力内涵的阐释,本研究从以下三方面来考察工作场所侵害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访谈资料的初步发现提出假设。
1.个人层面:资源重要性与权力依赖
在工作场所侵害中,受害者往往因为这份工作所带来的资源(包括工资、福利、社会身份等)对其太重要,不愿或者不能承担发声、反抗或辞职的代价。来自当前工作的收入对一个人越重要,他越难以在侵害发生后进行自我防卫(投诉、离职等),因此越容易成为工作场所侵害的受害者,本研究提出假设1.1:资源依赖性对工作场所侵害有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雇员越依赖从目前工作中获得的收入,成为受害者的概率就越大。
除了更高的收入,更优厚的福利也会导致对当前工作的更大依赖性。是否签订正式合同与雇员的福利待遇密切相关,起到了增加资源重要性的作用,进而也增加了雇员对于该工作的依赖程度,使离职或者换工作的机会成本变得更高。与前述关于工作收入的逻辑类似,签订劳动合同在一般情况下原本对雇员是有利条件,但在遭受工作场所侵害这一特定情形下,越优厚的条件越容易产生更大的依赖,反而成为个人通过离职来避免侵害的阻碍因素。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2:资源依赖性对工作场所侵害有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非正式雇员相比,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的雇员成为受害者的概率更大。
2.组织层面:制度规范性与权力强制
工作场所侵害并不发生在真空状态下,它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和组织文化里。不同的组织类型代表了不同的管理规范和管理文化,对组织成员所具有的强制性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存在差异,进而在侵害发生率上产生差别。管理规范的场所,较少出现人际冲突与权力压制,侵害情况也很大程度受到制约。
区域内河道杂草丛生,流水不畅,加之居民随意向河道倾倒垃圾,导致河水污染严重。同时由于区域内水面较少,水生态环境较差,与新城的规划定位不相适应。
在我国,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大量的资源和机会分配过程发生在工作组织中,后者掌握着重要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分配,工作组织对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作组织在我国存在体制内、外的差别,这对制约强制性权力、防范工作场所侵害产生实质性影响。其一,体制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和体制外(私营、港澳台、外资企业等)的组织相比,体制内组织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总体上更高一些。其二,由于体制内工作具有高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体制外的工作,考核和竞争压力相对较小,组织内部人员之间的直接冲突也相对较少,“对人的关怀更多”。其三,体制内雇员相对体制外雇员而言,自身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网络”的存在,有助于对工作场所侵害的抵御和曝光。相较而言,体制外组织在用工制度上自主性更大,雇员权益保障相对较弱,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制衡机制都比较欠缺。在体制外工作的受访者普遍认为,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员工之间氛围并不友好”,“效率最大化(对企业)是最重要的,员工的处境安危、健康与否不是它要考虑的”。
综上,工作场所侵害的发生率与组织对强制性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处理的渠道和机制密切相关。就本研究而言,对组织类型的划分,最重要的维度体现在体制内外之别,我们由此提出假设2:制度规范性对工作场所侵害有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体制内组织的雇员相比,体制外组织雇员成为受害者的概率更大。
3.市场环境:资源可替代性与权力边界
替代性是另一个对工作场所侵害发生率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它超越了权力不平衡的双方的个体特征和互动关系发生的组织场域,把制度环境的因素带入到分析框架中。权力的作用范围是具有边界的,如果弱势一方能够在组织之外获得其认为重要的、原本由组织内强势一方提供的资源,这将对原有的权力关系带来根本性的冲击和颠覆,权力不平衡的程度会大大降低。
就工作场所侵害而言,受害者所看重的重要资源(工作收入和福利)如果能够在组织外部的劳动力市场中较为容易地获得,那么让自己持续面临受害风险的可能就会降低。当我们把视角投向组织之外,考察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市场环境之间的结构性因素时,可以推论,在一个充满机会、更为健全的市场环境中,由于存在大量的工作机会可供选择,雇员离职的机会成本更小,对“跳槽”的接受度也更高,由此带来更好的流动性,有助于降低侵害发生的可能性。因此,组织外部资源的可替代性程度,对工作场所侵害的发生率具有重要影响,我们因此提出假设3:资源可替代性对工作场所侵害有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在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落后,雇员成为受害者的概率更大。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的混合方法。通过持续6个月的定性访谈资料帮助形成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继而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即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以检验假设,在数据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深度访谈的个案细节,进一步加深对工作场所侵害过程、机制和定量结果的理解和解释。
定性数据部分,笔者在2021年1月到6月之间,对年龄在25岁至59岁、至少有五年工作经验的男性/女性进行了访谈。在访谈对象选择上,为获得更深度的资料,笔者优先选择在工作中有过被侵害经历的访谈对象。此外,访谈研究力求在地区、单位类型、职级、教育背景和行业等方面保持案例的多样性。由于研究话题在部分受访者看来属于个人隐私,涉及内容敏感,最终接受完整访谈的被访者为20人。
基于研究框架和可获数据,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工作场所受侵害”,在CGSS2015中有这样一道题目:“过去五年,您在工作上是否被上级或者同事侵害过?例如:受过欺负,或者身体及心理上的伤害?”剔除回答“不适用”和“无法回答”的观测值,将回答“是”者赋值为1,回答“否”者赋值为0。
自变量方面,本研究从依赖性、强制性和可替代性三个维度来衡量权力不平衡程度。自变量之外的其他个人因素和雇员所在组织及其工作的情况都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访谈案例
多位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五年的工作经历中受到过不同程度的侵害,各行业、各类型的工作场所均出现辱骂、排挤打压、侵犯私生活等情况,多人表现出了在压力之下的无力感,有人受到身心伤害后生病住院,甚至产生抑郁厌世的念头。这对受害者本人、家庭,甚至是社会都带来恶劣的影响。
2.CGSS2015数据
在包含了666个观测值的最终样本中,我们发现有16.37%(n=109)的被访者表示在过去五年有过在工作场所被上级或同事侵害的经历。鉴于报告的时段为“过去五年”,与国外研究发现相比,我国的报告率相对较低(例如北美WBI 2021年最新调查中,一年内的侵害报告率为30%)。这一比率可能是实际发生率的真实反映,也可能是低报或瞒报的结果。在回答受到侵害的人中,性别、户籍等因素在工作场所受侵害的报告率上没有显著差异。
(二)Logistic回归分析
将测量“权力不平衡”三个维度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放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个体层面,雇员从当前工作获取的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侵害发生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1%(e0.01-1=0.01);有正式工作合同的雇员相比于没有合同的雇员,成为侵害受害者的概率高了74%(e0.55-1=0.74)。组织层面,与体制外组织的雇员相比,体制内组织的雇员受到侵害的概率减少了近一半(e-0.62-1=-0.46)。市场环境层面,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侵害发生的概率降低27%(e-0.32-1=-0.27)。综上,本研究提出的基于权力三维度的研究假设,获得了经验数据的支持。
讨论与结论
在本文提出的以“权力”视角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下,在个人层面,个人从工作中获取的资源的重要性决定了弱势一方在权力不平衡关系中的“依赖性”,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越重要、福利越完备,个人对这份工作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就越容易隐忍求全。在组织层面,组织在制度设置和运行上的规范程度会制约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施行“强制性”权力的可能性,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中,我们发现体制内组织相对体制外组织,为员工避免成为受害者提供了更好的制度支持。在市场环境层面,外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可替代资源越多,越有助于弱势一方从对组织的依赖性和组织内部对其施行的强制性中解脱出来,在本研究中,这种可能性来自提供了绝大多数就业机会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
本研究的实证发现也具有一些实践意义和政策意涵。从资源依赖性角度来看,政策的着眼点需放到如何降低被害者的潜在经济损失、如何为其赋能上。例如,可以提高因工作场所侵害而造成的非自愿失业的保险保障水平,从而减弱因失去工资收入对个人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冲击;另一方面,公益组织可以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经济资助,同时,司法部门在处理和判决中应充分考虑举报者潜在的经济损失,对其进行充足的赔偿,这些制度性的支持都能降低受害者对现有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的依赖性,鼓励其在初次受到侵害时能趋利避害,甚至勇于成为吹哨人。从制度规范性角度来看,应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群团组织的规范运行,发挥其对组织内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实现对劳工权益的有效保护,从而充分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资源的可替代性角度来看,应该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还要进一步理顺劳动力流动机制,消除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这些举措都有助于减少劳动场所侵害的发生。除上述方面,加强相关知识和法规宣传、培养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提高管理者职业素养也十分重要。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贯彻执行应该为防止和惩戒工作场所侵害提供底线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