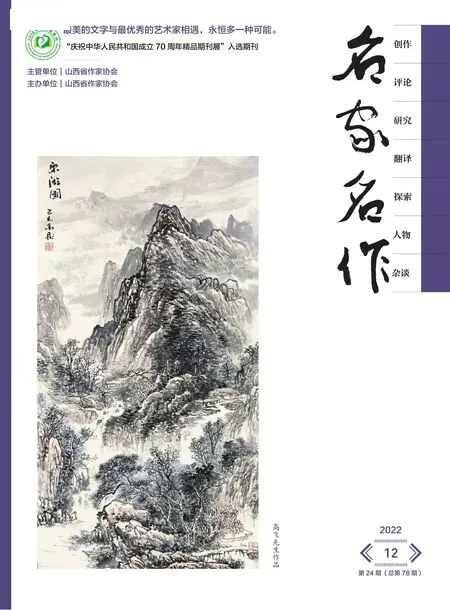青藤树,大学,我
宋 军
一
老家的屋子,有许多的妙处。首先单是在外面支起棚子,就能让青藤爬满,构成一片夏日里不可多得的荫蔽所,这是如今的楼房比不了的。这棚子是爷爷搭的,起初是为了晒肉,后来他年纪大了,做不动重活,于是便任由青藤爬满。等我到了能满地跑的年纪,那片青藤已经几乎覆掉了它们能去的所有的地方。佳兴是我儿时最好的朋友,这小子讲义气,又实在,还“傻”,作为朋友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平日里他总揣着几块钱,总是被我借来,然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用来换烤香肠或者甜冰棒。那时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在那片青藤底下打牌,有时候是最传统、最朴素的扑克牌,有时候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一种卡片,拍在地上看谁先打翻对面的便算是赢了。他又憨又呆,自是赢不了我的,但我也不会一直赢。有一次我竟把他赢得哭了,后面连着几天我都见不到他,打那以后,我知道了,做朋友是不能一直赢的。
自我学会偶尔放松,让他赢几次之后,已经是初中的年纪。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老家屋子的第二个妙处。那个屋子也不知道是怎的,我竟一直没注意到一楼不像现在,家家都是有防盗护栏的。许是老爷子孤身寡人,也不怕人偷。父母工作甚忙,一到寒暑假就把我送回老家,让老爷子看管。可老人岁数高,活动的时间自然是跟小他六七十岁的小孩子无法相比的。他每日九点便要睡,睡便睡了,偏要我也遂了他的作息。作闹几番,仍无可奈何,只能作罢。后来有一日,我趁他睡着,趴在床边的窗上往外瞅,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距离自由不到一米。只要掀开窗户往外一跃,我便获得了新的世界。于是当晚我便在屋子里数着念头,等老头睡着,溜了出去。其实出去了也无甚可做,只是在各处闲逛,但就是觉得高兴,打心眼里觉着开心。在黑暗的衬托下,瞧着什么都别有一番滋味。有时候我跳出来所幸哪也不去,就是把椅子拉来躺在青藤树下,任风吹过,听那片叶子沙沙作响。多年以后,我偶尔会想起这件事情,我仍记得自己头次回忆起这件事时的那个念头,就是以后我一定要在自己孩子的房间里装上一个防盗网。
像往常一样,那天我照例等老头睡着,跳了出去。那次我直奔大街,在路边寻找一只野猫,那是头几日我新遇见的朋友,它只在几个固定的地方出现,我那阵子把每日瞧见它一次作为冒险的目标。约莫两条街过去,我听见不远处有些动静,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过去。但那动静却非一只猫在作祟,而是一个人提着个布袋子在垃圾桶翻找什么。许是他听见了我跑过来的动静,或是他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他回头看去,正好与我的目光对视。我俩都一愣,倒不是因为彼此在黑夜中相遇,而是因为我们认识。
这个中年男人是个体面人,我是一直这么以为的。在他老婆生病之前,每逢过年都要给三街四邻做上一大锅饺子,然后挨家挨户送过去,好像不道上一声“新年好”,这年便不算过似的。别的不说,他包饺子和馅的手艺是有一手的,我每次吃完都想去再要一碗,但每回都让我妈给摁住了,她总是一边笑一边说“你个小要饭的”。后来也不知道是哪年起,他不再给大家送饺子,起初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他在新年十二点前来敲我家的门,然后在一声声热闹的祝语中把一碗饺子留下,是自打我出生以来就定好的,是像领红包、看电视、听爆竹一样天经地义的事。但他不送了,后来我也便像其他的大人一样,习惯了这件事。我从大人们的闲言碎语中大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之前是个做小买卖的,后来老婆生了病,便把生意卖了,一直在陪老婆全国各地跑,治病。但癌症就是这样,任你再一厢情愿地想也没办法。
“人没了,房也没了,原来多好的一家子,真可惜了。”
“还好没孩子。”
也不知道怎的就记住了,很好的一家人和没有孩子,是我关于那个男人身上的标签印象最深刻的两个。所以我在那个晚上跟他相遇的时候,心里是不害怕的。我看到他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东西是个塑料瓶子。显然他也没有料到,在那个时间居然会有人在这个无趣的镇上闲逛。我见他开了开口,似乎想说话,但却没说,只是一只手打开了袋子,然后将瓶子装了进去,缓缓地转头走掉了。我一直没有动,直到他的身影转过街角再看不到也没有动,只觉得自己头晕晕的,像是之前发烧的感觉一样。我讨厌生病,所以怕自己生病。于是我又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老屋子里,敲门把老头子弄醒,让他给我量体温。结果我没病,但在转天的夜晚以及之后的无数个夜晚中,我再也没有遇见那只猫和那个男人。我后来问过我妈,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结果连她也忘记了。
二
对于我的童年来说,甜蜜是离不开的。老屋子附近总是有卖各种好玩意的地方,马蹄酥、枣泥糕,还有冬天里烫手的甜山芋,有唱不完的歌和穷不尽的快乐。等到了少年,就仿佛刚登上陆地的第一批鱼一样,我睁开了眼,开始看这个世界,开始学习那些学不完的知识。我贪婪地将自己的意识挤进每一个我未曾踏足的世界,然后在目光所及之处选择一个最高的山顶,骄傲地向世界宣布自己所拥有的美好未来。
写下这些文字的晚上,外面梅雨初过,行人寥寥,叶落匆匆,屋檐上的雨水顺着窗沿落下,拍打在我养在阳台的那几盆小花里。此刻我心情杂乱,竟似乎敏感地听见那些花儿欢呼雀跃的声音。思绪回迁,仿佛看到二十余年前那个也是五月,也是初雨的,相似的夜晚,我坐在老家的那个旧藤木椅子上,顶着白炽灯在半夜一点复习着我憎恶的数学,紧张忐忑地数着时间,既期待又害怕着高考的到来。我看不见未来的模样,只能通过把脑子扎进知识里,在透出水面换气的瞬间靠着幻想撩拨开未来的面纱。如今的我坐在时间的这头,回望过去,我看到那个奋力向前游的自己,除了感激,还是感激。我如今的全部生活,都是靠那无数个挑灯夜战的日日夜夜得来的。
将思绪拉回到很久以前,一列火车载着一群怀揣着各自理想的大学生来到了“象牙塔”。我记得在那群稚嫩的“天之骄子”下车之后,拼命地呼吸着来自广袤平原新鲜的空气,那种气体灌入肺部的满足感让当时的我切实感受到一种幸福,一种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唾手可得的幸福。我对自己即将遇见什么样的人,自己身上发生什么样的事一无所知,但是偏偏就有一种确信,确信自己会在这里生活得很好,确信自己人生的起点就是在这里。
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带着信念来的。
但是,生活很怪,你不知道在哪个转角就迎来了波折。在来到大学之后的一年多中,我几乎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我被突如其来的自由撞击得失去了方向,我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离开了曾经的束缚,同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离开了过去的束缚,变得放荡不羁,不受约束,变得聒噪,变得懒惰,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草原上放肆奔腾,漫无目的,用尽浑身的力气,奔跑在旷野,奔跑在风中;这种生活是自由自在的,是非常痛快的,你不必去考虑任何人的感受,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不会有人对你说教。但是,自由的时光总是会有额度,你最终消耗光了你的额度。面对余额不足,你开始恐慌,你坐立不安,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一晃的时间,你就要突然面对另一种世界,一个你感到陌生和危机的成人世界。你根本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你压根就没有去准备,你曾经以为过去的这种自由时光将永远没有尽头,并沉浸其中,麻痹自我,殊不知自己将被滚滚的巨浪所吞没,把你带去另一个世界,你彷徨,你挣扎,你哭泣,你愤怒,然而无用,你只能独立面对这个未知世界。
在那时,我虽然开始走向独立,但我从来没有感到孤独。我的舍友陈小于、刘启明,同班同学陈斌、涂立公,我们在一起恣意高歌,一起奋斗学习,也一起熬秃了头。我的老师莫伯华、方长江、郑敏,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完成了学业,完成了成长,实现了一个更加完善、成熟、优秀的自己。也正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像个成年人一样思考,开始思考社会与自己的关系。在大学的四年生活中,我从过去的家庭包裹中破壳而出,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这是一种美妙的新生,大学就是很多人重新来过的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我有无限种可能。
春华秋实,四季衔尾 ;冬去夏归,桃成李就。四年时间,对于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学校来说,称为刹那也不为过。但对于一个人,四年可长可短,可薄可厚。从我们第一次迈出踏入学校的脚步起至我们毕业,也就是四年。在这四年里,在众多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我们逐渐褪去稚气,满载着希望地从青年向着成熟一点点长大。在这四年里,有的老师为了学生白了头发,还有的为学生的学习殚精竭虑。老师对学生视如己出,关爱照顾,千方百计地帮助学生进步成长,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每一位为我付出过、尽心过的老师。
三
自我大学毕业以后,兜兜转转,我又回到大学,成为一名老师。童年那处老屋子和附着在那屋子外的青藤早已埋葬在记忆的深处,小时候喜欢到处跑的爱好,变成了长大后散步的习惯。这么多年的时间里,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人越老越喜欢回忆。现在回忆起来,印象里捉迷藏玩得最开心的年纪,一定是大家选一块儿质量上好的纱布,蒙住一个人的眼睛。在嘻哈的笑声中轻蔑地听着他倒计时,然后各自消解在环境里,等待游戏的开始与结束。我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玩这个游戏,这大概就是我很喜欢雾天的原因。从夜里醒来,窗上的水汽像是帘子一样挂在外面。目之所及不过百米,睡眼蒙眬地打个哈欠,有种从一个似幻而非的梦境中跌入另一个幻境的穿越感,唯有道路上整齐排列的拥挤的车灯,提醒着你这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总觉得雾天是生活在与我们玩捉迷藏,只不过这回是生活把自己藏了起来。
太阳在雾天照常升起,我在雾天照常来到学校。只为看那些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一眼,便理解了生活的趣味在于无端平添的那些变化。远远看去,那个捧着书的少女雕像,像是朦胧在一段丝绸里。久久看得出神,竟品出几分维纳斯的神韵。漫步在操场上,浑然被一种神秘而诡异的气氛包裹住,若是看过《迷雾》《降临》之类的电影,大概就会开始期待起雾后会出现异形生物或者古神之类的东西。走上那么一会,脑海里就已经与无数的怪物大战了几天几夜。为这场冒险画上结局的,是那边楼里传来的早读声。楼前伫立着旗杆,国旗的颜色在一片白景里显得格外显眼,只是那日无风,它便在那儿安静地聆听着来自未来的钟声。在大雾天里,校园里的树也没什么想法,只是在那儿不紧不慢地等着云破雾开,再去贪婪地享受阳光。不同于雨天,下雨时我在教室里仿佛能听见它们欢呼雀跃的喊声,今天大概是雾让所有的事物变得有些慵懒。透过这层薄雾,生活又变得有趣了。
午休,我闭上眼假寐,思绪回迁,又跑进了上午那片雾景。只不过这回我出现的地方不是操场,是那个老屋子,我出现的年纪也不是当下,而是那个喜欢追小猫的岁月。爷爷在青藤爬满的棚子下,左手端着一杯凉茶,右手半搭着一把蒲扇,坐在太师椅上怡然自得。他对面的老邻居眉头紧皱,盯着棋盘久久不动。见我过来,爷爷问我假期为何来得这么晚,学习可有长进,考试怎样,吃饭怎样。待我一一答完,棋盘那边已走了一步,他便打发我几块钱让我自己去玩。我穿过薄雾,按照记忆中的路去寻那户男人的住处。我敲了敲门,开门的却不是印象里的那个男人,而是一个与我一般大的小孩。我俩都不说话,他便先开口,问我找谁。我不知如何作答,只是站着,于是又来了一个女人。她认识我,叫出了我爸妈的名字,问我来此有什么事,还说要留我吃完饭。原来她丈夫去外地做生意,这孩子是他们的儿子,叫冬冬。我心满意足,没有留下吃饭,跑回老屋子同爷爷告了别,还祝他武运昌隆,功不唐捐,便趁着黑夜未临、薄雾未散,回去了。
大学时偶尔还与佳兴有些联系,毕业后听同学说,他后来考上了辅警,再后来又考上了警察,而今天天加班,据说头发掉了不少。老家的屋子如今还留着,只是屋外的棚子被街道批评说占用公共场地,于是便拆掉了,听说因为那棚子上的青藤长得很密,当时还费了不小的劲。不过还好,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如是,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