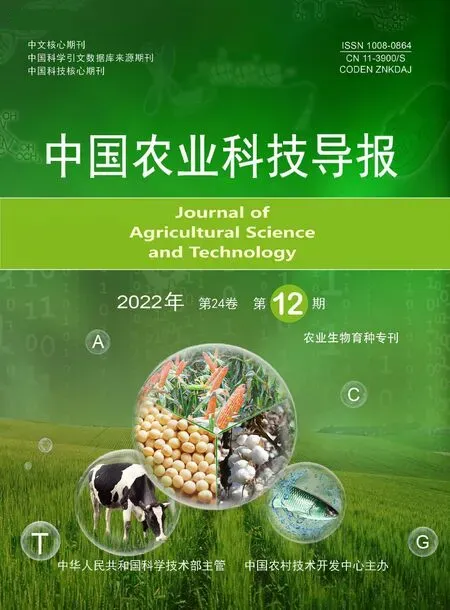重要养殖鱼类生物育种技术研究
孙永华 , 胡炜 *
(1.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武汉 430072; 2.湖北洪山实验室,武汉 430070)
鱼类等水产品作为蓝色食物,被公认为优质的蛋白源,在保障世界约30亿人的食物和营养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022年8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了《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再次明确指出,渔业和水产品现在和今后在为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营养方面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渔业只能通过不断发展水产养殖来实现[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水产养殖产量持续增长,成为大农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近30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水产养殖大国,水产养殖产量约占世界产量的60%以上,当今我国人民餐桌上近1/3的优质动物蛋白来源于水产品,中国水产养殖的成功经验也为世界所瞩目[3]。水产种业和新种质创制是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头和关键。因此,综合利用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生物技术学等方法开展鱼类等水产动物生物育种,创制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的水产新种质,将有力推动现代渔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是践行大食物观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
自然界存在的鱼类种类繁多,目前已知有3万余种,占到脊椎动物种类总数的一半以上[4]。如此众多的鱼类,其生长和繁育特性各异,为鱼类生物育种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种质资源和基因库。鱼类具有怀卵量大、体外受精、体外发育等优良特性,许多鱼类具有雌雄生长的二态性,不少遗传距离较近的鱼类物种间可以形成杂交品系,这为其生物育种和种质创制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和便利。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水产养殖的国家,2019年,日本学者通过研究公元前河南贾湖遗址中发现的鱼骨,发现鲤的咽喉齿具有养殖的特征,由此推断早在8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开始了鲤的人工养殖[5]。约公元前460年,范蠡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水产养殖专著《养鱼经》,记载和描述了在池塘中投放性成熟的雌雄鲤亲鱼配对、鱼苗繁育和成鱼养成的过程。我国鱼类选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晋朝(公元266—420年)对金色或红色鲫突变体的选择,此后1 000多年间经无数金鱼爱好者一代代的努力,育成了如今300多个金鱼品种。20世纪50年代,我国突破了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a)、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鳙(Aristichthys nobilis)“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6-8],解决了制约鱼类养殖苗种生产的瓶颈,掀开了我国水产养殖的革命。生殖是鱼类优良品种培(选)育与扩群应用的前提,“四大家鱼”人工繁殖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鱼类遗传育种的发展,随着现代遗传育种理论与生物技术的创新发展,我国已经在养殖鱼类中建立了选择育种、杂交育种、多倍体育种、性控育种、基因转移育种等技术,开展了鱼类基因编辑育种和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实践,并在鱼类生殖干细胞和生殖开关等前沿育种技术方面进行了尝试。利用这些技术创制出养殖鱼类新种质,培育出具有优良性状的养殖鱼类新品系和新品种,驱动和支撑着我国水产养殖的高质量发展。
1 鱼类选择育种和杂交育种
经典的选择育种是指从野生或已有的品种中根据表型特征进行多个世代的筛选,直至获得具有稳定优良性状的群体。虽然观赏鱼的选育开始较早,但我国对养殖鱼类的选育直到攻克“四大家鱼”的全人工繁殖技术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起步。1972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了我国首个从事鱼类遗传育种的研究室。随着群体选育和家系选育的广泛应用,我国鱼类遗传育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公告,1996—2022年审定的266个水产新品种中有152个选育新品种,包括鱼类、虾蟹、贝类和藻类等,这些新品种在我国水产养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许多养殖鱼类性成熟周期长,传统的选育需要至少4代的大样本选择,因此养殖鱼类新品种培育周期通常较为漫长和困难。以我国水产养殖的主要对象“四大家鱼”为例,青鱼、草鱼、鲢、鳙的年产量超过1 340万t,约占我国鱼类养殖总产量的48%。但是,目前仅有2010年审定的长丰鲢、津鲢2个鲢新品种,以及2022年审定的首个鳙新品种‘中科佳鳙1号’。草鱼和青鱼都没有新品种。“四大家鱼”的性成熟时间通常需要4~5年,新品种培育至少需要4代选育,再加上小试、中试和品种审定,理论上新品种育成的时间至少需要24年左右。以‘中科佳鳙1号’为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历经近30年,对鳙的生长速度和头部大小等主要性状开展了长期的群体选育,并经雌核发育、遗传标记辅助等手段,才选育出鳙的首个新品种。
杂交育种是指选择遗传背景不同的父母本,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形成具有杂种优势的群体,将父母本的优良性状进行整合的育种方法。杂交育种是被广泛采用的鱼类育种手段之一。根据亲本的亲缘关系远近,杂交育种分为近缘杂交(种内杂交)和远缘杂交(种间杂交)[8]。近缘杂交育种中,最为成功的当属鲤(Cyprinus carpio)的种内杂交。国内外学者先后育成了数十个鲤的优良品系,其中中国学者育成了‘丰鲤’‘建鲤’‘荷元鲤’‘松荷鲤’等30多个新品种。鱼类远缘杂交是亲缘关系属于不同种的个体之间进行的交配。我国鱼类远缘杂交试验主要涉及到鲤形目、鲈形目和鲇形目3个目7个科的40多种鱼类,杂交组合100多个[9]。其中,大多数远缘杂交在不同鲤科鱼之间进行,鲤鲫属间杂交是最突出的代表。湖南师范大学利用鲤科鱼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鱼类远缘杂交基础理论探索和育种技术的重要突破,发现父母本的染色体数目是决定鱼类远缘杂交育种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10],建立了鱼类远缘杂交技术体系[11],先后育成‘合方鲫1号’和‘合方鲫2号’等新品种。进一步研究发现,与父母本比较,远缘杂交形成的杂交鱼品系发生了来源于不同亲本的直系同源染色体之间的基因重组,重组导致DNA修复、非同源末端连接和转座子活性等产生了嵌合基因,嵌合基因分布于细胞周期调控、DNA损伤修复等信号通路,伴随异源基因组的融合,基因表达特征出现显著变化[12-13]。
2 多倍体育种和性控育种
多倍体育种主要是指利用人工诱导或自然染色体加倍的方法,获得整合有3套及以上染色体养殖鱼类新品系的方法。三倍体鱼通常表现出不育、生长快、出肉率高等特性,同时还可以避免杂交从而保护天然基因库,因此多倍体育种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养殖鱼类。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比如静水压、热休克、冷休克、秋水仙素处理等手段,抑制卵母细胞第一极体或第二极体的排出或受精卵的第一次卵裂,是诱导鱼类多倍体形成的重要方式,如用静水压法分别获得了三倍体水晶彩鲫[14]和半滑舌鳎[15]。此外,采用倍间杂交方式,利用四倍体鲤鲫为父本,分别与鲫或者鲤等二倍体鱼进行杂交,培育出不育的三倍体新品种湘云鲫和湘云鲤[9]。
除了人工多倍体育种外,自然界还存在一些天然的多倍体物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发现银鲫(gibel carp,Carassius gibelio)具有天然的雌核生殖方式和异精效应,由此培育出全雌的异育银鲫新品种[16]。进一步研究表明,多倍体银鲫具有单性雌核生殖和有性生殖双重生殖方式[17]。最近的研究发现,银鲫作为一种天然雌核生殖的双三倍体,其自然生殖过程中可以通过抑制减数第一次分裂产生不减数的卵子,从而克服3个同源染色体不能正常配对和均等分离的生殖障碍[18]。在揭示银鲫独特的生殖机制基础上,通过人工雌核生殖并与分子标记辅助等技术结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先后培育出异育银鲫、异育银鲫‘中科3号’和‘中科5号’等系列新品种,呈现出优良的养殖性状,有力推动了我国鲫养殖业的发展[19]。
鱼类摄入的营养物质和能量在性成熟前主要用于躯体生长,很多养殖鱼类的性成熟年龄存在性别差异,其生长特性表现出明显的性别二态性,有的鱼如鲤和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等卵巢成熟晚,雌性个体比雄性个体大;有的鱼如黄颡鱼(Pelteobagrus fulvidraco)和罗非鱼(Tilapia mossambicaPeters)等则是雄性具有明显的生长优势。因此,发掘鱼类性别决定基因和性别特异分子标记,建立鱼类性控育种技术,培育单性养殖新品种一直是鱼类遗传育种的重点[20-22]。目前已经建立的鱼类性控育种技术包括生殖内分泌调控、种间杂交控制、人工诱导雌核生殖、温度控制、内分泌调控与性别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并且在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控制鱼类性别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3]。利用性控育种技术,我国已经培育出养殖效益显著提升的黄颡鱼‘全雄1号’、全雄罗非鱼‘粤闽1号’、杂交鳢‘雄鳢1号’,以及全雌牙鲆‘北鲆1号’、全雌牙鲆‘北鲆2号’、虹鳟‘全雌1号’、全雌翘嘴鳜‘鼎鳜1号’和‘武农1号’等单性养殖鱼类新品种。
3 转基因育种和基因编辑育种
鱼类转基因育种诞生在中国,它开启了基于基因序列和分子遗传学的鱼类现代生物育种的大幕。转基因育种是指通过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决定生物优良性状(如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等)的基因分离出来,导入并整合到受体鱼的基因组中,从而提升原有性状或赋予其全新性状的一项定向育种技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制出世界首例转基因鱼[24],并建立了转基因鱼研究的理论模型[25],开创了转基因鱼育种研究新领域。目前,以提供优质食品蛋白来源为目的,全球已诞生了30多种转基因鱼,这些转基因鱼包括了世界水产养殖的许多重要品种,如鲤、罗非、鲇类(Silurus asotusLinnaeus)及鲑 鳟 类(Salmo salarLinnacus)等,其目标性状包括促生长、抗病、抗寒、抗低氧、提升营养品质等诸多方面[26]。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培育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growth hormone,gh)鲤——“冠鲤”家系。冠鲤比对照鲤的生长速度提升42%~115%,饵料转化效率低17.1%~18.2%,具有显著优良的养殖性状。按照国际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评价规范,全面、系统、严格的科学研究表明,冠鲤与普通鲤具有同样的食品安全性和生态安全性[27]。2015年底,转gh大西洋鲑在美国获得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例获准产业化应用的转基因动物食品。2017年8月,转gh大西洋鲑在加拿大首批售出 1万磅(约 4 535 kg)。历经长达30余年的研发与严格安全性审核,转基因鱼才获准产业化,严格的科学管理和安全性检验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食用产品。
与选择育种等传统的育种技术不同,转基因技术还能实现“超越性状”育种。比如,本团队将仅存在于低等蠕虫基因组的编码脂肪酸Δ15和Δ12去饱和酶的基因fat1和fat2转入斑马鱼基因组,使鱼类首次获得了从头合成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超越性状[28]。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出了与三文鱼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相当的fat1转基因黄河鲤——海优鲤,海优鲤还表现出抵御过度投喂导致的脂肪肝等优良特性[29]。
基因编辑育种是指通过靶向核酸酶技术对内源基因组序列进行定点改造,从而达到改变和提升目标性状的一种育种技术。近年来,各种靶向核酸酶介导的基因编辑技术在斑马鱼等鱼类物种中得到飞速发展,如锌指核酸酶(zinc finger nucleases,ZFNs)、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物核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TALEN)和 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ers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as9 技术等。相对于ZFNs和 TALENs而言,CRISPR/Cas9 系统组分较为简单并可达到更高的效率,因而CRISPR/Cas9系统成为发展最快的基因编辑技术并且广为所用。CRISPR/Cas9系统利用1个短的通常含有约20个碱基靶序列的向导RNA(gRNA)结合到它的DNA互补靶点,并介导Cas9核酸酶到此靶点切断靶序列从而造成双链断裂(double-strand breaks,DSBs)。这些DSBs一般通过非同源末端连接方式(nonhomologous end-joining,NHEJ)或同源介导的DNA修复机制(homology-directed repair,HDR)进行修复,从而引入定点突变或定向碱基改变,以达到移除“有害”基因或增强“有益”基因的目的。近期,研究者又开发出更加精准的基因编辑手段,如碱基编辑器(base editor,BE)和导向编辑(prime editor,PE)[30-31],可以实现单碱基或小片段的精确改变或置换,在基因编辑育种中表现出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28家机构联合完成了斑马鱼1号染色体全基因敲除计划,首次实现了脊椎动物整条染色体的系统性基因敲除[32]。该计划产生的所有突变模型全部保藏在国家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为我国提供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模鱼类遗传育种模型库。在重要养殖鱼类基因编辑育种研究方面,目前已经建立了黄颡鱼[33]、虹鳟[34]、罗非[35]、斑点叉尾鮰[36]、黄鳝[37]、鲤[38]、半滑舌鳎[39]、鲫[40]、小体鲟[41]、泥鳅[42]等多种重要养殖鱼类基因编辑技术,创制出高产、优质、抗病、性控等养殖鱼类优良种质。最近,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和华中农业大学以斑马鱼为模型,利用CRISPR/Cas9技术分别敲除斑马鱼的bmp6和runx2b基因,获得了肌间刺显著减少的斑马鱼突变体[43-44],为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最终实现生长发育完全正常且无刺的养殖鱼类育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4 全基因组选择育种
2001年,挪威学者提出了基于随机群体的基因组选择(genomic selection, GS)方法,该方法成功应用于畜禽等养殖动物的育种,对低遗传力性状选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鱼类很多重要经济性状由多个微效基因决定,针对基因组序列清晰的育种对象,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对特定性状具有重大贡献的基因型或分子标记进行综合选择,将有可能获得目标性状更强的育种群体。国内外已经完成了大西洋鲑(Salmo salar)[45]、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46]、虹 鳟(Oncorhynchus mykiss)[47]、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48]、鲤[49]、草鱼[50]、牙 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51]、小 体 鲟(Acipenser ruthenus)[52]、银鲫[18]等养殖鱼类的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图谱绘制,越来越多的鱼类重要经济性状相关的功能基因得以发掘和解析。这使得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在越来越多的养殖鱼类中成为可能[53]。而且,鱼类体外受精和发育,怀卵量大,家系群体构建非常方便,有利于从大量样本中进行全基因组分析和选择,鱼类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54-55]。
基因组选择育种的前提之一是可以对全基因组标记基因型进行高通量测定。目前较为理想的基因型标记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利用全基因组的SNP位点可以估算个体的育种值,在某些全基因组获得解析的养殖鱼类中已开发出相应的SNP育种芯片。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尚无参考基因组序列的养殖对象,则可以开展诸如基于限制性酶切DNA测序(restriction site-associated DNA sequencing,RAD-seq)等简化基因组测序分析。我国学者先后开发出鲤、牙鲆、大黄鱼等养殖鱼类育种芯片,用于生长或抗病相关性状的育种实践[55]。相对于基因组选择育种在畜禽中的广泛应用,其在鱼类等水产动物中的应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水产动物生活在水体中,对其表型进行精确测量相对较为困难。因此,未来需要大力发展基于全息影像学、人工智能等高通量鱼类表型性状精准测量技术,建立表型数据库,并研发适用于鱼类的全基因组算法模型等。
5 生殖干祖细胞育种和生殖开关育种
干细胞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无限自我更新和分化潜能的一类细胞,生殖干细胞则是成体性腺中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和分化为成熟配子潜能的一类生殖细胞。依其存在于精巢或卵巢中的不同,生殖干细胞可分为精原干细胞或卵原干细胞。除了成体性腺中的生殖干细胞之外,鱼类胚胎中还存在着一类生殖细胞的祖先细胞——原始生殖细胞。这些生殖干祖细胞(germline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GSPC)为开展遗传操作和高效育种提供了绝佳的靶细胞,这是因为,一方面GSPC是个体中唯一可以向子代传递遗传信息的细胞类型,另一方面GSPC可以通过移植到同种或异种体内以改变自身的配子发生进程,实现“借腹生殖”。很多鱼类的性成熟周期为几年甚至十几年,育种周期漫长,因此将育种周期长的鱼类GSPC移植入育种周期短的鱼类中实现借腹生殖,将有望从根本上加速育种周期。
原始生殖细胞在胚胎期即可以被方便地标记和分离,因此对于易于获得胚胎的供体鱼来说,是最为便捷的借腹生殖技术途径。鱼类原始生殖细胞移植借腹生殖首先在斑马鱼中实现[56],后来日本学者又将荧光蛋白标记的虹鳟原始生殖细胞移植入山女鳟性腺原基,首次实现了鱼类跨物种的借腹生殖[57]。精原干细胞可以通过解剖成鱼或幼鱼的精巢分离获得,通常移植的窗口期更长,因此成为使用更广的一种借腹生殖技术[58]。本团队利用斑马鱼模型,优化了基因编辑原始生殖细胞的诱导和移植体系,首次实现了鱼类基因编辑配子的借腹生殖[59];更进一步,以跨亚科物种的稀有鮈鲫和斑马鱼为对象,将基因编辑的稀有鮈鲫精原干细胞移植入斑马鱼幼鱼性腺,利用斑马鱼首次产出了跨亚科物种来源的基因编辑鱼类配子[60]。将基因编辑与GSPC移植借腹生殖技术相结合,是养殖鱼类高效和定向育种亟待发展的重要生物育种技术[61]。
养殖鱼类的生长速率、肉质等重要经济性状与其性腺发育特性密切相关。如果控制了鱼类的性腺发育,其摄取的食物将更有效地转化为体细胞的发育。鱼类性腺发育被抑制后,鱼体的品质明显提高,因此培育不育鱼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同时,不育鱼的应用也有助于保护种业企业的知识产权,避免养殖户盲目杂交、回交而导致养殖对象种质退化的问题。此外,转gh大西洋鲑获准产业化,取得了基因工程育种研究与开发应用的历史性突破,迅猛发展的基因编辑技术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养殖鱼类优良种质创制。但人们对遗传改良养殖鱼类新品种的担忧是制约其产业化的瓶颈,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基因改良鱼类的生态安全性与其繁殖特性密切相关,如果控制其育性,则逃逸或释放到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基因改良新品种不会形成优势种群而影响物质多样性,更不会通过有性交配方式导致基因漂移影响遗传多样性[62]。本团队提出了鱼类生殖开关育种策略。以斑马鱼为模型,通过巧妙设计的靶向原始生殖细胞发育的诱导型Gal4/UAS元件系统,初步建立了两系可育、子代不育的鱼类育性可控的生殖开关模型[63]。基于可控原始生殖细胞开关技术生产不育子代,是鱼类精准育种的重要途径之一[61]。进一步发掘重要养殖鱼类生殖发育调控关键因子,揭示其调控网络,在此基础上与基因编辑、分子设计、干细胞和“借腹生殖”等技术结合创建生殖开关的关键技术,将从根本上提高养殖鱼类的育种效率,实现养殖鱼类新种质开发利用、遗传改良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及其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6 鱼类生物育种技术展望
养殖鱼类的生物育种技术已历经选择育种、杂交育种、多倍体育种、性控育种的成熟运用,培育出当前应用于水产养殖的众多优良养殖品种。在养殖鱼类转基因育种、基因编辑育种、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等生物育种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我国诞生了一批重要的高技术成果和优异新种质。得益于模式鱼类等研究,在生殖干祖细胞育种和生殖开关育种等鱼类生物育种新技术的研发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技术突破,亟待应用于养殖鱼类的育种实践。
我国海域辽阔,江河湖泊众多,为众多鱼类提供了良好的繁衍空间和生存条件,为开展养殖鱼类生物育种提供天然种质资源和基因库。如何系统地保护好这些宝贵的种质资源和基因库,是当前和未来鱼类生物育种中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2019年,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设立了国家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国家海洋水产种质资源库、国家淡水水产种质资源库3个国家级种质资源平台,为鱼类等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养护和科学利用提供了新的国家平台。
我国科学家已经完成了诸多养殖鱼类的全基因序列图谱绘制,并发起了万种鱼基因组计划[64],对重要养殖鱼类的功能基因组进行系统解析,规模化发掘生殖、性别、生长、抗病、抗逆、营养等重要决定经济性状的功能基因和调控模块将成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为了提升转基因育种和基因编辑育种的精准性、特异性、适用性和安全性,亟待发展养殖鱼类中精准高效的基因定点敲入技术以及碱基编辑器和先导编辑等精细编辑技术。针对全基因组选择育种中养殖鱼类表型精确测量的痛点和难点问题,迫切需要智能遥感、远程控制、多维影像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建立和完善水产动物的下一代高通量表型测定技术。
鱼类具有丰富的性别决定和生殖方式,性腺发育和配子发生的高效和可控是鱼类生物育种和繁育扩群的基础和前提。未来需要加强鱼类性腺发育和配子发生的基础科学研究,解析鱼类生殖细胞-性腺体细胞互作、GSPC-配子转换、卵-胚转换等关键生物学事件的分子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不同养殖鱼类的繁育问题。在此基础上,将GSPC-移植借腹生殖技术成功应用于繁殖周期漫长或繁殖困难的养殖鱼类,将显著缩短其育种周期,提升其育种效率;另一方面,由于供体GSPC分化为精子或卵子仅由受体鱼所决定,因此有望利用GSPC移植借腹生殖技术产生仅含有单一性染色体的单性配子,从而开辟出性控育种的新途径[65]。然而,如何建立源源不断提供借腹生殖供体GSPC的“万能供体”鱼,培育免疫稳态可控、性别定制的“万能受体”鱼,是鱼类借腹生殖领域亟待攻克的重要技术难题。近期,本团队取得了单因子诱导PGC高效移植的初步成功[59],建立了体内扩增精原干细胞的突变体模型[66],发现调节性T细胞在性腺发育和配子生维持免疫稳态的重要作用[67],为上述借腹生殖万能鱼技术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最后,为了彻底解决生物育种新种质的生态安全风险问题,必需建立更为普适高效的鱼类生殖开关技术。
总之,在未来的鱼类生物育种研究和实践中,需要重视基础研究,大胆创新,果断创制和利用各类变革性技术,并与已有的生物育种技术有机结合,从而创制出生殖高效、繁育可控、生长快速、营养高效、抗病抗逆的集各种优异性状于一体的养殖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