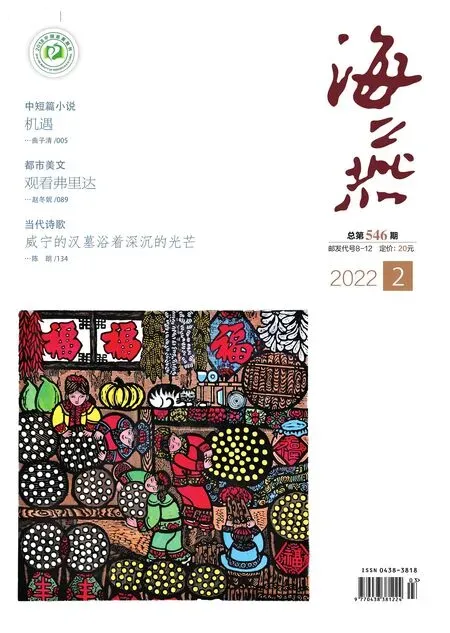一镜容天
文 樵 夫

一
缓缓地坐了下来,望着眼前夕阳下的湘湖,湖面如镜,镜映千峰。休闲椅的前面是一片清萋的草,两块洁净的不规则青石,它们的前方是湖边的蒿草,蒿草此时安安静静,目光越过它们,就是湖面,巨大的,静穆的,仿佛一位阅尽世事的人,心中无波无澜。更远处,就是参差有致的峰峦,几朵浸染着余晖的云,伏于山与水之上。但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被眼前这方巨大的镜子,雍容大气地纳于其中。我蓦然想到右边的那座水榭,水榭飞檐翘角,黑褐色,宋时营造法的工艺,氤氲着宋时的气息,水榭的匾横于榭的正上方:一镜容天。我立即觉出了这座湖的气质。此时,这座朴素、大气、澄澈的湘湖,确如一面巨镜,涵容万物。夕阳加浓了这种雍容的气象,不管在时光的深处,这座湖发生了什么事,不管这些事是如何沧桑了它的心灵与容颜,也不管在时光轴上,一代又一代名人贤士如列队的朝圣者,来谒见或祭奠它曾感天动地的魂灵,也不管它曾有过怎样的潋滟与安静,所有这一切,如今都被它涵纳起来。它没有一声叹息,只是静静地从容地呈现着它的美。
现在,我似乎有了些底气,可以与眼前的湘湖对话。整整三天,我把身子寄在与它一隧之隔的徐元纳大酒店,灵魂的飞鸟却是飞翔在这座湖,或是栖息在哪座亭台或廊檐。对这座人烟寥寂的湖,对它匍伏在大地上的每一条纹理,我都有过认真的观察,对其灵魂以及承载着灵魂的时空,我也有了与之融合般的体察。说实话,我是受了我的唐人兄弟诸如李白、韩偓的引导,在这之前,对这座唤作湘湖的湖一无所知,我一如尘俗中人,也仅是知道名声显赫的西湖,并且将珍宝般的生命时光,毫无节制地抛掷在那口被世人宠坏了的湖面上,让生命时光泛出些虚妄的光泽。面对眼前的湘湖,我越发觉得“言宜慢”的箴言的真理,对一个事物若没有融合般的体察与觉悟时,暂且慢言。而我现在可以说说了。
二
湘湖是有深度的。
一如所有的湖泊或潭,都是大地上的子民,它们都呈现出大自然自在的光泽。它们的分野,就在于跃动于其上的人及人与神、人与大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投射。在别的湖泊,比如西湖样的湖泊,依然在大地上撒欢时,而人,那些以树叶蔽体的人已开始活跃在这座湘湖。在漫长不懈的劳作中,智力的日益增盈给了先民的生存力量与生命尊严,他们用斧凿斫削了独木舟,使他们可以离开陆地,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捕鱼、采菱、摘蕨,他们用斧凿斫削了独木梯,使干栏式居住成为诗意的栖居。在先民漫长的栖居时光中,我只读到智慧与力量的光芒。海侵使先民蒙受了巨大灾难,但他们的悲伤点亮了人类那段幽暗的时光。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湘湖以人的灵性与觉醒,卓尔不群立于大地。本是高昂着头颅的河姆渡人,终于在这些先民面前低下了头,当神性光芒照在河姆渡人身上时,这片光芒定定地照在栖居湘湖的先民身上,其实已越千年。
在大地上许多山川湖泊自由流淌时,时间依旧是曾有的模样,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当时间与空间交集,并发生了亘古未有的事件时,时间与空间便一起被记住了。时间已不再是原先的面孔,空间也不再是大地上的自然空间,它们有了自然所不具备的历史厚度与人文光芒,它们的每一寸肌理都涵养着人的温度与人性的灵光。
这座被唤作湘湖的湖,在公元前2500年被越王勾践称作溟海的巨大水域,已不再是自然的湖泊,这里已开始弥漫着人的气质,氤氲着人性隐忍、坚毅、信仰、不屈的光芒。它是春秋诸侯争霸时越国的军港固陵港。几万艘战船,日夜固守在浩淼的溟海,它们以木质的身躯泊在深湖,守护着越人的梦想,拱卫着勾践一匡天下的宏愿。在那个时间的秩序里,大小诸侯国140多个,空间的狭窄,战乱的频仍,人民苦不堪言。霸主政治渐渐代替周王室正统政治,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第一个称霸。随后,在时间秩序的隧道上,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一个个粉墨登场,每一个霸主登场,诸侯国也纷纷被降纳。时光像只刺球最后抛在了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手上。文字以悲壮、苍凉的气质,记录了那个时间与空间;文字也终于树起了一座永不坍圯的凭吊台。时间与空间构成的坐标上,最后记载着吴越争霸的重大历史事件。《史记·越世家》叙:“无余之后二十余世传至允常,始见于春秋,允常之后即越王勾践。”吴越两国君王都怀揣争霸天下的理想,常发生攻伐战。公元前496年,吴又伐越,吴越两国在檇李(今浙江嘉兴市)开战,吴国战败,吴王阖闾被越兵斩趾最后因伤而死。吴王夫差誓死为父报仇,越王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带兵伐越,在夫椒(今江苏太湖椒山)打败越兵,并一直追至越地湘湖固陵港。越王勾践只剩五千甲士,保守在越王城。城下的旷阔湘湖越国的固陵军港,被吴国十万水犀军围困。尽管越王谋士范蠡用两尾红锦鲤,以馈鱼的计谋,智退水犀军,解了一时之困,但吴军依然重重叠叠地围在了湘湖的外围查浦,两军东西对峙。越王勾践清楚得很,自己五千甲士,已无力抵抗,越国进入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时间哒哒的仓惶声,一声一锤,重重地击打着这位越国帝王,此时,隐忍、大屈、沉雄这些词的大义,都横亘在他的世界。他终于听取了大夫文种与范蠡的谋略请降保越,派大夫文种去向吴王夫差讲和,愿意带上家眷、大臣等300人,入吴称臣3年,服侍吴王。这是何其的大忍大屈,而对于越国来说,这又是何等大悲大喜,人生悲与喜的巅峰同时抵达每一个越人的心灵。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记录下了一个撼天动地的场景:“越王勾践五年五月,与大夫文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阻道,军阵固陵。大夫文种前为祝,其词曰:‘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牵致,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觞。’越王仰天太息,举杯垂涕,默无所言。种复前祝曰:‘大王德寿,无疆无极。乾坤受灵,神祇辅翼。我王厚之,祉祐在侧。德销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吴庭,来归越国。觞酒既升,请称万岁。”何其悲壮的一幕,越王带上300人,行至湘湖,无数的越人,或横舟于岸,或身立水中,将离越入吴的水路围得水泄不通,众人恸哭、哀求,希望能阻止这一屈辱。但勾践、文种、范蠡都知道,大屈必大幸,一切只是时间。
无比的痛苦与屈辱,让人不敢直视时间。三年,每一分一秒,放大它的细节,那都是让人仰天长叹、悲从天降的煎熬。
归越后的越王勾践,不忘会稽之耻,不忘复兴之志。《吴越春秋·卷八》记载:“(勾践)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勾践‘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与百姓同其劳’。”而《国语·越语》也用文字记录勾践躬行实践恢复越国国力的事,“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人民生儿育女,都由政府“令医守之”。这种藏富于民和增加人口、发展生产的国策,经过十几年的履行,使越国国力大增,君民一洗家仇国恨的日子到了,国家复兴的日子到了。越王勾践十五年(公元前482年),卧薪尝胆10年后,乘吴王夫差率军北上国内空虚之际,便命范蠡从海道入淮,断绝吴军归路,勾践亲率大军攻入吴都,斩获吴太子。吴王夫差闻报后,迅速回国,与越求和。从此,吴国再也无力抗衡越国了。公元前473年,也就是越王勾践韬光养晦20年后,越王勾践突然大举进攻吴国,围困吴国3年,最终灭掉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亡。勾践,这个为了越国生存而忍辱负重的君王,终于在春秋末期成为一代霸主。
三
这座湖泊,敦而不言,至今素朴、厚讷、清淳、大气。它的底蕴与内在的功力不知要强过与它仅一条钱塘江之隔的西湖多少倍,但它静静的,不媚,不愠,不躁,与时光一起,摆着自己的钟摆,它只等待懂它的人,或者也不等,它只自顾自地蹲坐在时光深处,看天空云卷云舒。
一个有着灵魂光泽的地方,不管其姿态如何低调与沉默,它总会吸引后来者投射的目光。而究其实质,任何拜谒与登临,或者是气息的相投与吸引,是灵魂相互凝视后的拥抚和对寰宇生灵体悟后的深情握手,或者是灵魂与之凝视后的警醒与人性的归正。
唐代诗人来了。一个一个灵魂,拜谒着这方圣地。
唐人李白在《秋下荆门》中就表述了他舟出荆门,越地剡水是他远行的目的地,“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越地剡中一定有他灵魂的镜像。到了金陵城,在那个因西晋诗人孙楚登高吟咏而名的“金陵西楼”,李白依然一落笔,就将吴越之地揽入视野,“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吴越”。越地一定有着让他魂牵梦绕的山川湖泊以及叩响他心灵的人与事。
想必是越王台,高耸在李白的眼前。
这座筑于越王城山上的越王台,这座巍然屹立于湘湖东北边的越王城山,因为越王允常与其子越王勾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2500年来,人们在这里找到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精神家园,在这座家园里读到大义、隐忍、不屈、睿智等精神内涵。
与时光对视,时光终究会把它掩蔽的东西,一一返还。
不是每一座山都可以成为凭吊之地,只有那些深掩着重大历史事件,蕴藉着人性之美的山,才最终成为凭吊之地。
李白四入浙江,三入越地。湘湖、固陵、越王城山、越王台,都曾被他的目光凝视或眺望。这年是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25岁的李白,离蜀出荆门,一路奔波来到越地。李白眺望的目光落在越王城山时,越王灭吴凯旋的场景已去千年,辉煌与沧桑都沉入无涯无际的时间之中。时间以静寂而大气的姿态涵纳了一切。他终于写出了一首怀古之作《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越王沉潜20年复兴越国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年轻的李白,也曾心怀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历史的这一幕深深地烙在心灵深处。那是一幅怎样繁盛的图景,战士锦衣还家,满殿的宫女如花似玉,而如今只有鹧鸪飞落在断壁残垣。
诗人李白的内心是丰富的,他的诗升华了湘湖的意义,延展了越王城山以及越王台的多义性。诗人不仅重现了历史的精彩一刻,也审读了历史本身,他将我们带入对时间永恒的思索与关注。面对着自然宇宙与时间的永恒,一个人的一生何其短暂,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称霸春秋,一匡天下,无疑是沉雄、宏伟的,而一改沉溺于凯旋后的浮华与奢靡,躬身于改变历史并让历史向着宇宙文明矢向走,恐怕是更为重要的。
激发人性的美,使人性向真向善向美,这就是湘湖美的所在。
晚唐诗人韩偓写了一首《早起探春》,诗人用一个个意象,叙述了湘湖春天的美。韩偓也是一个才情了得的诗人,他年少时写的诗,就令他的姨父大诗人李商隐称誉不止,说他“雏凤清于老凤声”。看看韩偓的《早起探春》:
句芒一夜长精神,腊后风头已见春。
烟柳半眠藏利脸,雪梅含笑绽香唇。
渐因闲暇思量酒,必怨颠狂泥摸人。
若个高情能似我,且应欹枕睡清晨。
这首诗写得清新、逸致。一切物象在诗中的呈现,究其实质,都是诗人灵魂的呈现。在这首诗中,诗人选择了句芒、垂柳、梅,这可能是湘湖最打动诗人的景物。这么美的所在,暂且忘却时世的衰颓,欹枕睡清晨吧。
与韩偓同时代的晚唐诗人杜荀鹤,直接将湘湖这个地理名称嵌入题目中,他写有《将游湘湖有作》,这首诗依然弥漫着杜荀鹤的精神气质,有着对生的惊悚。杜荀鹤的许多诗歌直击唐末军阀混战造成的社会不堪局面,对晚唐社会沧桑、清冷的深切体验,也多有反映。他的《送友游吴越》,向友人介绍吴越时,对越地山水、旖旎风光,欣喜异常。而游湘湖时,却用了“别意”“潸然”“冷梦”“残篇”“风波”等意象。也许是他来越地赴任时,世事更加不堪入目,湘湖的那轮残月自然进入了诗人暗寂的天空。现在,来看看《将游湘湖有作》吧:
一家相别意,不得不潸然。
远作南方客,初登上水船。
岳钟思冷梦,湘月少残篇。
便有归来计,风波亦隔年。
世事的沧桑,必定会投射在诗人的内心。湘湖那弯钩月,悬于他的天空时,他一定是满心希冀何时能圆。
湘湖,一处灵魂的凭吊地,而凭吊有时又会自我挞伐。
就是那个素来以宫廷遣怀并且霉斑浸上心肺的唐人宋之问,被贬到越地,也是登上越王台,顾盼山川,或许是湮没在历史时光里的兵戈相见的厮杀声,或许是越王勾践扬起的灵魂长鞭,让他有了被鞭挞的痛感。他已是老迈的手,在无情光阴与精神挞伐的双重打击下,颤巍巍地写下《登越王台》,“江上越王台,登高望几回”,弥漫着生命沉雄、悲怆、激越的越王台,终于进入了他的视野,在他生命的尽头,咕咚一声,一丝暗红仿佛一石击下,光斑点点。
唐人之后的宋人、元人、明人,直接以咏湘湖或越王台吊古为题的愈来愈多。越王台或者说湘湖东北的越王城山,一定高高地托举了诗人们的魂灵,每每眺望那越王台时,那沉沉的历史回响,一定如滚滚涛声,漫卷而至。
四
我坐在湖边,闲适地享受着余晖中的习习清风,看时光中的湘湖风韵。我比之我的唐人兄弟幸福的是,我看到了他们没有看到的物事,这就是我不仅看到一个个唐人远去的背影,我还看到其他朝代与湘湖有关的一切灵魂的身影。他们让我对这座湖流连忘返,让我觉出了自己的幸运,我有了一座比之我的唐人兄弟更丰饶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徜徉三天,坐于初夏的清爽、温柔的余晖中,终于可以一镜容天。
在杨堤那座白色雕像前,我诧然、惊喜,然后是长时间地仰望,我觉得只有以这种仰望的姿态,才可以一步一步地靠近他。这座雕像的主人就是杨时。他脸庞清癯,神情端庄,步履从容,衣带飘飘,缓缓捋须,恭而安,目视前方,那眼神里溢满了一个大宋王朝士大夫的灵魂与气度,那是大宋王朝的气象。在他的目光里,我读到这样一些字眼:儒士、清澈、践道、情怀、社稷。与他凝视的瞬间,“程门立雪”的感人场景仿佛一幅画卷展现在我的面前,那是一代代读书人尊师重教的永恒典范,那是读书人求知路上一束燃烧的火把。
现在,我不妨借助那些历史记载,看看这位儒者在历史长河中的形象。《宋史·杨时传》:“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今福建)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1076年),中进士第。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当文字所记载的历史画面与眼前所见的物象碰撞时,我的心灵瞬间温暖且激荡飞扬起来,一下子掂量出了眼前所见物事的分量,一下子对眼前所见景致肃然起敬。这些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一个异常醒目的形象。杨时23岁即为进士,29岁拜师于程颢。4年后,程颢仿若一颗巨星陨落,杨时悲悼。40岁时,他又拜程颐为师,十年不仕,一心只为重振儒家理学。一天,他与学友游酢来到老师程颐宅舍,见老师正端坐着闭目养神,杨时蹑手蹑脚地退出屋,侍立在宅院门前。此时,外面已是雪花飘飞。待到老师程颐醒来时,门外已是积雪深数尺。程颐看到门外的杨时,已俨若一个雪人。杨时60岁时主政萧山,他一心为民谋求福祉。在时光的潮汐中,湘湖已不再是唐朝时那个烟波浩淼的湘湖,而只是一口不大的湖沼,萧山百姓纷纷诉求在这里建一座湖。因为干旱缺水,萧山九个乡的百姓无田可种,日子苦痛不堪。杨时亲自勘察后,应百姓诉求,在萧山城西一公里处的原湘湖区域,“以山为界,筑土为塘”,建成湘湖,从此解了九乡百姓的生存之忧。之所以将这个湖称为湘湖,是因为杨时曾出仕湖南浏阳,“邑人谓境之胜若潇湘然”,故名湘湖。萧山百姓,对杨时感念不尽,后人为他在湘湖边建德惠祠,祭祀这位大儒。
说杨时是一代大儒,没有一点溢美之词。他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有着显要地位。儒学是极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学说,一代又一代改变历史潮流的巨人,无不秉承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那种深厚的“家国情怀”无不被一代又一代历史巨人奉为圭臬。而儒学从孔孟之后,就没有多少新气象,直到时光的钟摆进入宋朝,新气象才若一股山间清岚萦绕开来。程颢程颐当然是这种新气象的开拓者,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被世人称为“二程”,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宋史·程颢传》叙评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杨时是“二程”理学的嫡传弟子,而且是程门四弟子(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中最重要的两个弟子之一。“二程”理学由杨时传至罗从彦,罗从彦又传至李侗,李侗再传至朱熹,而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从这条传承路径可见杨时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性。
程氏理学有趣的是,程颢主张“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人本无二”,人心与外物不可分,“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认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程颢的理学倾向,恰好为后来的陆九渊和王阳明的“陆王”心学打了地基。而程颐之“理”,是指客观事物的样子,“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所以,程颐认为为学的方法应以“穷理”为主。不过,“二程”都把“天理”看成是宇宙本体,把他们的全部道学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理”是自然界的本原和主宰,也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总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儒士的理想阶梯,他总是从人性的最初级起步,逐级登上理想的山巅。“修身”是一个儒士最重要的一级。“二程”在修养论上,将定性、主敬和格物致知作为修身的路径。当杨时拜师程颢,师生相谈甚欢后,程颢看着杨时远去的背影,颇为欣慰地说了句:“吾道可南矣。”
可见在程氏理学由北向南传道中杨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杨时没有辜负老师,他将“二程”的洛学南传,三传至朱熹。他继承了洛学“理一分殊”的观点,经过他的补充与阐发,“理一分殊”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杨时在《龟山文集·答胡康侯》中说:“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杨时主张人生以学圣人为准则,而入圣的功夫在于养气、节欲、致知、力行。他深得“二程”道学之精髓。
目前,海西州草原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由于鼠害繁殖能力较强,没有强大天敌,导致草原鼠害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使草原环境无法得到平衡和健康发展。因此,需要认真分析草原鼠害防治存在的多方面问题,采取科学方法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加强技术支持,达到科学防治鼠害、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目的。
养气、致知、力行,这是杨时的生命信仰。他一生安于州县,不求仕宦显达。为学,格物致知,穷尽事物之理;为官,灭私欲明天理,为一方百姓谋求福祉,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不忘”。
湘湖在杨时任上建好后,这个大儒身份的县丞,舟行湘湖,即写一首五言律诗《新湖夜行》:
平湖净无澜,天容水中焕。
浮舟跨云行,冉冉蠟星汉。
烟昏山光淡,桅动林鸦散。
夜深宿荒陂,独与雁为伴。
一位已年逾六旬的老人,在这座为民谋福的湘湖建好后,也许是兴奋与心安,与同僚们行舟湖上,看夕阳下的湖光山色,听桅杆振动后鸟儿展翅飞翔的脆鸣,湖水平静无澜,仿若一镜,纳天容于镜中,纳万物于镜中。
杨时将湘湖续写在历史时空的册页上,这座湖有了更多的美感。在这座湘湖,每个人都照见了自己,无论是感伤还是喜悦,都是这座湖的赐予,感伤使心灵疼痛起来,并澄澈心灵。
夕阳,仿佛一卷黄帛轻披在杨时的身上,他面容清癯、目光澄明地望着远方……当我虔诚地俯下凡俗的肉身,他一点一点越发地高大起来,我的影子却愈来愈短,最终融入那一片温暖平和的夕阳里……
余晖漫漫。天、地、湖,都已缓缓地融为一体。
我打开手机里收藏的音乐《神圣的土地》,将音量调至恰到好处,不扰人,只与我的内心共鸣。声音空灵、辽远、纯粹、温暖,是一种恬静的美。
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安安静静地纳于镜中。
一镜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