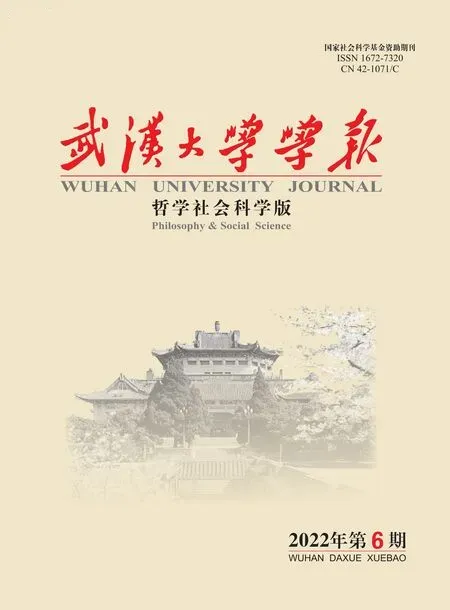在天堂的后面
——伊朗儿童电影新探
黄 津 黄献文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一直默默无闻的伊朗电影突然风生水起、大潮涌动,成为世界电影一道亮丽的风景。引领此次风潮的首先是伊朗的儿童电影。儿童电影是当代伊朗电影的标志和黄金品牌,也是伊朗电影走向世界的敲门砖。但伊朗儿童电影不像中国的儿童电影那样负载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话语和道德教化功能,而是还原到儿童世界,钻进儿童心灵,以儿童之眼来窥探成人世界。它们大都采用极简的情节,平凡琐碎,甚至是无事找事,然后用几乎是纪录片的方法拍摄,却能够从最平凡的事件中挖掘出人类最深切的情感。
一、成人视角
在一般人眼里,伊朗的儿童电影几乎清一色地表现儿童天真纯洁的世界,表现他们的童趣、童真、童心,晶莹剔透,不沾染一星半点世俗的杂质,涂抹上一层天堂般的颜色。他们是伊甸园里的孩子,是成人世界遗忘已久的良心。
然而,几乎所有论述伊朗儿童电影的文章都到此止步,没有探究为什么伊朗导演拍摄这类天真纯洁的儿童电影后面的深层心理驱动。即便有,也将其归为外部原因:一是伊朗电影面临着严苛的审查制度。作为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从编剧、演员、剧组直到样片的每一环节,都需经过严审,稍有不慎就会被删剪或被禁映,谁敢触犯禁忌,轻则禁止拍电影,重则面临牢狱之灾。只有儿童电影“容易得到伊朗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儿童来表现现实,通过儿童来代替电影的叙事话语权逐渐成为伊朗新电影人突破体制的重要途径”[1](P11)。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儿童电影的崛起与繁荣。二是伊朗儿童电影像一匹黑马,在国际影坛上频频获奖,客观上刺激着伊朗儿童电影的拍摄。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获得1987年德黑兰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198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等,把阿巴斯推向了国际大牌导演行列。随后,马基德·马基迪、贾法·帕纳西、易卜拉欣·法扎什等导演鱼贯而出,拍摄了一大批儿童电影,如《小鞋子》《天堂的颜色》《白气球》《水缸》等,这些影片为他们带来了国际声誉。从那以后,伊朗儿童电影便成为伊朗电影的品牌和名片。三是导演工作性质原因。阿巴斯就因为被邀请建立“伊朗儿童青少年智力发展学会”下属的电影制作机构,才开始拍摄小学生教育问题的《家庭作业》《小学新生》等儿童电影。
无疑,上述理由都是成立的,也是事实。然而,纵观世界电影史上的儿童电影,不外两大类:拍给儿童看的儿童电影和拍给成人看的儿童电影。前者如中国的《小兵张嘎》《喜洋洋》《熊出没》等和近些年美国出品的《哈利·波特》电影系列,这些电影一般具有游戏、幻想、科幻等特征。但我们发现,上面说到的伊朗儿童电影虽然表现的是儿童世界,却不是拍给儿童看的。这有导演们的自白作证。阿巴斯说:“人们说我拍儿童电影。其实……我的许多电影以儿童作为主人公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拍给儿童观众看的。”[2](P119)贾法·帕纳西也说:“我们拍摄以儿童为主角的影片,但并不是儿童片。儿童题材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是规避审查制度的途径,因为关于儿童的影片不用接受审查。”[3](P169)换句话说,儿童只是载体,或者说是掩体,导演们借鸡生蛋,别有怀抱。
首先,儿童的心理,因性别而异。在男孩那里,力量永远是他们憧憬的。力量包括体力和权力。童年时代是体力,成人世界是权力,成人对权力的崇拜其实不过是孩童时代对体力崇拜的延伸与位移。儿童身体弱小,渴望快快长大,拥有力量,征战四方,在虚拟的想象世界里,他们把自己当成英雄,或者附身于英雄,睥睨世界,一呼百应,万众仰慕。从这个角度看,正印证了马克思说的塑造了众多英雄谱系的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产生于“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弗洛伊德说:“孩子的游戏是由愿望决定的:事实上是唯一的一个愿望——它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起很大作用——希望长大成人。他总是装扮成‘成年人’,在游戏时,他模仿他所知道的比他年长的人的生活。”[4](P31)镜像理论也告诉我们,形成“镜像阶段”的前提是因为匮乏的出现。因为弱小,他们才渴望伟大。男孩子在游戏中谁没有扮演过他们看过的电影或小说中的英雄,在白日梦虚拟的想象中,将自己弱小的身躯无穷大化,统领千军万马。正因此,武侠小说、战争片、动作片、变形金刚、大力水手等从来都是男孩子们的最爱。与男孩子英雄梦的宏图伟业不同,大多数女孩显意识和潜意识都有一个公主梦,每个女孩都渴望成为一个美丽的公主,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王子公主的浪漫传奇是她们的最爱,最能击中她们心中柔软的部位,在观看这些传奇的时候她们完成了自我幻想的投射。至于童趣、童真、童心,他(她)们有的是。以此反观伊朗儿童电影,却找不到对于英雄的崇拜和王子公主浪漫传奇的任何影子。
其次,在儿童的世界里,只有一根评判尺度,一根他们得以稳住世界的杠杆——二维向度的善恶、好坏,没有中间状态,没有复杂的人性内容。他们尚未充分发达的心灵不具备成人世界多维的价值向度,只有借助好与坏这根泾渭分明、极易操作的道德标尺去把握对他们来说像迷宫一样纷繁复杂的世界。然而,伊朗儿童电影很少呈现、倚仗这根尺度,这也反证它们不是拍给儿童看的。换句话说,它们只是取的儿童题材而拍给成人看的电影。
只有成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一个个压力山大,焦虑抑郁,城府深深。他们的心由最初的鲜活、轻盈、纯洁逐渐变得麻木、迟钝、沉重。他们逐渐在社会的阶梯上找到了位置,金钱,权力,地位,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童心。然而,通过孩子们的一颦一笑,他们的萌、嗔,他们晶莹的泪和破涕为笑,他们未被世俗污染的心,成人们又仿佛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在想象中重走一趟童年之旅。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5](P29)镜像与幻想本质上是主体欲望的表达,正是在儿童的镜像中,作为“镜恋动物”的人类才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认出迷失已久的自己。而且,岁月流逝,人到中年或渐入老年,生命力逐渐衰颓,而童年一如天边的曙色,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童年就是生命力的象征。为什么老人和小孩总是天然的亲近?仔细考察,这正是潜意识中的心灵互补所致。艺术从来都是白日梦,没有满足的欲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成人世界越复杂、荒芜、沉重,艺术中的童年世界便越纯洁、轻盈、美好。世界电影史上,不少导演都喜欢拍儿童电影,但其中有很多不是拍给孩子们看的,而是拍给成人看的。虽然没有做过心理实验,但如果一定要做的话,估计十有八九的孩子看这些电影会感到索然寡味,掉头他顾。不是他们不熟悉,而是他们看不懂,因为它们不是取的儿童视角而是成人视角,是成人心灵的投影,怀旧是其主题底色。如日本名导小津安二郎和清水宏拍摄的儿童电影系列,中国第四代导演吴贻弓执导的《城南旧事》等,大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小孩子看后一定是满头雾水。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人潜意识里都有一种想回到黑暗、温暖、安全的子宫的冲动,这是一种本能。艺术创作的本质就是回忆,只有童年永逝,人们才会在心里反复地呼唤和咏叹。这种回溯的心理其实就是一种变相地回到子宫的冲动,这种心理指向使得古今中外很多艺术家往往喜欢在白日梦里重新打捞童年时烙印在记忆中的感觉的浮影。伊朗的儿童电影也是如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解开其内在心理驱动之谜。
二、早年记忆
尽管多以儿童题材表现成人世界,伊朗儿童电影却不是铁板一块。导演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不同,表现出来的风格特色和蕴藏的心理内涵各异。这里我们暂且搁置执导《乌龟也会飞》《醉马时刻》的巴赫曼·戈巴迪,执导《流浪狗》的兹耶·梅什基尼,执导《背马鞍的男孩》的萨米娜·马克马巴夫,执导《佛在耻辱中倒塌》的汉娜·马克马巴夫等儿童导演,后有详论。
作为伊朗新电影的旗手,阿巴斯是一个极富诗人气质的导演,这不仅表现在他的电影深受伊朗古典和现代诗歌的影响,而且在创作上尤重感觉、直觉和印象,尤其是童年时代的感觉和印象。他曾说:“艺术创作的间接目标是深深退回到儿童时代的游戏中。”[2](P121)“对于艺术家而言,重新连接年轻时代的冲动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必须。”[2](P121-122)我们仔细考察阿巴斯的电影,褪掉表面那被别人重复过无数次的表现儿童的纯洁和童真之外,总感觉有一层梦幻般的气质和感觉的浮影。换句话说,阿巴斯的儿童电影其实就是在打捞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记忆和感觉,这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影像”、感觉和记忆激发起他的创作冲动,成了他创作的原初酵母。这绝非武断臆测,而是有导演的话为证:“我经常是从一幅内心影像开始写作剧本的,也就是说,我是从存在于脑子里的一幅影像开始建构和完善剧本的”[6](P46)。阿巴斯童年时“性情孤僻,沉默寡言,从开始上学直到六年级,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6](P30)。一直到成年,这种孤独症还伴随着他,挥之不去。他说,为了医治孤独症,“曾到布拉格去看捷克电影”[6](P35)。从各方面考察,阿巴斯小时有着较明显的自闭症倾向。儿童自闭症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一种亚型,多发于男孩,起病于婴幼儿期,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言语发育障碍、人际交往障碍、兴趣狭窄和行为方式刻板。自闭症的孩子往往生活在他的世界里,与外面世界格格不入。这种倾向也反映到他电影中的小主人公身上,大胆一点说,他们就是童年阿巴斯的真实感受。在他的镜头里,儿童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世界隔着一堵厚厚的墙。且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一个细节:小穆罕默德在村头好不容易找到同桌的父亲,但他的声音那么微弱,完全淹没在大人谈生意的嘈杂声中,小穆罕默德的心事不断被搁置。好不容易等到同桌的父亲谈完生意,这一下该静下心来听听孩子的声音吧,但他谈完生意,马上骑着驴走了,小穆罕默德只得跟在驴后面拼命追赶。《让风带着我飘》(阿巴斯编剧、Mohammadali Talebi导演)中装玻璃的男生在最需要人手时,校役两次从镜头进出,却听不到他的声音,导致最后玻璃被风吹在地上摔得粉碎。从窗口吹过来的呼啸的风隐喻外面世界的恶劣。同类的作品还有1974年阿巴斯执导的《过客》。
童年的阿巴斯患有自闭症,讷于言却敏于思,内心世界极为活跃,感觉特别敏锐。又因他早年学画,养成了绘画思维,便在封闭的心灵世界里,“在内心里作画”“画一幅内心的影像”[6](P34)。“我画画的目的主要用‘绘画疗法’治病,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绘画。”[6](P34)所有这些使得他的电影有着强烈的画面感。他的创作灵感和创作冲动往往直接源自某个画面。如构思《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时候,“重要的场面是最先出现的:一个孩子朝着小路尽头的一棵树跑去,最后消失在山里。拍这部影片之前,这个影像在我脑子里已经存在了好几年……我的无意识被深山和孤树吸引,我们在影片中忠实重构的正是这样一幅影像,山、路、树是构成这部影片的主要因素”[6](P46-47)。在拍《橄榄树下的情人》时,他说“我从未想到《橄榄树下的情人》会在一片劲风掠过的麦田里拍摄,因为这个影像正是我10年前作的一幅画中表现的东西,最初的构思又可以追溯到20年前”[6](P34)。拍摄《面包与小巷》时,他说“我重新发现了很久以前的画面:街道、狗、孩子、老人,所有这些都曾是我的第一部电影《面包与小巷》里的元素。多年后它们潮涌而归”[2](P154)。阿巴斯的诗集《随风而行》中的一首短诗,与电影《面包与小巷》正相呼应:“狗儿在巷尾∕埋伏∕候着下一个要饭的。”可以说,熟稔亲切的童年记忆和画面感像珍藏地底的醇酒,一直潜藏在阿巴斯记忆深处,在某个灵感触发下,将此前的记忆、印象和感觉瞬间照亮。正因此,阿巴斯的电影往往“以一种悄然而至但又如顿悟般的影像捕捉,大大地拓宽了摄影机镜头的视野,赋予朴素空灵的影像以神旨般的诗意”[7]。掩目静思,阿巴斯电影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正是这些原初的画面。这印证了弗洛伊德的话:“现时的强烈经验唤起了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验)的记忆,现在,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又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一篇创造性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和代替物。”[4](P36)除此之外,死亡是阿巴斯电影的底色,在早期的作品里隐藏较深,越往后(中年以后)的作品,死亡的远影从画面的边角向中心围拢过来。即使是表现儿童世界,死亡也会突然光顾。如《让风带着我飞》中,背着玻璃的男孩来到一块寒风呼啸的墓地,一个刻有孩子头像的墓碑特写突然推到观众面前,让人联想到阿巴斯诗集《随风而行》中的诗句:“墓地/覆满了/积雪/只在三块碑石上/雪正融化/三个年轻的亡灵”。也再次证明了阿巴斯电影的灵感源于他的诗与画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仔细考察阿巴斯的潜意识心理,尽管在他的《生生不息》《随风而逝》《樱桃的滋味》中,导演一个劲地挥赶死亡的阴影,用充满生机的大自然,用年轻鲜活的生命来踩低死亡的天平,用生命的正面来否定、挤压死亡的倒影,又用死亡反衬生命的美好。但之所以要挥赶,正是因为死亡阴影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阿巴斯执意拍摄儿童电影的潜意识驱动:借对童年的回忆,重走一趟童年之旅,抵御越来越浓重的暮年和死亡阴影的来袭。
另一位著名的儿童导演贾法·帕拉西从1988年开始拍摄第一部短片起,迄今共创作了20多部影片,其中的儿童电影《谁能带我回家》和《白气球》依然表现儿童的天真、纯洁和萌趣。但帕拉西不像阿巴斯那样是一个冥想的诗人,而是一个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情怀的导演,他将电影取景点从阿巴斯镜头中的乡村转移到了都市,儿童世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是熙熙攘攘的德黑兰街头。在主题设置上,它已经跳出了阿巴斯电影那种打捞童年记忆和感觉的模式,扫描进了更多社会的面影和人情世态。他说:“希望影片与现实亲密接触,而不是以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讲述孩子们的故事,不是从呵护、抒情的视角来看孩子们和他们的世界。”[3]他镜头中的小主人公与其说是一个孩子,不如说是一面镜子,倒映出成人世界的心灵真实和社会的阴影。
马基德·马基迪曾说自己的童年是他创作“思路的泉源”,他喜欢将儿童作为家庭的一员,用诗意的镜语表现那些苦难而又充满幻想的底层孩子们心地的纯洁、善良以及面对贫穷苦难的坚韧品格,如享誉世界的名片《小鞋子》;或将孩子们心地的纯洁与成人世界的自私进行反衬,如《天堂的颜色》;或探讨亲情的温暖与沉重,如《后父》等。即便其中有阴暗,最后总有一束光从银幕顶端照射下来,那是人性的苏醒与回归。《天堂的颜色》片尾,一束仿佛来自天国的金黄的光束聚焦在死去的孩子手上,那是父亲心中升腾的对儿子的爱,也是导演对去向天堂的孩子的祝福。这种人性的回归也延伸到他的其他影片里,如《巴伦》等。《天堂的颜色》不是一部纯粹的儿童片,而是一部探讨人性的电影,远比他的其他儿童电影要沉重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打捞童年记忆与感觉的心灵指向并不能覆盖所有伊朗儿童电影,只是在阿巴斯那儿表现得特别鲜明。但表现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错位与隔膜,以儿童的天真纯洁反照成人世界的冷漠自私和人性的阴影则是共同的。
三、童年的苦难
伊朗儿童电影中儿童的心灵有多纯洁,苦难便有多深;有怎样的天堂颜色,便有怎样的地狱图景。如果我们将伊朗的儿童电影譬作一块硬币,表现“天堂颜色”的儿童电影是硬币的正面——在其中,人生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被孩子们心灵的柔光过滤了。下面这批儿童电影则是硬币的反面,它们表现的是战争转嫁给儿童的苦难以及给儿童心灵造成的创伤与人性扭曲。这类作品有:《醉马时刻》《佛在耻辱中倒塌》《乌龟也会飞》《黑板》《流浪狗》《我在漫步人生》《尘土之舞》《走向春天》《美丽城》《背马鞍的男孩》等,它们揭示出孩子、战争、人性、权力交织的复杂关系,以下分三点讨论。
1.战争与孩子。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给伊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山河破碎,民生涂炭,满目疮痍。伊朗电影最司空见惯的是破败的村落,衣衫褴褛的村民,流离失所的孩子,被地雷炸断四肢的村民和少年。同时,伊朗新电影也突破国界,将镜头伸向饱受战争创伤的邻国阿富汗,印象最深的是《坎大哈》片尾阿富汗难民像袋鼠一样拄着拐杖奔抢联合国飞机空降假肢的场面。战争的巨大灾难也转嫁到无辜的孩子们身上,给他们身心留下永难弥合的伤疤。对战争控诉最具力度的要数库尔德族导演巴赫曼·戈巴迪2004年执导的《乌龟也会飞》。少女亚格林和她的断臂哥哥父母双亡,相依为命,流离失所,被战争驱赶着辗转迁徙。亚格林在战难中遭伊拉克士兵轮奸而生下一个盲孩,那是她耻辱的见证和甩不掉的梦魇,为了抹去这段痛苦记忆,夜里她解开患梦游症的盲孩,希望他在梦游中摔死;后又将他抛弃在无人的乱石山岗,一直到最后给儿子绑上石头让他溺死在池塘里,她自己也跳下悬崖,结束短暂、屈辱而苦难的一生。花季少女承受着战争不能承受之重,生不如死,早早地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本是情窦初开的芳龄面对异性的爱情,心如死灰。她生下的“孽种”——不知父亲是谁的盲孩,大大的眼睛,天然卷发,天真萌趣,让人爱怜,却双眼残疾,当他翻着一双大而无法对焦的眼睛,一个人孤零零的被母亲抛弃,摸索着,哭泣着,让人心痛如揪。满屏废弃的坦克,堆积如山的弹壳,让无数人失去生命或四肢的雷区,战机的轰鸣声不时从头顶掠过,所有这一切都在昭示战争阴云不散。巴赫曼·戈巴迪把在战争蹂躏下库尔德儿童的苦难拍得这么残酷,这么血泪斑斑,让人心颤又欲哭无泪!这个在历史上被异族征伐无数,苦难深重,而今散落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四国边界,没有自己祖国的苦难民族,在新的世代又把苦难和宿命转嫁给了无辜的下一代。无父无母,无家可归,饱受战火蹂躏的儿童是库尔德民族苦难的缩影。巴赫曼·戈巴迪的电影惯用隐喻和象征。《乌龟也会飞》以乌龟为片名,令人费解,乌龟与整部影片的情节推进无必然联系。最后盲孩溺死池塘,慢镜头中一只乌龟从他身旁轻盈游过,与片中悲怆基调相反。其实,我们只要将它当成一部儿童电影就能理解。乌龟是盲孩喜欢的小动物,盲孩溺死时,只有乌龟来陪伴他,乌龟象征着他的解脱,也是对他最后的安慰,或者说乌龟就是这个盲孩。苦命的孩子虽然死了,却能像乌龟一样在水中飞起来,飞离这个苦难的世界。导演的悲悯情怀给了孩子最后一丝安慰,然而这又是怎样的悲哀与沉痛啊!
巴赫曼·巴拉迪的另一部作品《醉马时刻》(2000年)与《乌龟也会飞》异曲同工。影片通过一个少年及其家庭的不幸呈现出整个库尔德民族在战争蹂躏下的生存悲歌。导演曾说:“我在伊朗的库尔德族地区的一个小镇出生长大。我在那里的童年和青少年回忆,对我的电影影响最大。……片中呈现的库尔德族人生活,并非我的想象,而是现实世界中的库尔德族人如何勇敢地在困苦中求生存的纪录。”作为库尔德族的导演,巴赫曼·戈巴迪能“真正深入库尔德族人的信仰、生活和灵魂,描写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无奈与苦难”[8]。这种苦难是嵌进在血肉和灵魂里的苦难。巴赫曼·巴拉迪耳闻目睹了战争给库尔德民族带来的灾难,又从血缘上继承了库尔德这个民族亘古相传的苦难基因,所以在他的镜头里,在石缝中顽强求生的库尔德儿童的苦难才描写得入木三分,力透银幕,让人震撼。他的《栗色伊拉克》《半月交响曲》等电影同样表现库尔德民族的苦难,与此一脉相承。同样的题材和主题也出现在莎米娜·马克马巴夫反映库尔德难民生活的《黑板》中,本应该在教室中学习的孩子为了生计不得不在边境线上铤而走险,生存之路最后通向死亡!
2.扭曲的人性。美国学者哈米德·瑞阿·萨德尔曾从国家形象和导演自身两个角度分析了儿童形象在伊朗电影中的作用:从国家形象层面看,伊朗在外界被妖魔化,儿童则扮演着完全不同的富于诗意的形象,这种形象正好可以改变伊朗在国际社会一直以来的负面印象[9](P228)。然而,像一般域外观众一样,萨德尔只讲到了伊朗儿童电影温暖诗意的一面,忽视了伊朗儿童电影同时也表现了儿童身上的人性残忍和扭曲的一面,尤其是与战争造成的极端主义思想和宗教偏见相结合,覆盖、抽空了孩子们纯真的天性,让他们心灵扭曲。以记录苦难闻名的导演汉娜·马克马巴夫执导的《佛在耻辱中倒塌》(2007),片首便是阿富汗塔利班炮轰世界闻名的巴米扬大佛的场景,奠定了整部影片“文明与野蛮”的主题基调。一个住在巴米扬石佛的穴居石窟中的六岁小女孩芭缇执意要上学读书,途中遭遇一群男孩,他们手持棍棒树枝,扮成塔利班,一个个面目狰狞,人性全无。他们说女孩子不能上学,芭缇露脸涂口红,大逆不道,必须被消灭。她用家里四个鸡蛋换来的、寄托着她小小的上学梦的笔记本被男孩们恣意践踏,折成各式纸飞机。他们拿起被炸毁的佛像残留的碎石,威胁要砸她,惩罚她,然后将她活埋。他们恶作剧地将芭缇隔壁家的男孩引诱进设计好的陷阱里。在他们脸上,塔利班邪恶残暴的人性之恶显露无遗。芭缇好不容易来到她梦寐已久的学校,但所有小女孩们脸上挂着的都是冷漠与不屑,没有人愿意为芭缇腾出座位,甚至故意阻拦不让通过。影片表现的是塔利班的反文明暴行和极端主义思想对儿童的洗脑和心灵的戕贼,让反智的人性恶之花在下一代身上野蛮滋长。摧毁一个民族,可以再繁衍生息,摧毁一个国家,可以重建,而摧毁下一代人的心智,则万劫不复。“芭缇,死掉就自由了!”邻居男孩劝芭缇投降的绝望的呼喊表面上是孩子的语言,实则是对在塔利班统治下所有阿富汗人悲惨命运的隐喻。
3.权力之下的兽化人性。莎米娜·马克马巴夫导演的《背马鞍的男孩》(2008)是一部意义繁复、众说纷纭、在伊朗新电影中独树一帜的电影。双腿被地雷炸掉的小少爷需要雇人背他去上学,名叫吉亚的弱智少年被选中。吉亚每天背着小少爷上下学,宛如他的私人坐骑,还为他洗澡洗衣,做各种苦差事,小雇主对他颐指气使,拳打石砸,但仍不满足,他希望自己骑的是匹真正的马。吉亚又被套上马鞍,钉上马掌,勒着马头,完全当成了一匹马供他使唤,吉亚也把自己当成了马,这是主线。副线是自私、专横、残忍的小少爷,母亲被地雷炸死,他的双腿被炸掉,在埋葬自己双腿的墓地上,他为自己的身世痛哭,为母亲号啕,为失去的双腿而怨天恨地。有人说该片的主题是表现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压迫,有人说是表现战争和贫穷催生下的人性异化,有的说是对精神与肉体的隐喻。“残疾男孩与智残男孩的互相纠结,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欲望和肉身的搏斗”[10](P228);有的则读出了人性本恶;有的说是权力对人的异化。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初衷是表现“强权对人性的摧残,强权如何将人演变成动物。”[11]我们认为影片是借一个四肢发达却心灵弱智,一个身体残疾而心智正常的两个少年凸现出人性的畸形和黑暗,再也没有前面伊朗儿童电影的诗意和亮色。小少爷没有双腿,他恨这个让他失去妈妈、失去双腿的世界,在潜意识里他把这种嫉妒和仇恨转嫁到弱智的吉亚身上,对他颐指气使。为了满足扭曲的好胜心其实也是自卑心,让吉亚与人打架赌输赢,与真正的马一样赛跑,不管他的死活。为了将他变成一匹真正的马,残忍地给他钉上铁掌,勒上马头,绑上马鞍,变成了马厩里一匹真正的马。为了赚钱,小主人把吉亚租给其他同伴骑乘以寻欢作乐。导演说:“社会学研究已经证实如果孩子没有父母或监护人的监督和陪伴,他们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可能会持刀在同伴的眼睛前挥舞或掐着他们的喉咙久久不放,完全没想到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11]而吉亚最后不仅被别人当作马来使唤,自己也真的变成了马,在马厩里像马一样吃着草料,像马一样嘶叫。从影片中,我们既可读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诸如戈尔丁的《蝇王》、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影响,可看到伊朗新电影之父达鲁什·默赫朱依的电影《奶牛》的影子。吉亚和其小雇主的故事不过是人类社会权力与人性异化的写照,是亘古以来人类社会和人性的隐喻。
以阿巴斯为首的伊朗新电影导演在其镜头里写出了儿童的纯洁天真,温暖感人,唤起了我们对逝去童年岁月的无限缅怀,让我们蒙垢的心又鲜活如初。然而,伊朗的儿童电影因为受到题材的局限,也为了获奖,东施效颦,同质繁殖,题材和风格趋同,使得伊朗儿童电影大同小异,越来越陷入模式化的套路和瓶颈中,引起了伊朗本土评论界的不满:“伊朗儿童电影却不免陷入模式化的困境,重复的‘寻找’题材,从《白气球》延伸至《谁能带我回家》,孩子的无辜眼神与大人的世界隔膜,感动的滋味反复品验中日趋平淡”[8]。可贵的是,导演们即时调整了制片策略,以其独有的敏锐眼光和艺术直觉写出了儿童惨痛的成长空间,不应承载和不堪重负的苦难,在极端思想洗脑之下的人性恶,使得伊朗儿童电影开掘出另外一个空间,具有丰厚的立体感,既轻盈诗性,又深刻沉重,扫描进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具有丰厚的现实主义蕴含和人性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