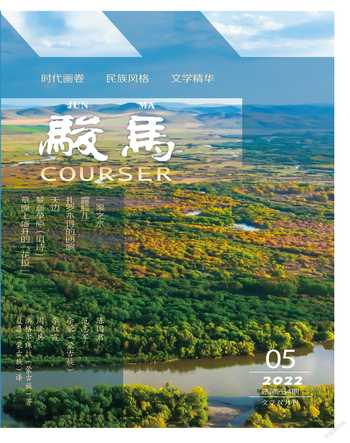扎罗木得的回响
李蒙(蒙古族)
初冬的草原,有着朴素之美。久居城市的人们,开着越野车,犹如刚出笼的百灵鸟一样,风尘仆仆地赶到一个叫扎罗木得的村子里,来品尝村子的主打名菜——酱马排。他们大多来自高楼成林、尾气如雾的市区,面对独特的美食,不禁觥筹交错,大快朵颐。但他们大多不曾知晓,这里曾是培育三河马的摇篮,这片草原,寄予了一代又一代马场人的希望。
扎罗木得是鄂温克语,译为“有小鱼的地方”。历史的车轮回转至两百多年前,清世宗雍正抽调布特哈地区的巴尔虎、鄂伦春、索伦、达斡尔等三千多兵民,翻越大兴安岭山脉,来到呼伦贝尔草原伊敏河畔驻防建城。扎罗木得水草丰美,地势开阔,迁徙而来的人们过着战时屯兵,闲时游牧的生活。
“要问父亲的故乡呐呦耶,是祖先放牧的布特哈河畔。要问我出生的地方呐呦耶,是大雁落脚的草原。”这首叫《故乡》的达斡尔族民歌,莫日登巴图爷爷唱了七十年,现在全村会用达斡尔语演唱的人只有老人自己了。据巴图爷爷讲,在离扎罗木得不远处的莫和尔图村,有一位郭布勒姓氏的老人也会唱这首民歌。巴图爷爷是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举家迁到扎罗木得,以养马为生。而莫和尔图地区的达斡尔人是三百多年以前从岭南戍边来此的,所以他们是同根同族。为此巴图爷爷还特地搭乘村里收奶子的车去莫和尔图找这位老人,老哥俩支起炕桌,倒上原浆白酒,放开喉咙,从日出唱到日落。那婉转的歌声就像门前的莫和尔图河那样向东流淌着,流经索伦湾,奔向扎敦河,汇入雅鲁河,最后融入黑龙江。
在巴图爷爷的心里,马是最亲近的伙伴,用他的话说,马有的时候比人还要重感情。现在想一想,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了,莫日登氏在布特哈地区曾是大家族,牛马成群,还有几百亩能攥出油的黑土地。在童年的记忆中,长辈们出行不是坐人抬的轿子就是骑马,粮食能从入冬一直吃到来年入夏。但这样的好日子巴图爷爷没过上几年,10岁那年乡里面把莫日登家族纳入了重点改革对象,几乎是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了。眼看着成群的牲畜被赶走,田地也被瓜分,当家的祖父气得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撒手人寰。父亲有两匹好马,是伪满时期父亲跟叔爷爷去海拉尔做皮毛生意时,看好的两匹三河马,一匹四岁的儿马子和一匹三岁的骒马,父亲用五块银圆买下了它们,这两匹马每年都会给家里的马群添一匹马驹。工作组来时,父亲乞求工作组将这两匹三河马留下,但是没有得到同意,父亲眼含着泪水看着他心爱的马群被分成了几小帮,不知被赶到了哪里。
没有了土地和牲畜,家中的生活一落千丈,远迁他乡或许还能东山再起。大伯家迁往嫩江地区,父亲想到了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他要沿着祖先勒勒车留下的印记,寻找新的牧场。就在全家人準备启程的头天夜里,姐姐听到门外有马的嘶鸣声。父亲打开大门,看到了他日夜思念的两匹骏马,骒马的嘴边还有不少血沫,身上全是汗,显然它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跑回来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
父亲怕工作组的人发现回家的马,赶紧将马藏在了后院,让马休息,又带着一家人给马割草、喂水。第二天天还没大亮,就赶着马、带着家人,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故乡。
由于带着两匹马前行,火车是坐不了的,只能坐着大轱辘车慢慢地走。两匹马似乎知道主人的良苦用心,不知疲倦地拉着车,爸爸和嬷嬷心疼马,只让两个孩子坐在车上,他们则是一步一步地跟在车后面。在过兴安岭的时候,嬷嬷和姐姐在山路旁挖野菜,突然听见一声稚嫩的嘶鸣声。顺着声音寻找,发现有一匹不足百天的小马驹被遗失在这里。爸爸将这匹小马驹带到车旁,这是一匹草黄色的蒙古马,脑门上带有一块闪电样的白色印记,爸爸给它起名叫“嚓黑勒刚”。虚弱的马驹发现了骒马的乳头,嗅到了母亲的气息,试探着一点一点地靠近,想要吸吮骒马的乳汁。此时骒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小家伙有些暴躁,踢咬着让它离开,眼看马驹的生命危在旦夕。就在此时,嬷嬷唱起了歌,低低的声音,如泣如诉……渐渐的,骒马停止躁动,轻嗅着马驹,马驹渐渐胆大了起来,吸吮着骒马的乳汁。母爱伴随着初夏的暖阳,笼罩在大地。
有了马,生活就有了希望。历经一个多月的风餐露宿,巴图爷爷一家来到了索伦湾山下的扎罗木得。那时的扎罗木得刚刚开始建设,新中国要在这里成立种马场,培育三河马,用于保卫边疆和生产建设。
巴图爷爷发现,来到扎罗木得种马场的人不光是当地的蒙古族人、达斡尔族人和鄂温克族人,也有从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来的汉族人,还有帮助种马场开发建设的苏联人,他们多来自苏联的赤塔、伊尔库茨克和乌兰乌德这些城市,他们也将当地的贝加尔马、顿河马种带到了扎罗木得。马场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二百多人增加至三千人,马匹也由建厂时期的三百多匹马增加至一千六百多匹马,一时间,种马场出现人畜两旺的场景。
当时的种马场几乎不具备医疗条件,就连马生病了都无法医治,只能靠苏联专家带来的药水进行临时救治,一些马因疾病失去了生命。为了方便马场的人和牲畜看病,巴图爷爷先是跟扎木苏老人学习蒙医,在老人家里当学徒,还尝试着自学兽医,给马接骨、配药。经过一番努力,种马场为巴图爷爷争取到了到海拉尔蒙古族卫生学校进修的机会,他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和蒙医。巴图爷爷学成后回到种马场,成立了种马场的第一个卫生所。
种马场需要人才,边疆更需要建设。巴图爷爷依稀记得,老人们曾经说过,森林之外是草原,草原之外是中原,在中原之外有一片雪域净土,人们叫它西藏。自西藏解放以后,在广播中经常能听到祖国各地支援建设西藏的消息。一天,军区的领导来到种马场,宣布要在扎罗木得地区选调两百匹蒙古马支援西藏建设,种马场的马匹自然是首选,就连巴图爷爷家的“嚓黑勒刚”也在征用的范围内。对于种马场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件好事,马没有白养,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激动与幸福就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哈达,把呼伦贝尔草原和西藏连到了一起。可是巴图爷爷却高兴不起来,他并不是不想他家的马被征用,而是他考虑到两百匹马到遥远的雪域高原上,没有一名兽医跟随它们出征怎么能行呢?巴图爷爷深夜从炕上爬起来,骑上马直奔军区领导的蒙古包。他向领导说明来意,说自己从小就与马打交道,到马场后又自学了兽医,能够治疗马匹寒热症、消化疾病,还能为马接骨。而且他告诉领导,自己不怕累更不怕苦,保证每一匹马都能活着到西藏。军区领导很佩服巴图爷爷的勇气和责任心,临时开会决定,让巴图爷爷作为马匹的医生一起进藏。
接下来的日子里,巴图爷爷带领大家进山挖药材,晾干后封存到布袋里,以备路上不时之需。他还找到苏联专家,要了一些玻璃瓶药水,以防突发情况。到了出发的那一天,种马场人头攒动,两百匹三河马头挂彩条,分别被赶上二十辆“解放”牌汽车。男人们犹如当年将士出征一样,送马向高原进军。
巴图爷爷和战士们尝尽了路途的颠簸,由公路转乘铁路再走山路,历经一个月的时间,才到达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据巴图爷爷回忆,刚一进西藏,高原反应就非常强烈,人们开始出现头晕、呕吐、呼吸困难的症状。而生长在呼伦贝尔地区的三河马,来到西藏也开始出现食欲不振、轻度脱水、腹泻等症状,巴图爷爷每天都要带领战士们照顾生病的马,直到马痊愈,巴图爷爷人瘦了一圈。
到了昌都县,巴图爷爷见此地人烟稀少,一派荒凉景象,远远望去,人们都穿着皮袄,留着长发,根本看不出来是男是女。不光是语言不通,就连饮水有时都难以保证,巴图爷爷心里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但是一想到从家乡带来的那些马,他还是决定留下来。
在平时的工作中,四匹马为一组,拉一套木头制成的大车,主要是运送石头和木材,用于建房。昌都地区多为山路,地势起伏很大,马拉得非常吃力,经常有马因体力不支,累倒在路上。有一个小战士见马在上坡的时候走不动,就拿起鞭子使劲儿抽马,口中还大声地吆喝着。巴图爷爷赶紧跑过去制止了他,并告诉小战士,在干活的时候,人和马要讲究配合,鞭子尽量不打在马身上,而是打在半空中,马听见鞭子的哨声,就知道要加倍用力了。高原的天气就像“孩子脸”一样说变就变,早晨还是晴空万里,有时到了晌午就风雪交加。战士们冻得直打哆嗦,巴图爷爷让马卧下,战士们依偎在马肚子旁取暖,才不至于被冻伤。
当地的牧民见到这样有耐力和适应力的马很惊讶,向巴图爷爷请教这是什么马。巴图爷爷骄傲地告诉牧民们,这是蒙古马,别看它们个头不大,力气和耐劲儿可不小呢。
巴图爷爷在西藏奋战了一千多个日夜,从扎罗木得入藏的两百匹骏马却所剩无几,大多数都因劳累、疾病、水土不服等原因长眠在了雪域高原。每當有马倒下的时候,巴图爷爷就会剪下它的一缕尾毛,揣在怀里,打算带回故乡,他说这样马的灵魂就可以回到草原了。巴图爷爷将援藏死去的马葬在昌都地区的一座山谷中,取名为“百马峪”,而存活下来的马,随着部队去了成都。作为军马医生的巴图爷爷也被分配了工作。在离开西藏的前一天,团长提出让全体战士到“百马峪”去祭奠为援藏牺牲的马,巴图爷爷在军车上流了一路眼泪。
后来,巴图爷爷找到军区领导,他要放弃在成都的工作,带着一匹七岁的儿马子回呼伦贝尔草原,回到扎罗木得种马场。军区领导劝巴图爷爷好好想想,不要轻易放弃进城工作的机会。但巴图爷爷已经拿定主意,他对军区领导说:“我和马都是从草原来的,所以我要把马带回草原,只要有马在,生活就有希望。”军区领导见巴图爷爷如此坚决,也就不再挽留,派了两名战士护送一人一马回扎罗木得。
岁月易老,时间流逝,只留下那无法抹去的痕迹,刻在巴图爷爷的脸上。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扎罗木得已不再是当年人畜两旺的种马场。草原加上了围栏,牧场有的被开成了田地,孩子们上完学几乎都选择留在城市里,甚至有的年轻人宁可在城市中打着零工、吃着外卖,也不肯回到家乡接过祖先留下的套马杆,他们认为做一个牧民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村里人不再养马,不少人沉迷于牌桌,更有经济头脑的牧民,将自家的牧场改成旅游景点,打造特色菜肴酱马排、烀马肉、爆炒马板肠……马肉宴一时成为扎罗木得的招牌。
巴图爷爷的孙子带着女朋友从城里赶来,女朋友第一次来到扎罗木得,她觉得村子里充满牛粪的味道,走在草原上,又害怕马粪弄脏了她新买的鞋子。他们来到景点,骑马、射箭,又在蒙古包里吃了酱马排和马肉馅蒸饺,老板为他们介绍这里的马全部都是三河马,是全国很有名的马种。他们感觉这才是扎罗木得最好玩、最值得体验的地方。
巴图爷爷坐在炕上,静静地听着孙子和他女朋友说着扎罗木得一日游的乐趣,尤其是听到他们兴致极高地说三河马不愧是名马,它的肉就是不一样,有嚼劲,好吃的时候,巴图爷爷的脸上抽搐了几下,有一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痛楚。时光老了,当年听故事的人成了讲故事的人,他想给孩子们讲种马场的来历,讲出征援藏的往事,讲那个经常在梦里出现的“百马峪”,巴图爷爷发现话到嘴边怎么也说不出口,感觉还没有景点老板介绍得好。巴图爷爷知道,他和扎罗木得种马场,都已经成为了故事。
草原的风依旧如长调般低吟,诉说着三河马的前世今生。巴图爷爷说他总是梦到自己像年轻时那样骑马奔向远处的山岗,在山岗上眺望着离云朵最近的地方。他感觉当年援藏的马,已经成为银河河畔的“天马”,化成云朵向他奔来。恍惚间他听到了嬷嬷唱的歌,听到了马在草原上奔跑的蹄声和嘶鸣,听到了“百马峪”呼啸回荡的风声。看天边鸿雁阵阵,牛羊如云,那从远古而来又逐渐消逝的文明,是扎罗木得最有深度的回响。
责任编辑 丽娜
——《幸福的拉扎罗》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