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正在重写物种
文|胡安·恩里克斯 史蒂夫·古兰斯
译|郝耀伟
1959年,苏联动物学家、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来到了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那里既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大学。作为一个骨子里流淌着实验主义血脉的科学家,他手头有什么资源,就会拿什么来做实验。最终,德米特里选择了饲养野生狐狸。
他不是随意饲养,而是每一年都会根据温顺或暴戾的秉性来对每一只狐狸进行排序。只有那些在这些特质上趋于极端的狐狸才会被选来繁殖。1/5 最温顺的狐狸和1/5 最暴戾的狐狸会被隔离开,分别饲养,一代一代,循环往复。最终,德米特里的“去野性实验”非常成功地改变了一个野生物种,这些狐狸中的一小部分变得像拉布拉多犬一样,后来甚至被运到美国进行销售,卖点是“温和的家庭宠物,特别适合陪伴孩子”。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可以通过人工选择快速增强或削弱一个物种的好斗性。
重写物种一 驯化自我
我们的自我驯化速度很快,几乎是在十几代间完成的。
人类自身从一个“全天然”的物种进化而来,如今,我们已经快速且大幅度地消除了自己身上的野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会觉得居住在干净、明亮、安全的城市中,水龙头里流出洁净的水,有马桶冲掉排泄物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99%的时间里这些条件都没能实现。我们现在已经适应了完全非自然的、由人工设计的环境,认为一切理所当然。
我们的自我驯化速度很快,几乎是在十几代间完成的。
过去,我们并不会与数百万个同类聚集在一起,秩序井然,和平共处。在之前的环境中,距离睡觉的地方几十米之外就是野地,可以采集到大多数食物。人类祖先部落的规模只有150人左右,当个体多于这个数量时,就会出现纷争,进而导致部落分裂。
我们所说的文明是伴随着农业的出现才发展起来的,始于约500代之前。公元前2000年,世界人口总量只有几千万,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得非常分散。大型城市的萌芽出现于新月沃地、亚洲、北美洲,甚至欧洲,但城市并不多见。1300年,英格兰仅有约5%的面积属于城市。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乡村是常态。即使到了1910年,仍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截至2007年,世界大多数人口都住在城市。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全球城市人口迁移只花了不到100年,或者说5代人的时间。从历史背景来看,从最早的古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到现在已经至少经过了12.5万代人。
今天,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全球范围内,城市人口到2030年估计会再增加1倍。在未来12年内,一些国家打算将2.5亿人从乡村迁往城市。要容纳这些新的居民,需要建立的城市总面积等同于将几十个特大型城市加在一起。
曾几何时,非自然环境对人类而言是非常有益的。在驯化自己和周围环境时,我们也在一点点移除阻碍人类延长寿命的绊脚石。
在人类的绝大部分历史中,大部分人的生命中都充斥着营养匮乏、疾病和暴力。人类生活的一个严重威胁是被“敌人”吃掉,各类捕食者不时出没。后来,我们消灭了这些大型食肉动物,改变了环境。现在,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寻找,才可能发现这些一度很常见的巨型捕食者。灰熊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剑齿虎也已成为化石。我们摆脱了食物链的束缚,大多数人会在自家床上或者医院里离世,而不是沦为另一种动物的果腹之物。我们还是有些担心鲨鱼,不过不幸的不是我们,而是鲨鱼——它们出现时,可能会遭到捕杀或成为科教节目中的稀有研究对象。罕见的鲨鱼攻击会引发全球媒体的关注,每年野鹿撞上汽车导致的人员死亡数量,是鲨鱼攻击致死人数的11倍。在大多数城市里,毒蛇则更为罕见。尽管更加原始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渐成一种时尚,但理智的人仍会追问:“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回到洞穴人的时代?那时候可只有10%的人能活到40岁。”
到目前为止,最危险也最常见的“捕食者”仍旧是人类中的其他成员。平均而言,我们死于战争的可能性是死于鲨鱼攻击的11 000倍。尽管世界上时有骚乱和喋血事件发生,但人类驯化自身的趋势仍是广泛而深刻的。总体而言,战争和暴力现象在各个地方都在逐渐减少。我们不会认为暴力致死是一种常态。
重写物种二 改变环境
对大多数陆生物种而言,应对极端温度和天气变化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本已适应气候波动的身体,仅仅一个世纪的光景,就适应了生活在恒定的环境中。
我们在驯化自身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生活的环境。暴露于自然环境下曾经是一个主要的致死原因。随后,我们发明了各种衣物和调节温度的方法,家和办公场所变得越来越舒适,我们对环境已经不再那么担忧了。龙卷风、飓风、洪水和干旱,甚至“末日暴风雪”都可以提前预知,进而由媒体跟进报道。得到预先警告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中,天气都是自然选择最严酷且恒久不变的驱动力量。
除了极端天气外,或许我们看到的最大变化就是无处不在、影响广泛的温度变化。对大多数陆生物种而言,应对极端温度和天气变化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本已适应气候波动的身体,仅仅一个世纪的光景,就适应了生活在恒定的环境中。我们待在有空调的大厦、居所、汽车和办公室里,在20℃~24℃之间惬意地生活着,远离寒风凛冽、暴雪肆虐、大雨滂沱。这种生活方式完全是非自然和非正常的,而且着实令人感到舒适。
对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获取食物不再是事关生死的问题,除非涉及过多的卡路里摄取。确实,仍有很多人食不果腹、缺乏营养,但饥饿已远不像从前那样泛滥。直到不久前,即使在发达国家,寻找、收集和摄入足够的卡路里都是人们每天的首要任务。而现在,饥荒已经不太常见,也远不像以前那样扮演大规模“杀手”的角色了。
重写物种三 改变其他物种
达尔文认为,如果人工饲养者能够将豢养环境中的单一物种操控改变到如此程度,那或许也可以操控改变野生的所有物种。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类改变了足以促使其他物种快速进化的绝大部分因素。
即使相对微小的环境改变也会导致植物、动物的极度多样化,但这种多样化往往发生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如果把野绵羊围进牧场,圈养几代,你会观察到绵羊的明显改变。如果把一种动物、植物或细菌物种从乡村环境迁移到城市环境中,在5代之后,可以预见该物种会发生极其迅速的基因变异,或者灭绝。一些鸽子物种,比如常见的广场鸽,从住在悬崖峭壁上、性格惊怯的鸟类,变成了盘踞广场的高空俯冲式害禽。与此同时,数十亿计的旅鸽没有适应变化,一直保持着易于亲近的秉性而常被猎手捕杀,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即从比比皆是落得销声匿迹。
达尔文明白人类驱动的非自然选择,及其后果和未来,因为当时人们已经将其应用于动植物的驯化了,他称之为“人工选择”。通过研究观赏鸽的饲养,达尔文记录了物种的快速变化。达尔文认为,如果人工饲养者能够将豢养环境中的单一物种操控改变到如此程度,那或许也可以操控改变野生的所有物种。
达尔文只是没有沿着这个逻辑继续延伸,没有预见到我们不久后掌握的巨大力量,直至改变这个星球,改变所有其他物种,改变人类自身。否则,他也会将非自然选择视为进化的一种关键驱动力。
你可能会认为,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寿命、智力和身高的显著增长趋势,好像是突然间发生的,其实不然。人们已经在漫长的时间中深刻地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使其变得不再自然、不再随机,不再那样具有危险性;同时,我们也已经彻底驯化了自己,就像驯化猫和狗一样,而这带来了重大的进化后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星球上的物种进化已经超越了临界点,转向了非自然选择和非随机变异,这甚至都不是真正的进化论2.0版,而是一种全新的、基于不同原则和机制的进化逻辑。这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进化,而是人类驱动的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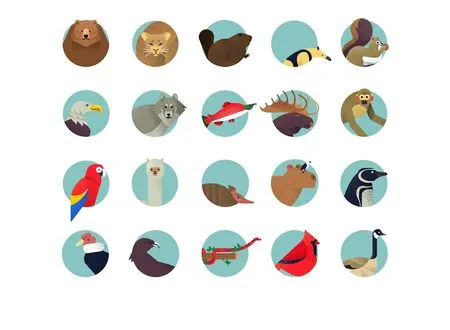
本文内容摘编自《重写生命未来》一书,胡安·恩里克斯、史蒂夫·古兰斯著,郝耀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