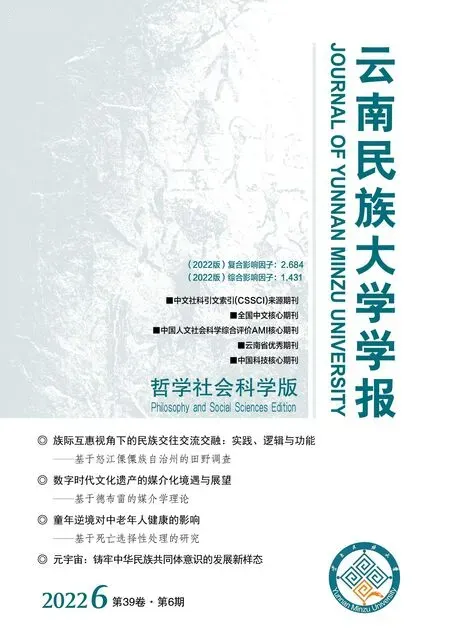“苦与不苦”:民族地区搬迁移民的生活体验研究
魏玺昊,费梅苹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一、问题的提出
易地扶贫搬迁是挖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1)肖菊,梁恒贵:《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教育保障研究》,载《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问题,“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全面展开。易地扶贫搬迁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深山、荒漠化、地方病多发等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以及生态环境脆弱、限制或禁止开发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历史上,出于躲避战乱或是远离中央王权统治的需要,部分少数民族长久居于深山之中。(2)周恩宇,卯丹:《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按照政策要求,该群体多数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踏上迁移之路。
为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各地实施差异化的补助和扶持,(3)叶青,苏海:《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开展技能和工作帮扶,(4)王春蕊:《易地扶贫搬迁困境及破解对策》,载《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甚至提供配套性居住用品。(5)王晓毅:《移民的流动性与贫困治理——宁夏生态移民的再认识》,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在政策动员和美好生活图景的牵引下,移民由农业社会迈向半工业化社会,最终实现脱贫的政策目标并获得积极的心理体验。国务院新闻办就易地扶贫搬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提到:“‘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近1000万人口解决了脱贫发展问题,完成了‘十三五’全国近五分之一贫困人口脱贫攻坚的任务。……易地搬迁让老年人更加幸福,让年轻人更有希望,让小朋友更加阳光。”不过,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脱贫过程中,移民的生活体验并非直线式正向发展的,而是矛盾且复杂的:入住新村伊始,本该享受美好生活的搬迁移民却产生了“苦”的诉说;在苦的诉说后,才有正向且积极的“不苦”的话语叙事。个别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蒙城华人移民中流行“一年大苦,两年小苦,五年不苦”的说法。(6)蔡鹏飞:《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增值转换——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入》,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那么,如何理解移民这一动态的生活体验?移民话语诉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7)“话语诉说”“生活体验”以及“生活叙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话语诉说展现出生活体验,“苦与不苦”的话语诉说便是“苦与不苦”的生活体验,两者之中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活叙事。
易地搬迁移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早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既往研究大多从政策执行角度分析易地扶贫搬迁所带来的现实困境,缺少对移民生活实践的考察。个别研究虽然深入到移民的生活现场进行微观分析,呈现了该群体在不同层面的社会适应情况,但研究大多带有一定的理论预设,并未以移民的话语为起点展开分析。同时,上述研究多聚焦于搬迁后的初期阶段,缺少在较长时间段中对移民的考察;聚焦于移民这一普遍性群体类别,缺少对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关注。文章延续微观研究的取向,以期深入到移民苦与不苦的话语诉说中,呈现移民在脱贫过程中动态的生活体验。苦与不苦的生活体验包含一系列相关联的叙事,一般通过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两个理论维度进行理解,在此基础上,研究对其进行拓展,引入“惯习”这一理论维度,基于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呈现移民话语诉说的内在逻辑。
苦与不苦的生活体验是移民生存和身心状态的重要体现,其中暗含着移民更深层次和更具常态性的发展需求。透视移民话语中的内在逻辑,可以展望有针对性的后续帮扶措施,这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其他移民地区和搬迁移民群体的后续帮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一)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现有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研究主要讨论政策执行的后果,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研究取向。宏观层面的分析基于评估标准,反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足和后续走向;微观层面着重探讨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
宏观层面呈现了易地扶贫搬迁所造成的“没有发展的安置”(8)马流辉:《易地扶贫搬迁的“城市迷思”及其理论检视》,载《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8期。。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性工程,产生了很多意外后果,具体表现为搬迁制度无法带动安置点的发展。(9)王春蕊:《易地扶贫搬迁困境及破解对策》,载《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这些反思秉承“问题导向”的思路,体现出很强的规范性导向,研究自行预设了一种“共同体”式的、且具有发展潜力的理想社区类型。研究拆分出一些评估标准,比如,移民的生计模式、收入、社会治理效益等,以诊断当下的政策执行困境及后续的发展对策。该类研究的聚焦点更多是“政策”和“数据”,移民的声音仅表达为“想要安全、舒适”(10)何得桂,党国英,张正芳:《精准扶贫与基层治理:移民搬迁中的非结构性制约》,载《西北人口》2016年第6期。,“满意与不满意”(11)史梦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感知融合研究——基于云南移民点的调查》,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或者“不适应”(12)陈坚:《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及对策——基于政策执行过程视角》,载《探索》2017年第4期。。移民的叙说被简化,且仅当做政策执行不足的注脚,移民更为丰富的心理感知和生活体验淹没于此一宏观层面的分析之中。
为弥补上述不足,研究在微观层面推进,主要围绕移民在文化(13)方静文:《时空穿行——易地扶贫搬迁中的文化适应》,载《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10期。、空间(14)丁波:《新主体陌生人社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构》,载《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经济(15)吴晓萍,刘辉武:《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经济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载《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方面的适应状况展开了讨论。这为我们呈现了移民不适应的层面,以及更具体的感知。但是,移民的适应是动态、复杂且个体化的,单一层面的研究不足以完整呈现移民的适应状况。更为关键的是,在新的生活空间中,移民的身体感受被忽视了。对此,江立华、曾铎从空间视角探讨了移民的身体适应过程和机制。(16)江立华,曾铎:《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空间变动与身体适应》,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综合来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政策执行的不足,较少关注移民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微观层面的研究虽然有所推进,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搬迁移民生活体验的研究较为缺乏,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丰富,并为后续帮扶提供更多的启发和建议;其次,既往研究多探讨移民这一普遍性的群体类别,缺少对于少数民族移民的关注,不可避免会忽视该群体的独特经历对其搬迁后感受的影响;最后,研究大多对易地扶贫搬迁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框定,认为这是一场文化、经济或者空间的转型。既往研究以不同层面的转型为起点挖掘移民的相应感受,而非以移民的感受为起点去理解其背后的深层逻辑,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前者的限定性较强,难以真正体现移民能动和自由的话语诉说,或者对其有所裁剪,而后者可以忠实于移民的整体生活体验,遵从其主体性。那么,当我们有了“苦”与“不苦”的研究起点,又该从何种角度理解移民诉说背后的内在逻辑呢?
(二)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理解个体生活体验的理论维度
“苦”与“不苦”的生活体验常见于土地改革(17)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以及弱势群体(18)何潇:《“苦”:上海打工者的社会记忆和日常体验》,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的社会学研究中。这些研究认识到,个体所诉说的生活体验属于一种叙事,包含一系列相关联的生活事件,蕴含着个人的理解、感知以及社会环境因素。(19)谢景慧,吴晓萍:《苦与不苦:时代规训与三线人的双重叙事》,载《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5期。此类研究着重分析苦与不苦的诉说对国家政治动员以及个体日常生活所发挥的功能,并未在叙事产生的原因方面带给我们更多启发。借助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关于个体叙事的理解主要聚焦于两个理论维度: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社会结构是影响个体叙事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总是镶嵌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因此,个人叙事是社会结构的反映。(20)周晓虹:《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载《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在不同研究中,社会结构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有研究呈现了终末期肾病患者三个层面的疾痛体验的叙事,社会结构是形塑叙事的重要力量之一。(21)何雪松,侯慧:《“过坎”:终末期肾病患者的疾痛体验》,载《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5期。此研究中,社会结构被转译为关系网络,即不同主体或者病患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关系。在留守儿童群体中,“爱而不亲”的能动叙说也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存有关联。(22)肖莉娜:《“爱而不亲”: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体验与建构》,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这一社会结构体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经济机会和制度障碍。总结来看,社会结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或者制度体系为个体提供的资源,它们通过促动或者限制个体的发展进而影响其话语诉说。在社会结构的促动作用下,个体可能有更加积极的话语表达;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作用下,个体的话语表述或许呈现消极的一面。
个体的叙事也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格根提到,我们的心理感知和话语叙述是嵌入在文化传统中的,我们只能从我们的文化和时代之中来言说和书写。(23)[美]肯尼斯·J.格根:《语境中的社会建构》,郭慧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景军关于记忆重构社会关系的研究也提到,人们在文化中成长,并获得了习惯性的记忆,它使得人们经常性地想起文化传统中的动作和语言的恰当形式。(24)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农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吴飞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人们的言说或借用的语言,或是直接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印记,如上山下乡知青提及的“青春无悔”;(25)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或暗含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意涵,比如,周飞舟揭示出,脱贫攻坚中部分农民呈现出主动发展的内生动力,这起始于农民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的行动意愿,意愿体现的是家庭本位和伦理本位的传统文化底色。(26)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载《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三)惯习:理解少数民族移民生活体验的特殊理论维度
上述两个理论维度为理解个体的生活体验提供了方向,但作为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他们的经历深嵌于历史、地理、主观性、脆弱性和复杂性之中,具有其特殊性,少数民族移民领域的部分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一群体的叙事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启发。
综合国内外研究来看,多数学者对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关注聚焦于文化层面,他们认为,少数民族群体的迁移势必经历跨文化情境的转变。(27)王建民:《扶贫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以少数民族主体性讨论为核心》,载《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从所属文化情境迈向陌生文化情境时,少数民族移民不可避免产生压力,(28)Young Yun Kim: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No.4,2008.这种压力体现为一种紧张、焦虑的负面心理体验,它源于移民自身能力、身份、期望与新环境要求之间的差距。(29)Margaret J. Pitts: Identity and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Stress, and Talk in Short-term Student Sojourner Adjustment: An Application of the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No.6,2009.对于移民旧有的知识、技能、信念和生产生活方式来说,塞耶(Sayer)结合布迪厄的理论,将其作为惯习的关键维度,同时,他拓展了惯习的内涵,将罪错、同情、内疚、羞耻等“道德情感”纳入到惯习的内涵之中。塞耶提到,如果行动者缺乏适当的惯习,不能在特定社会领域获得资本,那么他通常会经受被边缘化的体验和负面的心理感知。(30)[英]罗布·斯通斯:《核心社会学思想家》,姚伟,李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68页。由是观之,惯习与外部环境要求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理解少数民族移民生活体验的重要理论视角。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将借助“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惯习”这一整体性分析框架,呈现移民生活体验的内在逻辑。研究的田野调研地点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甸县苗村,它是由后村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新建的一个村,是纯苗族村,后村属地质灾害隐患点。2016年3月,为了改善后村生产生活环境,当地政府启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动计划”。2017年10月,后村苗民正式入住苗村。移民入住一年后,甸县正式退出贫困序列。2019年6月,笔者借助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入住苗村,从事为期6个月的社会工作服务。在需求调研中,研究发现了“苦”与“不苦”的不同层次的叙事。以最初提炼的叙事为基础,研究借用“饱和原则”进行资料的搜集。
三、移民“苦”的诉说(一)苦的三重叙事:生活支出、养育与人居环境转型
1.生活支出之苦
易地扶贫搬迁为移民建造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空间,却也使移民产生了较大的心理压力。苗村新建住房33套,每套105平米,统一的建筑模式、24小时可用的自来水以及便捷的网络使得移民迈入全新的美好生活。这一现代化的生活空间具有较高的生活成本。移民提到,除了与后村相同的日常支出,搬迁后,移民还需要考虑网络、煤气、电磁炉等新的生活成本。
此外,每家喂养的牲畜,也因空间的压缩,给移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猪牛羊是苗民最为看重的几类牲畜,它们可以为苗民带来收入。政府意识到牲畜对于移民生计的重要性,特地修建了牲畜喂养栏。虽然苗村的牲畜栏面积大大减小,牲畜喂养数量也相应缩减,但这并不意味着较少的喂养开支,土地面积的减少反而增添了原本并不需要的支出。在后村,每家大约有十几亩土地,搬迁后,土地数量仅为两亩。现有土地所产出的苞谷量难以维持牲畜喂养的需求,移民需要额外购买饲料,这些花费大约每年1000~2000元。因新产生的支出,村民纷纷抱怨日子“不好过”“苦的很”。
2.养育之苦
易地扶贫搬迁期间,苗村同步展开了控辍保学行动,这与苗家传统婚礼一起加重了移民的养育负担。为保证移民生计的可持续性,彻底斩断穷根,苗村将零辍学作为首要的脱贫评估标准。在后村,虽然较早接受汉语教育,学生还是因多重不适以及各方劝返工作的不重视而早早辍学,从事家务劳动。家长无需过多考虑孩子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相关支出。控辍保学后,苗村学生必将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甚至继续读高中、职校或是大学,孩子在当下以及未来可预见的支出给苗村家长带来苦的感知。
不仅如此,在养育层面,家长还有供养孩子结婚的苦。苗家人对于婚礼仪式较为看重。以男方家庭为例,结婚前,男方要为女方送彩礼,礼金为4000~6000元。婚礼要办两天一夜,整个婚礼的支出约为3~5万元,所收的礼金难以弥补婚礼的花费。同时,随着甸县各地区陆续脱贫,女方彩礼的要价有所提升。这种外部趋势和既有传统给移民带来了压力,不少移民提及“办个婚礼苦得很”。
3.人居环境转型之苦
为实现“建新村、塑新民”的目标,苗村实行“七改三清”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为打造干净、整洁的家居环境,社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评比“洁净之家”,获得评选称号的家庭将获得流动红旗。移民虽然对此并不是很在意,但觉得如果村子修建得很漂亮,但是屋里很邋遢,对比之下,其内心并不舒服。
为实现屋里屋外环境的一致性,移民认为,需要改变家庭布置,迈向主流美好生活。在移民的认知中,所谓主流美好生活意味着政策提倡的、和城里人一致的生活,也可以等同于现代化和自动化的生活。比如,移民在后村使用的是木制、竹制板凳,搬迁后,移民认为需要买皮质或者布质沙发。再比如,移民之前骑的是摩托车,搬迁后,移民需要购买汽车。这些符合主流美好生活语境的产品需要的支出较多,部分移民借助优惠政策和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购买,部分移民还是无力承担这部分花销。移民或是苦闷于无法立即过上政策宣讲的、也是自身所期盼的“好日子”,或是因分期付款而承受较大的家居环境转型之苦。
(二)苦的内在逻辑:族群惯习悬浮与践行文化传统的困境
1.族群惯习与制度规范的脱嵌
在后村长久的生活实践中,移民形成了适应山林空间的族群惯习,它包括移民谋生的手段、技能、日常的思维观念、生产生活知识等。搬迁后,移民迈入半工业化的生产生活空间中,其间的制度规范对移民产生了新的要求,而移民的能力在短期内难以适应这一外部要求,因而形成了族群惯习与制度规范的脱嵌状态,这给移民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感知,使得移民产生苦的诉说。具体来说,三重苦的叙事蕴含着移民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碰撞。
后村地形简单,山地面积居多,只有少部分适合耕种的土地,并未吸引工业投资。在长久依赖土地和山林的生活空间中,移民以土地和山林谋生,掌握的是耕种、节气、捡菌、挖药等农业社会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生产方式可以帮助移民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在远离工业化的生活空间中,移民的家具通过砍伐竹子和树木,就地取材加工制作而成;赖以维持生活的苞谷、洋芋以及萝卜等农作物也只需自行种植。移民极少参与市场交易,他们的生产能力足够应对婚丧嫁娶等传统礼俗的开支。对于教育而言,移民认为教育并不能实现代际更替,回家劳动是更现实的养家糊口的方式,这有助于维持家庭的生计和收入。因此,移民默许了孩子的辍学行为,只需关心孩子的婚姻大事。
当进入政府规划的生活空间中,电话、网络、家庭用水以及现代化的家具产品或者出行工具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移民的生活受现代化生活方式和市场交易逻辑影响的范围更广。此外,在日益接近劳动力市场后,移民家庭需要有足够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来应对市场风险所导致的不稳定就业状态,同时,教育意味着收入,这是保证移民脱贫、不返贫、过好日子最有力的手段。因此,当地街道实行了教育扶贫的一票否决制。精准扶贫以及控辍保学行动中的制度规范给移民带来了全新的养育责任,增添了新的养育成本。但移民还未适应市场化和工业化的生活节奏,未掌握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谋求生活所需,这便产生了生产和消费的断裂,族群惯习与制度规范的断裂,这种不匹配状态导致了移民的压力感知。
2.文化传统的实践困境
族群惯习与制度规范的断裂,意味着移民滞后的能力和短缺的收入,移民将其与苦直接关联起来。这种苦有更深层的逻辑,这指向了移民时常表达的“良心难安”和“过好日子”的困境。
移民的苦,蕴含着难以恪守良知的困境。不少父辈提到,作为“当家的”,如果没有能力获得足够的收入,满足家庭的正常开支,维持大家庭的生存,自己“良心难安”,也会让村里人指责。孩子正在读书的父母提到,作为“当父母”的,帮助孩子实现梦想是他们的责任,否则自己心里过不去,也会被别人嘲笑“不是合格的父母”。此种困境也是围绕家族传宗接代的使命展开的。苗村具有内向性发展的倾向,即“苗家人只找苗家人”。据甸县统计,苗族仅占总人口的1.27%,苗家青年男女必须尽快结婚,才能成为“有另一半”的少数群体。因此,在高支出的生活空间中,父母认为如果没有能力尽快攒钱,以备孩子结婚使用,那便无法帮助自己和孩子完成对于家族使命的承诺,这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移民的苦,蕴含着难以“过好日子”的困境。生活于美好生活的主流叙事之中,不少移民产生“怕别人瞧不起”的压力。比如,如果自己还骑摩托车,有可能会被嘲笑,因为摩托车属于过去的年代,当下生活环境中,汽车才是符合主流美好生活的出行工具。再比如,如果自己家庭依然脏乱不堪,没有像样的家具,也可能会被别人在背地里议论。无法实现政策所提倡的、与城里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便不会“过上好日子”,这种情况下,移民难以获得荣耀性表现,以至于自己不能获得他人较好的评价。
由是观之,因能力不足难以获得足够收入而产生的苦,其实质是难以践行文化传统要求而产生的苦。难以恪守良知的苦与家庭绵延相关,这一家庭不同于西方的家庭,具有较大的弹性,这不仅指移民的核心家庭,还指由核心家庭所扩展而来的父系亲属的家族。无法过好日子的苦与个人的荣耀性表现有关,深嵌于时代潮流和村落关系网络之中。无法恪守良知,表征为移民无法为家庭和子女做出贡献;无法过好日子,表征为移民的生活与时代和村落的主流生活存在差距。这二者导致的结果相似,即移民难以获得他人的认可和积极性评价。
四、移民“不苦”的话语转换
上述提及的困境,仅作为一种被觉察的状态出现在移民的认知之中,并没有成为业已发生的事实,这源于移民知晓彼此面临的现实处境并相互理解。移民清楚,如果长久无法实现改变,这种觉察的状态定会成为现实。移民提到,为了良心上过得去,也为了过上好日子,以获得别人的认可和赞许,他们决定不能再维持没能力、没钱的贫穷状态。就此,移民主动谋求发展的意识被激发。外部主体恰好为移民提供了知识和技能帮扶,移民得以满足自身需求,由此产生不苦的话语诉说。
(一)不苦的叙事:外部主体帮扶下的需求满足
1.外部帮扶网络形塑
精准扶贫期间,苗村具有多个帮扶主体,形成了颇有成效的外部帮扶网络。主要的帮扶力量包括县政府、街道、社区和其他地区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移民自身的亲属关系网络也参与到苗村的帮扶中,形成补充性帮扶力量。
县政府与当地街道起到牵头和统筹的作用。为帮扶移民脱贫增收,县政府与其他省市签署务工合作计划,移民可以外出参与铁路维修和小商品生产工作。当地街道积极探索“党支部+”模式,通过整合土地、资金与劳动力等资源,形成多种具有在地特色的产业和项目。比如,打造“党支部+企业+基地+贫困户”模式,建设稻鱼共生种养示范基地,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发展和壮大苗鸡养殖产业。此外,当地街道积极联络,引入外部帮扶力量,与其他地区采取“党组织联建共建”的方式,借此引入第三方资金力量,发展特色产业。比如,依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苗村流转耕地80亩,按照统一种植标准、统一技术服务、统一收购销售,产供销“一条龙”的模式,发展香瓜种植产业。
移民自身的亲属关系网络主要为移民在其他村落中的亲属,他们为移民积极联络资源,寻找工作机会。工作类型主要有服务型工作和技能型工作两种,前者主要是在餐馆当服务员,后者主要是去汽车修理厂或者建筑工作队。
2.移民行动能力提升
为使得产业、项目以及工作机会真正成为移民谋求发展的重要渠道,外部帮扶主体采取不同策略提升了移民的非认知能力和生产能力,前者开阔了移民的发展思维,后者提升了移民的生产知识与技能。
主要帮扶主体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改变了移民旧有的认知,使其认识并接受了脱贫致富渠道的多元性。移民久居深山,习惯以土、以山林谋生的小农生产方式,当转换发展方式,需要移民投入资金或者外出工作时,他们对此有很强的不安全感。驻村队员和包组干部主动上门宣传政策,通过“零距离”的沟通方式,深入把握移民的内心想法。为打消移民的疑虑,真正发挥帮扶措施的有效性,驻村队员和包组干部通过脱贫致富的相关案例,解决移民的困惑和行动难题。除此之外,通过召开户主会、党员会等方式,帮扶主体借助“致富带头人”的榜样示范效应,增强移民对新生产发展方式的信心和接受度。
多元主体在知识、技能方面为移民提供培训,提升移民的生产发展能力。比如,苗鸡养殖和香瓜种植需要种养知识和技术,合作社和公司定期无偿为移民提供培训。这有利于科学种养,提高种养的质量和产量。不仅如此,合作社与公司还为移民提供销售信息和渠道。按照协议,移民既可以自主销售产品,也可以按照保护价将其卖给合作社和公司。为进一步拓宽移民的发展空间,甸县定期派专家前往社区开办讲座,讲座类型包括耕种技术、烘焙、创业等。亲属关系网络为移民提供的工作通过“带教制”和“学徒制”进行培训。餐馆老板或是行业师傅经验丰富,他们既帮助移民学习经营理念、修理技术以及建筑技术,还帮助移民学习必要的礼仪。移民在带教关系和师徒关系中提升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和职业素养。
3.移民需求满足与不苦的诉说
多元帮扶主体提升了移民的生产发展能力,移民在当地产业和外出务工中获取了更多收入,满足了自身需求,消解了多重苦痛体验,并产生不苦的话语诉说。
移民不苦的话语诉说体现在填补生活开支、践行养育职责和满足人居环境转型需求三个层面。其一,填补生活开支。获得工作的移民通过现金或是银行转账获得收入,移民将其用于水电费、电话费、网络费以及牲畜喂养等日常开支中,这使得移民不必再苦于现代化生活空间中的高支出。其二,践行养育的职责。虽然义务教育政策减免了学生上学的绝大部分费用,但一些附带的费用不容被忽视,比如,学生上学的车费、学习资料的费用、购买生活用品的费用以及发展兴趣爱好的费用。移民无条件地为孩子的学业提供支持,并支付孩子发展兴趣爱好的费用。部分移民家庭定期送孩子前往县城参加钢琴、舞蹈、绘画等课外辅导班。移民剩余的绝大部分收入存入银行账户,以备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或是结婚使用。在满足孩子的教育需求,并且为孩子的发展和婚姻储备有较多积蓄后,移民产生了不苦的话语诉说。其三,满足生活转型需求。移民的收入除了用以日常家庭开支和养育,还被用来购买新的家居产品,比如汽车或是全新的家具。这一里一外的大件是帮助移民获得他人赞许最有力的保证。
在日常生活、养育和追求美好生活主流叙事上的努力,使得移民恪守住内心的良知,融入了主流美好生活。移民不仅获得了彼此的认可和良好评价,也赢得了外来人的积极评价。作为一项扶贫工程示范点,苗村每月不定期接待其他省市的参访团。在目睹了整洁的社区和家居环境,了解到移民生产生活现状后,参访团纷纷给予赞许。这些评价或是移民在与参访团交流中直接获得,或是从村长那里间接得知。在增收致富,有能力保障子女和家庭的生存发展需求并过上好日子后,移民认为“现在的生活不苦”“日子好过”。
(二)不苦的内在逻辑:族群惯习转型与道德情感驱动
1.族群惯习与制度规范的嵌合
移民需求的满足,源于自身行动能力的提升,这意味着移民族群惯习的转变。具体来说,移民不苦的内在逻辑是,族群惯习由滞后性转变为发展性,从而适应了制度规范所带来的现实要求。
发展性具有以下两种含义:首先,新的生产环境中,移民具有了参与和融入的机会。思维的开放性和基本礼仪适应于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有利于移民获得工作者的身份和角色,构建或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以嵌入不同行业、企业和工厂的生产体系之中;其次,不同领域中的培训,使得移民提升了生产效率,掌握了主流生产模式所需要的知识、话语、技能和身体实践能力,移民的生产技能更适应于工业化和半工业化的生产模式。
这一族群惯习的转型是以破除空间结构不平等为前提的。出于历史原因,移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处于边缘位置,且地形单一,不利于发展。多元主体的协同帮扶,拓展了移民的发展空间,移民既可以实现在地发展,还可以实现更远空间中的发展。多元帮扶主体为移民输送了发展资源,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破除了空间结构的不平等,激发了苗村和移民的发展动力。
如此一来,从后村迁移至苗村一段时间后,移民滞后的族群惯习被改变,获了进入不同生产领域的文化资本,产生了更具有适应性的行为,由此产生了不苦的话语诉说。
2.道德情感的推动作用
不苦的话语诉说与族群惯习的转型关联紧密,为深入把握移民话语转换的内在逻辑,需要继续澄清推动族群惯习转型的内在动力,这指向了上述所提及的移民“为了良心上过得去”或者“为了过好日子”的需求,前者深嵌于恪守良知的家庭行动伦理之中,后者扎根于美好生活的主流叙事之中。这种需求的驱动源于两种道德情感,一种是表征为内疚的道德情感,一种是表征为羞耻的道德情感。
塞耶提到,虽然惯习具有持久性,但很多情况下,如果行动者能够反思自身惯习,他们可以克服或推翻惯习的某些方面,道德情感是驱使行动者做出改变的关键。这种驱动作用是在困境中被激活的,这与一系列的标准相关,即过有尊严的生活,感受到他人的重视,有能力过一种他们认为值得过的生活(31)[英]罗布·斯通斯:《核心社会学思想家》,姚伟,李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69页。。如果行动者的处境与上述判断标准存在偏离,道德情感便会推动行动者迈向自我改变。
对于搬迁移民来说,旧有的惯习使得移民在家庭延续和家庭生活更替中产生困难,它无法帮助移民提升收入,移民陷入到难以恪守良知和难以过好日子的困境之中,无法过一种符合内心意愿、有面子、获得他人认可和赞许的生活。此时,移民的内疚感和羞耻感被激发,比如移民经常提及的“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或者“怕别人嘲笑”,它们推动移民产生改变的意愿,并主动接受外部主体帮扶,最终在增收致富中满足自身需求。
(三)话语转换的现实依托与内在成效
苦与不苦的话语转换扎根于移民从贫困到脱贫的过程中。移民苦的诉说产生于搬迁后的贫困阶段,不苦的诉说体现了外部主体帮扶下,移民提升脱贫能力和收入,实现脱贫的目标。话语转折的内在动力来自移民脱贫意愿的激发,外在动力来自多元主体的帮扶。
移民的诉说预示着其韧性的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属于一项现代化工程,也属于移民与新的生活环境之间关系的调适。在关系的选择中,移民或是维持现状,要求环境改变以适应自己;或是积极调整自己,寻求改变以满足环境要求。在前一种关系的调适中,环境改变所需要的能力和成本过高,无法长久维持下去,(32)白子仙:《学习:城市社区治理中知识的沟通与交流》,载《社会建设》2019年第4期。从长远来看,移民依然无法逃离负面的心理压力,且与最初相比,这一压力的强度相同甚至更高。在后一种关系调适中,移民的调整不但可以实现与外部环境的契合,还会使得自身在调适中积累经验,增强心理韧性。在此后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移民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小。(33)Young Yun Kim: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No.4,2008,P364.因此,移民谋求与环境契合的行动意味着移民韧性的提升。此一提升的过程是以外部主体帮扶为前提条件的,受限于不均衡性发展资源,移民无法依靠自身实现发展,外部主体的一系列帮扶措施与移民自身的发展意愿形成一种建设性合作关系,移民借此实现改变。
五、结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易地扶贫搬迁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动深刻影响了移民及其生产生活环境。研究跳脱出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立足于移民苦与不苦的诉说,呈现其搬迁后的生活叙事和深层逻辑。
(一)移民诉说的内在逻辑
苦与不苦的话语诉说呈现着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惯习之间的互动。在苦的诉说之中,社会结构具体体现为易地扶贫搬迁、控辍保学行动以及七改三清工作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多呈现为一种限制。文化传统体现在“苗家人只找苗家人”“良心难安”“过好日子”等文化术语或是行动逻辑之中。惯习体现为移民在后村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惯习与社会结构的脱嵌是苦的生活体验的核心所在。在不苦的诉说之中,社会结构具体体现为多元主体的外部帮扶网络与移民的关系,这种关系多呈现为一种促动。文化传统体现为“为了良心上过得去”和“为了过上好日子”的行动意愿,它们和内疚、羞耻以及发展性的生产生活惯习关联紧密。“不苦”诉说的关键在于道德情感的推动,以及生产生活惯习与社会结构的嵌合。
(二)研究贡献
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跳脱出对于搬迁移民在制度层面的考察,从微观角度研究移民苦到不苦的生活体验。宏观层面的分析,遮蔽掉了移民的能动诉说所蕴含的更丰富的现实景观。这一分析范式夸大了结构的限制作用和弊端,遮蔽了移民的能动性以及结构的促动作用,易地扶贫搬迁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安置”,从移民生活体验的流变来看,他们也在道德情感驱动和外部主体帮扶下迈向美好生活。从移民的叙事中可以看出,既往微观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他们的适应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元且复杂的,融汇着既往经验和现实转型的冲突,以及结构、文化和惯习的相互作用。从其他方面来看,研究拓展了理解个体生活体验和生活叙事的理论维度,惯习是可借鉴的视角之一。这是一种深入到个体内部的理论取向,聚焦于个体的知识、技能、信念和情感,遵从其生活经验和主体性,这区别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这些外部的行动条件。
(三)研究启发与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乡村振兴进程中,地方情境与社会文化转型的碰撞仍然存在,移民不可避免要承受转型的压力与自我发展过程。搬迁地区,从政策实践角度来说,后续帮扶可围绕下述措施展开:其一,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缓解转型中农民的心理压力;其二,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制定在地发展蓝图,借用行动伦理和美好生活图景激发农民生产发展的动力;其三,继续推进跨区域协作,提升移民发展能力,使其具备维持自我生存和发展、以及“过好日子”的必要条件。
对于研究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苦到不苦的表达是一种阶段性的话语叙事,在搬迁地区进一步转型中,移民又具有何种诉说?这需要再次回到移民的生活现场进行研究。其次,移民的诉说中隐含着多重结构性不平等,比如空间发展结构的不平等,以及教育的不平等,多重不平等的生成机理和破除路径还未被深入探讨,这也有待后续研究继续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