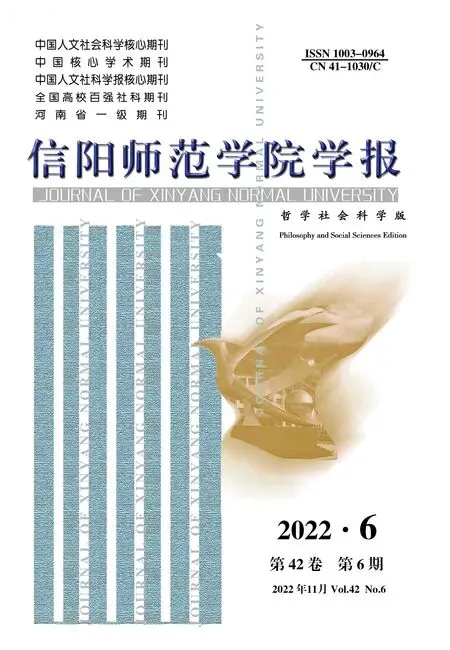炎黄文化与礼之三本
王文虎,毛瀛雪
(1.武汉工商学院 国学教育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65;2.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本文所说的“古代国家”是指成于五帝、盛于三代、衰于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治理机构。它是以礼为干的“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1]349三位一体的文明实体,亦称为“礼之三本”。“上事天”突出的是人对天的依赖关系,“王天下”的社会治理机构是“以天为王”的神道组织;“下事地”突出的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它尊主宰农耕生活方式的社稷,强调的是“有天下”;“尊先祖”突出的是后人对祖先的依赖关系,其所尊先王之政表现为宗庙、孝道,强调的是“治天下”。中国文化在宗庙制度出现以后,将事天、事地、尊祖进行了三合一的整合,从而将“中央+四方”的天下结构上升为王权国家。因此,从中国古代事天、事地、尊祖的祭礼中,我们可以探索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道路。
一、事天:依天令而立宇文国
我们研究古代文明即古代国家的形成问题,首先应该直面的是社稷与宗庙问题。但是无论是祭祀社稷,还是祭祀宗庙,所祭祀的都是有生命的人的社稷与宗庙,所以它包含着对生之本的确认。
确认生之本也是探索古代国家起源的逻辑前提。文化之初,所有部落社会组织都依“人对天的依赖关系”而建立,强调的是人生而有性,而人之性由天所授。《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2]896《大戴礼记·礼三本》云:天者“性之本也”。这里的“性”也即是“命”。故《中庸》称:“天命之谓性。”在郭店楚墓竹简中,有《性自命出》一篇。它被认为是儒家文献,其中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3]135“命自天降”意味着命由天生,君之产生以此为前提。
仰望日月星辰,感受风雷雨雪,初民无异于动物。但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震撼于日月星辰的如期而至,认为这是天令的结果,这就是《管子·枢言》所说:“天以时使。”[4]250他们试图与时背后的“神”(天)进行沟通。
在中国文化记忆中,第一个观天而通神明之德者乃伏羲氏。《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5]298他以“八卦”而“通神明之德”。据此“德”而安排生活,就有了秩序,此谓之“王天下”。不过当此之时,人类尚没达到文明的高度。伏羲氏的生活方式是“以细以渔”,由渔猎而成的社会组织是游团性的。而“游牧种族”“厌弃一切安定生活,时时破坏一切社会之组织”[6]3-4。这就无法在积累中使文化质变为文明。
“游牧种族”视“天”为最高的神。东汉马融曰:“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7]55从甲骨文看,“天”最初称为“帝”或“上帝”,如“王作邑,帝若(佑)我”(《合集》14200正),“来岁帝降其永,在祖乙宗,十月卜”(《小屯南地甲骨》723),“帝受我佑”到了殷周之际,“帝”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殷人说‘帝’,周初除了‘帝’之外,又增说一个‘天’字”[6]104,所以《诗经》《左传》等文献动辄呼“天”。人间的一切都由上天支配,帝或天可降福于人,亦可降灾于人。前者如“贞,唯帝肇王疾”(《合集》14222正丙),“王作邑,帝若(佑)我;”(《合集》14200正),“来岁帝降其永,在祖乙宗,十月卜”(《小屯南地甲骨》723),“帝受我佑”(《合集》14671);后者如“戊申卜,争贞,帝其降我黑,一月”(《合集》10171正),“帝降其摧(摧,原指鸟害)”(《合集》14173正),“帝唯其终兹邑”(《合集》14209正),“贞,帝其作我孳”(《合集》14184)。
但是“帝”或“天”并不亲自降人以祸福,它通过指令各职能神降以祸福而服天下。如武丁时期的卜辞说:“贞,今三月帝令多雨”(《甲骨文合集》14136),“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合集》14127正),“翌癸卯,帝不令风,夕雾”(《合集》672正)。这里的“帝令多雨”包括了帝令——雨神——布雨三个层次,帝是主神,也有日月星辰、风雷雨雪等现象背后的职能神。主神不直接与人联系,他以令的形式使职能神来具体操纵人间的兴衰。因为不直接与人联系,所以“皇天无亲”。依天神之意而建立的社会是“无亲”的社会。《易经》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至颛顼时代,他通过宗教革命使神道社会制度更加完善。颛顼规定一般平民只能与职能神沟通,而与天沟通却是王的专权。自此而后,历代帝王不论是开国者还是中兴者,抑或丧国者都不敢忘记祭祀上天。在郊谛形式中,君王宣誓自己的威权源于上天,而“非继前王而王也……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8]19。其对君王的威权其实是天对于人的威权显示,这种“人对于天的依赖关系”构成了后世所谓的“道义”观念的来源。
神教社会强调性自命出,后世史学家认为这纯粹是牵强附会之说,但是作为文化,自觉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人对于天的依赖关系的基础上,这使人类以天选之民的资格站在动物面前。当文化进入文明时代后,“神道”仍然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起作用,上面所引甲骨文即是华夏民族从文化上升到文明过程中以“天选”为首要观念的证明,董仲舒所说的“受命之君”也是“天选”观的体现。只不过这种“天选”观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日益淡薄。但是在文化后进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天选”观仍很流行,如魏晋时期北方鲜卑民族中有“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9]1。从宇文氏的“天选”观,我们可以窥视华夏民族早期的“天选”观,这就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
“神道”在古代国家的形成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之为国要有正义性渊源,“天授”就是国家形成的终结性根据。在考古文化中,“以神道设教”属于“古文化”的范畴,它因神道而“王天下”,也就是“宇文国”之概念。这种无“亲”的“古代国家”崇拜,实际上是对国家形成的正义性崇拜。
二、事地:依地而立社稷国
“以神道设教”的游团社会主要谛祭上天。所谓“游团”是指处在采集狩猎阶段的人类社会组织,这一阶段的人类是居无定所。当文化由游团进入农耕时代后,人们不仅要祭天,而且还要祭地。祭天谓之“封”,祭地谓之“禅”,合天地之祭而谓之“封禅”。《管子·封禅篇》云:“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4]953就是“封禅”,具体礼仪形式是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目的是报天之功;在泰山下的小丘上除地祭地,目的是报地之功。
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起的眼泪和心灵的波动,是任何别的人不能引起的。 “西比尔”和“预言”,只有在用来谈论他的时候才不带讽刺,而是直接的真理,清醒的真理。[2]205
农耕社会的治理机构虽然仍以“天选”为正义性渊源,但是它重视社会治理机构的财富供给能力,而支撑财富供给的是土地。所以这种社会里“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是“最近于人性的神”[10]2。中国传统文化称“土地”为“社”。《论衡·顺鼓》对社的解释为:“社,土也。”[11]683《说文解字》的解释为:“社,地主也。”依照《礼记》的说法,“地主”是主阴气的神,所以最初称“地母”。《周易》称坤称母,直到今天,仍有“大地母亲”的社神意识。
费孝通认为土地是人格的,是白首偕老的老夫妻一对。在土地崇拜里,人对上天依赖关系的重要性让位于天人对土地及其财物的依赖关系。社神的名目非常多。土地是广袤无际的,不可能一一都祭。正如《白虎通·社稷》所说:“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12]83。地主之所以值得尊崇,是因为它乃财之本。所谓“财”,即是由土地所生长的万物。《白虎通·五行》云:“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12]168土地包含着生育万物的能力,社神所崇拜的就是这种土地生产力。在农耕社会,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粮食,在中国所谓“食”也就是“谷”。“谷”者乃泛称,指一切栽培的禾本科植物(如黍、粟、稻、麻、高粱等)的大名,亦称“五谷”或“百谷”。从考古学上看,谷在中国北方即黄河流域是指黍粟,而在中国南方即长江流域是指稻[13]25。百谷百蔬背后皆有神灵,是谓“谷神”。北方的黄河流域的谷神是“稷”;南方的长江流域的谷神是“稻”,二者通称为“谷神”。百谷背后的神灵人们都是要祭祀的,但是一一进行祭祀太麻烦,于是人们在其中找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来祭祀。在古代五谷中的稷的地位最高。正如蔡邕在其《独断》中所言:“以稷五谷之长也,因以稷名其神也。”《孝经纬》云:“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白虎通》亦云:“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12]83《汉书·郊祀志》云:“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14]1269
社神与稷神都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社神。《管子》云“地以材使”[4]250。社(土)通过“财”即稷(谷)表现其神性。这样看来,社稷崇拜表明土地乃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没有土地,人类难以生存,所以社稷表达的是人对自然(土地)的依赖关系,由此而建立的社会组织在宗教上包括自然神崇拜,其实是对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崇拜。
社稷崇拜可以追溯到炎帝神农氏世。对这个问题进行溯源研究有两个路径。一是将稷神纳入炎帝神农文化的范畴。文献分析表明,在夏代以前神农氏是指烈山氏之子“柱”。“所谓神农者,得谓即烈山氏子农(即柱)矣”[15]222。《说文解字》解“柱”字云:“楹也。柱之言主也。屋之主也。从木。主声。”许慎的解释与《国语·鲁语》相合。《国语·鲁语》云:“楹,柱也。”可见“主”是“柱”的本字。“主”的篆文似草木的初生形态,它包括了土地,但主要是指草木从地而生之象,表明土地是生长万物的主宰,“柱”当为从土地里生长万物的主宰,据此可知,“烈山氏之子”即为地主,因为庄稼和粮食由他而来,所以又被尊为农神。不过到了商代,周弃亦为稷,他成为取代柱的新稷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16]1673-1674从柱到弃的过程就是“农神”的变革过程,不过具体对象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有一点是“百王不易”的,它就是重土重农精神。最初为这种精神奠基的是烈山氏。以烈山氏为逻辑起点,中国农神表现为这样一个序列:烈山氏→柱→弃→稷神(神农)。二是将社神、地主或地母纳入炎帝神农文化的范畴。《汉书·郊祀志》称社神、地主或地母为“后土”,是掌管土地的神。此神最初是指“句龙”。《周书·武成》曰:“告于皇天、后土。”蔡传:“句龙为后土。”《晋书·天文志上》曰:“弧南六星为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为星。”这就是说,句龙因为治理水土有功,所以他死后被祭为后土,是掌管土地的神。“句龙”属于炎帝系列的文化英雄。《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呜,噎生岁十有二。”[17]279这样看来,社神(地主)的起源,表现为这样的一个序列:炎帝→共工→句龙→后土(社神)。
可见社稷崇拜首先将天下财富(百谷百蔬)归于烈山氏(炎帝神农氏)子“柱”,并将生长财富的“土地生产力”人格化为“句龙”,其实质是对炎帝神农氏的祭拜。围绕炎帝神农氏这个“地主”而建立的人对土地、生产力依赖关系的社稷组织,古籍称为烈山氏。《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但是此时的天下并不归烈山氏这一个集团所独有。事实上,一个社稷组织意味一些人的集合,意味着一方“天下”,意味着一个“国家”。有多少个社稷组织,就有多少“天下”。炎帝神农氏世是万邦林立的时代,此时的社会治理结构就是以社为核心的“社稷国”。在国家构成中,“社稷国”虽然在“天令”之后,但也是古老、恒久的“建国”要素。历史常常是一个王权取代另一个王权,一个王权消失了,江山却仍然存在。杜甫在《春望》里讲:“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看似平常的两句话,却蕴藏了诗人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对“山河”与“王权”关系的观察与思考。这个问题也被孟浩然观察到,他在《与诸子登岘山》诗中歌咏:“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政权在代谢中形成历史,而江山(社稷)比王权更为恒久。
社稷对国家形成的作用体现在经济基础方面。“社稷”代表了天下四方。在社稷祭祀中,人们在社稷坛的坛面分别涂黄、青、白、红、黑五色以代表各方。青者,地之东,其神太皞,以持圆规掌春天的木神为佐,是有东方国;红者,地之南,其神炎帝,以持秤杆掌夏天的火神为佐,是有南方国;白者,地之西,其神少昊,以持曲尺掌秋天的金神为佐,是有西方国;黑者,地之北,其神颛顼,以持秤锤掌冬天的水神为佐,是有北方国;黄者,地之中,它将东、西、南、北连接成一个整体,是谓居中而理四方的“中央之帝”,即中央国。蔡邕在其《独断》云:“五方正神之别名:东方之神,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南方之神,其帝神农,其神祝融。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北方之神,其帝颛顼,其神玄冥。中央之神,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在“五方”之中,中央国是拥有天下、支配天下财富的“大宗”,代表着天下,这叫“天下为公”;四方国分别是经营各方的小宗,这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了的“小康”之国。侯外庐指出:“古代公、私的意义和现代不同。‘公’是指的大氏族所有者,‘私’是指的小宗长所有者。”[18]85各方关心自己的领土,而中央帝关心的则是天下四方。例如商王“占卜的记录表示商王对他国土的四方(东土、西土、北土、南土)的收成都非常关心,他对他的诸妇、诸子和诸侯的领土内的收成也都注意,但是他对别国的粟收则毫不关心”[19]14-15。这样看来,社稷国已经表现为“中央+四方”的治理结构。
三、尊祖:依庙而立王制国
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离不开事天与事地。在事天事地的阶段,社会组织在道义上是受“天令”而“王天下”,在经济上是为“地主”而“有天下”的治理结构。可是,这里的“有”还没有解决“天下归谁所有”,即“天下是谁的天下”的问题。当社会进到由某“氏”(集团)依天命(正义性)而主社稷(领土与财富)的历史时期后,“天下”就被“所有权”固化为我们的天下”,社会治理结构以王权的形式存在着。在礼制中,王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宗庙”问题,在这里“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被转换为现实的人对死去的人的依赖关系。
在当代人的认知中,宗庙指的是人们为亡灵而建立的寄居所,它以建筑为外在形式,但是宗庙的内涵并不是指建筑形式,而是指建筑形式里的先人之像。“庙”,据《说文解字》是“尊先祖貌也”。在东汉时期,这个解释是官方认同的,如班固《白虎通》也有同样的解释:“庙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12]567不仅官方认同此说,民间亦然。如刘熙《释名》云:“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庙之所以为庙,是因为它保存了先祖的“形貌”。东晋孙盛《魏氏春秋》云:“庙以存容。”《唐律疏议》对宗庙的解说可能是最全面的,其云:“宗者,尊也。庙者,貌也。刻木为主,敬象尊容,置之宫室,以时祭享,故曰‘宗庙’。山陵者,古先帝王因山而葬,黄帝葬桥山即其事也。或云,帝王之葬,如山如陵,故曰‘山陵’。”可见宗庙是指置之宫室里的尊貌。最初它是木刻的,但因易初遭火灾,后来改为石刻,被称为“石室”。我们不能小看木主、石室,它们是祖宗的象征。《诗经·周颂》的《清庙》云:“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2]934诗所颂之“庙”,郑玄笺:“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2]933可见周人在先王死后,在其“生时之居”立其“象貌”,目的是使其音容“可得而见”。所以,祖先崇拜中的人最初是十分具体的。
追溯宗庙的起源,我们应该将目光放远至黄帝时代。我们先从黄帝时代发生的一桩大事讲起。《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云:“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20]5-6此语由《汲冢书》而来,《抱朴子》引用此语,其引于张华《博物志》。不过,今本《抱朴子》不见此语,平津馆本《抱朴子》以之为外篇佚文。查晋人张华《博物志》卷八《史补》确有此语,“黄帝死后,其臣左彻削木做黄帝之像以奉之”。
左彻为什么要削木做黄帝之像以奉之呢?《博物志》没有交待。如果我们将此语与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的记载联系起来,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晰了。原来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这就是说,黄帝在荆山下用铜铸鼎时,天空中突然有龙垂胡髯而下以迎黄帝。黄帝于是就骑着龙上了天,而“从上者七十余人”。今天看来,黄帝骑龙上天的突发事件是不可能的。但是,假若像有人想象的那样,这起突发事件与发生在荆山的一场龙卷风有关,“不可能”的事件就变得“可能”了。这场龙卷风的威力之大,一下子卷走了黄帝及其从者七十余人。黄帝被卷走后,黄帝朝必然出现权力真空。为了稳定朝政,黄帝的大臣左彻想起了削木刻黄帝像以示黄帝还在临朝。这个办法使黄帝的朝臣们认为黄帝只是上了天,并没死,他还会回来处理朝政的。但是这一等就是七年。在这七年内国家没有改变黄帝在时的政策,即没有改变“父道”。可是七年过去了,黄帝还是没有回来临朝。这就有了左彻另立新君颛顼一事。张华《博物志·史补》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也”。
左彻削木象黄帝以朝之,实际上是在大地上建立起了第一座庙。立庙此后形成制度。黄帝死后有庙,颛顼死后亦然,《庄子·大宗师》:“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顓顼得之,以处玄宫。”[21]247这个“玄宫”恐怕与宗庙有关。有祖庙,也就有了对祖宗进行排位的昭穆问题。《国语·鲁语上》云:“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昭穆排序里有亲疏、远近、等胄之分。在“列祖列宗”面前,时王在更替,但宗庙却圣圣相传。子孙无改于宗庙之治,就是“孝”。《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22]42这里的“父”可以指君父,孔子强调孝乃是指君父死后三年无改于君父之道。一些探究《论语》“本意”的学者对这个话的解释只是直译,而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本意”究竟是什么,采取了回避的办法。只要我们把此事与左彻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事件联系起来思考,问题的答案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它与左彻削木象黄帝帅诸侯朝之七年何其相似。三代以前,“无改于父之道”是否称为“孝”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孔子那个时代,它被称为“孝”。以上想法虽然有些“大胆”,但在文献上,我们还是能找到相关的蛛丝马迹。《郭店楚简》有《成之闻之》一篇,其中讲“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郭沂曾将这个话解释为“枯木用过三年后,已经朽烂,自然就不能作为疆界标志继续使用了”。王博引用此语,并指出“槁木三年”应该是指三年之丧的礼制[23]294-300。在这期间,新君不问国事,由冡宰代行职责,此谓之“三年不言”。此俗很古。传说尧死,舜曾为尧服三年之丧。可是在削木为庙一事面前,它算不了最早。左彻在黄帝升天以后木庙为黄帝国标志或“邦旗”长达七年。在这七年间顓頊不言。从顓頊的“槁木七年”,至尧时的槁木三年,时间虽然缩短了,问题的实质没有变,即无改于父道。
当然,关于宗庙与黄帝的关系还有另外的说法,即认为是黄帝本人自作庙。如《黄帝四经·立命》说:“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这就是说,削木为黄帝像并非左彻为之,而是黄帝本人“作自为象,方四面”的。这与《吕氏春秋·本味》所云“黄帝立四面”相吻合。可是无论是黄帝“作自为象”,还是左彻削木为之,有一点是共同的,从黄帝氏世起,华夏文化就进入了以为祖宗治天下历史时期,《周易·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5]300“垂衣裳”即礼制,以礼治天下始自黄帝,他将人对社稷的依赖关系上升为“人对宗庙的依赖关系”。
宗庙的出现,使社稷国变成了王权国家。国家的本质要义在于首先确定谁才是天下的主人。我们常常说,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阶级。这个命题的中国文化话语表述当为“国乃江山主人的家”,它以宗庙形式对社稷主或地主进行确认,表达的是同一宗庙(祖宗)的人才是天下的主人,用今天的话说,才是统治阶级。第一位“天下宗”是黄帝,他是执有天下的土地与财富的“地主”。黄帝之黄原本是指土地颜色。《说文解字》:“黄,地之色也。从田从苂,苂亦声。苂,古文光。”许慎此解,并非一家之言。事实上,《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春秋纬》之《春秋考异邮》云:“……帝占曰:‘黄者,土精’”这里将“黄”理解为“土精”。王充《论衡·验符》进一步解释:“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11]844可见“黄”当作“地之色”解,轩辕之所以以黄为号,是因为他才是最大的“地主”。这个“地主”的经济学含义当是:取得统治权的部落或部落联合体以祖宗的名义对土地的占有。所有的人都要依赖这个“祖宗”,王权正是围绕这个祖宗而形成的天下治理模式,《管子》称为“官山海”,所谓“官山海”就是将大地分为五方。在这里所崇拜的“祖先”虽然已经超越了具体的个人,达到了族群的普遍性,但是总的来看,他并非一切人的祖先,因而与基督教所崇拜的抽象人是有很大区别的。
进入三代以来,祖宗不是天,但他可以坐在天之旁,其位与天齐,以致祖宗就是天。在甲骨文里,殷人所崇的帝既是宇宙的主宰,又是他们自己的高祖。因此,一切重大活动的向天报告,其实也是向祖宗汇报。《左传·桓公二年》说:“凡公行,告于宗庙……礼也。”[16]98“告于宗庙”意味着文化已经由对物的依赖关系转化为对祖宗的依赖关系。时王之政都要“告于宗庙”,因此“古代的宗庙不仅是统治者供奉其祖宗的地方,而且是重要的行政场所。诸如国之大事——隆重的祭祀(例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蒸尝禘于庙’),册命的典礼,每月的告朔听政,军事上的‘出师授兵’、‘献捷’、‘献俘’以及外交上的盟会等等,无不在宗庙里举行。因此,宗庙就成为古代政权的象征。‘失守宗庙’,实际上就是失去政权;灭人之国,往往‘毁其宗庙’”[24]171。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是以祖宗之名占有土地与支配财富分配的“宗庙国”。
四、结语
从中国古代事天、事地、尊先祖的祭礼中,我们可知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从逻辑路径上分析,应包括宇文国、社稷国与宗庙国三个阶段。“宇文国”属于“古文化”,以“天令”为据,强调国乃“天授”的“正义性原则”;“社稷国”属于“方国文化”,以自然与人格合一的土地为神,强调“天授”其国必以“江山”为基;“宗庙国”属于“王制文化”,以位与天齐的祖宗为尊,它将天授、社稷结合于“祖先”,于是有了王制。社稷国包含了宇文国的文化成就,宗庙国又是在宇文国、社稷国的文化成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华文明史一直以“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为礼之本,它将立国之道义渊源、经济基础以及“王制”紧紧结合起来,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国家。“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之大,于斯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