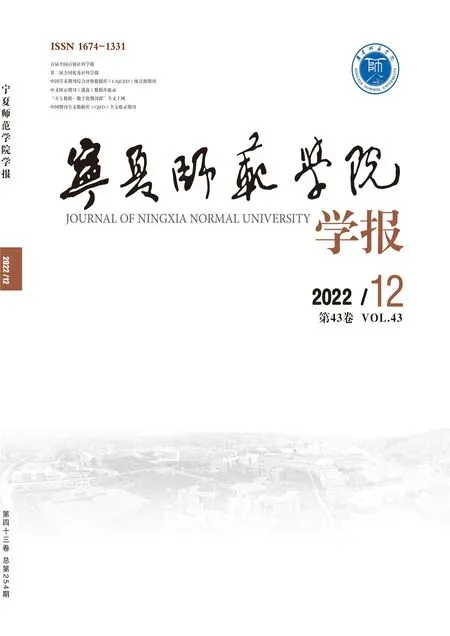马金莲小说中的生活物象
——以小说集《化骨绵掌》为例
杨彩荷
(宁夏大学 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物象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研究范畴。陆机在《文赋》中曾言:“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1],指出在文学创作中,需要选取恰当的客观物象,这样才能更好的表达文中之意。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从艺术构思的过程对物象和意象的关系进行了解释。意象是融入主体思想情感的物象,物象就是意象的物态化。蒋寅先生曾对物象作出过明确的界定:“语象是诗歌本文中提示和唤起具体心理表象的文字符号,是构成本文的基本素材。物象是语象的一种,特指由具体名物构成的语象。”[2]由此可见,物象是作者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选择的客观形象,从而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物象进入文学作品后,就不再是独立存在的物质,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小说中的物象带有作者独有的审美意识,是作者思想情绪的载体。小说集《化骨绵掌》中的物象选取显然具有极强的主体性,这是马金莲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选取的特殊物象,寄予着她的生活感悟和人生体验,隐含着作者记忆和情感的深度。马金莲小说中的生活物象别有意味地渗透在小说中,表达着个体的内心情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味,传达着复杂的人生意蕴。
一、人生岁月的纪念
物象是小说中的微量元素。马金莲在小说中通过对日常起居中常见物象的细致描写,以小见大,反映出人间烟火中的生活本质。人们每天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度过,渐渐对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都习以为常。但这些熟悉的事物却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承载着我们的生活过往,是人生岁月的纪念碑。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短暂的,岁月在无声无息中就会悄然逝去。当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事物离我们远去时,我们会忽然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甚至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马金莲在小说中敏锐地捕捉到现实生活中物的变迁,将这些物象融入小说,使其成为情感信物,表达自己对岁月流逝的无奈和对往昔岁月的留念。
马金莲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某种物象作为文章的题目,使其成为全文的文眼,小说便围绕着这个物象展开情节。《榆碑》围绕着老董等几位老人对老榆树的深切情感,再现了他们对往昔岁月的无限怀念。老榆树这个代表着过去时间的物象,成为这些老人内心情感的承载物。老董生活成长的地方,曾经是一片贫瘠的盐碱地。后来,随着新城区的改造,这里变成了房价昂贵的高档小区。由于乡亲们没有能力购买房子,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老董、老安等几位老人由于对这片土地的不舍,一直没有离开,但他们成为了外来者,只能以保安的身份留在该地,守护着自己曾经成长的村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昔日荒芜的盐碱地和大滩地早已消失不见,而老榆树是这个村庄消失后留下来的唯一物证。只有它还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始终坚守在原地。老榆树承载着大滩地上几辈人的回忆,见证着大滩地乡亲们的生活百态。“它不光是一棵树,它是大滩地的活历史。”[3]大滩地上的生活痕迹消失了,唯一屹立的只有老榆树。而如今开发商为了再起一栋楼,准备挪走这颗上百年的老树。老董为了保住老榆树,他向自己的孙子寻求帮助。通过他的努力,老榆树被挪的消息扩散到了全城,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下,老榆树保住了。但四个月后,老董发现老榆树枯萎了,后来他得知老榆树是被强硫酸腐蚀而死的。老榆树死后,老董心里空出了一个大窟窿。老榆树是大滩地的旧相识,它是老董的一个老前辈、故人和亲友。老榆树承载着大滩地最后的记忆,是大滩地人民生命历程的见证和记载,那些人的成长和记忆都留在了这里。然而,时间流逝,世事流转,老榆树消失了。老榆树成为了生活记忆的媒介,展现着大滩地乡亲们的悲欢苦乐。
《公交车》通过生活中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公交车这个物象,展示了苏苏十年人生岁月的流逝。马金莲试图通过这个生活中最常见的物象,去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重新体认。苏苏十年前刚进城的时候,她的小区门口只有5路公交车,她每天都乘坐5路公交车上下班,风雨无阻。如今她的小区门口有三个公交站点了,但她还是每天坚持去坐5路公交车。十年前的公交车非常简陋,空间小,也没有空调,尤其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公交车里挤满了人,车里的味道呛得人喘不过气。后来,随着全市大范围的整顿,政府增添了纯电动的绿色大公交,乘车环境舒适干净。然而,苏苏有点怀念以前乘坐公交车的日子,因为苏苏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度过了她的十年时光。苏苏在这十年里,生活得一地鸡毛,她有时候甚至都没有勇气回头去看以前的日子。然而,当苏苏回忆过往时,她甚至有点留念过去那段艰辛的时光。一年又一年,苏苏和那座小城一起经历着各种变化,也感受着时间的流逝。如今,苏苏要搬家了,离开那个她生活了十年的地方,也终于要告别长期挤公交车的生活了。但苏苏打算在离开之前再坐一次5路公交车,她想做个道别。她和往常一样穿着高跟鞋走在去往5路公交车站的路上,熟悉的节奏使她心里产生了酸楚。5路公交车的路线,她十年时间重复了上万次。在那十年时光里,苏苏厌烦那种琐碎平淡的生活,渴望结束那种日子。“当时总不是麻木就是觉得枯燥乏味,现在都变成了回忆和往事,回头看,不一样的滋味从岁月的底板下泛上来,酸,甜,苦,辣,都有。五味交织,把心泡在里头,慢慢腌制。原来那么普通的日子,真的成为过去以后,也会有如此不一样的味道。”[4]以前的日子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艰辛和无奈,但当这些成为过去时,又会依依不舍。苏苏是个念旧的人,她沉浸在以前的日子里,舍不得告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生终有一别。5路公交车见证着苏苏早出晚归的脚步,见证了她十年的岁月人生,它是苏苏的纪念碑。十年,说短也不短。这一别,算是苏苏对自己一个人生阶段的永别。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饮食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构成,它还包含着深层意蕴。当饮食进入文本中时,它就是作者味觉记忆的体现,成为作者表达自己情思的手段。马金莲的小说《蒜》通过腌蒜这个饮食物象,表达了老白对往昔岁月的怀念。《蒜》中的老黑老两口要去江苏给女儿带孩子,临走之前,他们把房子租了出去。老黑老婆把自己腌的两坛蒜,分别留给了租户小刘和老白,让他们等上半个月后再食用。老白没有等到半个月,就开始忍不住了。他打开坛子后,看到老黑老婆把蒜打理得非常精细。腌蒜更是五味俱全,他非常喜欢这种味道。这是小时候的味道,是妈妈的味道。老白小时候生活在乡村,家里的日子贫穷,为了调剂胃口,他的母亲经常给他做腌蒜吃,母亲腌出来的蒜具有别样的味道。老白从小吃着腌蒜长大成人,都没有吃厌。可是自从母亲去世后,他再也吃不到了。后来,他来到城市上学工作,渐渐地就完全忘了这个味道。老黑老婆做的腌蒜是老白曾经很熟悉的味道,他以为自己再也没机会吃到腌蒜了,而现在这坛腌蒜让他再次回想到了过去。老黑老婆做的腌蒜又重新唤起了他已经遗忘的味道和过往的回忆。腌蒜已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承载着老白对往昔的怀念和对母亲的想念。食物常与复杂的情感紧密相连,腌蒜的味道,就是人生岁月的味道,是情感的味道。
二、失意女性的挣扎
女性一直以来都是马金莲小说创作的重点描写对象。她在自己的小说中塑造了由乡村少女到进城的知识女性这样一个女性人物谱系。马金莲近年创作的小说,多写的是游弋于城镇之间的知识女性。小说集《化骨绵掌》就重点描写了城镇中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这些知识女性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独立的思想人格。然而,她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也面临着种种危机,生活处于两难的境地。马金莲着眼于身边之物,以其女性独有的视角和感受力,通过物象的描写极其巧妙地展现了这些女性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从更高的精神层面观照城市知识女性的精神状态与生存体验,把人物放置在城市文化的背景下,对其在现实人生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深层次挖掘,反映她们在城市空间下的挣扎和难于愈合的伤痛,使我们又可以发现其充满生活气息的物象里体现着一代正在逐渐苏醒的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
《化骨绵掌》中的苏昔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一天,她受邀准备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由于她上班时穿的衣服不大得体,下班后冒着大雪回了一趟家。回到家后,她首先是去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准备晚饭。这样她出去聚会,心里就不会有愧疚之感。一个女人结婚之后,她生活的所有重心开始转移到家庭上,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感受。苏昔做好饭后,告诉丈夫老王自己要出去聚会。因为苏昔很少在外面吃饭,老王便开始询问聚会的地点和同学。老王一般情况下不过问她去哪里,因为他们平时都清楚对方的行踪。婚姻生活在无形中让夫妻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两个人随时都要向对方汇报自己的事情,就这样他们各自都失去了独立的生活空间,两个人的生活捆绑在一起。当老王知道聚会的人全部是男性以后,他的态度开始变得冷淡。苏昔知道自己去不了。如果她去参加聚会,他们的日子就会产生隔阂。苏昔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为自己感到气愤,这些年她为了家庭,完全对生活妥协了,对自己越来越随意,自己的容颜在岁月的消磨中已经老去。镜子这个物象的使用不仅能够反映苏昔的心理活动,更能折射出人物的生活历程。苏昔最后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她看到自己的眼睛里煮着两条不愿赴死的鱼,“活鱼拍打着腹鳍和尾鳍,它不想就这么毙命,它渴望活下去。它渴望着。它渴望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渴望是这么强烈。却隐秘。藏在深处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到。”[5]在这一刻,苏昔对自己的婚姻生活动摇了,她开始经历着一场心灵的炼狱。她就像不愿赴死的鱼一样,不想再这么生活下去,内心深处开始有了一种强烈的渴望。自此之后,苏昔变得很恋家,老王说他这辈子娶到这样的老婆值了。老王的这句话反复了一年。这一年里,苏昔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她再也不愿意在婚姻的牢笼里失去自由,被别人束缚和捆绑,这表明苏昔的女性意识在不断觉醒。一年后的冬天,苏昔拿出了离婚协议书,对老王的唯一解释是“我是女人”。这句话看似很简单,但却柔中带刚,她是一个女性为自己的呐喊。苏昔被由婚姻编织的大网深深牵制着,在这段婚姻中,老王只想让苏昔成为一个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的妻子,从来没有真正在乎她的感受。如今,她亲手结束了这捆绑式的婚姻生活,重新去寻求自己向往的自由。
《听众》中的苏序是一个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知识女性。五年前,她被分进城镇中学教书,与这里的一个男人结了婚。五年后,他们开始相互厌烦,苏序最后以净身出户为代价,终于与男人离婚了,她也离职去县第一中学教书。离婚后的苏序开始沉默不语,不愿意与任何人交谈。而她的同事才子是一个啰嗦的人,他一直给苏序重复讲他婚姻的不幸。这引起了苏序的共鸣,成为唯一能认真倾听才子婚姻故事的听众。才子后来知道了苏序的不幸婚姻,开始给她介绍相亲对象。第一次的相亲对象之所以和苏序见面,竟然是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免费的家庭教师。第二个相亲对象是为了找一个能生育的女人,苏序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那次相亲失败后,苏序开始天天去鲜家汆面吃饭,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男人。苏序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男人是一个利用色相骗吃骗喝的人,他们长久不了,但她心甘情愿被骗下去,沉浸在这个虚假的梦里,不愿意醒来。当梦境消失的时候,她把自己弄的遍体鳞伤。后来,才子还是不断给苏序介绍相亲对象。谈论相亲对象成为他们之间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了。苏序放暑假时回了老家,开学后,她知道才子离婚了。又过了一周,她听说才子打算自杀。苏序去劝慰才子,才子才得以放弃轻生的念头。才子康复后,一直带着苏序送给他的羊绒带子。才子又开始给苏序介绍对象,最后都没有成功。一个月后,有人给才子介绍对象。相亲地点是女方定的,在鲜家氽面。他的相亲对象正好是苏序,他们同吃一碗面,两个人的脑袋被一根面条紧紧拴在一起。他们两个失意的人都知道对方曾经受过的伤害,彼此温暖着孤单的内心,在相处的过程中治愈着对方,各自给对方带来了温暖,不经意间两个人的心便开始紧紧依靠在一起。
《绝境》中的苏李遭遇了自己丈夫出轨的尴尬处境。马金莲通过建筑类物象宾馆来叙述整个故事,宾馆这个物象折射着苏李内心的绝望、无助与挣扎。苏李是一个性格很好的女人,与自己的婆婆小姑都相处得很融洽。而他的丈夫却恰好一直利用着她的大度。苏李其实早就知道张三福在外面有人了,但她不愿意揭开这个真相。因为张三福把每个月工资的一半都交给她,她可以自由支配,张家的一大家子人都对她不错,所以日子可以凑合过下去。苏李此时把婚姻当成了物质满足的工具,被婚姻紧紧束缚。后来,她的亲朋好友知道了这件事,她就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了,给亲朋好友一个交代。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她还想继续过现在的日子。苏李第一次去丈夫出轨的宾馆时,她半途而放弃了。尽管她一直以来都装作对这件事情无所谓,但当她真的站在宾馆门口时,她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她最后乘坐一辆私家车离开了。一个月后,苏李又出现在宾馆,但她又失败了,再次乘坐那辆私家车离开了。苏李后面又来了两次宾馆,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每一次她都会遇到这辆私家车,这辆私家车的男人每次都会默默陪伴着苏李。不久,她和张三福离婚了。离婚后,苏李和私家车男人结婚了,日子过得平平淡淡。苏李在宾馆拆迁时,最后一次去了宾馆,这时她的内心开始有点后悔,她在想如果自己当初去哭闹一场,结局会不会不一样。苏李具有女性的自省意识,反省着自己的婚姻悲剧。但她不知如何自处,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一个人咀嚼着其中的辛酸。最后,她又一次将自己困于婚姻生活的牢笼,独自愈合着苦涩的伤痕。
马金莲笔下的知识女性,通过读书进入城市生活,在她们的认知中,“进城意味着命运的转折和崭新的生活方式”[6]。这些女性努力追求经济独立,自主选择爱情和婚姻。但她们在现代化的城市里,生活也面临着种种困境。她们无法突破家庭的藩篱,受困于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围城”中。马金莲在小说中通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象,努力开掘出这些城市女性丰富的情感世界,窥探她们心灵深处所承受的痛苦。她们无法在婚姻中找到理解和慰藉,甚至迷失自我。但她们不断在自己的婚姻中抗争,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实现自我的救赎,深具女性意识。马金莲关注这些知识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对女性在城市中的两难境地予以怜悯和关怀,揭示出这些女性内心难以明状、隐秘忧思的精神状态。
三、城乡变迁的审视
马金莲近些年扩展了小说创作题材和叙事空间,逐渐走出了西海固扇子湾这一狭小地带。她把文学视角转向城乡变迁中的现实问题,开始关注现代化转型中城镇化对乡村的影响,以及反思城市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乡村的变革出现了各种问题,正如马金莲说的:“当下的乡村已经远远不是我们最初生长、生活、熟悉的那个乡村,社会裂变的速度和纵深度早就渗透和分解着乡村,不仅仅是表面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变化,还有纵深处的隐秘的变迁,包括世态、人心、乡村伦理、人情温度。”[7]现代化转型逐渐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恒定结构,迫使农民离开自己生活的土地,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挣扎在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但乡村的城市化转型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促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马金莲对于城市文明由以前的二元对立,开始转变为一种理性和辩证的创作姿态。
农村城镇化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结构,迫使乡村最后的坚守者也在逐渐消失。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所。面对城乡变迁,马金莲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剖析现实。《榆碑》再现了农民离开乡村之后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痼疾。老董生活的大滩地,如今变成了高档的太阳花园。可是曾经在大滩地生活的人们,只能以外来者的身份留恋着眼前的好景象。老董对自己的这种身份和生存处境感到焦虑和担忧,“留在太阳花园这些年,亲眼看着它变好,好的像梦里一样,可他从来都没有踏实过,他感觉自己的脚跟是软的,浮的,站着坐着睡着,都有一种不能和地面相接触的感觉。”[8]飞速发展的城市使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可是老董只能在城市生存压力的裹挟中渐渐被遗弃。老董在城市是一个没有家和归属感的人。而老榆树却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老董对此羡慕不已。对于老董们而言,老榆树是他们对自己故乡的情感寄托。但老榆树也躲不掉被搬迁的命运。老榆树最后被开发商浇注硫酸而死,老董等老年保安也被集体解雇,这预示着曾经的大滩地将彻底成为过去,有关它的遗迹也永远消失。正如马金莲所言:“变迁的车轮碾压而过,那些不能善终的村庄和庄稼地,把根系扎在泥土里的草和木,像文本中大滩地那些留守的旧人,终究都是尘埃。”[9]老榆树的命运和老董的处境折射了现在大多数人所面临的生存焦虑。老榆树是历史的承载体,最后却走向了死亡。老董他们是被时代抛弃的一群人,是城市边缘的打工者。因此,马金莲关注着城市生活中那些边缘人物的生存境遇与心理问题,“在急遽的变动、文明的交错以及偶然与必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被抛掷在现代性进程中的人们总会遭遇身与心、灵与肉的困局。”[10]农民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内心经历着复杂难言的心理波动,陷入精神困境中无法自拔,马金莲对这些渴求生活而不得的人满怀悲悯之心。
当今社会各种新媒体泛滥,它们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它们也以一股强大的力量吞噬着生存中的个体,导致人们被各种欲望和利益所束缚,最后产生了种种信任危机。马金莲在《众筹》里通过截取生活中常见的众筹链接这一生活物象,展现了一个普遍的有关医疗众筹的社会现象,那就是人们通过编造虚假的众筹信息博得大众的同情,从而获取捐款。主人公马圆每次看到众筹链接时,她都会捐几块钱,这可以使她心里感到踏实。一天,她的发小虎丽丽给她发来一个众筹链接,上面显示她的父亲需要十五万元做手术。马圆立马把链接分享到朋友圈和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还捐了五百元。而她的大哥告诉马圆,链接中的有些内容是虚假的,马圆当时没有多想。她一直关注着筹款进度,距离手术前一天,她又捐了五百。最后看到虎家提取了五万元左右的捐款,她的心终于踏实了。半年后,马圆发现虎家的众筹链接不见了,她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多彩。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一股被愚弄的感觉占据了马圆的心。我们的善良经常被一些贪婪的人利用,甚至连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不放过,这种利用让人无法容忍和原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荡然无存。马金莲对众筹这个事件进行层层剖析,逐渐露出现代生活中令人难堪的真相,由此揭示出现代性对传统精神的冲击与围困。在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的对比中,潜藏着马金莲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与失的衡量。进入现代社会,人们提高了生活质量,但人们的欲望也随之膨胀,道德底线崩塌,折射出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精神危机。
互联网技术在大众生活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媒介是把双刃剑,在给予人们便捷式生活体验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将人们裹挟进特定的空间中,最终导致人的某种异化。《良家妇女》中三床的小男孩不和任何人交流,总是拿着他奶奶的手机玩。苏于看到这种情况,向三床的老妇人劝谏,不要让孩子一直玩手机,要不然会对孩子带来一定的伤害。老妇人告诉苏于,这个孩子从小就是用手机哄大的,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这个孩子每天除了睡觉和吃饭,剩下的时间都在玩手机,对手机的依赖已达到了失控的地步。“如果一种文化只注意人的感官需要即文化的最表面层次的需要,那最终无疑会导致充裕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对立。”[11]这个小男孩每天的生活局限在手机虚构的狭小世界里,如果一直放任下去,他的生活恐怕就被手机弄得支离破碎。网络媒介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便捷,但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老奶奶告诉苏于,这个孩子是一个留守儿童,没有父母亲在身旁照顾。老奶奶年龄大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陪伴他。在孩子的成长中,父母的陪伴至关重要,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孩子从小缺少父母亲的呵护和教育,他们的成长是孤独和残缺的,这种成长中爱的缺失性体验甚至会给他们的一生和心理都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当今社会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的身体承担着重负,心灵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受到的是强烈的疏离感和孤独感。
马金莲在小说中通过老榆树这个代表着乡村传统文化和记忆的物象,揭示了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受到的冲击,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无限怀念之情。马金莲在常见的众筹事件中,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个体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欲望的膨胀,人们的道德体系开始瓦解,功利主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对立和紧张。马金莲洞悉人性中的各种虚伪、欺诈和冷漠,渴求人性精神家园的回归。现代媒体的发展具有许多弊端,马金莲通过手机这一物象,揭露了现代城市文明对个体的精神抑制。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牢牢地禁锢在手机这个狭小的虚幻空间里,个体的自由意志逐步被侵蚀。马金莲在努力寻求个人的精神出路。
四、结语
物象描写是文本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每个小说家描写的物象都有不同的意义,也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物象形成了不同小说家各具特色的创作基调。马金莲在小说集《化骨绵掌》中,选取了大量的生活物象,如汆面、宾馆、腌蒜、老榆树、众筹,等等,她用绵密的话语对这些生活中的常见之物进行白描式的细节描写,各种物象就如同在眼前那般真实,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生活气息的物象世界。“不管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还是叙事中透射出的虚构世界,都不可能没有物的存在,而物的世界是一个有待于解释,意义有待于现象的符号系统。”[12]对马金莲来说,小说中描写的各类生活物象并不是单纯的一种客观对应物,而是寄予着作者的深厚情感。她在小说集《化骨绵掌》中通过生活物象来叙述故事,这些物象寄托着某种叙事意图,也隐喻或暗示着某种情思,包含着丰富的人生意蕴。马金莲在小说《榆碑》《公交车》《蒜》中,通过老榆树、5路公交车、腌蒜这些物象表达自己对岁月流逝的无奈和对往昔岁月的不舍。这些物象见证着小说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和生活百态,是他们人生岁月的纪念碑。马金莲在小说《化骨绵掌》《听众》《绝境》中,借助物象展现了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状态。这些知识女性面对婚姻生活的不幸时,没有选择直面对抗的方式,而是避开对方的锋芒,用冷静温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温柔不意味着顺从,而是一种通透和选择。这份力量看似软弱,但这是一种坚定和理智的柔,隐含着巨大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潜藏在女性骨子里的那股韧劲。马金莲还在《榆碑》《众筹》《良家妇女》中以一种客观的姿态正面审视了城乡变迁的现实问题。她反思了物质消费时代中,人们随着欲望的放纵,渐渐沦陷在物质生活的旋涡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逐渐产生信任危机。现代多媒体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异化,人们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中被钳制。马金莲在小说集《化骨绵掌》中,对日常生活物象进行描写时,没有着眼于物象的外在形式,而是从多角度去把握物象蕴含的丰富内涵,挖掘和探索物象的意义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