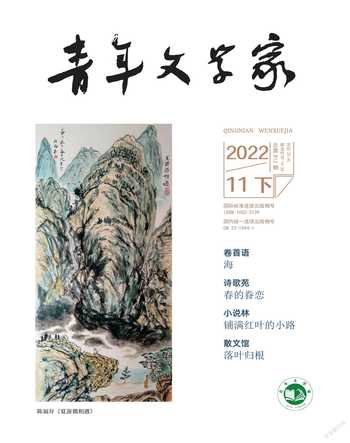论唐代茶诗里的“情”及其审美表达
周曦
烹茶赋诗,发轫于盛唐,多由独居或隐居的士、僧、道所作,风格飘逸脱俗或雅致狂放。中晚唐茶诗水准日臻炉火纯青,诗人独特的艺术审美将茶叶的自然属性化入诗句,用品鉴手法将茶叶烹煮过程中的态、色、香、味刻画得淋漓尽致,茶诗题材在融入更多元素、维度时,也给后世烹煮技艺树立了典范。
一、茶诗精髓在于“情”
(一)自然之情
具体而言,茶道包括场所选择、器具准备、粗茶精制、火候把控、饮前赏茶、饮后茶功。
为酝酿诗兴,择址有讲究。“静得尘埃外,茶芳小华山。此亭真寂寞,世路少人闲。”(朱景玄《茶亭》)选寂静山亭煮茶,于静谧中独饮,更助诗兴。“铁柱东湖岸,寺高人亦闲。往年曾每日,来此看西山。竹径青苔合,茶轩白鸟还。而今在天末,欲去已衰颜。”(齐己《怀东湖寺》)依湖寺院,竹林群立,小径满苔,于此幽深处入轩阁煮茶,又睹白鸟归巢,怀念彼时光景怎能不令诗人心生感慨?“石垆金鼎红蕖嫩,香阁茶棚绿巘齐。坞烧崩腾奔涧鼠,岩花狼藉斗山鸡。蒙庄环外知音少,阮籍途穷旨趣低。应有世人来觅我,水重山叠几层迷。”(贯休《山居寺·石壚金鼎红蕖嫩》)“棚,一曰栈,以木构于焙上,编木两层,高一尺,以焙茶也。茶之半干,升下棚;全干,升上棚。”(陆羽《茶经》)诗人隐于山林木阁,独自焙茶、烹煮、品饮,馝馞满溢,野畜嬉斗,其中旨趣即使阮籍也不可媲及,矧此恣意狂汲、隐逸之趣,无须他人打扰。
为显尽雅致,选器具有讲究。“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锦水有鲜色,蜀山饶芳丛。云根才翦绿,印缝已霏红。曾向贵人得,最将诗叟同。幸为乞寄来,救此病(一作‘穷)劣躬。”(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越瓯乃唐代茶具中的名器,蒙茗乃唐代名茶,二者搭配方可物尽其用。越瓯盛蒙茗,犹如锦水焕发鲜色,蜀山环绕芳丛,面对如此礼赞,自是盼其病瘳,不可吝于施赠。饮茶重在饮者心境,而非器具本身,品茶亦非辄止于味,而是探寻一种符合自然之道的叶外之味,品茶叶诗化的精神之道。皮日休曾言:“螔蝓将入甑,蟛蜞已临鍑……用以阅幽奇,岂能资口腹。”“鍑,以生铁为之……内摸土而外摸沙。土滑于内,易其摩涤;沙涩于外,吸其炎焰……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陆羽《茶经》)铁鍑胜过瓷鍑、石鍑,皮日休深得茶经精髓,懂物之用在于其质而非其形,凡入口之物,皆为形,形而上的精神体验才为质。
为使茶味正宗,制茶过程有讲究。“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牙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陆羽《茶经》)从采摘到封藏,到取出烹煮前,要经过七道工序。中唐始,每一道工序皆可化入茶诗:“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皎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乃清晨采茶;“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齐己《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乃破晓蒸茶;“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郑邀《茶诗》),乃夜间捣茶;“金饼拍成和雨露,玉尘煎出照烟霞”(李郢《酬友人春暮寄枳花茶》),乃暮春拍茶;“野碓舂粳滑,山厨焙茗香”(许浑《村舍》),乃山中焙茶;“天柱香芽露香发,烂研瑟瑟穿荻篾”(秦韬玉《采茶歌》),乃用荻篾穿茶;“药转红金鼎,茶开紫阁封”(贯休《赠造微禅师院》),乃封茶于阁。
为使茶味出,须把控好火候。“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皎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文火即小火,小火烹茶,香味更甚。“山谣纵高下,火候还文武”(陆龟蒙《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焙》),“武”指大火,焙茶须调节火候,先小火后大火,方能出味。
唐人饮茶,先赏其状貌、尝其味,后体其功用、得其神,所求匪啻安舒。所谓“荡昏寐,饮之以茶”“其隽永补所阙人”是也。赏、饮、体、品,皆于诗中可见:“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一作‘熳)缃花啜又(一作‘久)生”(皎然《饮茶歌送郑容》),乃啜前赏茶之烂漫;“对雨思君子,尝茶近竹幽”(贾岛《雨中怀友人》),惄焉如捣,乃饮茶尝其寒凉,拟以竹幽之韵;“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白居易《赠东邻王十三》),乃以茶功破酒倦;“幽谷生灵草,堪为入道媒”(无住《茶偈》),乃指茶可成为悟道的物质载体。
唐代茶诗体现的烹煮品饮艺术,是茶诗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篇章。诗人以饮者自居,将自身的视、听、嗅、味、触融入自然,冀求获得形而上的美学体验,并以诗铸就这种美的躯体,从而彪炳后世。
(二)名泉吟咏
中晚唐茶诗存在一类特殊题材,即对烹煮水质进行吟咏。“啜茶思好水,对月数诸峰”(常达《山居八咏》),首涉煮茶水质;李白的“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将泉水与茶叶生长环境连缀,茶诗中正式出现咏泉题材,兴起咏泉热。至中唐,茶诗始将泉水与茶叶注入人生哲思,“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以茶喻尘世,从容处之。
陆羽从盛唐咏泉诗中获得启示,将水质归为衡量能否煮出上等茶的核心因素:“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濑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效以前,或潜龙蓄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茶经》)并赋诗说:“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惟羡西江水,曾向金陵城下来。”(《歌》)水为上,器为下,极大影响了后世茶诗,使泉水吟咏这一类题材从烹煮艺术中分离,单独成类。
皎然与陆羽为挚友,《茶经》付梓,皎然功不可没。皎然将修道寄于泉水涤茗的自然,进而以之悟道:“望远涉寒水,怀人在幽境。为高皎皎姿,及爱苍苍岭。果见栖禅子,潺湲灌真顶。积疑一念破,澄息万缘静。世事花上尘,惠心空中境。清闲诱我性,遂使肠(一作‘烦)虑屏。许共林客游,欲从山王(一作‘主)请。木栖无名树,水汲忘机井。持此一日高,未肯谢箕颍。夕霁山态好,空月生俄顷。识妙聆细泉,悟深涤清茗。此心谁得失,笑向西林永。”(皎然《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师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皎然体悟深刻,观照视角超越物质,转向茶叶和泉水的内在,从中寻求顿悟,其品饮,从肉体感官上升到精神层面。其后,凡僧、道咏茶,多注入一己思悟,可以说,皎然凭一己之力将哲思茶诗引入中晚唐诗坛。唐代诗人煮茶,择址从“静”,所谓“参禅”,为“静虑”“思维修习”,“静”躯体与心,动神思,解沉菀,逾尘俗叨扰,臻至道境。诗人专注烹煮细节,内省自视,达到动静结合,本质属佛教静虑和思维修习,故佛教元素能与唐代茶诗完美融合,有其内在动因。
二、茶“情”与審美表达
唐代茶诗吟赞茶之美,描绘茶事活动,描绘咏赞茶的色、香、味、功效,诗人爱茶之心溢于言表。凡所述,刻画了唐代诗人的饮茶日常,凸显别具一格的审美理想—闲精雅逸、节俭清廉。
(一)虚实相韵之美
唐人通过茶事活动形成别具一格的审美标准,茶诗乃诗人审美过程诗化后的结晶。色彩之多姿、芳香之灵动、味觉之享受,于诗人笔下化作茶烟、茶色、茶香、茶波、茶味、茶器、茶具等一系列虚实相交的触感,殷勤礼赞,向往美好风雅,尽显生活情趣。
1.茶烟
唐人煮茶,享受茶烟般的缥缈宁谧。牟融:“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游报本寺》)烟影相交,禅榻对竹影,袅袅中烘托诗人候茶凝思的幽静氛围。“左右捣凝膏,朝昏布烟缕”(《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焙》),以凝膏喻茶,从捣到生火,乡野冉冉升起一缕茶烟,烟火味十足。
2.茶色
唐人赏茶,以色泽自然为佳。“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岑参《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岚飞黏似雾,茶好碧于苔”(贯休《题灵溪畅公墅》),“绿嫩难盈笼,清和易晚天”(齐己《谢中上人寄茶》),此三句乃言清嫩之自然。“茶影中残月,松声里落泉”(齐己《寄江西幕中孙鲂员外》),此色深之自然,复归清和自然状貌,无为物役,为宁静致远的精髓。茶色可浸饮茶器具,使茶味从触觉层面上升至精神层面,“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徐寅《尚书惠蜡面茶》),烟色相融,视觉意象更进一层,诗化更甚。
3.茶香
唐人品茶,重香味清淡溢远。“花醥(一作‘醴)和松屑,茶香透竹丛”(王维《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以虚写实,反以竹丛浓密衬出茶香馝馞,实为清玄意境。“清泠真人待子元,贮此芳香思何极”(皎然《顾渚行寄裴方舟》),茶香一如茶色,亦可沾惹饮茶器具,互促溢彩,更助诗兴—“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薛能《留题》)是也。
4.茶水
唐人煮茶,以水质近冰至洁为上。“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糜”(白居易《晚起》),冬茶融雪而煮,别有一番情志;“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白居易《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水至冰清,心愈洁净,所饮与所吟皆愈淡雅柔和,消冲了俗尘戾气。水质清澈愈近自然者更易出茶味—“涧(一作‘石,一作‘谷)水生茶味,松风灭扇声”(周贺《早秋过郭涯书堂(一作“郭劲书斋”)》)是也。
5.茶味
唐人尝茶,味因心境不同而异。“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香洁将何比,从来味不同”(姚合《病中辱谏议惠甘菊药苗,因以诗赠》),“种菊心相似,尝茶味不同”(齐己《又寄彭泽昼公》),此三句乃言尝茶在心境,往往静者能近其神得其韵;反之,得其神韵者,则神超形越,更促内心情至—“顾渚一瓯春有味,中林话旧亦潸然”(郑谷 《宜春再访芳公言公幽斋写怀叙事,因赋长言》)是也。
6.茶器茶具
唐人茶事注重形式,雅致初始在于器具,器具素雅为上,代表诗人心境所向。“松龛藏药裹,石唇安茶臼”(王维《酬黎居士淅川作》),“土甑封茶叶,山杯锁竹根”(李贺《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皆素雅不染铜臭。茶具适恰,亦助诗兴—“蜀纸麝煤沾(一作‘添)笔兴(一作‘媚),越瓯犀液发茶香”(韩偓《横塘》)是也。
(二)饮茶功效之美
茶之效用,由外而内,由身理至精神,素来为唐代文士所追求,稍不注意,或有患茶厄之险。
1.醒神净心
茶能止渴提神。“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饮茶除假寐,闻磬释尘蒙”(刘得仁《宿普济寺》),不止味蕾享受,情操亦是。“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韦应物《喜园中茶生》),“幽室养虚白,香茶陶性灵”(朱湾《赠饶州韦之晋别驾》),“尝频异茗尘心净,议罢名山竹影移”(黄滔《宿李少府园林》),此三句乃言饮茶对心境的善利,可逐散卑污淟涊。
2.茶疾茶厄
过度饮茶虽招茶疾,但亦能让诗人迸发诗情。“君若随我行,必有煎茶厄”(卢仝《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客谢竹》),“茶风无奈笔,酒秃不胜簪”(张祜《句》),“舍深原草合,茶疾竹薪(一作‘枝)干”(周贺《题昼公院》),万事过犹不及,饮茶如此,人生亦如此,疾厄却又可使诗人反思—“借书消茗困,索句写梅真”(唐彦谦《逢韩喜》),“病多疑厄重,语切见心真”(吴融《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是也。
(三)茶偈情思之美
焙茶精髓,在于情思,念浓则味至,情深则劳苦冲淡。“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见说焙前人,时时炙花脯”(陆龟蒙《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焙》),“生于顾渚山,老在漫石坞”(皮日休《茶中杂咏·茶人》),皆礼赞茶人之语,茶人焙茶之苦,当以诗歌咏,将普通品饮上升到艺术品饮—流连茶山中,所睹皆夭嫭。从以“茶”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离不开诗人精神情感的共性认同,让审美能力具体化。
初唐诗人品茶,尚未上升至审美层面。诸如“茶壶团素月”(陈元光《观雪篇》)、“啜茶思好水”(常达《山居八咏》)等句,仅涉茶之形,不辨水质品级,不涉茶精雅逸、节俭清廉的精神审美范畴。彼时茶非吟咏重点,至盛中方得捩转,而茶人劳苦迄被遮掩。
既有茶偈,必有茶思。茶饮成为解思途径。“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孟浩然《清明即事》),“对雨思君子,尝茶近竹幽”(贾岛《雨中怀友人》),“蒙顶茶畦千点露……杜甫台荒绝旧邻”(郑谷《蜀中三首》),皆饮茶而生思,怀旧想念凭吊,融入情思审美,动人心扉;或以茶换书画,代酒行一瓻之礼—“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是也。
中晚唐时局动荡,藩镇相干犯,同侪互倾轧,诗人们突破“一己之思”,将自身人生境遇及对世态人情的关注注入茶诗。郑谷曾云:“茶香紫笋露……政成寻往事,辍棹问渔翁。”(《寄献湖州从叔员外》)庙堂宦海沉浮,李唐内忧外患,人间动荡不息。对现实和人生,晚唐文人多身不由己,于王朝覆灭中胪欢。出入间岁月飘忽,偊旅蹒跚而又才气勃窣,转眼沧海桑田,迭见挫败壮志难酬,几经罹厄而抆泪蹈道,将殷切悲悯投入社会现实,唯诗抒万千喟叹。眙此人世俇攘,追念昔游,伤彼哀己,如饮陈茶,从苦荼到甘甜,将悲苦挫磨、轩豁旷达融入才情,澹辞慷慨,沈结含凄,独守仄陋,渗透灵魂燃烧成诗,且各体皆工,尽言无隐,不顾身害,毫无保留地献世、绽放,以自身曲蘖,酿人世芬芳。
唐代文人以茶诗为媒介,对友人、亲人、故乡摅吐思情,深入内心茶诗之美,实乃诗人心灵之美。品茶吟茶与诗人牵絷固深,这一表达过程,渗透着诗人们的审美,彰显的是诗人对自我理想人格的坚定追求。于后世,这是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