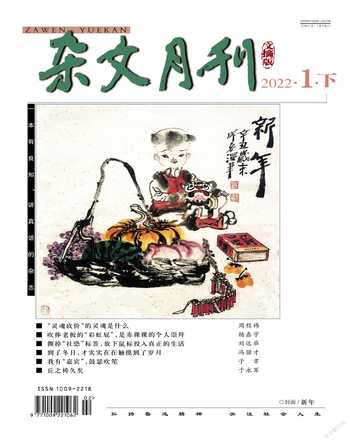多数与少数
王俊良
贞观之初,唐太宗面临“震耀威武,征讨四夷”与“偃武修文,中国既安”两种选择。前者以封德彝为主,代表大多数;后者仅魏征一人,占绝对少数。唐太宗纳魏征之谏,遂有“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局面。
魏征之谏,之所以可贵,不在最终证实结果的正确,而在决策之初。朝堂之上,大多数力挺“宜将剩勇追穷寇”,唐太宗亦纠结“不可沽名学霸王”。《资治通鉴》载,魏征谏言,与其说是力谏,毋宁说是响雷。此时说出来,就算你心在朝廷,也显得特别扎心!
尤其是,在魏征已省察到,唐太宗倾向“震耀威武,征讨四夷”,仍不唯上意所变,改变自己;更不因与大多数人意见相左,选择从众。此时,魏征面临说与不说,说了之后对方听与不听多种变数。魏征仍力主“偃武修文”达“四夷自服”之谏,不仅需要大智,更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
凡谏必勇。比干之谏于纣王,勇到剖心以证其忠;伍子胥之谏于夫差,勇到被诬里通外国毙命;海刚峰抬棺以谏,意在清誉,勇也欺世。
然而,谏的目的,是让对方纳谏;勇的前提,是谏之智。在这方面,宋代王素谏“色”,不仅见其勇,更见其智。想想看,谁敢跟皇帝叫板,说你找女人不对,还让皇帝心服口服?大多数人会选择只举手,视担这种风险的少数人,为实实在在的傻瓜。
《宋史》载,近臣王德用,给宋仁宗献二美女,王素谏阻。问题来了,朝堂之上,谁都知道这件事。可是,谁都可以装作没看见,没听见。谁都不提出不同意见。很明显,大多数默认了。只王素一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面对这种情况,宋仁宗找到王素,说“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意思是,我和你的关系,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跟别人不一样。况且,“德用实进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
无奈之下,宋仁宗将二女子已“事朕左右”,生米煮成了熟饭,这种非常私密的话题,也堂皇摆在了桌面上。这在讲究妇德的时代,人们尚无法冲破一女不嫁二夫的观念。别说皇亲贵戚,即使升斗小民,也笃信“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亲”理念。何况,还要顾及皇家颜面。
可以肯定地说,王德用所“进”之女,应该颇得仁宗欢心。此时,王素之谏,就颇见功力。因为,有勇无谋则败;有谋无勇则露。无论哪一种结果,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敢于甘当少数,而不去随波逐流,充当大多数中平庸一员,在王素是摸准了宋仁宗的脉。
纳之,有溺爱之嫌;退之,尤显仁君之明。溺乃奢,奢即糜。爱惜羽毛的宋仁宗,岂以女色害誉?由是,王素之谏,看上去是夺君所爱;实际上,谏“色”是假,凸显仁君风范是真。
原因在于,宋仁宗坐拥“三宫六院”,并不违规;近臣进美女“事朕左右”,也在祖制之内。宋仁宗不等王素再举女祸误国典型,主动“帝动容,立命遣二女出”,成就王素谏“色”传奇。茹太素步王素后尘,轻信朱元璋“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的话,直陈时弊,“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
结果,气得朱元璋“召太素面诘,杖于朝”。就是说,在朝堂之上,打了茹太素的屁股!《明史》将茹太素“杖于朝”,归“陈事务累万言”,实风马牛不相及。
长于制造“少数”震慑“多数”的李世民,担心“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上当者“上欲杀之”。裴矩力谏,“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既与圣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相违,亦与圣上“以至诚治天下”相悖。
裴矩曾为隋炀帝念过不少喜歌。如今,以一人对满朝文武,绝对少数对多数。司马光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以少数之北辙,收多数之南辕。“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诤”。
摘自《义乌商报》2021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