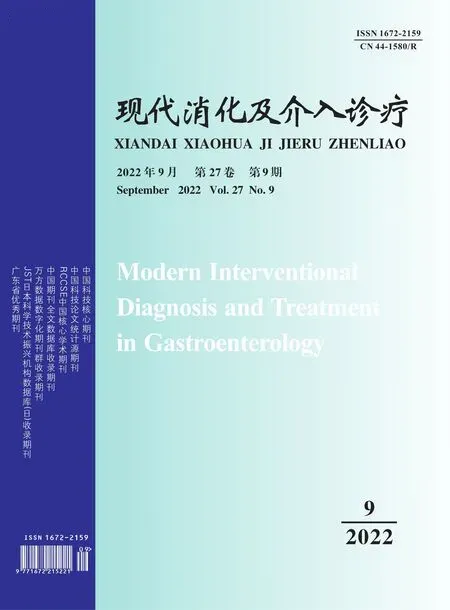晚期胃癌临床免疫治疗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究现状
陈玉华, 刘敏, 李强, 陈兆峰, 郑亚, 周永宁
【提要】 胃癌(GC)被认为是全球第三大死因和第五大常见癌症,传统的治疗方法有外科手术治疗、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近年来,免疫治疗有希望成为一种新的突破性的治疗方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方面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改善了包括晚期胃癌在内的多种癌症的总生存率及生存期限,此外,与靶向疗法等相结合的治疗方式有可能促使免疫治疗成为一线治疗方案,在本综述中,我们旨在探索不同免疫疗法治疗GC的进展以及迄今为止报告的临床结局。
胃癌(gastric cancer,GC)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发病率不断升高的恶性肿瘤,东亚地区的胃癌发病率最高,胃癌是我国第三大常见恶性肿瘤,我国胃癌死亡人数达到37万人,占全世界胃癌死亡人数的近一半[1]。
对于早期胃癌,确诊后及时行根治性手术可有效控制病情,甚至治愈。在这个阶段,内镜黏膜切除术(EMR)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是首选方法,其次是腹腔镜和传统的开放手术。但是由于本病起病隐匿,进展迅速,大多患者在首诊时已超过早期阶段,即使采用围手术期和辅助放化疗,Ⅱ期以上的患者5年生存率也急剧下降,由Ⅲa期的61%~63%下降到Ⅲc期的30%~35%[2]。晚期胃癌的常规治疗方法是化疗,常用的化疗药物有:氟尿嘧啶(5-Fu)/卡培他滨、紫杉烷类(紫杉醇或多西他赛)、铂类或是这些化疗药物的组合。传统的临床治疗效果很有限,进展期胃癌的中位生存时间(median overall survival,mOS)只有约8个月[3]。后来,面向胃癌患者的靶向药物问世,包括针对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肿瘤的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以及用于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的雷莫芦单抗(ramucirumab)。虽然化疗和靶向治疗提高了临床疗效,但由于化疗药物的毒性、筛选靶向治疗药物适宜人群以及对药物的耐药性的增长,导致胃癌患者的预后并无明显改善。目前氟嘧啶和铂类化疗联合方案(对于HER-2阳性病例使用曲妥珠单抗)为一线治疗,联合或不联合雷莫芦单抗作为二线药物是晚期胃癌的标准治疗方案,但预后仍然较差,中位生存期约为1年[4]。
免疫治疗药物的出现和进展为胃癌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获益,并且日益挑战化疗和靶向药物的治疗模式。这些突破为免疫治疗铺平了道路,特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最近,用单克隆抗体阻断免疫检查点分子治疗恶性肿瘤的策略已经被证实是有用的,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属于CD28家族的蛋白质,是一种在活化T细胞表面表达的负性共刺激受体。PD-1及其配体PD-L1/PD-L2在肿瘤细胞中的结合可以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反应,从而导致肿瘤细胞逃离免疫监视,因此阻断这种作用即可恢复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5]。在进展期胃癌(advanced gastric cancer,AGC)中,那武利尤单抗(nivolumab)作为一种针对PD-1的全人源免疫球蛋白单克隆抗体,已经在日本被批准为AGC的治疗方法[6]。临床试验多使用免疫肿瘤学单一疗法或联合免疫化疗来改善胃癌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和客观反应率。本文将讨论胃癌免疫疗法的现状,包括关键的临床试验以及未来展望。根据初步证据,我们相信免疫疗法可以在胃癌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积极影响,并改善胃癌亚组患者的预后。
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肿瘤细胞通过抗原缺失及抗原调变、肿瘤细胞的“漏逸”、MHC-I类分子表达低下、肿瘤细胞导致的免疫抑制、缺乏共刺激信号及肿瘤细胞抗凋亡等机制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其中,通过免疫抑制检查点介导的共抑制信号通路在肿瘤的免疫抑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化死亡配体-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是两个可靶向免疫检查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被开发用于阻断配体和检查点受体的结合,并重新激活人体细胞免疫应答。
1.1 PD-1/PD-L1抑制剂
PD-1是一种负性共刺激免疫分子,在T细胞、B细胞和骨髓细胞表面以单体形式表达。PD-L1是PD-1的配体,在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 APC)和多种肿瘤细胞上都有表达。它结合PD-1激活免疫抑制信号通路,导致T细胞功能受到抑制,介导肿瘤免疫逃逸[7]。因此,PD-1/PD-L1抑制剂可以通过阻断PD-1/PD-L1相互作用,增强对肿瘤的免疫应答。不仅限于胃癌,PD-1还是多种恶性肿瘤的潜在靶点,并且正在开发靶向药物,其中一些已经获得FDA批准,例如: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阿替利珠单抗(atezolizumab),那武利尤单抗(nivolumab)。派姆单抗已被批准用于治疗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8]。在一项全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3期试验CheckMate577中,在接受那武利尤单抗治疗的532例患者当中,中位无病生存期为22.4个月(95%CI16.6~34.0),而接受安慰剂的262例患者为11.0个月(95%CI8.3~14.3),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比为0.69(96.4%CI0.56~0.86;P<0.001),由于与活性药物或安慰剂相关的不良事件,那武利尤单抗组9%的患者和安慰剂组3%的患者终止了试验方案。在接受新辅助放化疗的食管或胃食管接头癌患者中,接受纳武单抗辅助治疗的患者的无病生存期明显长于接受安慰剂的患者[9]。2017年,另一项关于纳武单抗(ATTRACTION-2)的Ⅲ期试验显示,与安慰剂相比,作为AGC患者的三线或后期治疗,OS有所改善(5.26月vs4.14月;HR=0.63;P<0.0001),与那武利尤单抗的1年期,2年期和3年期OS率(27.3%,10.6%和5.6%)高于安慰剂(11.6%,3.2%和1.9%)。与安慰剂相比,那武利尤单抗也与PFS(1.61月vs1.45月;HR=0.60;P<0.0001),ORR(11.2%vs0%;P<0.0001),疾病控制率(40.3%vs25%;P=0.0036) 的改善有关。43%的那武利尤单抗患者报告了各个级别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eatment-related-adverse-events,TRAEs)。归因于研究治疗的死亡发生在1%的那武利尤单抗患者(急性肝炎,心脏骤停,劳力性呼吸困难和肺炎)中。大多数患者在开始使用那武利尤单抗后3个月内经历了第一次TRAEs[10]。
一项Ⅱ期临床试验(KENOTE-059)的队列评估了派姆单抗作为AGC患者三线或后期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全人群ORR为11.6%(95%CI8.0~16.1),此研究促使FDA批准派姆单抗用于PD-L1阳性AGC作为伴随诊断测定。mPFS为2.0个月(95%CI2.0~2.1),6个月PFS率为14.1%(95%CI10.1~19.7)。mOS为5.6个月(95%CI4.3~6.9),6个月OS率为46.5%(95%CI40.2~52.6)。KEYNOTE-059中派姆单抗的安全性与POTION-2中的那武利尤单抗相当,在60%的患者中观察到各级别的TRAEs,18%的患者具有3级或更严重的TRAEs[11]。而遗憾的是,一项关于派姆单抗作为二线治疗(KENOTE-061)的Ⅲ期试验中,在与紫杉醇和PD-L1 CPS≥1的AGC患者中的比较中,派姆单抗没有显著延长mOS(9.1月vs8.3月;HR=0.82)[12]。
阿替利珠单抗(avelumab)是一种针对PD-L1的人IgG1单克隆抗体(JAVELIN 300),与研究人员选择的化疗(如紫杉醇或伊立替康)作为AGC患者的三线治疗相比,一项全球Ⅲ期试验未能显示出生存获益,OS(4.6月vs5.0月;HR=1.1;P=0.81)。其临床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临床试验验证[13]。
此外,卡瑞利珠单抗(camrelizumab)于2019年5月29日在中国推出,是一种人源化抗程序化细胞死亡-1(PD-1)抗体。它用于治疗复杂或难治性经典霍奇金淋巴瘤,至少采用二线化疗。2020年3月4日,卡瑞利珠单抗在中国被批准为治疗晚期肝细胞肝癌的二线药物。目前,卡瑞利珠单抗正在对肝癌、胃癌、食道癌、肺癌等晚期实体瘤进行临床研究,均已显示出临床疗效[14]。
1.2 Anti-CTLA-4抗原
PD-1阻断的临床获益可以通过与CTLA-4抑制联合使用来改善。CTLA-4与抗原提呈细胞表面的B7结合,并阻止其与CD4+T细胞上的共刺激CD28受体结合。因此,CTLA-4剥夺了T细胞CD28的共刺激信号,削弱其杀死癌细胞的能力。Anti-CTLA-4抗体特异性地与CTLA-4结合,并从抑制中释放T细胞。CTLA-4阳性与PD-L1表达和高肿瘤浸润CD8+T细胞相关。因此,CTLA-4和PD-L1的阳性率是与GC患者生存率提高相关的独立因素。目前主要的抗CTLA-4抗体包括伊匹单抗(ipilimumab)和曲美木单抗(tremelimumab)。
在一项Ⅰ/Ⅱ期临床研究(CheckMate-032)中,伊匹单抗单药治疗(3 mg/kg)晚期胃癌患者的ORR为14%[15]。可惜的是,在Ⅱ期临床试验(NCT01585987)中,伊匹单抗仅作为一线化疗后的维持疗法,对晚期GC/GEJC患者并没有显著的生存益处。这表明未来需要生物标志物等指标来确定哪些患者可以从伊匹单抗中受益。
目前又发现一种单价双特异性抗体,可抑制PD-1途径,并提供调节的CTLA-4抑制,有利于对PD-1阳性T细胞的增强阻断。MEDI5752代表了一种新型免疫疗法,旨在将CTLA-4抑制引导至PD-1阳性T细胞,具有分化活性的潜力,这种分子代表了癌症免疫疗法的合理设计又向前迈出新的一步[16]。本文所涉及到的有免疫抑制剂参与的胃癌各项临床试验见表1。

表1 参与胃癌治疗临床试验的免疫抑制剂
2 免疫治疗结合其他胃癌治疗方式
2.1 免疫治疗结合化疗
为了评估胃、胃食管连接和食管腺癌中基于程序性细胞死亡PD-1抑制剂的疗法。我们报告了那武利尤单抗加化疗与单独化疗的初步结果。在多中心、随机、开放标签的3期试验(CheckMate649)中,患者通过交互式网络反应技术(6个区块大小)随机分配(1∶1∶1)到那武利尤单抗(360 mg每3周或240 mg每2周)加化疗(卡培他滨和奥沙利铂每3周或亚叶酸钙,氟尿嘧啶和奥沙利铂每2周),那武利尤单抗加伊匹单抗,或单独化疗。在评估合格的2 687名患者中,我们同时随机分配了1 581名患者接受治疗(那武利尤单抗加化疗[n=789,50%]或单独化疗[n=792,50%])。那武利尤单抗加化疗的OS中位随访时间为13.1个月(IQR 6.7~19.1),单独化疗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1.1个月(IQR 5.8~16.1)。与PD-L1 CPS为5次或以上(最低随访12.1个月)的患者相比,那武利尤单抗加化疗可显著改善OS(HR=0.71; [98.4%CI0.59~0.86];P<0.0001)和PFS(HR=0.68;[98%CI0.56~0.81];P<0.0001)。那武利尤单抗是第一种在既往未经治疗的晚期胃癌、胃食管连接处或食管腺癌患者中,联合化疗与单独化疗相比,表现出优越的OS、PFS益处和可接受的安全性的PD-1抑制剂。那武利尤单抗加化疗代表了这些患者一线治疗的新标准[17]。2021年中国胃癌诊疗临床指南中推荐,对于PD-L1 CPS≥5患者,推荐化疗(FOLFOX/XELOX)联合那武利尤单抗(证据Ia),对于PD-L1 CPS≥1患者,可推荐彭布珠单抗单药治疗[18]。
最近,报告了一项Ⅲ期研究(KEYNOTE-062)的结果,该研究比较了PD-L1 CPS≥1和CPS ≥10 AGC患者的一线派姆单抗单药治疗或派姆单抗加化疗与化疗的疗效。在CPS≥1患者中,派姆单抗不劣于OS化疗(中位10.6月vs11.1月;HR=0.91; 99.2%CI0.69~1.18),与化疗相比,mPFS相对较短(2.0月vs6.4月)且ORR较低(15%vs37%)。OS曲线显示出化疗的早期有利趋势。同时,在长期随访中,支持派姆单抗的分离持续,与CPS≥1患者的KEYNOTE-061中的12和24个月OS率相似,分别为46.9%和26.5%,而化疗为45.6%和19.2%。与化疗相比,派姆单抗患者PFS/ORR的差异与长期OS获益之间的差异可部分解释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增强对后续化疗的抗肿瘤反应[19]。
在胃癌中,Ⅲ期试验WATCHION-5(NCT03006705)正在进行中,以研究标准辅助化疗与S-1或卡培他滨加奥沙利铂联合那武利尤单抗治疗D2或更广泛淋巴结切除术后病理性Ⅲ期胃癌(包括食管胃连接癌)患者[20]。
2.2 免疫治疗结合靶向治疗
免疫联合靶向治疗是目前多种肿瘤的研究热点。对于晚期胃癌,抗HER-2单克隆抗体和VEGF/VEGFR抑制剂是联合免疫治疗的两种主要选择。
2.2.1 结合anti-HER-2治疗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是一种I型跨膜185 kDa蛋白。HER-2在多种正常组织类型和癌细胞中表达。HER-2与细胞增殖、分化和迁移有关[21]。HER-2的过表达已经在许多癌症中观察到,包括乳腺癌和胃癌。在过去十年中,基于曲妥珠单抗的化疗策略仍然是晚期HER-2阳性胃癌的一线治疗标准。基于曲妥珠单抗治疗胃癌试验,曲妥珠单抗联合顺铂和氟嘧啶全身化疗作为主要治疗方式,被确立为晚期HER-2阳性胃癌的一线治疗方案[22]。
曲妥珠单抗-德鲁替康(trastuzumab-deruxtecan,T-DXd)是一种抗体-药物偶联物,由抗HER-2抗体、可切割的四肽基连接物和细胞毒性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组成。与标准化疗(伊立替康或紫杉醇)相比,T-DXd在三线或后期治疗HER-2阳性胃癌中显示出生存获益[23]。同时,T-DXd增强了抗肿瘤免疫力,正如树突状细胞标志物表达那样,其增强了小鼠模型中肿瘤细胞上MHC-I类的表达[24]。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组合目前正在Ⅰ/Ⅱ期试验(NCT04379596)中进行研究。一项在老年HER-2阳性晚期胃癌患者中的研究显示,T-DXd联合替吉奥具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可下调肿瘤标志物表达含量,延长生存期,且毒副反应少[25]。
玛格妥昔单抗(margetuximab)是一种抗HER-2抗体,与曲妥珠单抗类似,但其Fc区域优化以更好地结合到Fc受体。一项关于玛格妥昔单抗加派姆单抗的Ⅱ期试验显示,在既往治疗过的HER-2阳性胃食管腺癌患者的晚期治疗中,玛格妥昔单抗加派姆单抗在PD-L1阳性亚组的ORR为44% (11/25),mFPS为4.8个月,mOS为20.5个月[26]。
2.2.2 结合VEGF/VEGFR抑制剂
先前的一项体内研究报道,用抗VEGF抗体或具有广泛多激酶抑制谱的VEGF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选择性抑制VEGF途径可有效控制肿瘤生长并抑制免疫抑制细胞(如调节性T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和骨髓来源的抑制细胞)的浸润,同时增加成熟的树突状细胞分数。因此,PD-1阻断与VEGF抑制剂联合使用可以增强抗肿瘤活性[27]。
阿帕替尼是一种抗血管生成药物,仅在一小部分晚期胃癌(GC)患者中显示出有益作用。鉴于免疫疗法最近取得的成功,阿帕替尼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可提供持续有效的抗肿瘤反应。给予免疫功能正常的小鼠皮下生长的胃癌荷瘤(MFC)联合阿帕替尼和抗PD-L1抗体治疗。阿帕替尼和PD-L1阻断联合治疗协同延缓了含MFC免疫功能性小鼠的肿瘤生长,提高了存活率[28]。
雷莫芦单抗(ramucirumab)是一种抗VEGFR2抗体,在GC中显示出疗效,但获益有限,部分原因是间质-上皮细胞转化因子(MET)介导的耐药性。其他VEGF靶向药物,如TKI,如雷戈非尼和卡博桑替尼,在早期试验中也显示出适度的单药活性。在几项Ⅰ/Ⅱ期试验中,当使用抗血管生成剂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PD-L1抑制剂)双重阻断组合治疗时,难治性GC/GEJC患者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临床活性[29]。事实上,那武利尤单抗加雷莫芦单抗,派姆单抗加雷莫芦单抗,那武利尤单抗联合紫杉醇加雷莫芦单抗的几个Ⅰ/Ⅱ期试验显示对AGC患者都有不错的疗效。最近,抗PD-1抗体与靶向VEGF受体和其他受体酪氨酸激酶如瑞格非尼(regorafenib)或乐伐非尼(lenvatinib)的多种抑制剂的组合也显示出AGC患者良好的疗效。雷戈非尼加纳武单抗的Ib期试验显示,AGC患者的ORR为44%,mPFS为5.6个月[30]。
2.3 结合放疗
放疗直接破坏和杀死肿瘤细胞并向免疫系统释放新抗原。然而,放疗可上调PD-L1的表达水平,从而通过诱导免疫抑制抵消放疗的益处。在放疗中加入PD-1阻断剂可以抵消肿瘤细胞的对抗作用,因此具有协同作用。在MFC小鼠模型中,放射治疗后未观察到明显的肿瘤消退。进一步的研究表明Sting蛋白表达,树突状细胞和T细胞的浸润以及肿瘤组织中PD-1/PD-L1表达的显着增加。而且,辐射处理激活了T细胞并增强了抗PD1抗体对MFC肿瘤的治疗效果。数据表明,尽管MFC肿瘤对放射治疗不敏感,但放射后肿瘤微环境仍可引发[31]。放射疗法与免疫疗法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对放射疗法不敏感的肿瘤模型的抗肿瘤活性。
3 结语与展望
尽管使用了化疗和生物制剂等标准疗法,进展期胃癌的预后仍然极差。而免疫治疗药物为胃癌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获益,并且日益挑战现有的治疗模式。其中,以PD-1/PD-L1抑制剂和Anti-CTLA-4抗原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晚期胃癌治疗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在与化疗、靶向治疗及放射治疗的联合治疗方案中更是体现出显著的生存获益。尽管如此,在晚期胃癌的免疫治疗中仍然面临一些困难亟待解决。例如目前尚不清楚如何选择nivolumab或其它可用的治疗方法如伊立替康或三氟尿苷/替吡拉西作为AGC的三线或更晚的治疗。对于联合治疗中ICIs药物的使用顺序、最佳剂量选择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其在晚期胃癌治疗中的最大获益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因此,有必要探索更多具有预测价值的生物标志物来评估不同阶段对ICIs治疗可能有良好反应的胃癌患者。不仅如此,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TRAEs)在临床实验开展及临床治疗中的“瓶颈”问题尚需更为严格的界定并积极探索相应的解决方案。此外,关于肿瘤微环境对免疫治疗的调节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改变肿瘤微环境促进免疫治疗效果对于增加临床获益至关重要。其中,PD-L1表达、MSI表型、EBV状态作为重要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必须在前瞻性研究中加以改进和验证。重要的是,根据分子分类评估免疫治疗的临床反应,以改进晚期胃癌个性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