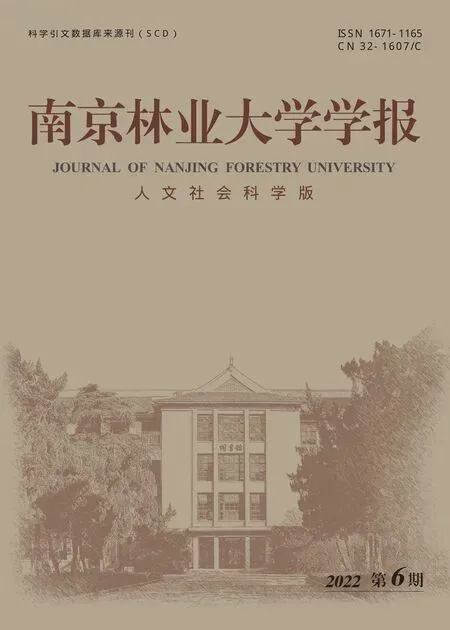《边城》暮年叙事的生态意蕴
——以“返魅”世界观视角⋆
陈桂霞
(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当前“严重老龄化社会”①注: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14.1亿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2.6亿,占比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13.5%。按照1982年老年问题世界大会指出的“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的标志是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之标准,毋庸置疑,我们现阶段处于“严重老龄化社会”。的大环境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逐渐加强了对老龄群体的关注。讲述人生暮年故事,描述老人生活现状、呈现面临的现实问题等“暮年叙事”研究呈兴起之势。暮年叙事折射老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内在品质,引发人们对更深层次上的生命哲学命题进行思考。本文以“返魅”世界观视角,解读《边城》中暮年叙事的后现代生态意蕴,对作品中慈爱质朴的老船夫(祖父)、公正无私的船总顺顺等老者的形象进行生态位反思,以探寻当下社会的老者如何以仁者之心、智者之慧努力做到对“他者”的认同,最终实现“生态自我”。
一、《边城》暮年叙事中的“自然之道”
以中国叙事学研修专家傅修延观点,鲁迅先生对“叙事”有最好的解释——人们劳动至疲劳时,会以“彼此谈论故事”[1]的消遣方式来达到休息目的。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消遣的方式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而“谈论故事”,即“叙事”——用语言文字去描述社会生活事件,仍是“最吸引人最简捷便利最能消磨时间的艺术活动”[1]。
这其中,“以老人为叙事对象,用散文、小说、电影等真实或虚构的手法书写、讲述老人特有的生活境况和情感变化的故事”则称为“暮年叙事”[2]。在传承了近百年的经典作品《边城》中,对“饱经风霜、超然物外,不为喜怒哀乐所动的”[3]老船夫、船总顺顺等质朴老者的诸多叙事,堪称“暮年叙事”的典范。
在20 世纪30 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有一个在自然中生活了70 年的老船夫。他以撑船摆渡为生,自二十岁起便守在一个叫“横溪碧溪岨”的渡口,五十年来把船来回渡过无以计数的过河人。作为一个七旬老者,他“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4]208;偶尔也有遇到忧愁、睡不着的时候,“一个人便跑出门外,到那临溪高崖上去,望天上的星辰,听河边纺织娘和一切虫类如雨的声音……”[4]257。
掌管水码头的船总顺顺,脚有小毛病,走路难平衡,为人却洒脱大方又公正无私。因其“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4]216,五十岁便能代替年高德劭者执行水面事务。在得知自己的大儿子行船遇难后,隐忍了痛苦,并体贴地安慰老船夫:“伯伯,一切是天,算了罢。我这里有大兴场送来的好烧酒,你拿一点喝去罢。”[4]271
这些老者行为朴实,语言平淡,似山涧溪流自然流淌,清澈见底。在这里,时间静静地流,日子平平地过,大自然帮助化解生活里琐事上的忧愁,治愈心灵上的创伤。
质朴自然的叙事,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典型东方智慧的老者形象——正直伟大,无私无欲。在《边城》里,他们性情善良,在大自然的风雨化育下,处处懂得为他人着想,时时恪守着自己的一份谦卑。有的学者认为,《边城》中的老船夫等老者具有荣格的智慧老人原型的典型特质——“遵循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过自己的本分生活,与人为善,与世无争”[5]。
在沈从文的笔下,大自然不只是人类生活的场所,更养育教化着人类,是人类精神的栖息地。这里的大自然教会人们与他者为善,成他者之美。这些老者虽然已至暮年黄昏,却也可以示青年以智慧、仁爱的风范。他们的生老病死正是遵循着中国人几千年来信奉的“自然之道”:天地间宇宙万物,各有其生存之道。万物亦都按自身的生存规律,在宇宙间生长、消亡,循环往复以至生生不息。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返魅”世界观
建设性的后现代“返魅”世界观作为后现代范式的一种理论成果,是对“祛魅”的现代科学的一种反思和超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它指出自然是有“生命”和“灵性”的生态整体,强调在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应更多关注人文精神对生态平衡的作用。
(一)世界的“附魅”与“祛魅”
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人类最初面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能够理解的自然现象少之又少,只得把一切归于神灵,认为“万物有神灵”。在这种将自然神秘化的世界观下,人类面对自然时既充满好奇又心生惧怕,从而对大自然充满了崇拜与敬畏。面对大自然,人们自发感受到的是自身的微不足道,惊叹大自然山水惊奇绝艳的同时,认为山、水、蛇、狐,甚至一草一木都有神灵鬼怪依附。因而有“附魅”之说。
附魅时代的大自然是具有神性的。在西方古文明中,希腊人坚信宇宙是一个有生命、有灵魂的整体。他们认为“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是有生命和有活力的,在它们的内部居住着的神的灵魂是驱动其生存和运动的依据”[6]。思想家泰勒斯(Thales)以磁石吸引铁块佐证“万物充满了神灵”;中国古代先贤则信奉“天人合一”这一朴素的世界观。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得益于人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人对自然的依附。人类生活在自然中,要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即人类行事应顺自然而为之,应敬畏自然的“神性”。
发轫于17 世纪欧洲的近现代自然科学,催生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使得自然的神性不断衰落。人类利用科学和理性征服和掠夺自然,将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破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导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岌岌可危。现代西方世界观秉承了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格拉(Protagoras)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格言,从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自然科学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更加巩固地建立和扩大人对自然万物的统治权”到康德“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的命题。科学家与思想家们一起运用科学、理性和逻辑的普世价值,无视神话和宗教信仰等人文精神,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人性从毫无根据的信仰和非理性行为中解放出来,鼓吹人性可以上升到自由、幸福和进步的状态,强调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排除了目的、个人原因以及一切非唯物论的相互作用,导致世界的“祛魅”。
20世纪后半叶开始,生态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了现代科学的危害,也认识到了西方工业化范式给地球带来的生存危机。美国后现代生态思想家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认为“现代科学祛魅了世界”,提出“祛魅的世界观既是现代科学的依据,又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并几乎被一致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结果和前提”[7]引言。
自然的“祛魅”意味着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界时,只是一味地从主观利益出发,忽视自然界作为“生命体”的承受力和反应,否认自然具有主体性、经验和感觉,从而把人类与自然界割裂开来,直至“有生命”的自然界开始“报复”人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指出,“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几个世纪以来,盲目追求理性、自由和进步的人类为满足自身无限膨胀的欲望,借着科学发展的旗帜把对自然界的掠夺和伤害编绎成正当理由。殊不知这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祛魅,加速了现代社会的消费欲望。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而进行的大量甚至过量的生产和消费,破坏了自然的法则,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代表科学理性的现代性不仅使人类的幸福生活变成了虚妄,更为恶劣的是它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异化。人类越来越贪婪,工作生活的唯一目标只有利益,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地破坏自身居住的自然环境,即便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恶劣情境下,仍然不忘巧取豪夺。格里芬在20世纪末就已经呼吁:“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扬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7]19。
(二)后现代的“返魅”世界观
经历三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人类习惯以科学为理由选择理性,任性地破坏了自然的平衡法则。韦伯认为理性让人变成没有情感的动物,“祛魅”的过程则可能让人类从“人”变成“非人”。所以,世界需要“返魅”。在《后现代精神》一书中,格里芬论述了对现代科学的起源、科学性质的新认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有利于科学新发展的后现代世界观——“这就要求实现‘世界的返魅’,后现代范式有助于这一理想的实现”[8]。格里芬论述了科学发展中“隐性”秩序的重要性,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观点正是生态学范式的中心思想。在批判了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格里芬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统一论的“返魅”世界观。“返魅”是寻找让事物返璞归真的方法,能抵御理性对于自然和人本身的侵蚀,提倡将科学、人文和自然有机的统一,主张让“心灵”重返万物,万物都有自己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
“返魅”的世界观以怀特海的哲学思想——“有机整体论”——为理论基础。柯布(John B.Cobb,Jr)和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两大代表经过长期研究,一致认为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有机哲学正是当今所亟须的后现代生态哲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寻求的是“一种后现代的生态学世界观,即承认人类与自然之复杂的相互关系因而承认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后现代生态学的世界观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世界观”[9]。
“返魅”意味着返回到事物的自然状态,恢复自然的原始生态。无论是“地母盖娅假说”还是“盘古开天辟地”,都凸显了自然的神圣性。人类从自然界汲取阳光、空气、水和食物而生存,依附自然的同时保持敬畏亦理所应该。当自然科学以“返魅”的视角去审视宇宙间的物体时,便能容忍复杂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和自然的神秘性。“返魅”世界观注重生态理念,格里芬提出后现代世界中人类“将拥有一种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直接的亲情关系”[10]。唯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才能形成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也才有可能实现“诗意地栖居”。
三、《边城》暮年叙事的后现代生态意蕴
从后现代的“返魅”世界观视角探究《边城》中的暮年叙事,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后现代生态意蕴:首先,《边城》的暮年叙事有对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的充分展现;其次,老船夫的暮年生活是“生态自我”的典型写照;再次,《边城》里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最后,《边城》中暮年老者们桃花源式的生活情境亦是后现代返魅生态世界观的目标——以简朴的生活手段达到精神丰富的目的(理想)。
(一)暮年叙事的生态属性
“生态叙事”是指用文字来讲自然与生态的故事,“任何能凸显作家关注生态的叙事,强调人类与环境的联系”[11]92都可谓之“生态叙事”。在生态文学批评者眼里,古今中外众多重要作家的作品中都不乏“生态叙事”的存在,譬如莎翁的经典剧作,又如古老的《山海经》叙事。特别是中国,“不仅自古就有道家圣贤倡导‘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叙事典籍;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中对生态叙事也有很好的运用。其中,1934年沈从文的《边城》就是生态叙事最好的代表作之一”[11]92。
历经近百年,《边城》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说中的巅峰之作”,它被看作是“生态叙事的典范”,其暮年叙事部分亦恰如其分地证实了这一点。《边城》中的暮年叙事,不仅具有“用文字叙述自然与生态”的特点,而且其叙事本身也是生态的——作者笔下的老者,始终作为整体的一员存在,人、物以及环境之间是普遍地相互联系着构成一个生态整体的。无论是老人自身的一言一行,还是老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至纯至朴的,恰如中国水墨山水画卷,无着色、不渲染。淳朴自然的描写,简洁明了的叙事,似清澈的溪水静静流淌,如轻盈的微风徐徐扑面:老船夫经年累月不论晴雨都守在渡口,话语不多,心思却如溪水般清澈。“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4]208作品通篇叙事极尽“简单”二字,只“静静的”和“很忠实的”,老人沉默寡言的形象、质朴善良的品质便跃然纸上。
老船夫生活在和谐美妙的大自然里,他摆渡的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4]207
“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中。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4]211这极具灵气的自然山水孕育了他的心灵,使得他看似漫不经心地生活在一个令人向往的生态乐境中。
70年的风雨历练,使他有着健康硬朗的身体和质朴厚道的性情。他秉承了大自然的生态理念,散发着淳朴的乡野气息;经年累月与青山绿水相依相托,应和着大自然的节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尔遇到天气晴朗而渡河人不多时,会觉得闲散倦怠,便以地为铺,以天为被“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4]209。
《边城》中反映老人慈爱、质朴的暮年叙事是作者整个生态画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彰显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亲相爱、共生共荣的生态之道。“这是沈从文竭力彰显的一种生态理想。在这种牧歌情调的描绘中,人不但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体现出从生命到生活与自然的合一和感应。”[12]231
(二)个体均有的“内在价值”
“返魅”的世界观是一种后现代生态世界观,它契合了东方智慧,是发展了的深层生态观。主张所有存在于自然界的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着的;所有的个体都具有“内在价值”;人的价值实现体现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自我”。而《边城》的暮年叙事正是对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的充分展现,老船夫的简朴生活可谓是实现“生态自我”的典范。
阿伦·奈斯(Arne Naess)和乔治·赛逊斯(George Sessions)为深层生态学确定了“八大纲领”。第一条便指出地球上的人类生命和非人类生命,其幸福和繁荣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即“内在价值”。这些价值与非人类世界是否能服务于人类的目的没有关系。深层生态学与格里芬的后现代世界观一样主张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应是一种伙伴般的“亲情”关系,并强调在此基础上的“共命运”[13]161——两者都主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有机统一,以一种系统、整体论的眼光,承认并尊重自然界中的各种生命以及非生命体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边城》的暮年叙事与“内在价值”理论是相契合的。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均得到了体现:一方面,自然界的山水草木、日月星辰,都有其自身的存在,这些存在本身有“道”可循,有自身的生存规律和秩序——无论是山的挺拔、水的清澈,还是草的葱绿、树的繁茂,一如文中栉风沐雨的老者,都显示了生命的活力;另一方面,人作为一个生物,从阳光雨露而生,经自然化育而长,循自然之“道”而存在。“生命经天地化育而来,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相互兴发,形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只有同大自然母体保有生命的联系,人的生命才能如火如光,保持鲜活与强健。”[12]229
在《边城》的生活细节里,人物三言两语的对话和简单朴素的行为无不在诠释着对事物“内在价值”的尊重。“要过端午节了,祖父与翠翠在三天前业已预先约好,祖父守船,翠翠同黄狗过顺顺吊脚楼去看热闹。但过了一天,翠翠又翻悔回来说:‘我走了,谁陪你?’祖父说:‘你走了,船陪我。’翠翠说:‘我决定不去,要去让船去,我替船陪你!’”[4]232在大自然里生活久了的人,自然能理解“船”已经不再是单个的存在物了。这种朴素的对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现实中那遥远的山村,老母亲念念叨叨的会是自己养的鸡群、老父亲每逢过年总要给自己种的树浇点肉汤,还有门前池塘边大树下那见证了太多故事的长石条……
在这令人流连忘返的“桃花源”里,大自然本身自有其尊严和魅力,也因此而成为读者驻足观赏的极有生命力的存在,而人物与故事只是山水间的点缀。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在看似悄无声息的对话与共鸣中交相辉映、互为存在,共同成就。
(三)“生态自我”的践行者
美国学者夏志清曾指出:“如果我们可以把沈从文的小说世界分成两边,一边是露西形态的少女如三三、翠翠,那么另外一边该是华兹华斯的第二种人物:饱经风霜、超然物外,已不为喜怒哀乐所动的老头子。”[3]473他在世界文学视域下审视了其他老者形象,认为无论是写出《当你老了》的诗人——“老态龙钟”的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本人,还是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里那个患了“空虚感失眠症”的老头子,与沈从文笔下的老头子相比较,“都显得渺小了”[3]476。因为前者代表了现代意义的“虚无”,而后者极具东方智慧,于朴实无华中践行着自然之道,符合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的价值的定位。
返魅的世界观坚持生态整体主义原则,主张“一切自然存在均有其内在价值”,一切自然存在的最高境界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个在坚持生命平等以及尊重生命基础上的不断扩大与自然认同的过程”。[13]49“认同”可以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拓展与飞跃;通过情感共鸣可以实现人与万物一体的大我感觉。“返魅”的世界观强调个体置身于整个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而对整个自然界所有存在产生深深的同情感,有对“他者”的深刻认同,能对其产生强烈的共情心理,从而实现“生态的”自我。
《边城》里老船夫的暮年生活正是“自我实现”的典型写照。在《边城》这个生命有机整体里,老船夫在广袤的自然中生活、劳作,他无从感知弗洛伊德的“自我”,只有与自然融成一片、化为一体而达到宇宙里的“忘我”、“无我”,这种无我的自然人格是绝对意义上的“生态自我”,即返魅的世界观里强调的“生态自我”。如果要刻意寻求一种存在,那广袤的大自然便是他的身躯,静谧的大山就是他的灵魂,清澈的溪流则是他的思想。
奈斯曾说“大我(Self)”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即“自然”。《边城》中的老船夫、顺顺、杨总兵等老者,对简朴的物质生活没有丝毫抱怨,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了极为高尚的精神风貌。他们“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中。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正直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的身上:成人之美”[14]。
这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身之间毫无功利之意、超脱于物欲之外的自我,在《边城》中随处可见,正如上文所论述的,这里的人们遵循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老船夫在大自然的风雨中生活了一辈子,终其一生与大自然肝胆相照,他的生命与溪流、渡船、黄狗以及白塔都是相融相通的。在生命临了的那一夜,他预感到天事的变化,并没有显得悲伤反而安慰孙女:“怕什么?一切该来的都得来,不必怕!”[4]285天降暴雨、电闪雷訇时,溪水涨了,白塔倒了;渡船没了,老人也去了……在大自然的召唤中,老人完成了生命的周期,重新回归了大自然。生命消逝了,痛苦与悲伤也消融在广袤的天地里,“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只局限于生,也通达了死。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
(四)和谐的“生命共同体”
返魅的生态世界观认为,一切个体都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存在脱离与其他实体的关系的孤立实体,个体的存在始终依赖于其所处的环境并深受其环境的影响。后现代生态观强调“包含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系统的生命有机整体,是自然的本质回归”[15]。《边城》里的生态系统正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边城》里的自然万物,并非只是一般的“物”,而是具有“灵性”的生命,是包括了整个生物圈的所有生命。这是因为沈从文“总是以虔敬之心面对他笔下的大自然,他没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与偏见,坚持以仰视的视角将自己的灵思妙想融会于大自然的‘生命’之海中,笔底流泻着自然万象翩然欲出的灵性……”[12]223
生活在边城里的质朴善良的老者们,作为自然的一分子,秉承了自然的造化,与静谧的山、清澈的水有着心灵的默契。在这优美的意境里,他们与生机盎然的大自然自成一体;人物的精神生命与大自然未曾有过片刻的分离。他们生活在一幅“桃花源式”[16]184的生态图景中——评论家刘西谓所称的“一部idyllica(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16]184里——这里的生命互相支持、互惠共生,与环境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牧歌式”的边城中,生命与自然浑然合一,大自然流动的旋律与人物活动的节奏互为交织,和谐美妙而无半点做作。这里的大自然正如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所说,“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17]93;同时也印证了王国聘教授所提出的“生态科学的重要思想是把自然的本质归结为生命共同体”[18]。
社会发展至21 世纪,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了当今世界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沈从文的《边城》提供了一种典型的生态范式:在这里,所有的个体都不是个别的存在,而是通过对其他生命的体验,感受整个世界的存在。特别是老人,他们与青年、与自然一起置身于这样一个“以爱来维护所有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共生”[17]93的生命共同体。
(五)“诗意的”暮年生活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就有“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的道理。林语堂曾说中国人所拥有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是最具人情味儿的、最合乎天地人和谐的方式”[19]108。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健全,最优美之处,乃是“淳朴”二字,教人认得简朴生活之美。简朴的真实境界就是要有与自然相契合的精神: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适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20]
《边城》中的暮年叙事,于不经意间“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老年生活的朴素之美。对于当下处于生态困境中的人们来说,它是“另一种与我们现状不同的栖居于大地的方式”[21]。后城市化时代,中国的乡村振兴,正是要建设这“牧歌式的桃花源”,追求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人类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与自然相争相执、互为劫难,而应该回归《边城》里的“整体主义世界观以及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想”[22],以简朴的手段达到(生活)丰富目的,正是后现代生态世界观的生活目标。
此外,《边城》中的老者“健壮而智慧”,也是“最美丽的”;他们“见惯了人世的忧苦,所以极仁慈”[19]184。他们对人生的诠释就像大自然中的季节交替,少壮中老,各得其所,各有其美。“白日里,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持”的老船夫,与林语堂先生笔下“有着红的面颊,雪白的头发,以通晓世故的态度,用和蔼的口气,谈着做人的道理”[19]182的中国老者如出一辙,争执的事端岂不正是“做人的道理”——“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可”[4]229。读《边城》中老者的暮年生活,自然就联想到中国的“大丈夫”们自古就是“以天地为庐”(阮籍),随天地之大而生长,而尽终其天年。世界范围内的老者,都该读一读《边城》,修一修东方的儒道,以期生命行至终点处,会有“伟大的和平晴朗,物质舒适和精神的富足,而不是破锣破鼓的刺耳响”[19]182。
四、结语
后现代生态主义者反对当今西方社会过高的物质生活标准,主张降低物质生活水平,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财富相比,精神质量和“亲情”关系更为重要。为避免盲目的经济发展将人类社会引向生态死亡,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J.里夫金(Jeremy Rifkin)指出:“人类需要将自己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起来,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共情(empathy)。”[23]
东方思想中的“尽人事听天命”是一种生存智慧:“天道”化育万物,“人道”尽其所能;天人相通,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是传统的东方哲学思想的精华。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哲学思想,会引领人类去探寻和反思,最终走向一个清晰和自由的世界。后现代生态世界观为人类充满智慧地生存指明了方向;《边城》中的暮年叙事为老龄化社会中乡村老者如何精神富足地生活提供了一种借鉴。积极思考,不断探索,世界终将达到著名学者费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4]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