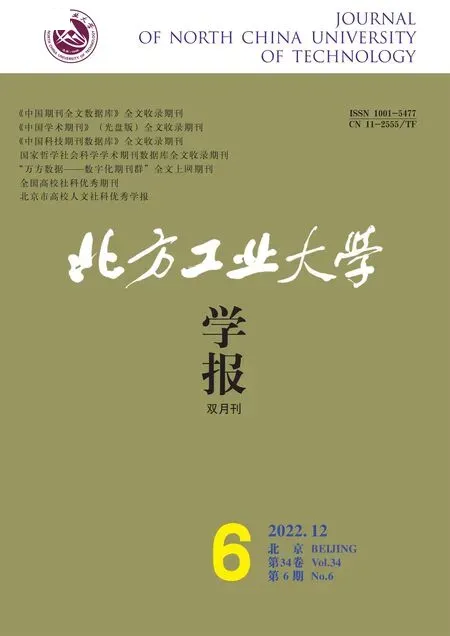论贝西·黑德的生态观*
卢 敏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234,上海)
非洲作家和批评家对源自世界大都会中心的生态批评一直保持警觉的态度。吉翰·霍齐曼(Jhan Hochman)认为西方主流的生态批评是白人为了保护带给他们“愉悦”[1]的环境,根本没有顾及黑人生计问题。罗伯·尼克松(Rob Nixon)指出,美国的生态批评论著有明显的“排外态度”。[2]拜伦·卡米内罗-桑坦格洛(Byron Caminero-Santangelo)指出,非洲对生态批评的抵抗主要原因是它具有潜在的“帝国的”含义。[3]来自非洲等第三世界的批评促成了生态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某种融合,推动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发展。[4]后殖民生态批评关注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退化问题,提倡一种更新的地方和环境意识,强调对环境的全球化的研究。[5]目前后殖民生态批评关注的文本多聚焦发展与环境、田园书写和反田园书写、动物再现、动物保护与本土居民权力等,[6]对发展中国家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如干旱地域关注不够。
贝西·黑德(Bessie Head,1937—1986)的作品以1960—70年代南部非洲内陆之国博茨瓦纳为创作中心,以令人震撼的笔墨描绘了卡拉哈里沙漠边缘地区的风景和生态环境,以及当地百姓和国际志愿者从事的农牧业发展试验,表达了深切的生态意识和科学精神,是1970年代日渐兴起的生态批评的先声。桑娅·达林顿(Sonja Darlington)认为,贝西·黑德的作品对理解黑人作家对“全球绿色的呼唤”[7]的回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博茨瓦纳的风景与迁徙文化、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土地制度、旱灾与求雨习俗、女性与现代生态农业、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非洲梦想5方面探讨贝西·黑德在作品中表达的生态观。
1 博茨瓦纳的风景与迁徙文化
贝西·黑德对博茨瓦纳风景的描写不仅给读者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印象,并且时刻唤醒读者对此风景中的人和动植物的生态关怀之情。贝西·黑德笔下风景与生态环境是紧密联系的。英国历史学家、文艺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风景与记忆》(LandscapeandMemory, 1995)中追溯了风景一词的丰富内涵。他指出,风景一词是16世纪末从荷兰输入英国的,源自荷兰在防洪领域中创造的令人惊叹的工程,其词根意味着人类占有,即“人类对风景的规划和使用”,[8]因此在以埃萨亚斯·范德·维尔德(Esaias van de Velde)为代表的荷兰风景画中,总有渔夫、赶牛人和骑马者点缀其间。米切尔(W. Mitchell)在《风景与权力》(LandscapeandPower, 1994)导论中则指出:“风景(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人造的或者自然的)总是以空间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空间是一种环境,在其中‘我们’(被表现为风景中的‘人物’)找到——或者迷失——我们自己。”[9]西蒙·沙玛和米切尔对风景的定义都强调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风景是人对自然的创造性利用,人在风景中找到自己,或者迷失自己。当然在风景中找到自己显然更为重要,这将激发出人与自然互动的新的创造力,贝西·黑德的情况正是如此。博茨瓦纳的干旱地貌和丰富多样且生命力顽强的物种和人构成的风景深深吸引了来自南非东部沿海地区的贝西·黑德,她在博茨瓦纳乡村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归属感。她笔下的博茨瓦纳风景给世界读者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审美体验和文化渊源。
贝西·黑德对生态环境有敏锐的感知和觉察力,她的作品中对动植物和生态环境的描写常常令人叹为神来之笔,这一方面和她的天赋相关,另一方面和她的生活经验相关。从生态环境宜人的南非东南沿海城市到缺水少雨的博茨瓦纳乡村,巨大的生态环境差异赋予她双重的感知体验和强烈对比的意识,这使得她的文字具有强烈的唤醒力,使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态环境,学会欣赏、珍惜,进而保护它。1964年,贝西·黑德从南非流亡到博茨瓦纳,她出生和生活过的南非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德班(Durban)、开普敦等地都处于东南沿海地区,属于地中海式气候,舒适宜人,植被丰富,风光旖旎,但是她从来没有描写和赞美过这些地方,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剥夺了黑人的土地,让他们成为自己家园里的流浪者。博茨瓦纳生态环境恶劣,但是贝西·黑德对离开南非不怨不悔,她用令人惊叹的笔墨描绘博茨瓦纳的赤裸荒凉之美。
在自传体小说《权力之问》(AQuestionofPower, 1973)中,贝西·黑德描绘女主角伊丽莎白初到博茨瓦纳看到的风景和生态环境:
莫塔本是指沙地。这是一个偏远的内陆村庄,位于卡拉哈里沙漠的边缘。……在旱季,泥草屋的主体和半灰色的茅草屋顶给了它一种灰白的外观。在雨季,莫塔本只会下一种沙漠雨。雨在天空飘落,拉着长长的雨丝,但雨还没到地面就干了。人们把鼻子转向风,嗅着雨。但在莫塔本往往不太可能下雨。伊丽莎白私下给它改名了:“雨风村”,来自她在某处读过的一首诗。[10]
这是博茨瓦纳村庄的常态,地处沙漠边缘,干旱少雨,地下水是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雨风村”是个非常诗意、贴切的名字,包含了作者对此地的精神认同。即使在雨季,这里的雨也只是沙漠雨,未落地就干了。偶尔会有暴雨,会造成洪水泛滥,但更多的是带来了新的生机,并为地下水做充分补给。人们抓紧时间在短暂的几周降雨期播种农作物,期待一年的收获。
在干旱环境中生活的博茨瓦纳人民一直在探索自然,发现自然的启示,以便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从而创造了独特的风景。贝西·黑德在历史著作《塞罗韦:雨风村》(Serowe:VillageoftheRainWind, 1981)中,记录了博茨瓦纳乡村特有的事物:绿树、村里的狗、老历法、人名含义、婚丧仪式。“绿树”被放在第一个位置,有三个原因:一是人们遥望村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绿树”;二是“绿树”在村庄大面积的种植表明当地人擅长互相学习;三是“绿树”特殊功能的发现和普及中,具有探索和尝试精神的先行者和有影响力的倡导者的引领和推广具有重要作用。
“绿树”是一种橡胶类植物,在茨瓦纳语中称为“塔哈瑞塞塔拉”(Tlharesetala),被当地人用来做庭院的篱笆。贝西·黑德这样描述道:
这种植物具有惊人的繁殖力。在只有一点水或几乎没有水的地方,人工插枝,绿树都能发出新根,开始生长。绿树上的蜡层能有效防止水分蒸发流失,乳状树汁的味道很差,阻止了山羊食用。汁液暴露于空气时就会凝结,因此只有茎干遭到破环,才会造成水分流失。叶子长得极小,达到绝对程度。[11]
这种“绿树”近看毫不起眼,遥看却形成郁郁葱葱的样子,其景致恰如我国古诗中所写“绿”色遥看近却无。用“绿树”做篱笆非常经济高效。塞罗韦是博茨瓦纳最大部落恩瓦托(Bamangwato)部落的旧都,曾是非洲最大的村庄之一,常住人口数达35 000,每家都有很大的庭院。据贝西·黑德粗略估计,大约需要将近1 000棵树的木桩来做一个院子的篱笆,35 000人家的院子,需要砍伐大量的树木,而木桩又很容易被白蚁吞噬,需要经常更换,费人力费材料。“绿树”不为动物食用,也无其他大功用,但作为庭院篱笆,则发挥了它的特性和功能,是物尽其用,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美好生态景观的例子,也是生态经验传播、传承的结果。
在塞罗韦,人们用“绿树”做篱笆的历史可追溯到1923年。那一年,普雷托瑞斯(Pretorius)夫妇搬到塞罗韦,他们去马翁(Maun)拜访亲戚,发现了那里的人用“绿树”做篱笆,有很好的防风功能,于是他们就带了一些枝条回来。刚刚摄政的蔡凯迪酋长(Chief Tshekedi, 1905—1959)看到“绿树”适合做篱笆,就召开霍特拉(kgotla)会议,鼓励村民种植“绿树”。莫萨瓦·奥尼恩(Mosarwa Aunyane)是塞罗韦人,嫁到布拉瓦约(Bulawayo),那里的人早就用“绿树”做篱笆了,听到酋长鼓励,她用卡车把布拉瓦约的“绿树”拉来出售,做了一笔生意。“绿树”布满了村庄,也无需花钱购买了,新庭院的“绿树”都是免费赠送的。“绿树”在塞罗韦的广泛种植体现了博茨瓦纳人本能的生态意识,但是在传统部落迁徙文化中,人们大多缺少科学理性的生态保护意识。
博茨瓦纳地广人稀,历史上部落逐水草而迁徙是常见的做法。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带,人们寻找地表水和地下水源丰富的地方居住、农耕、放牧,但是随着人畜增长,水源用尽而被遗弃的地方越来越多,适合生存的环境就越来越少。塞罗韦是博茨瓦纳历史上最著名的酋长卡马三世(Khama III, 约 1835—1923)于1903年带领恩瓦托部落从旧都帕拉佩(Palapye, 1889—1902)迁至此的,因为那里的水被用尽干枯了,至今帕拉佩的旧都废墟还和被遗弃时是一样的。[12]部落迁徙文化使人们只追寻自然丰饶和馈赠的一面,以简单抛弃的方式解决自然资源匮乏的问题。但随着欧洲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非洲土地资源被侵占,部落很难通过迁徙方式获得宜居生活环境,加上大小酋长对百姓的剥削,缺少教育的贫穷百姓只能向自然索取,日积月累,河流干涸,草木被牛羊吃光,土地沙化,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风景不再美好。
2 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土地制度
1960年代是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时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现代化发展被提上议程,很多国际志愿者到非洲进行科学发展试验。贝西·黑德的《雨云聚集之时》(WhenRainCloudsGather, 1968)以1960年代博茨瓦纳独立前夕农牧业改革试验为原型,描写了英国农业科学家吉尔伯特(Gilbert)以志愿者身份在小村庄霍莱马·姆米迪(Golema Mmidi)带领当地百姓以合作社形式艰难开展干旱农牧业发展研究并取得成功,具有鲜明的非洲特色、科学精神和生态意识。
博茨瓦纳典型的植被是荆棘,其中高大的金合欢最引人注目,而低矮的金合欢更具有生命力和保护土壤的能力。“金合欢有高大挺拔的树干,顶部黑色树枝形成精致的伞状,但更多时候荆棘长得像低矮的野草丛,枝条上是长长的白刺,根部长着成簇的浅绿色叶子。”[13]吉尔伯特认为解决土地沙漠化问题至关重要,他走遍村庄,发现大片被遗弃的村庄和干涸的河床,唯一能把土壤连在一起的植被是低矮的金合欢,这些观察结果使他确信,“只有大规模的土地围栏和控制放牧,才能拯救那些尚未被完全侵蚀成不适合人类和动物居住的区域。”[14]金合欢,属于豆科类,叶子是甜的,山羊最爱吃。要避免村民的山羊把刚长出的金合欢吃光,吉尔伯特提出用铁丝网把草场围起来,却遭到百姓的一致反对。
自古以来,非洲的土地属于酋长和部落,被称为“公地”,无人圈围土地,将其私有化。最早在非洲殖民的荷兰人1652年登陆好望角以后,便以“公地”无主为借口,大量侵占土地,后来英国人引入产权概念来改变非洲人传统的土地观念。南部非洲最大的原住民科伊(KhoiKhoin)部落原本在自己丰饶的土地上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土地被“欧洲人通过军事力量和不平等的协议”[15]掠夺光了。早期欧洲殖民者在军事力量尚弱的情况下,用欧洲烈酒攻破了科伊部落酋长,让他们在醉酒状态下签定协议而丧失土地,这些悲惨的故事在南部非洲各部落中广为流传。
19世纪茨瓦纳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三大著名酋长:塞库马一世(Sekgoma I)、塞舍勒(Sechele)和莫舒舒(Moshoeshoe)都以史为鉴,禁止部落成员饮酒。[16]他们在19世纪后半叶欧洲列强瓜分非洲时,审时度势,主动寻求英国保护,成为英国保护地贝专纳兰(British Protectorate of Bechuanaland, 1885—1966),以此确保酋长对部落的直接管理,维护了非洲传统土地制度。1895年,靠金伯利钻石矿发家的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欲以英国南非公司之名接管贝专纳兰。罗德斯庇护布尔人,强迫酋长把土地割让给布尔人,其野心和对非洲原住民的剥削和压迫臭名昭著。被誉为博茨瓦纳现代民族国家奠基人的三大酋长:卡马三世、塞贝莱(Sebele)和巴托恩(Bathoen)到伦敦抗议,罗德斯的野心未能得逞。[17]酋长直接管理使得博茨瓦纳在最大程度保留了黑人传统和部落公地观。
部落公地不得购买,也不许圈围,部落成员要种地,只需向酋长提出申请,无需付费,就可得到分配的土地。此制度旨在保护穷人的利益,防止土地落入少数富人的手里。吉尔伯特提出要圈围土地时,立刻遭到百姓的反对,他们担心他像其他狡猾的殖民者一样,以试验为借口,把公地私有化。吉尔伯特理解了“公地”制度后,向百姓展示了他的试验草场:
养牛场被分成了4个区域。 其中2个将空置一段时间。 在其中一个空置区域,他希望观察各种天然草的恢复速度。在另一个区域,他清除了树桩,耕好了地,播下了抗旱草种。由此,他将能够判断是本土草还是进口的抗旱草最适合放牧。
在2个被使用的区域里,他放养了从合作社成员那里购买的100头牛。其中最好牛的将用于繁殖试验,然后这些牛再卖给希望补充畜群的合作社成员。最后一个区域用于提高肉品档次试验。4号区域的牛以一种特殊类型的玉米秸秆为食,这种玉米只长茎和叶,并且作为一年作物的一部分在农场种植。此区域内围栏附近还为牛配有饮水、骨粉和盐舔。[18]
吉尔伯特圈围土地的科学意图对于有丰富经验的牧民来说,通过亲眼所见就能马上领悟,他们明白草场恢复的重要性,对新的抗旱草种和饲料作物的功效也充满好奇和希望。吉尔伯特进一步解释了圈养牛在一定范围内的科学头数,控制牛的存栏数,反而提高牛的质量,牧民出售肉牛,将获得更多的现金。此外圈养牛还可以防止牛跑丢,防止口蹄疫等疾病的传播。
吉尔伯特圈围草场养牛的试验与“公地”制度没有抵触,被当地百姓接受了,但是农牧业科学试验周期都较长,一般要3—5年才能见成效,之后还需要很多年才能普遍推广。在此过程中,人工控制的局部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尚未见大成效,气候却在变化,持续干旱发生,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加快,植物、动物开始大批死亡,儿童营养不良而造成的疾病和死亡问题凸显。农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依靠科学指导和相适应的土地制度,还需要应对气候变化。
3 旱灾与求雨习俗
气候变化对农牧业的影响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难题,也是文学中的一个母题。对于干旱,先民采用的祭祀和求雨仪式至今还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记忆在绝望之境就会被激活。祭祀和求雨仪式带来的是希望还是灾难成为文学中的一个沉重、严肃而复杂的议题,简单的道德判断和法律制裁是难以实现诗学正义的。博茨瓦纳是世界上最容易受干旱影响的国家之一。贝西·黑德在多个作品中书写了博茨瓦纳始于1958年的连续7年干旱,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一次大旱灾。恩亚拉德斯·巴蒂萨尼(Nnyaladzi Batisani)在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递交的《博茨瓦纳共和国国家抗旱计划》(RepublicofBotswanaNationalDroughtPlan, 2020)中指出,博茨瓦纳自1950年代经历了多重、多年的旱灾后,干旱出现的间隔时间缩短,而严重性增强。[19]该计划详细记录和分析了1981—2013年的5次全国范围的大旱灾,但没有详述1950年代的旱情,因此贝西·黑德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也再次证明她超前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对生态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多方位思考。
贝西·黑德在短篇小说《寻找雨神》(Looking for a Rain God, 1977)中描写了连续7年干旱对土地、植物造成的影响:
但从1958年开始,长达7年的旱灾降临在这片土地上,就连水源地也开始变得像荆棘地一样干枯荒凉;树叶卷曲枯萎;苔藓变得又干又硬,在缠绕的树枝阴影下,土地变成了黑色和白色粉状,因为没有下雨。[20]
连续7年干旱造成植被全部枯死,土地沙化,地下水资源无法得到补给,万物进入“干熬”状态。虽然博茨瓦纳的人和动植物具有超强的忍耐力,但是忍耐力也是有极限的。
对于牛这种大型牲畜,严重缺水必然造成大面积死亡。从牛的死亡开始,整个地区的物种就像连环套式的走向死亡。在《雨云聚集之时》中,贝西·黑德描绘了代表死神的秃鹫成为荒凉世界主宰的骇人场景:
在这荒凉之中,秃鹫称霸了。它们聚集在地上,60~100个一群,用嘶哑、粗暴的声音进行重要的讨论,它们长长的、邋遢的棕色羽毛表现出专横的愤怒。它们可以专横、愤怒、自居,因为它们将成为一个埋葬超过600 000头牛的群体。[21]
这段文字中的“超过600 000”是当地百姓饲养的牛,是他们的主要生计来源。在连续7年的干旱中,男人带着牛群不停地寻找水源,一批批的牛饿死、渴死,横尸遍野。而这死去的“超过600 000”的牛并不是多年的累积数,而是当年死亡的总数,称得上是灭顶之灾了。
在《雨云聚集之时》中,贝西·黑德不仅描写了大旱之下万物死亡的恐怖场景,而且聚焦死于大旱的儿童。通过细致刻画天真无邪的儿童面对死神的反应,激发读者深切的同情和对自然的敬畏与反思。寡妇波琳娜·赛比索(Paulina Sebeso)11岁的儿子伊萨克(Isaac)没有上学,独自在畜牧站放牛。当其他牧民发现自家牛群和野生的鹿群出现大量死亡状况时,都带着剩下的牛回村庄了,牛群大批死亡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但是伊萨克却不见踪影。人们帮助波琳娜到畜牧站去寻找伊萨克,驱车一天接近目的地时就看到秃鹫盘桓在上空,那是死亡地的标志。果然,波琳娜家的80头牛已经全部就地死亡。马克哈亚(Makhaya)推开伊萨克茅屋的门,只看到:“一堆干净、白色的骨头躺在地上。它们保持卷曲、紧缩的状态,手的骨头是向内弯曲的。白蚁和蛆虫相互竞争地把小男孩的肉全部清理干净了。”[22]这一死亡场景是结果式的描写,但是它的冲击力比直接描写男孩垂死的挣扎更让人揪心。
在贝西·黑德的笔下,秃鹫、白蚁和蛆虫得到非常客观公正的描写,它们虽然不讨人喜欢,但是它们在自然界的功能和存在的意义得以彰显,这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体现。人们通过秃鹫、白蚁和蛆虫来判断事态的发展,它们既是自然的信使,也是自然的净化者。人与动物在此意义上是完全平等的。医生从男孩死亡的姿势上判断他死于营养不良,很多送到医院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孩子都是以这个姿势离开人世的。伊萨卡的营养不良早有其他症状,他怕冷、发烧、咯血,这是波琳娜早就知道的,但是她没想到这是肺结核,贫穷甚至限制了她应该送孩子去医院看病的念头。
旱灾造成儿童营养不良和高致死率是近年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和世界银行非洲国际水域的合作项目(The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in Africa)[23]都特别关注的一点,各种食物救济和福利会首先考虑发放给5岁以下和学龄儿童。但是在1950年代,这些组织和机构尚无出现,儿童不仅没有得到特殊保护和关照,反而成为旱灾的主要牺牲品。伊萨克是旱灾的直接受害者,还有一些孩子成了求雨祭祀品,他们的死亡是愚昧落后信仰的产物,有深厚的传统根基,还有巨大的心理因素。贝西·黑德在《寻找雨神》中讲述了一个家庭杀死两个幼女祭祀雨神的故事,故事短小,但令人掩卷长思。
巫术在博茨瓦纳有悠久的传统,贝西·黑德在多部作品中对此予以批判。在短篇小说《巫术》(Witchcraft, 1975)中,贝西·黑德指出,这是一种出于嫉妒而进行的人伤害人的恶意活动,通过术士的草药、咒语、咒符等得以实现。为避免被别人伤害,人们也求助术士,在自家房前屋后撒上草药、护身符等。[24]最邪恶的做法是“祭仪谋杀”(ritual murder),凶手多是有权势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会杀死女童,食用她们的肉,并认为某些部位具有特别功效。卡马三世早在1875年任酋长职位后就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案,废除传统习俗中杀人祭祀的做法,包括求雨仪式,[25]但是很多传统习俗至今仍然存在。博茨瓦纳首位女性大法官尤妮蒂·道(Unit Dow)的小说《无辜者的呐喊》(TheScreamoftheInnocent, 2002)在真实案件的基础上,重写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祭仪谋杀案,揭露和批判了这一陋习,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达到诗学正义,呼吁国际社会舆论介入,促使博茨瓦纳司法改进。[26]但是在《寻找雨神》中,贝西·黑德没有一味地谴责“祭仪谋杀”,而是刻画了旱灾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并指出单一的法律惩罚无法彻底改变此习俗。
贝西·黑德在《寻找雨神》写道,干旱第7年夏初,空气中弥漫着悲剧,一些男人熬不下去了,径直走出家门,吊死在树上。连续两年,靠土地为生的人们种地一无所获,“只有江湖术士、咒术师和巫医赚了一笔钱,因为人们总在绝望中求助于他们,迫切希望用护身符和药草擦擦犁,就能让庄稼生长,雨水降落。”[27]这句话说明干旱使人们感到越来越无能为力,从而驱使越来越多的人求助巫术,这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小说随后聚焦莫科布亚(Mokgobjia)老人一家。老人已经70多岁,和小儿子、儿媳妇及其妹妹、两个小孙女生活在一起。从第一滴雨飘下,一家6口就赶到农田耕好地,坐等下雨播种。
博茨瓦纳的农业完全依赖降雨,没有充分的降雨,种子就不能发芽。人们满怀希望地看到雨云聚集,但是连续7年都没有盼到畅快淋漓的大雨。在此过程中牲畜卖光换取食物,而食物也已吃光,女人们无计可施,在夜里号哭。女人的哭声如鞭子抽打男人的心。孩子们不明白事态的严重,仍在玩过家家游戏。莫科布亚老人想起古老的求雨仪式,和儿子商议,杀死了两个幼女,把她们尸体切碎撒在地里,但是雨神并没有如期而至。一家人沮丧地回到村庄后,人们发现两个孩子不见了,报了警。莫科布亚和儿子被判处死刑。“法庭上不接受任何关于压力、饥饿、精神崩溃微妙作用的说法,但是靠农作物为生的人都知道,在他们心中,也就是一念之差使他们免遭莫科布亚家的相同命运。他们也会为求雨杀死什么东西的。”[28]小说以此句结束,看似超然的表述方式,实则蕴含了深刻的生态反思:要避免这样的悲剧,人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自然,读懂自然,寻找科学有效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干旱。
4 女性与现代生态农业
丹麦女经济学家伊斯特·博赛洛普(Ester Boserup)在《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Woman’sRoleinEconomicDevelopment, 1970)中指出,非洲妇女在农业生产和食物采集中承担了重要作用,因为殖民主义改变了非洲男性参与农业生产的传统,使他们变成西方人眼中的“懒惰的非洲男人”[29]这一刻板形象。伊斯特·博赛洛普的著作一经出版,妇女发展问题便引起了世界广泛的关注,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非洲妇女发展问题并没有多大的改善。[30]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凯伦·沃伦(Karen Warren)指出,非洲妇女生产了百分之七十的非洲粮食,但是她们很多人都没有拖拉机和耕牛,甚至没有犁。[31]非洲妇女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但是她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源极度匮乏,在父权统治下,她们还被限定在严格划分的社会性别空间,所能获得的资源和帮助受到更多的制约。
贝西·黑德在《雨云聚集之时》中深入探讨了妇女与农业发展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方案。波琳娜热情开朗,性格泼辣,乐于尝试新事物,具有领导力。通过迪诺雷戈(Dinorego),波琳娜了解到吉尔伯特种植经济作物土耳其烟草的计划,并愿意带头来做。在波琳娜的引领下,妇女们陆续都加入了烟草合作社,种烟草,搭建烟草处理和晒干棚架,学习烟草处理技术,烟叶直接供给新建的卷烟厂,一体化的生产和销售链建立起来。妇女们的成功,她们的丈夫看在眼里,随时准备加入更大规模的烟草种植项目。
吉尔伯特的烟草项目是在博茨瓦纳生态条件基础上发展的现代生态农业。经过几年的观察研究,他总结出博茨瓦纳发展农业的四大优势:第一,灌溉农业是最可控的农业,通过打深井、修水库和集雨水窖,能解决用水问题;第二,沙质土壤最适合种植土豆和烟草等喜旱作物;第三,这里的土壤非常肥沃;第四,这里的病虫害很少。这些科学分析和技术应用得到妇女的认可,并通过试验得到证明,体现了贝西·黑德对女性和现代生态农业的信心。
贝西·黑德在《权力之问》中更详细地描绘了博茨瓦纳妇女在菜园项目中的成功试验。蔬菜和水果在博茨瓦纳难以种植,这也吸引了国际上很多农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加入英国的国际志愿者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 IVS)、美国的和平队(Peace Corps)等志愿者组织,来到博茨瓦纳进行科学试验。《权力之问》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从南非流亡到博茨瓦纳加入丹麦政府资金支持的合作社菜园部的项目,她和莫塔本中学的学生一起,在丹麦农业专家贡纳(Gunner)的指导下种植蔬菜。伊丽莎白到菜园第一天,用笔记本记下了当地学生“小男孩”展示给她看的滴灌系统:
每个苗圃中央都铺设了长长的带孔水管,水从孔中喷出,像一个个微型的瀑布,形成一个连续的溪流。水管纵横交错,像个迷宫,把整个菜园的溪流和溪流都连在一起。一打开中央龙头,整个菜园就能全天自动浇灌了。[32]
滴灌系统很好地解决了博茨瓦纳地表干旱的问题。这项目前在全球干旱地区推广的灌溉做法,在当时的博茨瓦纳确实是创新型的尝试。贡纳还把菜园设计成了一个供人观赏之地,1条中央大道和40条边道穿行在狭长的菜地里,便于人们行走和观赏蔬菜。菜园变成了美丽的风景,这是干旱地区生态良性发展的喜人景象。
在解决灌溉问题的基础上,找到更适合此地生态的优良种子和掌握作物轮作规律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在这个菜园里,伊丽莎白第一次见到早熟巨型鼓状卷心菜。通过聪明勤奋的“小男孩”的传授,伊丽莎白了解了一套种植蔬菜的技术和知识:育苗、间苗、移植、施肥、保墒、通风、护根等等。这里的作物轮作规律是:先种卷心菜、生菜或菠菜等叶类作物,豆角和豌豆等豆类作物紧随,然后是甜菜根、胡萝卜或白萝卜等块根作物,再种西红柿、土豆或洋葱等。很快受过良好教育的伊丽莎白就成了当地妇女们的导师,她们一起创造了菜园奇迹。她们通过移植培育好的蔬菜幼苗,“卷心菜、西红柿、花椰菜和辣椒仿佛从天而降,闪闪发光的绿叶在炙热中生长。它们将使从约翰内斯堡订购半腐烂的绿色蔬菜的事成为历史。”[33]博茨瓦纳的蔬菜多依赖从南非进口,菜园项目的成功让当地人吃到自产的新鲜蔬菜,无形中又汇聚了一种对抗南非种族隔离制的力量。
伊丽莎白自家的菜园成了她的试验地,她种植的烟草、西红柿、西兰花、花生等长势喜人,不但令路人驻足观赏,而且还把自己得到的国外的种子拿给她试种。农场经理英国人格雷厄姆(Grahame)给了伊丽莎白一些灯笼果种子,告诉她这种浆果最适合做果酱。伊丽莎白从未见过这种植物,没想到它适合在此生长:
起初,奇迹发生在伊丽莎白的院子里。她种下了50棵幼苗。在3个月的时间里,它们长成了2英尺高的灌木。一天,当她穿过花园时,注意到灌木丛下的地上落了一层又一层的棕色的灯笼果外皮。她与凯诺西一起,收获了一大篮灯笼果,还有这些棕色、金黄色、绿色果实带来的如天堂般闪亮的秋色。[34]
灯笼果是茄科酸浆属多年生草本,耐高温,在沙质土壤易于生长。果实被灯笼形的绿色外皮包裹着,躲在叶子中间不易被察觉,但是果实成熟时,外皮变成浅棕色,半透明,可爱的样子引人注目。剥开外皮,露出闪亮的红色或黄色的圆形浆果,酸甜可口,可直接食用,还可作果酱。伊丽莎白的灯笼果果实和果酱让地处沙漠边缘的人大开眼界,人们争相抢购。这是伊丽莎白尝试现代生态农业的奇迹。
贝西·黑德在作品中表达了女性对现代生态农业的接受,并通过积极实践推动了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女性和现代生态农业形成互惠关系。朱丽安娜·恩法-阿本伊(Juliana Nfah-Abbenyi)指出,在非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只有把传统/当地的认知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才能最好地保证生产,也保护环境。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和所谓的“进步和文明”[35]正将环境恶化和人类生存推向极限。除非“进步和文明”也意味着人们学会将本地和外来的认知方式积极地结合在一起,否则他们的生存仍将是难以预料的。
5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非洲梦想
法国作家弗朗索瓦丝·德奥博纳(Françoise d’Eaubonne)在《女权主义或死亡》(Leféminismeoulamort, 1974)中指出,农业和生育带来了世界财富和人口的大幅增长,而财富与人口增长迅速的原因是父权制对土地肥力和女性受孕的征服,而人口膨胀与资源枯竭进而成为威胁人类的两个生态性灾难。[36]在《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异》(Écologieetféminisme.Révolutionoumutation? , 1978)中,德奥博纳倡导女性为主体的生态革命,并提出“变异”之说:变异包含真正、全面的革命,出自女性的主观性,是女性觉醒的根本,是对意识的全面唤醒。[37]只有唤醒全体人类意识才能构建彻底的革命计划。德奥博纳进一步指出,女性在这场变异的全面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妇女是斗争的主体。首先,作为人类成员,女性和男性一同受到生态威胁;其次,作为生育者,女性是两性中唯一能够接受、拒绝、放缓或者加速人类繁衍的性别人群。[38]德奥博纳呼唤女性和男性以全新的平等关系建构一个理想社会,共同解决生态难题。
贝西·黑德在《雨云聚集之时》中描绘的农业合作社,即是一种以女性为主体解决生存和生态问题的理想社会,但是合作社概念对于非洲特权阶层来说是一种威胁。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是“共产主义者”[39]的,无特权而言,因此特权阶层必定要设法阻止合作社的发展和成功。小说中,波琳娜带领全村妇女种植烟草,令小酋长马腾葛(Matenge)耿耿于怀。在合作社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他总是说这不行,那也不行,并以阻挠为乐。7年大旱中,他提出解决水源的方案是让百姓西迁,但是百姓知道西边是狮子的领地,有人就被狮子吃掉了,无人愿意去送死。波琳娜未能及时汇报她儿子的死讯,被小酋长抓住把柄,要置她于死地。波琳娜再次面临人生危机。无论是她丈夫的死亡,儿子的死亡,还是她自己面临的死亡,都充分说明非洲女性和自然一起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是极其深重的。
《权力之问》中的伊丽莎白遭受了更多的压迫和剥削。虽然逃离南非,但是南非种族隔离制下非人的生活经历一直出现在她的梦魇里,博茨瓦纳陌生的环境、语言障碍和离群索居的生活,让她孤立无助。在与幻象人物塞娄(Sello)和丹(Dan)的对话中,伊丽莎白看清了人类苦难历史的根源是权力的滥用和对权力的狂热,这对任何国家、民族、种族来说都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尽管摆脱了殖民统治,但是黑人权力阶层对权力的滥用和对权力的狂热带给人民的是同样的灾难。伊丽莎白在校长的胁迫下离开学校,失去了工作,只能求助于难民和国际志愿者组织,加入菜园项目。土地和当地百姓把伊丽莎白从精神崩溃的状态挽救回来。菜园项目中,人对土地的了解和关爱得到土地的慷慨回赠,菜园变成美丽的风景,人成为风景的创造者、呵护者和享受者。
人和土地形成一种生命共同体,这是贝西·黑德描绘的乌托邦,是她的非洲梦想。受压迫的波琳娜和伊丽莎白最终都因和土地以及百姓的亲密关系而得到解救。在《雨云聚集之时》中,以土地为生的百姓失去了自己的牛群,所有的生存希望寄托在波琳娜带领妇女种的烟草上,丰收在望,小酋长却让波琳娜到村法庭来,百姓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子中心小酋长豪宅门前的村法庭支持波琳娜:
今天他们想跟他见个面,他们的牛都死了,而他的牛在北部边境却很安全,那有一条川流不息的河,那里的草好,含盐分,绿油油的。他们想看看这个拥有一切特权的人,在这个2年好雨,7年干旱的国家,他没有挨过一天饿。……他们想让他知道他们不求他的雪佛兰轿车或豪宅。……他们只想搞好自己的生活……霍莱马·姆米迪的人民不可能永远被猎杀、追捕、驱逐和迫害。[40]
小酋长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他知道自己在干旱之年干了多少邪恶的事情,被逼上绝路的百姓团结起来的力量吓破了小酋长的胆,他在自家豪宅上吊自杀了。
贝西·黑德以此方式解决小说的冲突,虽然大快人心,但是也难免有“简单化、浪漫化倾向”的嫌疑。其实贝西·黑德的简单化和浪漫化是建立在善良和对人性力量的信任基础上的,小酋长的自杀说明他还具有人性和良知,知道承担自身邪恶的后果。更重要的是,贝西·黑德相信普通人的力量,相信只要大家团结如一个人,那力量就是无敌的。这也是贝西·黑德在《权力之问》中的结论:人民的力量是最强的力量,最高的权力。
贝西·黑德笔下以女性为主体,凝聚大众,通过科学的方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和自然是“双向生成的”。[41]人和自然是不可分离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相互依赖性:“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42]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也是每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梦想。
在《雨云聚集之时》中,贝西·黑德描绘的生态农业合作社寄托着普通民众同样的非洲梦想,他们包括厌倦了英国中上层阶级死板虚伪生活的吉尔伯特,逃离南非种族隔离制的马克哈亚,敢于尝试新事物的波琳娜,饱经人生磨难而获得丰富人生经验和智慧的迪诺雷戈和米利皮迪老人,还有全村渴望美好生活的百姓。他们的梦想是在生态农牧业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富裕生活:
他喜欢这个想法:未来霍莱马·姆米迪全村都是百万富翁。这和他自己关于非洲的梦想融为一体,因为只有非洲在未来成为百万富翁的大陆,才能弥补数百年来非洲人遭受的恫吓、仇恨、羞辱,还有全世界的嘲笑。加强合作和分享财富的公共发展体系比狗咬狗的政策、接管投标和大金融霸权要好得多。[43]
贝西·黑德在1960年代借助马克哈亚表达的非洲梦想并非完全是乌托邦,如今博茨瓦纳已经发展成非洲中等收入的国家。当代博茨瓦纳的经济发展中钻石经济和旅游业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些不是贝西·黑德所能够预见的,但是消除贫富差距,通过保护生态环境而获得红利,使百姓过上衣丰食足、尊严体面的生活是符合贝西·黑德的理想期望的。
博茨瓦纳在1967年发现了丰富的钻石矿,1980年代后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从独立初期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成非洲的中等收入国家。艾伦·希尔博姆(Ellen Hillbom)和尤塔·博尔特(Jutta Bolt)指出,钻石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传统农牧业造成的贫富不均,因为传统农牧业中优良的自然资源如水和肥沃的牧场都掌握在社会精英如酋长及其亲属手中。[44]这也正是贝西·黑德的作品所批判的。博茨瓦纳政府非常理性地认识到单纯依靠钻石不足以保持长久的经济发展,而积极寻找多种发展之途,旅游业成为首选。博茨瓦纳享有丰富多样的生物,被认为是地球上野生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奥卡万戈三角洲(Okavango Delta)、乔贝国家公园(Chobe National Park)、卡马犀牛保护区(The Khama Rhino Sanctuary)是世界级野生动物旅游点。为保护博茨瓦纳的野生动物,尤其是大象和犀牛,1987年博茨瓦纳通过公投决定由国防部承担保护野生动物的任务。在后殖民时代,人与动物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是实现非洲梦想的基础。
综上所述,贝西·黑德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生态观是建立在她切身的生活经验基础上的,面对博茨瓦纳荒凉贫瘠的生态环境,她没有被吓到、退缩或逃离,反而积极投身到对生态环境的研究和改造中。通过对动植物的细致观察,她敏锐地感受到博茨瓦纳乡村荒凉贫瘠风景中潜藏的强大生命力,发现部落传统迁徙生活方式和殖民统治对土地和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是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她和女性为主的当地百姓一起加入合作社,在农业科学家的指导下,从事土地改良和恢复工作,发展现代生态农牧业,目睹了很多生态奇迹的发生,得到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但是这一切并非一帆风顺,生态保护和乌托邦性质的合作社对传统部落土地制度、特权阶层、传统社会性别空间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气候变化和旱灾驱使底层百姓求助巫术。这些问题说明生态恶化是受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政治制度、经济利益、宗教信仰等多方因素交织驱动的人类行为的后果。贝西·黑德通过人与土地的相互关爱和呵护,表达了遭受破坏的土地和受创伤的人之间的相互治愈,人与土地上的万物由此获得新的生命,这是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体现。贝西·黑德通过作品表达了她深切的非洲梦想,这一梦想在博茨瓦纳今日的生态环境保护中仍然得到了积极回应。
——诗人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