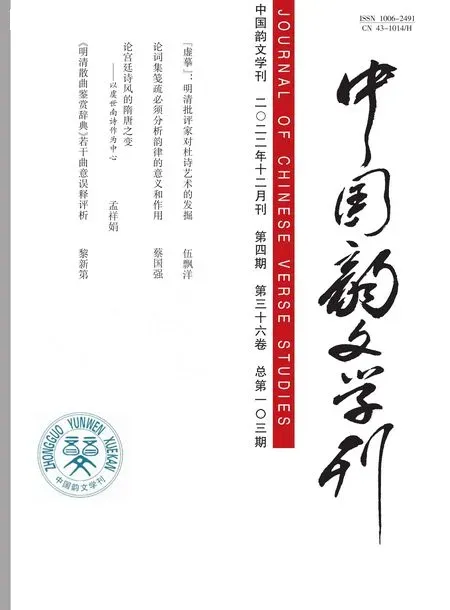唐宋贬谪文化语境与送人流贬诗的嬗变
王 莉
(长沙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P699)那么,这类将迁谪与离别两种题材加以融贯的送人流贬类送别诗,又有着怎样的艺术内涵呢?学界关于唐宋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间的互动研究,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关于唐宋贬谪文化与文学的代表性成果,有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唐宋贬谪诗的发展与嬗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还有沈松勤《士人贬谪与文学创作:宋神宗至高宗五朝文坛新取向》(《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宋代士人贬谪与文学创作》(《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5期),吴增辉《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中华书局2019年版)等。且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中第六编《唐五代逐臣别诗研究》从唐五代贬谪文化语境出发,透视了唐五代逐臣别诗的回归情结、意象选择、抒情方式等方面的艺术表现[2](P497-541),但尚缺乏系统从唐宋贬谪文化演进来审视送人流贬诗的嬗变研究。缘此,我们可循着唐宋变革命题,截取由唐至北宋的贬谪文化语境这个断面,以唐宋士大夫阶层结构、贬谪心态、社会风尚、诗学思想等与贬谪制度演进相互作用为路径,剖析其对送人流贬诗的命辞构思、风格形式及表达策略的影响。
一 贬谪文化演进与逐臣别诗的抒情方式
由于流贬“意味着一种人格的蹂躏和自由的扼杀,又标志着一种沉重的忧患和高层次的生命体验”(2)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中《导论:从执着到超越——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论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那么,遭贬者这种身处逆境、畏途的境遇,诗人该如何去疏解被送者的苦闷、忧恐呢?同样,倘若抒情主体为流贬之人,在他的留别诗作中又会怎样宣泄被贬的情感呢?
宋人周辉《清波杂志》卷四“逐客”条云:“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3]卷四(P138)这里所说的放臣逐客的“酸楚”之言,在唐代流贬诗人的留别诗中表现尤为显著。不管送别双方关系如何,送行之人的境遇、身份等有何不同,在他们的诗作中多弥漫着痛苦、焦灼、忧愤情绪。如宋之问神龙元年(705)贬泷州参军时,留别其舍弟云:“强饮离前酒,终伤别后神。”[4](P420)同时,他自越州长史流钦州途中,留别越州长史亦云:“依棹望兹川,销魂独黯然。”[4]卷三(P539)“强饮”“伤神”“黯然”等语辞,正是诗人被贬遭流所经受的悲痛、惨怆的直接剖白。再者,就连方外僧人法琳在被敕迁蜀中时,其写给毛明素的留别诗中,亦云“叔夜嗟幽愤,陈思苦责躬”[5](P638),流露出忧愤、自怨伤嗟之感。逮至中晚唐,朝廷内部党派斗争、宦官专权加剧的局面,不仅使得贬谪士人增多,对遭贬者的打击亦更为惨重。因此,在中唐遭黜诗人的留别诗中,既咀嚼着宦海的浮沉,又抒发着直道被黜的哀怨与悲愁。此中,堪称经典者,乃是元和十年(815)刘禹锡、柳宗元二人同被贬至岭南之际所作的唱和赠别诗。以下,试举二人在衡阳相别的唱和诗论之: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6](P291)
(柳宗元《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7](P553)
(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
刘柳二人因参与王叔文的永贞革新运动,遭到宦官保守派的反攻,二人同在惩处流贬范围内。柳诗先言二人同被贬在外十余年形容憔悴,又同被召回京,岂料数月间就被贬岭外耶?首联以句意的转折,营造出一种宦海浮沉始料不及之感;颔联想象经行地“故道”的“风烟在”与“遗墟”的“草树平”,岭外行之凄凉逗引着无数眼泪;颈联,诗人反观自醒并劝诫刘禹锡谨慎韬晦;尾联,乃化用李陵《别苏武》中“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二句,把穷途的深沉郁悒放笔直书而出。近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二评柳宗元此诗云:“慷慨凄惋,情景俱穷,直堪陨泪。”[6](P2800)再来看刘禹锡酬别柳宗元之作:其诗首联的立意与柳诗相同,皆是追忆二人官场遭际;颔联上句化用黄霸因受重用再授颍州事,以之与自己贬窜再授连州事形成反跌,下句则以柳下惠三黜而不改直道事人典实,以比柳宗元;颈联,诗人将视域转向分别地的回雁啼猿,南行贬人遇回北之雁、悲啼之猿声,不觉怆然泪下;尾联,转写将要各赴贬所的分别双方,彼此相望相惜相怜。刘柳二诗皆从涵宦海风波写来,并将之与荒凉、悲凄之景物描写相绾合,使得流人的哀伤、怨嗟之情跃然纸上。
不仅流贬之人的留别诗作充盈着凄切之情辞,唐代诗人赠别贬谪之人的诗作亦大抵如此。举如以下表达:“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8](P1556);“南过猿声一逐臣,回看秋草泪沾巾”(韩翃《送客贬五溪》)[8](P2751);“肠断腹非苦,书传写岂能”(林氏《送男左贬诗》)[8](P9078)。唐朝诗人常用“垂泪”“愁猿”“断肠”等悲苦意象,把流贬之人的凄惨境地意象化,进而以情景交融、情景俱穷的方式与远行者共感交鸣。
同时,唐代诗人多善于借描绘流贬者的凄惨细节、境地,来抒发对被送者的怜悯。如司空曙《送流人》言“童稚留荒宅,图书托故人”[8](P3309),刻画流人贬窜前嘱托事宜的窘迫之境,凄楚之情溢于言表。又张籍《送流人》一诗在营造出“黄云”蔽日的愁绝之景后,转而描绘被送者没家资充戍边塞的情景,刻画其冒雪修军墙、取冰为饮水的细节,于情景交融中凸显窜逐者的惨戚。再如杜甫《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一诗则通过刻画行人不仅“中兴时”被“严谴”,又临老陷贼中罹罪的双重悲境,将远谪人的凄惨和盘托出,寄寓着深广的同情。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杜臆》评此中二句言:“万里伤心,正为严谴之故。百年垂死,乃在中兴之时。严谴、中兴四字,含无限痛楚。”[9](P425)总之,唐人送人流贬诗多辞直而意哀之作,但因其把胸中对贬窜之情愁放笔直书,故又不失真切感人之处。
而到了北宋,儒学的复兴及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使得士大夫更重视心性观照与志节持守。文人士大夫普遍尚风节、道义,不仅对仕途贬黜胸次洒然,而且对正道直行而遭贬反引以为荣。(3)唐宋士大夫贬谪心态之变,参钱建壮、尚永亮《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及其文学影响》,周裕锴编《第六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论文集》,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50—58页。如北宋初期,多次被贬的王禹偁《三黜赋》言:“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10](P238)曾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更留下“三黜三光”的佳话。熙宁新政时期,吕陶为因忤王安石而被外放的吕诲作送行诗云:“进非为私谋,退亦为道隐。顾彼荣与辱,于吾不加损。”[11](P313)以上,王禹偁、范仲淹、吕诲皆有卫道的果敢与坚毅。缘此,与唐人逐臣别诗中多凄厉衰飒相左,北宋流人别诗中则较少哭穷途之作。如元丰三年(1080)苏辙赴筠州之贬,苏轼相送三十里,苏辙作《将还江州子瞻相送至刘郎洑王生家饮别》诗留别有云:“夺官正无赖,生事应且尔。卜居请连屋,扣户容屣履。人生定何为,食足真已矣。”[12](P226)与刘柳二人赴贬所别诗中的哀楚愤懑相比,苏辙对自己的被贬虽有无奈之感,但总体是超脱、放达自适的,“食足”而“扣户”已是人生乐事。又元符二年(1099)晁补之赴上饶之谪留别诗作《己酉六月赴上饶之谪醇臣以诗送行次韵留别》,许总《宋诗史》将之阐释道:“此诗虽写于赴谪之时,但由于‘思深志不悲’的内在主观精神的作用,漫长的谪贬途程变成‘双履步香炉’‘一帆飞彭蠡’般的轻松快捷,黯然的仕宦前途变成‘烟霞满衣’般的璀璨晶莹,已明晰可见其主体的高扬与心灵的涵盖。”[13](P413)再如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除名编管宜州,作《十二月十九日夜中发鄂渚晓泊汉阳亲旧载酒追送聊为短句》一诗留别汉阳亲旧。其诗从闻命赴贬不敢怠慢耽搁写来,落笔汉阳亲旧的“载酒追送”,结之以“故人情”的温暖及己身的愧疚。元人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三评此诗言:“此诗亦无一毫不满之意。”[14](P1547)综上,苏辙、晁补之、黄庭坚赴谪之留别诗中,皆可见诗人“不以贬谪为意”,贵自持、自适的主体精神。
与唐代送人流贬诗中多以哀景愁语摹写逐臣的惨淡相比,北宋诗人则多从士大夫道义坚守角度,褒奖其正道直行的高举,砥砺其超越遭黜被贬的悲恸焦虑。如宋初王禹偁送别因为越王爱姬撰墓志得罪的任户曹言:“身落蛮夷人共惜,罪因文学自为荣。”[15](P745)认为人臣因文学得罪实属光荣之事。端拱二年(989),田锡因直言不讳而出知陈州,王禹偁为其作送行诗云:“茜旆出过应曜墓,棠阴潜上伏牺坛。”[15](P701)则从陈州淮阴墓、伏羲陵立意,彰表田锡秉道直言上谏的光耀胜过开国功臣淮阴侯,激励他前去外放之地施行惠政。皇祐元年(1049),御史唐介因弹劾宰相文彦博阴结贵妃而南迁英州,朝野士人王令、李师中、徐九思、谢景初等皆有诗相送,并对唐介作为台谏官不顾性命之忧而勇于弹劾执政者的行为大加旌赏。王令《送唐介》诗开头即云“以谏得罪者为谁?四海多作唐介诗”,歌颂被送者的直谏精神,结尾处又以“后世选懦禄位徒”的尸位素餐与唐介以死殉道相比照,高唱道:“伟哉介也已不朽,日月为字天为碑。寄诗琐琐媒孽子,介纵蹈死吾何悲!”[16](P130-131)整首诗歌,于慷慨激昂中透露出诗人对唐介高风亮节的钦佩。李师中送唐介诗,亦从其“孤忠”“独立敢言”写来,凸显卫道之士的“高名”“重于山”,让其“并游英俊”不得不汗颜。而徐九思《送唐介谪英州》则采用正话反说的形式,对“忠党”窜逐而奸邪小人却得“安荣”政局加以鞭挞,既为唐介树名声、彰节义,更为其“特地发冤声”。谢景初更是以五首送别组诗,假借隐喻、反讽等手法表达了直臣被贬的愤慨,反复申述了对唐介之行的赞赏、慕顾。
综上,伴随着北宋士人贬谪心态的变化及其崇尚气节道义的风尚,不仅流贬者的留别诗作中多无自伤自嗟之语,而送流贬之人的诗作亦多表彰直言卫道、忠肝义胆的风节,并对受构陷、受攻讦的忠臣义士以气节、道义加以砥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北宋士人在其他文体中亦有身遭流贬的苦闷、幽怨,但因送别诗公共交际及应酬属性,使得诗人必须迎合矫厉尚风节的士风。因此,与唐代送人流贬诗的情辞凄切不同,北宋送流贬诗由于主体精神高扬及立意高蹈,多呈现出旷达渊雅的风格。
二 对贬谪遭际的超越:北宋送人流贬诗内容的丰衍
以上,我们主要从贬谪心态演变与抒情方式之关系,探讨了由唐至北宋送人流贬诗作的立意措辞之变。那么,从创作主体、写作生态与诗歌内容、形式关系而言,由唐至北宋的送人流贬诗歌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首先,从唐宋士大夫阶层构成而言,北宋基本已经进入科举士大夫时代,因为他们多来自社会中下层且需要巩固自身地位,决定了北宋士大夫要格外关注国家政治与社会人民。[17](P27)与此同时,北宋儒学的复兴,使得儒家人本主义价值观备受重视,而欧阳修以人心所向解释先王之道之举,则“重申了普通百姓的重要性”。[18](P378)因此,与唐代送人流贬诗的视域多落脚贬谪之地的荒芜、野蛮相比,宋人则更多会设想被谪者在贬地广阔的生活:既能抚育百姓施善政,又能在贬地山水胜迹中诗酒优游。唐人送人南贬之际,多云:“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张籍《送南迁客》)[8](P4317);“天涯浮瘴水,岭外向潘州”(李明远《送韦觐谪潘州》)[8](P6594);“瘴杂交州雨,犀揩马援碑”(贯休《送谏官南迁》)[8](P9422)。在唐人笔下,南方的瘴疠、阴雨是令人恐惧的,南方的骑象、用银习俗是蛮州的殊俗。而殊方异俗在北宋诗人笔下已不再是主要描述对象,其功用也不再是凸显荒远。在北宋诗人笔下,贬谪之地多是可居处,更是可以有所作为、施展抱负的。如梅尧臣送逐客王胜之,云“金锤一报恩,义烈垂竹素”[19](P254),劝其在贬地请缨报国、有利于国事。淳化二年(991),田锡因秉笔直谏落职出守陈州,王禹偁作《和陈州田舍人留别》五首酬赠。这组赠行组诗中,贬地陈州不仅“风物暄妍”且“土俗淳”,田锡在那里不仅可“尝新笋”“听琴鹤”“披鹤氅”“步龙鳞”,还可步棠阴、劝农耕、“颁条道”、“慰陈民”。淳化四年(993)寇准因被知院张逊诬陷,而被罢知青州。其时,王禹偁《送寇谏议赴青州》赠行云:“归梦寻温树,行尘动福星。上仪三道判,排设十间厅。风静衙门戟,霜寒郡阁铃。看山楼号白,封社土分青。花好诗难惜,梨甘酒易醒。”[15](P746)面对坐事被罢的寇准,王禹偁先称赞其“循良”“德馨”,继而想象他在贬地居官谨慎、克勤职守的办公生活,又由衙门的“风静”、郡阁的“霜寒”凸显“循良”的吏治之才,因可无为而治寇准亦可“看山”、“封社”、赏花饮酒、吟诗遨游。青州的山水物产、风俗习惯,不再是唐人笔下荒芜、蛮野的“贬地”形象,而成了可“诗意的栖居”之地;青州的谪官,不再是酸楚情状,而是平反狱讼、厘革庶务的循吏。
以上皆是北宋初期送人流贬诗作,这里再举北宋中期元祐朝士送别外放朝官的诗作论之。元祐二年(1087),张商英自开封府推官外放为河东提刑,朝士范祖禹、苏轼、黄庭坚、张耒等以“登山临水送将归”分韵赋诗,孔武仲与苏轼又作次韵送别诗,孔平仲亦有诗相赠。范祖禹《席上分韵送天觉使河东以登山临水送将归为韵分得临字》从河东为边境立论,希望张商英“慎所临”、断狱公允;苏轼《次韵孔常父送张天觉河东提刑》《送张天觉得山字》两诗,期盼张商英到任后能让疲兵、馁民得以休养;张耒《送张天觉使河东席上分题得将字》则从河东荒情、废耕桑写来,嘱咐被送者督促百姓开垦土地,广植庄稼;孔武仲《送天觉使河东》则以河东故吏范滂比况张商英,希冀他去严整疾恶、抑制盗贼。
综上,就送人流贬诗歌中贬地视域而言,唐代诗人笔下多是荒蛮的简略式、单一式呈现,而至北宋,贬地的视域已扩充至谪官如何体认、振兴地方。
其次,从贬谪环境与诗歌内容而言,北宋党争不仅更为激烈,且多交替执政,这种起复叙用几率的提升,促使北宋送人流贬诗歌较唐代多回朝期待。关于唐人送流人迁客诗的写作范式,清人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卷上总结道:“凡送流人迁客,大概止述其境地之远苦,而不肯多为吉祥祷颂之词,此一定体例,而后人不知也。”[20](P8)唐代诗人多意图状写被贬者的凄惨情状,以真情、哀辞传达同情、怜惜之情,获得情韵效果。虽然唐代亦有少数诗作言及被谪者的还朝,但多从圣恩垂顾、“外力”雪冤立论。如李白《送窦司马贬宜春》结句云“圣朝多雨露,莫厌此行难”[8](P1801),司空曙《送郑明府贬岭南》结束言“莫畏炎方久,年年雨露新”[8](P3320),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尾联云“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8](P2232),以“雨露”譬圣恩降临,祝祷被送贬人被赦起用。又刘长卿《送裴郎中贬吉州》尾联“知己酂侯在,应怜脱粟人”[8](P1486),同时其《送李使君贬连州》颈联“贾谊辞明主,萧何识故侯”[8](P1486),皆是化用萧何追韩信的典故,祝愿被贬行人能得到知己的帮助而蒙囿。
在北宋诗人笔下,被送流人的起复还朝不仅是可期的,更是合乎情理、有理可据的。如王禹偁送别贬为融州司户参军者,便从被送者御试“好科名”写来,结句云“君看咸通十司户,投荒终久是公卿”[15](P745),化用唐朝咸通中被贬“十司户”后终位极人臣典实,期勉同被贬为司户的行人他日亦能以文才被召。孔平仲送别外放的张商英时,乃言:“圣明天子聚群材,下至椽杙犹收拾。况君屡薄青云飞,暂尔低回岂长蛰。”[21](P390)诗人将天子招揽人才与被送者的磊落、清直及曾受重用相勾连,让被外放者相信他的沉沦“低回”只是暂时的。再者,陈师道送别为谏官所论的晁补之时,于诗句“圣世急才常患少”下又自注云“神宗御笔曰治世常患难得人才”[22](P564),通过再三强调当今圣上亟需人才治国,使晁无咎无不被起用之忧。总之,北宋诗人力图以忠臣、能臣与圣明天子的遇合,让逐臣迁客树立他日回朝的信心。综上,就流贬者日后仕途视域而言,唐人则较少论及,即便有所涉及,亦只是简略论之,缺乏因果逻辑。而北宋诗人多则将被送者的才性、履历与朝廷圣明需才相绾合,使得被贬者的回朝祝祷合于情理。
三 贬黜政策与送人流贬诗的表达策略演变
从官员贬黜制度演变而言,唐朝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且渐趋完善,至北宋,伴随着其“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右文政策与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官员管理制度,其罢黜制度的政策、方式、范围等发生了转型。鉴于此,下文拟从贬谪政策、类型变化切入,探析唐宋士大夫面对流贬同侪友朋,其勗勉方式与文本表达策略的演变。
从唐宋贬官特点而言,唐五代由于宦官专权、武人为祸、政权暴力更迭等,造成了“宽严交替、株连面广、贬杀结合、久不量移、文士多逐臣”的惩处格局。同时,就流贬地域而言,也主要集中在岭南道及江南西、东道[23]。在高压、严酷的贬谪环境下,面对生死难卜的友人,唐代诗人或多“直作尽情语、无可奈何语”。如司空曙《送流人》诗首联言:“闻说南中事,悲君重窜身。”[8](P3309)起首便直接道出悲慨之情,而其尾联更是将眼前“好风景”与分别双方“一沾巾”相对,以乐景对哀情状悲恸之深。除了以乐景衬哀情的手法,以哀景写哀情则是唐人送流贬诗歌中常用的手法。举如以下诗句:“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8](P1556);“南过猿声一逐臣,回看秋草泪沾巾”(韩翃《送客贬五溪》)[8](P2751);“零落残红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柳宗元《别舍弟宗一》)[8](P3950)。诗中“暮江”“猿啼”“秋草”“残红”等凄厉之景,正是诗人面对逐臣迁客的悲郁之情的化身。
由于作为唐代流贬集中地域的岭南,其“为‘异域’‘荒服’或者‘遐荒’,几乎已成为当时人的常识。”“以至当时度岭的人往往产生一种‘去国’的情绪。”[24](P317)。故部分唐代诗人着眼于贬地之远苦,传达对友人的忧虑担心。如白居易《送客南迁》一诗,从其自身“曾经身困苦”的南贬经历入手,接着以十二句巨幅铺述南中“秋瘴”“蚊蚋”“水虫”“山鬼”“飓风”等异质文化的惊骇、恐怖,最后以“宜醉不宜醒”劝诫南迁之人,对被送者充满担忧却又无可奈何。再如贾至《送南给事贬崖州》一诗,则从昔日在朝为官情景与如今谪往千里外的崖州相对比,从而逗引出“俱为恸哭”的抒情路径。张籍《送南迁客》有言:“青山无限路,白首不归人。”[8](P4317)临老衰病之人遭逢“无限路”之重窜,于质朴语辞中含无尽哀情。清人李怀民评此联云:“只作尽情语,此真谛,异于世谛。”[20](P25)综上,唐人送人流贬诗多着力刻画贬地的荒蛮,并以此申述悲愁。
除“作尽情语”外,亦有部分唐人或化用汉贾谊贬长沙过湘江吊屈原的典实,或采用放言直陈的形式,传达了对有才者遭贬谪的悲愤。清人赵殿成亦云:“送人迁谪,用贾谊事者多矣,然俱代为悲忿之词。”[25](P192)如刘长卿《送侯中丞流康州》尾联云“北阙九重谁许屈,独看湘水泪沾襟”[8](P1570-1571),暗用贾谊被谗陷而贬长沙事,为“臣道枉”、受“猜谗”而流康州的侯中丞鸣冤屈。又其《送李侍御贬郴州》亦化用贾谊“吊灵均”之典,抒发了“李侍御”不得遇的悲怨。另外,亦有直接为流贬者申述不满、不平的,如以下表达:“忠荩不为明主知,悲来莫向时人说”(钱起《送毕侍御谪居》)[8](P2600);“谪去刑名枉,人间痛惜深”(戎昱《送郑炼师贬辰州》)[8](P3005);“若似承恩好,何如傍主休”(齐己《送迁客》)[8](P9526)。诗人采用或直陈或反诘的方式,态度鲜明地申述被送者的贬谪是君臣不遇、枉法断案。
北宋减少了死刑及带侮辱性惩处,形成了一套带有尊重、礼遇官员的处罚程序。贬黜制度政策的这种变化与北宋诗人重气节的风尚相结合,使得北宋送人流贬诗歌较少情辞凄切者。但新的罢黜方式,如针对官员人身自由的编管、居住、安置等与针对差遣、职事官的对移、落职、置闲散官等处罚,成为北宋朝廷主要运用的手段。(4)本节罢黜制度的梳理,主要参考杨竹旺《宋代文官罢黜制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罢黜方式与类型适用》,浙江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8—62页。不同罢黜类型、不同等级的官员,不仅所受惩罚的毁折、限制等相异,赦宥途径亦稍异。鉴于此,北宋诗人如何跳脱出唐人树立的“作尽情语”书写范式,又该怎样应对贬谪文化演变呢?
与唐人“作尽情语”相较,诗人更倾向于围绕被送者的贬谪事由进行视域推拉,经由将被贬者的仕履、品德、才性与贬谪事件相勾连串接,实现以理遣情的劝慰目的。如司马光送别同年流人云:
得丧互循环,古今昧终始。
百岁落其间,仅与毫芒似。
所以达人心,身外不复纪。
愁来若乱丝,疏解当以理。
昔君关外来,籍籍声华起。
凭案一濡毫,万言俱落纸。
老生窥其文,色若寒灰死。
阁笔不能下,敢有疵瑕指。
或时抵卿相,入门俱倒屣。
阍夫迎受谒,不敢扬眸视。
解褐吏边州,长涂初进跬。
蛟龙得尺水,双骼方嶷嶷。
西羌负德泽,飞镝耸边鄙。
添兵十万余,斗粟无支拟。
州郡走符檄,纵横恣鞭棰。
闾阎浪愁苦,卒食半糠秕。
上官知君才,悉以储粮委。
开仓募平籴,至者车连轨。
严明束吏手,诱谕提民耳。
留谷受金去,若与同侪市。
弦朔未云周,露积丘山比。
曾无转饷劳,坐饱防秋士。
幕府上其功,明诏深嘉美。
为僚登九寺,长人专百里。
聊用报勤劬,未言穷任使。
何期逢怨雠,意外成疮痏。
刺骨舞文法,吹毛出瑕滓。
清霜五月飞,惨烈伤兰芷。
鸾凤失椅梧,飘泊还荆枳。
圣朝方任能,大过尚收齿。
况于济时具,暂然遭诋訾。
宁因青蝇恶,遂取璠玙毁。
良工构明堂,必不遗杞梓。
勉哉益自立,勿为穷衰止。
人生难豫期,神理无终否。
庸知今日忧,不为后日喜。
吾道诚无亏,壈坎安足耻。
关山迤逦长,百剑连天倚。
萦纡结危栈,迥入云星里。
蜀国富嬉游,花繁春酒旨。
莫作吊原文,投之岷江水。[15](P6016)
(司马光《送李汝臣同年谪官导江主簿》)
从诗歌内容与表达形式阐释之,司马光诗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前八句从人生得丧荣辱落笔,既褒奖谪官李汝臣为天地立心,又为其卫道遭黜发愁,并点出“疏解当以理”;第九至第五十句,诗人将视域转回李汝臣被谪前的仕履:从“昔君关外来”起笔,以“老生”“阍夫”的情状凸显其雄文巨笔、器宇轩昂,中经“解褐”边州的大材小用,终在“西羌”用兵之际,因“储粮”“转饷”展现了吏治才干而被升为县令;第五十一至第五十八句,以“何期逢怨雠”过渡到被送者被流黜事由解析,并以隐喻的手法言其受诬陷“成疮痏”;第五十八至第七十四句,则将前文被送者的文才吏治、气度识养与“圣朝方任能”“构明堂”相绾合,并结合时命、性理的解说,以“杞梓”之才终会进用及节义砥砺鼓励其“益自立”;最后八句,悬想被送者的征途,并翻用贾谊于湘江吊屈原之典,诫其过岷江之际不要自伤穷途。总上,面对被黜的同年友人,司马光以“疏解当以理”的写作动机,将被送者的文才吏治、勤劬立心与仕途荣辱、得丧及时命相拼接,排解谪官之人的忧虑,引导其树立起用的希望。
根据贬黜类型、贬者身份的差异,北宋诗人则选用了不同的以理遣情策略。对于那些因文学、直谏、言事而得罪之人,诗人多从君臣道义角度,或赞扬他们的忠直,或为其流落不遇郁郁不平。范尧夫从谏员“谪守蒲津,领漕于蜀,察民重困,不忍以厚敛加之”[11](P352),故左迁和州知州。吕陶作送行诗云:“暮对青蒲侧,朝留赭案前。堪忧逐江海,犹许治蕃宣。此地劳飞挽,何人念瘠捐。壮心摧更激,高节困尤坚。”[11](P353)诗人以散文笔法,铺叙了范尧夫谪守蒲津期间,不改“状心”“高节”,依旧察民之困,护卫百姓的亮节。除正面旌表逐臣迁客的高风亮节外,亦有不少诗人直接抒发了友人遭人迫害的愤懑。如庆历四年(1044),王益柔因参与苏舜钦奏邸会,醉作对时政多有不满的《傲歌》,黜监复州酒。[26](P9634)梅尧臣为其所作送行诗,则翻用贾谊困长沙之典云:“何须文学为,寄语长沙傅。”[19](P254)劝诫王益柔不要效仿贾谊上书言国事,以免遭到当权者的挤构。熙宁三年(1070),刘攽因上书多言新法不便,由馆阁校勘出为泰州通判。苏轼赠行诗有云:“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27](P505)告诫刘攽效仿口不臧否人物的阮嗣宗,不要以“张仪舌”蒙受不白之冤。又程师孟《送虔州通判周茂叔对移永州》云:“会是忠贤流落处,至今兰芷尚萋萋。”[15](P4391)以情景交融的方式表达了忠贤不遇的哀戚。在这里,梅尧臣、苏轼之所以训诫被贬谪之人要谨言慎行,实际上是在讽刺朝廷不容人直言;程师孟言忠贤的迁逐,亦隐晦表达了对执政者的不满。
针对那些由内官出为外官的高层被贬官员,由于他们多是文学高选、位高权重之人,且被起复叙用的概率极高,故诗人倾向于改变叙述立场美化其被贬因由,以勋业重臣关乎邦国社稷之逻辑预祝其早日归朝。如枢密副使寇准出知青州,王禹偁送行诗《送寇谏议赴青州》云:“表海镇峥嵘,枢臣辍禁庭。”[15](P746)言寇准的被外放只是“枢臣”暂时离开朝廷,去镇守兴盛的青州。而王禹偁送别由中书省出牧郡守的田舍人,则云“宛丘分理藉贤明,暂辍词臣抚百城”,言其外黜是圣上借贤明之臣前去抚育百姓;又云“演纶多暇每封章,暂去颁条道更光”[15](P703),言其只是因政务闲暇前去发布律条,从而使得正确的政令得以光扬。孔武仲送别由朝官外放河东的张商英,则从其近臣的身份,将其被黜美化为“新持金节领诸侯”[21](P172),是作为诸侯使臣去统辖地方。
综上所述,唐代送人流贬诗歌由于多情辞凄切之作,故往往能直接刺激作用于人类共通的情感,能“感动激发人意”。但从作品内容与表现形式而言,正是由于唐人多以“眼泪”“猿声”“断肠”等意象来状写流贬之人的悲惨,多“止述其境地之远苦,而不肯多为吉祥祷颂之词”,促使唐代送人流贬诗的视域较为狭窄、单一。同时,对于被送者迁逐原因呈现而言,唐人多避而不谈,即便有所涉及,也只是简要、约略言之。究其缘由,唐代“诛连面广、贬杀结合、久不量移”与多将逐臣流往岭南道及江南西、东道的贬谪环境,使得被惩处官员多处在惊恐畏惧、幽怨苦闷中。面对恐畏的被送者,“尚情韵”的唐人,故或多“作尽情语”“无奈语”,或以直辞发抒愤慨之情。逮至北宋,科举士大夫时代的成型与儒学复兴,使得北宋士大夫更为关心政绩、百姓,更推重风节、道义。这一方面推动了送人流贬诗歌精神风貌转向峭健精深,一方面为诗歌视域扩充了济世忧民、砥砺节义与被贬者好是懿德、清廉仕履等内容。而北宋儒、释、道的融合及理学的兴起,不仅为北宋士人调适贬谪心态作了助力,亦为北宋诗人提供了以时命、性理慰勉被谪行人的渠道。而从北宋贬谪文化与诗歌内容形式来看,其右文政策不仅使得残杀、侮辱迁客的惩处手段大为减少,迫使北宋诗人跳脱出唐人以尽情、书愤的表达策略;其党争的频繁增大了逐臣起用概率,使得北宋送流贬诗较唐代多回朝期待;其主要贬黜手段的变化,亦推动其书写策略转向以理遣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