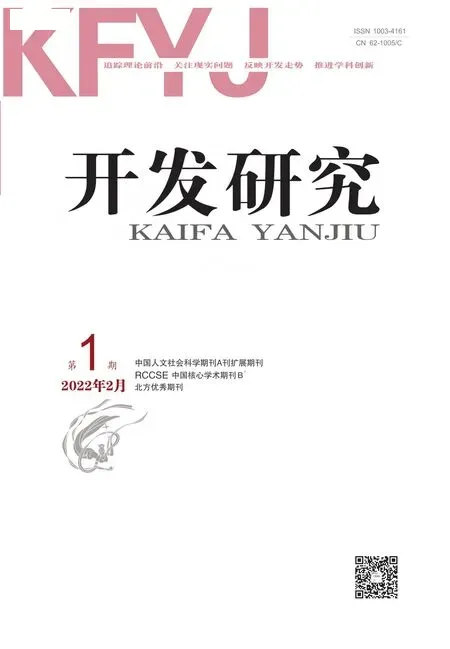基于地理学尺度转换的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安倬霖,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一、引言
(一)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厘清管理思路
在民族复兴、文化强国、旅游发展的背景下,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正式被提出。2019年7月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指出,国家文化公园是“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建立、管理的特殊区域,以保护传承和弘扬具有国家或国际意义的文化资源、文化精神或价值为主要目的,兼具弘扬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爱国教育、科研实践、国际交流、旅游休闲、娱乐体验等文化服务功能”,并明确指出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大方向——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基础工程建设。因此,旨在塑造国家象征、促进全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多功能、公益性的大尺度空间的国家文化公园的模式,是中国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创新性贡献[1]。
这里所说的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2]。两类文化遗产在空间上的复合区域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区范围的确定依据。国家文化公园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文化遗产保护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传承国家历史、弘扬文化和民族精神,过程性目标是以新的管理机制,克服已有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的弊端。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用新的文化设计和组织管理机制保护、活化文化遗产。一方面,文化设计在于挖掘、传承文化遗产之精神价值:国家文化公园串联了不同地域文化圈构建“共同价值载体”,同时通过教育、公共服务、旅游休闲、科研等复合功能,将这种价值引领和共享出去,赢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实现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品牌价值的创建,带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1-3];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的组织管理在于全面协同和虚实结合——全面协同即中央和地方、不同部门、大方向设计和实际保护利用的协同,虚实结合在于划定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和边界,是指文化遗产本体及环境严格保护和管控、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适度发展文化旅游和生态产业三者灵活共存[4-5]。
(二)具有地理属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难点
目前,我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保护有许多难点,所具有地理特征的活化利用与保护难点大致有如下4类。
第一,管理文件政出多级行政区域的部门。“政出多门”一是指管理政策法规出自不同行政区。由于一些文化资源或文化遗产分布范围广,在保护和利用中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政出多门”二是指管理政策出自不同的行政部门,如出自文物部门、旅游部门、城建部门、宣传部门等。政出多门带来一系列保护和利用的问题,如长城地跨多个省级行政区域,在诸如北京段等地段中,长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而在有些省区因为保护资金短缺、保护理念落后,文化资源保护水平良莠不齐,甚至会出现破坏性保护——如辽宁绥中县小河口长城出现了垛口墙被砂浆抹平,原有构件被随意丢弃的情况。因此,线性跨区域的文化遗产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尺度转换地进行保护。通过建立国家公园对全国性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统一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势在必行。这样可以避免管理混乱、不可持续开发的情况。
第二,文化遗产保护区边界难定。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边界定在哪里?尤其是包含多个遗产集群的国家公园的边界定在哪里?确定空间界既是尚需探讨的学术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国家公园的管理实施。仅就我国文物保护而言,现实管理中就有关于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控制区边界划定的批评。以长城为例,因为长城保护沿线涉及资源环境多样,导致长城文化带空间范围边界很难确定,大量与长城相关的历史遗存被“边缘化”和“孤岛化”。此外,人们对文化遗产认知的不断深化也使得文化遗产空间范围划定变成一个动态的过程[6]。
第三,多区域开展文化遗产活化利用难免同质竞争。一些地方在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中出现同质竞争。例如,在旅游形象定位、客源定位市场等方面存在极强的相似性,从而出现旅游恶性竞争、价格战等。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同质化的问题严重阻碍了文化遗产旅游业的发展,久而久之,通过旅游产生的经济收入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提供服务所需的成本。将这些同质竞争的文化遗产联合开发是一种解决同质化竞争比较成功的经验,如炎帝故里的多地开发[7-8]。
第四,文化遗产资源空间分散难以统一。在一些区域内传统文化资源类型多样且空间分散,从而导致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不一。例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由文物部门重点负责管理,但级别较低或未列为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常常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甚至被破坏性开发[9]。文化资源空间分散,偏远地区就成为“冷点地区”[10]。这些散落的文化遗产无法与“热点地区”的历史文化构成一个景观网络[11]。
解决上述4类问题需要地理学家的参与分析和讨论。文化地理学的尺度转换可以成为一个分析工具。这里所定义的尺度转换就是指大区域与小区域文化之间的转换。
二、隐含尺度转换逻辑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一)体现尺度转换的整体保护实践方式
由于存在上述4类文化保护和利用的空间问题,因而有必要依据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思路进行保护。所谓整体性保护,是围绕多个遗产的整体性价值,将单体遗产的保护纳入多个遗产整体保护的框架之中[12]。例如,将具有某种文化联系的历史城镇、文化村落、历史建筑整合在一起保护。1964年公布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下文简称《宪章》)指出:“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但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宪章》将文化遗产与其周边环境作为整体统一保护是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首次尝试[13]。而针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4类空间问题可以看出,许多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价值必须纳入更大尺度(如国家尺度)的空间环境中进行考虑。换言之,就是要将小尺度空间的文化遗产嵌入大尺度空间中去保护——完成文化遗产的升尺度、跨区域关联。目前,世界上对文化遗产的升尺度保护主要分为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两种实践方式。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结合的线性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族群[14]。它既是基于特定历史路径、文化概念、文化现象的综合性遗产类型,同时也是一项旅游合作项目[15]。文化线路最早由欧盟委员会于 1987 年提出,旨在加强旅游业的“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向人们展示欧洲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多个文化遗产是如何拼装在一起的。欧洲的这些文化线路,对人们认识超越国家界限的欧洲具有重要意义,即帮助人们建构出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整体意识[16]。1993年,欧盟第一条文化线路遗产“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Th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Pilgrim Routes)——西班牙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17]。在2005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将“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列为世界遗产的一种类型,与古迹、建筑群、遗址型文化遗产这3种类型并列[18]。关于如何在文化线路中整合各种文化遗产,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出版的《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简称为《文化线路宪章》)给出了很好的解释。《文化线路宪章》认为,文化线路以任何交通线路为基准,它必须有拥有清晰的物理界限、文化活力和历史功能,其构建服务于一个特定的明确界定的目的。文化线路的构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a)它必须产生于并反映人类的相互往来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相互交流;b)它必须在时间上促进受影响文化间的交流,使它们在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上都反映出来;c)它必须要集中在一个与其存在于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相关联的动态系统中”[19]。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另一种跨区域的综合性遗产保护利用方法。它从属于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源于美国环境学家怀特(William H.White)在1950年提出的“绿道(green way)”概念[20]。由此概念衍生出遗产廊道这种大范围的线性遗产保护理念:它是指一定尺度范围内由遗产综合体组成的线性开放空间,具有遗产保护、历史文化、旅游休闲、教育审美、生态维护等功能[21]。这种遗产组合反映了一定社会背景下人类的某种社会活动路径,如迁徙、交通工程、商贸往来等文化——它们构成了遗产廊道的主题,具体可分为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游憩3种类型——由与廊道关系最为密切的关键性遗产来决定[22]。因此,遗产廊道对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不仅仅是多处遗产的组合保护利用,还是由遗产本体向周边环境点—线—面扩展,由绿道、遗产、游步道、解说系统共同构成了一种跨区域的保护与开发平台[23]。与脱胎于欧洲的文化线路相比,遗产廊道并没有过多地强调跨区域的文化认同诉求,其对共同价值的追求也不高。同时,因为其广泛应用于地广人稀的美国国家公园区域,为了串联和保护文化遗产而延伸出来的大量的空间成为遗产廊道的一个重要特征。
仅凭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这两种遗产保护方式是无法完全解决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4类空间问题的。与国家文化公园相比,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虽然都是将文化遗产通过“打包”的方式升到大尺度进行保护开发,但是其组合的方式无疑与国家文化公园有出入。第一,文化遗产的组合模式为线性区域,而国家文化公园的范围在概念辨识层面,不限于线性文化遗产;第二,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的实践尺度多为跨越省(州)级区域或城市的中尺度,而在涉及广阔地域的国家文化公园中,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模式对于文化遗产的整合性可能会捉襟见肘;第三,二者虽然都强调保护区域内文化遗产的关联,但是缺乏对文化遗产组合机制的深层解读,特别是文化意义层面的机制,因此无法满足国家文化公园塑造国家象征、促进全民族文化认同的要求[24]。诚然,国家文化公园对于文化遗产的升尺度保护理论应该在研究中得到更为精准的解读。文化地理学中地方的尺度转换方法或许能够为这一问题提供方案。
(二)文化地理学尺度转换的特点
许多学科都涉及“尺度转换”的概念,例如地图学、测量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但是文化地理学的尺度转换有自己的特点,即一切尺度转换的根本基于文化。文化地理学的“尺度转换”包括降尺度和升尺度。降尺度指将大区域的文化或文化目标分解为小区域的文化或文化目标;升尺度是将小区域的文化或文化目标融入上一级区域的文化或文化目标中。在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中,常会遇到不同尺度区域的文化目标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情况,因此就需要用尺度转换的方法,统一目标,化解对立。下面的例子就可以解释上述抽象的表达。马来亚(当时称为马来亚,1957年独立后才称为马来西亚)霹雳州金宝镇的金宝镇战役纪念地曾面临着本镇、马来亚政府(国家)、金宝镇战役参战国(国际)3个主体的文化目标对立危机。金宝镇战役发生在1940年年底到1941年年初,驻马来亚的英军为抵抗日军南下攻占柔佛(今新加坡)组织了阻击战役。英军和日军双方伤亡惨重,英军虽然撤退,但是他们成功地打破了日军的美梦,即在1941年元旦前攻克柔佛,并将此作为给日本天皇的新年礼物。金宝镇居民在战役期间曾积极支援英军作战,因此本镇居民希望建立战役纪念馆,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却不批准,因为在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府要尽力抹去英殖民者的文化痕迹。而英军和日军的参战老兵及其后人,出于各自的情感,前来金宝镇凭吊,并竖立了若干纪念标志,这些标志之间也出现了情感态度的对立。最后,人们用“反殖反战”的文化理念,统一了各个尺度区域的文化诉求[25],从而达到小区域文化目标与大区域文化目标的融合。这种尺度转换属于后面将介绍的超有机体主义尺度转换方法。
文化地理学尺度转换不能与地理学的“一纵”脱离。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约翰斯顿(R.J Johnston)指出,地理学的基本思维是“一横一纵”[26]。所谓“一横”指不同区域中的要素彼此相互作用,文化地理学的尺度转换是“一横”体现形式之一。所谓“一纵”,是指一个区域内各个要素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尺度转换属于“一横”,但是却不能脱离“一纵”来理解一个地点或区域的地理“品质”。人们有了对区域特性或本质的理解,才能决定是否向这个地点或区域投资、迁移、就业、求学、旅游等。例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虽然是以红色文化作为核心,但展现红色文化也要从自然要素、生计要素、制度要素中找到与红色文化的联系。例如,位于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一定要建在当年战斗发生过的赤水河畔(自然要素),这样才能让参观者从实地景观中感受到红军在山区机动作战的艰辛;博物馆的实体空间不但要包括展览大厅,还要包括当年红军主要领导人居住的房屋、红军医院的遗址(生计要素),从而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博物馆展陈内容中还包含了制度要素,如毛泽东当年指挥红军,利用川、滇、黔交界地带的行政地理特点,穿插于国民党各方兵团之间,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最终成功地跳出敌人40万重兵的围堵。按照符号学的解释,如果定义红色文化精神是所指(signified),那么自然、生计、制度的元素就都是能指(signifer),能指和所指是不能分开的。
三、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意义尺度转换方法
文化地理学中有5种主要的区域尺度转换的方法,它们分别是文化景观尺度转换、文化扩散理论的尺度转换、超有机体主义尺度转换、结构功能主义的尺度转换和后现代主义尺度转换[27]。
(一)文化景观学派的尺度转换
文化景观学派的尺度转换,即指有相似文化特质的、彼此临近的文化区可以整合为一个大的文化区。大文化区可以有多种,如穆斯林文化区(Muslim region)、亚太文化大区(Asia-Pacific cultural realm)等。文化地理学创始人索尔(Carl O.Sauer)从景观入手,指出一个文化区内部的文化景观相同或相似,体现为相同的文化特质(cultural trait)[28]。索尔还指出,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为区域知识(areal knowledge),而区域知识等同于景观分布学(landscapes or chorology)[29]。在美国,国家公园的景观保护要遵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NPS)的规定。NPS启动了文化景观清单 (cultural landscapes inventory,CLI)项目,有学者分析了CLI 数据,发现清单给出的景观属性数据,如自然或文化的属性、景观古老程度,使得国家公园在景观上具有“一致性”。譬如落基山国家公园有一种荒野的景观风格[30]。换言之,景观上的相似性确定了国家公园的基本范围。中国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就是将所有具有相同文化景观(长城墙体、长城关隘所在市镇、长城相关军事设施等)作为小区域,而后整合为一个大文化区的。
(二)文化扩散理论的尺度转换
文化扩散理论的尺度转换,即由文化源地和该文化扩散到的区域组合为一个大文化区。20世纪50 年代,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T.Hägerstrand)在索尔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某种文化在时间扩散过程中的现实表现——文化扩散(cultural diffusion)[31]。他采用“文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从一类景观在不同时期的分布变化上来看,大的文化区是由小的文化区扩散而来的。中国的黄河文化区就可以视为以渭河谷地的文明源地,扩散到中原地区,乃至黄河上游和下游地区的一个大文化区。那么如何判断文化扩散,并以文化扩散的时空过程来整合大文化区?或许以色列的熏香之路(Incense Route)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香料有两种,一种是食用香料,一种是熏香。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产自非洲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乳香。乳香是乳香树的树脂,带有挥发油,可散发出温馨清纯的木质香气。乳香既可药用,也被大量用于宗教仪式的熏香。与乳香地位相当的还有没药。这些香料通过贸易线路扩散到产地之外的地区,如古埃及、古以色列、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古印度等地区[32]。以色列官方用熏香扩散的概念,将境内的熏香之路—内盖夫的沙漠城镇群(Incense Route - Desert Cities in the Negev)整合到跨三大洲的熏香之路上。虽然哈鲁扎(Haluza)、曼席特(Mamshit)、阿伏达特(Avdat)和席伏塔(Shivta)这4座沙漠城镇遗址的景观特征差异很大,但是在香料扩散的意义上,它们被整合到一起,共同展现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世纪当地香料贸易的繁荣历史。熏香之路—内盖夫的沙漠城镇群还包括了熏香之路沿线的堡垒、驿站、灌溉系统、商道等[33-34]。2005年7月15日,熏香之路—内盖夫的沙漠城镇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名录[37]。
(三)超有机体主义尺度转换
超有机体主义尺度转换,即有一个超有机体的文化统领各个小区域。伯克莱学派将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定义为在历史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超越个体”覆盖到社会群体的文化[35]。因为这种共享文化超越了个人存在,个人必须接受、服从,所以具有“超有机体”特征。索尔的弟子,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泽林斯基(W.Zelinsky)用超有机体理论解释了美国内部文化小区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虽然美国各个小区域的文化特征差异很大,但是它们共同组成美国文化[36]。每个内部文化区的人们可以保持自己的衣食住行文化特点,但是认同美国宪法。超有机体主义尺度转换的关键在于找到各个小区域社会文化中那些共同或共通的思想信仰、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等,前面所述金宝镇战役纪念地案例选择了“反殖反战”的文化理念,下面是另一个超有机体尺度转换的案例。巴西的卡皮瓦拉山国家公园(Serra da Capivara National Park)建于 1979 年,其中包括900多个考古遗址。1991年,卡皮瓦拉山国家公园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该国家公园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即3个不同尺度群体的态度对立。这3个群体分别是小尺度的印第安人、中尺度的当地社区、国家尺度的巴西政府。对立的表现之一是当地居民并不认同要保护的遗址的价值,因为他们认为保护区内的岩画是印第安人制作的;对立的表现之二是当地社区从未获得巴西政府的财政支持,因为巴西政府认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是当地的事务。因此,有学者提出了解决3个群体之间保护态度不一致问题的办法,即通过文化遗产的教育让人们了解到印第安文化的魅力,既借助非正规的教育途径,如博物馆、媒体等;也借助正规的教育途径,如在大学考古专业本科课程中加入卡皮瓦拉山国家公园的案例[37]。这些教育的途径旨在用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让不同尺度的人们认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而保护印第安人的岩画遗产,显然是超出各个尺度群体“有机体”需求的。回到中国国家文化公园话题,中国人对长征、大运河、长城和黄河所产生的国家认同就具有一定的超有机体主义特点。
(四)结构功能主义尺度转换
结构功能主义尺度转换。此方法论认为,功能上彼此联系的小区域组成了大区域。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Skinner)以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为研究对象,借鉴德国地理科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小区域都在大区域中具有自己的角色或功能,其中一个小区域的中心城镇作为区域自组织中心,统治着所有的小区域,它就是大区域的中心,它所在小区域与其他小区域被划归为“中心”和“边缘”[38]。小区域的文化特性由大区域的整体性控制。控制整体性的机制会随时间变化,前后两个机制变化点之间,整体性具有相对稳定性。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印度尼西亚官方在划定婆罗浮屠考古公园(Borobudur Archaeological Park)缓冲区时,没有按照欧洲的文化遗产保护区的做法,即没有让文化遗产缓冲区的风貌与婆罗浮屠的佛教风格高度一致,而是注意到该历史文化遗产公园周边是穆斯林社区,出于文化多样性的考量,政府鼓励穆斯林社区居民参与到婆罗浮屠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婆罗浮屠周边的穆斯林认识到社区与考古公园之间有多种功能结构关系,如可以从婆罗浮屠考古公园的旅游业获得经济收入,并可以在缓冲区的空地举行开斋节庆典等,因此他们积极参与到婆罗浮屠的保护中,譬如在火山喷发后,他们参与了火山灰的清扫工作[39]。这个案例证明,国际组织(UNESCO)制定的世界文化异常保护的机制,控制和左右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当地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并用历史文化的共同功能,将多层级的目标整合起来。中国的大运河文化区也可以视为每河段功能区彼此联系,完成大运河的整体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各个运河河段功能区彼此的结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五)后现代主义尺度转换
后现代主义尺度转换,即景观和功能上没有清晰逻辑的小区域组成了大区域。20世纪80年代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到文化地理学。按照迪尔(M.Dear)等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家的观点,没有一个宏大的文化区分析理论可以解释所有小区域[40]。后现代地理学家索加(E.Soja)以洛杉矶为例,指出洛杉矶“大文化区”是由众多城市内部的“小文化区”如同马赛克一样拼装成的。小文化区之间不一定是由功能结构联系起来的,也没有被文化“超有机体”覆盖。小区域是超越物理的空间,本体存在的,具有边缘性、差异性、开放性、批判性的空间,索加称之为第三空间(表征的空间)。每个区域不断突破原来空间结构赋予它们的地位或形象,从而将整个城市不断变为一个新的城市[41]。第三空间是相对于第一空间(实践的空间)、第二空间(空间的表征)而言的。所有国家文化公园都是第三空间,小区域之间关系的混沌乃至矛盾,恰恰展现出真实的文化区。美国学者分析了历史建筑遗产的“原真性”概念,虽然在20世纪之前很少有人关注建筑的原真性,但到20世纪学者们开始强调之,被定义、表达出来的历史建筑遗产原真性本质上是第二空间,它指导着人们在第一空间实践中如何保护历史建筑。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样的空间互动是现代的、原教旨主义和纯粹主义的实践,意在实现“建筑师初心愿景”(architect’s original vision),即在确定的“重要时期”内建筑呈现的理想状态,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原始“结构的重要性”的实践很难实现[42]。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建筑的使用功能、景观意义也在变化,且总处于新旧差异,甚至新旧矛盾的状态。以中国北京的天安门为例,在现代意义上,它的真实性就是明清两代京都皇城诸门之一,但是如今它更像是20世纪50年代扩建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重要元素。这种建筑与建筑群的尺度关系的不断变化是一个常态的真实。
尺度转换的方法无疑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启示。第一,无论是何种小尺度向大尺度的转换方式,所有的小尺度文化遗产都能够在大尺度的组合之中寻找其文化意义,从而使得每个公园之内的文化遗产价值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有利于增强保护依据,实现辖域内不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公平性。第二,从文化可持续的角度衡量,尺度转换的方法能够确保将文化遗产的小尺度意义嵌在文化公园的大尺度意义中,实现意义不冲突,使其更好地联合。这是今后国家文化公园突破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选择。第三,尺度转换能够更好地阐释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象征性,使其概念更加完善。
四、尺度转换思路与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机制
2019年发布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标志着3个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正式启动[43]。此外,其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将陆续提上议事日程,如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44],但是目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运用文化地理学的尺度转换思路,探索解决上述4个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是有价值的。
(一)文化景观尺度转换——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例
历代长城的遗存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遗产基础,长城历经我国春秋战国、秦、汉、唐、明等历史时期,传承两千余年,总长度达21 196.18千米。范围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一级行政区。它们是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线性文化遗产,具有时间范围广、种类繁多、建筑规模大、防御体系复杂、文化内涵丰富的特征[45]。而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认同意义来讲,长城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它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换句话说,长城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凝聚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强大力量[46]。
建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用文化景观尺度转换思路有助于解决目前各段长城的保护措施存在差异的问题。现存历代长城在景观上各有特色,因此各地的长城景区都可以视为小文化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后,可以制定统一的保护标准,从而形成一个景观保护水平一致的大区域。第一,将各区域的长城保护划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统一保护和活化利用,能够解决分割保护的弊端,如分布于地质较差、边远贫困地方的长城保护不足,地方基层文保力量薄弱,地方政府和公众对长城保护的意识不足。第二,对长城景观一致性的突出有利于强调长城的总体价值。第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意味着通过建立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体系,由国家统一管理。这里要补充的是,虽然强调景观特征的统一,但不意味着修复标准的统一,有砖石长城,有土长城,还有建筑形态保存较好的长城,坚持长城景观和地方历史和自然层之间的联系,进行分类保护。因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打破了“政出多门”的问题,实现不同年代不同区域的长城协同整合,串线成珠,构建一条长城文化景观带。
(二)文化扩散的尺度转换——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例
许多国家文化公园都面临空间范围难以划定的问题。以长征文化公园为例,长征路线共约二万五千里,主要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线路,从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沿线共涉及贵州、江西、重庆、陕西等15个一级行政区[47]。长征路线上有众多大小不一的长征遗迹,以往长征线路上的红色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瑞金、遵义、大渡河、腊子口、延安等地,但是红军长征路线沿途还有许多知名度不是很高的小的红色资源区,如祥云、小金、卓克基等。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不在长征主要路线上的小地方,这些地方也上演了与长征有关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例如贵州六盘水的龙场乡碗厂村。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长征经过水城时,红军战士朱云先、王红军因病掉队。病愈后,他们已经赶不上大部队,后几经辗转来到龙场乡碗厂村,并领导碗厂群众组织“齐心会”继续革命。1939年,朱云先、王红军在一次抗击地方反动武装的战斗中壮烈牺牲[48]。龙场乡碗厂村虽然不在主要的红军长征节点上,但是这些地方所发生的历史同样是长征精神的生动反映——它们同样浸透了长征的文化意义。这些地方小尺度空间单元的意义都是长征红色文化传布的结果。
文化扩散的尺度转换思路可以用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确定上。在江西赣州市下辖的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有一个自然村叫华屋,这里不是长征线路上的主要节点,但是它也与红军长征有密切关系,当年村里17位青壮年种下17棵松树,相约革命胜利之日回乡团聚。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人回来。在长征路线的沿途,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村子,红军大部队行进的线路虽然不经过它们,但是它们都是红军文化传播到的地方。如果可以将这些村子都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中,可以有两个好处:第一,国家公园单位的确定不一定受文物部门确定的红色文物的局限;第二,包含的与长征相关的小村越多,长征文化被保留得越完整。
(三)结构功能主义尺度转换——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可以分为不同的小文化区。首先,按照行政区可以划分为北京段、天津段、河北段、山东段、江苏段、安徽段、河南段、浙江段;其次,按照运河名称可以分为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下面又有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永济渠(卫河)、通济渠(汴河)10个河段。大运河的文化包括与之相关的物质性文化,如与水利、水运相关的闸、桥梁;与聚落相关的城市、商埠、码头等[49]。非物质的有大运河的传说、技艺如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田氏船模等。不同的文化区及其所包含的运河文化共同构成了大运河的文化意义[50]。
大运河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下是一个被各个小区域组织的统一体。一方面,大运河的各部分可以看作一个个小尺度的文化区,有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共同组织了大运河整体功能的发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漕运功能。漕运主要的运输货物为粮食,北京作为明清两朝的都城需要大量来自南方的漕粮支撑皇家、官员和军队的需要。正所谓“天下大命,实系于此”,清道光时运河中断,故而威胁到了北京的粮食安全[51]。在漕运的征收、运输、交仓环节,运河沿线各区域的职能各不相同且具有差异性。例如征收环节中,漕粮(正米)包括征自运河沿线各区域:江南江宁、安庆(上下江的范围)等十六府州征收粳糯粟米,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征收粳米和糯米;浙江杭嘉湖三府征收粳米和籼米;江西、湖南、湖北等收稻米兼收糯米;河南、山东征收粟米和麦豆。在运输环节,漕船航行次序也有规定——主要依据是距京师的远近程度,山东、河南在前,两江、浙江居中,两湖、江西居后,继续细分,一省之内同样按各地离京师的距离排顺序。交仓环节,运河沿线往北不仅一路设置存储漕粮的水次仓,如临清、德州等仓——各地将漕粮就近运交粮仓,然后由官军分段运送,同时在漕粮的最终归宿地建设京通仓[52]。在漕运制度下,大运河运行的结构分明,除了朝廷设置的漕运总督,还有运河中的重要节点包括码头和枢纽(如济宁)[53]。各运河段的主要职能也不同,如流经河北、天津和北京的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北段的漕粮北终段,来自南方各省的漕粮最终经此段运至北京。另一方面,大运河联系了沿线自然水系和区域,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其建立了整体性。以江南运河为例,它是大运河重要的一段,它穿越经济富庶地区,促进了沿线城镇的联系。因为江南运河流经雨量充足地区,运河段水面和水深都利于航运,故而运输成本低廉,使得明清到近代,这里的商贸运输多依仗水道。明清两代与运河相连的商业、手工业市镇开始兴起,如以产丝为主的乌镇,还有那些以茶、丝、湖笔、黄酒等行业为主导的大运河浙江段市镇[54]。大运河促进了不同商业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例如大运河中段的中运河联通了江苏北段、淮河流域沂沭泗水系。明清时期航线的通畅致使来自南方的徽商和来自北方的晋商将市场开拓至此。来自不同区域的商业活动也带动了本地人参与经商活动,大大刺激了本地商帮的发展[55-56]。
结构功能主义尺度转换能够有效地解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同质竞争的问题。结构功能主义尺度转换强调不同组成部分在整个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地位和功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在管理上,可以在各段强调不同的文化遗产功能的相互联系,突出不同节点城市、不同段的独特性,从而解决同质竞争的问题。这个方法还可以调动各地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上相互协同的积极性。
(四)超有机体主义尺度转换——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
在4个国家文化公园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资源最为分散。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涉及黄河流经的9个省和自治区。黄河流域既有从马家窑文化到大汶口文化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址,又有像丰镐、长安、西安、洛阳、开封等闪耀文明之光的古城。这个区域中历史上曾有许多民族在此生活,而今这里还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几十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本区域从上游开始,可以分为河湟文化区、陇右文化区、河套文化区、泾渭文化区、三晋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河济文化区、黄淮文化区等。这些次区域在空间上彼此也有交错。从文化类型上看,本区域还有农耕文化、水利文化、商业文化、艺术文化等。鉴于文化的多样化,人们很难找到一个表征(如图腾、文字)来体现这么丰富的文化,因此只有用“黄河”两字作为一个抽象符号,代表所有黄河国家公园中的文化。
超有机体主义的尺度转换思路针对资源分散的问题。黄河流域的小文化区,虽然被黄河干流和支流串联起来,但是它们之间并无明显的结构功能联系,因此不能像前面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那样,采用结构功能主义尺度转换方法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文化在构建历史文化遗产网络上缺乏优势。因此在各种文化之上,我们可以用“超有机体”的“黄河精神”来统一各个文化。黄河精神可以解释为竭诚为民、社会奉献的人文精神,自强不息、勇于斗争的民族精神以及顺应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思想[57]。通过突出这样的“超有机体”理念,将极大丰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文化遗产的景观意义和精神内核。
五、结论
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遗产升尺度保护与开发的新模式。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面临着政出多门、边界不定、同质竞争、资源分散的问题,通过完善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管理机制,能够解决这4类空间问题,进而实现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塑造国家象征、促进文化认同的目标。
文化地理学尺度转换方法能够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管理机制的改善提供新视角。基于上面介绍的5种尺度转换方法及其相关案例,归纳出4个结论:第一,文化景观尺度转换的思路有助于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因为针对同样的文化景观,各部门联合出台一个管理文件就可以了。文化景观尺度转换还可以解决保护边界难定的问题,因为将同类景观所在的县级行政区所形成的大区域就是保护区的边界范围,这是基于县级行政单元是最低一级财政单元,可以承担文化保护的财政责任。第二,文化扩散的尺度转换思路可以用于确定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其道理与前面的文化景观尺度转换思路有类似之处,但是用这个思路确立的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景观,可能有一些形态上的差异,但是文化主题是一致的。第三,结构功能主义尺度转换思路为人们提供了解决历史文化活化利用时的同质竞争问题,因为每个区域都可以找到自己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且可以将这种独特性与其他区域的文化资源建立起结构功能的联系。第四,超有机体主义尺度转换思路可以将多类型的文化统领在一个文化主题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