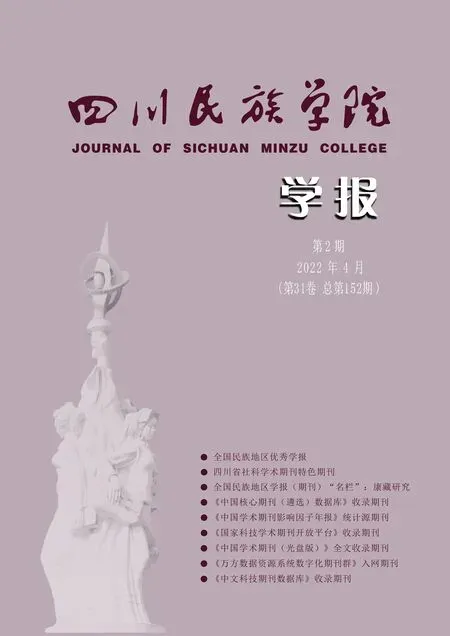沃日河谷勃发的生命力
——论小说《沃日河谷的太阳》
郭晓艺
(西华大学,四川 成都 610039)
涉藏地区文化的书写成为近年来文学表现的热点,尤其是在阿来的《尘埃落定》出版之后,四川涉藏地区独特的文化形态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近日,王跃、泽里扎西合著的同题材长篇小说《沃日河谷的太阳》(2020)出版,被称为一部文学的民族史,呈现了百年历史大事件背景下的沃日河谷的社会生活,以宏大的叙事结构、丰富的历史史料、瑰丽而又奇幻的文字,展现了土司制度笼罩下川藏高原人们的生活百态。此书出版后,广受好评,许多读者惊叹其“庞大的篇幅”、娓娓道来的精妙写法,称其为“史诗性”的经典之作。因此,对此书加以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沃日河谷的太阳》展示了三代人之间的纠葛,以土司洛桑郎卡、多吉马、三木羌,百姓才旺措美、丹蓉娃、绒布仁钦三代人为主体,蔓延出一系列故事情节;又以清廷与土司之战、土司与土司之战、土司与山民之战构建彼此之间的联系。作品中有人性的阴暗之处,也有人与牲畜之间最原始的情感;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在新的生命里的延续,也有现代文明的侵蚀……这一切在小说中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沃日河谷的壮烈图景。通过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形态、自然法则下的生命欲望、土司制度从繁华到消亡等,展现了沃日河谷勃发的生命力。
一、嘉绒地区生命力的文化符号表征
小说在展现河谷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将嘉绒地区的典型文化符号罗列出来,如碉楼、猪膘文化、沃日河、藏族民谣等。这些文化符号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从而凸显出沃日河谷富有野性而又勃发的生命力。
据调查,嘉绒藏族大约分布在北纬 30-32度,东经101-103度之间,地跨四川省阿坝、甘孜两州以及雅安部分地区。[1]2独特的区位条件使嘉绒文化在藏文化体系中有着鲜明的特色,促使嘉绒文化成为各界研究的热点。嘉绒文化是藏文化体系中极具地域特色的一个亚文化系统。墨尔多山、琼鸟、苯教、碉楼、嘉绒语、猪膘、“三片”等符号,既是这个独特文化系统的固态内涵,也是这个独特文化系统的物质性表征。[1]7《沃日河谷的太阳》中有不少文字是对这些文化符号的描绘,展现了独特的嘉绒文化。
小说开篇这样介绍碉楼:“才旺措美家的碉房是擦耳寨的头一家,择险而居,有百年历史。家碉的左右墙和后侧墙留有枪眼,砌法精湛。不远处的碉楼用沃日山上的阿嘎土和石块加石灰和糯米汁勾缝砌成,四周的墙体则用片石垒叠……大小金川及丹巴等地是一个千碉之地,碉楼林立,蔚为壮观……”[2]3-5。碉楼是嘉绒地区最为典型的建筑,无论是土司还是百姓都以碉楼作为自身的居住场所,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独特建筑,更是地理与环境等综合因素下最适宜的选择。碉楼,汉文史籍中称之为“邛笼”[1]4,普遍认为“邛”即“琼”,指的是琼鸟或琼鸟图腾的族落,邛笼则指琼鸟之巢。因为嘉绒地区以琼鸟作为自己的图腾,所以以琼鸟为尊,也就可以将碉楼的解释引申为琼鸟图腾的族落居住的地方。
嘉绒地区的碉楼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用于纯军事防御的碉楼,即人们平常所称的“高碉”;另一类为纯民居建筑,也是目前嘉绒地区较常见的一种民居。[1]4-5小说中对高碉的描述主要是将其作为战役时的防御碉堡,清廷与土司之战尤为体现碉堡的作用。正是有了碉楼的存在,才使清军久攻不下,寸步难行,若不是才旺措美失误点燃了火药库的引线,擦耳寨也绝非如此轻松地被攻下。另一类碉楼是人们的居住地,碉楼是地理区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晶,同时也与河谷人的性格相呼应,碉楼的原始与粗犷是人们豪放、野性的性格特征的体现。沃日河谷的独特环境赋予了嘉绒人勃发的生命力,这样勃发的生命力下的智慧所凝结出来的碉楼,赋予沃日河谷更具野性的魅力。河谷边屹立的一幢幢碉楼正是嘉绒人野性生命力的写照,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具有充盈生命力的群落。
嘉绒地区的“猪膘文化”也是小说中所叙述的一大特色。猪膘文化是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一,小说中写道:“才旺措美家的屋顶是嘉绒地区特有的密梁构造,板棚里有整片的猪膘肉,有些肉已放置了好些年,早已风干,沃日河谷干燥的阵风使猪膘肉愈久弥香,直接用刀削一片放在嘴里,嚼得口舌生津。猪膘肉的丰足显示着才旺措美家的殷实……”[2]4。猪膘作为一种食物是人们智慧的结晶,人们充分利用寒冷干燥的气候特点,采用风干的形式使猪肉能够长时间地保存;同时猪膘也是财富地位的象征,它代表着人们的经济状况,稍微富足的人家都会将猪膘肉晾晒在显眼的地方,借以显示自己的财富实力。猪膘肉的形成过程是自然与原始的融合,才旺措美吃猪膘肉的方式也是充满了随意与豪放,是自然欲望支配下随心所欲的任意而为,显示出原始的生命激情。
沃日河是河谷人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人类文明起源于河流文化,河流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沃日河是一条生命之河,接纳了无数有形或无形的生命,它默默陪伴着嘉绒人演绎了一段又一段的历史故事。人们面向沃日河修建了幢幢碉楼,日常生活与沃日河密不可分。河谷人在湍急的水流、陡峭的地势中生长起来,形成了豪放、粗犷的性格特点。丹蓉娃与守备的女儿在河边肆意地拥吻,阶层的界限全然被打破,守备的女儿完全不顾周围人的眼光,随心所欲地释放自己的情欲,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作为曾经在狗群中领头的西娃,选择以悲壮的方式来告别,一头扎进了湍急的河流,将自己的生命回归于河流。河流见证了河谷生命的喜怒哀乐,也最终接纳他们的逝去,包容着河谷的一切生命形态。
小说还有一大特色则是藏族民谣的运用。民间歌谣是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作品,是反映民众生活、表现民众思想感情和愿望的诗歌形式。民间歌谣可谓是藏族人民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算得上是藏族民间文学的鼻祖或乳娘,在整个藏族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3]小说中充斥着民间歌谣,小说中的歌谣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传达出藏族人的生活习俗和性格特点。藏族人历来以能歌善舞著称,歌舞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迎接远方客人、欢庆节日、庆祝重大喜事时都必然有歌舞的身影。藏族人借助歌谣来传达难以明喻的情感,传达美好的祝愿,祈求美好的希冀等。在藏族传统文学中,歌谣和格言在塑造人物、结构安排、行文叙事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作用。[4]这样的传统表达方式自然在当代藏族文学的创作中延续,体现出独特的藏族风味。《沃日河谷的太阳》在表现人物形象时,自然而然地融入民谣,其中尤其以情歌为主,使藏族人的形象更为具体可感。
丹巴嘉绒藏族的情歌是甘孜藏族民歌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优美的曲调、纯美的音色、亲切自然的表现闻名于川西高原,是嘉绒地区数量最多、传唱频率最高、最具特色的歌种。[5]旺姆在阿牛走后一直以歌谣寄托情思:“纳尼色莫,纳纳哟耶,纳尼色莫,纳纳哟呀!布扎戏绽芬芳,撒拉子绣画廊,口弦子飘过沃日河,在蛇皮梁子悠悠传响,穿过枷担湾的牧场,醉了嘉绒的吉瑞香……”[2]102。入营路上的汉子唱情歌来聊以慰藉:“郎在山上打石头,妹娃河坝放黄牛,石头打在牛背上,看郎抬头不抬头,郎在坡上盖石屋,妹在屋后摘石榴,郎说热得嗓冒烟,妹扔石榴让你酸……”[2]127。王轩为桑吉巴拉所唱的情诗:“爱情渗入了心底,能否结成伴侣?答曰:除非死别,活着永不分离……”[2]206。这些情歌或是表达思念之情、或是互诉柔肠、或是激情澎湃时打发无聊时光的调味品,成为嘉绒人日常交际的必备品。民谣深入嘉绒人的骨子里,人们似乎生来就会唱几句,就连牲畜也能以别样的方式哼唱,才旺措美养的狗也会应和主人的歌声:“关键是西娃,它也不会闲着,会把歌唱得呜呜咽咽,还会跳狗舞,双腿直立,转着圈……”[2]35。这些歌谣都是直白、裸露而又热烈的,凸显出嘉绒人率真、热情的性格,从而展现出嘉绒人充满激情的生命力。
小说中展现了嘉绒地区特有的文化符号,碉楼、猪膘肉、沃日河、民谣都是嘉绒地区独特的象征,除此以外,还有五香味糌粑、酥油茶、烧馍馍……这些文化符号无一不彰显着嘉绒人的性格特征,凝聚着嘉绒人的审美偏好和生活习惯,故而是他们自身品性的浓缩,是他们民族性格的融合。这些文化符号充满着原始气息,体现嘉绒人骨子里的自然性,是勃发生命力的展现。
二、河谷中的野性生命力
人性总是具有两面性,能够震撼人心灵的优秀作品总是能够将最真实的人性细致地描绘出来,不管是善或恶,只有将最真实的人性展示出来,看到其中令人唏嘘的愚昧,令人扼腕的可悲,才使文学更靠近现实。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立体化的人物形象,作者将人性中的善恶都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展现出沃日河谷中富有野性的生命力。
《沃日河谷的太阳》中章节的名字是极有特色的,大量的章节名由人物的名字构成,比如“丹蓉娃”“老罗布的儿子”“格桑玫朵”“旺姆”“丹巴拉加”“管家仁青”等等。有的人物不是主角,只在个别章节出现,这些人物不是单纯善恶的化身,他们只是普通的民众,但是他们共同构成了沃日河谷中富有野性的生命力,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平民百姓只敬重摸不着看不清的神,对一清二楚的东西视为无物。多吉马太亲民,不像他父亲把自己当成神一般供在神龛之上,所以多吉马不受人尊敬,百姓朝拜的是天神,多吉马不是神,只是一个凡人,因而无人来朝……”[2]268。人们崇拜的是难以言明的事物,对于可以感知的,便觉得失去了威严性。正如现实中不少人都有崇洋媚外的心理,正是我们不够了解其他国家的具体实际,在一些表面的情况下不断地美化心中的陌生形象,越发觉得这个形象伟岸;对于自己国家,太了解其中的藏污纳垢,才会生出更多的怨气。究其根本,我们只是太了解自身的情况,而缺乏对外在事物的了解,我们也对陌生的事物有着太多的包容心,对自己熟悉的事物却毫无耐心。多吉马太亲民竟成为人们不愿尊崇的理由,可以见到其中的荒唐、可笑,但正是这样的荒唐才更靠近嘉绒人。人性的愚昧暴露无遗,这种不加掩饰的愚昧引发了读者的同情。
地窝子主人罗布丹专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凭一张牛皮大被拦杀过往旅客,以获取足量的财物,毫无怜悯地将败兵彭措晋珠闷死在牛皮大被之下。败兵娶了老婆就出来打仗了,却因怕被清剿而在外游荡,满心期待回乡却死于非命。罗布丹杀人后反而哼起了欢快的曲调,对他而言,杀人无非就是捏死了一只蚂蚁。在艰难生存的年岁里,平安活着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各自都为生计奔波忙碌。地窝子令人闻风丧胆,但是去的人还是不计其数,只因它能够提供较为便宜的落脚地方,而安全与否全凭命运造化。罗布丹代表着人性的恶,但这样的恶是在特殊的时间点和环境下所催生的,他的存在也是生命力的表现,是寻求生存的表现,他为着生存掩盖温情的人性,麻木不仁地活着。
人性也并非完全没有温情,小说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至深情谊。在土司制度的笼罩下,等级制度也不是不可逾越。洛桑郎卡与才旺措美之间的情谊延续到了多吉马与丹蓉娃、三木羌与绒布仁钦身上,他们之间更多时候是超越了主仆情谊,是依依惜别、同生共死的兄弟情谊。丹蓉娃在迎接多吉马 “毛辫”的路上离奇失踪、绒布仁钦拼死保护三木羌的骨血……沃日河谷人们展现的是由河谷所养育的豪放、不拘小节、淳朴的品性,释放出最原始的自然欲望。张家的不顾周遭的眼光毅然与年纪大的寡妇丹巴拉加结合、丹蓉娃与守备的女儿在河边肆无忌惮地拥吻、桑吉巴拉与王轩跨越阶层的结合、格丹巴措与绒布仁钦违背道德伦理的相爱……他们所展现的都是藏族人民骨子里最原始的冲动,不受外界抑制自然而然地生长,即使道德伦理会在心中形成阻挡的力量,但却难以抑制其内心深处的欲望。
小说中人与牲畜之间展现着人类最本原的爱。西娃终其一生保护着才旺措美一家,从守护才旺措美到蓉娘,再到丹蓉娃。西娃不忍让主人伤心,以跳河的形式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它与才旺措美一家完全是等同于家人般的存在;老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家人,一家人也尽可能地回报,老马年老时喂养它的是比人类的食物还要好的蚕豆,一家人也舍不得让它干任何事;边巴次仁喂养在山里的牲畜,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即便现在的一批没有再受边巴次仁的饲养,但它们仍旧保留着旧时的习惯,每天太阳落山前就成群结队回到老屋转悠,王苍远回到老屋悼念母亲后,离开时,猪群为他们送行。“山猪留恋老屋,更留恋老屋的主人,它们早已幻化成这山林的精灵……”[2]308。人与牲畜之间互相依存,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成为小说中的一大亮点。
沃日河谷中生长的人、牲畜都带有浓厚的野性色彩,他们未被现代文明完全裹挟。他们的身上充满了野性和古朴,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欲望,这样原始的力量,使得生命勃发出旺盛的生机。这样野性的生命力不仅没有在时代前进后受到压抑,反而迸发出更强的活力,成为催化土司制度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三、野性生命力的反抗
土司制度在嘉绒地区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是嘉绒地区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土司制度是小说最核心的存在,土司的统治维持着所属范围内的表面平和。河谷人们在土司制度的压抑下麻木地活着,但嘉绒人骨子里的野性生命力在时间的推移中越来越不可抑制,最终迸发出巨大的活力,成为土司制度消亡的重要因素。
小说预示着土司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而这样的消亡与生命力的反抗作用是分不开的。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政治制度。[6]土司拥有极大的权利,奉行的规章制度也是最大化地维护土司的统治,土司政权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土司一方面利用暴力来镇压、威慑一切违抗其命令的群众,同时,又用宗教来使民众精神臣服。民众处于神权的压迫之下,反抗的结局不单单是暴力的处决,而且还有心灵的巨大折磨。因此民众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土司的统治,将土司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并将这样的观念世代沿袭下去,这也就导致了命运的轮回。一方面是土司代表着权利的中心,骄奢淫逸,随意处置民众的性命;另一方面是民众的艰难度日,科巴身份的妇女甚至不如土司家的一条狗。民众的生命不断被践踏,他们的儿女继续重复着他们的命运。身为管家的仁青享有极高的地位,他手下掌管着其他各类管家,他只需要在土司面前毕恭毕敬,伺候土司的一切杂事,而他自己也有差役侍候,他可以趾高气昂地指挥一切地位比他低的人,即使百姓非常厌弃,但也只得服从。由来已久的制度赋予他地位与权利,臣服、遵从的观念也根植于百姓头脑中。
自古以来强调“民贵君轻”,受民众爱戴和拥护的必然是“仁君”,这些观念放在土司制度下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土司成为一方主人,他们有义务维护统治地区内人们的安居乐业,小说中的土司只是保障了统治区内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单纯的活着。女佣山丹被误会为奸细,遭到惨无人道的点天灯处置,字子君也遭受到严酷刑罚,这些人固然犯了错,但在土司的眼中,他们不过是可以随意处置的猫狗。这还是在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背景下产生的事件,是受过大儒教育的三木羌做出的处罚,十多年的教育仍然没有改变他血液中的极端利己主义,他所受的儒学教育只是短暂地压抑内心的残暴,而当他一回到故土时,娶妾、暴打发妻、处决仆人……一一上演。“他爷爷洛桑郎卡是河谷之鹰,可以飞上天空去翱翔;他父亲多吉马是河谷之豹,在河谷里纵横捭阖;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掉光了羽毛……”[2]314,并非一代不如一代的衰败现象,而是人们开始唤醒骨子里的野性,以推翻不合理的制度。他仍然想要固执地维持古老的秩序,坚决收取买路钱,造成了大量的山民摔下悬崖。三木羌固执地维持古老的秩序,为的无非是用无上权力来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在这样的秩序下,反抗自然也就成了必然,推翻土司制度也就势在必行。
新一代的青年成长起来,他们对于等级观念也是遵循的,但并非像父辈一样盲目信仰。他们开始抹去原本的界限,管家仁青的话不再是绝对的命令,桑吉巴拉可以公然挑战管家的权利;丹蓉娃不理解为何自己不能和守备的女儿结合;作为大儒之子、少土司兄弟的王轩,却与一个地位低下、相貌平平的侍女结为夫妻;山地女子格丹巴措公然挑衅土司太太,并对其反复戏谑,这些“不可能的事件”都在嘉绒地区上演了,原本的秩序不再是坚不可摧,年轻的一代奋起抗衡旧秩序。年轻的一代在新事物的影响下唤醒了血液里的野性与激情,用自身的行为来一步步瓦解土司制度。
小说中也有鸦片带给沃日河谷沉重灾难的描绘。“牛老三挖到金子要下山去懋功交易,把金子换成银子,然后去窑子把银子败光,淘金人走的都是这条路。后来发财的就去抽大烟,再多的金子也不够他们败。懋功的街上有二百多家烟馆,而人口不过二三万……半山土地贫瘠却非常适合种植大烟,那里开满了罂粟花。靠卖烟土,饶坝比河谷富裕,河谷就是饶坝大烟的倾销地……”[2]22。种植大烟是走向富裕的捷径,挖金人用性命换取的金子在烟馆无尽地挥霍,用完再继续挖金,挖到金继续挥霍……陷入无止境的循环。两三万人口的街上却养活了两百多家烟馆,可以想象人们对大烟的需求量之大,人们的生活成了没有目的性的存在,生存好像只是为了那稍许的慰藉。饶坝土司借助鸦片使自己领地的百姓富裕起来,洛桑郎卡土司在享受到了大烟的“无穷乐趣”后,命令才旺措美取回罂粟种子,使自己也能尽情享用。土司放纵鸦片在土地的泛滥,把其视为财富的重要来源,受压抑的人们把鸦片当作抚慰精神世界的“良药”。鸦片作为一种外来的物品流入嘉绒地区,给这些地区带来了短暂、畸形的繁荣。“从1935年起,国民政府厉行禁烟,声言6年内予以禁绝。清末以来禁烟的规律是,每禁一次,鸦片种植就向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转移一次。”[7]罂粟带给我们的都是沉痛的记忆,往往代表着腐化、堕落,无尽的深渊。在罂粟的迷幻下,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处于一种迷醉的状态,连乌鸦也患有烟瘾。长此以往,原本拥有富裕粮食的领地也将落入粮食短缺的局面,无一例外的成为罂粟控制的傀儡,何谈富足?反抗也就随之而来。
土司制度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可阻挡地走向了末路。小说详尽地突出了这些因素,明晰地展现出这种制度的不可挽救。土司制度在历史潮流下必然走向灭亡,个人勃发的生命力也将推翻土司制度。
《沃日河谷的太阳》展现了一幅富有生命力的少数民族画卷。画卷中有展现嘉绒人质朴野性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有凸显勃发生命力的立体化人物形象、有生命力的反抗加速土司制度的消亡……我们通过这本小说更能感受到一个明晰的嘉绒图景,感受到嘉绒人们的痛苦与欢乐,感受到嘉绒人充满欲望与生机的旺盛生命力。除此以外,这本小说在某些方面将阿来《尘埃落定》所挖掘的嘉绒土司的过往历史进一步细致化,让读者再次看到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的历史生活,激励更多的人去挖掘这片土地的价值,使其文化得以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