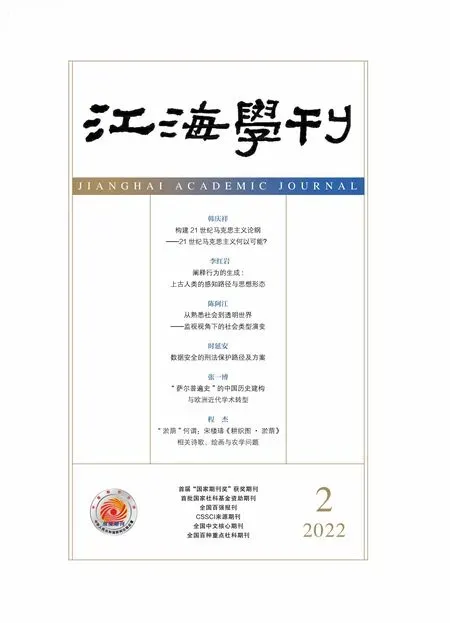数字服务税开征的正当性及其思路*
——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视角的考察
侯 卓
问题的提出
数字服务税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热议话题,域外也已有相关的制度实践。我国有无必要开征数字服务税,如果开征,又应遵循怎样的进路设计规则,可从不同角度切入思考。其中,至为重要却受观照不足的一个角度是其对公平竞争的影响。相较于传统行业,互联网行业的勃兴相对晚近,其运行和获益逻辑一定程度上也异于传统行业。部分是为促进这一新兴行业发展,部分也是出于在条件不成熟时慎重行事的考虑,其税负轻于传统行业。这种有违公平竞争的税制安排,使互联网从业者相对其他行业从业者处在竞争优势地位,在“互联网+”等新业态的助力下,能便捷地将自身的优势地位延伸到不同领域。
针对互联网行业的税法规制不足,是使相关企业得以居于垄断性地位的制度成因之一。当下在考量数字服务税的开征问题时,必须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视角。本文拟首先探寻传统税法适用于互联网行业时存在的问题,以明晰该行业税负偏轻的制度成因,进而考察矫正税负失衡的三种思路,在对比中揭示开征数字服务税这一方案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运用可税性分析框架来考察开征数字服务税的正当性。在明确开征数字服务税可兼顾需要与可能后,本文以三组主体间关系为线索,提炼开征数字服务税的核心思路,以更好促进不同维度公平竞争的实现。
互联网反垄断何以需要税法规制
税负均衡是公平竞争的题中之义。在现行税制对互联网行业过于有利的背景下,强化针对性的税法规制之于互联网反垄断颇为重要。
(一)传统税法之于互联网行业的低兼容性
互联网行业的税负偏轻,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税法适用于互联网行业时存在一定不适配性,使税负测定和税款征取较为困难。
1.税收管辖权的确定难以由传统的联结度规则导出
互联网行业高度依赖在线交易,互联网企业的收益也多是通过在线交易获取。这给《企业所得税法》及《增值税暂行条例》中据以判定征税权的联结度(或称“课税连接点”)规则造成冲击。
当前各国多依常设机构规则确定征税权,据此,仅当一国企业在另一国设有常设机构时,另一国方对相关利润有征税权。常设机构包括三种类型,也即基本型常设机构、建筑型常设机构和代理型常设机构。前两种类型的常设机构均要求存在固定的实体,代理型常设机构则需要存在代为签订合同的常设代理人。互联网交易所依赖的服务器设备可轻易转移,难以判定为基本型常设机构或建筑型常设机构。此外,在线交易中,互联网企业可通过网络程序签订合同而无须设置代理人,亦难认定为代理常设机构。(1)白彦锋、湛雨潇:《欧盟税改与国际税收发展新出路——针对互联网巨头跨国避税问题的分析》,《公共财政研究》2018年第2期。据此,跨国互联网企业可以分离常设机构与利润产生地,利用国际税收规则的差异来规避税收负担。2016年,谷歌公司便曾通过虚设常设机构、在低税率地区设置空壳公司等措施避税数十亿美元。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条规定,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在中国境内缴纳增值税。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7条,“在中国境内”是指销售货物的起运地或者所在地在境内或提供的应税劳务发生在境内。换言之,货物的起运地、货物的所在地及应税劳务的发生地为征收增值税的课税连接点。但在线交易中,三个课税连接点均不易识别。以货物的起运地为例,数字产品的发送、传输和接受在瞬间完成,数字产品可能存储于卖方网址所在的服务器或第三方数据仓库中,此时货物的起运地或所在地便存在卖方网址所在的服务器所在地、卖方主要营业机构所在地、卖方注册地、第三方数据仓库所在地等多种选择。究应如何取舍,各方意见还不一致。(2)廖益新:《远程在线销售的课税问题与中国的对策》,《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实践中似乎呈现以卖方注册地为征税地的倾向,(3)王卫军:《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从生产增值税到消费生产税》,《税务研究》2020年第12期。但在前文所列举的四个选项中,卖方注册地的经济关联度最弱,作出该选择的合理性存疑。
2.数据信息未被现行征税客体框架所涵盖
提供数字服务是互联网行业的主要盈利方式。针对数字服务通过互联网交易产生的无形资产,传统税法已将其纳入征税范畴。但提供数字服务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用户数据,其同样蕴含可观的经济利益,传统税法对此却缺乏足够关切,基本未将其纳入征税客体的范畴。
传统法律对信息的调整着眼于信息背后蕴含的隐私、智力成果等特定内容,本文所述用户数据信息乃是处于传统法律明确保护以外的具有信息内容的数据。其法律地位虽未明晰,(4)梅夏英:《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但不可否认,用户提供的数据信息深切影响数字服务平台的收益。数字服务平台主要通过投放广告、出售数据分析报告、用户增值业务(会员)等行为赢利,用户提供的数据信息影响平台的价值——用户数据信息与平台通过发布广告等行为获得的服务费等收入密切相关。诚如OECD所言,数据的收集行为将在其后的分析、储存、运用等环节带来价值。(5)OECD, Tax Challenges of Digitalization, Comments Received on the Request for Input-Part 1, 2013, p.39.基于上述分析,用户数据信息可给互联网企业创造收益,增进其税负能力,已具备被纳入征税客体的条件。然而,传统税法所确立的征税客体框架具有鲜明的“物化”特征,包括商品、所得和财产三大类。民法学界对于数据信息能否成为一类“物”尚无定论,税法通常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从保持法体系统一的角度出发,自然也不便过于急切地将其纳入征税客体的框架。
3.计税依据难以确定
承前,纵然通过拓展征税客体的范畴,将数据信息纳入其中,囿于数据信息的价值难以计量,在从征税客体具体化为计税依据的环节也会遇到障碍。颇多数字服务平台不直接向用户收取费用,但用户在使用平台时向平台提供富有价值的数据信息,这部分数据的价值未以货币形式呈现,故很难成为计税依据。OECD曾提出基于数据的市场价值或个人价值的六种测量方法,但不同市场参与者仍然难以对同一数据集采行一致的测量方法,且每种测量方法均有其缺陷。比如,若是采行相对主流的市场价值测量法(market price for data),则数据的价值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不同,且数据的质量在很多情形中也有较大差异,这都会引致价值衡量的失准。(6)OECD, Exploring the Economics of Personal Data:A Survey of Methodologies for Measuring Monetary Value, OECD Digital Economy Pape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3,pp.10-32.
此外,数据价值还具有间接性和潜在性特征,这也增添了计算难度。用户与服务平台间形成易货交易,但用户提供之数据信息的潜在价值远超用户所享服务的价值。一般而言,用户可自由进入平台享受广告、影视、新闻等服务,平台则可获取用户的偏好、联系方式、居住地址等个人信息。据此,平台搭建关于用户个人信息的数据库,并可与其他平台合作发布定制化广告、开展用户增值业务等。循此路径,用户提供的数据信息可使大量潜在的关联企业受益,(7)[英]阿里尔·扎拉奇、[美]莫里斯·E.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余潇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08—210页。这部分收益也难精确测定。
4.对互联网企业实施税收征管面临技术困难
互联网场域各类交易的无形性、虚拟化、数字化特征增添了税收征管的难度。首先,互联网行业高度依赖的无形资产具备流动性,这导致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活动常相分离,判断所得归属愈加困难。其次,互联网交易主体的隐匿性和虚拟化使得税务机关难以识别交易主体的身份及地位,交易内容的数字化使税务机关无法有效监控税源。最后,互联网企业不乏跨国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和运行模式的隐身性,其通常会在全球范围内考量成本等因素,利用数字技术及各国税制差异,借分离无形资产的所有权等方式,将无形资产及相关权利转移至税收洼地,同时重组处于正常税负国家的经营实体,使其参与分配的利润微薄,这从根本上造成对互联网企业征税难。(8)李蕊、李水军:《数字经济:中国税收制度何以回应》,《税务研究》2020年第3期。
(二)矫正税负失衡的传统路径及开征数字服务税的优势
既然传统税法适用于互联网行业时“水土不服”,是诱致互联网企业税负轻于实体企业的重要肇因,那么制度回应自很必要,回应思路有二。
1.现行制度框架下的修补思路
首先,数字经济的兴起对于既有确定税收管辖权的联结度规则形成挑战,对此,可通过建立“显著经济存在”(significant economic presence,以下简称“SEP”)(9)2015年OECD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BEPS Project)的第一项行动计划《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中提出“显著经济存在”。2019年OECD发布“双支柱”方案,其中第一支柱修订了联结度规则,新的联结度规则是以“显著经济存在”为基础,汲取“用户参与”等概念形成的新规则。规则或重新定义机构场所予以解决。在前者,SEP规则的引入可使信息数据、用户参与、网站浏览等互联网行业的独特要素在判断是否具备联结度时成为有价值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税法可以规定,前述要素若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具备了可税性基础。此外,在采用SEP替代PE作为管辖权标准的同时,可将“用户参与”要素作为“零星分配法”(10)OECD,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s, 2017,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oecd-transfer-pricing-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tax-administrations-20769717.htm.下的分配基础,通过税基分割、要素分配的方法来确定“起征点”,从而有效调节跨国互联网巨头企业利用要素优势垄断行业的状况。在后者,现行“机构、场所”概念主要指具有生产经营属性的物理存在,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做法是,将“虚拟机构场所”也纳入其中,进而将用户参与数量、链接或网页点击数量、交易金额或交易合同数量等作为认定“虚拟机构场所”存在的标准,从而使《企业所得税法》等税法能无差别地适用于传统行业和互联网行业。
其次,征税客体覆盖未及的问题,可通过解释或调整税种法上税目规则的方式部分得到解决。互联网企业所提供的数字服务,有些可为现行税种法所涵盖,比如基于互联网平台销售货物、提供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等行为属于增值税“销售服务”项下的“销售无形资产”,线上广告收入则属于“现代服务”中“文化创意服务”的范畴;有些则需要对现行规则适当地进行扩大解释,比如将前述“文化创意服务”的外延扩张至通过互联网销售虚拟产品或数字化产品,又如将“广播影视服务”扩大解释为包含通过网络平台向不特定对象播放音视频、进行直播,当然,扩张解释仅为权宜之策,虽然税法为追求税收公平而不绝对排斥扩张解释,但更理想的选择还是修改《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的附则。
再次,针对计税依据难以确定的问题,OECD“双支柱”方案中“第一支柱”关于金额A(11)金额A、金额B和金额C都是OECD“双支柱”方案中“第一支柱”的内容。金额A是由完全数字业务创造的新增利润,金额B是传统基线业务创造的利润,金额C是传统非基线业务创造的利润。的计算方法的规定,颇具借鉴价值。(12)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Secretariat Proposal for a “Unified Approach” under Pillar One, 9 October 2019-12 November 2019, 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secretariat-proposal-unified-approach-pillar-one.pdf.概括地讲,不妨遵循如下四个步骤确定计税依据:第一步,通过合并财务报表得到总利润率X%。第二步,依据征税对象的行业状况设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常规利润率Y%。须注意的是,常规利润率的设定要考虑行业状况和国家差异,基于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目标,对于国内企业,不妨以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的利润作为参考,而对于国外企业,则可参酌谷歌、亚马逊等企业财报来设置相应的常规利润率。第三步,用总利润率X%减去常规利润率Y%,得到非常规利润率Z%=X%-Y%。第四步,区分目标调整企业中不同的数字要素,确定各自在数字经济收益中的占比,以此为基础确定各企业的计税依据,这一做法的前提是默认非常规利润率的来源是数字经济中的独特要素,例如数据、用户参与、不必设置实体机构所带来的成本削减等。
最后,就互联网企业跨国经营时税源不易把握而言,可考虑通过第三方代扣代缴并征收预提所得税的方式解决。(13)高金平:《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与国内税法之衔接问题思考》,《税务研究》2019年第11期。付款方(购买境外数字服务)或收款方(向境外提供数字服务)在发生金钱往来时,由国内的平台、机构、程序、软件(例如支付宝、微信)承担扣缴义务,自动代扣代缴交易方的税款。若出现交易行为性质认定错误也即交易并非数字服务行为的情况,纳税人可通过“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方式退税。征收预提所得税则是指市场地国的居民作为扣缴义务人,在向非居民互联网企业支付价款前,先按适用税率计算应向市场地国缴纳的税款并履行代扣代缴义务。(14)Adapting Current International Taxation to New Business Models: Two Proposals for the European Union, 2017,71(12): 681, p.6.实际上,预提所得税作为企业所得税的一种特殊类型,已被许多国家运用于对非居民企业的税款征收,将其一体适用于互联网企业也是理所应当。据此,市场地国适用该方案仅需将数字服务产生的收入纳入预提所得税的征税范畴,如希腊便针对软件的使用者征收预提所得税,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也采取了类似措施。(15)陈勃:《论数字经济挑战下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回应》,《税收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我国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9条第1款载有预提所得税的规则,企业所得税法内外统一后,《企业所得税法》第3条第3款、第27条第5项和第91条第1款合在一起实际上仍然规定了预提所得税制度,在该框架下,可考虑将数字经济下大型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广告收入、技术服务收入等纳入预提所得税的范围。
2.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必要性及其相对优势
数字服务税是对互联网业务产生的特定利润进行征收的税种,其立税初衷之一是限制大型跨国跨行业互联网公司的垄断式发展。由此出发,其征税对象是企业而不包括个人,故有些类似于企业所得税。但不同的是,该税种侧重于对实施特定行为的主体征收,而非行为本身。(16)管彤彤:《数字服务税:政策源起、理论争议与实践差异》,《国际税收》2019年第11期。
首先,通过SEP联结规则确定税收管辖权虽然理论上可行,但从OECD的一系列方案在成员国间尚未达成共识的事实可知,意欲使他国让渡税收管辖权绝非易事。SEP联结规则自身的模糊和不确定,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概括地讲,运用SEP规则确定“起征点”时须采用要素分配的方法,但各要素占比应如何设定,并无唯一正解,其既是技术问题,又牵涉价值判断,规范目标的选定和排序将深刻影响要素占比情况。但麻烦之处在于,即便确定了调整目标,制度手段和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背离。若设计不当,可能损害中小互联网企业的利益,却宽纵了“头部企业”。与之相比,数字服务税可通过简便易行的“起征点”设定和调整,确保征税对象仅限于目标企业,也即具有一定市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企业。譬如法国的数字服务税便仅对年全球营业额超过7.5亿欧元、国内营业额超过2500万欧元的居民和非居民企业征收,征税范围则是前述企业来源于法国的在线广告收入、销售用于广告目的之个人数据以及提供点对点平台服务的收入,税率为3%。(17)龚辉文:《数字服务税的实践进展及其引发的争议与反思》,《税务研究》2021年第1期。
其次,重新定义机构、场所和解释、调整税目规则的做法虽然操作起来并不复杂,但其对数字经济、互联网行业的特质缺乏足够关切,尤其是对互联网企业所依靠的“用户参与”等因素未实施针对性的调节。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其对海量数据的搜集和掌握,而不限于已经呈现出来的提供数字服务等行为,仅对后者征税不敷需要。相较之下,数字服务税是以数字要素的信息价值作为征收依据的专门税种,其将“用户参与”作为税种设计的核心要素,基于各企业对数据信息的占有征收税款,不仅科学合理,还能收到辨证施治的效果。一方面,从互联网企业和实体企业的关系来讲,在征税时适应互联网企业的特质,对数字要素给予特殊关切,能使二者在公平的税法环境中竞争;另一方面,从互联网企业内部的关系来讲,用户参与情况是区分互联网行业中“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键,以此为据设定税负,能较为合理地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分配税负。
再次,借鉴OECD方案确定计税依据,在实践中会遇到两大难题。其一,常规利润率的设定要建立在充分占有行业大数据的基础之上,这需要与纳税人相关的各单位、各部门主动提供或披露涉税信息,而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第三方涉税信息提供的规定并不完备,实践中税务机关从第三方主体获取数据信息的情况亦不理想,这极大地制约了常规利润率设定的科学性。其二,囿于数据信息价值所具有的间接性、潜在性和难以计量性等特征,不易确定各数字要素在收益中的占比,单是给互联网企业带来特定收入的究竟是传统要素还是数字要素都殊难判断。而数字服务税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确定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以企业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总收入作为应税门槛,据此识别征税对象,继而以其所实施的数字服务行为作为征税范围,能较好反映征税对象的商业规模。其看似简单粗暴,实则在征管环节更加高效,也可压缩部分“头部企业”规避税负的空间。
企业财务工作在新的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逐渐暴露出问题,通过对“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要实现对财务工作的有效管理,不断提高财务数据的准确性,编制科学的财务预算报告,创新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最后,预提所得税方案存在征税范围过宽的弊端,无论何种类型、何种规模的企业,有所得便须课税,而且较之一般税率,预提所得税的税负水平虽然偏低,但其税基未扣除成本费用,有悖于“净额所得始能征税”的税法原理。此外,开征预提所得税,需要国际社会达成普遍共识,否则易诱发法律性重复征税。与之相比,数字服务税内含谦抑性,若能较为合理地设定应税门槛,可将征税对象限定在必要范围内,也即主要指向“头部企业”,而使中小企业在相对友好的税制环境中茁壮成长,营造竞争更为充分的互联网市场。
数字服务税的可税性基础
前文已阐明,开征数字服务税的方案较之修补式的做法,更能从根本上矫正互联网行业税负畸轻的状况,对于互联网反垄断而言可发挥长效机制的作用。但这仅是从外在功能的视角揭示其“有用性”,尚未触及数字服务税的正当性问题,而后者更为基础和关键。这便要用到可税性的分析范式。通常来讲,具有收益性则可税,具有公益性则例外地不可税,故可税性分析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18)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43页。具体就数字服务税而言,收益性分析有两个层次:一是收益是否存在;二是该收益若很难精细测量,会否销蚀其可税性。公益性分析则主要关注互联网企业的收益是否具有公益性。此外,数字服务税的开征会否损害营商环境也待检视,这亦属于广义上可税性分析的范畴。
(一)“用户参与”的收益性检视
依据OECD 2019年《公众咨询文件》中“统一方法”(unified approach)的适用对象,数字服务税的征税对象为面向消费者的大型跨国经济体,(19)OECD,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Secretariat Proposal for a “Unified Approach” under Pillar One, 9 October 2019-12 November 2019[EB/OL]. (2019-11-12)[2019-11-12].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secretariat-proposal-unified-approach-pillar-one.pdf.具言之,是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数字服务而产生收益的企业,其关注面向消费者的因素(consumer-facing element)。此类跨国互联网企业较之传统企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用户参与”,这使其在客户所在地产生大量营业额,不仅由于常设机构的缺失致使国内所得税法、增值税法鞭长莫及,而且其消费者导向属性(B2C)使消费者个人作为服务接收方相较于B2B方式更容易诱发税收征管的漏洞。(20)《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行为,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购买方为增值税扣缴义务人。然而,当扣缴义务人为个人时,依据现有税收征管水平,征收率很低。此外,在数字经济时代,价值转收入有多种方式,无论是用户贡献浏览和点击量便可养活无数广告商,还是互联网平台依靠用户的交互参与从而得以销售有形货物服务以及虚拟产品,均能体现“用户参与”具有收益性。至于其无形资产属性,虽导致收益难被测度,但就收入转化能力而言,更胜过传统的有形资产。
更重要的是,用户参与所带来的海量电子数据,其价值足以转化为互联网企业的竞争优势。对“头部企业”来讲,用户数据的收集能产出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21)即先进入市场的企业在用户积累方面有显著成效,产生用户粘性,并利用此优势继续适应用户习惯,使后进入的企业难以占有市场份额。为延展垄断领域创造条件。欧盟立法提案认为应针对用户在价值创造方面处于核心地位的三类数字服务课税,包括“通过数字界面对用户提供广告”“通过提供数字界面中介使得用户之间进行交易往来”“销售通过数字界面获得的用户信息”。(22)See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igital services tax o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digital services.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taxation-1_en.英国认为“用户参与”主要通过四种渠道创造价值,即提交数字内容、深度参与平台建设、互联网效应和外部性、品牌建设。(23)See Finance Act 2020.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20/14/contents.意大利在界定应税收入时也以“用户参与”作为数字服务总收入计算的核心要素。(24)源自以下数字服务(用户位于意大利境内)的总收入:(1)在数字界面发布广告;(2)为用户提供买卖商品或服务的多端数字界面;(3)传输用户使用数字界面而产生的用户数据。See Daniel Bunn, The Italian DST Remix[EB/OL], https://taxfoundation.org/italy-digital-tax/, 2019-08-12.可见,“用户参与”的收益性已被诸多发达国家所接受,其在考量或开征数字服务税时,多以“用户参与”作为界定征税对象的核心要素。
进言之,何种程度的用户参与方才具有可税性基础?参照欧盟数字服务税立法提案中对“显著数字存在”(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的认定,(25)一家企业满足下列三项标准中的任意一项即可被认定为“显著数字存在”:(1)在某一成员国境内的数字化服务年收入超过700万欧元;(2)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某一成员国拥有超过10万名用户;(3)一个纳税年度内和某一成员国用户订立超过3000份数字服务合同。See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laying down rules relating to the corporate taxation of a 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 {SWD(2018) 81 final}, 21.3.2018, COM(2018) 147 final.不妨从四个角度入手,确定因用户参与而获得显著收益,进而应受税收规制的市场主体:(1)基于用户参与(包括用户浏览、用户交易、用户信息持有等)而产生的收入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26)若依据现有技术,基于用户参与而产生的直接收入不能精确计算,则该条件在实务操作中将难以推行。此时,可考虑以年收入进行同水平替换。(2)在纳税年度内用户浏览、访问、点击量达到一定数量的网页、程序、搜索引擎等所属的企业;(3)附着于网页产生的广告年收入(定向广告、社交媒体资讯等)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4)以互联网销售为主营业务、年收入金额达到一定数额的电子商务企业。在以上情形中,互联网企业从用户参与中获得收益且有相当之程度,从具有显著收益性的角度讲,已具备可税性的坚实基础。
(二)为何不以“净收入”来衡量收益
税法的一项基本原理是,课征税款仅能针对收益而不得及于财富的本体。故此,开征数字服务税必须面对的一个诘问是,其能否将税基严格限定在“收益”的层次。理论上讲,“净收入”也即扣除成本费用后的收入,是衡量“收益”的最佳指标,以此作为税基似乎较为合理。然而,纵观现已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多将总收入而非净利润作为税基,进而简单适用比例税率得出应纳税额。何以不用“净收入”来把握收益,值得考究。
(三)有无公益性豁免的情事
有人倾向于认为,互联网企业所提供的数字服务对社会公共利益大有裨益,故而应当基于其公益属性而得以享受一定的税收利益。这是对可税性分析框架中“公益性”因素的误读。公共产品不同于私人产品的典型特征在于其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正因如此,市场主体一般不愿主动供给公共产品,而是由公共经济部门承担这方面责任。国家也可能借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激励政策,促导市场主体“代为”提供相关公共产品,此种情况下当然不宜对市场主体的相关收益征税。数字服务虽能增进大多数人的福利,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排他性(用户过载时会降低使用体验)和可分割性(不同用户的消费可以明确区分界限),不属于公共产品,这正是市场主体乐意进入相关领域的重要缘由。在该前提下,不能单纯因相关服务使众人受益便判定其具有公益性从而当然地没有可税性。
虽说整体上不能逸出税法的辐射范围,但不排除互联网企业的某些收入因其基础行为的公益性而仍应被剔除在税基之外。比如,在数字界面投放定向广告作为互联网行业典型的交易方式,几乎被所有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纳入应税服务的范畴之中,但当数字界面的广告投放行为与公共信息传播行为耦合时(例如公众号通过疫情通报获得流量收入),该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属性,相应收入不能被定性为纯营利性收入,而应给予税收豁免的待遇。同理,互联网企业的某些行为是在给行业提供基础设施,例如阿里巴巴作为最大的电商交易平台,从事了平台建设、交易规则构建等方面的工作,为众多互联网企业提供了交易渠道,这些行为在本质上也是在供给公共产品,同样也不应对相关收入课征税款。
(四)能否通过营商环境影响评估
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导向。税费负担水平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税费负担过重会束缚企业的发展,是营商环境不佳的表现。开征数字服务税必然加重某些互联网企业的税收负担,但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将税负的主要承担者限定为互联网行业的“头部企业”,从而使税法规制更为精准,中小企业也能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更需要强调的是,优化营商环境不意味着要迁就企业,而是要为其发展营造公平、规范、有序的外部环境。在此意义上,使互联网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头部企业”享受不应得的税收利益,本就同优化营商环境背道而驰。所以,适时开征数字服务税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企业都能公平竞争,方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营商环境由多个要素组成,除税费负担水平外,还包括但不限于创新活跃度、市场准入难易度、经济开放水平、数据信息保护水平等。开征数字服务税对这些方面的营商环境都有促进功用。首先,因为数字服务税无论在立税初心还是制度设计方面,都具有鲜明的辨证施治特质,使“头部企业”相较于一般企业承担更重的税负,能部分缓解互联网行业内部的力量对比失衡,起到鼓励创新的作用。其次,数字服务税的开征短期内可能降低外国互联网企业进驻我国的意愿,但长期看,此举不过是与国际税收规则接轨,并不会从根本上干扰相关市场主体跨国经营时的行为取向。最后,税收的征取还可能产生正外部性,为开征数字服务税,须有效识别用户参与、数据信息等数字要素价值,这便为其受到公权力保护创造了条件,进而使每个互联网用户都能受益。
立足三维公平竞争的税制设计思路
公平竞争不代表要厚此薄彼,而是指不同行业、类型乃至国籍的市场主体能在大体公平的制度环境中展开竞争。数字服务税的开征本身即有矫正不公平竞争的意图,如何防止矫枉过正以至产生反向歧视现象,也值得思考。
(一)互联网行业与实体行业的关系
前文已述及,相较于实体企业,互联网企业的成本核算较难确定,故而不得不将总收入作为税基进行征收。但须强调的是,该处的“总收入”不是互联网企业全部经营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剔除部分项目后,具有互联网特质项目的收入集合。互联网企业可被视为传统企业与数字经济要素的结合,其有一部分经营活动并无显著异于实体企业之处,仅交易媒介稍有不同而已。这部分经营活动收益已受企业所得税调整,自不应再行征取数字服务税,否则便有重复征税的嫌疑。在正向列举“具有典型数字经济特质的收入”殊为不易的条件下,改由反方向切入,通过排除法厘定税基成为可能的替代性方案。故此,在确定数字服务税税基的过程中,免税项目的确定至关重要。
除根据税法原理和税收政策应一体适用于互联网行业和传统行业的免税项目(如技术转让收入、国家补贴收入等)外,数字服务税的免税项目还应包括如下行为所带来的收入:(1)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数字内容(digital content);(2)通过网络平台提供通信服务(communication services);(3)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支付服务(payment services);(4)管理法律明文规定的应受监管的金融系统和金融服务(regulated financial systems and services);(5)仅以购买、出售和投放广告为目的而利用网络平台;(6)集团内部不同企业间的服务(intra-group services);(7)不以广告为目的,不通过网络收集信息的数据销售行为。(28)张春燕:《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的出台背景及影响分析》,《国际税收》2020年第1期;孙南翔:《全球数字税立法时代是否到来》,《经济参考报》2019年8月7日;See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igital services tax o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digital services,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taxation-1_en; see LAW no.2019-759 dated 24 July 2019 concerning creation of a tax on digital services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downward correction of the corporation tax; see Finance Act 2020,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20/14/contents.这些免税项目的设置是为了剔除互联网企业所实施的本质上仍属于提供传统服务的行为。
(二)互联网行业不同企业间的关系
在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兴起相对晚近,若干先行者因其先发优势而迅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进而在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方面较之其他互联网企业具有碾压性优势。公允地讲,这些企业享受一定的先发优势是合理的,但稳固而难逢挑战的优势地位则并非合意。传统意义上的平台是给交易当事人提供渠道和信息的第三方,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企业作为数字平台,不再简单扮演居间人角色,同时也具有交易当事人的身份,而且其还能制定交易规则,从而有能力将资源倾斜投放到自营业务上,剥夺本该属于平台内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机会,因之获取强大的自我扩张能力。此外,相关平台还可通过制定“二选一”“限制定价”等规则,打压同行业初创企业的发展。若放任“头部企业”扩张,消极后果自不待言。
由此出发,立法开征数字服务税应当体现差异化规制的思路。目前,大多数国家开征或拟开征的数字服务税皆采取比例税率,无法实施差异化调节。采行超额累进税率,基于总收入的不同设定多档税率,以实现“阶梯式”税款征收,能够抑制“头部企业”垄断式发展,一定程度上抵消其仅因“先占”而获取的优势地位,促进相关领域的竞争更加充分。总体上,不妨使税率级次稍微细密一些,对其中较低几档适用宽级距、低税率,较高几档所对应的级距则可适当窄一些,税率水平相应高一些,以凸显税法规制的重心,在有效调节互联网行业少数几家企业的同时避免误伤。至于最高边际税率,不应设定过高或过低,过高可能抑制“头部企业”的创新发展动力,还易诱发避税行为,过低则很难真正发挥调节作用。
此外,亏损结转规则也为理顺互联网行业内部不同企业间关系所必需。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有一过程,特别是对创业企业来讲,亏损并不鲜见。互联网企业在某一年度的“收入”不足以真实反映其经济实力,因为这可能建立在过去若干年度“亏损”的基础上。因此,允许其向以后年度结转,更能准确把握企业的税负能力,同时也有利于支持互联网行业新兴企业成长,避免在其熬过初创期的困境并开始获得收益时即课以征税,从而使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格局不至于固化。
(三)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关系
数字服务税的征税对象多为跨国、跨行业的互联网巨头。《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极不均衡,长期由美国和中国主导。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集中在中美两国,其中,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阿里巴巴这七个超级平台占据总市值的2/3。相比之下,欧洲的份额占比仅为4%,非洲和拉丁美洲份额合计仅占1%。(29)陈镜先、周全林:《数字服务税:内容、挑战与中国应对》,《当代财经》2021年第4期。这意味着,各国数字服务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中美两国的互联网企业。鉴此,对中国来讲,如果选择开征数字服务税,由于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并无太多互联网企业成为可能征税对象,故而即便相关规则一体适用于国内外企业,也会使国内互联网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境不利。在税法原理指引下设计相关规则,调和国内外企业的竞争关系,缓解前述不良影响,很有必要。
针对国内互联网企业,一方面,考虑到现今各国关于数字服务税的征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且普遍存在单边税收保护主义的倾向,(30)李辉、张成:《数字经济征税的现实困境、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经济体制改革》2021年第2期。故应基于不同国家税制差别对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影响,积极地与有关国家谈签税收协定,赋予国内互联网企业在已开征数字服务税国家进行产品、服务定价调整的权利。同时,我国还可发挥税法的行为诱导功能,促使跨国经营的国内互联网企业依据各国数字服务税的征税范围,在不同国家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以合理地规避不必要的税收负担。譬如,欧盟数字服务税的应税服务包括“销售收集到的用户数据以及用户在数字界面上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法国数字服务税的应税收入则未包含此项,(31)See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igital services tax o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digital services,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taxation-1_en; France’s Digital Tax Bill,https://www. gouvernement. fr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locale / piece-jointe / 2019 / 04 / 11_taxe_gafa.pdf,2019-07-24.有鉴于此,我国可在税法或相应的税务规范性文件中明确,以销售用户数据作为主营业务,在法国市场销售额达到一定数额的国内互联网企业,其在该市场上的收入可适用低一档的税率。另一方面,从量能课税的角度出发,计算税基时不妨允许互联网企业以境外亏损抵减境内收入。在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上,境外亏损不得抵减境内盈利,这主要是为避免企业虚构境外亏损以损害我国税收权益。但在数字服务税的部分,潜在纳税主体数量有限,很多都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高、获取便捷,故对其境外收入和亏损的核查难度远低于传统企业。在此条件下,可明确境外亏损得抵减境内盈利以契合量能课税的要求,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国内互联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针对国外互联网企业,提高征管效率、确保应征尽征,是开征数字服务税后的核心任务,也是使国内外互联网企业能够实现公平竞争的关键。毕竟,税务机关对国内企业实施征管的便利程度远高于国外企业。就此而言,一要由税务机关牵头,完善第三方涉税信息的收集机制,加快信用平台建设,积极探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CRS)以外的其他涉税信息共享机制;(32)彭敏娇、袁娇、王敏:《数字经济下跨境税收征管问题及路径选择》,《国际税收》2021年第6期。二要推动税收协定的签署,建立多方协同治税的征管模式;三要在数字服务税制中设置反避税规则,防止跨国经营的国外互联网企业滥用税收协定或采用其他手段规避税负。OECD“双支柱”方案中的“支柱二”即旨在打击国际避税行为,值得借鉴。我国若要开征数字服务税,可通过设定最低有效税率的方式,对在我国境内有避税嫌疑、总收入超过一定金额的跨国互联网企业额外征收税款,使其在我国实际适用的税率水平处在合理区间,而不享受不正当的税收利益。
结 论
传统税法在设计制度时更多着眼于实体经济和实体企业,对晚近兴起的互联网新业态和互联网企业的观照严重不足,这导致相关规则适用于互联网企业时未免不敷需要。概括地讲,税收管辖权的确定难由传统的联结度规则导出、数据信息未被现行征税客体框架所涵盖、计税依据难以确定以及税收征管时常遇到技术困难,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四方面问题。通过调整、充实既有的税法规则,如建立“显著经济存在”规则、重新定义机构场所、解释或调整相关税种法上的税目规则、借鉴OECD“双支柱”方案中“第一支柱”关于金额A的确定方法、针对跨国经营的互联网企业实施第三方代扣代缴并征收预提所得税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前述问题,但这些方法各有其不足之处,或是对数字经济的独特属性关注不够,或是在操作层面滞碍难行,或是同某些税法原理有所抵触,推行开来也难以很好调节互联网企业和实体企业以及互联网企业相互间的关系。
与之相比,开征数字服务税更有助于从根本上矫正互联网行业税负畸轻的格局。数字服务税的征税对象具有独特的收益性,不以“净收入”来把握收益也具有理论上的合意性。同时,互联网企业所取得的收益在整体上不存在公益性,只需要将其中具有公益性的部分从税基中剔除即可。“优化营商环境”也不能成为使互联网企业长期享受低税负的充要条件,正如“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一样,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样是优良营商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如要开征数字服务税,应通过在税基、税率等方面妥善设计规则,充分发挥该税种促进互联网行业和实体行业、互联网领域“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国内互联网企业和国外互联网企业等三个维度公平竞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