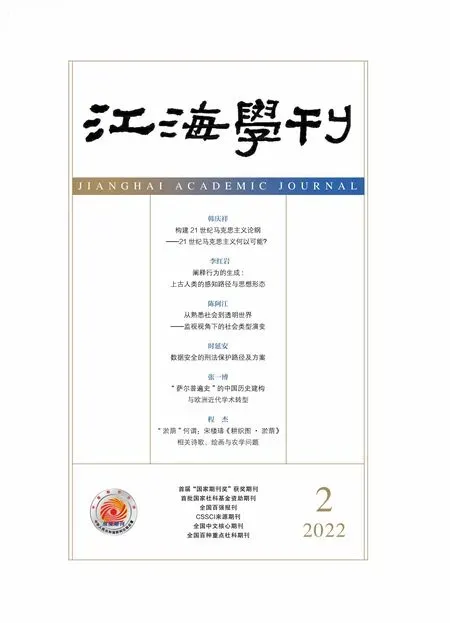机会不平等的历史唯物主义检视*
包大为
政治国家的“完成”无疑是现代社会创生的必要条件。在观念上,这一“完成”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无等级之差的主体身份将不断投身于普遍的合作、社会的良序,从而实现个人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但是,政治国家承诺给人民的平等权利和发展自身的平等机会却并不具有物质基础,是与阶级化的物质生活相对立的抽象生活。政治哲学作为这种类生活的话语形式,不断提供给人们机会平等(equity of opportunity)的愿景。但是,正如鲁迅先生在九十多年前指出,“费厄泼赖”(fairplay)诚然是一个清晰和良善的伦理概念,但在实践中往往会成为纵容压迫者的犬儒主义说辞。鲁迅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道出了平等概念应该回归现实的紧迫性。而历史唯物主义则针对阶级社会的客观规律呈现出了机会平等概念的现实条件和理论限度。
“拒斥”自然的不平等
在政治哲学或者声称具有政治哲学向度的理论中,始终有一种旨在实现机会平等的规范的“冲动”,主张平等主体应该获得趋利避苦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平等机会,而“插队”“走后门”“以权谋私”“垄断”等“搭便车”行为在道德上是无法接受的。这种“冲动”表现出分配性的特征,即获取善的条件在不同主体间的平等分配。但是,若追溯其原初的规定,就不难发现某种先于分配的假设,即社会条件应该允许所有主体平等地进入社会状态。因此,机会平等或机会均等主义可以理解为一个远比分配正义古老的政治哲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社会原则试图对抗自然性,人们一般会循着这个理论意图辨识出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直至阿玛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的漫长的思想线索,将人类的社会性活动视为最可靠的善的根基。(2)Paul Gomberg, How to Make Opportunity Equal: Race and Contributive Justic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7, p.45.
但是,社会性的平等毕竟有其限度。在社会条件无法实现机会平等的情况下,自然性将介入不平等的现实,并由此为不平等提供去道德化的条件。例如在亚里士多德对城邦起源的解释中,自然和运气这两个形式因同时得到了承认。(3)技艺同存在的事物、必然要生成的事物,以及出于自然而生成的事物无关。这些事物的始因在它们自身之中。而技艺与运气相关的是同一类事物。正如阿加松所说,技艺爱恋着运气,运气爱恋着技艺。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1页。在古罗马和基督教哲学中,自然性和偶然性被进一步承认为本体论层面的、高于此岸世界的秩序,支持出身、血缘、族群等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成为等级支配关系的理论奥援。这一时期,人们承认某种“卡理斯玛支配关系”,效忠乃至献身于拥有卡理斯玛特质的世俗或宗教的统治者,呈现出“狂热、绝望或希望”(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7页。的社会心理,接受自然的、必然的不平等的宿命。当然,要维持基于自然性的不平等秩序,就必须保持自然性的社会表征——共同体的纯洁性。因此,古代共同体的统治者通常致力于“高贵”的血统、宗教的苦修、对异族的排斥、战场的英勇行为,并最终促成了关于“主性”的教养和“奴性”的规训。
当然,市民社会的形成逐步瓦解了支撑“主性”及其特权的意识形态外观。曾经不惜“杀身成仁”的“主人”试图将天赋的特权折算成物质利益,而始终无法获得平等人格和发展机会的“奴隶”则突然发现血统、信仰等神圣的自然因素已经成为一门“生意”。这就为启蒙政治哲学提供了客观条件。“天赋”的不平等被视为与公共秩序相对立的恶,基于人格平等和自由观念的政治伦理诉求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理性和科学重新阐释了自然性。未经反思的感觉、现象和宗教情绪被判定为非法,自我成了反思的价值出发点。在本体论层面,机会平等的基础并非是天赋的观念,而是此岸世界中理性存在者的主体身份。理性存在者所能够把握的真理,作为“思想的功能”不是外来的,而是完全“出自我的本性”。(5)[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7页。笛卡尔以降,平等或自由摆脱了自然性主宰的话语。霍布斯进一步指出自然性和偶然性的悖谬,人们之所以把运气当作“偶然事件的原因”,其实不过是“把自己的无知当成自然事件的原因”,其本质不过是“虚幻的哲学”——圣保罗也警告人们“避免这一套”。(6)[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50页。康德则最终把自然性和偶然性排除出了实践理性的立法原则,即认为理性的立法必须“以自己本身为前提”,因为“客观而普遍有效的”法,定然要排除“那些使有理性的存在者一个与另一个区别开来的偶然的主观条件”。(7)[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当代政治哲学延续了启蒙主义“对抗”自然性和偶然性的任务。即使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法律改革者们都为平等理念所引导,这种理念并非来自法律本身,而是法律所必须遵从的”。因为近代以来的“社会的进步”,迫使政府“逐渐变成一个优秀的保护者”,同时又使得法律不断地“在众目睽睽下被公开地修改”——“以期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的平等理念”。(8)[英]赫伯特·斯宾塞:《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谭小勤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事实上,斯宾塞所说的“平等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在市民社会中合法争取、保有财产所有权的平等机会,其底线规范是法律面前平等人格的公民主体身份。这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反对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在私法和公法方面实施的、“在口头上”被承认的“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政治自由主义继承了进一步拒斥造成机会不平等的自然性与偶然性的理论任务。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主要意图就是建构一个更为平衡的分配结构和道德观念。这种分配结构一方面试图补偿和矫正因为非选择性因素所带来的个体不平等境况,减少运气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主体为自己的选择担负责任,使资源分配状况与个体的选择密切挂钩。(10)杨伟清:《正当与善:罗尔斯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作为公平的正义”直接针对自然性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试图为每一个人的自然资质、自然能力和自然禀赋等“自然资产”(natural assets)(11)[荷]佩西·莱宁:《罗尔斯政治哲学导论》,孟伟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因而广受西方左翼人士乃至部分保守主义者的支持。诚然,没有人应该为自己出生时便被给予的“自然资产”(或“自然负资产”)担负道德责任,因为这超出了主观能力的所有范围。换言之,单纯自然意义上的运气谈不上正义或非正义,因而不应该成为伦理思考的对象。但是,从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出现的实践高于技艺(以及运气)、社会重构自然的思想传统,使得诚实且正视现实矛盾的哲学家们不可能不去追问这些自然因素作为潜在的机会不平等在社会状态下的发酵和强化。罗尔斯认为,那些由于先天的自然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在道德上是过于专横的。那些有着众多原因的不平等,只有与正义原则相一致,适合于最弱势群体(the least advantaged)的最大利益,同时“机会的公正平等意味着由一系列的机构来保证具有类似动机的人都有受教育和培养的类似机会;保证在与相关的义务和任务相联系的品质和努力的基础上各种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12)[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269页。才能够避免良序社会所依赖的社会合作的崩塌。但是,良序社会毕竟无法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1页。注定需要机会不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的“滋养”。
偶然的道德
政治自由主义无疑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困境。很显然,由于某种自然性条件,出生时就拥有好运(富裕、强壮、聪慧)的人,在道德上并没有必然的义务为其好运“买单”,让出身就遭遇厄运(贫穷、残疾)的人在社会再分配中受惠最多。毕竟,自康德以降,任何脱离主体理性范围的道德建构就被视为独断,能够潜在造成不平等的先天因素只能被理解为既不是正义也不是非正义的给定条件。德沃金认为,个体必须为主观选择所致的结果承担责任,而非人为——“自然或运气不佳”——的结果则“不适合责任要求”。(14)[美]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332页。事实上,罗尔斯、德沃金,乃至G.A.柯亨所说的“自然的不平等”永远只能是一个“未解之谜”。从潜在走向现实的“自然的不平等”必须经过社会的中介。(15)Lesley A. Jacobs, Pursuing Equal Opportuniti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galitarian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3-54.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即使看起来最自然、先天的机会不平等的社会性中介,而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范畴。因此,风靡20世纪的新自然法传统昭示了政治哲学应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失败,表明伦理建构无法承担起解除政治危机的重任,人们需要做的只是基于私有制的平等观念来不断修正当代法权制度的价值基础。例如H.L.A.哈特等自然法现代“复兴者”一方面承认人类生存状态的脆弱性与不平等的关联,另一方面却无法抛弃私有制法权,最终只能折中地将自然禀赋解释成社会状态下“大体平等”的样态。因为即使是自然禀赋出众的个体也无法时时刻刻保持其发挥禀赋的理性,特别是在睡眠状态下自然禀赋将“暂时地失去了它的优势”。(16)[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这种折中乃至诡辩的解释当然只能满足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在这种自然法之下,平等的内涵被降低至所有主体都有可能杀死其他主体的“对等关系”,(17)例如科耶夫所说的“主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关系在古代社会中表现为不可折算的尊严和名誉,以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决斗等与之相关的法律现象。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机会平等,更遑论分配平等。
当代资本主义向人们呈现出令人困惑的历史特征,即18、19世纪资本主义政治所依赖的小有产者社会结构正在走向终结,代际、族群、教育和收入的不平等,正在表现为高度近似于古代社会的等级化的不平等及其话语。这种话语事实上已经逼退了启蒙的政治哲学传统,使得自然法不得不以“最低限度”的样态来重构当代政治伦理,使得道德与真理成了法律之外的偶然因素——既不值得追求,更不应该付诸实践。一些学者将这种话语指认为新自由主义,而更多的学者则不得不连同人民一起承受着丛林法则在当代不加掩饰的出场,以及由此带来的机会不平等的诸种危机。
首先,公共性的危机,无法从正面回答“搭便车者”问题。在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中,理性主体为了最大的公共福祉而结成良序社会的理想模型无疑在现实中遇到各种障碍,其中最为直接的障碍是“搭便车者”(free riders)行为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直观而言,“搭便车”就是私人对他者和公共利益的攫取,最终造成公共物品总体上的匮乏。虽然作为一个固定术语,“搭便车”在20世纪60年代由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但其实质在18世纪就已经被启蒙政治哲人察觉。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詹姆斯·麦迪逊认为党争大多是由“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引起的,不同的收入群体,由于其掌握的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巨大差距,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18)[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7页。卢梭则更为直接地指出,社会失序的战争状态并不是由“物的关系”,而是由“人的关系”所引发的。物质财富的占有,不仅会影响生存条件的充沛或匮乏,更会造成一部分人拥有支配他人的强力,最终造成社会失序和城邦腐化。《理想国》中“两个国家”(19)柏拉图在《理想国》(551d)认为,如果一个民主政体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就会实际上分裂成“一个富人的国家”和“一个穷人国家”,二者“总是在互相阴谋对付对方”。参见包大为:《重塑公共的立法实践:卢梭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转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旷日持久的对抗,被卢梭表述为“富人将撕破法律的网络,穷人则从撕破的网络中逃出去”。(20)[法]卢梭:《政治经济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页。在当代,“搭便车”行为造成的公共性危机已经远远超出了道德的限度。在古代的等级社会中,“搭便车者”通常是以特权直接剥夺劳动者的贵族。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搭便车者”却隐藏在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背后,控制着从剩余价值剥削到舆论、审美、政治的权力链条。经济上的绝对不平等立刻生成了影响社会文化乃至国家政治的“搭便车”行为。为了将有限资源配置偏斜于垄断者的最大利益,人为造成的价格信号紊乱、市场失灵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为了解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操控国家政治、发动战争乃至毁灭文明成为18世纪有产者无法想象的“搭便车”行为。可见,损耗公共性的“搭便车”现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但是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搭便车”行为背后的“物的关系”却并不能被直接回应。而卢梭或许已经道出了这一理论困境的原因,因为“无论是在无任何固定财产的自然状态中,还是在一切都受法律管辖的社会状态中,都不可能发生私人战争或个人对个人的战争”。(2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3页。
其次,自由主义表象下的合法化危机。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无疑塑造了近现代政治文明,塑造了几乎占据所有合法性话语的治理技艺。自由主义以统计学的方式(投票)将人民的意见转化为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自由主义的行政系统为了维持“搭便车”化的、危机频发的经济系统,不得不将自身塑造成对立面。福柯所分析的国家忧虑症、国家恐惧症,(22)[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危机的“投入产出”机制。“搭便车”行为和“赢者通吃”的利益分配格局反映了作为“产出”或表象的合理性危机(Rationalitätskrise),微观上表现为“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宏观上表现为各类政治主体丧失执行公共理性的能力。在政治层面则更多地表现为作为“投入”的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skrise),“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2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但是,在哈贝马斯所分析的“行政—经济”结构之下,对主体的危机心理和动机影响更为直接的是生存、发展的机会的不平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试图拆除不平等代际传递的制度,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阶级结构“自我复制”的事实。(24)Michael Walzer, Politics and Passion: Toward a More Egalitarian Liber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危机的“投入产出”机制是所有被抛入人世间的个体所生活的客观环境,社会上下流动的空间正在随着金融—技术垄断资本主义的日趋成熟而收窄,而合法性危机不过是应对不断加剧的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阶级矛盾的减压阀。
再次,机会不平等使得权利的抽象性被激化,部分权利主体被他者化。《人权宣言》和启蒙哲人承诺社会整体平等的人格,资本运行和剩余价值剥削的“自由”为所有阶级展示了机会平等的现代样态。这种抽象的平等很快就被大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所否定了。工人的生活要素之所以无法支撑起工人所应该拥有的现代公民的政治身份,是因为他们甚至无法在贫穷和繁忙中满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肮脏、堕落和腐化使得工人的生活条件成了“文明的阴沟”,他们“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5页。遑论拾起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权利,并通过才学、智慧和能力将权利发展为有朝一日主导社会的力量。当然,在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下,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以及被压迫者掌握生存条件的绝望,并不应该得到过多的道德关照。在自由主义话语中,工人阶级被压迫之宿命的“原罪”是具有道德属性的懒惰、不节制,而确保资产阶级能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却是理性、勤奋、节制的。
历史唯物主义对道德方案的祛魅
过去一个世纪,人们一方面忙于应对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应然平等和实然平等、分配平等和程序平等的理论论争,另一方面却放任资本公开地将结构性的不平等转化为历史性的、代际性的不平等。今天,在大多数生产力足以提供公共产品的地区,虽然地域、自然环境仍然作为机会不平等的先天因素,但是却能够以分配正义的方式对最少获利者进行公共代偿。例如在拥有悠久考试选拔传统的中国,高考一方面具有机会平等和阶层流动的严肃程序,另一方面也对少数民族学生或烈士子女有招生照顾。这在总体上体现了平等和正义原则,但是也以差别原则弥补了一些先天的偶然因素造成的机会不平等。然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试图通过差别原则实现机会平等的制度,因为标准模糊、执行不当,也难免会出现“搭便车”现象。
当金融—技术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固化现代阶级结构,并呈现出“新中世纪主义”(26)即“世袭中产阶级”(Patrimonial Middle Class)。参见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2014, p.347.的特征,平等观念愈发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取人民的重要工具。在拉丁美洲,平等观念成为20世纪60年代革命实践仅有的思想遗产之一,转化为解放神学的理论底色。在西欧和北美,平等观念成为各种群体施展身份政治和提出正义诉求的出发点,替代了“五月风暴”之后丧失社会根基的马克思主义。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坚持“消灭”哲学和道德的历史科学,但是都相信着“某种平等”,即使他们拒绝承认作为观念的平等及其原则。(27)G.A.Cohen,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03.总之,在回避政治事件的情况下,法律、教育、经济和政治的机会不平等,正在推动朴素的平等(均等)观念急剧蜕变为某种抽象的道德或宗教意识,启蒙政治中以理性和契约为限度的平等方案也面临着颠覆性的挑战。
其中,最为突出的症候是被“遗弃”的同情。在理性和自觉的行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多数机会不平等都不是偶然的。但是,孑遗自封建社会的偶然的不平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迫使政治哲人不得不在道德的领域寻找解决不平等的方案。如果说苏格兰启蒙哲人对同情的推崇过于常识性,那么在饱受大陆启蒙政治哲学(尤其是卢梭哲学)洗礼的康德那里,同情则成为公民社会的必然特征。康德公开地赞扬“放射出伟大、无私和富于同情心的意向和人性之光的行动”,不是因为其体现了“灵魂的高迈”,而是因为这是“对义务的由衷的服从”。在黑格尔指出“贱民”现象之前,康德已经认识到不平等带来的道德危机及其对现代政治伦理的危害。“只要有人作一点点反省,他就总是会感到一种他以某种方式对人类所承担的罪责”——“我们通过人类在公民状态中的不平等而享受到好处,为此之故别人必然会更加贫困”。(2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210页。但是,康德式的作为义务的同情在当代已然失败。这不仅是因为小有产者社会及其政治伦理已经荡然无存,更是因为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一部分无产者(例如工头、技术专家或白领)宣称对阶级地位的离弃,以丛林法则来看待不平等,将自己视为应然的胜利者和机会平等的实然结果。因此,哈特的观点已经表明当代自然法与启蒙主义的断裂,作为一种公民社会义务的同情被“遗弃”了。主体即使对同情、博爱等道德有所坚持,也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因为“有些人从值得牺牲的审慎考虑出发,有些人从对他人利益的无私出发,有些人则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规则本身值得尊重而立志忠于它们”。(29)[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193页。诸如政治自由主义试图以康德的路径去建构适合现代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政治伦理,然而却同样也排斥了作为义务的(过于厚重的)同情及其平等观念。
这种转变表明了生产领域已经被改造为一个自然的先天条件(正如古代人必须面对等级社会中的血缘和出身)。这个生产领域一方面生产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使得人口当中的一部分注定要在贫困、失业和沮丧中度过一生;另一方面则不断地滋养着规训劳动力后备军的政治力量和暴力机关。尽管人们总是能够找到社会底层“逆袭”为成功人士的案例,但是这种生产不平等的机制是结构性的,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无法获得发展机会的普遍事实是绝对的。当然,仍然有一些足以构成意识形态却无法改变现实的方案为舆论津津乐道,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对这些方案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尤其是在道德层面被人们大加推崇的慈善和教育。
关于慈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有教养的”英国人以慈善机关来遮盖剥削,但是其实质却是“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虚伪地施以小恩小惠,以使自己感到满足,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大慈善家的姿态”。(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78页。这种现象在当代并没有消失,甚至“收买”了一部分齐泽克所说的“自由派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对利润的残忍追逐可以用慈善来抵消”,但是慈善不过是“隐藏经济剥削的人道主义面具”。(31)[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唐健、张嘉荣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慈善财富的来源是非人化的生产。这种生产“不仅把人当做商品、当做商品人、当做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1页。甚至最终将道德本身也纳入了商品化的生产。慈善为资产阶级收获了道德,但是却造成了工人身体、智力和道德的衰退。慈善所依赖的治理技艺,其设计和运行都遵照着对工人道德的摒弃和忽视。在卡夫卡所说的“法律之门”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获得正义的机会并不是平等的。因为这种法律属于一整套为工人所设计的制度,“当工人向资产阶级步步进逼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法律来钳制他们;就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一样,资产阶级对工人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28页。
关于教育。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但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教育对阶级社会的主体性塑造和规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流水线的附属物,无产阶级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在超大规模社会化大生产中所需掌握的技术和知识越来越少。教育虽然是一种公共的乃至国家的职能,但是却大张旗鼓地经历了产业化的过程,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足以塑造出下一代无产阶级的教育,同时又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学识、教养和社会资源。或许有人会有疑问,降低无产阶级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难道不会损害资本主义生产力吗?毕竟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资本竞争的关键是人才。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当代劳动方式中的极小一部分,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经发现,大机器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大部分都不识字,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服务”机器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识教育”,这就使得这些工人“很少有机会接触技艺,更少有机会运用判断力”。(34)《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8页。在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尽管高等教育仍然向无产阶级开放,但是代工厂和外包生产线的机器“附庸”式的劳动能够更为直接地向劳动者提供低门槛的就业机会,最终出现了大量无产阶级的子女放弃高等教育乃至高中教育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教育所隐含的位置善(positional good),而是因为相比简单劳动所带来的直接、确切的物质资料,教育有可能带来的不同阶级平等竞争的机会更为抽象、遥远甚至渺茫。一些第三世界的人民或许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将进一步造成人与人在智力和知识方面的不平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在第三世界寻觅廉价劳动力,高精尖的研发部门以及相应的高等教育体系则留在了资本输出地。原本应该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更多公共教育服务的空间被挤压了,畏惧失业甚于失败、畏惧贫穷甚于平庸的无产阶级,被迫理性选择成为机器、技术和代码的“附庸”,成为“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35)《资本论》第1卷,第460页。阿尔都塞通过分析“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社会技艺的再生产指涉为社会关系再生产。朱迪斯·巴特勒认为,社会技艺通过劳动和教育得到再生产,后者则塑造了主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被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先在于主体本身,事实上构成了主体性的再生产。(36)Judith 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17.
事实上,强调慈善、教育或再分配体现了一种足以维持社会合作的差异原则实为扬汤止沸。这些所谓差异原则的举措,试图弥补无产阶级在物质善和位置善层面的结构性匮乏,但是这些匮乏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结构性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主动地扬弃阶级社会(即使成为自身的掘墓人,那也是非自觉的)。无产阶级的生命的一大部分,注定要以物(财富)的、剩余价值的形式被资产阶级所掠夺,亦即“工人实际上一直为自己耗费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要转化为资本家耗费的劳动时间”。(37)《资本论》第1卷,第364页。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和生产过剩风险的加剧,当代无产阶级不得不承受越发公开的“强度更大和更加紧”的劳动,“骇人听闻地超越劳动时间的自然界限”(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页。的现象将不再鲜见。与此同时,作为机会不平等的典型表征,强制分工所带来的别无选择的异化劳动将加剧工人的“颓废堕落”,感官至上、拜金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工人社区肆虐。因为“强制劳动”是“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目的的”。(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32页。强制劳动不仅把人“动物化”,甚至把人“器官化”。在劳动过程中,大多数器官(包括一部分脑力)都无法发挥作用,在劳动的不过是人形的双手或双脚,“工人的活动都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重复着,年年如此”。(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32页。这种“动物化”和“器官化”在生产空间之外则更为明显。由于始终没有机会和时间像资产阶级那样发展自己的兴趣,抑或通过“想走就走的旅行”开拓自己的视野,在异化劳动的疲惫之余,无产阶级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0页。酗酒、好赌、噬辣等刺激感官和心理状态的极端行为,不过是这种异化生活状态的表征。
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回顾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对机会不平等的历史唯物主义洞见。无产阶级从过去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机会不平等,并不是无产阶级在生产和生活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要让公共善向创造者——无产阶级平等地开放,从而激发占人口大多数的阶级在兴趣、理想乃至乐趣中迸发其创造力,就必须超越作为“庸俗伎俩”的“等价交换的平等观念”,(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让人民在“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中成长。(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58页。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实际的”——而不是“表面”的平等,亦即通过社会主义乃至更高形式的生产关系消除机会不平等的先天物质因素。(44)越是分散的私有制,越无法为小有产者提供平等进入市场、社会竞争的稳定物质条件。例如19世纪中期的法国小农,“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