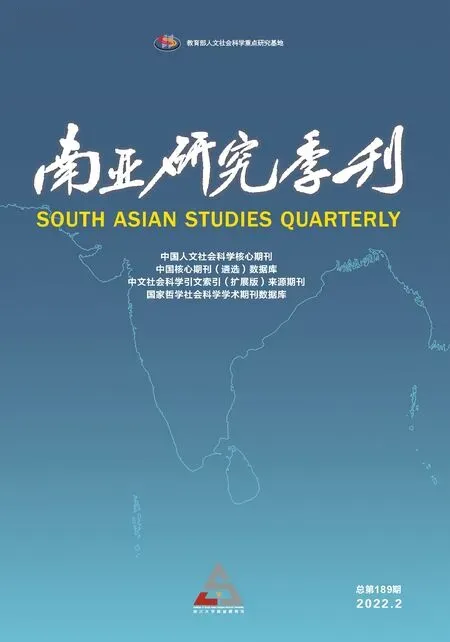阿富汗政治演变进程中的部落因素解析*
杜 军
【内容提要】 阿富汗的政治演变与部落社会密不可分。部落缔造出了阿富汗近代首个以普什图族为代表的部落制国家,同时开启了阿富汗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不论是君主制、共和制,还是塔利班时代,均可看到部落体制对阿富汗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产生的影响。部落与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二者常常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虽然长期遭遇战乱,阿富汗的部落至今依然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本世纪初,阿富汗在内外力量的主导下开启了国家重建和民族和解进程,部落因素仍不可忽视。随着阿富汗局势的演变,受部落影响的塔利班实现了自我变革以及再度崛起,与此同时,部落也留下了深刻的塔利班烙印。历史反复证明族群与部落是阿富汗社会的核心纽带。塔利班再度执政后凝聚民族共识、构建统一和谐稳定的阿富汗仍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阿富汗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具有鲜明部落社会色彩的伊斯兰国家,其历史处处充斥着自身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多民族互动、部落社会、伊斯兰教,以及外部势力干涉等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在阿富汗个别原始现象长期存在,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部落就是这种现象之一。在阿富汗历史上,它一直试图重登历史舞台,因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1)孟庆顺:“试论阿富汗杜兰尼王国的性质”,《西亚非洲》,1987年第6期,第60页。普什图部落是阿富汗部落社会的主体,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部落组织。部落社会不仅是阿富汗最重要的社会组织,而且还是政治认同的基本来源。(2)闫伟、刘伟:“部落问题: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制度困境与社会危机”,《南亚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4页。
从国家内部层面上看,自近代阿富汗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其国家形态一直保有深深的普什图部落烙印。(3)1747年建立的杜兰尼王朝普遍被视为阿富汗民族国家形成的开启阶段。部落制(Qawm)(4)“Qawm”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其意思为“家族、以地方为基础的稳固结构”。与国家加强中央政府职能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成为阿富汗近代国家构建的一个核心问题。
阿富汗的民族构成较为复杂,各主要民族生存和繁衍的重要单元均依托区域性和封闭性较强的部落,例如作为阿富汗第一大民族的普什图族是最典型的部落族群。广义上,阿富汗的部落社会泛指其国内基于传统而形成的以部落为单位、以宗族为纽带的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具有半独立性或较大的自主性,每个单元内都具有维持该单元有效运行并得到成员一致认可和遵守的各种机制和基本规则。对于大多数阿富汗人而言,他们的部落代表着政府。(5)Alexander Charles Guittard,“Qawm:Tribe-State Relations in Afghanistan from Darius to Karzai,” Boston College Electronic Dissertation,2001,p.2.在中东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中,以部落民主制为核心的治理制度经过几千年发展最终保留下来,演变至今成为当前中东地区政治体制中特殊的部落文化模式。(6)刘锦前:“当前中东政局新发展中的部落文化因素分析”,《世界民族》,2014年第6期,第22页(7)“中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东主要指西亚地区,而广义的中东地区范围与界限较为模糊。可泛指位于 欧、亚、非三大洲接合部的北非和西亚地区。作为亚洲重要枢纽国家阿富汗也属于广义上的中东国家。而这种结构在阿富汗具有浓厚的历史传统而且极具广泛性。
阿富汗是扼守中亚、南亚和西亚的门户,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这一独有的地缘政治特性成为阿富汗发展易受外部影响的重大因素。在阿富汗近代国家构建和发展进程中尤其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对其渗透与影响。由于部落社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外国势力对阿富汗的干预策略中也包含了与各地方部落势力的互动和联系。部落社会与阿富汗的政治演变及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以部落社会的特征与发展脉络作为观察阿富汗政治发展进程的视角,能够为观察和分析阿富汗问题的历史与现实提供特有的思路与解决相关问题的路径。
一、近代以来的阿富汗部落与国家 (1747—2001)
(一)君主制时期的部落与国家
部落体系由若干个家庭串联而成的宗族组成,它像是塑造阿富汗历史发展的一套模具,将一切历史文化囊括其中。这种部落社会的传统深刻影响了阿富汗君主制的特质。
在阿富汗历史上,杜兰尼王朝是第一个把所有阿富汗人联合在一个国家之中的王朝。部落首领作为政治领袖,在遇到国家危机时,以传统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招募他们的部落力量,并带领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入侵者。这种传统的方法使阿富汗的汗王或部落首领在1747年通过支尔格大会(或议事机构)选举普什图族阿卜杜勒部落的艾哈迈德汗为君主,建立了近代阿富汗国家。(8)Nassi Jawad,Afghanistan:A Nation of Minorities,London:The Minority Rights Group,Brixton,1992,p.9.阿富汗王国的建立是部落首领自愿联合的直接结果,他们在民众和宗教领袖的支持下获得了合法地位。(9)Louis Dupree,Afghanistan in the 1970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Inc.,1974,p.14.1747年杜兰尼王朝的建立是一个分界线。此后,“阿富汗”不但是用来界定所有普什图部落,而且是用来界定包括生活在阿富汗土地上各民族、各部落的国家名称。(10)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8页。
阿富汗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难以回避的难题是如何平衡具有深厚根基的部落传统和代表阿富汗民族的国家政权二者之间的关系。君主制时代中央政府的实际运行往往要在多重因素中维持平衡。虽然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于国家进口了现代化的坦克与飞机,阿富汗国家军队才变得强大到足以击败一般的部落起义,而这种优势只持续了30年,随着70年代后期反抗亲苏政权的斗争和军队叛乱而崩溃。此后,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成功地垄断整个阿富汗的武装力量。(11)Antonio Giustozzi, The Army of Afghnistan: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 Fragile Institution, London: C. Hurst & Co.,2016, pp.124-131.因此,发轫于近代的阿富汗部落型国家呈现出兼具部落特色与古代帝国治理遗产的二元形态。
君主推行各项措施尤其是改革需要构建国家与部落权责共识和力量平衡。(12)在阿富汗历史上当然也不乏具有政治抱负且敢于突破部落藩篱的君主。例如,19世纪末期拉赫曼成为阿富汗近代化根基的奠基者,20世纪初的阿马努拉一度引领阿富汗步入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行列。二者都试图打破部落社会的约束,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拉赫曼推行将南部的普什图族向中北部强制移民和迁徙的政策,从而对部落分布及民族构成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从整体上对阿富汗部族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开明君主的阿马努拉曾经仿效西方及中东新兴国家土耳其,推行过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改革,然而由于他在国家与部落利益平衡和妥协方面缺乏长远的思路和理念,导致其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二者往往呈现出相互利用或相互合作的态势。政府为了实施更加有效的管理采取强制措施在二者之间建立了协调和沟通的桥梁。
君主制时代的历任统治者都试图打造一种集“阿富汗民族与普什图文化”于一体的广泛性民族认同。阿富汗普什图民族身份本身虽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从来未能以强大的民族主义姿态要求普什图人完全忠诚。部落和宗教忠诚一直并且依旧非常重要。国家的贫困状况和农村人口对教育的冷漠使阿富汗无法模仿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通过广泛的农村公立学校系统灌输明确的普什图民族主义。(13)Anatol Lieven,“An Afghan Tragedy:The Pashtuns,the Taliban and the State,”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63,no.3,2021,p.12.
(二)苏联入侵引发阿富汗部落国家关系的变化
1973年7月17日,阿富汗发生军事政变,由苏联支持的亲贵达乌德推翻查希尔王朝,成立阿富汗共和国。随着苏联的全面渗透,阿富汗不可避免的被苏联深度控制。阿富汗立国的“外交中立”政策难以维系,其封闭的地理环境、脆弱的经济基础及对外资的极度依赖造成苏联对阿富汗全面介入与控制,最终苏联于1979年12月全面入侵阿富汗,并建立了亲苏政权。
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和控制不仅改变了普什图族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对部落体制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一方面,大量难民营的出现冲击着原部落格局。苏联的占领以及与抗苏势力的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难民潮的出现。大量普什图族,尤其是位于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部落被难民营取而代之,这一状况对普什图部落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14)Jonathan N Amato,“Tribes,Pashtunwali How They Impact Reconcil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Efforts in Afghanistan”,Master Degree Thesis of Arts of Georgetown University,16 April 2010,p.15.原普什图族部落所依赖的地区、聚落和血缘亲属集团被战争破坏,各部落赖以运行的载体和环境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宗教势力的崛起削弱了传统的部落体制。在阿富汗部落社会中,“大家长”(即“马利克”或“汗”)和宗教领袖“毛拉”共同掌握着部落的权力。掌握世俗权力的大家长是沟通国家和部落的重要的媒介。他们既是部落的最高领袖,同时也是政府在各部落的代表,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君主制时代统治者往往通过部落的大家长实施间接统治。反苏战争爆发后,国内各部落成为各类宗教性质的反抗组织动员的对象。原来的治理体系已被亲苏政权所取代,各部落最高首领的家长制受到政府的约束或取缔。掌握宗教权力的毛拉等宗教阶层在难民组织中成为唯一的权力代表。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德奥班迪”(Deobandism)及“萨拉菲主义”(Salafism)组织掌控着大批难民营。这些组织也成为沟通难民与外界,以及外界提供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唯一管道。毛拉因而成为掌握各种权力的领袖。(15)Ibid.
在反苏战争期间,作为阿富汗邻国的巴基斯坦成为阿国内各类“穆贾希丁”(Mujahedin,意为“圣战者”)的重要援助国。大量阿富汗普什图人因战争而逃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本土扶持各类圣战者组织,以物质和宗教并举的政策对抗阿富汗的普什图民族主义。巴基斯坦在国内成立了许多与阿富汗难民有关的宗教学校或教育机构。
巴基斯坦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将宗教做为对抗阿富汗意识形态武器,使得毛拉成为部落核心。获得宗教政治双重权力的毛拉采取措施改造原有的部落体制,其中最典型的做法是削弱部落支尔格(16)“支尔格”(Jirga)是阿富汗历史悠久的冲突解决机构。在普什图语中为“议会”或“国民大会”。支尔格被视为“长老大会”,由“受人尊敬的人”和非正式的政治领导人参与,通过对冲突或争端各方有约束力的决定来解决问题。案件的解决方式依据为伊斯兰法和普什图族的习俗。的地位而提升舒拉(17)“舒拉”(Shura)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协商”, 通常指穆斯林通过相互协商来决定内部事务。在阿富汗舒拉特指宗教阶层以理事会或公民投票的形式组织的协商会议。舒拉经常用于组织清真寺、伊斯兰组织的事务。的作用。这些措施打破了各部落间原有规则所设立的界限,将各成员以非部落和宗教情节的范式加以整合。
(三)内战与塔利班政权时期的部落与国家
1989年2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很快陷入内战。多元化的族群争权模式的开启旋即加剧了阿富汗的动荡。1992年4月24日,在联合国斡旋下,阿富汗各主要武装派别在喀布尔举行谈判,准备组建临时政府。各派最后签署了《白沙瓦协定》,成立过渡政府。(18)美国和巴基斯坦支持的东部普什图地区军阀希克马亚蒂尔未参与。难以弥合的派系分裂与冲突,裹挟着民族与宗教矛盾的军阀混战拉开帷幕。这一局面直到1996年塔利班崛起而结束。
塔利班上台后又推行了一系列极端政策,公开反对阿富汗的传统部落体制与阿富汗民族主义认同。这不仅与部落体制难以调和,而且极端保守和反现代。其反部落的基本政策正是反苏战争以来由巴基斯坦支持的以宗教对抗民族主义政策的延续。
然而,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塔利班面临着各种突出的问题。长期以来,塔利班政府脱离阿富汗传统,其以浓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政策难以获得认同和推广。与北方联盟的长期对抗和孤立的发展环境,反部落政策造成部落与塔利班的冲突成为塔利班执政的重大挑战。因此,在塔利班运动崩溃和纯伊斯兰教社会建设思潮出现危机之后,阿富汗社会的部分普什图族重新开始回到了传统部落组织形式上来。(19)汪金国、王国顺:“论阿富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部落症结”,《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23页。
二、阿富汗部落与民族和解进程(2001—2021)
(一)后塔利班时代的和解进程
2001年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联合退守北部的“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发动阿富汗战争,一举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战争胜利后,阿富汗建立了新的民族联合政府。随着以塔吉克族等非普什图族为代表的北方联盟入主政坛,普什图族居主导地位的格局从此结束。此后,阿富汗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组织协助下进行新政府的重建。2001年底《波恩协议》的签署正式确立了阿富汗的政治和平进程和重建进程。与此同时,被推翻的塔利班残余势力退守在阿富汗边境及山区,继续与阿富汗政府鏖战。
2010年4月阿富汗政府提出名为“和平支尔格”的重构和平计划,拟邀请国内各部落以及反政府组织代表以和谈的方式共商国是。阿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和谈促和解”代替军事对抗的新思路。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和族群对立的问题,政府多次向塔利班抛出和解的橄榄枝。安全计划的尝试最终在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专门会议中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和解计划不仅成为解决安全问题的新方案,而且与和平过渡路线图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既体现出阿富汗政府施政思路的灵活,也体现出民族和解的宏观视野下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决心。
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的和解进程包括两大主题。一是与塔利班组织进行政治谈判,争取在国家建设和决策中达成谅解和共识。(20)Ashley J.Tellis,“Reconciling with the Taliban?Toward an Alternative Grand Strategy in Afghanistan,”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9,p.2.二是“采取措施让地方反叛势力的指挥官以及追随者重新回归融入阿富汗社会”。(21)Office of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Afganistan and Pakistan,“Afganistan and Pakistan Regional Stabilization Strategy,”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Updated 15 February 2010,http:∥www.states.gov/documents/organizaion/135728.pdf.前者多针对塔利班及其他抵抗组织的高层,后者主要针对抵抗组织的中下层成员。虽然他们参加塔利班的动机和原因各不相同,但和解意味着使他们重新融入阿富汗社会,如何为他们提供各种社会生活与安全保障则是关键。
(二)部落机制与阿富汗政府主导下的民族和解
和解问题一直是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政治进程中的一大主题。部落体制依旧能发挥政府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阿富汗的部落体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经历了塔利班的伊斯兰化政策影响之后,各部落的宗教属性及其影响大大加强,同时其世俗层面的政治属性也被显著地削弱。部落体制虽然屡经战乱冲击和破坏,无法和政府部门直接对接,然而部落体制仍具有难以替代的社会效应。
首先,部落首领、长者等部落高层能够在和解进程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部落首领历来在各部落中居于核心地位。族群首领或重要的非官方长老是以聚落为基础的传统领袖,他们关心的是自己聚落的福利,而不是其他。虽然这些非官方的部落和社区领袖大多不担任公职,但他们是阿富汗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成员。(22)N. Nojumi,The rise of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Mass mobilization,civil war,and the future of the region,Palgrave Macmillan,2002,p.5.在国家重建与和解时期,部落在阿富汗的地位也经历着恢复和重塑。部落中的首领和长者在重新树立部落权威的过程中担任政府与塔利班组织之间的中介和调解者角色。阿富汗政府于2005年成立了“国家独立和平与和解委员会”(PTS),该组织专门负责与塔利班高层接触与谈判,各部落首领以及宗教领袖成为重要的见证者和沟通者。政府代表在部落高层构建的和谈平台上就他们未来的身份和境遇展开谈判。假如他们接受政府的出价,这些反叛者将会获得一式三份的证明信。一份自留,其余交与政府与北约。(23)Antonio Giustozzi,Koran,Kalashnikov,and Laptop:The Neo-Taliban 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pp.206-207.部落首领曾在政府与塔利班谈判中扮演着沟通渠道的作用。
其次,部落曾在实施塔利班成员身份改造及其社会融入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放弃对抗转而拥护政府的塔利班成员接受改编,仅仅意味着赦免环节的结束。随后他们还将面临重新融入社会的长远挑战。除政府外,部落在为接受和平改造的前塔利班成员提供庇护、防止原组织的骚扰以及打击报复等方面作用显著。塔利班的宗教属性较为突出,将前成员纳入部落机制后能够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加强其对部落和族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淡化其意识形态特性。
再次,普什图瓦里(24)普什图瓦里(Pashtunwali)是普什图社会特有的道德准则总称,也可被称为“普什图法则”。参见张敏:《阿富汗文化和社会》,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钱雪梅:《普什图社会的政治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4-85页。与支尔格机制在民族和解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普什图瓦里作为习惯法,是部落运行的重要依据和规范,对塑造部落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即使是宗教特性极为突出的塔利班也深受普什图瓦里的影响。塔利班组织曾与“基地”组织过从甚密,在面对美国政府的警告时也不愿与其划清界限,塔利班的思想和行为根源显然与部落习惯法中庇护原则息息相关。在塔利班看来,若交出“基地”组织与其领导人,不仅有悖于普什图瓦里的规则,同时也影响其公共形象,不利于组织的团结与稳定。塔利班组织的扩大也和普什图瓦里中的复仇原则有关。许多普什图人认为北约军队清缴塔利班的行动不仅违背了普什图习惯法,而且也伤害了民众的情感和荣誉观。因此,依普什图习惯法规定,他们有权拿起武器为受到侮辱和丧生的家人报仇,而同情、支持塔利班组织是他们复仇的唯一选择。
普什图瓦里的应用是部落习惯法中的平等原则与宽恕原则的体现和贯彻。在所有普什图人看来,部落习惯法是他们心目中期盼的理想,甚至那些没有严格执行习惯法的群体也对它极为重视。(25)Jonathan N Amato,“Tribes,Pashtunwali How They Impact Reconcil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Efforts in Afghanistan”,Master Degree Thesis of Arts of Georgetown University,16 April 2010,p.23.习惯法中处处体现着普什图人追求的内核,即荣誉。所有成员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捍卫集体或者个人的荣誉。彼此之间的竞争以及结仇的双方进行较量的终极目标都关乎荣誉。在国家的和解进程中,普什图瓦里的作用可以体现为平等原则的强调和调解手段的实现。平等与调解两大功能曾经发挥过改造塔利班中下层成员的重要作用。以平等为基础,支尔格或舒拉发挥其争端调解机制的作用,既宽恕对手又维护了荣誉。
部落首领、普什图瓦里和支尔格在普什图部落体系中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在国家建构层面,参与和解进程的各方对吸取以往支尔格与现代国家制度融合的经验极为重视,最终仍以大支尔格会议作为制定阿富汗新宪法及推举领导的机构。而在偏远的山区和农村,民众往往更加信任基层支尔格的作用。微观层面的事务只需经地方或部落支尔格调解即可。在部落民众看来,前政府机构往往效率低下且腐败不堪。从阿富汗的历史可以看出,大支尔格在政局稳定时极为有效,这也使人们选择将大支尔格作为战后恢复秩序、走向和平的重要工具。(26)蒲瑶:“支尔格:阿富汗解决重大问题的传统社会组织”,《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7页。
然而从结果看,和解进程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2001年以来,美国无视阿富汗的历史与现实,强行在阿富汗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其对阿富汗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改造”最终遭遇“水土不服”。由于北约成员内部矛盾重重,而美国当局无暇关注阿富汗,塔利班似乎找到了战略良机。他们试图将西方人拉入持久战,这一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27)〔巴〕艾哈迈德·拉希德:《塔利班》,钟鹰翔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243页。西方政府与相关组织清剿塔利班的军事行动最终也遭遇挫败。美国从最初的野心勃勃到后来的战略收缩,直至最后完全撤军,这一系列挫败使阿富汗重建与民族和解归于失败。
一方面,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都将部落视为拓展地区认同和拉拢对象,各普什图部落的认同始终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自2002年以来,美军一直试图利用部落来打击塔利班。特别是在霍斯特地区采取的举措较为典型。为了利用当地部落对抗塔利班,驻加德兹的美军成立了驻扎当地的第一个“省(级)重建队”(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简称“PRT”)。其性质是小型军民单位,主要是协助省和地方政府更有效地治理和提供基本安全、医疗卫生等服务。其年度预算为数千万美元,重建计划赋予当地指挥机构能够与地区部落交涉,并参与管理地方农业等方面的重要项目。
另一方面,塔利班组织并未因政权更迭而退出历史舞台。战争结束后,阿富汗逐渐形成了西方支持的阿富汗新政府、以非普什图族为主的北部反塔利班民兵以及塔利班三股力量并存的局面。失去政权的塔利班成功地在南部普什图部落地区站稳脚跟,甚至能有效的弥合敌对部落间的分歧,有时以杀害或恐吓的方式向反对他们的部落长老施压,试图反抗的部落在所辖范围之外的活动能力因此受到了极大限制。地方部落被迫与塔利班达成利益妥协,塔利班允许各部落从省重建队获取资金。作为回报,各部落许诺塔利班武装可自由穿行于各部落地区。部落地区既是阿富汗政府重建与改造的对象,同时也成为塔利班蛰伏与积蓄力量的平台。随着国内形势向塔利班有利的方向发展,依托部落实施变革与发展的塔利班实现了崛起。
三、塔利班再度掌权与和解进程(2021年至今)
2021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驻扎在阿富汗的2500~3500名军队将在同年9月11日前撤离阿富汗,受到鼓舞的塔利班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势如破竹,并在8月16日宣布再次掌控阿富汗。部落体制在塔利班重掌权力后体现为二者相互结合及相互影响的新格局。
(一)部落格局影响下塔利班的革新与重组
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再次退居南部山区及阿巴边境,尤其与南部普什图部落构建了紧密的关系网络。长期在阿富汗山区普什图族聚居区深耕与经营对塔利班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在反美斗争期间迅速融入地方并反客为主,把部落地区发展成抵抗运动的大后方。
首先,部落促成了塔利班的“更新换代”。部落地区的人口结构与格局受塔利班影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再度执政的塔利班成员发生了更新换代。塔利班的第一代组织来自普什图南部的村落,最初意识形态似乎是1979年以前南部普什图人村庄生活规范的复制品。(28)Anand Gopal and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AAN Thematic Report,January 2017,p.11.塔利班的第二代成员并非直接与苏联作战的一代。相反,他们出生于巴基斯坦难民营,其父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离开阿富汗前往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出生的新一代在那里接受宗教学校教育,并从设在那里的圣战组织中学会了战斗本领。(29)Ahmed Rashid,Taliban:The Story of the Afghan Warlords,London:Pan Books,2000,p.208.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被称为“新塔利班”,他们被认为更倾向于在阿富汗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不仅仅是维护伊斯兰改革运动本身。其意识形态主张将伊斯兰教和政治治理有机结合。2001年后,他们不再把自己描绘成穆斯林狂热者,而更多地描绘成敬畏神明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将不信教的外国人驱逐出该国。他们利用农村人口的怀疑,即喀布尔政府及其国际支持者试图将外来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们,回避旧的热点问题。他们淡化了先前对严格遵守萨拉菲派伊斯兰教义的要求,并暗示如果再次获得权力,他们将不会像以前那样严苛地对待其他教派。(30)Thomas Barfield,Afghanistan: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327.
其次,部落为塔利班的“影子政府”提供了有利的生长土壤。自失去执政权后,塔利班以高效的地方治理填补了阿富汗政府无法触及的底层权力网络。阿富汗政府的地区治理一直较为薄弱,部落地区民众对地方行政机构由于治理缺失、低效和腐败造成的不安全感深感沮丧和恐惧。脆弱的治理体系使得南部部落地区日益疏远中央政府,认为中央政府受到非普什图人领导人的影响,造成各地区的利益分配不公,并对政府与西方联合实施的治安举措的意图和有效性缺乏信任。
随着阿富汗内部冲突的加剧,塔利班在南部山区建立了名为“奎达舒拉”(Quetta Shura)的武装组织,凭借南部地区的“影子政府”逐步扩大势力。当地人越来越多地转向塔利班法庭,他们认为塔利班法庭比腐败的官方系统更有效、更公正。(31)Rubin Barnett,“Saving Afghanistan,”Foreign Affairs,vol.86,no.1,2007,p.6.塔利班构建的治理机构较为隐蔽,其发挥的区域治理效能往往不为外界所知,却能时刻与阿富汗中央政府构成两条并行不悖的平行网络。在传统的普什图部落看来,虽然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但也非常有限。除了领导人民抵御入侵者之外,它还要对部落纠纷进行裁决,从而防止这些纠纷形成永久性的战争状态。(32)Buzkashi Whitney Azoy,Game and Power in Afghanistan,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2,p.103.塔利班通过提供一系列社会服务维持一种“影子政府”,并显示出招募战斗人员的非凡能力。一般来说,塔利班作为一个组织,在结构上和意识形态上最准确的描述是双重性的。(33)Thomas Ruttig,“How Tribal Are the Taliban? Afghanistan's Largest Insurgent Movement between its Tribal Roots and Islamist Ideology,” Thematic Report,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AAN), Kabul,no.3,2010,p.125.一方面,可以观察到一个垂直的组织结构,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影子国家”的形状;另一方面,塔利班的横向网络也是如此,反映了其在分化的普什图部落社会中的根基。(34)Thomas Ruttig,“How Tribal Are the Taliban?”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Kabul,no.4,2010,p.22.就这样,塔利班分子有了税收制度、影子行政系统、快速发展的(移动的)司法系统(35)作者在著作中所指为非正式地位的“巡回法庭”。和(模拟的)货币。塔利班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卡尔扎伊政府的替代者,至少在各省是这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是使阿富汗无法治理的力量。(36)〔美〕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3页。
最后,塔利班的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能够在维持固有理念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的改革。塔利班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展现出空前团结的面貌。深厚的宗教信仰、对异教徒入侵者的仇恨和坚定的毅力,最重要的是这种团结和纪律使塔利班在喀布尔国家的派系和腐败势力中占据优势,并使它在政府和抵抗运动中发挥传统而重要的作用。(37)Anatol Lieven,“An Afghan Tragedy:The Pashtuns,the Taliban and the State,”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63,no.3,2021,p.23.为了树立在部落地区的权威与威信,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基础具有了更加包容开放的新形态,新理念使他们不再将宗教行为规范作为信仰虔诚与否的唯一评判标准。
(二)阿富汗部落的“塔利班化”
阿富汗的部落格局在美塔对抗时期不断受到两方冲击。相比而言,塔利班对于部落体系的影响与改造更加深刻。当前阿富汗在塔利班统治下部落体系呈现出新的面貌,即出现了所谓“部落的塔利班化”。部落体系在塔利班冲击下实现了自我革新,重新构筑起更强大的基层网络体系乃至于身份认同重塑。这一状况将伴随塔利班执政而长期化。
塔利班重塑了部落地区的政治秩序与规范,在掀起的抵抗运动中一直致力于对乡村秩序与规范的改造。
第一,抬高宗教势力的权威,压制当地原有的部落首领。塔利班通过与部落互动及交往逐渐将原部落长老的角色边缘化,宗教阶层参与部落公共事务决策的作用得到了极大提升。由于每个村庄都有一个毛拉,这也使塔利班有能力系统地深入到每个普什图村庄,以确保其命令得到遵守。这是除阿富汗以外其它(或巴基斯坦,甚至印度)国家从未实现过的。(38)Ahmed,Millennium and Charisma Among Pathans:A Critical Essay in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1976,pp.53-54.塔利班推行分化瓦解策略,注重拉拢妥协派,恫吓、打击亲政府的部落。在少数反对塔利班的部落,经过塔利班分化渗透之后已不具备反塔的实力。塔利班还通过“影子政府”进行裁决纠纷、利益分配、治安管理等治理方式,逐步削弱原部落支尔格或舒拉的权力。
第二,淡化普什图瓦里的影响,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缓慢植入伊斯兰主义理念。普什图瓦里是普什图族传统风俗习惯和民族传统的见证而被世代传承,承载了浓厚的“荣誉观”,彰显出特色鲜明的“血亲复仇”“殷情好客”“宾客至上”和“独立平等”等理念。虽然普什图瓦里不是一套成文的规范,但它仍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文化体系,其中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习惯法关系密切,相互交织,涵盖了普什图部落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普什图人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生活图景。(39)畅红:“浅析阿富汗普什图瓦里的内涵与功能”,《世界民族》,2018年第1期,第73页。
塔利班扎根南部山区之时,力图用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取代部落传统礼仪与文化。普什图部落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本地化的特征较为明显,然而塔利班宣扬的宗教则强调向伊斯兰世界的“普适性原则”看齐。普什图人恪守的“血亲复仇”与“保护宾客”的理念在塔利班的恫吓与威胁之下难以运行。塔利班的强大武装使被害者亲属无力复仇,杀人者得以逍遥法外,“血亲复仇”的古老法则被打破,部落共同体的法律和感情基础遭到动摇。(40)钱雪梅:“美国与塔利班,谁能改造阿富汗?”,2022年3月25,https:∥new.qq.com/omn/20220325/20220325A0D42900.html,2022年4月13日。普什图部落内原有的文化习俗与价值观不断经受着塔利班统治带来的冲击。生活方式是惯例化的实践,这些惯例被整合进服饰、饮食、行为模式以及为遇见他人而设计的舒心环境等习惯中,但是鉴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动态性,被遵守的那些惯例会以反身性方式等待改变。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或创新,会受到诸如群体压力、标杆式角色以及社会经济大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4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6页。塔利班对普什图部落的文化传统与规范产生的影响可能会伴随其执政地位的确立发生更加显著的变动。
塔利班运动已嵌入部落社会,同时也在不断适应部落社会的新变化。但这并不是说塔利班完全是一场部落运动,它一定程度上也超越部落社会。阿富汗战乱将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打破之后,部落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塔利班重构了部落社会的秩序,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部落社会的整合和超越,并向后者提供了急需的安全与秩序。(42)闫伟:“从‘塔利班’到‘新塔利班’——伊斯兰复兴在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形构与表达”,《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8页。
塔利班未来执政仍面临着一些显著的挑战。对新型转型国家来说,战争风险尤高,这些国家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推行稳固的规则以规范人民的政治参与并增强国家权威。(43)〔美〕杰克·斯奈德:《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吴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面对战争的摧残国家仍面临贫困与人道主义危机。目前,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状况十分严峻,获得必要且充足的国际援助成为塔利班施政的物质基础,经济援助往往又与其在国际社会得到的承认直接相关。
塔利班在南部实现了他们的大部分目标,其影响力毋庸置疑。然而塔利班未来可能会面临许多部落及族群的抵抗,特别是在北部,但他们不会像美国所尝试的那样,试图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44)Jeremy Suri,“Why Afghanistan's Tribes Beat the United States,”16 August 2021,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8/16/afghanistan-taliban-tribes-state-withdrawal/,14 November 2021.虽然塔利班并非由单一化的普什图人构成,即使它通过呼吁宗教保守主义在其他民族中获得了大量的支持,但其领导层仍以普什图族为主,并被其他民族视为普什图族的代表。(45)Thomas Ruttig,“Negotiations with the Taliban,”in Peter Bergen,Katherine Tiedemann(eds.),Talibanistan:Negotiating the Borders Between Terror,Politics,and Relig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435-436.面对塔吉克、哈扎拉、乌兹别克等认同度较低的非普什图族群,如何应对民族、宗教信仰多元问题,凝聚共识,成为塔利班更大的挑战。塔利班前一个执政周期的统治表明,以民族(普什图族)为中心的统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不会持久的。这个国家以前即使是在所谓的阿富汗民族的“伪装”下,也经历过重大的族群对抗。两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执政党都来自人口占多数的普什图族。(46)Ahmad Rashid,“Afghanistan:Ending the Policy Quagmir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4,no.2,2001,pp.395-410.能否与其他非普什图民族及其部落实现和谐共处,成为考验塔利班执政实效的试金石之一。正视阿富汗部落与多元族群的基本国情,继续促进民族和解仍将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小 结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曾对国家有如下的经典定义,即“国家是一种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47)〔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这一状况实际上在阿富汗从未出现过,即使是重新夺权的塔利班也概莫能外。纵观阿富汗近代以来的历史,迄今为止的任何政权都无法实现其社会既“清晰可辨”又“尽在掌握”之中。阿富汗的部落传统影响根基深厚,国家建构的历程处处体现着部落制度的烙印和痕迹。制度的最初出现是为了历史上不确定的原因,其中某些制度存活并得以流传开来,因为它们能满足某种意义上的普遍需求。(48)〔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6页。部落社会与政治史的演变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普什图人为核心的君主制度首先在部落体系与伊斯兰教的共同影响下诞生,各君主的统治权威的扩展与部落权益的维护之间形成既斗争又融合的格局。共和制时代部落体制因内外因素冲击受到了一定的削弱。本世纪初国际社会与阿富汗新政府重建及和解进程启动后,部落仍是最突出的国情特点。塔利班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部落因素的影响,塔利班再度执政后的阿富汗仍需在国家重建和民族和解问题上继续探索最适宜的发展路径。族群和部落作为阿富汗社会核心纽带的地位,迄今从未被超越,国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都未能真正弥合族群和部落界限,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难有真正长期有效的替代品。(49)钱雪梅:《国家智库报告:阿富汗的大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美国参与经营阿富汗国家构建失败的案例再次说明,照搬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制度根基并不牢固。基于紧密联系的亲属网络而形成的部落格局经过历史的检验,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对时代变革、外来势力的应对与适应。整体而言,经过历史和现实的部落社会比对,内外环境的综合作用使得当前的阿富汗部落社会既有历史的遗存,同时也与以往存在明显的不同,部落社会无疑为我们长期关注阿富汗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参考视角。
- 南亚研究季刊的其它文章
- 莫迪政府时期印度国防产业的本土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