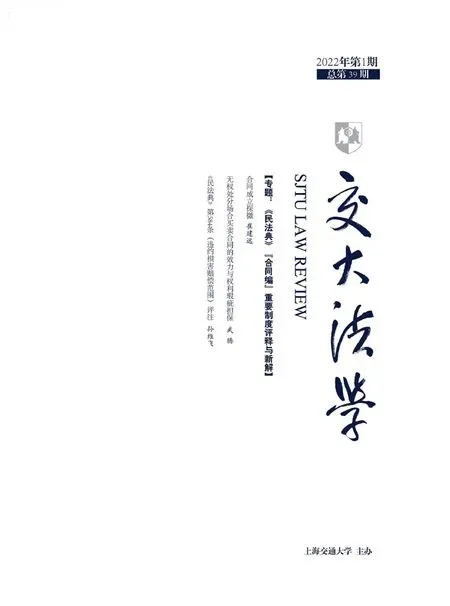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说”之反思: 自然法与功利主义之比较
王传辉
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正当性,目前学界流行“利益平衡说”,即主要平衡知识产权人个人之利益与他人及社会之公共利益。该说也被认为是知识产权法的基本问题、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或基本理论。(1)笔者用“知识产权”和“利益平衡”作为篇名之主题词搜索(2020年3月14日访问),在知网获得论文120篇;如进行主题搜索,则获得2 465个结果。该学说如此流行,以至于“但凡讨论知识产权理论问题,学者们言必称平衡”。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的价值构造: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研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第67页;冯晓青:《利益平衡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载《知识产权》2003年第6期,第16页;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0页。吴汉东教授指出:知识产权法的平衡精神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是“知识产权法律价值二元取向的内在要求”。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的平衡精神与平衡理论——冯晓青教授〈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评析》,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157页。有学者经由经济学分析,指出:“利益平衡观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具有核心价值意义。”参见王新华、梁伟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经济学分析——以利益平衡观为视角》,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57页。张玉敏、陶鑫良、唐超华等学者的教材将“利益平衡”或“利益兼顾”列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参见王玉凯:《反思知识产权领域“利益平衡”》,载《中国版权》2011年第3期,第60页。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之利益平衡:智力成果之创造(创造人)与智力成果之传播和使用(他人),创造者之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2)参见冯涛:《国家干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4—75页。鉴于“他人”为不确定的社会公众,因此他人之利益可归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中。
利益平衡的前提是存在利益冲突。对于利益冲突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知识产品兼具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双重属性。因此相应地,知识产权法具有保护个人利益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元价值目标,(3)见前注〔1〕,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的价值构造: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研究》,第68页。知识产品是个人创造之结果,故为个人产品。产品之创造需吸收和借鉴他人之成果,有社会性,故为公共产品。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法中专有权与公共领域的平衡机制研究》,载《政法论丛》2019年第3期,第57页。通过平衡,可协调互相冲突之利益并进而实现该双重目标。
社会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之限制是传统的、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利益平衡说强调的不是“权利”而是如何规定和限制权利以平衡相冲突的“利益”。依庞德之观点,法律的本质和制度的出发点,是人们的利益、目的和要求。(4)转引自张旭、孙海龙:《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利益平衡原则》,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15页。因此,与权利相关的制度安排之目的是要满足或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经济学上,该利益为法律要实现的最佳收益或效益,权利和义务之安排,如同市场中资源之配置,应达到效益之最优。(5)参见冯晓青:《产权理论中的财产权、知识产权及其效益价值取向——兼论利益平衡原则功能及其适用》,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27页。
很显然,利益平衡说是以结果为目标,有功利主义导向。但与传统功利主义之一元目标相比,它又重在二元目标之协调。值得商榷的是:究竟应以权利自身的正当性还是以权利人和社会要实现的利益作为法律之价值,尚存争议。即使以“利益”为目标,如果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彼此对立和冲突的法律价值或目标,那么它们可以并存作为知识产权法的二元目标吗?如果互相冲突的利益或目标可以被平衡,那么所谓的冲突是否真正存在?或者该所谓“冲突”只是表面上的或局部显现的对立?利益之间,除了冲突,是否还有一致性的存在?
本文通过对比物权和知识产权之客体的差异,阐述自然法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视角下之知识产权之性质,并进而比较分析两种理论下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指出:无论是自然法的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导向,还是功利主义的社会效用导向,知识产权制度都存在着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的“互驳式”的悖论问题,而并非仅仅是“二分式”的利益冲突;知识产权制度之根本问题是法律制度之终极价值选择及其相关的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之分野问题。
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之分类,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及工业设计、著作权及邻接权、商标及地理标记等。(6)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hat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2020), p.5,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450_2020.pdf.从广义上讲,它与有形财产权相对,来源于人的思想,具有一定创新性。(7)See 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77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87, 294(1988).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及相关理论争议主要是以专利和著作权为核心,商标与相关标记作为识别性标记,附随于商品和服务流通,并非知识产权之最典型代表。专利因其创造性和权利的垄断性最强,引发的与他人和社会之利益冲突最为突出,因此,本文论述主要以专利为例。
一、知识产权之正当性:自然赋权抑或法定赋权?
知识产权由立法所规定和保护,权利及其限制共存。权利之限制,主要是在权利之获得和实施两个方面。以专利为例,权利获得之限制有专利申请条件之要求、专利公开要求和专利有效期等;权利实施之限制,典型规定有涉及他人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之强制许可。依利益平衡说,权利和对权利之限制,分别顾及发明创造人和社会公众之利益。同样,物权及其限制,也有类似的利益冲突,同样也可采利益平衡说来说明其正当性。那么知识产权之正当性,相比物权,是否有其不同之处?并且,利益平衡本身未必是正当性,或许只是一种方式或路径,而正当性指向的是“为什么要利益平衡(或者,为什么要限制知识产权)”。如果回答是“要消除利益冲突”,那利益平衡只是消除利益冲突之方式或变通式表述,仍需进阶回答:“为什么要消除利益冲突?”
无论物权还是知识产权,均指向私人财产性质之权利。有关私人财产之正当性,主要有自然法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之阐释。(8)有关知识产权正当性的理论,根据费歇尔的总结,主要有:功利主义、自然财产权、意志或人格说、可欲社会(a desirable society)论。可欲社会论本质上仍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着重未来的以“公正的和令人向往的文化”为目标的社会的塑造。意志或人格说则是在个人财产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权利对于创造者意志表达与人格实现的重要性,从而影响了知识产权法中对创造者精神权利的保护。因此,功利主义和可欲社会论是社会效用导向的理论,自然财产权与意志/人格论为个人权利导向的理论。因此,本文以功利主义和自然财产权这两个基本理论分野为对比进行论述。参见[美]威廉·费歇尔:《知识产权的理论》,黄海峰译,载《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2页。
自然法理论以洛克的“劳动获得论”(labor-desert)为代表。洛克的论证有三步:一是消费资源是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二是人拥有和控制其资源的正当性是:人向外界之公共资源中投入了劳动,因此相对应有权获得财产;三是人通过控制资源,既维持生存,又实现自由。(9)See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Book Ⅱ, https://www.johnlocke.net/major-works/two-treatises-of-government-book-ii, at section 27.总而言之,私人财产作为权利,是因人之劳动所自然获得的权利,为人维持生存和实现自由所必需,为自然法权利。(10)洛克认为的自然法权利为:生命、自由和财产。黑格尔认为人之终极目的是人的自由,私有财产使得人通过对物的支配在物上体现其意志,从而获得人格上的自由。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42页。哈耶克认为财产与自由不可分割,私有财产使得社会中的权力分散,因此保障了个人的自由。See generally F.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art 9.
功利主义理论对私人财产之正当性的解释可以《公地悲剧》为代表,即相比于“公地”,私人财产有利于资源的持续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而“公地”会导致资源浪费和穷竭。(11)See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62(3859)Science 1243-1248(1968).私人财产被认为是可有效配置资源之市场经济的基础。
综合上述两理论,专利等知识产权获得的正当性为:创造人因其智力创造而自然或应当获得对其智力产出的权利,该权利有利于激励和促进创造者之创造,从而促进社会智力成果之丰富和社会发展。虽然物权和知识产权之理论上的正当性相似,但就具体的有关权利之法律制度构成而言,物权和知识产权却有重大差异,原因何在?
物权之客体为“有形物”,其物理形态具自然之排他性,使得权利人无论是在自我的占有和使用,还是对外的交易和流转方面,均具有控制力量,即可利用物之物理上的排他性进行控制。(12)物,自产生时起,即在社会中独立存在,为社会存在物,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和可支配性;智力成果,依附于创造主体,不具有在社会中存在的独立性,虽可附诸物质载体,因其易复制性,创造人的支配力量和支配范围有限。参见王传辉:《知识产权的基本特点》,载《学海》1997年第4期,第35页。相应地,有关物权立法之重点非在创设新的权利,而是确认和保护权利;(13)法律上的确认是将自然法中私人对财产的占有、支配和实施及其正当性予以条文化,成文立法并非是权利及其正当性产生的基础。依洛克,设立政府及相关的法律制度,是保护而非创设自然法中已存在的财产权。并且,在保护权利方面,以权利人自助为主,公权力保护为辅。智力成果不具物理形态,因此不具自然之排他性,权利人控制力量受限。因此,权利的自我实现,仅限于自我保密下的占有和使用,而在交易和流转中,无法通过自我控制来保护权利,从而也阻遏了权利在自我控制基础上的完全实施。(14)经济学家阿罗以发明为例指出如下悖论情形:购买发明的人需要了解发明之信息方才决定其价值,但一旦购买者了解该信息,信息的价值就丧失了。因为不像有形物,信息一经了解,即在事实上完全转移且不可收回。See Kenneth 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in Universities-National Bureau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 & Committee on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609-626.相对应,有关知识产权立法之重点在于补足其产生时所欠缺之排他性或排他权;并且在保护权利方面,因权利人自助力量有限,以公权力保护为主。
以专利为例。在历史演进中,专利的排他权之形成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早期的君王之特权授予,主要赋予收费特权。该收费特权可以授予一人,也可授予多人,可限定时间,也可撤销或收回。排他权的来源为君权之滋生,并非独立主体之独立权利。第二个阶段是通过立法规定了专利的排他权,并逐步演进为现今的专利权获得制度:符合法定条件之发明创造人,经由申请获得有一定时效限制之专利权。
从君授到法定,虽然专利权成为法律上的独立权利,但与物权相比,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完全独立之物权具有永续性(perpetuality),但专利权有时效限定。一个不可回避的质疑是:如果知识产权是自然法性质而非功利主义性质,那它为什么会过期?(15)See J.Boyle, The Public Domain:Enclosing the Commons of the Mi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9.在理论上,如何解释该时限之正当性呢?
相比于物权之自然的排他性,专利等知识产权之法定弥补的排他性超越了自然排他性的正当边界。物权之排他基于物之物理形态,物权仅及于物理形态之物本身。即使他人占有的物与此物是相同或相似的,也不可排斥他人之物,即物权的排他只及于“同物”(本人之物)而不及于“物同”(他人与本人之物相同或相似之物),即“一物一权”,符合自然法上个人对各自付出劳动之物各有独立之物权。而专利之排他,无论他人之发明创造是否正当地产生或取得,只要与专利权人之智力成果相同或相似,均可及之并排斥,其排他性远远超出物权之排他性,即类似“多物一权”。(16)由于智力成果不具自然之物理形态,即使法律所规定的相应权利模仿“一物一权”,也只是法律上的虚拟或象征权利,权利人仍无法依赖该权利对其智力成果达到物权人对物那样的有效支配和控制。法律赋予知识产权的必须是也只能是排除所有“相同性”或“相似性”之智力成果的垄断性权利。此种过度的或超越正当边界的排他权,会被认为具有垄断性,因此专利权被认为是法定的垄断权或作为非法的垄断权之例外出现。(17)对现代专利法影响最大的英国于1623年颁布的有关专利之法规名为《垄断法规》(Statute of Monopolies)。这也是目前专利权被称为法定的垄断性权利的一个历史性依据。但是,这里“垄断”指对专利的独占的、排他的权利,并非现代反垄断法上限制或损害竞争之垄断,因为拥有专利未必就一定损害竞争。该排他权之不正当性被批评为过度控制或排斥他人思维之创造,阿塔斯(Attas)指出:一个人有权控制其思维的内容(contents of minds),不等于就可以进而控制源自其思维而外在表现出来的想法(ideas),凭借排他权控制或排除他人思维中相同或类似的想法,侵犯了他人控制其思维内容之权利。(18)See Daniel Attas, Lockean Justific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Gosseries Axel, Marciano A.& Strowel A.e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ories of Justice, Palgrave Mcmillan, 2008, p.40.
因此,由于专利权之客体不具物理形态,法定之补足的排他权只能是超越正当边界(或“自然法边界”)之过度的“垄断性”的排他权。为修复该过度性所致之不公平,唯有设定对专利权之限制性条件以达至衡平。以时限为例,如果物权控制之自然法性质的正当边界决定了权利之内容和收益的正当范围,其是永续的;假设专利权同样为永续,则权利人可借超越正当边界之排他权获取超越正当范围之收益,故应通过时间限制等来约束使其权利内容及可能实现的收益仍在正当范围之内。
功利主义导向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以“自利”为人性设定,认为个人财产权可激励生产从而促进经济乃至社会繁荣。同理,智力产品之生产亦需个人权利所致收益之激励。与“有形物”不同,智力产品因其无形性及复制的低成本而呈现公共产品之特征,即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19)See Paul A.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36(4)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87,387-389(1954).即前文所述之控制和支配力量的有限性,因此生产者如果只是依赖于自我保护,无法在竞争市场上回收投资,更遑论获得收益。波斯纳指出回报对促进发明之激励作用:“如果生产厂商预见到无法补偿其发明成本,他开始就不会去从事发明;如果他不能收获,他就不会播种。”并且,“在一个没有专利的世界里,发明活动也严重地偏向于可能被保密的发明”。(20)[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上)》,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由此,人类的发明和创造活动被大大抑制。
但是,专利法所规定的具有过度排他性的垄断权及其滥用又会损及社会效应,由此产生考特和尤伦所称的信息生产悖论问题:“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21)[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与经济学》,张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因此,通过法定的垄断性的排他权来纠正上述公共产品特征所导致的回报不足,从而产生对创造者的激励;又通过施以时限等限制,促进其应用。有期限的专利权要比永续性的专利权,更能促进社会福利,因为限定期限可促进创造者积极应用并且努力升级研发。
以现代专利法之立法蓝本——1623年英国之《垄断法规》为例。由于作为君授特权之专利导致了对某些产业或行业的垄断,影响自由贸易,因此国会通过该法规,规定:有一定期限限制之垄断权(专利)方为合法(或者“不是非法的垄断权”)。(22)See Tyler T.Ochoa and Mark Rose, The Anti-Monopoly Origins of the Patent and Copyright Clause, 84 Journal of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ociety 909, 912-913(2002),http://digitalcommons.law.scu.edu/facpubs/77.对此可作两方面理解:一是由于王室所授予的特权有的是无限制的王权滥用之后果,因此超越了该权利应有的正当边界,规定时限来使其回归正当边界;二是无限制的过度的垄断权会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依激励论,通过限制来使其促进科技进步和公共福利之效用回归最优。
自然法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之共同之处在于:都支持对有形之物和无形之智力成果,赋予个人权利。依自然法理论,个人对无论体力抑或脑力之劳动的产出具有独立支配的权利,为自然之正当性,并与个人自由紧密关联。物权和知识产权均为自然赋权,法律之规定并非创设,而是确认和保护。但是,由于智力成果自身不具排他性,因此只能通过“过度的排他权+限制性调整”来做制度安排,既弥补排他性不足,实现权利人之有效支配,又对过度的垄断性予以限制,回归自然法的正当边界。依功利主义理论,该垄断性的排他权虽可有效激励创造人,但也会被滥用影响效率或社会福利,因此应作限制以达至总效用最优。
两个理论的区别在于此种制度安排之价值。(23)近年来,有关自然法价值和功利主义价值之论战再度兴起,尤以墨杰斯(Merges)和莱姆利(Lemley)之争引学界关注。墨杰斯认为目前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分析永远不会确定出各种知识产权的“最优数”(optimal number),而应将知识产权理解为一种完全而真正的权利。See Robert P.Merges, 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4.莱姆利则坚守功利主义,批评墨杰斯不应因实证数据的不充分而放弃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基于实证的思考,转向毫不需要实证的犹如宗教信仰般的权利论。See Mark A.Lemley, Faith-bas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62 UCLA Law Review 1328, 1336-1337(2015).自然法理论是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其自身之价值,为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但功利主义则以社会效用为目标,知识产权之正当性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其所实现的目标,故为外在价值(extrinsic value)。换言之,自然法认为知识产权为个人之自然的正当权利和自由,个人权利和自由即为知识产权之正当性,知识产权所致发明创造成果及经济、科学和文化之繁荣是该权利实现过程中的副产品。但功利主义则认为社会效用是目的,个人权利及其限制的制度设计,只是达至此目的的方式或途径。
二、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社会契约抑或社会效用?
任何权利均有义务同行。自然法上的权利之产生与义务之产生同步。洛克认为作为自然法权利的财产权,有两大义务约束或例外:一是“足够的并且同样好”(enough and as good)的保留,即在公共资源中,要为他人留出足够的同样好的部分;二是不浪费原则(non-waste proviso)。(24)See Locke, supra note〔9〕, at section 27, 38.该类义务可被称为“内在义务”(intrinsic duties),即与财产权作为内生价值并存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该义务要求知识产权人要以负责的方式来实施其基于知识产权而拥有的力量。(25)See 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U eText, 2016, p.261.虽然权利人经由对有形物的控制可以自助,但不可完全避免被侵害,因此国家和政府的建立是强化对财产权的保护。(26)See Locke, supra note〔9〕, at section 124.政府对财产的保护是基于民众联合组建国家之契约,是该契约之根本价值。
上述从自然权利到政府保护之社会契约,也可解释知识产权之保护,但并未明晰的问题是:智力成果并不具有自然的排他性,排他性权利在立法的表面形式上是政府代表国家法定赋予的,对排他性权利的限制或共存的义务也是法定施加的,该权利和义务展现出并非“内在”而系“外在”的特征。那么,这种外在特征的权利和义务,是否也是社会契约?
洛克的社会契约观之论述有三步:一是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和平等的,财产权为自然权利;二是人形成国家之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三是政府是有限的,其功能仅为保护人民权利。虽然洛克之论是基于有形物,但是该理论的思想仍可突破表面用词的局限,扩展到对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的解释。
财产与生命和自由紧密联系,其为生存和自由之基础。同理,人对智力创造拥有个人权利亦具自然法之正当性,因智力成果来自人的创造性劳动,其财产收益形成生存基础,人的控制和支配为自由之体现。洛克所称之政府保护权利,其实质为政府不可不正当地限缩或侵害权利,而应保护权利。另外,知识产权之“过度排他性”权利,权利之正当性的获得源自自然法,其本质仍为先于政府之自然权利。表面上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了权利及其限制,实质上该立法之规定并非权利及其正当性之产生和获得的基础,只是政府充分地、正当地(即不过度逾越自然法之正当边界)保护智力成果之权利之必须方式或手段而已。
卢梭的“交换式”契约观,相较洛克的“演进式”契约观,会更容纳上述扩大式的理解。与洛克一样,卢梭认为国家和政府是民众自由协议的产物。卢梭认为:人基于社会契约,交出自己所拥有的自由(权利),但可从集体中获得与其丧失部分对等的等价物。(27)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在自然状态下占有财产的自由和权利,经由共同同意之社会契约,转换为国家确认的所有权,并因此获得国家对财产等权利的有效保护。无论是有形物还是智力成果,人的自我保护都是不足的,都有必要通过社会契约获得国家的有效保护。
基于社会契约,国家对智力成果的有效保护主要有二:一是通过规定“(过度)排他性”之权利(或“有效保护方式”)使权利人可有效控制、支配与实施智力成果;二是通过对权利的限制,使得该排他性权利之有效实施处于正当边界内。以专利为例,传统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契约的双方为发明人和社会(由政府代表),社会以(提供)有限的垄断权来换取(发明人同意的)技术公开。(28)参见李洁琼:《从专利社会契约论角度重新审视专利制度——评彼得·达沃豪斯〈知识的全球化管理〉》,载《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244页。依前文所述,该垄断性的排他权“自身”有超越正当边界的过度性,应予以限制,例如施以时限。另外,该权利之“实施”有超越正当边界的可能,例如其导致垄断的可能性会更大,由此应予以反垄断约束;以及,与物权之实施(使用与交易自由)一样,都受制于公共利益。以专利为例,对该权利之实施的限制,有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两类,前者有技术公开、及时地本地实施之义务等,后者主要包括不可损害他人权利、不可阻碍发明与创造、不可阻碍竞争或公共利益等。因此,包括了专利权及其自身和实施两方面的限制(义务)的专利法实质上是政府提供给发明创造人的一个“要约邀请”,申请人经由申请提出了“要约”,之后经由审批过程完成“承诺”,从而形成了有关专利权获得和实施的专利人和政府之间的契约。申请专利是专利法为发明创造人提供的“有效保护”之机会,而非强制要求,发明创造人仍可自由选择“不实施”或“自我保护”(例如保密),因此凸显了自由和平等之契约理念。
从社会契约视角,似乎可将利益平衡视为知识产权之社会契约安排的表现:政府代表社会公众,与发明创造人达成契约,从而实现了专利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但这并不妥当。首先,社会契约论强调的是“权利”而非“利益”,准确地说,重点在于权利人的权利之“保护”而非利益之“实现”。其次,来自社会一边的约束,例如卢梭所说的“公意”,(29)见前注〔27〕,卢梭书,第26页。是基于权利人之共同同意,并且该共同同意是因该约束,作为制度的一部分,可有效地保护权利。因此,社会契约论之基础是个人权利及其保护,而非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30)莱斯诺夫指出:社会契约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是理性个人基于自愿选择彼此之间所达成的一致同意。参见[英]迈克尔·莱斯诺夫等:《社会契约论》,刘训练、李丽红、张红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所谓的社会或公共利益,既来自个人之共同同意,也是为了个人,即保护和扩大所有人的所有可能的权利,并非是个人与社会之二分的对立。再次,即使将利益平衡作为现实中的社会契约之内容或知识产权制度安排,需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利益平衡只是社会契约安排的具体表现或结果,还是社会契约要达到的目的或彰显的价值?对此,社会契约论的回应是:社会契约是基于权利人之自然法权利,其形成是为了有效地保护权利人之权利,因此利益平衡或者知识产权及其限制作为权利保护之制度,仅仅为契约之安排本身,并非目的或价值,因此也不可作为相关法律之正当性。
相较之下,利益平衡说会更接近同样重结果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理论被认为是目前知识产权法之主要的和最流行的理论,概因其所保护的对象为具实用性之成果,而该成果以更为有效地满足人们之需要为目的,此为其社会价值。(31)See Robert P.Merges, Peter S.Menell, Mark A.Lemley & Thomas M.Jor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Publishers, 1997, p.135-136.功利主义的古典原则为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32)参见[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序言。它强调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之效用结果,如果某一行动或安排(例如知识产权法之制度安排),相较于其他可能的行动或安排,会更大地促进该共同体的幸福,则该行动或安排是正当的。经济学认为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安排会促进经济效用或社会福利的优化,因为:一是它既激励发明创造,又通过时效等限制来抑制成本之增加和无谓损失之产生;二是有助于生产者了解消费者之需求,从而更好地使其投资和生产与消费者偏好匹配;三是规定独占权利可有助于节省重复发明之浪费。(33)见前注〔8〕,费歇尔书,第14—22页。还有理论认为从更广泛和更长远的视角来审视知识产权制度,认为它“应有助于实现一种公正的和令人向往的文化”,以实现理想中的“社会规划”(social planning)。(34)同上注,第6—8页。无论是偏狭义的经济效用还是偏广义的社会规划,都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应为所要实现的社会之效用目标服务,本质上都为目的和结果导向的功利主义。与利益平衡说不同,功利主义并非将个人权利或利益与社会利益并列,个人权利或利益只是达至社会利益或社会效用之方式,而且社会效用的实现也只能指向“最大多数人”而非“每一个人”,所实现的效用也只能是“最大程度的”而非“完全的”。利益平衡说重结果,是与功利主义类似的现实主义,但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兼顾,在功利主义看来,则不具可完全实现之可行性。如果利益平衡最终的目标是社会利益或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而非前述的二元目标的完全实现,那么利益平衡只是对权利及其限制做结果导向的扩大化阐释,与“个人权利及其限制”一样,只是达至社会效用目标的方式或手段而已。
利益平衡说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进行二分,由二者之冲突引出平衡,旨在努力兼顾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用为基础的社会利益,是一种融合自然法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的努力。要平衡的两个方面各有其自然法和功利主义的正当性,此种兼顾或平衡并未产生新的法律之正当性或价值解释。并且,如果的确可以完全兼顾或平衡,长期发展并且影响巨大的自然法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是否有忽略或无视这种可以平衡两种利益的可能?
三、知识产权制度之难题:利益冲突抑或价值悖论?
专利强制许可,是用来阐述利益冲突及平衡的典型例子。作为对专利权之限制,专利强制许可之情形主要有:拒绝交易、公共健康等紧急状态或情形、反竞争行为、公共使用、依赖型专利情形下的交叉许可等。(35)例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31条第2项。其合理考量包括:促进专利之应用、促进创新、维护有效竞争、维护重大的公共利益等,从广义上讲,都可归为社会效用。其中,公共健康等为非经济性的社会效用,而应用、竞争和创新则为经济性的社会效用。
依利益平衡说,专利权指向专利权人之利益,而强制许可指向包括其他人在内的社会利益。依社会契约论,专利之强制许可为专利社会契约中的专利人之义务,其中,与促进专利应用相关的义务为积极义务,与不可损害创新、有效竞争和公共利益相关的为消极义务。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平衡或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契约,如深入剖析,其根本问题并非二分式的对立,而存在价值或目标上的悖论。依利益平衡说,如果专利人A有专利之利益(A之利益),他人和社会B有其他之利益(B之利益),则专利权及其限制分别指向保护A之利益和保护B之利益,因此达至兼顾而平衡。但是,如果旨在保护A或B的规则却伤害了A或B,或者,对A或B之限制,却有益于A或B的权利或利益,则更为复杂之悖论问题产生。
依自然法理论,创造人因其劳动或创造而获得权利,因此个人权利保护是专利制度之内在价值。对专利权之限制,本质上只是抵消被法律设定的排他权在内容和实施方面的“过度”部分。极端的个人权利导向观点,会认为专利之强制许可是对创造者个人权利的不正当损害。但是,即使在视财产权为自然法权利的洛克看来,一个人拥有的个人财产权虽至关重要甚至几近神圣,但仍受约束,即要为他人留出“足够的同样的好”的部分以及不可浪费。依利益平衡说,此所谓专利权人利益与他人及社会公众利益之平衡。其实不然。当法律要求任何权利人,无论是财产所有权人还是专利权人,都要为他人留出“足够的同样的好”的部分的时候,可能被限制的权利人,本身也享有未来获得更多的同样好的部分的机会或权利。而如果任何人的个人权利都不受任何限制,则某一时段拥有了过度的或垄断的权利的人,在另一时段,也可能成为被更为过度或垄断之权利的拥有者伤害的对象。从更长远的角度,即使他一生维持过度或垄断之权利,他的后代也有被伤害之可能。因此,限制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为了每一个人现在和将来拥有更多的权利,而不限制每一个人的权利最终会伤害每一个人的权利。当专利权人因促进应用、维护创新和有效竞争等而被强制许可,他也获得了将来有可能从经由他人专利权之强制许可而产生的应用、创新和竞争中受益的机会。当政府因公共健康、公共危机等公共利益之理由对专利权人之专利进行强制许可,该被限制之权利人,也获得了将来他或他的家人在身陷公共健康或危机之危境时获得救济之机会。然而,同样复杂的悖论状况是:如果强制许可等限制逾越了合理的边界,打着“公共利益”“多数人权益”等旗号而为的不适当的或过度的强制许可所致的对权利的伤害,不仅会伤及目前的专利人,也会伤及目前所保护的“他人”或“社会公众”中任何将来有可能进行发明创造的人的权利,并进而蔓延到伤及其他的重要个人权利。
依激励论等功利主义理论,国家立法设定和保护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之目的,是激励社会中智力成果之创造,主要有三个实现路径:第一个路径是,以专利权保护来解决专利人因智力成果易被复制而收益无法内部化的问题,以激励其发明和创造;第二个路径是,以排他性专利权来抑制发明人竞赛所致之资源浪费;第三个路径是,以排他性专利权来激励发明人进行创造之竞争,从而促进市场之竞争。
但是,专利权人却又有可能利用其垄断性的排他权利来做出与上述目标和路径背离的行为,相应有:1.专利人借其排他权来控制其智力成果之应用,甚至阻遏后续发明人的创造及其应用;2.专利人借其排他性权利在市场之外,通过法律诉讼来打击竞争者和压制潜在竞争者,造成新的资源浪费;3.专利人滥用专利权损害和抑制竞争。
由此可见,专利权激发生产又抑制生产,节约资源又催生新的资源浪费,促进竞争又抑制竞争,影响经济效率或社会利益的正面效用和负面效用兼具。
如果没有专利权保护下的收益回报,社会缺乏有效的智力成果之生产;但,如果不限制专利权,则智力成果得不到广泛的应用。由此,专利激励人积极创造并生产智力成果,而强制许可又可制约专利人滥用专利权所致对应用、创新和有效竞争的阻碍,从而达至智力成果生产和应用的总效用最大化。然而,更为复杂的悖论问题仍然存在:正如专利权有促进和损害社会效用的两面性,强制许可也是如此,本为抑制专利权之滥用从而促进社会效用,却有可能抑制了专利权本应发挥的促进作用从而也损害了社会效用。
至于公共健康,激励论认为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供给,由市场供给比政府提供更为有效。(36)激励论主要有两个分支理论:一为传统的奖励—激励论,即专利之直接回报的收益为激励源;二是前景—激励论,专利保护未来垄断利益实现的机会或可能性,该机会或可能性的实现需长期而持续的商业化过程,因此专利保护应标准提高、时间延长、范围拓宽。参见陈朝晖、谢薇:《专利商业化激励:理论、模式与政策分析》,载《科研管理》2012年第12期,第111—112页。政府为了公共健康对医药专利进行强制许可,但如果过度,又会影响专利人研发和生产药品的积极性,反而从更广泛和更长远之视角,社会公众无法获得充分的药品供给,会损害公共健康乃至引发危机。
另外,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社会效用之实现也存在冲突。例如以强制许可解决公共健康问题,但因为限制了专利权,可能会抑制专利人的发明和实施之积极性,会损及经济效用。同样,如果弱化或拒绝公共健康下的强制许可,虽可促进发明及其实施的经济效用,却会损及目前的非经济性效用,导致重大公共健康问题,甚至酿成人道主义灾难。
自然法权利悖论之产生,是因每个人的权利或利益,并非局限于目前所拥有的权利或利益,而且还包括任何在法律上拥有“合法资格”的具有获得与实施之可能性的权利或利益。因此专利权人A和其他人B在法律上可能获得或拥有的权利或利益的范围和机会是一样的,而非只局限于目前的A之专利与B之其他利益的二分。
功利主义悖论之产生,是因为无论专利权还是专利权之限制,均有促进和抑制相关社会效用的可能性。另外,该社会效用也有局部和整体以及近期和长期之分,对局部或近期社会效用的实现,可能会损及整体或长期的社会效用。最后,社会效用本身之构成部分也会导致冲突,其原因在于有限的资源无法实现各个效用的最大化而只能促进最大限度地最大化。
无论依自然法之社会契约还是功利主义之社会效用,知识产权人之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并非是二分式的利益冲突,而是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的悖论状态。保护知识产权人之权利既有促进也有损害他人之权利或社会公众利益之可能,同样,限制知识产权人之权利也有此两面性。由此悖论状态,很难达至利益平衡所需的二元目标。
四、知识产权制度之终极价值选择
法律体现社会之价值。如个人之道德价值选择一般,法律制度之价值依其等级,有终极价值(terminal value)和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之分。
自然法理论以个人权利为终极价值,知识产权以个人权利为内在之正当性,发展出个人权利及其限制之社会契约,是为在最大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保障和实现个人权利。由此,个人权利为社会契约之内在的和终极的价值。功利主义理论则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之外在价值为终极价值,设定知识产权等个人权利是为促进社会效用,因此知识产权之制度安排为工具价值。
以美国《宪法》的知识产权条款(第1条第8款)为例,对其价值之解读存在功利主义和自然法权利视角之争。该条款规定:“国会有权……为促进科学和有用技艺的进步,保障作者对作品、发明者对发明在有限时间内的排他权利。”(37)条款译文引自[美]卡尔·卢茨:《专利与科学——对〈美国宪法〉专利条款的澄清》,敖海静译,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9年第11期,第10页。该条款被解读为是为了解决利益平衡问题的利益平衡机制,体现了在知识产权人之利益(排他权利)与社会公众利益(促进科学和有用技艺之进步)之间进行平衡的理念。(38)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目的与利益平衡关系的实证分析——以美国〈宪法〉知识产权条款为例》,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66—67页。并且,个人的排他权利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的目标,因此是功利主义导向。美国国会报告指出制定版权法之目的并非基于作者对其作品拥有自然之权利,而是通过保障作者一定期限内的排他性权利来促进公共福利和科学进步。(39)See H.R.REP.No.2222, 60th Cong., 2d Sess.7(1909).美国最高法院在“Mazerv.Stein”一案中指出:依该宪法条款,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一样,激励所有人是第二位的考虑,是为了激励所有人创造出让世界持续受益的智力成果。(40)See Mazer v. Stein, 347 U.S.201, 219(1954).其还在“Sony Corp.of Americav.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案中指出,版权等知识产权法律之挑战在于如何解决作者和发明人之利益与相冲突的社会在思想、信息和商业之自由流动方面之利益之间的艰难的平衡。(41)See Sony Corp.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417, 429(1984).之所以“艰难”,是因上文所述的悖论状态:保障该排他权利既有促进也有损及公众利益之可能。
对“促进科学和有用技艺之进步”的解读,未必只拘泥于功利主义。首先,宪法条文规定的国会的权力是“保障”而非“授予或创设”。因此可解读为:该排他权是权利人应该或自然而然具有的,国会不过是进一步来保障其有效实现。即使该排他权是国会立法授予的,依自然法理论,该权利授予的正当性仍然基于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创作人或创造者因其创作/创造之劳动而享有保护,该享有保护的权利仍为自然法性质。其次,“促进科学和有用技艺之进步”并非是排斥个人权利作为终极价值,因为可以理解为在促进科技进步中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一个人可能的创作和创造自由以及相关的收益权和其他权利。此种个人权利导向的社会契约式的理解,可由知识产权之人权化获得支持。《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1)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2)人人对由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42)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有相似规定。
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7条的规定也常被用来作为利益平衡和公共利益导向的佐证。该条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利于促进技术革新、技术转让和技术传播,有利于生产者和技术知识使用者的相互利益,保护和实施的方式应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并有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该条文仅规定知识产权之保护和实施,但并未说明知识产权产生或获得的正当性之所在。技术之革新、转让、传播以及社会和经济福利等,既可理解为社会效用目标,也可理解为是一种要达至的、在其中个人权利和自由得以最大程度得到保护和实现的状态。最接近于利益平衡的文字描述是“生产者和技术知识使用者的相互利益”,鉴于二者之利益存在悖论,“相互利益”(mutual advantage)应理解为促进所有人在创造和应用方面的权利,包括可能获得权利的机会。
由此重新理解专利之强制许可,其本质并非是专利人之权益与强制许可所指向的社会公众利益之平衡,更深层的思考是:该规定是以个人权利还是社会效用为终极价值?如果是个人权利导向,是经由专利权保护和限制来保护更广泛范围的所有人的个人权利;如果是社会效用导向,则是达至社会效用最大化。
反垄断情形下的专利强制许可指向经济效用。传统观点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的价值冲突,知识产权法规定的保护垄断之权利是为了激励创新,而反垄断法则抑制垄断,因此二者是冲突的。(43)See Michael A.Carrier, Unraveling the Patent-Antitrust Paradox, 15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761, 762-763(2002).依利益平衡说,要平衡互相冲突的知识产权所保护的个人利益和反垄断法要促进的竞争(社会公共利益)。但是,更为复杂的是它们存在既冲突又一致的悖论关系。一方面,专利权人有滥用其垄断性排他权达至垄断从而抑制创新、伤害竞争的可能;另一方面,专利权可激励发明创造人促进创新,而创新是促进竞争的。因此,依反垄断法对专利权人之规制既有修复有效竞争的可能,也有因抑制创新动力而损及竞争的可能。更为准确的认知应该是:对于有效竞争之目标的达到,是专利法和反垄断法共同的任务。因此,专利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的冲突并非是两个分支法律之价值或目标上的冲突。莱姆利指出,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根本上不冲突,它们“共同致力于经由激励创新来促进有效市场和长期的、动态的竞争”。(44)See Mark A.Lemley, A New Balance between IP and Antitrust, 13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Law and Trade in the Americas 237, 248(2007).两个法律作为实现共同目标之方式或路径是有冲突的,因此要考虑的是如何搭配或组合各个法律工具以达至共同的目标。(45)Ibid., at 249-250.但这也只是硬币的一面,因为专利权的垄断性与反垄断都有激励和抑制竞争的可能,既有反向也有同向,因此不是单向的(促进竞争的)反垄断法制约(损害竞争的)专利权,也有(促进竞争的)专利权的个人权利及其保护来制约(损害竞争的)反垄断之滥用。
更进一步的思考是:该经济效用是法律的终极价值吗?以《谢尔曼法》为代表的美国反托拉斯法,在早期为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之民粹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因受芝加哥学派影响,以经济效率为目标。(46)波斯纳指出:反垄断法唯一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即经济性的社会效用。由此反垄断法重整体而不重个体或部分的中小企业,也不考虑其他的社会性目标。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第2版),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经济效率是经济方面的社会效用,它不保护单独的竞争者,而是保护以消费者福利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效率。但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不可由此认为目前美国的反垄断法的目标由个人权利保护目标转向社会效用目标。更深入的理解是:以宪法为代表的美国法律制度的终极目标仍然为个人权利导向,作为分支法律的反垄断法的目标或价值仅为实现法律终极目标的工具目标或价值之一。因此无论早期的民粹主义还是目前的经济效率,都仅为不同时期所发展出来的工具价值。民粹主义强调对消费者及中小企业的保护,并非等同于个人权利导向的终极目标,因为被反垄断法制约的大企业仍然享有私人财产权与交易自由权。准确地说,民粹主义目标不是个人权利之终极目标,只是对大企业权利进行适度限制的社会契约安排。同样,目前的经济效率只是工具价值,它要达至一种竞争状态的社会契约安排。无论是何种契约安排,终极价值是要保障和实现所有市场主体(包括被反垄断的市场主体)最大程度的公平的权利和自由。(47)以在先和在后专利之交叉许可为例,从社会契约视角,通过双向强制许可,权利人都获得了更多的可能的技术应用之机会和权利。
同样,公共健康或公共危机作为公共利益对专利权的限制,依功利主义,该公共利益代表的社会效用为专利权及其限制应实现的目标。但是,公共健康只是社会效用的一部分。如过度以公共健康等侵蚀专利权,则因导致个人权利不稳定和不安全从而伤及基于权利激励而生之发明创造及其关联效用,并且也会导致公共健康产品之供给不足。从社会契约的视角,以公共健康等限制专利权等,并不是以专利权的个人权利来服从更高的公共利益,也不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只是通过特殊情形下对专利权的限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保障和促进个人权利。因此,个人权利仍为终极目标,公共利益之限制为有限的例外。当然,这里的个人权利不是具体的个案中的个人权利,也不是某一个法律分支的个人权利,而是作为终极价值的更广泛范围和更长远视角的作为法律正当性的个人权利。(48)对药品专利以公共健康为由进行强制许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国实施最为积极,但这引发了美国等药品专利大国的强烈反对,对其进行贸易制裁,而投资者也忧虑其投资之安全环境,此为经济效用之损失。美国政府有以公共健康为由进行强制许可或政府使用的权力,因侧重个人权利保护,甚少行使此权力。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出现炭疽病毒传播事件,引发民众恐慌。政府最后只是以强制许可为谈判筹码与当时国内唯一拥有治疗该病毒之专利药品的德国拜耳公司谈判,使其降低药品价格。See Lauren Keller, Ciprofloxacin and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s, p.2, http://nrs.harvard.edu/urn-3:HUL.InstRepos:8852122.
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认为专利权及其限制为内生的权利和义务,一起达至个人权利之保护。这并非法律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平衡,因权利而保护权利是长远的广泛范围内的对所有人权利之保护的社会契约,无论保护还是限制知识产权均可归结为对知识产权和其他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社会效用论则以知识产权及其限制为达至社会效用目标之工具,无论是知识产权,还是他人之应用权,还是基于反垄断和公共健康等的限制,都会发生对社会效用之达至的正向和反向作用,因此表面上的利益冲突之本质为各种工具效用发挥之冲突,存在悖论的复杂性。
另外,悖论中的一致性之可能导致了在以下假设中,二者实质上的差异远小于表面的差异:虽然社会契约是源自个人的自然法权利并以个人权利保护为目标,但唯有其产生良好社会效用方可维系该契约,故理性个体所发展出来的社会契约自身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社会效用;(49)洛克指出:一个人通过劳动将土地归为私有,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人类的共同财富(common stock),私有状态下产生的人类生活所需之供给数量,要远远超过公地状态下的产出数量。See Locke, supra note〔9〕, at section 37.如果个人权利之激励是促进社会效用之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具路径,(50)边沁认为维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是国家达至富裕的唯一途径,因其可激发人的创造和进取心。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111页。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在“Mazer v. Stein”一案中指出美国宪法之知识产权条款的目的是促进智力成果之创造,是立法的经济理念,但又强调:国会立法之经济理念是认为“作者和发明者的才能”是促进公共福祉之最佳途径,因此创作/创造者们应被给予有价值的、有保障的、没有过重负担和要求之权利。See Mazer v. Stein, supra note〔40〕.则无论以个人权利还是以社会效用为法律之终极价值,社会效用趋向最大化和个人权利保障趋向最广泛化是同向和统一的。换言之,若假设之前提成立,则以个人权利导向的社会契约,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社会效用结果,而在以社会效用为目标的发展中,个人权利也可以最大可能地实现。
尽管如此,现实中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是以个人权利抑或社会效用为终极价值,仍有选择和明确的必要。效用是有条件的正当性标准,即个人权利是否保护以及如何保护以社会效用实现效果为条件,从而导致个人权利设定与保护的相对性和变动性;权利则为无条件的标准,其存在和保护决定于自身内在价值的正当性,因此具绝对性和稳定性。前者指向“我们想要什么”的现实主义理性,追求结果在现实中的更好;后者则为“我们应当做什么”的理想主义思辨,回归人之尊严与价值的道义基础。(51)仍以墨杰斯与莱姆利之间的论争为例,可以看出二人之深层价值基础的差异。莱姆利声称以实证为基础是基于科学的理性思维,而对方则是将权利视为信仰,甚至是不允许被证伪的宗教信仰。See Lemley, supra note〔23〕, at 1346.其实,即使莱姆利支持的法律经济学之分析竭力去量化现实中的效用,并以此支持或反对目前知识产权之有效性,其本质仍然是结果导向的有条件之价值。墨杰斯则反击道:将“faith”理解为宗教信仰,是莱姆利自己夸张的修辞,而本意应为对知识产权必要性和重要性之“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基于道义法则的权利观,而法则是“指引我们向着更好的目标前进”,即康德的“目的王国”。实证或功利主义并非通往真理的唯一之路,道义论亦是基于详尽的理性思辨。[美]罗伯特·P.莫杰斯:《驳功利论原教旨主义》,郝元译,载《清华知识产权评论》总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10、26—27页。如果以个人权利为终极价值,相应的制度,无论是权利之保护还是限制,均以更好地保障个人权利为目标,因此对知识产权的限制,相比于社会效用导向之制度,会有严格的条件和程序限定。例如以公共健康为理由进行专利强制许可,类似于公共利益情形下财产之征收,是极其有限和重大必要之情形方可为之,并且要经由司法的正当程序和给予专利人合理而正当的补偿。相应,该制度会限缩政府介入和干预之权力。
理论上,个人权利的保护及其稳定性有助于个人之自由和安全以及在此基础上之制度的长期稳定与可预见性,对政府权力的抑制可减少权力滥用之风险,可促进社会契约的偏市民自治或自发秩序的理想化状态。但回到现实,可能的忧虑是由于政府权力之限缩,导致现实中发生的垄断、公共危机等问题无法及时有效解决,因现实的效用不理想而引发部分的或局部的个人权利无法得以实现或满足,从而导致或加剧社会中之利益矛盾与冲突。社会效用论注重效用之结果,理论上可强化最大范围内的最多数人的权利之实现和满足。但回到现实,基于社会效用论的政府介入相较于社会契约会更加积极,由此影响个人权利之稳定与可预见,有导致激励被抑制而损及社会效用之可能;并且,政府相较于社会契约中的政府有更多的权力,值得商榷的是:政府是否具有准确判断什么效用才是社会所实现之目标的能力?政府是否具备充分的把控和实现社会效用之能力?
由此,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首要问题并非是知识产权权利人个人利益(权利)和社会公众利益之表面上的冲突及其解决,而是更为深层的思考:知识产权制度安排是以个人权利导向之社会契约还是以功利主义导向之社会效用为终极价值?或者,仍然是有关权利之任何制度都要面对的根本问题:是更多地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发展社会契约,还是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以扩展社会效用?德拉霍斯(Drahos)反对知识产权之个人财产权性质,他认为知识产权作为主体之权利(subjective right),是一种抑制自由的特权,而特权的拥有者总是倾向于扩张其特权,从而威胁和损及他人之自由。因此,他认为任何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应服务于一定的目的。(52)See Drahos, supra note〔25〕.可是,当知识产权只是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工具时,掌控和运作此工具的政府由此所获得的特权,不也同样具有自我扩张的倾向和抑制个人权利和自由之危险吗?
——兼评专利法第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