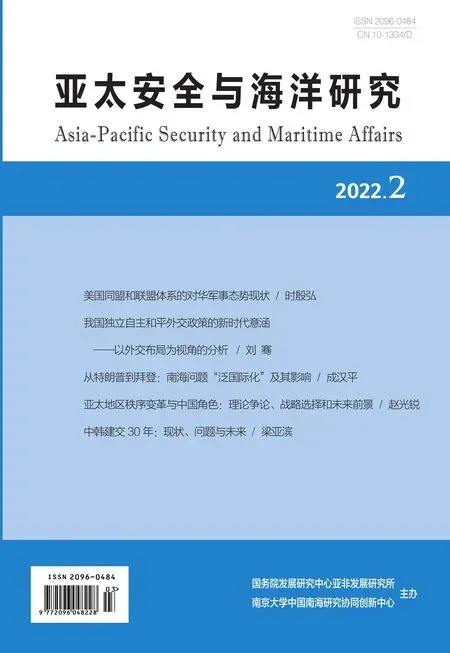亚太地区秩序变革与中国角色:理论争论、战略选择和未来前景
赵光锐
内容提要: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最终形态取决于大国的竞争,也取决于中国发展最终能达到的程度以及中国希望扮演的角色。中国要在地区秩序各方面扮演更加积极有为的建设性角色,还应恪守一些基本的战略底线。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谋求亚太地区霸权,不在周边经营势力范围,是中国亚太角色的战略基石。不谋求地区霸权的角色定位,主要由中国各种“内生性”因素所决定。新时代中国需要在亚太秩序的稳定和变革方面与美国达成基本共识,增强亚太区域合作方面的战略互信。中国要明确界定不称霸、领导权、主导权等概念,处理好增强“地区能力”与不谋求地区霸权之间的关系,关注和引导国内有关中国角色的舆论,树立“亚太的中国”而不是“中国的亚太”的观念。
亚太地区秩序正在经历变革,崛起的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对变革的方向和最终形态起到关键性作用。中国的角色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涉及中国在亚太地区如何更加积极有为、主动作为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中国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1)关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积极角色”的研究和思考,参见刘宏松:《中国参与APEC机制30年:角色与机遇》,《人民论坛》2021年第36期;沈明辉、李天国:《百年变局下的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李开盛:《特朗普时代的中国新角色》,《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1期;吴心伯:《论亚太大变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59页;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18—24页。中国要扮演更为积极的区域建设性角色,做地区和平的维护者、发展繁荣的贡献者、区域合作的推动者。同时,中国的贡献还应包括不做什么,坚持战略克制和审慎,为对外行为设置基本底线,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尤其重要。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并坚持至今的不谋求霸权的外交战略,是中国的长久国策。不称霸的首要体现是不谋求亚太地区霸权或领导权,不在周边经营势力范围,这构成中国在亚太地区角色的战略基石。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复兴为国际关系的“进化”带来的历史性贡献和积极的“文化信息”。(2)杜维明很早就提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古老文化的民族,经过百年屈辱后现在重新再生所带来的文化信息是什么(What is the culture message)?”的问题,并且指出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能够再生,中国的知识精英绝不像有些西方人认为的“只有报复、夺权这两种情绪”。参见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以“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等为代表,近年来中国的亚太战略展现出积极主动、有所作为的特点。这引发了一些国家的疑虑,认为中国正试图谋求亚洲霸权或亚太主导权,“一带一路”倡议则被看作是中国试图打造势力范围的例证。亚太大国之间的“不良战略互动”以及中国国内舆论的变化,对新时代中国不谋求霸权的角色定位带来一定的挑战。面对疑虑和挑战,中国可以进一步阐释不谋求亚太地区霸权的意图,更为清晰地界定中国人对霸权、领导权、主导权等概念的认知,通过新的外交行动和策略更好坚持不谋求霸权的角色定位。
一、亚太秩序变革背景下关于中国角色的理论争论
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和大国战略博弈的舞台,地区力量格局、经济和安全秩序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在经济领域,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总额的近六成,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世界经济重心在转向亚太,而亚太经济重心在转向太平洋西部。原来在经济总量、技术创新、发展水平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加拿大以及太平洋西部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进入21世纪以后,亚太经济增长、科技创新的动力日益转向亚洲大陆东部和南部边缘,中国、东盟、印度开始崛起。亚太地区传统的产业分工、贸易关系、技术扩散、金融投资关系和相关规则也正在经历调整和变革。
在安全领域,美国“有限霸权”式的亚太安全秩序正向“多元复合”结构转变。(3)参见吴心伯:《论亚太大变局》,第34页。中国、东盟、印度等新兴力量与美、日等传统强国,都在力图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新地区秩序。美国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将其发展为“印太战略”。拜登政府继续强化和充实这一战略,组建新的亚太安全同盟机制,诱导欧洲和北约向亚太转移资源的意图增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加剧。日本虽然在大战略上紧跟美国,但也有自己的设想,对于自身单独能做什么的可选择范围和意愿大大增加,中日关系正在经历结构性变迁。中美之间在安全问题上互相戒备,但也发展出各种层次的安全合作和危机管控机制。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是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最大变量,中国将“走向何方”、扮演什么样的地区角色,以及其他大国对此的判断和反应,决定着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方向。这些都将带来亚太秩序的巨大变动。(4)参见张蕴岭:《转变中的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外交评论》2018年第3期;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都在关注亚太地区,并对亚太发展前景做出各种预测,争论也日益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中国将扮演何种地区角色尤其是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是否会谋求地区霸权。实际上,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对此进行诸多探讨。(5)Aaron L.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1993;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1994; Karl W. Ikenberry, “Does China Threaten Asia-Pacific Regional Stability?”Parameters, Vol. 25, No. 1, 1995;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进入21世纪后,学界的争论在总体上演变为泾渭分明的两派,即审慎乐观派和悲观派,他们彼此不认同对方的论证逻辑和对中国角色的预测,所提的政策建议也大相径庭。
悲观派的论证逻辑和预测方式与各种“中国威胁论”大致相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有西方学者明确提出,随着经济和实力的增强,中国将成为东亚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的潜力和发展趋势使它比日本更有可能在东亚建立霸权。经济上中国会取代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在军事上发展为超级大国。中国会更自信地使用实力,采取更多单边和不合作行动。(6)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pp.156-167.近十几年来,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关于中国强大后一定会追求亚洲霸主角色的观点广受关注。他的理论逻辑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只有变得最强大才能生存,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国。但是成为全球性霸主几乎是不可能的,理想情况是成为所在区域的唯一霸主,努力防止其他地理区域出现霸主。因此,中国一定不会和平崛起。中国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亚洲建立地区霸权,第二件事就是把美国挤出亚洲。(7)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晓松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0—425页;《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载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35—447页;《米尔斯海默:我一直认为中国不能和平崛起》,《环球时报》2012年5月26日;John J.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No. 4, 2006, pp.160-162。照此逻辑,有西方人将中国近几年在亚太地区更为积极的外交和行动看成是搞中国版的“亚洲门罗主义”。(8)参见罗杰·科恩:《中国把“门罗主义”用到亚洲》,《纽约时报》2014年5月10日。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当前中美的竞争首先集中于辽阔的印太地区,尤其是双方正陷入争夺东南亚霸权与影响力的漫长而全面的竞争。(9)David Shambaugh,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4, 2018. 与沈大伟观点相似的还有佛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参见阿伦·佛里德伯格:《中美亚洲大博弈》,洪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大国”,并声称“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扩展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并重塑有利自身的地区秩序”,把中国描绘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10)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25,45-4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2021-11-02].谢淑丽(Susan Shirk)则从“领导者的不安全感”角度预测中国无法和平崛起。(11)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近来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似乎正在印证悲观派的观点。国内一些学者对于中国不谋求地区霸权的战略选择也持审慎态度,认为虽然中国官方否认有谋求亚太主导权的意图,但实际上中国对于未来获得一定的地区主导权有所期待,中美现在进行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已是客观现实。有学者提出,中美可以通过建立某种亚太的“两极体系”“两国共治”“共享领导权”等模式来避免因亚太主导权之争而引发的剧烈冲突。(12)参见凌胜利:《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当代亚太》2017年第1期;凌胜利:《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认知差异及化解之道》,《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贺凯、冯惠云:《中美国际领导权的竞争与共享》,《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孙西耀、吕红:《亚太“双领导”与中美自贸区战略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
审慎乐观派认为,悲观主义的论证逻辑过于简单,既没有认真研究中国的真实意图,也没有考虑中国自身面临的困难,更忽视了现有霸权国的优势和国际体系的弹性。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在内部和外部一系列条件限制下,中国的崛起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避免与亚太地区强国尤其是美国的正面冲突和战争。他们质疑“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认为必须考虑中国崛起面临的诸多困难及其被意外事件冲击和阻断的可能性,他们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霸权的强大和适应性抱有信心,对于中国能否最终实现持续的和平发展并不完全乐观。(13)Mark Beeson, “Hegemonic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ow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1, 2009, pp.108-112.
约瑟夫·奈(Josef Nye)和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是代表性学者。奈认为,从中国现有实力和面临的困难来看,未来几十年中国都不可能挑战美国。美国对中国应该采取“接纳与保险”的双重政策。美国要接纳中国,使中国融入国际秩序并欢迎中国崛起。同时,美国要有风险意识,巩固美日同盟,防止中国成为地区霸权。他提出:“如果一个崛起的中国向四周展示力量,那就会驱使邻国寻求平衡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如果美国继续避免以遏制作为其战略,而中国接受美国在西太平洋存在的合法性,这将为两国创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机会。”(14)参见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邵杜罔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XI—XIV页,第59—105页。柯庆生则强调,中国体量大是一个优势,但是“大也有大的难处”,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自身合法性、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国内问题上,没有精力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全球化的发展使当代东亚和大国政治完全不同于19世纪和20世纪,大大降低了中国将美国排挤出亚洲的意愿和可能性。发展和崛起的中国比一个停顿和混乱的中国更有利于美国和世界,美国及其盟友不应遏制中国而应“塑造中国”,引导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积极力量。(15)Thomas J. 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16;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 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也对中国的地区角色持较为正面积极的态度。江忆恩通过对近几十年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对外政策选择、军事力量建设等情况的研究,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国际或地区秩序的“修正主义者”。中国人现在关注的是如何变得更富有和更强大,这种愿望还没有转变为另一种愿望——采取实际军事方面的努力取代美国在地区或全球层面的主导地位。(16)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56.江忆恩与奈、柯庆生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认为,美国的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等综合性国家权力是中国在短期内无法超越的,中国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不会主动冒险挑战美国在全球和亚洲的优势地位。伊肯伯里则相信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西方国际秩序的生命力和容纳力,认为如果美国从现在开始强化和巩固这一秩序,中国可以被和平地纳入其中,避免中美间的大国战争,虽然美国单极世界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结束,但是在中国与西方国际秩序的对决中,胜利的将是后者。(17)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2008.巴里·布赞从国际社会角度所作的研究也认为:“和平崛起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容易,它需要中国找到新的思路。”(18)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2010, pp.35-36.
美国政府和部分美国学者提出的中美已经在亚太展开了所谓的“地区霸权之争”,并没有切实可靠的证据,尤其是他们对于中国到底有没有与美国争霸的意图的研究非常薄弱。即使从基欧汉对霸权的界定来看,他们也只着重分析一国追求“霸权的能力”,却忽视了一国追求“霸权的意愿”。(19)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35页。中国不谋求区域霸权的战略选择,主要是一种“内生性”的行为,需要更多地从中国自身寻找解释路径。正如美国学者熊玠所言:“许多分析家们推测快速发展的中国必定会对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产生威胁,却没有人了解中国本身对于这一形象的看法。……另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是,中国人是否如外界评论的那样渴望领导他人。”(20)参见熊玠:《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李芳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26—227页。持悲观态度的学者,仅从国际体系和大国竞争的角度解释、预测中国的地区角色,忽视国内政治和人在历史结构中的能动性、选择性,落入了“历史宿命论”的窠臼。
但是,很少有人重视并较好地分析各种“内生性”因素,对中国所希望扮演的国际角色的决定性意义。这些“内生性”因素,包括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基本国策、决策者的价值观念和历史认知,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外交所确立的一系列崭新的精神品格等。西方学者一般不认同中国的领导体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而潜意识中也不看好由此产生的中国外交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性诉求。他们也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代在国际政治中的曲折遭遇,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世界观的深刻理解,无法认真看待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不称霸、不谋求地区霸权等外交理念。而一些国内学者对中国亚太角色的探讨,过多使用西方概念和理论逻辑来框定中国的国际行为。一些研究在解释中国为何能和平崛起时,未能清楚梳理中国和平发展思想的历史脉络和实践,没有足够重视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坚持和平发展思想的连贯性、继承性,对中国不称霸的战略选择缺少“自信”。
二、中国的战略选择:和平发展、不谋求地区霸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不称霸、和平发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外交思想,尽管历史背景、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是都在回应“中国威胁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将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的重大问题。米尔斯海默认为,关于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还只限于学术界,是一个学术问题,而现在已经成为政界和学界都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一判断表面上符合事实,但是如果对新中国外交史有所了解,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实际上,中国周边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不断提出中国强大以后是否会侵略扩张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和平发展”问题的思考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而且一直将其作为重大的国家方略问题加以探索。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近平等不同时期的中国领导人都不是在一般的理论、策略意义上,而是站在国家性质和国家战略、决定中国兴衰成败的长远立场来对待这一问题。毛泽东很早就预见到中国强大后可能会重蹈历史上的“大国覆辙”,也认识到决定能否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人自身。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制度、外交战略以及引导人民观念变革上作出了种种努力以避免可能的危险。在外交战略领域,对于不争霸、不称霸包括不追求地区霸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中国始终有很强的战略自信和政策连贯性。地区或全球霸主都不是中国强大以后追求的角色,这是由中国的社会制度、精神品格、基本国策、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世界秩序发展趋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一)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国际角色
国家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国际角色。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内坚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对外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决定了中国不能搞侵略扩张、霸权主义。毛泽东在1964年会见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亚洲、非洲、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说:“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21)《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37页。1975年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阐释了不称霸思想,提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侮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22)《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1975年6月30日,病中的周恩来在同泰国总理谈话时,对这个发言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国家越大,麻烦越多。但是,我们决定了一条原则,不称霸,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达、强大。”(23)《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03页。中国将不称霸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标准,如果在对外政策中不坚持和平主义,搞霸权主义、压迫、剥削,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改变。在新时代,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从国家的精神品格来看,坚持和平发展、不搞霸权主义是中国的一种国家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被看作是中国要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必要条件。周恩来在1971年会见美国友人谢伟思时说,对世界人民,首先对中国人民,我们要讲清楚在中国的地位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明确说明我们到底在国际上能够做点什么贡献,要把中国搞成这样一个新中国,将来强大起来以后,也不是去主宰世界和干涉人家的内政。要对世界有所贡献,而不是去统治世界,强加于人。(24)参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92页。邓小平后来也指出:“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因此,中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世界贡献的界定有两个维度:一是中国要秉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中国还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必须恪守一些基本准则和行为底线。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除了要通过做什么来体现,不做什么同样重要,不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也应该被理解为强大后的中国对世界的建设性贡献。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总结的“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不仅指出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而且提出了“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等原则,两方面一起构成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的智慧和力量。(26)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8—99页。
和平发展、不谋求霸权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是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基本定位。1973年,周恩来明确指出,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是世界大动乱的根源。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是我们的国策。(27)参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654页。1975年1月,邓小平在向日本朋友解释不称霸时,关于其长远战略意义讲得更明白: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叫永远不称霸,不是讲现在,是讲将来永远不称霸。(28)参见《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页。习近平一再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67页。。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已经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从国家制度层面进一步确定了不称霸的战略意义,意味着“从我们的根本政策看,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30)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3日。。长远看,和平发展道路、不谋求地区霸权、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道路、和平解决争端等,都是中国从国家层面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这些是以往任何崛起大国都没有承诺过的,中国既然敢于承诺,也就有信心和意志做到。”(31)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25页。这些“国家承诺”从根本上限定了中国应该做什么和应该走什么道路、不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走什么道路,限定了中国不应该扮演的地区角色,构成中国亚太政策的底线和基石。
(二)亚太国家具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区域安全的历史共识
不谋求地区霸权也是亚太主要大国的历史共识和互信基础。中国在与美、日关系正常化之初,就特别强调各方不谋求亚太霸权和势力范围的问题,并作为正式条款写入有约束力的声明和条约。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有一条专门针对亚太地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32)参见中美《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又将这一原则扩展运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3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原封不动地采用了中美《联合公报》的反霸条款,后来主要因为日方对如何将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有异议,双方经历了长期缔约谈判。(34)参见王泰平:《中日关系的光和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7—204页;Yung H. Park,“The ‘Anti-Hegemony’ Controversy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49, No. 3,1976。最终双方都做了让步,将反霸条款的表述方式略做修改后作为条约的第二条,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3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人民日报》1978年8月13日。。
虽然中美、中日都没有在任何场合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具体范围与含义做明确界定,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主要指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反霸条款”是此后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得以延续、这一地区的和平基本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一个核心理念和一条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打破,一定会出现大的混乱甚至战争”(36)牛军:《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秩序的演变》,《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第8页。。
毫无疑问,20世纪70年代中美日的反霸共识主要建立在反对苏联的基础上,但是三国领导人也都意识到,任何一个大国或势力集团试图谋求地区霸权,必然会导致其他一方安全环境的绝对恶化。因此,中美日三方所规定的反霸条款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自我约束和克制,中美日各自都不进行谋求亚太地区霸权的行动和计划;二是反对和抵抗,对于任何国家谋求亚太地区霸权的企图进行共同反对和抵抗。邓小平曾经非常清楚地阐释过反霸条款两层含义对于三个大国以及亚太地区的长远战略意义。1975年1月,他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时说,中日联合声明之所以确立了我们两国间长期友好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在亚洲也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也好,都不谋求霸权。我们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了这一条,我们友好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关系。(37)《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第9—10页。
中国身体力行,后来将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反霸和不称霸主张,转变为一项约束自身行为的长久国策和战略选择。不谋求亚太地区霸权是中美日三方在亚太地区各自行为的底线,是三方实现长久合作的基本条件,也是对其他亚太国家基本安全的共同保证。三国坚持不谋求亚太霸权的共识对于亚太地缘政治的稳定具有关键性意义,维持该共识就能从根本上避免亚太主要大国发生战略性冲突。
从世界秩序的发展趋势看,霸权的时代已经结束。就中国而言,“中美新两极、新冷战都违背不称霸的战略宣示,也不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信念。中国的基本目标和最高利益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霸权地位不是民族复兴的标识,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38)参见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发掘自身潜力,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在于通过内部调整,解决内部矛盾,实现财富公平分配,不将社会矛盾转嫁给外部世界。中国超大规模的内部市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一些国家不具备的先天条件,中国可以不通过对外掠夺和扩张的方式实现发展。跨国生产带来中国与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在经济、贸易和技术上的高度融合。(39)参见李滨:《东亚悖论:经济依存与安全戒备》,《国际观察》2016年第4期。除了与美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达到了极为紧密的程度。跨国生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虽然并未消除亚太地缘政治上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但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安全合作,降低了地缘政治竞争的强度。
谋求亚太地区霸权,不仅不符合时代潮流,而且会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米尔斯海默认为,要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生存下来,最好的办法是当独一无二的地区霸主,中国发展起来后必然要追逐亚洲霸主之位,因为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但是,他又指出:“美国是现代史上唯一的地区霸主。拿破仑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五个大国都曾努力尝试称霸其各自地区,但无不失败。”(40)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94页。这显然存在逻辑矛盾,也就是大国追求霸权成功的概率极低,近代只有美国一个成功案例,其余大国都因追求地区霸权而失败。从这种历史经验看,追求地区霸权显然不是大国的最佳选择,反而是“失败陷阱”。新中国领导人对此早有深刻认识,并将“追逐霸权必然失败”这一教训,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经常从世界历史教训的角度,向周边国家友人和政要解释中国为何不能走侵略扩张之路,指出霸权、势力范围就是搞干涉、控制和颠覆,是无法持久的。周恩来认为,现代任何一个国家要进行扩张,建立霸权,总是要失败的。(41)《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710页。邓小平后来也指出,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2)参见《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1251页。“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4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6页。谋求地区霸权、势力范围或某个集团的“头头”,会严重损害本国的声誉和形象,最终将过分透支自身实力,招致失败,这是历史上众多崛起大国普遍所犯的“颠覆性错误”。
对于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而言,任何大国建立地区霸权的企图都会损害它们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等国家的公报或联合声明中,都写明了“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各国人民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的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的共同主张,也都有“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图谋”或者“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的内容。近代以来亚太地区大部分国家都沦为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对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尊严都倍加珍视。在当今亚太地区如果哪个国家还想试图建立某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必然会遭到坚决抵抗。相似的遭遇和共同的命运,使中国对亚太国家维护自身主权和独立的愿望感同身受,对它们的独立和主权有着天然的尊重。
(三)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示范区”
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步,与整个亚太经济活力不断增长、安全局势基本稳定、地区合作蓬勃发展相同步,安定繁荣的亚太构成中国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的发展既为亚太地区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巨大机遇,也构成整个亚太地区繁荣进步的一部分。平等合作、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已经成为亚太各国的共识,是亚太地区的发展大势。谋求地区霸权会搞乱亚太稳定繁荣的局面,必定带来本国安全和形象的根本性恶化,最终损害自身发展和安全方面的根本利益。因此,不谋求亚太地区霸权并非中国外交的一种纯粹的道义要求,也基于重大国家利益考量,是道义与利益的结合。
奉行了100多年“门罗主义”的美国,将美洲变成了“后院”,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将侵略矛头首先对准相邻的朝鲜和中国,纳粹德国最早侵害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邻国。这些历史案例似乎印证了一个“历史定律”,即一些大国崛起后,首先遭殃的是其邻国。吞并和控制周边是大国崛起的初步阶段,而后才是它们更大的全球野心。强大后的中国一直在坚决避免重复这一“历史定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首要表现是如何处理周边关系,如何定位自身地区角色和作用,具体体现在与周边建立何种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互动关系。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战略和主张,都是从亚洲周边地区先行。正如习近平在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指出的:“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44)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981.htm[2022-01-11]。
中国将周边外交置于外交全局的首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通过和平方式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已经通过友好协商,与14个邻国中的12个国家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与俄罗斯共同提出亚太安全与合作倡议,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因此,中国将亚太地区作为自身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示范区”。中国不谋求霸权的承诺,首先在中国的亚太战略中得到实践和证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就会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
三、新时代中国亚太角色的未来前景
在新时代的亚太地区秩序变革中,中国的角色定位面临各种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大国之间不断加剧的“不良战略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合作与机制创建方面缺少互信,以及中国国内舆论和民众观念的变迁等。为了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更好地坚持和平发展、不谋求地区霸权的基本角色定位,中国需要与美国、日本等大国,在亚太区域机制的创建和地区安全合作方面建立基本的互信。中国应该清楚界定不称霸的战略含义,加强民众教育和舆论引导,处理好增强“地区能力”与不谋求地区霸权之间的关系。中国需要更为明确地以底线思维,将不谋求地区霸权的角色定位,作为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条件。
(一)积极应对主要亚太大国之间的“不良战略互动”
对新时代中国亚太地区角色而言,外部的最大挑战是日渐明显的大国之间的“不良战略互动”,这将冲击中国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和认知。我们不能忽视现实主义对中国地区角色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解读。中国的地区角色不仅受自身战略选择的影响,也受大国发展不平衡以及随之而来的“不良战略互动”的影响,恶化的国际体系和外部环境也会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的政策选择。冲击中国自我克制的战略文化的主要外部因素,是亚太大国对中国在亚太积极角色的误读与反制。我们一再表明和平发展、不争霸、不谋求势力范围的意图,但是美国并不相信中国的战略诚意,实施了一系列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政策和行动。
美国可能会对中国不谋求地区霸权政策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行为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突破中国底线,采取“翻转型”政策,增强与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在亚太采取平衡中国实力增长的重大战略行动,甚至建立明确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地区机制。例如,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组成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及美、日、印、澳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等;美国协同日本突破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共识,过度强化自身在亚洲的战略优势,导致中国安全环境的急剧恶化等。这些反过来会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疑虑,迫使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并重新审视自身的亚太角色。
中国应向美国和日本更为明确传达不谋求亚太霸权或领导权的战略意图。如果说,美国在亚太的某种优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对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至关重要,那么中国既不否认这种现实,也不试图挑战和改变这种格局。当然,巨型中国的存在,永远使美国在亚太的优势或霸权都是有限度的。美日也应正面看待中国在亚太事务中扮演的更为积极的角色,为中国的发展留出空间,使中国相信它们不试图在亚太构建遏制中国的包围网,同时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如台湾问题有足够的尊重和善意。
(二)增强中美在地区合作与机制创建方面的互信
当前的关键问题是要使中美日韩等主要亚太地区大国,在亚太秩序的稳定和变革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尤其要在亚太地区合作与机制创建方面建立互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战略一方面巩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的双边关系,保持前沿性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努力创建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等地区多边机制,作为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平台,保证美国能持续从高速发展的亚太经济中获益。(45)Renato de Castro, “U.S. Grand Strategy in Post-Cold War Asia—Pacific,”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 16, No. 3, 1994, pp.347-348.近十几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和倡导亚太及各种次区域的多边经济、贸易、投资机制,而大部分机制都没有美国参与,例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澜湄合作机制、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新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
对于这些没有参与的地区机制,一部分美国人担心美国在太平洋西部被边缘化,认为这是中国试图用多边主义和多极秩序削弱、排挤美国。美国则试图创建一些新的不包括中国的区域机制,例如夭折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在中国看来,这一协定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将使中国在亚太经济技术分工、贸易、投资方面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亚太主要大国在区域合作机制方面缺乏共识、互相猜忌,一方面导致区域合作停滞不前,另一方面会造成区域合作机制的分裂甚至不同机制之间的对立。在亚太地区新的多边机制创建过程中,中美应加强合作和沟通,使这些机制彼此包容而非相互排斥,尤其是中国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创造美日韩澳等国家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多边机制。
(三)明确界定领导权、主导权等概念
中国还需清楚界定不称霸的战略含义以及领导权、主导权等概念。概念不清,不仅影响自身外交战略设计和实施,也可能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霸权在中国人的认知中除了超强实力的物质含义,还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中国人对霸权的理解更侧重于其行为方式和道义形象方面。中国人把霸权主义看作是霸权的必然伴生物,认为与霸权地位相伴相生的是专横霸道、称王称霸、倚强凌弱、侵略扩张等。(46)显然,与中国人对霸权的负面评价不同,霸权国自身对于霸权的看法是“积极正面”的,例如“霸权稳定论”“美国的仁慈霸权”等观点,并且对霸权的理解侧重于实力优势方面。关于这种认知差异,参见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7—9页;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30—45页;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5, No. 3, 1981;Robert Kagan, “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 No. 111, 1998。对中国而言,不称霸的战略选择,主要是界定和限制中国对外行为的方式,而不是限定中国自身国家实力的增长。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肯定会超越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地区或世界霸主。霸权国既要具备独步全球的经济和军事硬实力,也要具有全球吸引力和号召力的软实力,还必然会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实施对外政策。
所谓的地区霸权,至少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在本区域内拥有广泛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力量存在;(2)具有广泛的军事和准军事同盟关系和网络;(3)具备对地区内其他重要国家内政、外交的重大影响力或控制力。中国既不具备任何一项条件,也没有表现出对它们的追求意图。更重要的是,争霸和称霸主要不是指国家的力量,而是指一国执行的政策。不称霸主要指不搞倚强凌弱、侵略扩张、剥削压迫、欺侮弱小、强加于人等。霸权、领导权、主导权的含义有所区别,但本质上都是指某一势力范围或集团的“头头”,凌驾于他国之上,依靠实力贯彻意志。(47)对于“中国领导权”的一种积极正面解读和设想,参见郭树勇:《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与中国的角色定位》,《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7月(下)。
中国在一些重要的区域问题上会扮演更重要的倡议者、协调者、组织者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但这种角色并不是领导者或主导者的身份。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中国都是主要的倡议者和推动者;在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过程中,中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这些活动主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并没有打造势力范围或领导者角色的意图。例如,美国学者陆柏彬就明确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但是并不具有“侵略性”,其核心内容是一项开诚布公地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经济政策。(48)参见陆柏彬:《大国政治、权力转移和美中风险管控》,《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6期,第13页。
2017年3月,针对外媒提问中国是否会承担起“全球领导角色”,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认为应把国家分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当让联合国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切实发挥好处理国际事务的功能;与其说领导,不如讲责任,大国拥有更多资源、更大能力,理应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49)参见《王毅谈中国的国际作用:与其说“领导”,不如讲“责任”》 ,新华网,2017年3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lh/2017-03/08/c_129504224.htm [2022-01-10]。这不是中国政府刻意回避领导权问题,而是非常清醒地避免落入西方式“霸权话语”的陷阱,中国学者也应避免这种话语陷阱。
(四)重视国内舆论和民众观念变迁带来的影响
中国还应重视国内舆论等国内因素对不称霸的战略选择的挑战。对于大国而言,地区霸权或领导权确实具有极其巨大的诱惑力。当一个大国的实力迅速增强并且对发展前景高度自信时,其大众追求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导者荣耀的冲动将变得难以抑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克制一个崛起的中国的关键力量是中国自身。中国的迅速发展更为迫切地提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审慎问题。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强调不称霸主要考虑的是“将来”中国强大了应该怎么做,那么当代中国领导人则要考虑已经初步强大的中国“必须怎么做”的现实问题。以前我们向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反复解释和宣示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当时中国比较穷,是真正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和军事实力也有可观发展。在新的条件下中国会不会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见到了这样的问题,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当时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50)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7页。毛泽东永不称霸的思想,主要是预见到中国强大后,可能会出现冒然扩张和透支实力的问题,而在当时确立的“未来战略”。
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国内出现了某些“大国主义”情绪上升的现象,谋求主导权、领导权或东亚霸权的观点和声音不时出现。很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学者,把不称霸的战略选择解读为纯粹的外交宣传,认为这是中国为减少崛起阻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有人认为,国家战略应该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一味坚持不称霸,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而中国崛起的标志之一,是具备某种程度的主导权或领导权。
事实上,如果没有长期以来中国对和平发展、不称霸等的不断宣示,中国的国际形象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美好,周边国家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的担忧会更加强烈,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会更加恶化。如果中国主动谋求地区主导权、霸权或所谓“共享的领导权”,就会真正落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从根本上排除了使中美避免直接对抗的出路。当前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接近于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这样的时刻也最有可能蕴含困难和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就会出现重大挫折,谋求地区霸权则是一种“颠覆性错误”。在这样的意义上,不追求亚太地区霸权或领导权,既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防止中国在对外行为上犯“全局性错误”的一条战略底线。因此,除了国家制度和外交政策的规定之外,从教育、舆论等方面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际作用,理性定位自身的区域角色,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牢固树立“亚太的中国”的观念,积极推动区域合作
中国还要处理好增强“地区能力”与不谋求地区霸权之间的关系。明确加强“地区能力”的目的,在于更积极地推进地区合作,保证周边稳定和发展。(51)参见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构》,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43页。中国的发展和外交能力的增强,虽然可能引起周边国家不安,但总体上是建立利益共赢的过程,双方都从合作尤其是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区域组织所具有的天然的多边性、制度性、规则性,为各成员国对彼此的行为提供了可预期性。原来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德、法通过在欧盟内部的积极合作,消除了各自的霸权野心,实现了国家间的和解。尤其是德国通过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恢复了其正常的国家身份,也完成了从追求“德国的欧洲”到真诚做一个“欧洲的德国”的转变。(52)参见连玉如:《再论“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连玉如:《“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新德国问题”前景探索》,《德国研究》2003年第1期。
中国应牢固树立“亚太的中国”而不是“中国的亚太”的观念,积极推动和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创建更多新型合作平台和地区治理机制,使中国在转变为现代化强国过程中释放的巨大发展机遇传递给其他国家。在区域合作机制框架内的紧密互动,可以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互利共赢的关系模式,发展相互信赖的共同身份,从而消解周边国家的疑虑。
中国尤其要处理好与东盟的关系。中国尊重并接受东盟提倡的规范,通过紧密的经济与安全纽带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表现了与东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共同保证东亚地区安全、繁荣和稳定的战略意愿,也增强了中国对东亚地区一体化的认同。中国承认东盟在东亚地区多边进程中的中心地位并在发展过程中选择开放性的合作战略,是东亚地区秩序没有因为中国迅速崛起而发生剧烈动荡的根本原因,也是东亚地区没有发生战乱的主要原因。(53)参见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大国的社会化:东亚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崛起》,载秦亚青主编:《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200—201页。
在东亚地区化过程中,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扮演了规范提供者、区域协调推动者的中心性角色。中、日、韩三个东亚地区大国都表现出对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的尊重,这也避免了地区大国对地区发展领导权的争夺,保证了东亚区域进程的多边协商色彩。中国应该在东亚区域事务和区域一体化问题上,更为坚定明确地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通过积极推动各种区域性、次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使中国全方位地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周边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有了牢固坚实的战略依托。
四、结 语
亚太秩序的最终形态取决于大国的竞争,也取决于中国发展最终能达到的程度以及中国扮演的角色。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并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大国,除了要在亚太经济、安全和区域合作等各方面扮演更为积极有为的建设性角色,还应在国家行为上持之以恒地恪守战略底线,即不谋求地区霸权、不搞势力范围和经济剥削,这对于亚太的和平繁荣同样至关重要。正如张蕴岭指出的:“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开始很多人可能不相信,如果我们坚持下去,让时间考验,慢慢大家会把它作为国际关系准则。”(54)张蕴岭:《中国与邻国关系的转变与思考》,载许振洲、汪卫华主编:《自主 理解 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60年》,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270页。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访华时说:“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整个世界将会受到中国的决定性影响,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中国人之长处与美德能否存留于世?或者,中国为了自存必然沾染那些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罪恶?如果中国人真的模仿了侵略中国的那些民族,我们整个人类将会成何体统?”(55)参见张家康:《罗素:“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百年潮》2019年第12期,第90页。这指出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民族复兴的方式所具有的重大文化意义。中国、印度等作为非西方式的东方大国复兴和崛起,在世界近代历史上是极为独特的,这一过程将带来很多不同于西方式的国际关系理念、行为方式。不在亚太争霸、称霸,既是中华民族复兴体现出的一种历史进步和社会进化,也是中国带给世界的积极文化信息。
中国人对于近代中国战火频仍以及被侵略、被奴役的痛苦经历记忆犹新,刻骨铭心。中国人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境界,注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情怀。近代的痛苦经历,要求中国不能刻意模仿丛林法则,不走西方列强的老路,不再将痛苦加诸别人。中国不谋求地区霸权,有减小美国及其他大国猜忌的“工具理性”目的,但主要是源于自身传统文化、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对世界历史经验的中国式理解,体现了中国外交的道义原则和世界的进步性要求。中国坚持不称霸、不扩张、不建立地区性的势力范围,这种大国崛起所倡导和实践的和平发展理念,代表了世界历史新的进步潮流和国际关系的进化。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要有自己鲜明的外交准则和价值追求。中国赢得的国际声誉与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程度,也有赖于中国外交能否具备一种持久鲜明的“道义可信性形象”。中国持久鲜明的国家形象,主要来自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自尊自信的大国展现的独特外交风范与品格,也就是中国外交的个性。个性不是行为乖张,漠视或颠覆既有秩序,而是既能借鉴遵循国际公认的基本价值和准则,又洞察国际政治的缺陷,能有所匡正和改进,才是真正承担了“建设性”的国际责任。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对于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弥补现有国际体系的缺陷,尤其是对克服极端国家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都能有所帮助。这与西方主要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的干涉主义、霸权傲慢、黩武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不谋求霸权的战略选择之下,中国形成了制度性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塑造中国鲜明的大国外交个性和道义形象。
向国际社会讲好和平发展、不称霸的“中国故事”,关键是靠中国的实际行动和一以贯之的坚持,这本身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好宣传和证明。种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对中国强大后的行为方式、发展道路有不确定性预期,从而产生了焦虑和恐惧。最先直接感受到中国体量和影响增长的是亚太周边国家,它们对于中国崛起的顾虑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中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地缘政治舆论环境。这是任何崛起大国都不得不面对的“成长的烦恼”。通过融入亚太和平发展的大潮实现自身发展、通过多边机制应对共同发展和安全问题、通过区域合作培育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这样的亚太政策,中国就更易于获得周边信赖。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必然受到重大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在不谋求地区霸权问题上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对此中国要始终坚持战略决心和战略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