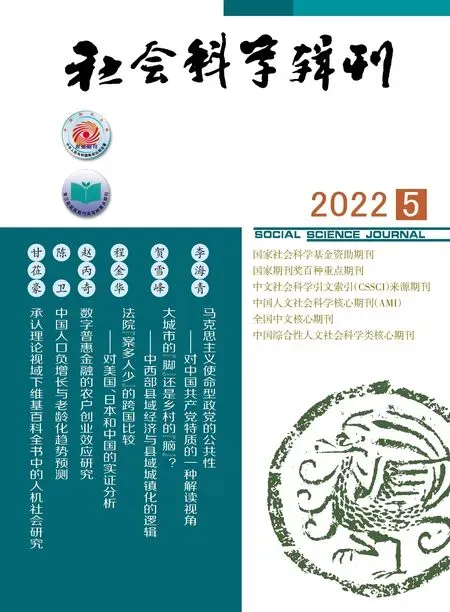《玉台秋》传奇及其副文本的书写与建构
马丽敏
黄燮清(1805—1864),原名宪清,字韵珊,又字韵甫,号吟香诗舫主人、茧情生、两园主人,海盐(今属浙江省嘉兴市)人。诗词曲皆工。著有戏曲九种,按时间顺序依次为《茂陵弦》《帝女花》《脊令原》《鸳鸯镜》《凌波影》《玉台秋》《桃溪雪》《绛绡记》《居官鉴》。①除了《玉台秋》《绛绡记》,《茂陵弦》《帝女花》《脊令原》《鸳鸯镜》《凌波影》《桃溪雪》《居官鉴》合刊为《倚晴楼七种曲》。本文所引《倚晴楼七种曲》,为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其《重刊〈倚晴楼七种曲〉序》说为影印同治四年(1865)刻本,但据黄燮清女婿冯肇曾《居官鉴·跋》所署时间,应为光绪七年(1881)刻本。本文引自此版本之七种戏曲及序、跋、题词等,不另出注。另,《玉台秋》《绛绡记》之所以未与七种曲合刊,最大的可能是当时冯肇曾手中并无这两种戏曲的抄本或印本。据冯肇曾《居官鉴·跋》,《茂陵弦》《帝女花》《鸳鸯镜》《凌波影》《桃溪雪》在其合刊前已有印本,而《脊令原》《居官鉴》亦有藏稿。《玉台秋》原本应一直在吴廷康手中。《绛绡记》为咸丰二年(1852)底或三年(1853)初黄燮清在京谒选期间应梨园艺人所请而创作,只有手稿本,为曹春山收藏。见关德栋、车锡伦编:《聊斋志异戏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作家及作品简介”,第6-8页。以戏曲创作持续时间之长、作品数量之多,尤其是探索程度之深而言,黄燮清都应归属于戏曲史上少有的专业性作家。然梳理其创作的发生,除了他主动创作的具有自喻性质的《茂陵弦》以及没有明显创作信息、写晚清官员王有龄的《居官鉴》外,其他作品皆明示与他人之“命”“托”相关——《帝女花》是在好友陈其泰的影响下所作,《脊令原》《鸳鸯镜》是浙江学政陈用光给的“命题作文”,《凌波影》是对《鸳鸯镜》的更进一解,《玉台秋》《桃溪雪》是应好友吴廷康之请而撰,《绛绡记》是应戏曲演员要求所作。其中,《帝女花》《桃溪雪》作为黄燮清戏曲的代表作,流传较广,为他带来了诸多声誉。吴梅曾品评黄燮清戏曲道:“韵珊诸作,《帝女花》、《桃溪雪》为佳……”〔1〕并确认其晚清戏曲家代表的地位:“今自开国以迄道光,总述词家,亦可屈指焉。……道咸间则韵珊、立人、蓬海耳。”〔2〕
与《桃溪雪》相比,吴廷康请求黄燮清创作的另一部戏曲《玉台秋》,则在当代戏曲研究中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玉台秋》演绎吴氏夫妻之真人真事,创作于道光十七年(1837),共16出。完成后由吴廷康收藏,直至光绪六年(1880)才将其刊印出版①杨葆光《补〈玉台秋〉下场诗跋》有“吴君康甫……今复刻此本,属予评校”之语,时间为光绪六年(1880)。本文所用《玉台秋》及其序、跋、附录等,出于《古本戏曲丛刊》十集影印光绪六年(1880)琼笏山馆刊本,文中不另出注。,时间已经过去了40余年。出版时,吴廷康进行了一次征集序、跋、题词的活动,并将一些与戏曲正文无关的论著附于其后,导致《玉台秋》所附序、跋、附录等颇多:前有黄燮清《自序》、杨葆光《序》、徐维城《题词》,后有杨葆光《补〈玉台秋〉下场诗跋》、张开福《〈侍疾图〉书后》、钱泰吉《桐城吴君夫人权厝铭》、吴廷康《茹叟漫述》、杨晋藩为吴廷康之子吴福成所作《浙江补用县丞吴秀峰遗像记》、纪吴廷康之女吴珩的《列女传》、吴廷康关于金石文字之著述《问礼庵论书管窥》,以及杨晋藩、俞樾、杨葆光为《问礼庵论书管窥》所作二序一跋。这些序、跋、附录等,文体多样,内容驳杂,篇幅将近《玉台秋》戏曲正文的3/4,与《玉台秋》传奇一起,构成了晚清戏曲创作中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梳理戏曲及序、跋、附录等副文本②“副文本”概念来自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副文本:阐释的门槛》,本文借以指“依附、穿插于正文本的序跋、题诗(词)、插图、评点乃至题目、署名、凡例、目录等”。见杜桂萍:《明清戏曲副文本及其互文性解读——以乾嘉时期徐燨戏曲创作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29日,第4版。,由其中所蕴含的复杂内容与思想可窥见晚清戏曲观念变化之一斑。
一、风化:戏曲及副文本传播的密钥
吴廷康(1799—1881后),字康甫、康父,晚号茹叟,安徽桐城人。其妻张氏,张氏母为桐城姚鼐女侄③吴廷康《茹叟漫述》载:“外父砚峰公为文端公族孙,外母姚孺人为端恪公裔孙女,惜抱先生犹女,石甫先生从妹。……时(浙江)学使为道州何文安公,公既爱才重士,公子子贞、子毅复皆风雅淹贯,相与考索吉金乐石,结契甚厚。继文安者为新城陈硕士先生,先生本惜翁门下士,又与石甫丈有儿女亲,以康亦与外姻。”,而时任礼部侍郎兼浙江学政的陈用光④陈用光(1768—1835),字硕士,嘉庆六年(1801)进士,道光十三年(1833)以礼部侍郎兼浙江学政。据《奏报到任日期》《奏为奉谕转补礼部左侍郎谢恩事》《奏报交卸浙江学政篆务日期事》等,道光十三年(1833)三月初二,礼部右侍郎陈用光到浙江学政任,七月初八,由礼部右侍郎转补礼部左侍郎。道光十四年(1834)九月二十五日,交卸浙江学政事宜。陈用光原作,许隽超、王晓辉点校,蔡长林校订:《陈用光诗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19年,第1025、1028、1033页。为姚鼐门下弟子,吴廷康仕宦浙江时曾依附于陈用光,由此与黄燮清相识、相交。⑤吴廷康《茹叟漫述》载:“先生(陈用光)既胎息桐城,经学深邃,大江南北讲求实学者闻风远至,康以是益得广交焉。……尝与海盐张石匏(开福)、黄韵珊(宪清),萧山陆次山(㙨),结诗社于中。”道光十四年(1834),吴廷康染疫卧病,张氏竭尽心力照顾,以致积劳成疾去世,吴廷康怀念不已,广邀友人进行题写,以为悼念。如张开福《〈侍疾图〉书后》云:“岁甲午五月,桐城吴康甫之妻张宜人歾于武林,及期,康甫将释服,思宜人不置,绘《侍疾图》,赋四截句以自写其悲情,并索友人之能文与诗歌者,缕其懿行,书于册。”钱泰吉《桐城吴君夫人权厝铭》亦指出吴廷康的主动求取:“吴君熟于金石文字,出所撰行述以示泰吉。”本人或请人为亡妻作传、墓志铭等,自是常见之事,然吴廷康并未止步于此,又请黄燮清作戏曲以传之:“康甫既痛其(张宜人)逝,而又悯其代己也,嘱为乐府以传之。予不文,何足以传宜人,而康甫请之坚……”(黄燮清:《玉台秋·自序》)因有《玉台秋》之作。想必吴廷康对此非常满意,因为十年后,担任永康县丞的吴廷康,访得当地才媛吴宗爱(字绛雪)于三藩之乱中殉节事迹,“惧其久而泯焉”,于是又想到了黄燮清,多次请求其“制曲以传之”(黄燮清:《桃溪雪·自叙》),因而黄燮清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创作了《桃溪雪》。
《桃溪雪》创作完成后,即由吴廷康刊刻面世①杨葆光《补〈玉台秋〉下场诗跋》有“吴君康甫昔尝刻《桃溪雪》院本”之语。,迅速流播天下。本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吴宗爱,其人其事借由《桃溪雪》而为世人所知。如黄燮清友人陈其泰弟子胡凤丹云:“忆道光己酉从海盐陈琴斋师游,尝论文人学士以著述寿世,其不朽与勋名等。一日,出《桃溪雪》传奇示余曰:‘此吾友黄韵珊孝廉所著也,所述为永康故事,汝知之乎?’余曰:‘吴绛雪者,向熟闻之,然其沈埋于荒烟蔓草间者已百余载,至今以女烈士特传,则韵珊先生之力也。’”〔3〕其人之节烈、其事之传奇,可为风教典范。如时人孙恩保所谓:“丝竹中年感慨多,冰池涤笔画霜娥。文章悲喜关风教,此是人间正气歌。”(孙恩保:《桃溪雪·题词》之三)至吴梅,亦赞赏其风教意义:“(《桃溪雪》)其词精警浓丽,意在表扬节烈。盖自藏园标下笔关风化之旨,而作者皆矜慎属稿,无青衿挑达之事,此是清代曲家之长处。韵珊于《收骨》、《吊烈》诸折,刻意摹神,洵为有功世道之作。”〔4〕
黄燮清创作《玉台秋》时,亦强调“以风世之为夫妇者”(黄燮清:《玉台秋·自序》)的作用,或者这是吴廷康看重其创作的原因之一。彼时,在陈用光的指导下,他已认识到戏曲“意盖为维风俗、正人心发也”(黄燮清:《鸳鸯镜·跋》),并在《玉台秋》中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揭示出来。如《得士》一出,提及高斗华(即陈用光)重视吴仲泰(即吴廷康)、恽士珍(即黄燮清)、乐奇(即陆㙨)三人。高提及恽之戏曲,并进行评论:“沧桑泡影,仙禅意境,吊河山曲演琼花,写儿女神追玉茗(只是一句,文人之笔,易业口孽,词虽小道,亦须有关世道人心为佳)。要维持气运,要维持气运,须不在风云驰骋、烟花齐整,笔落鬼神惊,(才见得)游戏关风教,文章本性情。”创作《玉台秋》并强调其风化作用,自是必然。其《自序》开篇言:“《诗》三百篇,皆言情之作,而《关雎》首夫妇,以其得乎情之正也。”以《关雎》篇为其讲述夫妻之事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吴廷康为“情种也,笃于伉俪,得国风之正”。张氏的行为也符合“情之正”:“宜人张氏,温雅柔顺,善侍君子。康甫病疫,常二十昼夜目不交睫,侍汤药不稍懈。夜静辄焚香祷佛,愿以身代。宜人固善病,以病者侍病者,及康甫病愈,而宜人遂至不起。其亦以身殉情者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夫妻关系为五伦之一。所以,以吴氏夫妻二人之事演绎为戏曲,可以“以风世之为夫妇者”。
值得注意的是,40余年后,当吴廷康将记录本人及其子女事迹的文本附于《玉台秋》后刊刻出版时,宣传风教不仅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识,还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即将自己一生以风化为己任的经历、子女有关风化之言行实践,一一附录于戏曲之后,借机完成了其家族史的书写。
吴廷康科场不顺,而于风化尤为用心,数十年如一日,汲汲于此。黄燮清在创作《桃溪雪》传奇时,已指出吴廷康具有以宣传教化为己任的责任感:“凡忠孝义烈之未经表著者,必阐扬其隐,以为世风。”(黄燮清:《桃溪雪·自叙》)光绪七年(1881),吴廷康在《茹叟漫述》中总结自己一生之成就,亦突出在风化上的用心:“康少不喜帖括,多识前言往行,以是久困场屋,援例县佐。筮仕浙江,首诣栖霞岳忠武王庙、三台山于忠肃公祠、孤山姚芳麓公祠,俯仰感喟,慨然于立身行事,必求践履笃实,有裨于国计民生,不徒生膺爵禄,死隆庙祀已也。”“私念事权不属,无可利济,惟借表扬忠孝,亦足挽回世道人心。”“康以天道虽远,而愚民无知,最为倾听。大忠大孝,妇孺皆知,转移风教,莫此为易。故于修建祠宇不遗余力,名胜基址皆为题志,孝义节烈皆为表彰,而于岳忠武王尤若夙契。”长期身处下僚,满腔抱负无所施展,只能用心于风化,期待达到教化百姓、挽回世道人心之目的。同人好友于此亦积极应和。如光绪四年(1878),杨晋藩为吴廷康《问礼庵论书管窥》所作《序》中强调:“(吴廷康)所至之处,无不表扬忠孝节烈,立碑绘像,以激励风俗为己任。虽未大展厥用,被其泽者至今颂之。”光绪六年(1880),杨葆光为《玉台秋》所作《序》亦如此评价吴廷康:“盖君于世味淡,尝权知杭湖属县,授平湖丞,而君不以为意,尝曰吾幸不为烦剧,得以专力阐扬,为世道人心计,所至必表彰节烈,修复祠宇,今杭城内外,石碣相望,皆君所表,古圣贤仙佛庙祀旧址,或已修复,或尚榛莽,行路者皆唏嘘感叹,以为君莫大之功也。”吴廷康之女吴珩,骂贼被杀,事迹被《浙江忠义录·列女传》记载:
吴氏,名珩,安徽桐城人,浙江县丞廷康女,归候选府同知兰溪蔡钲。廷康故以金石学有重名,珩少从父读书,恒举古节烈遗事,若甚艳之者。长而工画,得者珍之。咸丰十年,珩随廷康在严州与金华,是冬嫁于钲,仍依廷康以居。明年四月,贼犯金华、严州,珩奉姑登舟,于桐梓滩遇贼,罄其所藏书画装敛,珩恐不免,即跃入水。贼去,姑挽救之,得不死,寓杭州五福楼。十一月,城破,钲间道逸去,珩与姑又相失。贼入室掠,珩奋身骂贼,贼杀之。初,廷康尝题珩画枫鞠云:“奇节皆从血性成,文章婉娩见真情。画图省识冬心冷,留取人间清白名。”殆诗谶云。
吴珩不屈被害,以古代节烈故事为榜样,源于其少时所受父亲的教导。吴廷康之子吴福成(字秀峰),亦秉承庭训,以维护教化为己任。吴廷康《茹叟漫述》云:“凡此者,次男(吴福成)无事不共,无役不先至。光绪二年,重修于忠肃公庙墓。次男栖止山中,积受风湿,然犹奔走随坛,四方延请,虽远必赴,病极而殒。”光绪三年(1877),杨晋藩《浙江补用县丞吴秀峰遗像记》云:“凡康甫监造忠显庙、精忠殿,并置墓亭,增广前后余基,拓桥亭,建照墙及教忠孝堂前后殿宇,崇丽宏壮,规划黼藻,悉令秀峰董其役。”杨葆光《玉台秋·序》亦云:“次子福成,助君筹购忠骸旧址,奔走督率土木尤力。……而次君赞成阐忠之功甚伟,益见宜人教泽之深矣。”由其子女之言行,可见其家族从事风教之实践,可谓薪火相传。
由上可见,黄燮清创作《玉台秋》时,强调“得国风之正”的“情之正”,从而实现其“以风世之为夫妇者”之目的,在暮年吴廷康的心中已经沉积为其家族荣誉的一部分,并构成了家族书写的核心内容。正如杨葆光之概括:“予尤有感者,表忠义、复祠宇,皆为有司供职中之一端,乃有司者不为,而君独毅然为之,宜人之奇节懿行,感应即在门内,可以风世之为有司者,则《玉台秋》之关系实大,又岂特美其不深晦而明贯矣乎!”(《玉台秋·序》)由此,作为家族美德之文学化典范的《玉台秋》及其副文本的书写与建构方式,使戏曲及副文本的“风化”表征更具现实指向和文化实践意义。
二、真实:戏曲及副文本传播的基础
《玉台秋》是据真人真事创作,真实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黄燮清在《征词》一出中借剧中人之口言:“他(吴仲泰)自悼亡之后,悲肠抑郁,意兴阑珊,前日做了一篇张宜人的行略,托兄弟带来,要求吾兄妙笔,替他谱入乐府,借以流传。”根据记述张氏生平事迹的行略而作,戏曲之真实性自不待言。黄燮清当然也做了一些艺术想象,如最后《演曲》一出,写高斗华乃天上欢喜佛,“劫满返真,仍归莲座”,“近闻吴生丧偶,哀丝缠绵,嘱恽生谱得新词一册。俺既爱恽生之才,兼悯吴生之痴,将所谱新词,教座下仙女演成歌舞,顷着梦神引吴生梦魂到此一观新乐”。此为曲家常见套路,就黄燮清而言,其在《帝女花》《桃溪雪》中亦有此种人间天上之轮回勾连。但本出每一歌舞前都有一句概括语,如“第一篇名为孝顺歌,是写你室人侍奉庭闱之事”,“第二篇是双飞舞,写你夫妇闺房静好之情”,“第三篇思归曲,是写你室人随宦西湖,系恋家乡情况”,直至“这末篇离鸾舞,是写你感逝哀衷”。如是等等,是为张氏作传记,也是为整部戏曲主要内容做一总结,亦强化了张氏之贤良与吴廷康之深情。
《玉台秋》戏曲内容的真实性是吴廷康、杨葆光等在副文本中尤为着力强调的。杨葆光在评点中常常指出情节或事件的真实性。如第一出《情叙》中,生云:“娘子从前病危之时,几乎不省人事,亏了令弟梦白虔祷于大士跟前,愿减己寿十年,为娘子延寿,后来遂得渐渐苏醒。”眉批云:“身代衬笔,补叙实事。”又如关于两人姻缘似是天定之意,生说:“我与娘子定情之前,母亲命拈阄于先大人之灵,三卜皆吉,可见前生注定,非比等闲也。”眉批云:“正恐至诚感神,菩萨亦为首肯,实事处处补叙。”再如吴廷康喜爱金石古砖等,张氏协助其整理收藏。戏曲中写道:
〔副净上〕枝上时栖同命鸟,阶前尽种合欢花。老爷宜人,原来在此闲话。〔生〕孙妈来此何干?〔副净〕老太太房中无事,要取老爷所购的金石古砖赏玩赏玩哩!〔旦〕这些东西都是奴家收藏的,待与相公同去取来。
眉批云:“补叙实事,当与《茹叟漫述》参看。”这一情节确与《茹叟漫述》中“凡生平所嗜书籍金石,皆张宜人主之”之语对应。杨葆光所作《序》,更是将戏曲中情节与张氏生平一一对照,如:“素虔奉大士,尝梦老人偕白衣者授以儿,而感孕。宜人初未见君舅,醒以其状告君,乃知为君父咏泉先生。故长子候选训导福崇之生,初名志祖,以志其异。及长女式顺生,宜人病甚。其弟梦白,名长庚者,祷于神,愿减己寿十年,以延姊算。既感梦大士,病霍然愈。生次子福成、次女式柔,以迄于没,适符十年之祷。《祷佛》下本拟有《麟兆》《试唬》二阕,以著大士之显应。韵珊以上下卷次不匀,故阙之。君少好博览,不得志于有司,谓当读有用之书,不宜逐逐于词章之末,益发所藏古书金石文字,沈浸秾郁,多识前言往行。宜人复为之收掌编纂。及宦游至浙,受知大吏,所交多贤俊士,座上客常满。宜人主持中馈,脱簪供客,无难色。有如皋张寿承者,为故方伯张朝觐之子,巡查钱塘门外,老病且贫,临终以身后托君,君为经纪其丧,供给乞贷以归其孥,宜人复解手钏以济之。如《情叙》《哭弟》等篇中所及,皆实事也。”
如是,基于真实人物、真实事件创作的《玉台秋》传奇,与张开福《〈侍疾图〉书后》、钱泰吉《桐城吴君夫人权厝铭》等可为传记资料的文章形成互文,补充、印证和阐发。
基于真实性诉求,吴廷康亦将自著的《茹叟漫述》附于戏曲文本之后。《茹叟漫述》是关于吴氏家族的发展史资料,其远溯安徽休宁之始祖,近从明末七世祖吴应琦起,讲述吴氏一族由南京至桐城,因明清易代,隐于民间,以耕读传家的家族历史,直到吴廷康之子女为止。又将杨晋藩为吴福成所作《浙江补用县丞吴秀峰遗像记》以及《浙江忠义录·列女传》中关于吴珩事迹的传记性文字也附于戏曲文本之后。
这样的副文本建构方式,来源于乾嘉以来戏曲观念的变化,深受蒋士铨以史笔从事戏曲创作的影响。作为乾隆时期最著名的戏曲家,蒋士铨曾强调“安肯轻提南董笔,替人儿女诉相思”〔5〕,以史家心态从事戏曲创作,赋予戏曲更高的要求、更深的寓意。如《空谷香》下场诗云:“大千中现一贞魂,苦海茫茫敢细论。偶借酒杯浇磊块,聊将史笔写家门。”〔6〕其戏曲诸题词亦褒扬其史笔叙事模式。如高文照为《空谷香》题诗,其一云:“史公家世传金笔,阐得幽微信可征。一代庐陵风教在,肯教小说没王凝。”其二云:“词苑曾推若士汤,南安梦境太荒唐。不传梅柳传兰蕙,压倒风流玉茗堂。”〔7〕王凝为隋朝史学家,著《隋书》未成而卒。汤显祖为明代戏曲家,在戏曲史上影响深远。两首诗在对王凝的推崇与对汤显祖的不认可中寄寓明显的褒贬之意,而“阐得幽微信可征”“南安梦境太荒唐”之语更体现了创作观念的转型——更加重视真实性。
晚清曲家及其评论者,多有直白地表露以蒋士铨戏曲为圭臬的话语。如黄燮清《帝女花·自序》云:“声捐靡曼,不同燕子吟笺;事涉盛衰,窃比桃花画扇。”透过坤兴公主与驸马周世显的悲欢离合,探讨的却是有明300年基业毁于一旦之根源。时人张泰初即评道:“数文心,前汤后蒋,与君鼎足。”(张泰初:《金缕曲》,《帝女花·题辞》)至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戏曲《居官鉴》,则更为明确地体现了黄燮清欲为“曲中之龙门”(《传鉴》出眉批)的历史担当。如第26出《传鉴》〔南尾声〕云:“《居官宝鉴》非虚诞,燕翼贻谋启后贤。(待付与)当代龙门,(演成)《循吏传》。”以戏曲的方式塑造一位能吏的形象,注重其在处理种种困难中展现出的治世之才。晚清另一位曲家、评论家杨恩寿,较早指出黄燮清对蒋士铨的承袭:“海盐黄韵珊谱作《帝女花》院本,本末较详,词笔逼近藏园,非《芝龛》可同日语也。”〔8〕杨恩寿亦盛赞蒋士铨之戏曲:“《藏园九种》为乾隆时一大著作,专以性灵为宗。具史官才学识之长,兼画家皱瘦透之妙,洋洋洒洒,笔无停机。”〔9〕在《续词余丛话》中以蒋氏“安肯轻提南董笔,替人儿女写相思”之语来劝诫同乡黄其恕勿为“绮语”〔10〕。在戏曲创作中亦实践着蒋士铨的理念,如其《理灵坡·自叙》云:
前明崇祯末,张献忠陷长沙,司理蔡忠烈公死事最烈,迄今邦人士类能言之。同治戊辰冬,重修省志,余滥充校录,读公传略焉弗详,考《明史·本传》,亦多讹脱,亟求公年谱参益之未得。越明年,从旧书肆购得新化邓氏所定《遗集》,附刻《行状》纪轶事较详,多《本传》所未载,喜甚,如获珙璧。至是,于公生平十悉八九矣。庚午夏,以余不任事,为总纂所屏,遂辞志局。家居多暇,辄取公事,谱南北曲为院本,以广其传。叙次悉本《行状》暨各传记,不敢意为增损,惧失实也。〔11〕
杨恩寿参与编撰湖南省志,却不为总纂所喜,愤而辞去。其在《理灵坡》创作上恪守修史作志者的基本素养,即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据实而作,“不敢意为增损”也。
可见,晚清曲家多重视以史家笔法创作戏曲,真实性成为戏曲的一个重要追求。而如《玉台秋》一类基于真人真事而创作的戏曲作品,更便于题材的结撰,但如何以“史笔”传达出关乎社会、时代、伦理的价值观成为作家最为在意者。吴廷康、杨葆光等的评点、序、跋及相关著述,皆在“风化”上立意,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而副文本以数量之多、内容之广构成晚清戏曲史上一个典型的现象,亦可作此解。
三、立言:戏曲及副文本书写最本质的诉求
《左传》曾指出实现人生价值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12〕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13〕。可见“三不朽”中,最上为“立德”,然似只有圣贤才能做到;其次为“立功”,然“功之立必凭借乎外来之富贵,无所借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14〕。因此,立言成为一些沉沦不偶的文人毕生追求之目标。明代以后,文人立言之途径已由诗文而及于戏曲,晚清时期的文人则更因此而用心于戏曲文本形态的建构。
晚清戏曲家多沉沦下僚,长期处于“在野”状态,又生逢乱世,深感“流离但觉乾坤仄”〔15〕之苦痛,其“立言”之心尤切,治世之念尤深。如黄燮清,六入秋闱,方得中举人,又六入春闱,终无功而返〔16〕,仅在晚年得任宜都知县、松滋代理知县等。他在陈其泰、陈用光等师友的鼓励下放手创作戏曲,一度想借此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与之同时的余治,五赴乡试而不中〔17〕,晚年才因宣讲功由附生保举训导。〔18〕身为以“训蒙”〔19〕为业的老塾师,余治一生“专以挽回风俗、救正人心为汲汲”〔20〕,尝试过编撰《发蒙必读》《续神童诗》等启蒙诗歌〔21〕以及宣讲等各种教化民众的途径,最终发现了戏曲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优势。所以余治强调:“古乐衰而后梨园教习之典兴,原以传忠孝节义之奇,使人观感激发于不自觉,善以劝,恶以惩,殆与《诗》之美刺、《春秋》之笔削无以异,故君子有取焉。……乐章之兴废,实人心风化转移向背之机,亦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也。”〔22〕在强调戏曲作用可与《诗经》《春秋》比拟后,指出自己创作《庶几堂今乐》之目的在于“于以佐圣天子维新之化,贤有司教育之穷,当亦不无小补也”〔23〕。由是,晚清文人以戏曲为立言之具,力图通过戏曲创作实现其经世济世之目的,已然为创作之常态。
通观《玉台秋》及其副文本,则可进一步发现借助戏曲而立言之目的,又因为方法与途径的多样而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的特征。吴氏夫妻之事迹借助《玉台秋》戏曲流传于世,这是吴廷康一生之所求,其暮年所作《茹叟漫述》指出其征求序、跋、题词之目的:“于是海昌钱警石(泰吉)为撰权厝铭,石匏题《侍病图》,韵珊谱《玉台秋》传奇,皆激扬咏叹,可传后世。”为此他常常主动征求题咏,如杨葆光《玉台秋·序》云:“顷以此本乞序,因得并及其生平如是。”围绕《玉台秋》广泛征求题咏,并将家族有关风教言行事迹的各种文体附于《玉台秋》文本之后,是吴廷康实现立言传名的一种策略。对于“久困场屋”,只能“援例县佐”,担任下层官员的吴廷康来说,“私念事权不属,无可利济,惟借表扬忠孝,亦足挽回世道人心”,是其无可奈何之下的一种选择。在宣传风化之外,对于吴廷康来说,唯独治学之成绩可为立言之内容,由《玉台秋》后附《问礼庵论书管窥》(原名《金石文字释言》),杨晋藩、俞樾两序,以及杨葆光所为《〈问礼庵论书管窥〉后跋》即可见出其目的。杨晋藩《序》云:“光绪四年,老友康甫吴君年正八十,编辑生平所著金石文字凡若干卷。书成,并自述得力之处,皆古人不传之秘,因仿古者以言为寿之例,问序于予。”表明吴廷康宣传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而吴廷康与俞樾的文字之交,更能体现出吴廷康立言传名的人生追求。吴廷康于同治十三年(1874)请俞樾为自己的《慕陶轩古砖图录》作序〔24〕,后俞樾又为其《问礼庵彝器图》作序。〔25〕彼时俞樾已为经学大家,在晚清学界有重要地位。其自言“谬以虚名流播海内,来求余文者无月无之”〔26〕,许多求序者之目的即是附其姓名、生平事迹于俞樾文集内,以达到传名后世之目的。吴廷康亦应有此目的,因而,光绪五年(1879),他又请俞樾为其《问礼庵论书管窥》作序,并将其序亦附于《玉台秋》文本之后。由此形成了《玉台秋》内容驳杂、文体不一的副文本形态。
借助戏曲及其副文本实现立言之目的,也反映出晚清戏曲在诗文结构关系中的新变化,戏曲作为“词余”的地位进一步上升。陈用光《鸳鸯镜传奇·序》云:“词曲,古诗之流亚也,而世之作者每多绮丽淫佚之语,虽曰体制类然,亦必合乎风人之旨为佳。”“发乎情止乎礼义,洵足惩创逸志而感发善心者”之戏曲,即能由“曲而进于诗矣”。至杨恩寿则直接宣称:“诗、词、曲固三而一也,何高卑之有?”〔27〕并将蒋士铨之戏曲比拟为“诗之盛唐”〔28〕。将戏曲与在文学上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歌相比附,这无疑提高了戏曲的文体地位。时人对戏曲影响力的认知也非常深刻。陈用光《脊令原传奇·序》云:“曲之感人,捷于诗书。今有至无良者,气质乖谬,师友弗能化焉。试与之入梨园,观古人之贤奸与往事之得失,其喜怒哀乐,无不发而中者,则曲虽小道,固亦风俗人心之所寄也。”戏曲由其感人之速而成为风化之最佳载体。俞樾亦有相似之论述,其为余治戏曲作序时指出通俗文学强大的影响力:
天下之物,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师巨儒坐皋比而讲学,不如里巷歌谣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张布于通衢,不如院本平话之移人速也。君子观于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29〕
对戏曲文体地位、风化功能等更为深入的了解,使晚清文人赋予戏曲更多的重视与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六年(1880)杨葆光为《玉台秋》所作之《序》,也从多方面论述了戏曲的优长。开篇言:“桐城姚惜抱之言曰,著书者欲人达其义,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尝不明贯,必不故为深晦也。夫著书之不深晦而明贯者莫院本若矣,一人一家之事,非单辞短章所能尽,而悲慨郁勃,必使首尾曲折以出之,此《玉台秋》所为作也。”通过对一代文宗姚鼐的论文之旨之攀附,指出讲述事件时戏曲在文体上的优长,即“不深晦而明贯者”非戏曲莫属。接着指出戏曲中人物为现实中真人,戏曲中情节、事件亦为现实中之真实发生者,使戏曲文本具备了史传文学的基本特征。进而指出吴廷康以“表彰节烈”为志之人生追求。最后亦以姚鼐收尾:“桐城固多名儒,惜翁尤以斯道自任,有契圣贤之旨,而君之以神道设教,亦推广圣贤之余意。韵珊此作,曲尽缠绵悱恻之情,与惜翁论文之言合。而予尤有感者,表忠义、复祠宇,皆为有司供职中之一端,乃有司者不为,而君独毅然为之,宜人之奇节懿行,感应即在门内,可以风世之为有司者,则《玉台秋》之关系实大,又岂特美其不深晦而明贯矣乎!”在宣传风教观念上将《玉台秋》戏曲与姚鼐联系起来,其文体品格之高自不待言。总体来看,这篇《序》集中体现了晚清时期戏曲观念。
总之,晚清时期,文人立言之途径已堂而皇之地由诗文转向戏曲,戏曲及副文本不仅成为重要的立言途径之一种,且因之附丽更多的其他文体,而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文本形态。长期沉沦不偶的遭遇,加上晚清动乱的社会背景,使晚清文人借助戏曲立言之心较前文人更为迫切,方法与途径也更复杂多样,这对于戏曲文体的“非戏曲化”而言,实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正是这样的“求生”操作,最后导致了戏曲文体的消解。
四、结语
《玉台秋》传奇及其文体多样、内容驳杂、篇幅较多的序、跋、附录等副文本,构成了晚清戏曲创作中一个极为典型的现象。以黄燮清创作之《玉台秋》为中心,吴廷康完成了其家族史的书写。作为家族美德之文学化典范的《玉台秋》及其副文本的建构,使戏曲及副文本彰显出更为复杂丰富的文化意义,而文本及其副文本的建构过程,又体现出借助戏曲立言之方法与途径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凡此,反映了晚清时期戏曲创作与观念上的种种变化,《玉台秋》传奇及其副文本之书写与建构,也因之成为考察晚清戏曲观念变化的一个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