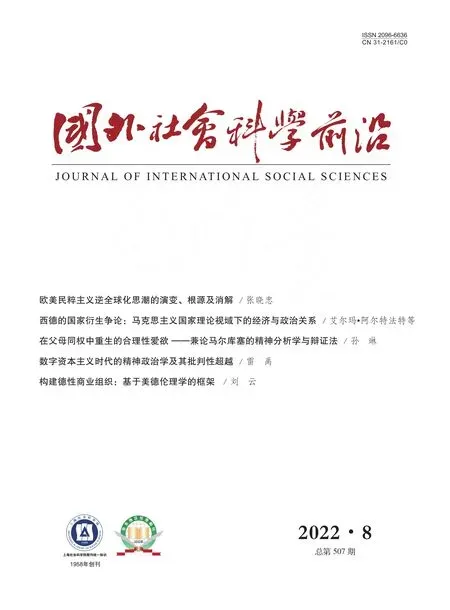西德的国家衍生争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下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
艾尔玛·阿尔特法特 于尔根·霍夫曼/文 李乾坤 覃钰淇/译
为了更好地了解20 世纪60 年代末以来西德国家讨论的特殊性,尤其是国家衍生争论(Staatsableitungdebatte),我们有必要先回顾这个国家社会发展轨迹的历史前提。
首先,在魏玛时期蓬勃发展的批判的也即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被纳粹的恐怖主义打断,战后又被斯大林主义庸俗化所打断,因此最近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很少能够接续上这一传统。数十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为成熟的批判理论左派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参考点——除了少数自认为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进行研究的“独行者”(即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列奥·科夫勒和欧内斯特·曼特尔,他们为在联邦共和国保存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次,西德并没有像许多左派,尤其那些紧紧依附于社会主义官方阵营的圈子所预言的那样经济崩溃并逐渐贫困化。相反,西德社会在20 世纪50 年代到60 年代经历了一个“经济奇迹”。因此,20 世纪50 年代,在阿登纳总理的带领下,联邦德国的政治发展走向了反共的专制民主,并获得了广泛共识的支持。这种共识使得左派被边缘化,甚至被非法化。
再次,在这些过程中,社会民主党迎合了守旧者的复辟要求,并于1959 年著名的“巴登—戈德斯贝格转折”完成了这种调整。尽管如此,这种调整仍然是完全积极的,因为它服务于一个独特的政治计划,即将“国内改革”与外交缓和(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相结合。在长期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他们提出了可以被称作为开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旨在促进就业和完善收入的再分配,以造福广大群众。
最后,这三个因素不仅对西德的社会理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且从1956 年开始,成为了学生运动的社会政治出发点和理论参考框架。而学生运动,反过来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复兴的核心。它在社会变革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国家讨论有决定性影响,此外,它也使得左派将一般理论讨论集中于国家本身。
一、国家讨论的历史背景
法西斯主义结束了德国的批判讨论。从那时起,德国流亡者关于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对话,深深地受到了那些他们被迫流亡国家的理论和政治氛围的影响。这体现在1933 年之后,大部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员流亡美国后对“批判理论”的发展;流亡中的社会民主党内部对被称作修正主义潮流的巩固(受瑞典和英国经验的深刻影响)以及流亡中的共产党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mokap)理论的详尽阐述。在联邦共和国成立早期,这三个组织中没有一个取得过重大的政治权力。此外,随着联邦共和国的发展和经济奇迹给民众带来的非政治性的幸福感,各种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影响力都逐渐降低,不论内容是什么,都普遍被定性为“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违反宪法的”。
像阿本德洛特、曼德尔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回归的成员这样一些理论上“独行者”们,也无法阻止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在法西斯主义之下对工人运动的政治打击。此外,同样重要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经济奇迹的出现)和冷战中的反社会主义情绪,西德资本主义重新恢复了活力,并在民众(以及相应的科学)中达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基本没有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它的论断和预言似乎被资本主义在实际中取得的成功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具说服力的实际情况所反驳。除非这种发展符合当时的立场前提——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政治悲观主义被西德社会中的“美国化”所证实——否则就只剩下理论上的辩护。这一发展采取了在宪法许可范围内坚持民主原则的形式,并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抵制专制主义,从而至少保留社会解放的可能性(这一点在阿本德洛特20 世纪50 年代到60 年代的工作中尤为明显)。
不可忽视的是,西德的民主在阿登纳及他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带领下走向了专制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这一过程事实上是由1945 年以前专制结构的残存甚至是延续(包括部分纳粹主义者的延续)所支撑的。正是这种专制国家——它通过1966 年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执政大联盟而清除或整合了反对派——而非社会或经济的条件,为科学中的批判潮流提供了动力,尤其是为20 世纪60 年代下半叶知识分子的造反提供了动力。这种造反旨在反对执政大联盟对社会所做的“塑造”(Formierung);反对执政大联盟推动下建立的紧急法案;反对工会在资本、劳工和国家三方面进行社团主义的“协调行动”整合。理论上来说,这种“新批判”立足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极权国家问题”(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以及对“民主的转型”(阿格诺力)1Johannes Agnoli, Die Transformation der Demokratie, in Agnoli, J. / Brückner, P., Die Transformation der Demokratie,Frankfurt, 1967.的具体分析之上(社会主义学生会的理论杂志被命名为“新批判”并非偶然)。
随着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组成的新政府的成立,国家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左派讨论的核心问题。为了促进充分就业和更公平的财富分配,这个政权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一个关于调整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计划。此外,在“敢于争取更多的民主”的口号下,它十分重视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基本社会政治诉求,并承诺会实现这些诉求(例如在教育、公共卫生、刑法以及对国内少数群体的保护方面)。突然间,国家通过改革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大,这一观点吸引了学生运动中的很多部分。在1969 年随后的几年中,社会民主改革政策似乎能够在进步中产阶级、工人以及过去持反对立场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广泛共识。这一政治体系似乎具有一种自主调节资本主义经济,以产生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秩序的能力。经济危机似乎终于成为过去,有效的反周期管理将“增长周期”转化为以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为特征的平稳增长。这些想法不仅存在于大众的意识中,还存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的言论以及政治阶级的自我意识中。此外,它们也体现在政治危机理论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哈贝马斯2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M, 1973.和奥菲3Claus Oあe, 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 Frankfurt/M, 1972.提出的,也因此他们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者。
我们在评估国家衍生争论的意义时必须考虑这一整体框架。
二、重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
自20 世纪60 年代末,理论界开始在“重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主题下联合起来。他们试图通过系统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创造一个理论基础。1这里指的就是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译者注这种理论在过去当然也被提出过,然而它们通常停留于对理论的重建,而未提出任何新的概念基础。正如学生运动自觉地、甚至是傲慢地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实践形式,并且轻蔑地拒绝“传统政治”,这种对理论的重建也在追寻一种新的、原初的并且具有挑衅性的理论方法,并希望以此来解决当代的政治问题。在这个计划中,国家理论可以说是恢复和应用马克思从概念上重建社会总体方法的第一个中心点。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论蓝图还在罗斯多尔斯基关于马克思《资本论》起源的讨论、泽勒尼对《资本论》科学逻辑的描述以及卡莱尔·柯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等著作中有所体现。
1970 年以后,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展开的概念上的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争论为自己设定了双重任务:制定既不同于极左派的国家观念(法西斯主义国家没有给社会留下进步空间),也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幻想(社会民主党带领下的国家驯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魔鬼)的更具基础性和政治意义的替代方案。归根结底,影响这两种观点的决定性因素都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和政治关系不正确的理解,这种理解来源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对这两个领域所做的“修正主义分离”的悠久传统。
沃尔夫冈·穆勒和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在1970 年发表的文章,以一个纲领性标题:《福利国家幻想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2Wolfgang Müller and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Sozialistische Politik, Nr. 6/7.,开启了关于国家问题的争论。这篇文章试图从理论上对所谓修正主义国家理解进行严肃批判。这两位作者评估了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立场,如魏玛共和国关于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哈贝马斯和奥菲的政治危机理论。他们发现这些理论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福利国家的幻觉,因而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没有能力避免危机的倾向,甚至没有能力通过对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有效干预,而将那些危机倾向引入系统的安全领域。相反,国家受到了双重限制:作为干预主义国家,它必须尊重资本积累的条件;而作为福利国家,它又必须通过一定措施对收入和财富进行有效再分配,从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此,它甚至需要反对个别资本的抵抗(通过阶级对抗“强加于它”的方式),然而,事实上这些措施也只会为剩余价值生产创造新的条件,以及新积累的可能性。因此,如果国家试图限制剩余价值生产(例如通过社会政策)的条件,它就立即创造出新的条件。也就是说,国家的可干预范围实质上是小于“修正主义者”们所假设的那样。由此可推知,关于资本和资本家对政治的个人影响所做的阴谋理论和调查,例如民主德国所宣传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文学或米利班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3Ralph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1969.中所例证的那样,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也是有问题的。
穆勒和诺伊西斯参考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部分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论述,以此来论述再分配制度的局限;同时将《资本论》第八章中关于10 小时工作日的论述,作为贝恩哈德·布兰克在此后提出的关于“改革的功能性矛盾”的证据。1Bernhard Blanke, Sozialdemokratie und Gesellschaftkrise, in W. Luthardt (Hrsg.),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bewegung und Weimarer Republik, Bd.II, Frankfurt, 1978.缩短工作时间只能限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然而,与此同时,为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提供技术和劳动组织基础的政治经济压力增加了。因此,福利国家的建设仍然受制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客观条件,即使在它试图对剩余价值进行改变和调整时也是如此。最终,这只会促进现代化的发展,也就更加有利于资本在各民族国家之间竞争,民族国家通过制度机制的手段来确保工人阶级的“被动整合”。葛兰西所说的“转型主义”在离开福利国家制度体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这种方法下,正如衍生争论的其他成果一样,关键在于国家活动(在超越了个人影响的层面上)的结构性限制。这些限制是由资本的再生产规律所决定的。争论中的每一种不同方法都研究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做的形式和内容的描述,以便在当下能够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起源进行推导与重构。因此,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是从“资本的一般概念的发展”中所推导出来的。在明确提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背景下,国家形式问题成为了国家衍生争论的中心。这种方法绝非新鲜物,但它被埋没在国家法学说(Staatsrechtslehre)、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里。
法学家基本上将国家理解为对国家定义的划界,即从“主权”的来源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来理解国家。在被阿尔都塞称为“法律幻象”2Louis Althusser, Marxismus und Ideologie, Berlin(West), 1973.的资本主义立宪制国家结构中,国家限制了它自身,并以此向私人领域开放了国家的一个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经济事务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处理。当“现代”“社会工业”国家3Emst Forsthoあ, Der Staat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München, 1971.逐渐发展为社会立宪国家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摩擦,因为这种社会立宪国家不仅仅会用一般法律来定义游戏规则或者是在争端中担任仲裁者角色,而且还会有目的地干预社会发展。立宪国家被定义为福利国家的对立面,这也形成了20 世纪50 年代进步的、社会导向(阿本德洛特)的立场与保守的立场(如福斯特霍夫和韦伯)对立的分界线。国家的合法化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基础。“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国家”不需要“精神上的自我描述”,因此不需要像黑格尔关于道德国家的论述中那样,将服从看作履行道德义务。
从这一观点来看,对工业社会功能模式的理性化方向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心态”4Emst Forsthoあ, Der Staat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München, 1971, p. 57, p. 57.。而这种理性化方向反过来又取决于工业社会的稳定性。“然而一切工业社会的风险也同时就是国家的风险。因此,国家对于危机的敏感性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5Emst Forsthoあ, Der Staat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München, 1971, p. 57, p. 57.此外,国家转移危机的策略以及对相应干预能力的发展,作为一种制度存在于国家自我利益之中。在这里,福斯特霍夫运用了一个在马尔库塞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著作中,例如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6Jürgen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M, 1968.一文中,都能找到的一个论点,尽管它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们重新对这种思想进行了阐述。在“资本主义晚期”,国家本身内嵌于生产关系中,并通过政治调控机制广泛地消解了市场的交换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出现了新问题,尤其是在国家权力行使方面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方面。
根据这一思路,霍克海默推断出极权国家是无法避免的,这表达了在20 世纪30 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经由赫尔曼·海勒和奥托·基希海默等人在理论上流露的担忧。然而,对奥菲和哈贝马斯来说,晚期资本主义对一切生活领域的政治化,将问题从合法性领域转移到了行政管理系统中,这个系统需要通过运用其管理资源来避免危机、保障军事安全、执行有效的外交政策、提高群众凝聚力,从而稳定经济。福斯特霍夫在这一语境中提到了“效能国家”(Leistungsstaat),即确保一切国家职责都能得到履行。另一方面,对奥菲和哈贝马斯来说,系统性矛盾只能以政治危机的形式暴露出来。从现代干预主义国家有能力从根本上调节经济危机,以及“避免危机的必要性”1Claus Oあe, Politische Herrschaft und Klassenstrukturen - Zur Analyse spätkapitalistischer Gesellschaftssysteme, in G.Kress and D. Senghaas (Hrsg.), Politikwissenschaft - Eine Einführung in ihre Probleme, Frankfurt/M, 1969, S. 115 あ.这两个论点出发,他们认为被抑制的经济危机将会转化为政治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合法性危机。然而,“国家自身的利益”会引导政治系统进行恰到好处的社会改革,以此来巩固其存在的条件。在哈贝马斯看来,决定性任务是通过调动社会的“自我适应机制”来解决经济系统中的“小”问题,以此避免可能危及社会存在的“大”危机的出现。
正如埃瑟所说,国家理论由此变成了政治危机理论。2Josef Esser, Einführung in die materialistische Staatsanalyse, Frankfurt/M, 1975.阶段理论方法(奥菲和哈贝马斯并未对其做充分论证)总是假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经历了一个转型过程:从能够通过市场交换形成合法性的竞争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国家渗透”(durchstaatlichten)3Karl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7.使得交换渠道解体,国家中的各个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一切领域都被极端政治化。合法性再也不是作为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而产生的一种稳定性资源了。它越来越需要国家以政治的方式来生产和再生产。
在德国的讨论中,这些主题在两个层面上得到解决:首先,由于马克思没有在概念上明确区分“垄断”和“一般资本主义”,有人批判垄断的“新特征”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德国的国家衍生争论以类似日本宇野学派的方式提出了问题,尽管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工作)。4c.f. Sekine, 1978; actuel Marx no. 2.毫无疑问,已经发生的社会形式转变在表象上大多都与属性的变化有关,但对其内在辩证关系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理论分析。
其次,正因如此,对国家不同概念的需求不能用向晚期或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来解释,也不能用合法性问题的政治化来解释。这种政治化毫无疑问存在,但它必须建立在批判理论和政治危机理论所提出的东西之外。国家衍生争论的参与者因此试图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般结构原则与政治化联系起来。从本质上说,这关系到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形式和在国家具体形式中表现自身的内容之间关系的定义。
然而,现在需要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只有少数教条主义者才会把国家理论极端地简化为它形式的方面。垄断这个概念并不能充分展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社会发展可以产生形式上的变化,或者说转型。然而,这种变化不仅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还会影响到社会调节的整个系统;社会发展将影响劳动、增殖过程和整个市场。因此,我们不能忽略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同样也不能认为国家采取的形式是在历史上不变的。
三、“衍生争论”中国家理论的不同方法
与其按照时间顺序来说明这次争论的贡献,不如将它系统地分开讨论。关于资产阶级国家一般形式的问题,指的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价值矛盾,或者说是对形式—内容问题的调解,产生了实例的具体分离的动力,必然表明它要超越交换网络来构成自身。1Dieter Sauer, Staat und Staatsapparat, Frankfurt/NY, 1978.这就涉及帕舒卡尼斯在1929 年提出的“经典问题”2Eugen Pasukanis, Allgemeine Rechtslehre und Marxismus, Wien/Berlin, 1929. S.119f.:“为何阶级统治没有停留在它所是的东西之上,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民在实际上屈服于另一部分人?为何它要采取一种官方的国家的统治形式,或者为何同样是这一形式,这一国家强制的机构没有变成统治阶级的私人机构,为何它同后者分离开,并采取了一种非个人的、和社会分离开的公开权力的机构的形式?”这个问题涉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国家和社会的二重性以及这种二重结构(劳动和商品的二重性)产生的原因。这种二重结构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也使经济和政治自动地相互分离,然而又自动地作为矛盾统一体中的环节,而非处于外部联系中的社会总系统的子系统。
(一)交换形式和法律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章问道:如何才能保证需要交换的商品能够全部进入市场,怎样才能使“商品拥有者”能够尽可能获得最大利润,从而在获利的同时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答案是:存在一种在交换主体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并且它与经济上的等价原则相呼应。这只能是一种法律关系,因为只有利益能够使交换主体之间结合起来,也就是商品所有者用自己的商品来交换对其有使用价值的其他商品。交换价值在契约关系中复制自身,法律诞生于经济关系中,且必须要被“设定”和监督。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必须被制裁。由于处于交换过程中的人的利益是单向的,因此法律的权力不能被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可以说,它必须被委托给一个中立的权力机构,否则就会被其他已存在的权力机构篡夺。
假设强制权力可以被转授,是早期资产阶级社会契约论者的基础,让·雅克·卢梭对此问题阐述得最为清楚。如果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出现理解为欧洲封建国家变革的结果,这一理解的过程或隐或显都能体现出篡夺的论题,格斯腾伯格1Heide Gerstenberger, Zur Theorie der historischen Konstitution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PROKLA, no. 8/9, S. 207 あ.,Berlin (West), 1973.、佩里·安德森都强调了这一观点2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LB), 1974.。因此,从这一解释来看,需被“衍生”的国家事实上早已存在。只是它的形式始终随着社会变革的进程不断发展。那么,是否应该像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将国家仅仅理解为一个制定游戏规则、监督其遵守情况的机构呢?
(二)财产和占有
布兰克、于尔根斯和卡斯腾迪克3Bernhard Blanke, Ulrich Jürgens and Hans Kastendiek, Kritik der Politischen Wissenschaft, 2 Bände, Frankfurt/Main,1975.对衍生争论最系统的贡献在于明确了在国家所制定和保障的一切法律中,产权法是最重要的。正如迈克·费森4C. B. MacPherson, Die politische Theorie des Besitzindividualismus, Frankfurt/Main, 1973.所指出的,在所有早期资产阶级理论家中,霍布斯和洛克是最早从这种基本形式理解法律的。马克思则是第一个厘清财产和占有之间关系的人。5参见早期证据,1846 年12 月28 日给安年科夫的信,载于MEGA II/2,第74 页。在做这项工作时,他为国家分析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建议:国家是为保护私有财产提供法律保障的机构。然而,如果在资本主义占有法的基础上,从财产所有者中分化出阶级,即出现了拥有供他们支配的生产资料的人,和除劳动外一无所有的人,这种作为自由财产保护机构的国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次,由于占有财产的过程具有经济性、周期性以及结构性的长期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利润下降规律”那样,而导致这种占有无法从财产中得到政治保证时,又会发生什么?
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财产权的排他性,也就是说,财产权要求排除一切没有能力获得特定财产权的人。因此,从本质上讲,财产不仅产生了拥有财产和不拥有财产的阶级分化,同时也产生了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并且当它们被中和或被从具体的财产中分离出来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政治权利关系。在这里,又与帕舒卡尼斯的“经典”问题相呼应:为什么这些权力不再是简单、粗暴和公开的阶级权力,而是成为了——用韦伯的话来说——建立在所有人(拥有财产的人和不拥有财产的人)共识上的合法关系?
(三)表象和“收入来源”
在未对复杂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详细说明的情况下,西比尔·冯·弗拉托和弗雷尔克·胡伊斯肯6Sybille von Flatow and Freerk Huisken,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PROKLA, no. 7, Berlin(West), 1973.试图在衍生争论中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论点完全基于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神秘化:资本关系从“表面”上看,由于财产、占有以及劳资、资本的对立而产生的阶级结构是模糊的,并且被社会化形式(商品交换、货币中介、工资形式等)神秘化,以拜物教的形式重新出现,由此,社会中所有不平等的人看上去变得平等了。同时,所有人作为国家的公民,都被视作在物质上平等。在这一观点上,弗拉托和胡伊斯肯只是转述了马克思关于流通和生产之间关系(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或者说是关于“资产阶级”和“公民”之间关系(1844 年《论犹太人问题》)的论述。
然而,弗拉托和胡伊斯肯走得更远,他们通过社会个体作为收入来源的所有者在质上的平等,来说明他们作为公民的平等(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部分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论述)。所有“收入来源所有者”的利益都来源于他们的资源能够持续地、尽可能多地投入生产。这种统一的利益超越了阶级的边界,与收入来源(财富)和收入(收入)1此处两个“收入”,前者原文是“revenue”,后者是“income”。——译者注量上的范围以及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功能(在工资、利润、利息的职能分配中)无关。正是这种统一的利益能够使得对立阶级的成员成为公民,并进一步构成国民。
与下文要讨论的国家的话语或民粹主义理论相比,这种方法预设了生产方式(由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对立所构成)和社会形态(作为市民活动的场所)之间存在着的系统联系。这种“深层结构”和“表象”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马克思的神秘化范畴实现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范畴来理解那种特定的颠倒,即拜物教。这不仅构成了卢卡奇意义上的“虚幻意识”,而且还预先塑造了日常生活经验,限定了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行动框架。它们是“虚假的现实”,即异化的背景。因此,公民作为收入来源的所有者在质上的平等不仅仅是一种也许可以通过启蒙来澄清的“虚假表象”,而且是一种经验生活的现实展开,它能够促进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并不是单纯的幻觉,而是有物质基础的。
因此,资产阶级国家得以存在的可能性(而不仅是它的必然性),是这种利益的表面平等的产物。因此,国家不能从社会的核心或“本质”的利益矛盾中“衍生”出来。弗拉托与胡伊斯肯的这一立场,无论逻辑上多自洽,还是受到了多方的攻击和批判。格斯腾伯格2Heide Gerstenberger, Zur Theorie der historischen Konstitution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PROKLA, no. 8/9, S. 207 あ.,Berlin (West), 1973.和莱希尔特3Helmut Reichelt, Einige Anmerkungen zu S. von Flatows und F. Huiskens Aufsatz'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Gesellschaft, no. 1, 1974.准确地指出这个计划没有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影响。“表象和国家”4Arbeitskonferenz (AK) and Rote Zellen München 1974, Resultate der Arbeitskonferenz, Nr. 1, 1974.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顶点,生产的基础联系对二者的结构化及其矛盾的发展被明确排除在分析之外。此外,收入来源所有者的收入受到资本流动的不平等影响,这又反过来产生了新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必然会被弗拉托和胡伊斯肯“表象和国家”的片面考虑所忽略。最后,正如其他批评家所指出的,他们的方法建立在一种社会和谐的理论之上,因此也可以为多元主义理论提供一定基础。
(四)阶级关系和资本再生产
我们再次回到上面提出过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有形式(源于财产权)将会对政治关系及其制度形式带来怎样的影响?第一个关键点在于,拥有生产资料的人的占有,决定了对那些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他们仅仅能够将劳动能力作为商品)的剥削。这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形式的剥削引起了两方面利益的冲突,例如关于工作日长度的讨论,这是穆勒和诺伊西斯在上述文章中提到过的一个例子,并已对其进行了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看法同弗拉托和胡伊斯肯的看法一样,并不认为国家是集体利益的代言人,而是一个调节利益冲突的机构。贝恩哈德·布兰克1Bernhard Blanke, Sozialdemokratie und Gesellschaftkrise, in W. Luthardt (Hrsg.),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bewegung und Weimarer Republik, Bd.II, Frankfurt, 1978.扩展了这一看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穆勒和诺伊西斯,认为国家不应该继续被当作按照社会规则的需求来运行的黑匣子。相反,考虑到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的经验,就要考察“群众进入国家”。
这里有一个和法国讨论的连接点:国家及其多样的机构被看作“阶级冲突的领域”2Nicos Poulantzas, Staatstheorie, Hamburg, 1978.。因为如果“这种”国家在社会斗争的驱使下,作为依赖工资生存的那部分人的代表采取干预措施(例如通过限制工作日,或者像福利国家那样补偿工厂制度对民众奴役产生的负面后果),那么工人阶级通过一定组织来“监管”这种改革是如何被执行的,就说得通了。由于福利国家的不断发展所采取的一些制度形式(部分国有的机构,例如社会保障、劳动交换、公共基础设施安排等),很明显,工人阶级组织“进入了”这些安排,并在制度允许范围内自己成为实施改革的主体。这样一来,阶级冲突就通过福利国家的一些措施,以及阶级和群众组织的相应参与权等被“制度化”了。国家形式随着社会冲突的内容及其动态而变化。此外,以这些变化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剥削都会随之变化。马克思分析认为,缩短工作日事实上是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转变的历史性契机;也就是说,对占有的经济机制的政治反应引发了经济和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的重组。而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布兰克所强调的“改革主义的功能性矛盾”3Bernhard Blanke, Sozialdemokratie und Gesellschaftkrise, in W. Luthardt (Hrsg.),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bewegung und Weimarer Republik, Bd.II, Frankfurt, 1978.。这种观点(与弗拉托和胡伊斯肯的观点相反)考虑到了社会结构的冲突,并对历史分析持一种开放态度。
(五)国家和“生产的一般条件”
考虑到资本增殖的一般功能性要求,国家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形成也可以用“一般的生产条件”来解释,它不能由单个资本产生,用恩格斯在《反帝论》中的说法,就是它需要一个“理想的总资本家”(ideellen Gesamtkapitalisten)4Friedrich Engels, Herm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MEW, no. 10.。阶级分析计划5Projekt Klassenanalyse, materialien zur Klassenstruktur der BRD, 1. Teil: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und Kriterien,Berlin (West), 1973.以一种当时典型的论战风格运用了这种方法。然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生产条件(例如在基础设施或整体的法律框架中)是一般性的,它们无法被个人或单个资本,而只能被一个由于一般性任务而被分离出来的机构即国家所认识。在这里,国家不再通过形式分析来推导,而是作为一种解决方法被反复定义。
然而,迪特·兰勃6Dieter Läpple, Staat und allgemeine Produktionsbedingungen, Berlin (West), 1973.的看法更具野心,他同样使用了“一般生产条件”来说明国家作为独立机构与社会并行,同时又在社会之外。他参考《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7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1953 (MEGAII, 1.1 und 1.2), S.430.以及《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这些条件的少数评论,试图明确“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具体的“资本主义的一般生产条件”之间的差别,同时将历史经验调查与推导粗略地联系起来。弗拉托和胡伊斯肯试图解释国家存在的可能性,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化能力上的缺陷,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成为国家存在的必然性。国家存在的必要功能是维持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也就是维持资本增殖的系统。这个系统在回应发展过程中的机械性差距时也会发生变化。然而,在这里,为了更好地进行功能性分析,必须先把形式分析放到一旁。
(六)积累和利润率的下降
在衍生争论的这一点上,下一步是具体地解释资本增殖的历史趋势问题,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重要的规律”,即平均利润率的下降问题。这一规律对讨论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如果资本增殖因利润率下降而不再可能,那么即使财产权和占有能够得到政治上的保障,也不再具有经济意义。政治也不再主要保障经济秩序的基础,而是转向了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从“政治秩序”到“政治过程”的转向,即“人的自由主义下落”,被深深地内嵌在积累机制的矛盾性中。这里显示出了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在国家对其存在的形式保障和积累过程中利润下降的经济趋势之间的固有矛盾。有两件事需要注意:一方面,在积累的过程中,国家保障和政治监管能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另一方面,政治系统需要发展其适应性机制,以便能够通过政治的反复干预帮助资本实现其增殖。由于内含于资本积累动态中的原因,国家成为再生产过程中的积极经济因素。
阿尔特法特1Elmar Altvater, 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Staatsinterventionismus, PROKLA , no. 3, Berlin (West), 1972.提出了一个基于“积累理论”的国家衍生理论。他从资本再生产结构的缺陷出发来阐述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由于物质生产需要(换句话说就是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方面),国家必须接管或组织所有不可或缺的生产过程(以国有企业或公共服务的形式),而这些生产过程又由于无利可图,或者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而变得无利可图,因此无法在资本增殖的个别条件下进行。
在这里,与阶级分析那种同义反复的论证不同,“生产的一般条件”概念需要历史维度的支撑:它涉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上来说是必要的,但从私人生产角度来看又是无利可图的方面。只要国家能够对这些必要但无利可图的部门进行有效管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私人资本利润率的下降,甚至可以在危机中通过“将损失社会化”的政策对其进行补偿。
阿尔特法特、霍夫曼、许勒和塞姆勒2Elmar Altvater, Jürgen Hoあmann, Wolfgang Schöller and Willi Semmler, Entwicklungsphasen und - tendenzen des Kapitalismus in Westdeutschland, Teil 1, PROKLA, no. 13, 1974; Teil2, PROKLA, Berlin (West), 1974; Elmar Altvater, Jürgen Hoあmann and Willi Semmler, Produktion und Nachfrage im Konjunktur, und Krisenzyklus, WSI-Mitteilungen, Heft 7, Juli 1978.在对西德资本积累趋势的历史分析中进一步发展了“积累理论方法”。其中的基础性假设已经在布兰克3Bernhard Blanke, Formen und Formwandel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Volkhard Brandes u.a. (Hrsg.), Handbuch 5, Staat, Frankfurt/Main, 1977.和霍夫曼4Jürgen Hoあmann, Stattliche Wirtschaftspolitik als Anpassungsbewegung der Politik an die kapitalistische Ökonomie, in Brandes, Hoあmann, Jürgens and Semmnler (Hrsg.), Handbuch, Staat, Frankfurt/M, Köln, 1977.的“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性调整”概念中得到了清晰表达。在经济及其矛盾发展倾向中,政治可能是相对独立存在的。然而,经济体系的矛盾和危机往往会被转移到政治领域,并使政治政策来适应其发展,也就是政治“适应运动”,即制度转型。
政治危机理论假设经济危机趋势成功转移到政治体系中,标志着通过国家干预来避免危机的策略取得了成功,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随着凯恩斯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结束”,危机将作为潜在的、无法避免的合法化危机发生。然而,在“积累方法理论”中,凯恩斯主义关于如何避免危机的方法更值得质疑和讨论(关于繁荣时期的证据,参见阿尔特法特1Elmar Altvater, Zur Konjunkturlage der BRD Anfang l970, Versuch einer Methodik für Konjunkturanalysen,Sozialistische Politik, no. 5, März 1970.、霍夫曼和塞姆勒2Jürgen Hoあmann and Willi Semmler, Kapitalakkumulation, Staatseingriあe und Kohnbewegung, PROKLA, no. 2, Berlin(West), 1972.的论述)。正如布兰克、于尔根斯和卡斯腾迪克3Bemhard Blanke, Ulrich Jürgens and Hans Kastendiek, Zur marxistischen Diskussion über Form und Funktion des Staates, PROKLA, no. 14/15, Berlin (West), 1974.所解释的那样,国家的行动潜力似乎不仅受到系统性的规定(作为财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保证),同样受既定社会中先于国家而存在的“活动限制”的制约,这种限制是以历史上特定的阶级和权力结构为标志。这些都不能独立于经济的发展来定义。
当然,还需要考虑到,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单纯经济的”危机是“次要的”危机,也就是不会给霸权制度带来任何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危机。只有政治危机(贝尔格在这里谈到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干扰因素”4Johannes Berger, Wandlungen von Krisenursachen im wohlfahrtsstaatlichen Kapitalismus, Alternative Wirtschaftspolitik 3, AS 68, Berlin (West), 1981.)才会危及整个体系的存在,因为共识的基础和公民的忠诚将被破坏。但是,这个不证自明的说法并没有揭示出随着利润率的下降,经济矛盾会逐渐凝结为结构性矛盾这一变化。因此,以“积累理论”为导向的学者们继续对利润率发展趋势展开分析,他们将其解释为考察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一个“综合指标”。这些调查是为了能够提高评估社会危机的结构和动态,及其对政治制度的必要调整的结果时,历史维度上的精确性。
(七)国家的形式与功能
在这一方法中,一些特定的任务或功能被分配给了社会增殖语境(Verwertungszusammenhangs)中的国家(或者说更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因此,在形式分析完全成型之前,就已经向功能分析迈出了一步,可能是不成熟的。许多学者因此批评了阿尔特法特。
国家一般有四个基本职能:第一,建立一般的生产条件(即基础设施);第二,为社会成员与国家自身的干预机制建立一般的法律规范;第三,通过法律和“镇压性国家机器”性质的机构来调节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第四,保障全部国家资本对外进入世界市场竞争,包括外交和军事政策。5Elmar Altvater, 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Staatsinterventionismus, PROKLA, no. 3, Berlin (West), 1972, S. 9あ.
针对功能性批判分析,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形式和功能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如果同沃尔夫冈·穆勒一样将形式理解为“前一个过程产生的矛盾的结果和伪装”,那么就可以认为功能从更精确的程度上来说是由形式决定的。这可以与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对比起来看,货币形式是从商品中衍生出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并通过赋予其职能来更精确地定义其形式(第三章)。国家职能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来划分,这些机构在历史的发展中生成了国家机器。它们以与再生产体系中承担的功能相适应的方式进行干预,尤其是法律与货币的方式。1Bemhard Blanke, Ulrich Jürgens and Hans Kastendiek, Zur marxistischen Diskussion über Form und Funktion des Staates, PROKLA, no. 14/15, Berlin (West), 1974.只有当国家对社会特有的功能、机构和媒介被清楚地确定后,形式才会被定义。只有这样,才能明确为什么特定的内容会采取相应的形式,反过来说,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和运动——会适应其内容的需要。这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变成社会和国家的“双重结构”的唯一解释,这种结构已经被多次讨论,它显在或潜在地构成了所有国家衍生形式的根源。
(八)作为阶级关系领域的国家
约阿希姆·希尔施在他的一些文章中指出,在最初的标准推导框架中(经济与交换、法律与政治、作为担保人的国家)产生了利润率下降的历史趋势和资本主义由此产生危机的问题。和阿尔特法特相反,希尔施和法兰克福的一个研究小组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利润率下降趋势。通过这一讨论,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经常出现的经济主义保持了距离。
利润率下降会对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对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资本关系这一基本概念,希尔施赋予了国家三个基本职能:第一,保证资本关系和生产的一般条件;第二,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以及对流通的控制;第三,还有他曾经考虑过的观点之一2Joachim Hirsch,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 politisches System, Frankfurt/M, 1970.,即发展生产力3Joachim Hirsch, Elemente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Staatstheone, Braunmühl, 1973, S. 235, S. 244.。国家职能不断增加的历史趋势源于政治—管理职能执行过程中受到的干扰,这种干扰不可避免地与由利润率下降而引发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因此,政治—管理系统会根据经济职能的不同需求而有所区别。
到此为止,系统论者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都同意希尔施的观点,除了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论点。然而他以另一种方式丰富了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其之后的分析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利润率下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以国家只能在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期间,在最基础的层面4Joachim Hirsch, Elemente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Staatstheone, Braunmühl, 1973, S. 235, S. 244.上通过重组再生产的社会条件来遏制这种趋势。最初,希尔施只是笼统地定义了重组的过程,提到了垄断的趋势、资本在世界市场的扩张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后来,他对这一点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讨论,提出国家理论只能作为“转移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发展。5Klassenbewegung und Staat inder BRD,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no. 8/9, Frankfurt 1976, S. 128.在明确地提到葛兰西、阿尔都塞,尤其是普兰察斯时,希尔施也将国家定义为“阶级关系的领域”6Joachim Hirsch, Bemerkungen zum theoretischen Ansatz einer Analyse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no. 8/9, 1976, S. 108, S. 155, S. 155.。鉴于“阶级关系的特殊性质”7Joachim Hirsch, Bemerkungen zum theoretischen Ansatz einer Analyse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no. 8/9, 1976, S. 108, S. 155, S. 155.,希尔施和阿尔都塞一样,区分了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性国家机器,但随后又增加了“整合大众的”国家机器的类别。在葛兰西那里,与镇压机器相对应的政治社会,和与意识形态机器相对应的公民社会都被理解为无法再简化的组织关系,因为它们也包括了非物质性的机构,而在希尔施和阿尔都塞那里,“机构”的概念特指“资产阶级统治机器的体制结构”8Joachim Hirsch, Bemerkungen zum theoretischen Ansatz einer Analyse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no. 8/9, 1976, S. 108, S. 155, S. 155.。
(九)小 结
尽管被零星地引用,但“衍生方法”既没有在意大利(以及一般的罗马国家)与越来越重要的葛兰西传统联系起来,也基本没有在阿尔都塞和普兰察斯的作品中被提及,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作品在盎格鲁—撒克逊圈子中被广泛阅读。矛盾的是,尽管这项工作在其他国家和理论传统中仅仅停留在有所耳闻的程度,尽管论域非常狭窄,西德国家衍生争论仍被认为是富有创造性的。霍洛韦和皮乔托1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Hrsg.), State and Capitalism. A Marxist Debate, London, 1978, S. 14, S. 10.在介绍争论的开创性文本的英文版本中提到了这一点。鉴于英国国家理论存在着某些“不足”,他们希望“强调(他们认为的)德国关于国家分析讨论方面取得的进展”。2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Hrsg.), State and Capitalism. A Marxist Debate, London, 1978, S. 14, S. 10.对他们来说,衍生争论对国家形式问题的基本贡献在于,在对权力结构进行实证调查(米利班德)之前,或进行关于经济或政治谁处于首要地位这一无效辩论之前,将国家的形式问题主题化。因为“两种倾向(政治主义和经济主义)……之间的区别,不是取决于分析的出发点,而是取决于作为分析基础的社会整体概念”。3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Hrsg.), State and Capitalism. A Marxist Debate, London, 1978, S. 14, S. 10.
在所有分歧和争论之外,在衍生争论中有一个问题始终是一致的:问题不在于政治或经济、国家或社会谁处于首要地位,而在于如何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思想中把握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分离。在这一层面上,拉克劳4Ernesto Laclau, Teorias Marxistas del Estado: Debates y Perspectivas, in Norbert Lechner(ed.), Estado y Politica en America Latina, Mexico, Madrid, Bogota, 1981, S. 25-29.认为“资本逻辑学派”关于国家的问题局限于一种以“资本”为推导起点的“经济参考框架”中,而这一观点,只有在以去除经济的方式也能理解资本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自然很难做到。在衍生争论中,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一个“自动的经济主体”是所有讨论的共识。但这一理论构造的具体内容却是一个敏感的主题,易激起不同方法和观点的争论。
四、国家衍生争论之外
希尔施一直在试图解决他在方法论中提出的问题,而许多其他参与讨论的人则早早远离了这一问题,并不希望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贡献上。关于在危机中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导致的重建或改造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为后来从阶段理论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调节体系打下了基础。这些讨论采用了阿格里塔5Michel Aglietta, A Thoe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g, 1979.和葛兰西关于“福特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德国模式”6Joachim Hirsch and Roland Roth, Modell Deutschland'und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PROKLA, no. 40, 10. Jg., Berlin(West), 1980, S. 14 あ.,以更好地理解西德国家的重组能力。希尔施也可以在另一个方面建立他的方法:在把工会、协会和政党描述为确保资产阶级霸权系统的组成部分的“大众整合机构”时,他阐明了一种社会进程,这种社会进程在20 世纪70 年代末的批判性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地描述为“社团主义(corporatism)”,尽管他详细提及“社团主义”这一概念体系的其他部分。这并不奇怪,因为社团主义概念是描述性的,即使用最精炼的方法也不能以分析的方式使用这一概念,而希尔施的概念体系虽然只能系统地描述社会权力结构,仍完全属于国家衍生争论的传统,这一争论试图超越历史经验考察,对形式进行范畴定义。正如格斯腾伯格在总结国家衍生争论时所说:如果不从根本上反思需要应用的理论范畴,就不可能从历史描述进展到历史分析。
然而,希尔施从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概念的重建,转向对决定利润率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倾向分析,有可能构成连接概念分析和历史调查的桥梁。还需要考察的是:这座桥梁是否不会回到这场国家讨论的起点,即回到抛开所有复杂的和矛盾的描述,而仅仅按照机构或精英理论的路线来构建极权国家。1Joachim Hirsch, Nach der 'Staatsableitung' Bemerkungen zur Reformulierung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Staatstheorie, in Argumen, Sonderband, AS 100: Aktualisierung Marx, Berlin (West), 1983.
布兰克、于尔根斯、卡斯腾迪克2Bernhard Blanke, Ulrich Jürgens and Hans Kastendiek, Kritik der Politischen Wissenschaft, 2 Bände, Frankfurt/Main, 1975.和霍夫曼3Jürgen Hoあmann, Stattliche Wirtschaftspolitik alsAnpassungsbewegung der Politik an die kapitalistische Ökonomie,in Brandes, Hoあmann, Jürgens and Semmnler (Hrsg.), Handbuch, Staat, Frankfurt/ M, Köln, 1977.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他们试图通过将范畴具体化来分析发达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在无需回到机构理论的情况下,他们认为政治制度是发达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的中介。
回过头来看,西德关于国家形式和功能,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讨论——国家衍生讨论——不仅被详细地描述了,而且被否定了。反对者解释“衍生”概念时,好像这次讨论的参与者只关心从资本概念中推导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复杂现实。衍生争论的许多成果确实支持了这一唯心主义的含蓄指责,即试图在概念中重建物质世界。然而,这种批评忽略了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和功能进行分析的目的。这场争论试图从概念上重建一些混乱的社会关系,包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有机的、系统的社会结构出现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也许能够通过追溯这些关系最简单的社会化形式,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系统表述的那样来实现。在这一层面上,这一争论也是经验的。
当然,在这里仍然没有行动的理论。在国家讨论中提出的社会民主改革政策的局限,在1973 年后的发展危机中成为历史现实(滞胀危机)。因此,政治改革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选择:要么在政策上退回到政治的系统限制(私有财产),要么“调整”到更大限制。4Jürgen Hoあmann, Stattliche Wirtschaftspolitik alsAnpassungsbewegung der Politik an die kapitalistische Ökonomie,in Brandes, Hoあmann, Jürgens and Semmnler (Hrsg.), Handbuch, Staat, Frankfurt/ M, Köln, 1977.随着改革的失败,关于国家的讨论也失去了作为其讨论的特权政治“对象”,走入了死胡同。在少数人的反对下,旨在克服制度限制的想法没有机会在政治上实现。他们注定要遭受的政治失败更加痛苦,因为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失败。当经济繁荣结束于20 世纪70 年代初的危机时,改革的氛围也随之消失了,由于社会民主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计划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空洞的。与改革相反,一个政治高压时期(从业禁令以及“西德之秋”)和限制经济和福利国家政策(紧缩型政治)的时期开始了。在20 世纪70 年代,联邦共和国被定义为“专制民主”5Elmar Altvater, Jürgen Hoあmann and Willi Semmler, Produktion und Nachfrage im Konjunktur, und Krisenzyklus,WSI-Mitteilungen, Heft 7, Juli 1978.和两种意义上的“安全国家”1Joachim Hirsch, Der Sicherheitsstaat. Das 'ModellDeutschland', seine Krise und die neuen sozialen Bewegungen,Frankfurt/M, 1980.:一方面,它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安全;另一方面,它也增强了警察的安全。在20 世纪80 年代,联邦共和国采取了一种政治“转向”,从社会—自由主义联盟转向保守—自由主义霸权,这种转向在许多方面都与70 年代相悖。不过,这一发展也是形成新社会运动的开端。随着社会中经济和政治分裂的加剧以及生态危机,它们的出现可以作为传统政治形式的替代品。
在这里,衍生争论中的不足不仅出现在了政治上,同样也明显地出现在了理论上。由于争论的抽象程度较高,因此要对社会运动进行分析,才能够构想一种能够克服这些限制的制度。然而,这一要求是十分抽象的。此外,正是这些“新社会运动”从根本上对主流社会形势提出了质疑。工人阶级组织无法提出这种批判,因为他们已经被收编并停留于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中,因此他们被迫与现有制度和规则妥协。这是国家衍生争论的一个重要结论。然而,“资本逻辑”的范式不允许有超越阶级界限的新激进运动出现,也不允许这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并在对国家的讨论中提出新问题(例如对使用威胁生命的技术和反对权的多数决定问题)。
在替代运动中提出的问题常常与国家讨论的“旧”问题范式有密切联系。新提出的问题包括:关于福利国家的功能问题,2Christel Neusüß, Der 'freie Bürger 'gegen den Sozialstaat, PROKLA, no. 39, Berlin(West), 1980, S.79 あ.关于超越社会民主国家主义的另一种经济政策的讨论,关于重组生产以实现经济民主化并建立能够满足需求的系统的机会问题,以及抵制国家借助新通信和信息技术所可能实现的对公民进行全面控制的趋势,等等。所有这些由快速发展的替代问题提出的问题都回到了老问题上。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了一些与“左派”经典的空洞口号(例如要求实现国有化)不同新的答案。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替代运动的存在是对马克思主义讨论的战略缺陷所做的一种明确的实践批判:在“经典”(国家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答案之外,缺乏社会变革的概念。这些缺陷在20 世纪70 年代末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仅出现在联邦共和国(我想到阿尔都塞1976 年在威尼斯的“宣言”)。很明显,无论如何,仅仅在形式上确定战略规划是不够的。
国家衍生争论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结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冗长而枯燥的论战。真正的原因涉及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形式分析的明确限制。然而,勇于对国家进行形式分析并寻求其坐标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吗?答案很明显:当然不是,因为即使形式分析遮盖了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许多方面,但为了回答一个始终具有时代性的问题,这仍然是必要的。国家干预社会的系统性限制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必定只能在未来被发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衍生争论中的许多思考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3论文最后有原作者写的一句跋:“在我们写这篇文章时,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于1988 年4 月2 日因病去世。这使西德的左派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和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家。近年来,她专注于女权主义理论,并通过该理论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批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