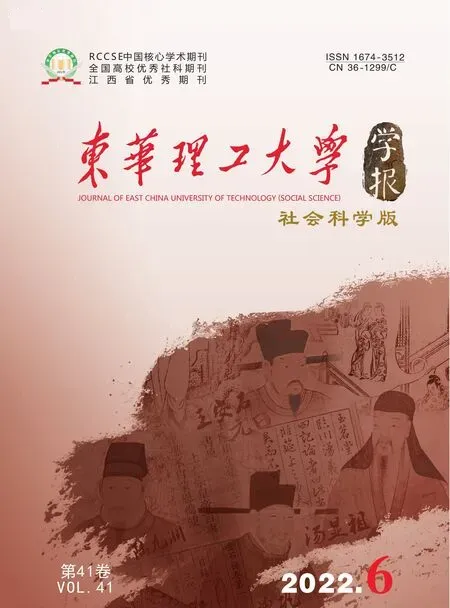《列朝诗集小传》的事件书写与诗史建构
——以汤显祖批评王世贞事件为例
彭 涛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分类,古代文学史可从史料、史观、史纂三个板块进行分析。《列朝诗集小传》(以下简称《小传》)作为明清之际一部重要的著作,学界对此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史观部分(1)仅专著便有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丁功谊《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杨连民《钱谦益诗学研究》等。,史料(2)对于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的史料运用,已有学者针对某个特定的个案进行了研究,最著者如“弇州晚年定论”说,李光摩、魏宏远等均对此有详细的考述。还有一些学者对此有较为全面的讨论,如叶晔《材料的声音: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选材策略》一文认为钱谦益通过材料的取舍、编排、曲解表达诗史观念;徐隆垚的博士论文《明人诗史书写研究》提出《列朝诗集小传》有控制型及对话型两种史料学模式。整体而言,学界对《小传》的史料学考察仍不充足。及史纂(3)学界对史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列朝诗集》,如陈广宏《〈列朝诗集〉闰集“香奁”撰集考》、刘佳《〈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的编次与寓意》,徐隆垚《〈列朝诗集〉闰集“神鬼”撰集考》等,鲜少对《小传》史纂形式的考察。受到的关注则有些不足。《小传》中的史料并非完全客观,有相当一部分史料经过有意处理,在隐性的层面上传达其诗史意图,成为钱谦益诗史建构的重要手段。《小传》使用的史料主要集中在履历、事件、转引他人评语三个部分,本文主要讨论的便是其中的事件部分。本文拟以汤显祖对王世贞的批评事件为例,考察史源的原始面貌、钱谦益对史源的改写方式以及诗史意图、《小传》事件书写的影响,并探讨《小传》中事件书写为清人所接受的影响因素。
1 汤显祖批评王世贞事件的原始面貌
汤显祖《答王澹生》一文对此事件有完整的说明:
因于敝乡帅膳郞舍论李献吉,于历城赵仪郎舍论李于鳞,于金坛邓孺孝馆中论元美,各标其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见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雄,妙者称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论文心之一二。而已有传于司宼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随之。汤生标涂吾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弟闻之,怃然曰:“王公达人,吾愧之矣。”[1]1303
这段话涉及几方面信息。其一,批评主体,汤显祖是主要批评者,参与批评活动的分别有帅机、赵世卿(4)徐朔方先生考证了帅、邓的对应人物,未言及赵仪郎。日本学者野村鲇子提出为赵邦清(《〈列朝诗集小传〉研究》,汲古书院2019年版,第583页),但赵邦清为陕西真宁人,且仕宦经历无仪郎,有误。叶长海提出为赵世卿,但仅言其为历城人,没有列出更多证据(见《答王澹生》注5,《汤学刍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2页)。据明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一百四十七《光禄寺少卿年表》言,“赵世卿,山东历城人,隆庆辛未进士,万历十三年六月由礼部仪制郎中任,十五年三月升四夷馆少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80页)。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四十二《仪制司郎中》亦言“赵世卿,象贤,山东历城人,隆庆辛未进士,万历十二年繇祠祭,调任升光禄少卿,任户部尚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75页)。因此,赵世卿万历十二年为礼部仪制司郎中,十三年六月即调任为光禄寺少卿。与龚延明《简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辞典》中言,“仪郎,(明)礼部仪制清吏司郎官省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3页)相合。、邓伯羔等三人;其二,批评客体,被批评者分别为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涵盖了七子派的主要领导者;其三,批评时间,第一次批评活动当发生于万历四年或八年(5)据《汤显祖年谱》,帅约万历四年前后为南礼部精膳司郎中,万历九年即升任贵州思南太守(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49页),另汤显祖《赴帅生梦作》“子为膳部郎,予入南成均。今上岁丙子,再见集庚辰”,徐先生笺,汤于万历四年及八年两晤帅机,汤、帅的批评活动当发生于这两次见面。,第二次当发生于万历十二至十三年间(6)赵世卿于万历十二年至十三年六月任礼部仪制司郎中,之后便调任。,第三次当在万历十二或十三至十八年之间(7)汤文虽言“司寇公”,而王世贞于万历十七年六月升南京刑部尚书(司寇公),十八年三月乞休,同年卒,然此文创作时世贞已去世,司寇公可能是对王世贞的尊称,不一定当时世贞已任刑部尚书。邓伯羔为金坛人,生平经历不详,无别集存世,难以确定形迹。汤显祖十二年至十八年均在南京为官,材料不足以确定二人何时见面,进行批评活动,但一定在王世贞去世之前,应在赵世卿之后。;其四,批评观点,汤显祖得出“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雄,妙者称能而已”的结论。这里汤显祖使用了移自传统书画评的“能品”概念(8)叶长海提出此句中之“能”指艺术评论中的“能品”概念,见《答王澹生》注7,载《汤学刍议》,第3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对“能品”的描述是“长于临仿”“状貌似而筋骨不备”[2]69,次于“神”“妙”两品。元人夏文彦说得更加清楚:“故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谓之神品;笔墨超绝,传染得宜,意趣有余者谓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规矩者谓之能品。”(9)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4册,第542页。夏氏此说在明代被广泛接受,曹昭《新增格古要论》、唐顺之《荆川稗编》、王世贞《艺苑卮言》《弇州四部稿》等皆有引用。“能品”的特征在于“形似而不失规矩”,与“神”“妙”两品的区别在于“气韵”“意趣”之有无。
可以看到,针对七子派,汤显祖先后进行了三次批评活动,此数次活动的核心都在于讨论“神情声色”与“形似”“规矩”两种学古方式的优劣,对七子派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其“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这种外在的模拟上(10)关于汤显祖与七子派诗学方面的差异,学界已有很多讨论,不需赘言。也有一些学者从汤显祖戏剧中集唐诗的使用方面对此有新的说明,如袁茹《论汤显祖戏曲文体选择之后的诗学宗尚》,《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309-312页。。除此之外,数次活动的发生时间、地点及批评的主客体均不同。
后世文人对此事件批评过程的书写,有两种流向与汤氏自述存在较大出入,一为张岱《石匮书》,二为钱谦益《初学集》,均可断定为杜撰。张岱于《王世贞等列传》后论曰:“当时四部稿初出,临川汤若士涂抹之曰:‘莫学王弇州以枵腹欺人。’”[3]2944-2945从时间来看,张氏言“四部稿初出”,然《四部稿》有万历五年世经堂刻本(11)据许建平《〈弇州山人四部稿〉的最早版本及编纂过程》所言,四部稿最早为万历四年初刻本,但印量甚少,万历五年所刻则成为通行的一百八十卷善本。见《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第185页。,《续稿》则迟至“万历二十七年前后才由王世贞长子王士骐刊印”[4],前后《四部稿》“初出”的时间均与汤显祖自述中的时间不合。从批评语言来看,参与此次批评活动的邓伯羔无相关文献留存,且张岱于崇祯元年写书评此事,距批评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年左右,事实上很难知晓批评现场的详细情况。
《初学集·汤义仍先生文集序》的记载为:“义仍官留都,王弇州艳其名,先往造门。义仍不与相见,尽出其所评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翻阅,掩卷而去。”[5]905清人多有沿袭此说者,如施闰章《矩斋杂记》:“弇州艳义仍之名,先往造门。义仍不与相见,有所评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翻阅,掩卷而去,无他言。”[6]79王嗣槐《与方渭仁书》:“牧斋称汤义仍官留都时,弇州闻其名而造之。义仍不与相见,出其批抺弇州集,散置几案间,弇州信手翻阅,嘿然掩卷而去。”[7]200李茹旻《玉茗堂》“后先七子逊琳琅”句下注曰:“又简检献吉、于鳞、元美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散置几案间,使元美知之。”[8]614蔡显《闲渔闲闲录》:“临川汤义仍官留都,弇州艳其名,先往造门,义仍不与相见,尽出其所评抺弇州集散置几案,元美信手翻阅,掩卷而去。”[9]有学者提出,钱氏应是将汤显祖《答王澹生》中批评事件与《复费文孙》中与二美同仕南都时“不与往还”的自述组合,形成了新的故事[10]128。清代也有文人注意到了此事的杜撰成分,王弘撰《砥斋集·书钱牧斋汤临川文集序后》言:
弇州艳义仍之名,先往造门,有古人之风焉。义仍不与相见,过矣。云尽出其所评抺弇州集,散置几案,预出之以度弇州之至耶?抑延弇州至堂而后出之耶?其述事似饰而未确。弇州信手翻阅,掩卷而去,卒不闻有他言以复[11]408-409。
无论是预知王世贞到来而先将评抹之作置于案上,还是请王世贞至堂而后示以文赋,都有不合情理之处。王弘撰势必没有读过汤显祖原文,但从叙事逻辑上也认为钱氏说法存在编造的部分。
2 《列朝诗集小传》的事件书写与诗史建构
钱谦益对此事件的文本处理体现在《初学集·汤义仍先生文集序》及《列朝诗集小传·汤遂昌显祖》两文中。《初学集》提供了《小传》事件书写的早期面貌,且两文在处理方式上具有延续性,与《初学集》的互文也成为《小传》的一种论证手法,因此下面将对《初学集》及《小传》两种文献的处理方法进行考察。
《初学集》对此事的记载为:
义仍告许生曰:“吾少学为文,已知訾謷王李……始读乡先正之书,有志于曾王之学,而吾年已往,学之而未就也。子归以吾文视受之,不蕲其知吾之所就,而蕲其知吾所未就也……
义仍官留都,王弇州艳其名,先往造门。义仍不与相见,尽出其所评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翻阅,掩卷而去……
古之人往矣,其学殖之所酝酿,精气之所结轖……今之人耳佣目僦,降而剽贼,如弇州四部之书,充栋宇而汗牛马,即而视之,枵然无所有也,则谓之无物而已矣[5]905-906。
《初学集》的论述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首先引用汤显祖对钱谦益的寄语,点出汤氏对七子派的基本态度以及有志于曾王之学的文学观点,为后文论述张本;第二层通过对事件的书写,形成例证;第三层为钱氏本人的评论,从辨体学角度剖析曾王之学与王李俗学之间的区别,为此事件定性。第一、三层是语境设置,第二层是史料改写,钱谦益综合使用了两种手法,以明其尊曾王之学、抑王李俗学的文学观念。

相较《初学集》,《小传》对事件的文本处理更加隐蔽、巧妙,但在叙述结构、用意、史源等方面具有连贯性。事实上,《小传》的事件书写在早期的《初学集》基础上形成,钱氏对此又进行了一些深化。《小传》的记载为:
尝谓我朝文字以宋学士为宗,李梦阳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
万历间琅琊二美同仕南都,为敬美太常官属。敬美唱为公宴诗,不应。又简括献吉、于鳞、元美文赋,标其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流传白下,使元美知之。元美曰:“汤生标涂吾文,异时亦当有标涂汤生者。”
自王李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雺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驳,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尝自叙其诗三变而力穷,又尝以其文寓余,以谓不蕲其知吾之所已就,而蕲其知吾之所未就也[12]563-564。
《小传》的叙述结构同样分为三层:第一层引用汤氏《答张梦泽》一文,铺垫汤氏对七子派的基本态度及推崇宋濂的文学观念;第二层是对事件的书写,以为例证。《初学集》将《复费文孙》中“不与往还”与《答王澹生》中标涂事件合而为一,《小传》则将两事前后连缀,分别书写;第三层是钱氏本人的评论,从辨体角度分析汤氏的文学取径,并且确立了其文学史定位。
《小传》的史料处理手法及用意,相较早期的《初学集》更为隐蔽、深入。材料取舍上,《小传》基本遵循原貌,仅有一些细微的删改,如新增“流传白下,使元美知之”一句,原本为“有传于”,是被动传播状态,此处则化为主动状态。保留了王世贞回应,但删去“微笑”神态及“随之”二字,并隐去汤对此的再回应,将王世贞“达人”形象转化为挟怨报复者。通过一些微小的调整,钱谦益强化了汤、王之间的冲突;材料编排上,将《初学集》对《复费文孙》《答王澹生》的糅合化为并列书写,叙事效果不变,但对史料的运用更加巧妙;语境设置上,钱氏未如《初学集》般直接提出以曾王之学反对王李俗学,而是于七子派登上文坛之前拈出宋濂,于七子派盛行海内之时举出归有光、汤显祖,形成一条前后延续之正脉,具有文学史辨别正变的意义。宋濂与归有光均主张尊经师古,接续唐宋古文传统,汤显祖则“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如此,《小传》虽未明言,但实际上已将此文学、学术路径作为解驳七子云雾之正途。此外,《小传》通过“又尝以其文寓余,以谓不蕲其知吾之所已就,而蕲其知吾之所未就也”一句,不仅与《初学集》形成互文,强化了论证说服力,并且由宋濂、归有光、汤显祖之后,自然地将重振文坛的重任引向钱氏自己。
钱谦益改写、编排史料的用意在于,建立晚明以归有光、汤显祖、钱氏本人前后相继之正脉。钱氏于《列朝诗集·丁集中》末尾安置了归有光、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钟惺、王思任等人,构成了其诗史中排击七子的主要群体。归有光为这一群体之首,汤显祖的定位为“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这是钱氏欲立之正统。徐渭诗歌间流入“偶尔幽峭,鬼语幽坟”,不符合钱谦益的诗学观念。公安派为泄七子派邪气之“劫药”,但矫枉过正,又产生了新的弊病。竟陵派(钟惺为代表)为“输泄太利”所生之“别症”,虽然试图纠正公安后期及七子派之弊病,但反而使文坛的病症更加严重。王思任则为竟陵之外“又一旁派”,均无法引导明末诗学复归大雅,不能成为正脉。钱氏本人并未出现在《小传》中,但如其自言“万物盛于丙,成于丁,茂于戊”[12]820,作为隐身之“戊”,钱氏担负着矫正竟陵、七子之弊,使文坛归于正途之责。钱谦益在《答山阴徐伯调书》中对此诗史意图有更为明确的说明,“嘉靖末年,王李盛行,熙甫遂为所掩没。万历中,临川能讼言之,而穷老不能大振。仆以孤生謏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海内惊噪以为希有,而不知其邮传古昔,非敢创获以哗世也”[5]1347。归、汤分别为嘉靖末及万历中排击七子之正,钱氏所处之文坛形势则更为复杂,七子派仍有余声,竟陵派则代七子派“起而执会盟之柄”,成为新的时弊,钱谦益“通经汲古之说”所排击的既包括王李俗学,也包括竟陵,而这一学说“邮传古昔”,承自归有光及汤显祖。
钱谦益对此事件的书写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初学集》与《小传》在叙述结构、用意上具有一致性,《初学集》可视为《小传》的早期版本。《小传》的语境设置、文本取舍、材料编排、互文等史料处理手法更加精致隐蔽,并且对文学史的思考也更加成熟,建构了一条晚明文学正脉。
3 《列朝诗集小传》事件书写的影响
受钱谦益书写的影响,明清文人对此事件的书写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差异,集中体现在文本来源、内涵解读、诗史定位三个方面。
明人对此事件的书写呈现出同源异流的特点,就文本来源而言,均源于汤显祖《答王澹生》,但在处理方式及内涵解读上存在较大不同。范景文《来禽馆文集序》(13)此文同时见于范景文《文忠集》及蒋臣《无他技堂遗稿》,然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全录》第1584条“来禽馆集二十九卷”则称,“检上海图书馆藏本,更有万历戊午范景文《重订来禽馆文集序》,此本缺失”(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67页)。上海图书馆藏本中所存序可证明此篇为范景文所作。的处理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史料取舍上,遮蔽批评行为,仅保留观点,并且将观点中“神情声色”的部分删去,转引为“汤临川每言自有此道,前人业已登峰造极,后有作者,度无有能过之,称能而已”,略去规矩与神情的复古方式对比;二是设置语境,首先将此置于“或曰‘文章一道,与世运为升降者也。’余应之曰:‘非也,各随其耳目之习尚移之’”的文章之道升降语境下,而后围绕“称能而已”,对比“能者”与“无能者”。“其无能者,随人步趋,如优人之行乡饮,献酬秩秩,未免俳气;能者,则才及于格,情轨于法,踌躇满志,不极不止”[13]513,将汤氏批评的内涵转向文章升降及注重“格”“法”的复古阵营内部比较上。蒋臣《邛山月序》(14)蒋言“近代汤临川,雅称哲匠,其所称述李何诸君子,不少袒戈。但谓前人业已登峰殚精,更难居上,后有作者,称能而已”(蒋臣:《无他技堂遗稿》卷五,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2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对史料的运用方式与范景文相似,不再赘言。
沈际飞仅使用了王世贞对此的回应:“王司寇为临川云:‘汤生标涂吾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其言则验,予又免于后之人哉!”(15)此本仅南京图书馆有藏,故转引自《汤显祖全集·诗文集原序辑存》,第1695页。为自身《独深居点定玉茗堂集》中标涂、批评之举寻求合理性。
明末清初张岱《石匮书·汤显祖列传》(16)两本书的成书先后学界目前尚无定论,但这里主张张岱的汤显祖传是袭用了钱谦益所作传记。《石匮书》中有“又尝以其文寄所知,谓不蕲其知吾之所已就,而蕲其知吾之所未就也”一句,《列朝诗集》的文字是“以其文寓余”,其余均同。此句已见于《初学集》中《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不蕲其知吾之所就,而蕲其知吾所未就也”,则此实为汤显祖对钱谦益的寄言。此言不见于显祖别集,许子恰所刻《玉茗堂集》中钱氏原序也不见此句,张岱只有可能是得于钱氏著作。此外,《石匮书》中亦有“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之语,然归、汤对钱氏文学思想形成有极大影响,推尊二人在排击俗学中地位是钱氏的特点,不当由张岱首先提出。同时,《石匮书》同卷《袁宏道列传》有“余录中郎诗,参以小修之论,取其申写性灵而不悖于风雅者”之句,与《列朝诗集》同,然《石匮书》为史书,并非总集,不可能有选诗之举,只有可能是承袭自《列朝诗集》,可为旁证。基本沿袭了钱谦益《列朝诗集》“汤义仍显祖”,对这一事件的书写除个别用字外完全相同,无需详述。
清人对此事件的书写较晚明为多,在文本来源、内涵解读、诗史定位方面整体呈现趋于稳定的状态。就文本来源而言,钱谦益的两种书写代替汤氏原文成为清人的主要史料。《初学集》的沿袭情况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说明,此处主要讨论《小传》。就用字而言,清人文献更偏向《小传》文本。如尤侗《艮斋杂说》“后人亦当有标涂汤生者”[14]53之句,更近《小传》的“异时亦当有标涂汤生者”,不似汤生原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之简;严遂成《汤遂昌显祖》句下注“曾摘王李增减汉史唐诗字面,流传白下”[15]525中的“流传白下”,出自《小传》;朱仕琇《半江书屋课义序》言“由选体而规欧曾,标涂王弇州作者,略与震川同意”[16]366,叙事极简,但将“规欧曾”作为汤显祖标涂的用意所在,是受到了钱谦益的影响。李茹旻《玉茗堂》句下注呈现出混杂的特点,“先生为南太常博士时,元美弟敬美为太常卿,敬美唱为公宴诗,不应,又简检献吉于鳞元美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散置几案间,使元美知之”。“散置几案间”自然是出于《初学集》,而将不应公宴诗与标涂文赋两事连用,则是《小传》的笔法,“使元美知之”亦是《小传》所用文本。

就诗史定位而言,清人注意到了归有光及汤显祖在面对七子派立场及文学、学术上的一致性。明人将汤显祖与归有光放在一起讨论,主要是因为二人在制义成就上的相似性。如陈际泰《陈士业新艺叙》言“试取归震川之博奥,汤若士之清远,即置之杂秽之中而光气喷薄”[18]164,郑鄤《明文稿汇选序·汤海若》、李蛟祯《楮叶斋瓦注篇叙》、曾异《复潘昭度师书》等均是如此。汤显祖在文中提到归有光,如《王季重小题文字序》言“时文字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归太仆之长句,诸君燮之绪音,胡天一之奇想”[19]1134,也是因为其制义成就。
清代虽然也有很多文献并举归、汤的制义成就(17)如钱谦益《家塾论举业杂说》,赵士麟《徐子文时艺序》,田雯《韩祖昭制义序》,赵俞《王震来制义序》,陈仪《张天池制义序》,焦袁熹《代汪炽南绍焻序复所先生稿》,何焯《两浙训士条约代颜学山学使作》,周寅清《四书文源流考》等。,但新特点在于,归、汤在对待七子派态度上的一致性进入清人的书写。如尤侗《艮斋杂说》言“近如弇州四部,震川讥为妄庸巨子,临川复从而标涂之”,蔡显《闲渔闲闲录》《四库全书总目·玉茗堂集二十九卷》、平步青《霞外攟屑》“王弇州文”条均对此有所说明。甚至出现了二者融合的现象,王嗣槐在《与方渭仁书》中记载:“牧斋称汤义仍官留都时,弇州闻其名而造之,义仍不与相见,出其批抺弇州集,散置几案间,弇州信手翻阅,嘿然掩卷而去。末年亦自悔其少作,义仍死为文哀之,追叹不能已。仆尝询诸长老,亦未知其有是事与否。”[7]200汤显祖去世远在王世贞之后,不可能存在王世贞哀汤显祖之死的情况,这里实际上是将王世贞晚年赞归有光画像事与汤显祖涂抹世贞文赋事混杂到了一起。清人朱仕琇对此现象有所解释,“汤固豫章之隽也,迹其生平,由选体而规欧曾,标涂王弇州作者,略与震川同意”。归有光“肩随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汤显祖“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归、汤均排击七子,且均倡宋代文章,虽不属于同一流派,但在清人的明诗史认知中,二人在阵营、理论上具有相似性,诗史中地位也前后相连。
还有一些文献虽未记载此事件,但也涉及了清人对此的诗史认知,如阎若璩《秋寓杂兴赠陈子寿先生五十诗》言“临川嘉定百年中,新变方能许代雄。若为门庭求广大,瓣香合礼绛云翁”[20]209,句下自注曰“谓汤义仍、归熙甫两先生之学”。黄之隽《壬申文选跋》引用徐伯调答复钱谦益的书信,“长者历引李长蘅、汤若士之言,尊景濂熙甫,以规橅秦汉为俗学,不如奉唐宋大家为质的”[21]454,注意到了归、汤至钱的源流脉络。
就此事件的书写流变过程而言,明人书写呈现同源异流的特点,而清人受钱谦益的影响,对此事件的书写趋于稳定,对事件文本内容、内涵解读、诗史定位的认识均难以脱离钱氏书写的范畴。钱谦益对此事件的书写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浅层的事件认识层面,事实上,依靠成熟的史料处理技术,钱谦益于整体的诗史层面,定位了汤显祖的文学特点及诗史位置,清人对汤显祖诗文方面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钱氏书写的影响(18)已有学者对清人关于汤显祖诗文的评价进行了考察,如黄建荣《略述清人对汤显祖诗文的评价》载《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 《列朝诗集小传》事件的历史真实性
以汤显祖对王世贞文赋的批评事件为例,可以看到钱谦益在《小传》中对事件的处理方式及其诗史意图。值得注意的是,钱氏书写相较史源已发生变形,但清人对此事件的文本、内涵、诗史定位的认识主要依托于钱氏书写,而非史源,这产生一个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了清人对钱氏事件书写的认可?笔者认为,这与文学史的历史真实性有关。
英国学者奥克肖特在《历史是什么》中对历史真实性有所讨论:
历史有两种要素:(1)在特定时间内发生的各种事件;(2)人的头脑中收集起来的这些事件[22]26。
历史中的真实性不完全依赖于纯粹的文献证据的准确性,还依赖于考察证据的方法和考察证据的头脑中的思想材料[22]31。
通常认为,历史事件是客观的,但奥克肖特提出,历史是书写下来的历史,事件在进入历史书写时势必会有判断的介入。史家依据个人观点及所处时代的知识水平,判断事件的真伪、价值、内涵,进行权衡、取舍,建构起历史。因此,历史的真实性不能完全依靠文献证据的准确性,还有赖于史家对史料的考察方式。
朱彝尊在对钱谦益《明史》的批评中也有类似的说明,“考证失真,又多主门户之见,假令书就,未必称信史尔”[23]356。将此移入《小传》批评中,“考证失真”是文献证据层面,“门户之见”则是对钱氏选人、选篇、选史料及文学评价等方面的批评,具体到事件层面,则可指钱氏对事件考察方式的公允性。
就文献证据准确性而言,《小传》所用材料必有出处已成为学界共识,日本学者野村鲇子便在《〈列朝诗集小传〉研究》中梳理了三十九篇人物传记的史源。钱谦益的考据功力也有学者进行研究,如徐隆垚在《明人诗史书写研究》中对“对话型史料运用”进行了分析。清人认可《小传》历史真实性的一方面原因,便是钱氏在史料来源及考据方面的修养。周亮工《章丘追怀李中麓前辈》言“近虞山刻列朝诗选,始为阐扬。小传颇悉公生平”[24]268;王士祯提出了数条《小传》中的错误,但亦言“牧翁博极群书,亦有此误”[25]4084;潘耒《从亡客问》言“牧斋虽大节有亏,然其学问之宏博,考据之精详,亦岂易及”[26]110;陈梓《论列朝诗选》、张照《石渠宝笈》、郭麐《灵芬馆诗话》、刘承干《明史例案》卷三也对此有所说明。当然,在文献证据出现问题时,《小传》中事件书写也会招致清人的质疑,如“陆少卿师道”条中所记文徵明在翰林为姚涞所窘之事,便有姜宸英《姚明山先生拟传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姚涞”条、梁章钜《姚明山之诬》、李祖陶《湛园未定稿文录》、方浚师《蕉轩随录》卷十“尚书疏证中论状元”条、陈田《明诗纪事》“文徵明”条为之辨诬。
对史料的考察方式是否公允,也是评判事件历史真实性的重要因素。以汤显祖对王世贞文赋的批评事件为例,钱谦益对此事件内涵的解读是基于汤氏《复费文孙》《答王澹生》两文以及汤对钱的两次寄语。钱氏从中提炼概括了汤显祖的文学主张,虽与史源语意存在出入,但与汤显祖的整体观点并不冲突,也符合清人对汤显祖的认知(19)屠隆《汤义仍玉茗堂集序》、虞淳熙《徐文长集序》、袁宏道《喜逢梅季豹》、王思任《天隐子遗稿序》、张师绎《萧斋诗序》、谈迁《上吴骏公太史书》、何棅《拉云小集序》、吴乔《围炉诗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等文献均对汤的基本文学取向及对七子派态度有所说明。。诗史定位是基于其对归、汤对待七子派态度及文学取径上一致性的挖掘,在清人判断中具有真实性。还有一些事件则因其考察材料时所采取的压制方式而为人所质疑,如“张主事凤翔”条中李梦阳对“光世诗赋有《伎陵集》六卷,信手涂抹,不经师匠,如村巫降神之语。而献吉作传,以为子安再生,文考复出”[27]317事,此段文字出于李梦阳《张光世传》。朱彝尊及陈田提出,李梦阳对张凤翔的文学批评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传记,二是李对张别集的评点“献吉为作佳传,而又于《伎陵集》指谪其失,一以殉友谊,一以著公评”[28]1245。李对张别集的评点是出于客观的诗文评价,而传记中的溢美之词则是“殉友谊”。钱氏于此压制了客观的别集评点,彰显传记部分的“殉友谊”,将此事内涵界定为七子派“党护曲论”之举。这种史料考察方式对朱、陈而言有失公允,故而朱、陈二人对钱氏事件书写提出“殊不其然”的批评。
文献证据准确性及钱氏对史料的考察方式成为影响《小传》中事件历史真实性的重要因素,也进一步影响清人对《小传》事件书写的接受。如果将此问题进行扩展,对清人关于《小传》事件引用及批评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应会对此有更多发现。
总括而言,针对汤显祖标涂王世贞文赋这一文学批评事件,钱谦益通过材料取舍、语境设置、互文等方式,重新塑造了此事件的文本内容、内涵解读及诗史定位。钱氏用意在于凸显曾王之学与王李俗学之间的冲突,并据此对晚明流派进行辨别正变的工作,建构以归有光、汤显祖、钱氏本人前后相续之晚明文学正脉。以此为例,可以看到《小传》中事件书写与诗史建构间的内在关联。钱谦益的书写影响了清人对此事的文本、内涵、诗史定位的认识,这涉及文学史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文献证据准确性及史家考察文献的方式成为《小传》事件历史真实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影响了清人对《小传》事件书写的接受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