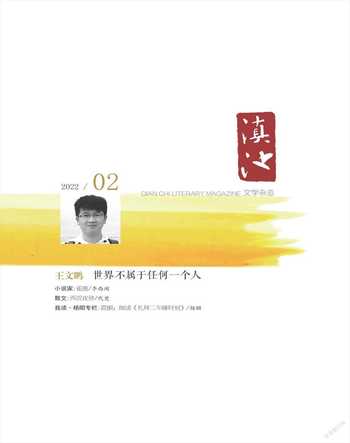矿山纪事
马友宏
初到矿山
2005年,我到了雷波县马颈子矿山山脚的集镇。
因为暂时不能上矿山,只能临时寄住于几个矿老板在集镇上租用的民房。三层砖混结构的民房里,大厅天花板上的三叶式风扇不断旋转着,脱了漆的黑色沙发、木制的桌椅、老式的水壶、上了锈的铁桶等,摆放在大厅的各个角落。橱柜上摆放着一台十七寸彩色电视,电视背部的天线一直连接到屋外,由一根五六公分粗的竹竿将101天线托到房顶高处……
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向夜间12点,关了灯,我静静地躺在大厅的沙发上。大厅里,漆黑一片,不时听到蚊虫的飞鸣声,徒增了夏夜的烦闷之感。屋里发霉的气味不断刺激着我的鼻腔,透过呼吸,传入胸腔,渗透到每一处神经。
似乎有千万种思绪不断向我袭来,闭了眼,是乱得无法理清的画面。
矿山山麓的天气热得让我无法入眠,身上只能盖上一块薄薄的床单。矿老板们已然睡去,而我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这是集镇上一栋临街的三层楼水泥砖房,算得上是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马颈子集镇上相对抢眼的一栋建筑,红的砖,过硬的水泥板,与街面上的瓦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集镇是矿区最多的人口集聚地,也是上矿山的必经之处。
集镇的对面,是一个小型发电站,电站机组全天运转,水流的冲击声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不断传入耳畔,只感觉耳际充斥着嗡嗡的响声。水流冲击声和蚊虫叮咬声混杂在一起,让我心神不定,更加难以入睡。这种无法入睡的感触,同时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夹杂着丝丝焦虑和淡淡忧郁,充斥着我的每一处神经,让我几乎不能呼吸。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马颈子集镇除了闷热以外,不到一炷香的功夫,蚊虫已经在我的手臂和小腿上叮咬出了几个红斑,奇痒难忍。
我心里清楚,两天以后,我就要上到矿山,下到矿井,开始我的矿山打工生涯。平日里常听人们说矿山到处都是矿,走路都能踩到矿,捡矿能捡到手酸,数钱能数到手抽筋。我当然不相信这些让人神魂颠倒的传言,囊中羞涩的我,只想早一日到达矿山,下井干活,补贴家用。
几天前,我就决意随本村的一个堂叔到矿山闯一闯。在今早天刚泛白的时候,搭乘了堂叔的吉普车颠簸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达这矿山集镇的。据说到了集镇,还得再乘半小时的车才能到达矿山山脚,然后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上到矿区。到达集镇时分,天色已晚,只能择日再上矿山。
一路上,茫茫的大山深处,松林和巉岩纵横交错,黄绿相间的山林浸染着这茫茫的乌蒙山脉,把这深秋的大地点缀得绚丽多彩。远山,大地,吉普车在弹石路上急驰,穿梭在这崇山峻岭间,一路向西,奔矿山而去。吉普车卷起阵阵尘土,尘土四处飞扬。
车辆穿过永善县城后,堂叔告诉我,车辆要跨过金沙江,才能去到雷波县,最近的一条道就是从屹立在金沙江江面上的铁锁大桥上经过。大桥选建在两岸相对较窄的地方,却足足有两百多米宽,由无数根近似手腕粗的铁索连接着两岸混凝土浇灌的桥墩。铁索上,铺着厚厚的钢板和枕木,用铁卡锁住,由硕大的螺丝旋紧。
铁索桥边站着几个执勤的武警,我们的车辆被拦住了。透过车窗,我看到金沙江若彩带一般,镶嵌在高山峡谷之间,江水湍急,奔流而去。对面行驶过来的车辆从铁索大桥上经过,桥面产生了剧烈的晃动,我心中顿时产生了一丝恐惧,这种恐惧,让我久久不能释怀。但这是去雷波县节省一个多小时行程的必经之路,两岸执勤的武警,正用不同颜色的旗子和手勢,让雷波方向驶来的车辆先行,我们只能静静地等待。当我们的吉普车被允许通行时,桥头的执勤武警很严肃地告知我们,车辆在铁索桥上一定要缓慢行驶。
堂叔告诉我,车辆通行时,禁止行人通行,只有等车辆通行以后,才放行两岸的行人,这样的做法既减少了桥面晃动,又确保了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回忆零星而琐碎,把我的思绪带入了无尽的斗争中,这种斗争,是内心的纠结和迷茫,是沉重压力之下的挣扎与反思,也是冲破内心苦楚的萌动和激进。思绪不断,回忆茫然,夜已深,我,渐渐睡去……
矿山下的集镇
醒来时分,阳光正透过大厅的门和窗户,直接照射在大厅的地皮上,溅落在地皮上的水滴折射着穿入屋中的阳光,发出刺眼的光芒,直入我的眼眶。
堂哥杨志豪正在准备早饭,我起身折了床单,放到他的卧房里,然后上到三楼的阳台,开了水龙头,用凉水洗了脸。水龙头里的水,不是自来水,而是房东用红砖在三楼楼顶砌了围水,将天上下的雨水聚集起来,然后用一根手指粗细的胶管连接,装上水龙头,就当作平日里的生活用水。
吃完饭的时间,已是早上十点多。见几个矿老板吃完,我便起身,同堂哥一起收拾了碗筷,并清洗干净。堂哥是一年前来矿山的,自己投资了三万块钱,和几个矿老板合伙开矿,一起租住在集镇上。
堂哥告诉我,今天是几个矿老板休息的一天,几个老板都不打算上矿山,只能等一天才送我上山。通常情况下,老板们都是三四天才上一次矿山,主要是上山的路来去较折腾,加之山路陡峭,来去几乎就是一整天。
在马颈子赶集的日子,几个矿山老板通常情况也是不上山的,几口矿井的领班一般会下山到集镇上采购矿井所需材料,和生活中所需的肉类、蔬菜等。矿洞里的领班,负责整个矿洞的人员调度、材料采购、采矿指导等工作,不像打眼、放炮、拉沙、洗矿的工人,几乎每天都要下到矿井作业。领班很少下井作业,所以下山采购的“肥差”自然被领班“承包”了。
平日里,当地彝族村民也会隔三差五地杀了自家养的肥猪,用伽底背箩背到矿洞兜售。矿洞领班为了省事,只要猪肉质量中意,都会购买。即便不杀猪的日子,当地村民也会背上自家的熏肉、土鸡、核桃、板栗等,拿到矿山各个矿洞问询售卖。
几个领班在集镇上采购好所需的物品以后,暂时寄存在熟悉的店铺里,然后相约在一起,找一个满意的饭馆,点上一桌子菜和几瓶冰啤酒,美滋滋地享受着在矿山上花钱也享受不到的快乐。
租住的楼房下便是集镇,建在高耸挺拔的大山之间,山上树木葱茏,大山遮挡住了一半的天空,山脚的小型发电厂运作发出的水流声填满了山谷。集镇旁是一条从矿山上流淌而至的河流,河流日夜不停地怒吼着,由西向东奔腾而去。楼下传来集镇特有的嘈杂声,不时还能听到摩托车喇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从阳台就可以看到,几个青年男子正张扬地骑着摩托车穿梭于街道上。
集镇上很少见得到汽车,山里人家,住在高山,多数经济拮据,家里能有一辆摩托,自是难得。每逢赶集的日子,骑摩托便成了炫耀的最佳时机,在人多的时候,还故意加大手柄油门,让发动机发出的怒吼声充斥进街道上旁人的耳膜,还时不时按响经过特意改装的大喇叭,让这代表着财富和身份的铁疙瘩满足自我的炫耀心理。
我自觉无聊,想去集镇走走,于是下了楼。从山上早早来赶集的农户,用背箩将自家种植的各种蔬菜背到集镇售卖,用一张塑料薄膜或者化肥口袋垫着,隔山差五地摆在铺面门前的街道上,见过往的人投来目光,便会急切问询,青豆、茄子、地瓜、花生……售卖的人用我听不懂的彝族话吆喝着,表示出极度的热情。我没有要买的想法,便以微笑的方式回绝这些热情的售卖人。
铺面里,老式木制柜台上陈列着门锁、门扣、电线、胶鞋、铁锅、铁锹……穿着羊毛马甲的两个中年男子,正拿着胶鞋和店主讨价还价。肉摊前,屠户正用力地在案板上砍着排骨,发出声声脆响……街道嘈杂,络绎不绝的男女老少不断穿梭于集镇上,平添了街道的热闹氛围。街道拐角处,两个喝醉了酒的汉子,斜靠在店铺石坎旁,一个已然呼呼睡去,一个正喃喃自语……
彝族特有的服饰成了集镇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流动,这种流动之美,显得格外抢眼,荡进了我的心里。
上矿山
在集镇上短暂休息了一天以后,我便整理好行李,随同几个矿老板乘坐皮卡车准备上矿山。对于陌生的矿山,曾经听说条件简陋,矿井工作危险而艰苦,但现实已让我无路可择。此时,内心的无助在这充斥着无尽困惑与纠结的空气中不断蔓延,也伴随着对矿山工作的渴求慢慢分散,这种渴求,既是希冀,也伴随着惶恐和一丝悲凉,让我茫然而无助。
经过半小时的颠簸,皮卡车停在了矿山山脚的矿坝里。
矿坝坐落于矿山山脚,是Y字形三座大山汇集的山岔口的地方,地势相对平缓。矿坝里,潮湿的路面上,深浅不一的马蹄印深深地嵌入泥土里,马粪、尿液与泥土糅杂在一起,散发出刺激的马尿味,呛鼻而让人反胃。
来往的马帮正将矿石从矿山上驮运下来,卸载在不同的矿堆上。只见一个忙碌的马帮汉子用衣袖揩完脸颊的汗水以后,就将驮矿的马匹赶到矿堆上,他喊了附近另外一个驮矿的马帮汉子过来帮忙,两人一同站在马匹的两侧,并将箩筐中大块的矿石抱了丢在矿堆上,然后两个人同时解开系在箩筐底部的绳子,矿石就同时被卸载下来。卸矿的,整理箩筐的,牵着马匹喝水的,牵着马匹站在树脚歇息的……呼喊声,吆喝声,马匹嘶鸣声,各种声音殽杂在一起,显得热闹而忙碌。
成堆的铅锌矿堆放在矿坝里,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刺眼的光点。不远处,几台推土机正在作业,推土机高高的烟囱里不断喷着浓烟。在推土机发出的怒吼声中,驾驶员把油门踩到底,正加大马力将马帮从山上运输下来的矿石不断铲起,堆高。
据说,山上开采出的矿石,都由马帮从陡峭的矿洞旁源源不断地运下山来,堆垒在矿坝里。矿山有一百多口矿井,矿坝面积不大,所以要在矿坝里租用到一块堆矿的地皮,很是难得,有时候要等上一个多月。
我们沿着矿山曲折的山路一路前行,上山下山的马匹与来往的人群穿梭在这狭窄的山路间。马背上,垫着花色不一的布袄,布袄上架着马鞍,马匹的两侧,挂着人工缝制过有化肥口袋的箩筐。这些比大青石还重的铅锌矿,正在被马帮源源不断地托运下山,当行人和马匹在路上相遇的时候,上山的人和牵着的马匹都会自觉地站立在路的一侧,让托着七八百斤矿石的马匹先行。
上矿山的路是石头和泥土混杂的山路,有的地方既陡又险,刚好够一匹马驮着矿前行。深山峡谷中,阳光从高耸入云的大山缺口处斜射到对面山的悬崖上,各种不同的乔木和灌木丛生长在巨石旁,倒挂刺从树枝上倒垂下来,在空中悠闲地飘荡。在这样陡峭的山涧行走,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山谷,因为山路艰险,马匹跌入山谷的事时有发生。
知更鸟发出的啼鸣声,与沉闷的空气混杂在一起,增加了我的灼热感,让我觉得全身处于蒸笼里,每个毛孔都不能很好地散热,沉闷、炽热、火辣……糅合在一起,让人浑身难耐。
上山的路越来越陡峭难行,一路上,驮矿的马帮互相打着招呼,偶尔也会和我们上山的一行人搭讪、寒暄几句。
渐渐地,我显得有些吃不消,停下来歇息,只能用衣袖擦着额头上不断溢出的汗水。汗珠流淌进了眼角,辣辣的,澀涩的,汗水沾湿了背心,汗淋淋地贴在背上。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攀爬,我们终于到达了B-1矿洞。B-1矿洞的洞口开凿在一块天然的巨石之下,几颗碗口粗细的水冬瓜树长在巨石旁,周围杂草丛生,倒挂刺从洞口的灌木丛上垂下,被矿洞工人用虎头钳修剪过,只留下半截吊着。
B-1矿洞的老板是与我们一同上山的肖兴国,只见他坐在木凳上,向领班黄满朝交代着矿洞的相关事宜。比如喝酒不能下井作业;不能用燃着的烟头去点营头的炸药;在营头放完炮一定要等炮烟散去以后才能进入巷道拉矿石;巷道支护木要用钢筋制作的抓钉抓牢实,并用大马钉钉紧……
我走出工棚,前行十多步,便见到了B-1的矿洞,只见洞口有山体中渗透出来的水滴从矿洞的岩石上滴下,或浸透在石壁上,滴答着落在矿车碾压过的矿道上。洞口的旁边,堆放着成吨的铅锌矿石,几个工人正在洗矿槽里的矿石。
在洗矿的工人中,有几个是当地的彝族,在和一个工人的搭话中,我了解到:洗矿的彝族小阿哥、阿妹子,是附近的村民,闲暇之余就来矿洞帮忙洗矿。
矿石正被井下工人从矿洞内用矿车运送出来,倒下,堆在矿洞旁的矿坝里。
转了一圈,回到工棚以后,堂叔给我介绍了B-1矿洞的领班,安排我以后就在B-1矿洞上班。领班叫黄满朝,永善大兴人,在矿山已经有五六年的光景了。
只见黄满朝从衣兜里拿出山茶牌香烟,分发给我们,并示意矿洞里一个叫阿卓吉布的彝族姑娘为我们沏茶。阿卓吉布是这口矿井负责做饭的姑娘,只见她认真地为我们沏着茶,用别扭的汉话问我们泡水要不要放茶叶,说矿山上的水泥土味重,加了茶叶以后,泥土味就会少一些。
工棚内极其简陋,用抓钉将粗大的木料抓牢、固定,木板和炸药纸箱铺垫的床铺上,分散着七零八乱泛黄的床单和被褥。床铺上,还有人在睡觉,黄满朝告诉我们,睡觉的是昨晚上夜班的工人,天亮才开睡。
黄满朝介绍着这几天矿洞的情况,只见肖兴国老板从口袋里拿出带过滤嘴的龙泉牌香烟,分发给在场的所有人。有三个约十五六岁洗矿的彝族小阿哥和阿妹子接过肖兴国递过的香烟。阿卓吉布也接过香烟,并从牛仔裤包里拿出打火机,熟练地点燃,悠然地享受着香烟带来的快感。
肖兴国又向黄满朝交代了一些矿洞事宜,然后就带着堂叔一行人去了其他矿洞,而我,被安排在了B-1矿洞上班。在领班黄满朝的安排下,我的床铺被安置在了矿洞出口一处岩石下的简易工棚里。
第一次下井作业
到达矿山井洞的第二天,按照领班的要求,我就被安排下矿井学习打眼作业。
领班分发了一顶安全帽、一双水鞋、一双绿胶鞋和一盏矿灯给我。在领班黄满朝的带领下,我戴好安全帽,穿上水鞋,背上矿灯,跟随黄满朝和另外三个工人就进了矿洞。
矿洞的巷道上,坑洼不平,矿洞的天顶上不时有水滴滴落,水滴夹杂着矿物成分,与主巷道的流水混杂在一起,静静地流淌着。巷道是曲曲折折的,显得阴暗而潮湿,有的地方只有一米多的宽度,刚好够工人推着一张六十多公分宽的矿车经过,狭窄巷道的地面到天顶只有一米六左右的高度。
巷道很低,我猫着腰跟在后面,一會儿低头,一会儿弯腰,但还是被岩石碰了几次头,潮湿的岩石和头盔碰撞发出的声响让我感到头部嗡嗡作响。
水滴不时从巷道的天顶滴落,和我们踩在巷道的水坑里发出的水声混合在一起,增加了巷道的阴森之感。走过一段路,我显然已经分不清处于矿洞内的何处方向了,一股凉意袭来,我打了个寒颤。我第一次进矿洞,矿洞内让人感到异常沉闷,充满了让人昏昏欲睡的腐朽的阴森气息。恐惧和害怕随之而来,这种来自内心对黑暗的恐惧,让我感到一丝凉意,这种凉意,冲击着每一处神经,让我后怕。
在采矿点,我看到部分地方留下了采过矿石的空洞,空洞中还留有几根矿柱。黄满朝告诉我,矿柱是采矿留下的,是用来支撑采过矿的整个空间的,如果将这些含矿丰富的矿柱也开采了,那这个地方就有可能随时坍塌。这些矿柱,等把这条含矿巷道的矿石开采得差不多以后,矿洞老板几乎都会抱着侥幸的心理,让采矿工人冒着风险把这些矿柱的矿石也开采出去,所有的矿采完以后,这条矿道也就废弃了。我想,这样的采矿作业,采矿工人不知道要背负多大的风险,才能把这最后的矿石开采出去,或许潜在的危险就是矿洞的塌方,采矿工人一不小心,就会被矿石埋葬。
巷道天顶有水滴不断滴落,洞内的凉意和外面的闷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仿佛置身于无尽的黑暗之中,惊愕、恐惧、后怕……五味杂陈。我开始担心起来,担心这巷道会不会塌陷,身处这大山腹中,会不会因为缺氧而被活活闷死……
按照黄满朝的安排,我跟炮工董家宽在矿洞营头学习打眼和放炮。黄满朝用矿灯仔细看了一阵矿洞营头的岩石,然后交代炮工董家宽沿着现在营头开凿的方向继续打眼。
黄满朝告诉我说,董加宽是多年的老炮工,对于打眼工作算得上是得心应手、轻车熟路,是矿山的好把式,让我潜心学习打眼技术。
黄满朝带着一起下井的两个工人走了以后,董家宽就开始给我讲解关于打眼的知识。董家宽说,打眼讲究的是见机行事,这凿岩机有几十斤重,一般打眼的时候,需要两个人才能操作,一个负责打眼,一个在后面帮着托起凿岩机,这样才省时省力。
董家宽一边给我讲解,一边示范给我看,并喊我提起凿岩机感觉一下。给我简单讲解完以后,就让我带了口罩,同他一起从地上抬起凿岩机。只见他双手扶住凿岩机,打开气阀,只听到凿岩机发出刺耳的怒吼声,当凿岩机和岩石接触的时候,岩石上顿时碰撞出浓浓的粉尘,这粉尘,扑面而来,伴随着这轰鸣声,四处乱窜。我第一次学习打眼作业,只感到双手被凿岩机震动得酸疼,耳畔充斥着凿岩机发出的怒吼声,这轰隆隆的声音,一直传到洞外。
半小时过去了,我们才打了三个炮眼。董家宽关了气阀,示意我先休息一会儿再接着打眼。
董家宽就地坐在了巷道上,从口袋里拿出山茶牌香烟,点燃,抽了起来,并示意我一起抽,我不会抽烟,便委婉地谢绝了。矿洞中没有可坐的板凳之类的东西,我也就直接坐到了巷道上。董家宽告诉我,铅锌矿矿洞中的打眼工作,是很讲技术和技巧的。矿洞不产生瓦斯一类的可燃气体,也就是说不会发生爆炸,即便在矿洞中吸烟也没什么大碍,所以我们常常用烟头或者燃着的香去点炮。要打好眼,柴油机的功率越大越好使,只是有些费柴油,柴油机带动空压机产生的强大气体,通过风管输送到凿岩机上,带动钻杆、钻头,才能在这坚硬的岩石上凿眼。打眼的时候,产生的粉尘吸入肺部对身体产生的危害很大,时间久了,就有可能得肺气肿或者哮喘病,所以作业的时候要带口罩进行防护。钻杆基本是用1.5米、2米、2.5米的,一排炮一般是打十五到十八个炮眼,这样用炸药炸下来的效果才理想。
炸药的重要成分是硝、石、硫磺,用油纸包裹,将导火索插入雷管,再将雷管插入火药中,包裹紧,这就是制作炸药筒子的过程。炮眼打好以后,将包裹好雷管的炸药筒子放入炮眼中,点燃导火索,接下来就看炸的效果了。
董家宽吸完一支烟,又点燃一支,接着说道,这矿洞巷道打得深一点,里面缺氧,就得保持通风,空气要用空压机输送到矿洞营头上,这是为了保证打眼、除沙、拉矿和进入矿洞的安全……
三个小时以后,一排炮十八个炮眼全部打完了,董家宽喊我拉来吹风管,让我用吹风管把炮眼中打眼余留的沙粒吹干净,又教我如何将炸药放入已经打好的炮眼中。
出了矿洞,洞口的柴油机发出的轰鸣声还没有停息,由柴油机带动的空压机不断发出巨大的声响,在山谷里久久回荡,浓烟从柴油机烟囱管中被喷出,慢慢消失在这山涧里的空气中。
第一次事故
时光流逝,岁月缱绻。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逝,化作无声的回忆,融入到矿山生活的每一个片段,让我在磨砺中彳亍前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还学习了洗矿的工作。
洗矿,要用到洗矿水槽、锄头、铁镐、钉耙等,将从矿洞中拉出来的混合矿石倒在洗矿水槽里,然后用一根塑料管将矿洞旁河道里的水引来,经过不断翻洗,大坨的石头首先被分离开来,直接倒在矿洞的矿坝边沿,再由人工分捡出矿石。由于矿石的密度大,石头的密度相对小一些,粉末状的碎石和矿石经过不断翻洗,矿石自然就下沉到底部,将上部分的碎石取走以后,剩下的就是矿石了。
矿山也有规定,若要下到矿井里进行打眼、放炮、拉沙、巷道支护等不同的工作,必须年满十八岁。倘若矿洞违反了这样的规定,被矿部或者县安监局检查到,面临的处罚多半是停业整顿和罚款。对于如此严厉的处罚,矿洞老板也是再三对领班进行强调,杜绝使用未满十八岁的工人下井作业。
在我来矿山一个多月后,我们在开凿主巷道营头时遇到很明显的马牙石(采矿人统称为酸引),我们都异常兴奋。这也意味着一旦遇到大矿,我们的工资就会翻倍,因为平常打主巷道是按进尺算,分摊的工资低。遇到大矿,情况就大有不同,一般都是按照采矿的吨位来计算,老板收入可观了,我们的工资自然就上去了。
黄满朝说,从经验判断,不出十排炮,就会出大矿。接矿心切的黄满朝激动不已,不断鼓动我们说,如果晚一天,新矿源可能就会被附近的六十三号矿井提前打到。这样一来,几个月找矿的心血就白白浪费了,没有了矿源,老板投下的成本开支将会血本无归,我们领到的工资也就不多。
心急如焚的老板肖兴国和黄满朝经过商议,决定加班加点推进开凿进度,让我们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三班倒,机器不熄火,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矿井主巷道开凿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进出的矿车能够在相遇的时候错车,按照矿井老板的要求,我们开凿的主巷道规格是一米五宽和一米六高,同时每隔五十米就在巷道的两侧的帮子上打一个错车道。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矿洞营头的水流很大。在打眼作业时,两米深的十五个炮眼还未打完一半,衣服早就湿透了。水,不断从营头上流出,即便用了防水的岩石型乳化炸药,每排炮炸开岩石的效果仍旧不理想,而且经常出现哑炮。这样一来,巷道的帮子上经常留有炸不下来的岩石。
营头不断流淌的水成了我们打眼、放炮、除沙的棘手问题,补炮也成了最近几天常见的事。
吃过早饭,炮工董家宽就领着我进了矿洞,将营头上的十几个炮眼打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我负责点补炮的炸药,董家宽负责点营头的炸药。水,不断从营头和巷道帮子两侧流出,哗啦啦的声响回荡在矿洞中,连讲话的声音都很难听清楚。因为水大,我点燃两根导火索以后,剩下的两根导火索经过几次努力都没能点燃,董家宽点完营头上的导火线以后,见我还没点完,回头问道:“点完没有?”听到董家宽的询问,我回头说道:“水大,视线不好,还有两炮没点燃,香都熄了两次了……”矿洞营头,水流声和被点燃的导火索发出的滋滋声混合在一起,加上导火索的刺鼻味儿,让我顿时紧张起来。借着矿灯灯光,我们注意到有导火索快燃尽了。一种不详的预感突然袭来,见势不妙的董家宽一把扯着我臂膀上的雨衣,竭力地喊到:“快跑,炸药要炸了……”听到董家宽的呼喊声,加上董家宽用力地拽我,我一时慌了神,就顺势跟着董家宽一起往矿洞外跑,急促的脚步声在矿洞里回荡,我的心更加紧张起来。
此时我们心里都知道,跑不出20米,引燃的雷管和炸药一定会爆炸。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料想今日难逃厄运了。
刚跑出十多米,我们看到了矿洞巷道右侧帮子边有一个拉矿的错车道。刚到错车道旁,不料董家宽转过身来,一把抓住我,将我推入错车道。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踉跄跌倒在错车道上,炮响了……
从矿洞营头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由里到外迸出。只听到董家宽“啊”了一声,怒吼般的爆炸声让我彻底懵了,我感觉董家宽用猛力拽了我一下,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董家宽的左脚跪在主巷道上。此时我才明白,董家宽为了救我,把我拽入了错车道,自己的左腿还来不及收回,炸药就爆炸了。我一下惊醒过来,第一预感就是董家宽的左脚受伤了。董家宽抓住我的手说道:“我……我的脚被炸到了……”借助矿灯灯光,我看到他小腿上的裤子破烂不堪,鲜血已经从裤子破洞中溢出,我的心顿时凉了。
这是雷管引爆炸药后产生的爆炸威力将山体岩石崩开,巨大的冲击力将碎石推出,直接钻入了董家宽的腿中。只见董家宽忍着剧痛,咬着牙对我说道:“快,快背我出去,不然炸药的烟雾马上就散过来了,我们两个就会中毒,被闷死……”此时,已经能闻到火药味了,刺鼻而呛人。
听到董家宽的话,我来不及细想,立刻蹲下去,背起董家宽猫着腰就往外跑。只听到耳朵里传来嗡嗡的声响和董家宽的头盔碰到岩石发出的碰撞声。
后来黄满朝告诉我,见去点炮的董家宽和我超过了预计的时间还没出来,心里就感到忐忑不安。正打算进矿洞去查看,就听到了炮响,他心里咯噔一下,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心头。巨大的爆炸声强烈地震动着工棚,洞口的杂草也被洞内传来的气流吹动了。正在用水烟筒吸着烟叶的他丢下烟筒,竭力喊道:“出事了……”来不及换鞋,就喊了身旁正在下棋的工人,提起矿灯,慌乱中抓起安全帽就往矿洞里跑。
在黄满朝的内心,十有八九是没人的了。巷道里,强大的爆炸威力和冲击力,再坚硬的岩石都要被炸得粉碎,何况是人!
平日,点炮要出来半分钟左右,炮才会响,这排炮响了,去点炮的我和董家宽还没出来,大家都推测这回是凶多吉少了。
巷道内,炸药爆炸产生的烟雾不断向外蔓延。背着董家宽跑了一段路以后,我看到微弱的灯光从巷道外傳来,并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声,火急火燎的心里顿时有了少些安慰,我心里明白,只要董家宽没有生命危险,就是万幸。
进来的工人有七八个,只见黄满朝一把从我肩上拽过董家宽,背起就跑,工人们跟在后面,奋力朝矿洞外奔去。黄满朝边跑边问:“董家宽,炸到哪里了?”听到黄满朝问自己,董家宽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炸……炸到了脚……”黄满朝听到董家宽的回话,悬着的心感到了一丝安慰。
出了矿洞,另外十几名工人早已在矿洞口等待。黄满朝将董家宽放在工棚的床铺边缘坐下,此时,董家宽左腿上的鲜血正从裤管中流出,染红了被炸得破烂不堪的裤子。看到董家宽痛苦的表情,黄满朝拍着董家宽的肩膀安慰道:“兄弟,忍着,别怕……我们都在……”黄满朝几乎吼了起来,让工人赶快拿绷带,绷带拿来以后,黄满朝便用绷带紧紧地捆住董家宽的大腿,防止血流淌过多。幸运的是,经过初步查看,碎石进入董家宽的体内不深。
看到董家宽痛苦的表情,我的心一阵酸涩,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我扶着董家宽的肩膀,此时,我的内心慌乱如麻、五味杂陈,惊恐、害怕、无助,不断袭上我的心头。我自责,自责于董家宽为了救我,被炸得如此严重。
我們知道,这个时候,要想用人将董家宽抬下山,那是痴人说梦。时间不容许我们再三思考,董家宽是走不下山的了,唯一的方法,就是用驮矿的马匹将董家宽驮下山。黄满朝拨通了经常为矿洞驮矿的吉克依左的电话,简单说明情况以后,几乎用哀求的声音让吉克依左用最快的时间把马赶过来。
此时,工人们都在忙前忙后帮董家宽查看伤口和准备衣物。挂了吉克依左的电话,黄满朝又立马拨通了矿井老板肖兴国的电话,汇报了刚才发生的情况。电话那头,肖兴国听到刚发生的爆炸事故,得知没有人员死亡以后,简单给黄满朝交代如何处理以后,就挂了电话。
大家心里都清楚,矿山上,只要没死人就是万幸,毕竟在矿山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拿着血汗钱,矿井里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危险,发生事故已经是家常便饭。
董加宽最终被驮矿的马匹运送到矿坝,再由租用的微型车送到雷波县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那一夜,忧心忡忡的黄满朝带着我和另外一名工人将董家宽送到医院以后,董家宽在手术室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的紧张抢救。我的耳朵也一直嗡嗡作响,经过检查,医生告诉我,这是被炮声震的,并无大碍,过几天就恢复了。
手术结束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手术还算顺利,董家宽的腿总算保住了,从董家宽的小腿上共计取出十七颗大小不一的碎石。
也就是在董家宽住院的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开凿的矿洞接到了开凿主巷道以来的第一线铅锌矿,足足有八十多分厚,而且综合品味很高。
在接到大矿的第二天,大喜过望的老板肖兴国自己掏了腰包,让黄满朝买了一只肥羊,算是犒劳矿工们打到了高品位的大矿。据说,这也是老板肖兴国第一次杀羊请客。
而我,和董家宽一样,却没有机会吃到那香喷喷的羊肉。我待在医院里陪伴着董家宽,一直觉得缺少了什么,但又说不出来。
死亡事件
时间在炮声与机器的轰鸣声中无声地流淌着,化作岁月的痕迹,镌刻在矿山的每一个日子里。
那一日,秋风萧瑟,山涧里,树上的叶片少得可怜,树枝上依附着不多的叶子,在微风中孤零零地摇曳着。一身疲惫的我,在天刚泛白的时候才打完炮眼。昨晚的后半夜,我在上一轮班工友的催促声中醒来,照例跟随董家宽把柴油机发动起来,开了空压机,进入矿洞,拽着沉重的凿岩机打好十八个炮眼,并点燃炸药。
这段时间,除了在矿洞营头上打眼,我还熟悉了除沙、巷道支护等工作。知道了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打完十几个炮眼,如何用炸药、雷管、导火索熟练地制作好一条炸药,用炸药把炮眼填充严实,并熟练地放完炮。
我刚走出矿井,不到半分钟的时间,矿井里就传来一阵炮声。这一排炮,炮声沉闷,从炮声中可以推断,这排炮爆炸效果好,没有哑炮,不会有补炮的情况。如果听到炮声是绝响的,声音脆而响,爆炸以后多半就会出现哑炮、闷炮,那么营头上的岩石就炸得不完整,打了两米深的炮眼,最后只能炸下一米多深的岩石。倘若帮子上有炸不全的,为了方便运输矿石和下井出井的方便,还得再打眼,补炮,或者用风镐处理。
四个多月的矿山生活,我已经习惯了睡潮湿的工棚,习惯了上夜班,习惯了矿洞中的一切工作。
也就在前一个月,对面半山腰的七十六号矿洞发生的死亡事件至今让我心有余悸。七十六号矿洞洞口开凿在对面半山腰的一处悬崖边,要上到矿洞,必须经过一段近乎七十度的陡坡,让人不寒而栗,陡坡的路沿被工人用凿岩机打了眼,将钢筋嵌入山体,又填充了高标号的混凝土,并用焊机焊接了牢实的钢筋扶手。
七十六号矿洞的矿石出产量大,品味又相当高,但马帮却无法上到矿洞驮矿,运送矿石却成了难事。于是矿洞老板花了大价钱,从矿洞堆矿的矿坝处安装了溜索,溜索一直连接到一百多米距离的对面山脚。矿洞运矿的时候,在矿洞的矿坝处用固定好的铁皮装载箱装满矿石,对面山脚放置有几个固定好的废旧轮胎,等矿石通过溜索传送到山脚时,因为受到固定在岩石上的轮胎阻力,装满矿石的铁皮装载箱便会停下来,最终矿石被工人卸载在山洼里。
那一天,我休息,闲来无事,想到处去转转,出于好奇,于是就约了我们矿洞的一个工人一起去七十六号矿洞耍。
在七十六号矿洞耍了两个多小时,已经是接近天黑时分,热情的工友们硬是要留我们一起吃晚饭,觉得大家平日里工作繁忙,很少聚在一起,执拗不过,只能留下。
饭吃到一半,工人刘二堡说闹肚子,说完提起矿灯就出去了。我们边吃边聊,从采矿聊到洗矿,从马帮聊到矿坝。过了好一阵子,却不见刘二堡回来,一个工人突然说道:“刘二堡这饭还没吃完呢?上个厕所不至于花这么长时间吧!”工人这么一问,我们才想起刘二堡的确出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感觉不对劲,于是就提着矿灯朝厕所方向喊,却不见回话。这七十六号矿洞的厕所和其他矿洞的厕所有着天壤之别,是用几根木料搭建在悬崖边的,因为厕所不能隔矿洞和工棚太近,选来选去,矿洞工人为了减少清除粪便的麻烦,加之厕所下方是一个无人去到的乱石林立、杂草丛生的沟壑,当初就选在了那么一个特殊的位置。
我们喊了一阵,寻不到刘二堡,一个工人说道:“会不会从厕所那边掉下去了,这黑洞洞的……”听这么一说,七十六号矿洞领班李文雄就骂了起来:“你狗日的竟瞎毬说”。说话的工人听到被骂,便不再说话。寻不见刘二堡,我们便有意识地朝厕所方向去找,厕所里还是寻不到刘二堡。顺着矿灯的灯光,我们看到厕所附近的草和杂木上有物体滚过的痕迹。心里突然一惊,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几个人再次扯着嗓门喊刘二堡的名字,但还是没有回应。
后来,刘二堡的尸体在厕所下方六十多米的乱石堆里被找到。眼前的刘二堡衣服破烂不堪,面目全非,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声旁的乱石,成了一具无法动弹的死尸,眼睛睁得硕大,死不瞑目一般,静静地躺在冰冷的乱石堆里一动不动,没有了生命迹象。
此时,周围的空气似乎凝固了,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中。我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好端端的一个人,眨眼间,说没就没了,伤感和忧郁挂在每个人的脸上,令人痛苦而心碎。
我们等了两个多小时,矿洞老板白芷江才赶到刘二堡的尸体旁。确定刘二堡已经死亡以后,让工人找来纸钱,点燃,算是烧给刘二堡死亡以后的落气钱,告慰刘二堡的亡灵。最后白芷江出了六百六十块钱,找了四个本地胆子大的村民,将刘二堡抬到了一处溪水边,擦洗了模糊的血肉,换了衣服,制作了一副简易担架,才将刘二堡抬到山脚的矿坝。
尸体被抬到矿坝的第二天,他的家人一大早就赶到了矿坝,看到了停放在零时搭建的简易工棚里的尸体,瞬间哭成了泪人。刘二堡的姐夫也在七十六号矿洞打矿,在刘二堡的姐夫和矿洞其他人的证实下,证明了刘二堡不是在矿洞里出的事。矿洞里的人都说,那晚刘二堡没有喝酒,上厕所的过程中踩空了跌入山崖,谁料想偏偏就出了这样的纰漏,是意外死亡。
白芷江只想早点私了这件事,毕竟出了人命,不赔偿是说不过去的。一旦经公,将面临矿部和县安监局联合调查、开会、罚款、通报、停产、整顿。这样一来,损失更大。
家属也没有过分为难矿洞老板白芷江,经过协商,白芷江赔偿了家属三万块,又出了一千八百块钱包了一辆微型车将尸体拉回了刘二堡的老家。
几天后,刘二堡被埋在了老家的后山上。
矿山第一次发工资
入冬时分的马颈子矿山,寒意在每一个白天和黑夜里不断袭来,卷席着矿山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山涧里的凉水也充满了寒意。
矿洞有冬暖夏凉的特性,所以,尽管矿洞之外已经是寒气逼人,矿洞内却是暖意十足。此时,无论待在工棚中,还是蜷缩在被窝里,为了抵御刺骨的寒意,我们不得不把床铺聚到一起,两个人将被褥凑在一起睡,以这样的方式来增加暖和度。
隔回家过春节的日子只有十多天了,按照惯例,在大年三十的前半个月,县里就会强制要求矿部派人上山,对矿山进行强制封洞口,停工停产。再则,矿山老板和矿工们辛苦了一年,都要回家与家人相聚,带着一年的血汗钱,过个肥年。
听黄满朝说,最近两天矿洞老板肖兴国就会给我们结算下半年的账。这也是黄满朝催了矿洞老板好几次以后得到的回复,眼看天气越来越寒冷,我们都担心回家的路上大雪封山,希望老板早点结算工资,在下雪的日子里抢在封路之前赶回家。
停工停产了,肖兴国迟迟不肯给我们结账,大家心里憋得慌,只能在工棚里干等。
在黄满朝多次催促以后,终于在矿部封矿山以后的第三天,肖兴国才把黄满朝叫到集镇上结了账。
我们在无聊的等待中煎熬着,有的下起了象棋,有的玩纸牌来打发时间……
终于,在夜幕降临两个小时以后,黄满朝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工棚。看到黄满朝板着的苦瓜脸可以推测,肖兴国拖欠工资已经成为事实。黄满朝的回答果然应验了我们的猜测,黄满朝说,在自己死磨硬缠以后,肖兴国只付了矿洞一半的工钱,找了各种理由,让我们先回家,在春节前会把剩余的钱打到黄满朝的卡上,然后再分别转给我们。
已经有矿工开始谩骂起来,说肖兴国似乎吃透了工人的心思,拿他没辙,所以故伎重演,赚了钱又故意拖欠工资,拿钱在县城买房、买车,又养了小婆娘。有的指爹道娘地骂道,说这狗日的不讲良心,辛辛苦苦在矿山上干了一年,还故意拖欠工资;有的说指不定这狗日的到了过年又要放鸽子,付工资又是来年的事了;有的说来了矿山一年多,除了接大矿那次杀了一只羊,哪里见肖兴国放过血……
各种赌咒、谩骂不断发酵,在整个工棚里蔓延开来。黄满朝用力地吸了一口烟,然后说道:“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埋怨有个毬用,先把领到的工钱给大伙结一下吧”。听到黄满朝发话,一个工人说道:“结个毬,这狗日的肖兴国,玩这么一出,早晚要遭到报应的”。另一个工人插话说道:“要不大伙一起下矿山找肖兴国结清账再走,谁知道这指望救急的钱过年能不能兑现?上学的娃开春就得用钱呢!”
在矿山的日子,我偶尔也会听到关于矿洞老板肖兴国的段子,和部分矿工发泄的不满,但出于是同乡,我不想评论肖兴国的是与否。我不想掺杂进这没完没了的指责中,因为我知道,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已然无法改变。
事态在黄满朝的万般保证下平息了,通过核对工时,扣减共同的开支,以及扣除个人的支出,算账一直持续到夜间十二点多。在接过四千多元工资的时候,我知道,矿洞老板还欠我六千多元的血汗钱,这也是我来矿山半年付出了汗水的回报,是收获,但却饱含艰辛。
夜已深,明早,我们即将奔赴县城的车站,乘车颠簸十多个小时,回到那魂牵梦萦的家。
八九个工人已经聚在一起,玩起了纸牌。工棚里,声音又开始嘈杂起来,我知道,經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总有人收获快意,也必定有人经历失落。
山谷在晨鸟的啼鸣中被唤醒,山峰依旧静静地矗立在寒意之中,河谷中的冷气不断灌入工棚,矿洞中的水依旧静静地流淌……
山路上,我们背着行囊,迎着寒气,正朝着家的方向赶,但,这脚步却越走越沉。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