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漫卷》:守候中国大地上蓬勃的生命
张恒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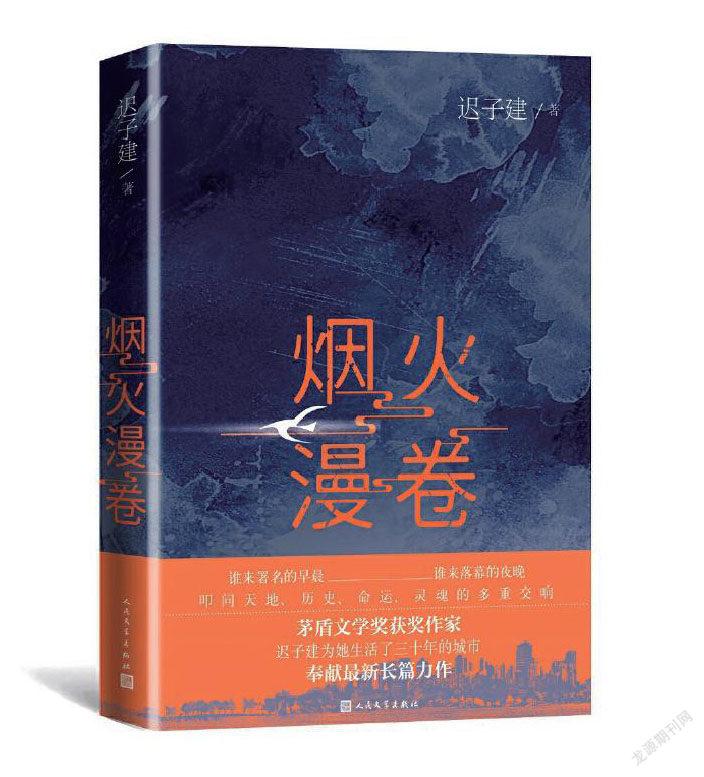
有了如迟子建一系列文字的书写,黑龙江岸上这片广大的黑土地,也才成为中国人意识中真实可触的、血肉丰满的真实存在。
——阿来
来自中国领土最北端的迟子建,1964年出生于北极村,1983年开始创作,迄今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學文本600多万字,出版单行本近100部,代表作品有《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荣获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和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奖项,在国内外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目前,迟子建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外,特别是日本和法国,并有多种语言的海外译本,如英、日、法、韩、瑞典、波兰等。其中,长篇小说《烟火漫卷》以浪漫与伤感交织的诗学世界赢得读者。据《2021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该小说以39家馆藏位居第二,仅次于莫言《晚熟的人》。
苏童说,很少有作家像迟子建一样,在长达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始终能够保持均匀节奏、稳定风格、坚定追求和明亮品格。《烟火漫卷》继承了迟氏小说一贯的风格。
平实随和的叙事基调
这是迟氏小说的惯常基调,小说中更多体现为底层生存的状态,集历史、政治、风俗等为一体的现代城市生活景观,人性善恶、自然衰老、爱恨情仇等生命主题,达到了一种圆融超脱的境界。正如学者翟苏民所评价的,迟子建笔下的自然与人物、历史与时代等符号,都是充满活力的,所承担的“艺术使命”之重在当代作家中少见。迟子建自评,曾用“哀而能诗”,即善于从最普通的现象还原,回归最核心的笔法,终用平凡意象呈现生活意境,平缓而有力,这也是《烟火漫卷》的一大艺术魅力。小说中,无论是景色描写还是人物描写,都会伴随抒情性文字的渲染,情节的发展随着环境变化而逐渐铺开。但文本叙事并不是“强情节”模式,而是在“弱情节”的叙事框架内呈现人物戏剧性、传奇性的命运,非但没有产生冲突,反而在整体圆融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基调,极大地凸显了情节的戏剧性和命运的沧桑感。
内敛有力的现实批判
迟氏小说擅长以对“通灵”事物的描写赋予文本更加空灵诗意的审美色彩,并通过与现实主义叙事的巧妙结合,将意义指向拉回现实批判,进而形成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融合。从《炖马靴》中的狼,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驯鹿,再到《烟火漫卷》中的雀鹰,实际上均为对人物命运的一种特异视角的审视。小说中,通灵的雀鹰小鹞子从寂静的鹰谷来到喧闹的城市。在榆樱院,它见证了租客们艰辛的生存境遇和隐秘角落中的人性秘密。但小鹞子最终却被塑胶跑道的胶水困死,如此结局,更多蕴含了迟子建对浮躁社会、激进时代的批判,也表达了其对现代生态破坏的深层忧虑。正如学者於可训指出的,迟子建空灵诗意的叙事背后,是内敛有力的现实批判,其独特的自然观念对消解束缚感性生命的现代社会工业理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相较于部分作家直截了当的解构行为,迟子建这种做法显然更加贴合文学本义,更具人文色彩。这一评价,直接指出了《烟火漫卷》中通灵书写最真实的意义。
生命主题的深层书写
迟氏小说始终注重从纷繁生活中看穿人的本质,直面个体欲望,这也是其笔下人物血肉饱满,充满烟火气息的主要原因。最为重要的是,在世俗书写的基础上,她还善于借助人性善恶的复杂性再现真实的人,然后采用救赎的方式让人物向善而行,最终获得精神慰藉,形成独特的“罪与罚”模式,完成生命主题的深层书写。法国批评家让·波德里亚指出,作为社会存在,个体需求是没有限制的,所有生命个体都在释放着内心欲望,并不断追逐新的欲望,特别是在城市景观的隐蔽下,人们任由欲望控制自己,最终带来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灵异化。《烟火漫卷》正是异化人群的人文观照,在人性善恶对立的二元超越中,回到了复杂的人性本身,呈现了最本真的民间生活,如刘建国用余生来赎罪、黄娥的深度忏悔、刘娇华的深层伤痛等,所有人都背负着属于自己的伤痛,并在各自的赎罪中活出生命的本真色彩,这无疑是生命主题深层书写的应有之义。而迟子建在理解之后的关怀,如蒋子丹所言,是一种将自我融入生活的超脱情怀。
作为2020年度最佳长篇作品,《烟火漫卷》受到国内读者的一致好评,及文学评论家的高度认可。
神秘书写下的期待满足
学者褚云侠指出,“神秘”是迟子建小说进入西方文学世界的密码,其超自然现行和原始经验的描写,吸引了西方读者、译者和评论家的关注。2003年,乔伊斯基金会将“悬念句子文学奖”颁给迟子建,并推出小说集《超自然的虚构故事》,由此拉开了西方主动译介迟子建的序幕。在小说集序言中指出,所选小说中的神秘书写所呈现的自然原初经验,是最核心的选取标准。《烟火漫卷》中也有许多神秘书写,如“文武开江”民俗、极乐寺的断佛手、歌剧二人转等,对于西方读者来讲,都是陌生而新奇的中国东北意象。在其海外译本简介中,基本都会强调“中国东北”这一身份标签,以及神秘书写的呈现。细究起来,神秘书写背后的文化逻辑与西方文化神秘尊崇因子相契合,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优越理论形成了某种回应。
小人物书写下的文化共情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小人物,并逐步构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人类学新架构。引领者萨林斯指出,应通过小人物的社会历史来折射整个社会的人文景象。显然,《烟火漫卷》的小人物书写与文化人类学内核思想形成了高度契合,或者说是完成了本源化人文关怀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情感抵达。正如王安忆笔下的弄堂人生,迟子建聚焦城市空间那些平凡的市井小人物,呈现他们独特的生活状态。如其所言,“在我眼里,每个市井人物都像一面多棱镜,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更折射着他们不同的生活侧面。这里有生之艰辛和不平,也有苦中的快乐和诗意”。通过小人物书写,不仅展现了哈尔滨现代化发展中的艰难与欢欣,而且折射了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悲苦与实绩,能够引发最广泛的文化共情。
救赎书写下的原罪契合
救赎始终是迟子建小说的基本主题,《烟火漫卷》也不例外。在她笔下不存在绝对的善,也不存在绝对的恶,人性如同天气一样,复杂多变,但无论如何,人必须要有赎罪感。对自然、对他人、对历史,人们总会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在她的笔下,人物都能够找到自我救赎之路。《烟火漫卷》中偷婴孩的煤老板想要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来补偿刘建国,而刘建国却想要用余生去陪伴吴磊,各自都有着自己的救赎。而救赎是西方文化的构成基因,基督教中的原罪思想,也是西方文学创作的重要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的赎罪书写与西方文化的救赎思想达成了内在契合。
《烟火漫卷》呈现了别样的哈尔滨城市景象,酣畅淋漓地叙写了这座城市的自然更替、人情冷暖、悲欢离合,这其中既有作家浪漫主义的审美追求,也有现实主义的深层书写,在直面生死、善恶的冷峻中,以超脱的姿态表达着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这部小说进一步拓宽了迟子建的叙事空间,在“神秘”书写的本土化与世界化交织中,在“守候大地卑微的生灵”中,成功完成了一次创造、蜕变与升华。
作者系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