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博物学文化的重要意义
刘华杰 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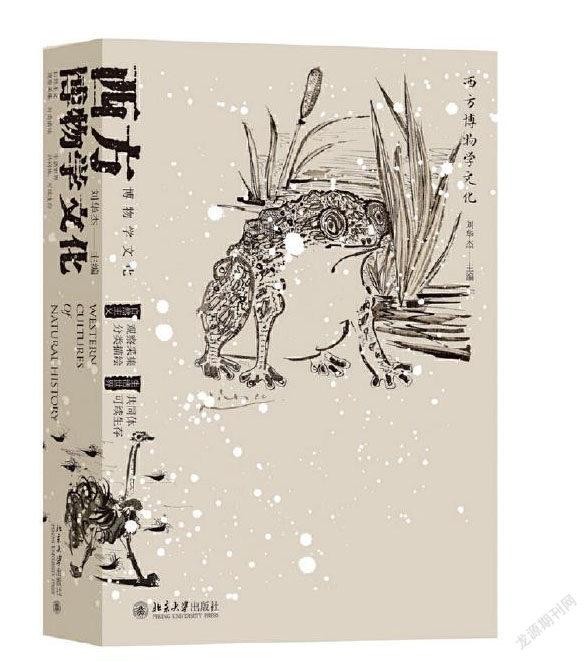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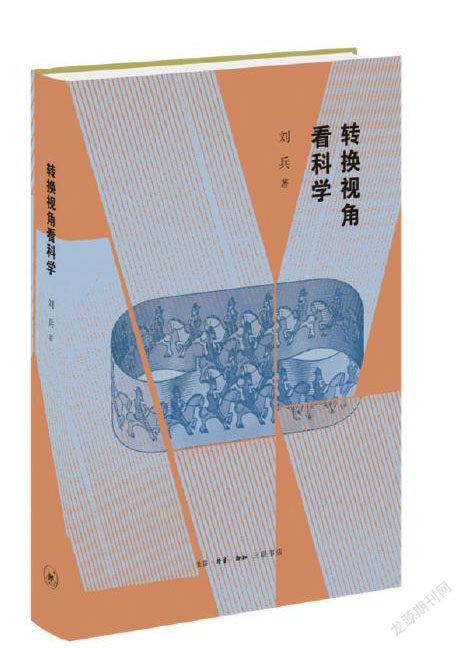
博物学与我们关系密切,博物学涉及到认知。博物学和科学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博物学文化,如何转化人们深层的价值观?
刘华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博物学文化
我们以前曾说梭罗是文学家,利奥波德是林学家,卡森是科学家,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今天要提及他们三人共同的另一身份——博物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博物学文化》,我只是主编,作者一共有20位,包括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书很厚,信息量不小,但并不全面,也不可能全面。考虑到“做增量”,许多重要人物都忽略了。
为什么要写《西方博物学文化》这本书?为什么偏偏看重博物学?现在,人与自然打交道最为密切的就是近代科技,如果不反思近代科技的负面作用,环境问题没法解决。为了当下活得更好,也为了可持续的明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老掉牙的学问,现在课程表没有列出的博物学。博物学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多悠久?至少跟科学的历史不相上下,严格讲比科学的历史还长!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博物学,他本人写过《动物志》等,他的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探究过植物,留下两部植物书,都没有翻译成汉语。老普林尼留下的37册《博物志》,没有任何一本译成了汉语,我不知道清华大学图书馆有没有收藏,希望将来会有中译本。西方博物学家非常多,我按个人喜好列了九个大佬:亚里士多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林奈、布丰、怀特(Gilbert White)、A.洪堡、达尔文、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威尔逊(E.O.Wilson)。
对亚里士多德我打了五星级,给怀特也打了五星,还用红色表示,表示我们极其重视怀特。怀特没有特别了不起的自然科学贡献,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一个名乡村牧师,一辈子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只写了一本书《塞耳彭博物志》。怀特的家乡是典型的英格兰农村,我专门去看过,还小住了几日;达尔文也拜访过他的家乡,为什么?达尔文要向先贤致敬。他是极重要的博物学家,他做的那种类型的博物学,人人可及,是我们今日特别要倡导的。洪堡、达尔文、利奥波德、威尔逊也是科学家,但同时他们也是重要的博物学家。威尔逊的自传就是《博物学家》,中译本译成了《大自然的猎人》。
博物学在今天确是衰落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大学课程一般不讲博物学,但是衰落程度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博物学在正规教育中也衰落了,科研体制中不考虑博物学,但是在社会上博物学依然发达,可以说相当发达。中国要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不会例外,博物学也会得到重视、流行起来,只是迟早问题。
卢梭是哲学家、启蒙作家、教育家,也是博物学家,写过一本书《植物学通信》,我的学生熊姣把它译成了中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歌德是博物学家,通常人们说歌德是诗人,怎么又是博物学家?他写过《植物的变形》,用诗歌体写的,事后看,这也是一部有重要科学创新的作品。他提出了植物学中的一个创新性观点,认为植物的朵是叶连续变形演变的结果,竟然是正确的!他不是基于近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得出此结论的,而是基于多少有点神秘性的博物学方法认识到这一点,也可以称为歌德式方式。梭罗是《瓦尔登湖》的作者,他对种子非常有研究,有人认为他是科学家,梭罗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科学家,甚至瞧不起科学家。他的笔记整理出一本书《野果》,其中讲到:荒野胜于多所哈佛大学。他认为荒野对人有教育意义;哈佛大学很牛,但是教育意义没有荒野大。如果这话是别人说的,有酸葡萄的嫌疑,可是梭罗是哈佛毕业的。法布尔写过十卷本《昆虫记》,是博物学家,他一生有一个“巨大的”愿望:自己有一个不太大的园子,去种金子,发大财?不是,而是让它荒着,让里面昆虫随便生长,他有权利在里面观察它们。法布尔喜爱昆虫,他要了解昆虫,他是个有趣味的人。人有趣味似乎不难,似乎又非常难。很多人非常成功,按现代性的标准非常成功,但是无趣。很多人就是看了法布尔的书成为了科学家、博物学家。“国家公园”的概念谁提出的?博物学家缪尔。缪尔和老罗斯福一起聊天、露营,讨论不要随便开发一些东西,要把一些荒野留給后代。领导人周围的人整天念叨什么东西,显然会影响到领导人的思维、决策,老罗斯福总统本身就是博物学家,喜欢观鸟、狩猎。很多人觉得打猎和生态环保不相容,这要从历史来看,很多优秀的猎人是博物学家,这和现在激进环保主义者考虑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诺贝尔奖获得者梅特林克是博物学家,他提出一个修辞“无用而美好”,我经常引用,用来为博物学辩护。博物学现在就是“无用而美好”,博物学有没有用?有用。
博物涉及到认知。博物和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大致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从属说:博物从属于科学,最终收敛于科学,好的博物就归于科学了。第二种,适当切割说:认为博物与科学各有千秋,但最终价值还要用科学来判定。第三种,平行说:指博物与科学平起平坐,评价标准来自于另一层面。
从平行论角度思考博物学,探究复兴博物学,是有意义的。是否成立,要看大家是否认同,要历史来检验。古代有没有博物学?有,早到什么程度?有科学之前就有博物学。那古代有没有科学?可以说古代有科学,科学史不是一直写到古希腊吗,博物学史也可以写到古希腊,中国可以追溯到先秦。这些历史都是事后建构的。我们这本书《西方博物学文化》也是建构的、编出来,是有文献证据和其他学理根据。研究博物学,是一项长期任务。长远的目标是建构人类文明史,中期目标是重写科技史,近期工作侧重于研究非西方博物学文化,初步尝试西方博物学文化。
从博物角度可以重新思考许多问题。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什么?洋人告诉我们四大发明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从博物学角度看,完全不是这样,那些东西离百姓的生活世界可能还不够紧密。西方所谓的四大发明是针对他们的需要来讲的,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可以是:茶叶、瓷器、蚕丝、豆腐。我觉得这四样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特别重要,而前三者曾经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角,影响巨大。它们是环保的,可持续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博物学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各地都有自己的博物学,现代为何要复兴博物学?是为了让我们生活更加美好,减少折腾。高科技让人们得以快速升级。我们对快速升级可能要有所反省。
中国古代讲“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并不是生一年两年,要长久,可持续。博物学是经过考验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应该丢。恰好我们古代也有丰富的博物文化传统。现在我们能做的第一步是了解西方博物学。为什么我不敢考虑中国的博物学,太难了。中国的博物学太难了,那西方的博物学就容易吗,也不容易,但是西方的博物学研究者较多,框架相对清晰,先把西方的博物学消化一下,获得我们可以利用、参照、比较的框架,回头再做中国的博物学就好办了。博物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是公民成长中需要的一项权利,教育和社会要为实现这种权利提供方便。
刘兵:博物学复兴,需要转变深层的价值观
这些年来,刘华杰老师一直关注博物学,研究博物学,实践博物学,这是很难得的。我本科是在北大念的,辗转来到清华教书,我刚到新斋的时候发现窗外的空地长满了野草,长得非常茂盛,很好看,我们从窗户里看也很舒服,但是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人工种的草人工种的花和树了,其实不少老师都有同感,觉得人工种的草长得不好,还是原来的野草很自然,很茂盛,很舒服,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割掉?这本身是很有意味的问题,类似这种思维模式,有一个类比,可以看到我们经常有那么多人工草坪,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也有一些草坪,局部的,但是在校园里相当多的荒地是长野草的,而在我们这儿是不大被认可的,总是认为那是代表了有问题,一种不发展,是需要被修理修正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重要劳动项目是拔草,为什么要拔草?就是认为长野草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就是一个观念。我们越来越不太认可纯粹天然的欣赏方式,而变成了更加追求一种人工化的、现代化的,一种所谓更高大上的模式,当然这个不同时期不一样。曾经有段时间人们认为最高大上,最现代化的是烟囱林立,后来发现这个有问题。现在就变成了大数据、自动化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逻辑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为什么今天博物学衰落?刘华杰最后讲到了科学和它的关系,当然这个也看怎么理解,更严格来说,刘华杰说的科学更多是近代科学,是跟近代西方科学的关系,当然我也和其他一些朋友倡导,如果我们把科学这个概念泛化,不只是指近代西方科学,我们把人类对自然界各种系统的认识,不同方式,不同范式的都当做不同的、复数形式的科学的话,博物学就进入了一个更宽泛的领域。
当然这也不重要,但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博物学衰落,地方医学比如中医也在衰落,类似很多不符合今天的科学范式的东西都在衰落之中。我们今天讲科学的时候,其实可能背后有一种更深层的动力、观念和价值影响了我们,所以今天科学也不以研究这个为重要的内容,但是有一些少数的、有远见、有眼光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发现这个东西对人们是有利的,对社会发展生活是有利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生活在这种矛盾当中,明明知道很多東西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仍然不可抗拒地、不自觉地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比如我们今天都关心饮食,都知道吃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好,但是我们真正种食品的时候,并没有像说的那样,下大力气种有机食品,反而是拼命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我们心里的追求和我们不自觉被迫的走向,其实选择是有矛盾的。
刘华杰他们做这样的研究,试图让人们发现这种矛盾,找到让我们从心底里,从历史上来说更有意义的其他传统,来对抗现代化的发展。
前几天我们在讨论一本关于创新的书,那本书是谈老科技,严格来讲是老技术。科学不等于创新,今天谈创新特别多,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今天追求的创新,真正能够转换成有用的,能够实现的,能够持续的并不多。而相反很多我们认为过时的产物,反而在我们生活中起的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就是观念的变化。这样一些最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和选择,决定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博物学复兴,呼吁公众参与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没有深层价值观转变,这件事很难做起来。而且还有一个观察,就是说博物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虽然在科学意义上是衰落的,但是在社会层面来说并不衰落,而且很有活力。比如像观鸟、看鲸鱼、植物观察、野外远足等等这样一些活动。
当我们有了钱,我们GDP增长了,我们消费的时候,我们消费主流是出国买奢侈品,而不是到那儿看看鲸鱼,看看鸟这种自然的东西。这种观念背后是什么?还是一个现代化、物质化的资本追求。类似的话,其实在科学史上,爱因斯坦早就讲过,既然今天科学如此发达,为什么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没有同等增长,而变得更加焦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开始意识到绿水青山问题。
西方近些年来,在科学史研究对博物学这样一种传统的关注的转向是非常鲜明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但我们这儿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这本身也是有意味的,科学史算是人文研究的领域,但是在人文领域,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问题,比如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我们更多的人文学者更像经济学家,是以赞成的、促进的、支持的态度来讨论现代化,讨论全球化问题,生怕它发展的太慢。
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一些博物类图书也有所兴起,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也开始转向注重博物的生活方式,这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但是我绝不认为这是很乐观的。比如刘华杰作为博物学家,他身体挺好的,他没事去爬山,去看花看草,要走路,但是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健身,那些人健身更多是到健身房里,用现代化器械,而不是到自然中按照天然的方式健身。目前,人们在观念和价值上有很多冲突。所以我们愿意在博物学传播和倡导上做更多工作,虽然很难,但很有意义。
作者刘华杰系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冰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博物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刘华杰;《转换视角看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作者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