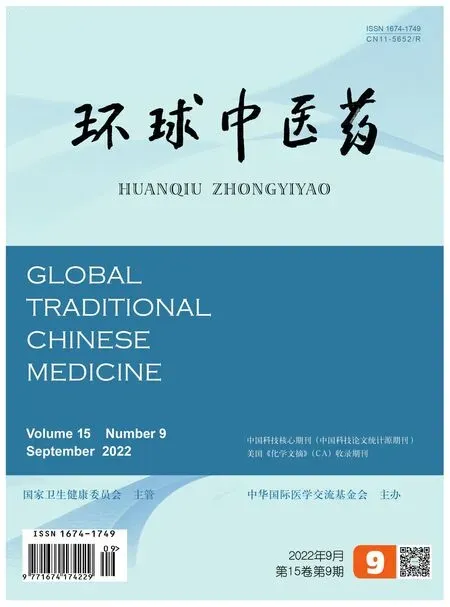杜雨茂教授疏达少阳法治疗肾病验案心得
陈新海 步凡 李世梅
1 病案摘要
患者,男,40岁。2000年10月9日初诊。主诉:全身浮肿3月余。患者3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全身浮肿,尿少困乏,在当地医院治疗1周,病情加重,遂转入西安某三甲医院。尿检:蛋白(+++++),隐血(++++),红细胞(++),白细胞(+)。血检:血清总蛋白37.30 g/L,白蛋白26.13 g/L,甘油三酯3.27 mmol/L,肾功诸指标在正常范围。肾图示:双肾功能中度受损,肾小球滤过功能降低。肾穿病理报告: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IgM肾病。入院后第1周给予环磷酰胺冲击,口服泼尼松、贝那普利、双嘧达膜等效不显。至第3周临床症状加重,查肾功:血肌酐239 umol/L,尿素氮15.3 mmol/L,患者出院而来求治。
刻诊:全身浮肿,按之凹陷难起。神疲乏力,梦多眠差,心慌,语音低沉,口干口苦,偏头痛,恶心厌食,左脚根部疼痛,痛甚时向腘窝处放射,四肢时有颤抖,小便不利,夜尿2~3次。望其舌体胖大、舌质紫暗,舌苔微黄腻;切脉左弦右滑而数、尺部沉细。西医诊断:肾病综合征;肾功能不全。中医辨病:水肿;关格证。辨证:湿热浊瘀蕴滞少阳,太阴少阴亏损。治法:利湿泄浊化瘀疏达少阳,扶太阴益少阴固摄精微。处方:桑寄生35 g、怀牛膝15 g、续断15 g、鹿衔草25 g、山萸肉15 g、丹参15 g、姜远志12 g、猪苓12 g、车前草15 g、生大黄后下4 g、茵陈10 g、酒黄芩12 g、桔梗10 g、炒枳壳10 g、西洋参7 g、生白术10 g、茯苓15 g、炒杏仁10 g。21剂,日1剂,水煎至400 mL,分早晚温服。金水宝胶囊4盒,3粒/次,3次/日。
2000年10月31日复诊:服上药3周后浮肿减轻,食欲增加,精神好转。查舌淡红苔白腻,脉滑微数右尺部浮芤。尿检:蛋白(+++),隐血(++),血检:总蛋白56.81 g/L,白蛋白35.92 g/L。肾功指标正常。
治拟:扶太阴(脾、肺)以防少阳(三焦、胆)达邪伤正,固少阴(心、肾)以涩精安神。处方:丹皮12 g、虎杖15 g、地龙15 g、土茯苓25 g、生白术12 g、生薏仁30 g、太子参15 g、生黄芪45 g、芡实30 g、金樱子12 g、毕澄茄6 g、女贞子12 g、夜交藤25 g、天冬10 g、生大黄后下6 g、覆盆子6 g。14剂,日1剂,水煎两次取汁400 mL,分早晚温服。继服金水宝胶囊。
后多次来诊,坚持二诊治法,随证化裁一年余,复查各项检验正常,身体无其他不适。又巩固治疗3月停药。停药后患者遇感冒或劳累时,偶见蛋白尿(少量),余无异常。经建议又服药巩固1年余停药。2005年4月12日、2007年10月16日随访,患者无不适,化验检查均正常。
2 讨论
2.1 慢性肾病常现六经合病、并病
仲景在六经辨证之外又提出了合病、并病理论,以此来贯通六经并弥补六经的不足[1]。《伤寒论》直接论及合病与并病的条文有12条,但只见于三阳经之间。若局限于《伤寒论》的字面结构也就局限了临床辨证。临证中的合病并病是复杂证候,从疾病临床演变角度看,阳经、阴经以及阴阳经之间都有合病、并病。
杜老学贯伤寒法六经,活用经方治肾病,认为《伤寒论》316条就属阴阳合病(太阳与少阴),只是没有明显标示而已,并主张“肾脏常见疾病治从六经入手”观点,且提出肾脏病六经辨证论治体系[2]。
该患者三焦不畅,湿邪浸渍,筋脉失养则水肿、肢颤;气血不利则舌紫暗;胆热郁而上达则头昏偏痛,中犯胃气则口苦恶心;此为少阳(三焦、胆)经病变。
土不生金,肺气不足则语声低沉而少气、神疲乏力;火不助土,脾失运化,则厌食纳差、腹胀;此属太阴(脾、肺)经病变。
肾气亏虚,失于温摄则小便不利、夜尿次多、尺部脉沉细、足跟痛;水不济火,心神浮越,则眠差心悸;这些则属少阴(心、肾)经病变。
故该病案杜老辨证为少阳、太阴、少阴合病。
2.2 六经传变有手足,背反偕同当遵守
六经病机清楚了,如何遣方用药又是下一步的关键。杜师生前教诲学生临证要“善抓主证,直中肯綮”。主证是疾病的主要方面,主证消,可能疾病的次要症状也会迎刃而解;但也可能在复杂的病证中的某一次证上升为主证,需继续治疗[3]。当然,抓主证是正确辨证的第一步,这只是整个治疗过程的开始,紧接着组方用药又成为关键,如治疗太少合病,不能将太阳病麻黄汤方加上少阴病四逆汤方来治疗,这样机械相加临床效果差,甚至适得其反。何哉?病机有主次轻重,用药有君臣佐使,与辨病机同等重要的是用药契机。
该患者合病并病虽复杂,疏达少阳是关键。本病案初诊以畅达少阳为主,固护少阴为辅。以桑寄生、怀牛膝、川断、山萸肉、丹参、远志益少阴(心、肾);猪苓、泽泻、车前子、大黄、茵陈、黄芩、桔梗、炒枳壳畅达少阳(三焦、胆);西洋参、生白术、茯苓、杏仁扶太阴(肺、脾)。三经并调,下元得生,精微自固。二诊以固护少阴为主,疏达少阳为辅。以丹皮、桑寄生、土茯苓、虎杖、酒大黄、地龙调和少阳(三焦、胆);太子参、生黄芪、生白术、茯苓、薏仁护太阴(肺、脾)以防伤正;芡实、金樱子、毕澄茄、生地、女贞子、夜交藤、天冬等济和少阴(心、肾)以固精安神。这正是脉证分主次、方药随证变、用药兼手足的具体体现。
仲景对合病并病的治疗原则:合病治疗应分清主次,并病治疗应遵循先表后里、先外后内、先急后缓的原则。杜师医案也正体现出此治疗原则,同时也启迪笔者在临床上精研仲景及杜师原著,以六经辨证为纲,谨辨并病、合病,进而提高六经辨治肾病及疑难杂症之疗效。
3 杜老治肾病用药思想特色
杜雨茂教授系原陕西中医学院副院长,首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陕西省名老中医、伤寒大家。杜老有关六经治肾病的学术思想,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已多有探析[4-10]。本文只对杜老的用药学术思想特色的新认知谈及一二,以就正于同道。
3.1 巧用活血之品通达少阳之气
杜师医案中常配伍活血化瘀之品,杜老认为活血化瘀药有保肝利胆、畅达三焦之功,属治少阳病范畴。仲景治妇人热入血室的治法,提出服小柴胡汤和刺期门二法。后世医家仅用小柴胡汤加活血化瘀之品获效亦显。这是对仲景思想继承与发展的例证,如果再结合杜师病案的用药思想,正是治疗少阳病的珠联璧合,是继承与发展的又一深层次的例证。具体用药前医案已有分析。
医案中重用桑寄生,这是杜老的经验用药。杜老曾强调桑寄生可畅达三焦而利水,为少阳药;又有益肾安脉之功,是少阴(心、肾)之良药,治少阴少阳并病不可或缺,善用该药可收一药多效之功。
3.2 守仲景之法用同效之药
杜雨茂教授宗六经之法,活用经方多效组方之则而鲜用经方之药,法指挥药,药彰显法;或法常而药变,或药味同而法已变,得心应手,屡起沉疴。
纵观本案用药特点:手经与足经兼顾、滋阴与燥湿并用、温阳与寒消相使,补泻相济、升降结合、药虽背反,但异曲同工,可达协同,正是杜雨茂教授“背反谐同”[11]学术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本案少阳病方药的组合而言,杜老或理气或活血、或温化或寒下、或祛风或通络、或利湿或甘润,其用药更显出神入化[10]。
再研杜老医案,新悟出诸多“用其法不用其药”的临床用药思路,如益少阴用远志伍天冬,或生地伍菖蒲等;补太阴用黄芪伍西洋参,或扁豆伍桔梗等;调厥阴用吴茱萸伍黄连,或苏叶伍黄连等。从药性而言,寒热相济,润燥相伍,相反相济、背反偕同。诸药对多相替换而少相叠加,有汤新效著,药精力专之妙。
3.3 杜老六经手足兼顾用药思想探源
宋代医家朱肱著《类证活人书》为《伤寒论》六经经络学说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医家的六经脏腑学说影响很大,但他却提出了伤寒“传足不传手”的论点,后世多有附议。如匡武[12]认为“伤寒足经症状多而手经症状少”的现象不仅与邪气性质相关,也跟经脉循行、气化升降理论相合,当尊此论。也有持异议者,如封鑫宇[13]认为六经传变并非“传足不传手”,而是由于早期经络理论重视足六经,且足经在人体分布范围广泛,因此详于足经症状,或以足经症状代替手经症状。
杜雨茂教授认为《伤寒论》六经病证是由《素问·热论篇》六经分证发展而来,《素问·热论篇》无手经证候,故《伤寒论》六经病证多从足经论述。但继承之中又有发展,从《伤寒论》六经病证的具体内容来看,各经病中均有手经病证的端倪。因此,杜老强调伤寒袭人是通体病,既传足也传手[14]。
少阴病篇提纲曰“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显然,少阴病传足(肾)也传手(心)也。少阴病篇多处提及“心烦”“心烦不得眠”及“烦躁欲死”等症状,这些都是传手的例证,对临床用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本病案中主要涉及少阳、太阴、少阴三经病证。无论何经用药,杜老均手足并治。不仅本案如此,笔者发现杜师的其他诸多医案中亦如此。这一点给笔者临证用药带来了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