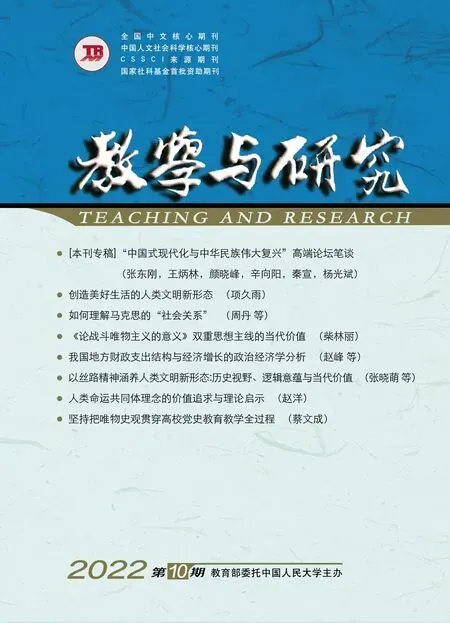背叛者还是创新者:透过鲍尔斯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高 岭,唐昱茵,卢 荻
一、引 言
从1968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URPE)正式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于1969年刊发论文(Wachtel,2018)(1)H.M.Wachtel,“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t Its Half Century: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8, 50(3): 487-503.算起,激进政治经济学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在这50余年的发展史中,鲍尔斯(Samuel Bowles)是一位值得特别关注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一方面,鲍尔斯是为数不多的既能够在诸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wnomics)和《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等主流经济学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又能够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和《剑桥经济学报》(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等异端经济学顶级刊物发表论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鲍尔斯的学术生涯见证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全过程,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纵观鲍尔斯的学术生涯,他从批判教育学切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了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的跨学科研究。然而,这种转向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放弃,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了一种特定的、不同于作为行为公共选择理论衍生物的“行为政治经济学”。(2)关于行为政治经济学的评述,参见汤吉军、戚振宇:《行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2期;高岭、卢荻:《政治经济学在思想史中的嬗变——政治、经济、心理由分化向融合的复归》,《经济学家》2018年第10期; J. Schnellenbach and C. Schubert, “Behavioral Political Economy: A Surve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5, 40(B): 395-417.
鲍尔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均有深刻的反思。(3)S. Bowles and W. Carlin, “What Students Learn in Economics 101: Time for A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20, 58(1): 176-214.在这一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鲍尔斯的学术影响力逐渐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甚至其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领域也获得了高度肯定。(4)[美]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与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一个关于其学术影响力的例证是,鲍尔斯在转向行为科学研究后,其研究在《自然》(Nature)和《理论生物学》(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等顶级自然科学刊物也有发表。鲍尔斯的学术历程不仅贯穿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还为激进政治经济学向行为科学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路径。特别是,鲍尔斯致力于开拓的“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代表了众多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研究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历程不仅能够明确其对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立场,还能够透过其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和突破,为创新中国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思想素材。
回顾现有研究,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理论贡献和研究成果异常卓著的鲍尔斯都没有赢得与其学术成就相称的关注。为纪念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立50周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于2018年出了一个特刊:“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Radical Economics: URPE at Fifty”。然而,让人十分意外的是整个专刊并没有提及萨缪尔·鲍尔斯的名字,其研究也没有入选论文精选集“The Influence of 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Insights on Selected Key Articles”。(5)Schroeder and K. Susan, “The Influence of 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Insights on Selected Key Articl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8, 50(3): 549-575.事实上,不仅2018年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的专刊没有提及鲍尔斯,韦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在2014年《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一文中,以及在纪念戈登(David Gordon)对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SSA)的贡献的演讲中,也没有提及作为戈登的合作者的鲍尔斯。(6)④ T. E. Weisskopf,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46(4): 437-447.就国内相关研究来看,CNKI的检索结果显示,截至目前,关于鲍尔斯著述的中文评论只有12篇,且其中6篇的主题是关于鲍尔斯的批判教育学学术成果(7)杜亮:《鲍尔斯和金蒂斯教育思想探析:“对应原理”及其批判》,《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8期;漆明春:《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公平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以鲍尔斯、金蒂斯为例》,《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贺晓星:《论教育社会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S.鲍尔斯和H.吉丁斯的对应理论及其转向》,《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章敏:《简论塞缪尔·鲍尔斯经济再生产观对美国资本主义教育系统的影响》,《文教资料》2016年第18期;章敏:《简论鲍尔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与教育结构的“符应”观》,《时代教育》2017年第15期;章敏:《简论鲍尔斯关于美国学校教育文化研究视角的转向理论》,《教育现代化》2017年第46期。,仅有5篇是对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述的评述和介绍。(8)王晴、孙珍:《美刊载文谈鲍尔斯反对总和为零的传统理论》,《经济学动态》1984年第5期;杨玉生:《马克思、瓦尔拉斯和新霍布斯主义生产过程模型比较——萨缪尔·鲍尔斯经济理论观点评介》,《当代经济 研究》2006年第11期;赵峰:《激进学派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任保平:《对真实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解读——读鲍尔斯等人的〈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张衔、王洪东:《鲍尔斯对“护卫劳动”的研究及启示》,《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4期。本文所关注的后一类经济学文献无一例外地只是对鲍尔斯某一论文或著作进行的评介,因此,国内基本不存在对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的系统梳理,更谈不上对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路径进行理论审视。
作为激进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学术特色鲜明、成果丰硕的代表性学者,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贡献在理论界缺少深入的讨论和研究,这既不利于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同仁的交流和互动。事实上,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繁荣期不足10年,衰落和收缩才是50年来的主旋律。(9)① T. E. Weisskopf,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46(4): 437-447.在高光时刻,激进政治经济学刚起步就受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关注(10)H. M. Wachtel,“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t Its Half Century: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8, 50(3):487-503.,《经济学文献》(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早在1970年就发表了一篇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综述文章(11)M. Bronfenbrenner, “Radical Economics in America: A 1970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0, 8(3): 747-766.,但而后作为整体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就再也没有受到《经济学文献》的关注,独有鲍尔斯的研究还能发表在这个重点刊发经济学前沿的期刊上,这足以说明鲍尔斯在激进政治经济学中的超凡位置。不论是要为衰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注入强心剂,还是旨在加深国内学者对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贡献的认识,我们认为都需要对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生涯进行回顾。
本文试图基于鲍尔斯从1970到2020年间发表的所有马克思经济学及相关论文,对鲍尔斯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发展轨迹进行勾勒,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鲍尔斯的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并为他的学术转向提供了一种解释。具体来说,本文将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1975至1981年的转型期;(2)1982至1989年的理论成型期;(3)1990年至今的理论拓展期。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系统梳理了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起源、发展和成熟过程,全面展现了鲍尔斯的理论图景及其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第二,本文对鲍尔斯“放弃”劳动价值论和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科学研究转向进行了逻辑一致的解释;第三,本文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思想风暴”:“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会损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理论穿透力。
二、经济学研究转型期:1975至1981年
即使撇开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12)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由戈登(David Gordon)、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和赖希(Michael Reich)三位学者于1982年首先正式提出,如今在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光环,鲍尔斯身上也还有一枚耀眼的“勋章”,即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在1975年之前,鲍尔斯和他的终生好友兼合作者——金蒂斯(Herbert Gintis)主要活跃在批判教育学领域。批判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批判教育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流派,它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用阶级分析以及辩证思维的方式把教育问题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等结合起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13)徐玲:《批判教育学的新主题:世界主义及其理性的研究——以托马斯·波克维茨为例》,《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原本,作为教育学的批判教育学和作为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会有交集。正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使批判教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了共同的对话(批判)对象。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通常对由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的科学性持一种批判的观点。(14)李连波、谢富胜:《马克思有人力资本理论吗?——与顾婷婷、杨德才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而后来自我定位为“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15)“后马克思主义”通常是指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莫菲(Chantal Mouffe)开创的,对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进行了相当大的延伸和修订的流派。关于“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理论究竟是发展还是背离并无定论。参见R. D. Wolff and S. Cullenberg, “Marxism and Post-Marxism”, Social Text, 1986, (15): 126-135; E. Laclau and C.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New Left Review, 1987, (166): 79-106; J. Robinson, “Post-Marxism with Apologies?”, Theoria: 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1991, (78): 159-171.经济学者的鲍尔斯,同样对人力资本理论持否定态度,而体现这种否定态度的代表性研究是其于197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下简称《人力资本理论的问题》)一文。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理论的问题》一文值得关注的论点有以下两个:其一,学校教育既可能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学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例如它既能通过影响雇佣劳动力体系的扩展与再生产来影响经济增长,又能通过对阶级冲突的缓和从而改变资本积累率来影响增长;其二,收入分配的基本规则很可能与人力资源差异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特征直接相关,这一结构性特征受到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和其他群体的相对权力的影响。这些论点并不是鲍尔斯和金蒂斯的主观臆测,而是基于两人在批判教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所列出的事实。从这两个论点不难看出,鲍尔斯并不赞同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年限和未来收入直接挂钩的做法,认为人力资本的理论视角只是“通过从社会生产关系和学校教育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作用中抽象出来……分析教育决策提出的一个单维规范性框架”(16)S. Bowles and H. Gintis, “The Problem with Human Capital Theory—A Marxian Critiqu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5, 65(7): 74-82.。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学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一部分,在学校教育中阶级间、种族间、性别间的经济不平等被合法化或者说被再生产出来,所以,实际上是收入结构决定了人力资源的配置,而不是人力资源的配置决定了收入结构。
在《人力资本理论的问题》一文中,鲍尔斯有意或无意地借鉴了马克思对劳动与劳动力概念的区分,而对劳动和劳动力认识的系统化梳理和展开则是鲍尔斯在由教育学向经济学过渡的转型期中另外两篇论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并不限于教育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更为深远,这篇论文可看作是鲍尔斯第一次正式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经济学理论进行对话。经济学的旗舰期刊《美国经济评论》能刊载此文,也能表明这是一篇经济学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并不是鲍尔斯从批判教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标志。事实上,在1975年这篇论文基础上,鲍尔斯和金蒂斯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教育学研究,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 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一书。这本书把学校教育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17)D. Cohen and B. Rosenberg, “Functions and Fantasies: Understanding Schools in Capitalist America”,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77, 17(2): 113-137.,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和阶级理论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和传统功能主义社会学视角的学校教育分析,驳斥了“民主主义学派”(Democratic School)和“技术功绩主义学派”(Technocratic-Meritocratic School)关于教育的统合、平等化和发展等三大职能合一论,认为资本主义教育本身内生于(对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会极大地受到社会阶级背景和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学校本身成了制造“不平等”的场所。在现存制度下,运用社会主义教育策略有可能实现教育改革和资本主义制度改革的双重目标。(18)S. Bowles and H.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Basic, 1976.
从鲍尔斯对美国学校教育实质的审视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反思中,能够发现鲍尔斯并不认为学校教育是简单劳动转换为复杂劳动的培训过程,或者说他认为这种转换在工资差异上的体现微乎其微。沿着这一思路出发,鲍尔斯和金蒂斯于1977年在《剑桥经济学报》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异质劳动:批判与重构》一文,从异质劳动这一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进行了“重构”。我们认为,这篇论文可以视为鲍尔斯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志。或者说,鲍尔斯对批判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的探寻促使其回归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研究。但是,鲍尔斯的回归并不是直接接受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论,相反,鲍尔斯想要在批判马克思的基础上实现对“劳动价值论”的重构。
在经典的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对不同劳动的抽象处理方式是将其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抽象为同质的劳动,复杂劳动也被还原为数倍的简单劳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页。鲍尔斯则在这篇论文中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一处理方式无法揭示更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相反趋势:工人阶级内部基于种族、性别、国籍、民族、教育和生产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的分化持续存在。(20)S. Bowles and H. Gintis,“The Marxian Theory of Value and Hetero-geneous Labour: A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 11(2): 173-192.
为在劳动价值论框架下解释这一趋势,这篇论文构建了一个给定工资束的异质劳动线性生产函数,在该模型中各种劳动不再还原为一种元素,而是以向量的形式表示它们的异质性,并且不同劳动可以有不同的剥削率——甚至可以为负。(21)当某类劳动剥削率为负时,相当于某类劳动与资本分享剩余价值,或者说是在剥削其他劳动。但在计算剥削率和利润率时,鲍尔斯又把这些劳动时间简单加总了,不过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说明存在异质性劳动或劳动间存在剥削关系时,将不同形式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所得到的基本命题也能够成立。这一观点与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多重剥削”概念有相近之处,即认为某些劳动者也可以成为剥削者,他们依靠不同类型的“资本”来获取剩余产品。(22)参见E. O. Wright,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 Society, 1984, 13(4): 383-423; [美]乔纳森·H.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60-161页。鲍尔斯声称,这种将劳动间剥削带入到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价值论发展方向,可以系统地分析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剩余价值的榨取过程,并且能使得理论与实际的劳动过程在性质上相符。
如果说这篇论文是鲍尔斯突破传统劳动价值论的第一步,那么,四年后他和金蒂斯共同发表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的《劳动价值论的结构与实践》则标志着鲍尔斯重构的劳动价值论的最终成形。(23)④⑤⑥ 参见H. Gintis and S. Bowle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1, 12(4): 1-26.这篇论文的结论奠定了鲍尔斯的劳动价值论立场,并且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撰写论文专门对劳动价值论进行讨论。
要全面理解这篇论文的思想内涵,还需要对这篇论文创作背景有所了解。1977年,英国斯拉法学派经济学家斯蒂德曼(Lan Steedman)在《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中,利用斯拉法生产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诘难。斯蒂德曼在书中证明,利润率独立于投入品和劳动的价值,由生产技术和实际工资水平所决定。除此之外,他还在书中给出了存在固定资本时,机器折旧的价值量为负、联合生产时商品价值为负等例子。基于书中的证明,斯蒂德曼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多余且错误的。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既然马克思的各种劳动量完全是以物质形式表现的实际工资和生产条件的衍生物, 而这些物质的量本身足以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 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 对于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决定来说, 劳动时间量是没有意义的。”(24)[英]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126、138页。
鲍尔斯在这篇论文中多次对所谓“斯蒂德曼诘难”进行了回应。鲍尔斯明确指出:“近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斯拉法经济学家批评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文认为,对劳动价值论的通常表述和辩护确实是错误的,但是劳动价值论本身却是必不可少的。”(25)②⑤⑥ 参见H. Gintis and S. Bowle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1, 12(4): 1-26.不过,鲍尔斯对作为斯拉法经济学家族一员的斯蒂德曼则持赞赏的态度,认为“斯蒂德曼非常正确地指出,如果利润率是由生产矩阵、工资束和劳动投入向量决定的,那么,就不需要求助于价值范畴来推导价格和利润——只要我们有关于利润的这些直接决定因素的社会决定的充分理论”(26)②④⑥ 参见H. Gintis and S. Bowle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1, 12(4): 1-26.。由此可见,一方面,鲍尔斯和斯蒂德曼的立场一致,对劳动价值论采取消极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不可放弃的。那这两个对立观点如何在理论上逻辑自洽?鲍尔斯的处理方式是“清除该理论的经济学基础,从而增强其逻辑上的一致性,增强其揭示先进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动态特征的能力,并提高其与当代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总体相容性”(27)②④⑤ 参见H. Gintis and S. Bowle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1, 12(4): 1-26.。
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鲍尔斯是想要对劳动价值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重构。而进行这种重构并不单单是为了回应斯蒂德曼诘难,而是要改变以劳动价值论为核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主义”(Economism)倾向。这里的“经济主义”是指把社会结构中所有非经济事实简单地还原到经济层面,即将所有事件视作经济的反映和衍生产物——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决定论”。而劳动价值论就是经济主义的,“通过把政治和文化实践从经济的内部构成中剔除,它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场所缩小到各种实践活动的一个有限的并且实际上是贫困的子集上,但明明是这些实践活动共同决定着资本积累的动力。”(28)H. Gintis and S. Bowle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1, 12(4): 1-26.
金蒂斯和鲍尔斯对劳动价值论的重构是从四个经过严格证明的命题开始的:1.如果工资率为正,那么劳动就不是经济中唯一的基本要素(即价值度量);2.任何能作为基本要素的商品都可以作为价值论的一致基础(29)一种商品当且仅当被直接或间接作为实际生产投入时才能成为基本要素。;3.任何市场化的商品生产投入,若其增殖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场所之外,则价格方程形式可能与劳动力的价格方程形式相同;4.任何基础资源都可以被视为价值理论的合理基础。这四个命题可推导出鲍尔斯所谓的“花生价值论”(30)花生是一种比喻,泛指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品。和“能源价值论”(31)能源符合命题4中关于“基础资源”的定义。。基于这一精心构造的反驳与其在文章中指出的将劳动力视作商品所带来的其他问题,鲍尔斯进一步指出,将劳动力视作商品不能坚持劳动价值论——即便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同样的逻辑也支持“花生价值论”和“能源价值论”,从而无法论证劳动的独特性。由此,鲍尔斯提出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视为占有、政治、文化和分配实践的集合体,而不再视作一种决定产品价格的客观存在。此时的“劳动价值论”唯一的作用,就是将所有社会实践场所连接起来,同时也在劳动过程中引入了阶级冲突。这里的“实践”与所谓的“结构”是对立统一的,即作为经济主体互动方式的实践以能动的方式在塑造着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实践的范围和方式。
到这篇论文成文为止,可以说鲍尔斯从批判教育学向马克思经济学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了。在转型期中,鲍尔斯从其在批判教育学领域中深耕所得研究结论出发,重新审视了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硬核的劳动价值论,并对其进行了重构。在完成这一基础理论的重构之后,鲍尔斯就将研究重心转到了建立和发展自己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上了。
三、理论成型期:1982至1989年
这一时期鲍尔斯写作和参与写作的论文主要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关注微观的劳动过程以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劳动榨取函数,并最终发展为一个纳入劳动纪律的宏观经济模型;其二则是对宏观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相关理论(SSA)及其应用的发展。这两个努力方向并不完全独立,具体表现在前者的研究结论部分嵌入了后者的理论中。许多学者一提到鲍尔斯总想到他在SSA上的贡献,但事实证明SSA只是鲍尔斯在理论成型期的一个重点努力方向而已,真正延续到理论拓展期,并且与近年来鲍尔斯的研究息息相关的,还是前一种努力方向——这将在后文予以说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鲍尔斯有一篇论文比较特殊,它不从属于上述两个方向中的任意一个,而是鲍尔斯对自己的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总结,可以说这篇论文的思想概括了这一时期他的两个研究方向。纵览本文所考察的发文时期,鲍尔斯专门撰写学术论文阐释自己的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论文仅此一篇;而从内容上看,笔者认为这篇论文是把握鲍尔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关键“钥匙”。因此在对这一时期鲍尔斯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之前,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他在这篇论文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
该篇论文名为《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学习与历史》(以下简称《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于1985年发表于《社会科学信息》。鲍尔斯在该文中声称自己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为“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一学派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着重大区别:其一,为克服传统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与政治、文化理论割裂发展的情形,再考虑到“斯蒂德曼诘难”中表现出的劳动价值论的一系列缺陷而放弃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其二,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致力于探索并用数学手段表达行为人行动的微观基础,并从微观基础中发掘出不同阶级或群体行动导致的宏观后果;其三,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劳动榨取过程,而这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缺失的部分,因为后者仅将劳动力视作一个自带给定劳动投入水平(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工资束(劳动力价值的物化)的商品;其四,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实践和结构”这一对概念取代“内生和外生”这一对概念,实践即行为人基于目标和约束所做出的行动(进行着劳动),而所谓结构就是这些行为促成的宏观后果,实践无法完全还原到结构上,正如结构也无法完全还原到实践上一样,实践不断侵蚀旧的生成新的——即再生产资本积累所需的结构,而结构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定着实践的场所和进行方式;其五,实践既是物质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再生产活动,个人的偏好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延续或是发生变化,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时间是不可逆的。(32)S. Bowles,“Post-Marxian Economics: Labour, Learning and Histor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5, 24(3): 507-528.
本文认为,鲍尔斯在理论成型期的两个理论发展方向与他的“实践和结构”的二分概念是对应的。第一个方向关注微观的劳动榨取过程,而这在本质上就是受结构影响的实践;第二个方向则明显是关注表达无数个人和集体实践所促生的宏观结果——积累的社会结构。
(一)第一个理论发展方向:劳动榨取模型
金蒂斯和鲍尔斯于1982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福利国家与长期经济增长:马克思的、新古典的和凯恩斯的方法》一文围绕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结合以劳动榨取为核心的劳动过程探讨了相应的经济后果,是鲍尔斯对劳动榨取理论思想的首次阐释。有趣的是,这一思想很可能最初源于他的好友金蒂斯。(33)H. Gintis, “The Nature of Labor Exchange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6, 8(2): 36-54.
不过,劳动榨取的建模工作是鲍尔斯在3年后独立完成的。在同样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竞争经济中的生产过程:瓦尔拉斯、新霍布斯与马克思模型》一文中,鲍尔斯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劳动榨取模型”,这一模型具备微观基础,即资本家和工人分别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可以采用提高工资水平和加大监管力度以及分化工人三种手段来榨取工人的实际劳动投入。具体而言,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会提高工人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的监管力度会提高工人偷懒被发现的概率,工人团结程度的降低会提高工人偷懒被发现的概率——这三种措施都会通过影响工人的效用水平从而促使其选择更高的实际劳动投入。(34)③S. Bowl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1): 16-36.
这一模型给出了四个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产业后备军的持续存在、生产关系对最优技术选择的阻碍、工人内部无关实际贡献的收入分化以及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由于所有企业都会设定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因而劳动力市场上会存在持续的非自愿失业;因为提高物料投入量可以提高工人偷懒被发现的概率,所以相应要素的边际产出不会等于其边际成本;由于偷懒被发现概率是工人团结的减函数,因而选择工资结构分化工人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可以提高工人的预期收入,所以在企业内部建立它能起到加强榨取的作用。(35)④S. Bowl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1): 16-36.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鲍尔斯在开篇就提到,这个理论模型的成立与否是完全独立于劳动价值论的,这与他在《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文中表达的对劳动价值论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使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来确定价格、工资和利润同时也被证明出来是不必要的。从纯粹的形式上看,投入和产出可以用劳动时间、每蒲式耳的玉米或每吨钢来衡量;采用何种衡量单位并不会影响用数学推导出的重要结论。因此,劳动价值理论……是多余的”(36)S. Bowles,“Post-Marxian Economics: Labour, Learning and Histor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5, 24(3): 507-528.。
在针对失业损失对罢工水平的影响对劳动榨取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37)失业损失,即就业时税后收入水平与待业时收入水平之差。(38)J. B. Schor and S. Bowles, “Employment R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Strik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7, 69(4): 584-592.,这一理论模型在鲍尔斯和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博耶(Robert Boyer)于1988年合著并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劳动纪律与总需求: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一文中走向了完备。这篇论文中发展的宏观经济模型实际上是两种理论的结合:劳动榨取模型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所表现的是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的封闭经济,雇员根据工资选择消费水平,雇主根据利润选择投资水平,政府根据失业水平发放失业救济金——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总需求。收入分配通过其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成为总需求的关键决定因素,而收入分配又是关于工作时间和工作薪酬的阶级冲突的结果。其中,阶级力量的均衡位置取决于就业水平,从而最终取决于总需求水平。通过对工人和雇主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政府的救济金发放水平将影响私人收入的分配,并且本身也会直接影响总需求水平。(39)S. Bowles and R. Boyer,“Labor Discipline and Aggregate Demand: a Macroeconomic Mode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2): 395-400.
这一模型通过打破萨伊定理和将劳动力视作商品的惯例,成功将总需求内生化,并将阶级冲突引入了生产场所。除此之外,这一理论结合还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首先,工资率变动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业水平的反向变动,还存在两者同向变动的可能,这种状态下的经济被称为工资引导型(Wage-led)经济;其次,工资率的提高如果导致就业水平的下降,那么这种状态下的经济就被称为利润引导型(Profit-led)经济,意为利润率水平和就业水平同向变动。而工资率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超额需求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就业水平。因此,超额需求对工资的导数和就业水平对超额需求的导数共同决定着经济体究竟处于工资引导型状态还是利润引导型状态。
除了对劳动榨取模型进行精细化和形式化发展之外,鲍尔斯还从劳动榨取这一过程所揭示的劳动力市场交易的特殊性质中总结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竞争性交换(Contested Exchange)。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鲍尔斯和金蒂斯于1988年合作并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竞争性交换: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一文中。文中对竞争性交换给出的定义是:“当交换的商品的某些方面具有对买方有价值的属性,并且提供这种属性需要耗费成本,同时这一属性还难以被衡量或是不受确定的合约规范约束时,这种交换即为有竞争性的交换。”(40)S. Bowles and H.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2): 145-150.
竞争性交换的典型例子是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在这两个市场的交易中存在着一种“事后”的交易,例如劳动力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后才提供劳动,而借款人也是在订立借款协议后才决定贷款的投资去向——而劳动力在付出真实工作努力和借款人在选择投资去向上与雇主和贷款人存在着利益冲突,雇主和贷款人又难以准确衡量或用成文合约条款对实际工作努力和投资去向进行严格限制。因此,这种事后的交换是由买方为诱导卖方做出合乎买方本意行为而建立的监督、制裁和激励机制决定的。而这种竞争性交换的存在正是理解经济体中政治结构的重要切入点,因为“在竞争性交换中,这些内生的执行竞争性权利主张的制度可以被视为经济中的政治结构要素。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因为国家垄断了合法的人身控制权,所以经济行为人可用于内生执行合同的工具被严格限定了。在这些工具中,‘相机续约’(Contingent Renewal)处于核心地位:买方通过承诺只在对卖方的表现感到满意时才续约,来诱使卖方遵守合同。”(41)S. Bowles and H.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2): 145-150.(42)所谓内生执行,即需要交易中的经济主体以花费资源的方式进行合约的强制执行,这一概念与外生执行——即第三方机构(例如国家)以对交易中的经济主体而言无成本的方式强制执行合约相对。
但这种“相机续约”手段要想保持有效性,买方就必须向卖方提供一种“履约租金”(Enforcement Rent),使当前交易对卖方而言严格优于次优选择,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续约才能成为一种威胁。可以证明,这种租金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均衡现象,因此,这些市场上的价格永远高于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并且存在权力关系——因为竞争性交换市场永远都是卖方市场。(43)J. E. Stiglitz and A.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 393-410; S. Bowl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1): 16-36; C. Shapiro and J. E. Stiglitz,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3): 433-444.与履约租金相辅相成的,另一种强制执行的手段是对代理人的监督,但它的有效性也以履约租金的存在为前提。竞争性交换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驳倒了支持把政治排除在经济之外的新古典经济学命题(44)S. Bowles and H.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2): 145-150.,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概念贯穿了鲍尔斯第三阶段的理论发展方向,甚至是鲍尔斯在此后转向行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将在本文第四节展开。
(二)第二个理论发展方向:SSA模型
呈现这一理论发展方向的论文共6篇,其中鲍尔斯和戈登(M. Gordon)、韦斯科普夫(E. Weisskopf)合作的论文就占到了5篇,因此可以说只要看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某篇论文的作者栏中,就可以断言这篇论文的主题是积累的社会结构。这一发展方向的核心就是积累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广义上是指一个社会中一切能塑造和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制度结构,例如劳资协议、国际贸易制度等等。
鲍尔斯的这一理论进路的真正起点并不是与另外两位SSA学派代表人物合著的某篇论文,而是那5篇之外的另一篇。这篇“起点”论文是鲍尔斯和金蒂斯1982年发表于《政治与社会》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以美国为例》。这篇论文重在分析造成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因此自然而然地追溯到了塑造积累过程的社会结构上。这篇论文给出了一个粗糙的SSA分析框架:美国经济摆脱周期性危机的两种方式——扩大失业后备军增强资本权力和通过海外投资榨取他国劳动以提振利润率——被美国国内扩大的民主权利所限制了,而这就是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的原因。(45)S. Bowles and H. Gintis,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m: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 Society, 1982, 11(1): 51-93.
单从文献呈现的信息来看,鲍尔斯正式加入SSA学派是在1983年,此后SSA学派也理所应当地吸纳了鲍尔斯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劳动榨取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鲍尔斯参与的三篇论文最能反映这一时期鲍尔斯的SSA理论发展进路,这三篇论文分别是1983年发表于《布鲁金斯经济活动报告》的《心智与思想:美国生产率增长的社会模型》(以下简称《心智与思想》)、1986年发表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的《权力与利润:积累的社会结构与战后美国经济盈利能力》(以下简称《权力与利润》)、1989年发表于《经济展望杂志》的《商业优势和经济僵局:对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建构性回顾,1979—1987》(以下简称《商业优势和经济僵局》)。
但在介绍这三篇论文之前,还需要介绍戈登、韦斯科普夫和鲍尔斯在1983年合作并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长周期与非再生产周期》一文。笔者认为,这篇论文对再生产周期和非再生产周期的界定和区分明确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再生产周期又称为表现良好的周期,是指“经济衰退能被周期本身的运作所纠正的周期……因为它可以内生地恢复快速积累的条件,因而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积累过程的结构。”(46)非再生产周期则与之相反,是一种反常的周期,即“衰退不会内生地自我纠正,因此需要对调节积累过程和建立盈利条件的制度进行基本的改变。”(47)显然,如果经济周期都是再生产周期,那么研究所谓的社会积累结构似乎并无必要,因为经济体会自动走出危机。即便是有进行反周期的政府干预的必要,目前的经济理论也足够支持此类活动,而无需再开辟新理论。但这篇论文通过建构再生产周期和非再生产周期的判定指标,发现美国经济在1890到1981年间出现过3次非再生产周期,而当非再生产周期出现时,“如果资本主义要继续下去,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能够重新点燃盈利能力、投资和经济增长的SSA”(48)D. M. Gordon, T. E. Weisskopf, and S. Bowles, “Long Swings and the Nonreproductive Cycl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73(2): 152-157.,而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心智与思想》是鲍尔斯加入SSA后的第一篇应用SSA理论的定量实证论文。这篇论文和接下来要介绍的其他两篇论文一样,都旨在探寻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生产率下降的因素。从一个包含产能利用率及其变化水平、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水平、单位劳动力贡献的有效劳动、进口品相对价格和与企业创新压力有关的技术进步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函数出发,作者建立了一个体现积累的社会结构计量方程。结果表明,劳动强度的下降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劳动生产率下降最重要的因素。这与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相同,并且这一解释生产率降低的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解释生产率提高现象——这也是主流经济学无法做到的。(49)T. E. Weisskopf, S. Bowles, and D. M. Gordon, “Hearts and Minds: A Social Model of US Productivity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3,14(2): 381-450.
《权力与利润》是SSA走向成熟之作。这篇文章发展了一个开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决定公式,该公式涵盖了产能利用率、投入系数、贸易条件、工资束、有效劳动水平和税率。在该文中,SSA被进一步明确为资本-劳动协议、美国治下的和平与资本-公民协议。资本-劳动协议是用失业损失和工人反抗水平指数度量,美国治下的和平是用军事力量指标和调整后的贸易条件指数度量,而资本-公民协议则是用政府管制强度指标和资本负担的总税收比例度量。实证结果方面也有新的研究结论:1959—1966年到1966—1973年的利润率均值变化中,负面贡献最大的是资本-劳动协议的崩塌——其主要原因是失业损失的减少;在1966—1973年到1973—1979年的利润率均值变化中,造成利润率下滑的主要因素是周期性因素和美国国际力量的相对衰落。(50)S. Bowles, D. M. Gordon, and T. E. Weisskopf, “Power and Profit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Postwar US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6, 18(1&2): 132-167.
《商业优势和经济僵局》是鲍尔斯在SSA领域的最后一篇论文,它同时也标志着这期间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走向相对完善的状态。这篇论文总体沿用了《权力与利润》一文的框架,内容上也似乎是该文的延伸——因为在《权力与利润》一文的末尾有对“里根经济学”的政策效果的简短分析,而这篇论文则对此展开了更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里根经济学”看似壮大了资本相对权力,但实际上是通过实际利率的提高使得斜率为负的“资本相对权力-产能利用率”边界向内移动了——即削弱了资本的潜在相对权力。但为何资本相对权力又在事实上表现得更强呢?文中给出的解释是这一时期资本相对权力的提高是靠更低的产能利用率实现的。简单来说,如果保持现有的产能利用率,在“里根经济学”施行之前是可以达到更高的资本相对权力水平的。实证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理论解释。(51)S. Bowles, D. M. Gordon, and T. E. Weisskopf, “Business Ascendancy and Economic Impasse: A Structural Retrospective on Conservative Economics, 1979—8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9, 3(1): 107-134.
四、理论拓展期:1990年至今(52)笔者认定理论拓展期延伸至今有以下两点原因:1.鲍尔斯本人从未声称过自己不再研究马克思经济学;2.一直到2020年鲍尔斯还在论文中使用自己所发展的含有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理论。
前文提到,从劳动榨取理论发展出的“竞争性交换”是理解鲍尔斯的“理论拓展期”的重要线索。鲍尔斯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完全集中在对竞争性交换这一概念的分析和阐明上(53)S. Bowles and H.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1990, 18(2): 165-222; S. Bowles and H. Gintis, “Power and Wealth in a Competitive Capitalist Econom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92, 21(4): 324-353; S. Bowles and H. Gintis, “The Revenge of Homo Economicus: Contested Exchange and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3, 7(1): 83-102.,除此之外是基于竞争性交换的理论成果的应用分析。(54)S. Bowles and H. Gintis,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ase for the Democratic Enterprise”,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993, 9(1): 75-100; S. Bowles and H. Gintis, “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Incidence of Worker-owned Firms”, Metroeconomica, 1994, 45(3): 209-223; A. Jayadev and S. Bowles, “Guard Lab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79(2): 328-348; S. Bowles and W. Carlin, “Shrinking Capitalism”,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20, (110): 372-377.可以说,鲍尔斯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上唯一的重大进展即为竞争性交换,其他研究几乎都是在完善和应用这一理论,因此笔者将这一阶段定为理论拓展期。
在1990年发表于《政治与社会》的《竞争性交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微观基础》(以下简称《竞争性交换》)一文中,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竞争性交换的提出解决了长期困扰左派的一个问题:他们的经济民主化主张不存在微观基础,因为他们无法解释在自愿进入和退出的市场中,买卖双方的权力关系如何存在。这里的竞争性交换概念与《竞争性交换: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一文中给出的定义是一致的:“当主体B的货物或服务的某些属性对主体A而言具有价值,且B提供它们需要成本,但在无执行成本的合同中又没有对此完全规定时,这种交换就是竞争性交换。”(55)S. Bowles and H.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1990, 18(2): 165-222.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中定义了短边方(Short-side)和长边方(Long-side),所谓长边方即在竞争性交换市场中受到数量约束的一方——例如雇员和借款人,而短边方则是不受到数量约束的一方——例如雇主和贷款人。因为竞争性交换需要卖方赋予进行交易的买方一定的执行租金,因此市场无法出清而永远是卖方市场,所以处于短边的一方拥有“短边权力”(Short-side Power)。
这篇论文为这一“竞争性交换理论”总结了9个命题:命题1(短边权力):一个竞争性交易系统的竞争均衡可能会将权力分配给无法出清的市场中的短边方;命题2(生产中的政治):那些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拥有决策权的人占据了劳动力市场的短边位置,并对雇员行使权力;命题3(分而治之):竞争性交换经济的竞争均衡可能会造成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工人群体进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者其他类型歧视的现象;命题4(资本主义技术):在权利主张的执行手段是内生的情况下,雇主所采用的技术尽管是成本最小的,但通常不是有效率的;命题5(钱会说话):拥有财富所有权的主体可以成为竞争性交换市场中的短边方,从而将财产权转换为权力;命题6(财富的形式很重要):具有同等现值的不同资产(例如可转让的财产或未来劳动收入的现金流)也会对应于竞争性交换市场中的不同位置,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结构中也处于不同的位置——这种差异取决于对资产的权利主张必须被内生执行的程度;命题7(收入不是资产的回报):一个主体的收入不能表示为其所持有资产的回报,即使这些资产的定义广到包括技能;命题8(收入和权力之间的不对应关系):在合约处于相机续约状态的均衡时,处于长边的交易者比其他相同的处于长边但没能交易的人收入更高(56)没能进行交易的主体即为市场无法出清状态下超额需求的载体。,但短边和长边交易者的收入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命题9(财富和权力的不对应性):财富所有权既不是拥有短边权力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57)因为存在有财产却无短边权力的个体经营者和无财产却能代行短边权力的经理人。(58)S. Bowles and H. Gintis,“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1990, 18(2): 165-222.
除此之外,这篇论文还指出,可以根据瓦尔拉斯范式的两条基本假设来界定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此时鲍尔斯已不再强调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这两条基本假设是:1.行为主体偏好外生,2.权利主张执行手段外生。不过这里的划分并不是最终的版本。最终版本在1993年发表于《经济展望杂志》的《经济人的复仇:竞争性交换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以下简称《经济人的复仇》)一文中,该文认为这篇论文是对《竞争性交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微观基础》一文的接续发展。文中,作者按是否坚持这两条基本假设将经济学划分为四个派别:1.坚持两点假设的瓦尔拉斯式交换,代表人物是李嘉图、瓦尔拉斯、阿罗和德布鲁、科斯等;2.放松了权利主张执行手段的外生假设,主张行为人进行工具性的竞争性交易,代表人物是索洛、夏皮罗、斯蒂格利茨、霍姆斯特朗和威廉姆森等;3.只放松了偏好外生的变迁文化与合约交易,代表人物是穆勒、马歇尔、哈耶克和阿马蒂亚·森等;4.放松了两条假设主张文化变迁且行为人进行竞争性交换,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阿克洛夫、马克思和诺思等。(59)
《经济人的复仇》还进一步把《竞争性交换》一文中提出的9条命题精简为了6条:命题1:短边权力,竞争性交换系统的一般竞争均衡会将权力分配给无法出清的市场上的短边方;命题2:无效率的强制执行,将成本最小化的相机续约作为执行策略是无效率的;命题3:无效率的产权,资本主义公司的雇佣关系是无效率的,因为把公司的所有权和对权利执行策略的控制权重新分配给工人并对公司以前的所有者进行补偿,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命题4:竞争性市场中的权力集中,等级制企业比多头制企业或民主制企业更容易生存,这一事实可以用它们在执行分配主张方面的效率来解释,而无需以它们在配置资源上的效率来解释;命题5:金钱万能,财富所有权使经济主体在有竞争性交换市场的短边位置,从而赋予他们权力;命题6:劣帕累托性质的瓦尔拉斯规范,市场交换中的匿名性助长了不利于有效解决协调问题的规范。(60)S. Bowles and H. Gintis,“The Revenge of Homo Economicus: Contested Exchange and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3, 7(1): 83-102.
从更新的6个命题和文献中,我们发现,鲍尔斯在研究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两个地方:其一是通过减少监督成本而促进企业内甚至社会范围内的帕累托改进(61)因为监督成本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损失,而履约租金只是利益的分配。,其二是关注个体的偏好演化过程及其衍生出的解决执行问题的多种方式。这两点最终都旨在应用竞争性交换理论于现实生活中,即通过制度设计和寻找人类历史上的协调问题解决方式来减少作为纯粹社会损失的监督成本。而鲍尔斯逐渐关注个体的偏好演化过程很可能是他在之后转向行为研究的重要原因。因此,与其说鲍尔斯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了行为研究,倒不如说鲍尔斯是在继续探索和实践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鲍尔斯和金蒂斯于1994年合作并发表于《现代经济研究》(Metroeconomica)的《信贷市场缺陷与工人所有企业的发生率》一文就体现了这种应用思路。这篇论文是对两人1993年发表于《经济与哲学》的《民主企业的政治与经济案例》一文所提出的分析方法和结论的模型化发展。(62)S.Bowles and H.Gintis,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ase for The Democratic Enterprise”, Economics & Philosophy, 1993, 9(1): 75-100.该篇论文在理论上建模分析了民主企业,即工人所有的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分析表明,民主制企业在对劳工的管理上可能更有优势,而资本主义企业在有关企业风险投资行为和资产管理方面通常更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意味着民主企业的发生率是工人财富水平的增函数。这对公共政策的启示是,将财富的再分配于民主制企业可能会提高生产力,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在效率和公平对立的基础上做权衡的政策思维。(63)S. Bowles and H. Gintis,“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Incidence of Worker-owned Firms”, Metroeconomica, 1994, 45(3): 209-223.同样地,2006年鲍尔斯和贾亚德夫(Arjun Jayadev)合作并发表于《发展经济学杂志》的《护卫劳动》一文也体现了这种应用思路,即通过界定执行监督和捍卫产权的劳动数量来分析此类劳动力增加的经济原因和后果,在实证上支持并在政策建议中应用竞争性交换理论。
鲍尔斯在截至本文撰写完成为止发表的最后一篇与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的论文,也依然是沿用竞争性交换的框架提出政策建议。这篇于2020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协会论文集》(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上的名为《萎缩的资本主义》一文,旨在呼吁培育良好且可持续的社会价值观,通过改进社会中内生的合约执行手段以支持一个更加公正、民主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64)S. Bowles and W. Carlin, “Shrinking Capitalism”,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20, (110): 372-377.
五、结 论
50多年来,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从劳动价值论、劳动过程理论、利润率和经济危机理论、金融化等经典论题更多地转向了环境、种族与性别歧视、不平等等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论题。在研究路径上,激进政治经济学可以区分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65)T. E. Weisskopf,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46(4): 437-447.前者承认借鉴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和分析框架,但同时又修正了马克思的某些理论,甚至否定某个理论,比如劳动价值论;而后者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整体上持肯定的态度,特别是在对劳动价值论的坚定拥护上。正是因为新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分歧,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实质上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组织,作为一个学科也没有形成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鲍尔斯的学术身份就比较微妙。鲍尔斯既不属于新马克思主义,也不属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如其所说,他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从鲍尔斯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学术立场来看,他属于新马克思主义阵营。但是,鲍尔斯又没有真的放弃劳动价值论,而是重构了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是重构,鲍尔斯致力于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鲍尔斯从批判教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行为科学,其学术历程折射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反思和发展。鲍尔斯涉猎领域之广,理论创新能力之强,奠定了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中的特殊位置。笔者基于鲍尔斯从1970年到2020年间发表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相关论文,对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轨迹进行勾勒,在此基础上介绍了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并为他的学术转向提供了一种解释。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1975至1981年的经济学研究转型期,2.1982至1989年的理论成型期,3.1990年至今的理论拓展期。通过分阶段系统阐释,笔者发现鲍尔斯的研究思路是一贯的,他在第一个阶段中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放弃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背叛,因为至少他的初衷是试图革除马克思经济学中存在的“经济主义”弊病(66)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否真的存在鲍尔斯所认为的“经济主义”或“经济决定论”,理论界是有争议的。从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的史实看,“经济主义”或“经济决定论”更多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一种误解。参见刘菲菲:《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吗?——以饶勒斯与拉法格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的争论为理论案例》,《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期;蒋正峰:《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唯经济决定论”》,《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尽管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态度是需要立场鲜明地进行批判的。笔者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关于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方面的假说:1.鲍尔斯很可能是从金蒂斯的研究中获得了劳动榨取理论的灵感;2.鲍尔斯通过将劳动榨取理论发展完备,最终为“竞争性交换”这一重要理论成果的开花结果提供了基本前提;3.鲍尔斯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研究转向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近期鲍尔斯的学术活动内容来看,他依然支持将自己的“竞争性交换”理论作为新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微观基础,这也间接佐证了本文的部分假说。(67)S. Bowles and W. Carlin,“What Students Learn in Economics 101: Time for A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20, 58(1): 176-214.
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看,鲍尔斯致力于发展的实际是一套“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特征是:虽然不同意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但并不一概否定劳动价值论,同时却又试图发展出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也是很多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者采取的分析路径。虽然鲍尔斯重构了不同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且重构的劳动价值论为其行为科学导向的“行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如果缺少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榨取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偷懒(Shirking)理论就没有本质区别了。(68)关于新古典的偷懒理论,参见C. Shapiro and J. E. Stiglitz,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3): 433-444.就解释历史而言,这是贬低而非抬高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即使把马克思说成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也无济于事。(69)参见S. Bowles, “Marx and Modern Microeconomics”, April 21,2018,https://voxeu.org/article/marx-and-modern-microeconomics.事实上,“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甚至是学科整体特性,其思想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斯威齐等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驱,而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欠缺了列宁所特别强调的黑格尔哲学视角。因此,中国学者在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需要对鲍尔斯在内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进行批判吸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