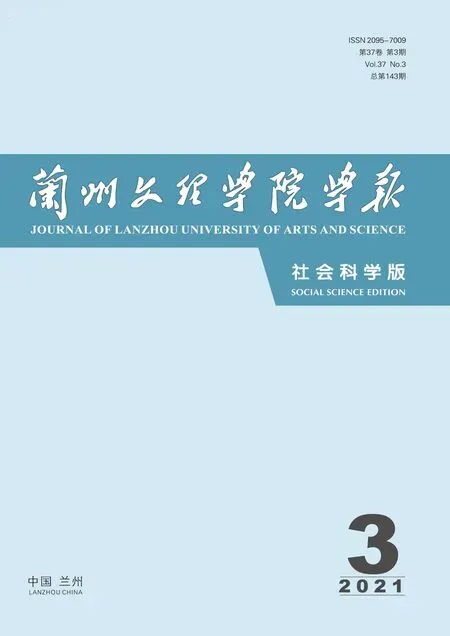图绘维柯思想肖像
——评叶淑媛《人文时空:维柯和〈新科学〉》
杨 有 庆
(兰州交通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人?》中指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1]正是通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断裂、脱节的不合时宜的奇特关系,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天才瞥见了时代之光的阴影,并领受了长期被遗忘的命运。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与其所处的启蒙时代的关系正是如此。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维柯作为启蒙的第一个批评者“生于他所处的时代之前”[2]21,导致他在生前和死后很长时间不断被误解和忽略。但对维柯这类不合时宜的独创性天才来说,每一次后世人们的深入阅读和阐释,无疑都是“死后的诞生”。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在汉语学界的命运,自朱光潜先生的中译本1986年出版以来,仍然如伯林所说“是一个被半放弃了的矿脉”[2]22。现在,叶淑媛的《人文时空:维柯和〈新科学〉》,是一个试图使维柯在当代汉语学术语境中再次诞生的真诚尝试。
一、以效果史策略展开的还原与回望
面对维柯“这一巨大的、杂乱的、有时甚至是稀奇古怪的巴洛克大厦”[2]13,叶淑媛选择他的代表作《新科学》为中心,重点阐释其诗学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特魅力。具体的阐释,主要是通过一种类似效果史的阐释策略来实现的。
所谓效果史,即理解是力图达成对象和对其理解的统一。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3]换言之,一种真正好的理解,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是对象的历史性与理解的历史性的统一。在《人文时空》中,作者采取的正是这种效果史的阐释策略。
一方面,通过对维柯的生平、思想渊源、早期著述等情况进行考察,试图还原或者重建作为被忽视的启蒙思想家维柯生活的时代与思想语境。在对维柯生平和著述的描述中,勾勒出维柯与其生活的启蒙时代的复杂关联。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认为:“哲学家总要先在某天某地诞生,然后才开始思考和写作。”[4]哲学家所生活的时代,会对哲学家提出问题。每个真正的哲学家必然是在对其时代所提出问题的描述和回答中开始自己的思考。启蒙时代哲学家面对的核心问题是认识论问题。虽然维柯确实如伯林所说是启蒙思想的第一个批评者,但他仍然与笛卡尔等启蒙哲学家分享着面对着其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认识论问题。区别在于,启蒙哲学家从理性及其运用出发去回答这一问题,维柯则独辟蹊径以感性作为出发点。
叶淑媛认为,维柯对于认识论问题的回答首先是从其基督教信仰出发去改造了柏拉图的“理念说”,发展出“天神意旨”这一形而上认识基点,继而结合塔西佗的对人性的强调,以及培根的融合经验与理性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自身的“认识凭创造”原则,或曰“真理-创造物”认识论。他以此反驳当时占据启蒙哲学主流的笛卡尔唯理论认识论,并发展出为人文科学奠定哲学基础的巨著《新科学》。在叶淑媛看来,“维柯是意识到笛卡尔的现代理性主义在认识自身上包含着错误种子的第一个思想家,也是身处强大的启蒙主义浪潮中第一位启蒙的批评者,因为维柯的著作代表着第一次不从理性主义出发来导出现代认识论哲学的重要努力”[5]86。这是中肯的评价,在语境还原中凸显维柯的原创性。
另一方面,从当代学术语境出发,通过后世诸多维柯思想后继者的观点去烛照其精神世界的轮廓和细微之处。伯林在评价维柯的影响时曾略带嘲讽地说:“思想深刻的一种属性就是:非常不同的思想家都认为他们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2]23但毋庸置疑,“生于他所处的时代之前”的维柯所著《新科学》确实为后来许多思想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和启迪。
在当代人文学科的视野和学术语境中,去考辨后世不同的思想家、艺术家如何从维柯的观点中汲取养分,并在其洞见的启迪中开拓出新的天地。这是必要的,因为文本的效果也是其意义构成的主要成分。通过分析马克思对维柯“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与阶级斗争学说的推崇,在二者的对比中揭示维柯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要素及其意义。探究哈罗德·布鲁姆如何挪用了维柯的历史循环三段论将西方文艺复兴至现代主义的文学经典划分为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三个阶段,通过对《西方正典》的细读表明即使在极端憎恨文化研究、推崇文学审美功能的文学精英主义批评家布鲁姆那里,依然有维柯思想的当代回响。分析维柯的“诗性智慧”说中关于想象和情感等问题的论述对浪漫主义诗学的影响,指出维柯作为浪漫主义美学的先驱,直接开启了浪漫主义崇尚原始主义与自然、注重神话、想象与强调情感等诗学命题与传统。而维柯在《新科学》中对荷马史诗进行审美和文化的双重阐释,则被视为现代民俗学与人类学诗学的滥觞。维柯对通用于一切民族的“心头语言”的探索则可视为结构主义的比索绪尔更早的先驱。可以说,通过考察维柯的主要观点在后世以及现代学术传统中的流变与影响,有利于我们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审视维柯的洞见与局限。
总之,通过跨越时空距离的还原和不断回望,本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精神半径丰富驳杂、极具原创性的维柯思想肖像。这大概也是书名——“人文时空”的意涵所在,即在将维柯置于人文学科的谱系中,去审视维柯作为“一位首屈一指的典范的现代思想家”超越时代的思想和洞见[6]。
二、通向一种历史哲学
在《人文时空》中,维柯的历史哲学是全书思考的核心问题。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之前,维柯的《新科学》早已通过具体实践创立了历史哲学。这已是学界公认的常识,但维柯是如何创立历史哲学的呢?这是本书集中思考和阐释的主要问题。
叶淑媛认为,维柯对历史哲学的创立首先体现在,他将自己迥异于启蒙时期理性主义唯理论认识论的“真理-创造物”认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所谓“真理-创造物”认识论,即真理与创造物同物异名,创造实践即是真理。这是对意大利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看来,上帝创造自然界,人类则通过实践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因此上帝了解自然界的奥秘,人也能够知道人类社会的历史。维柯的“真理-创造物”认识论正是从这种人文主义传统出发,认为人类社会既然是人类自己创造的,那就可以被人所认识。在他看来,人认识人类社会也是创造世界的过程,创造实践构成了人的认识内容或曰真理。这种认识论的人文主义色彩还体现在,不但试图构建一个无神存在的历史世界,而且相信相比较于那个试图了解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的自然科学而言,探究人类自己所创造的人类社会之历史知识是更具真理性的内容。这种独特的认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形成了对启蒙主义理性观念的批评。维柯为了克服以往哲学研究与历史分离的情况,“反对把认识自然科学的那一套理性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5]105,强调历史是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主张历史与哲学的结盟。所谓哲学与历史的结盟,指的是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揭示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与规律。
关于维柯进入历史的具体途径,叶淑媛概括为“从语言学进入历史”和“神话即历史”。所谓“从语言学进入历史”,源于相信“在用语言表达精神方面的事物的时候,语言的演变恰恰也反映着各种事物在人的精神观念中发展的过程”[5]109,所以从语言学(具体来说是词源学)来考察人类历史,以发现各民族在不同时期都必然会经历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图案”。维柯的语言学不仅是词源学,还包括各种表意象征物,诸如姿势、实物、礼仪、神话等能表情达意的符号。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与此对应的是三种语言:神的语言、英雄的语言和人的语言。神的语言,是在神的时代初民们运用符号、姿势和事物等无声语言,凭借想象力以自己的感觉来给事物命名,赋予事物生命和神圣性,这种语言是诗性的;英雄的语言,是无声语言(如英雄的徽文或徽章)向有声语言过渡的时期,是神的语言和平民的语言混杂;人的语言是现实生活中使用的发音和书写的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维柯将语言学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途径,但他的研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语言本身的阐释上,而是在其提供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朝着哲学思辨深入,以求归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
至于所谓“神话即历史”,在维柯看来,世界各民族最初的神话或寓言中都是以诗性智慧记录的民族最初的历史。他认为,对天帝的敬畏标志着宗教的诞生,赫拉代表了合法的婚姻和财产继承权,狄安娜表明了人类早期的生产方式,阿波罗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的知识的增长和艺术的诞生,而火神不仅表征了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意味着平民地位的上升,地神则代表了氏族制度和阶级斗争的出现,海神代表了航海事业的开始。叶淑媛指出,维柯将诸神的创立视为早期人类生活世界发展的历史过程之诗性反映,试图还原其以神话寓言呈现的诗性智慧中蕴涵的原始意义,“通过他列出的希腊神话的神谱和次序,描述人类社会生活民政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5]125。
维柯的历史观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也是其创立历史哲学的重要贡献。叶淑媛认为,维柯的历史观——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在启蒙时代具有革命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受神学影响的历史学将历史视为上帝所创,认为上帝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维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的基础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具有基督教信仰的维柯,将历史分为犹太民族的神圣历史和异教民族的世俗历史,试图通过对犹太民族历史之外的其他异教民族历史的研究,构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想的永恒历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细节上粗枝大叶,忽略甚至藐视具体历史事实的精确性。
维柯将这种各民族都要经历的理想化普遍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等三个依次演进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语言、政治和艺术,而且不断循环往复,即所谓历史的重演。对此,叶淑媛认为这源于维柯试图从琐碎的历史事实中探寻历史规律的思维方式和形而上诉求,而所谓历史循环论也不过是其对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历史相似性的某种抽象概括。
总之,通过对维柯进入历史的途径、历史观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的探究,回答了维柯缘何被视为历史哲学的开创者以及究竟如何创立历史哲学这一关键问题。
三、诗性智慧:注重感性与想象的美学
“诗性智慧”是维柯《新科学》中的轴心概念,指的是原始异教民族在人类童年时期拥有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思维结构。与启蒙时期强调运用理性去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存在及关系的唯理论不同,维柯推崇原始人由于没有推理能力而发展出的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他这种玄学称为“诗性智慧”,认为是凭借源于肉体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去对待并创造世界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也是一种具有实践功能的能力,“是在无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对待世界的感性、个别的、在想象中支配和创造世界的能力”[5]192。在叶淑媛看来,维柯以“诗性智慧的思维作为打开原始社会的钥匙,来研究古代的语言学、生活、寓言故事、民俗,以及古代生活的遗留物,以想象性的理解,来揭示隐藏在这些事物背后的历史真相”[5]147,为西方美学开辟了一条迥异于德国古典美学的、注重感性与想象的新道路。
叶淑媛认为维柯揭示了诗性智慧的主要特征。首先,诗性智慧作为思维方式是一种以己度物的隐喻为基本原则的诗性逻辑,通过想象赋予无生命的事物感觉、情欲和生命。正是依据这种以己度物的诗性思维方式,维柯阐释了神话、语言与诗。在维柯看来,神话不是虚构的荒诞故事,而是原始人类以自己为中心来通过想象把握外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诗性言说;维柯认为诗来源于童年时期的异教原始人类天生具有诗性逻辑这一事实,因为他发现在人类语言的起源中就充满以己度物的隐喻原理。他进一步分析了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等四种比喻类型,认为前三者都属于原始人类的诗性逻辑范畴,而反讽则是人类思维具有理性之后能够进行反思时才出现的。
其次,原始民族的诗性智慧体现在对“想象性的类概念”的创造。维柯指出,处于人类童年期的原始人类,犹如儿童,往往“制造出某些范例或理想的画像,把同类中一切和这些范例相似的个别具体人物都归纳到这种范例上去”[5]19。 他分析了《荷马史诗》,认为其人物塑造方面即采用了将诸多不同属性集合在某个诗性人物身上的策略。比如希腊人把英雄具有的属于勇敢这一属性的各种不同情感——诸如暴躁、拘泥繁文缛节、易怒、执拗不饶人、习惯凭借武力夺取权力等——都归诸一个具有想象性共性的诗性人物阿喀琉斯身上;同样,也将英雄具有的属于智慧这一属性的各种不同情感——诸如警惕性强、忍耐、好伪装、口是心非、诈骗、惯于说漂亮话但无行动、自欺等——都归诸一个具有想象性共性的诗性人物奥德修斯身上。
维柯认为,人类童年时期的异教诸民族是以注重感性和想象力的诗性智慧确立与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创造了人类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人类早期的原始文化无不具有某种诗性特征。叶淑媛通过对《新科学》中涉及原始文化的诸多方面诗性特征的分析发现:对维柯而言,诗性智慧不仅是原始民族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整体生活方式,“远古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社会制度、宇宙观等的起源,都是古人运用诗性智慧对于世界的想象和创造”[5]207。
另外,本书也勾勒了维柯提出的诗性智慧作为一种美学创见,以其对感性、想象、情感的强调和以己度物的隐喻原则以及对人的审美本性之揭示等,在其后的浪漫主义美学与立普斯等人的“移情说”中如何不断回响。美学史上19世纪末以立普斯为代表的德法美学家所推崇的“审美移情说”,强调物我同一或主客体在审美过程中的同情、共鸣与回环往返,正如叶淑媛所说,基本上没有超出维柯“诗性智慧”美学中关于“以己度物”的思想。而浪漫主义诗人对情感的推崇以及视想象为一种创造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滥觞于维柯的诗学智慧之美学创见。
总之,在本书中作者对维柯的阐释,力图从当代学术语境出发去阐明其思想的原创性与看似矛盾、粗陋之处背后的幽深思虑并为之辩护,充满了“理解之同情”与敬意。虽然在对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所“残留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当时盛行的语文学研究方法如何影响维柯等问题上论述略显不足,但本书对维柯之思想轮廓的勾勒,仍然为我们在当代理解维柯作为“一位首屈一指的典范的现代思想家”提供了有效的参照。尤其是作者运用现代思想学说资源去烛照维柯那些当时不合时宜的观点,图绘了与启蒙主义迥异的时代之另一幅面孔以及“它奇特的现代性”[7],给当下省思启蒙现代性提供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