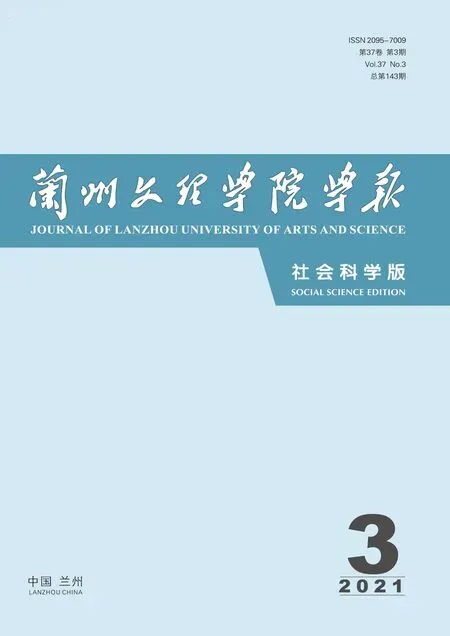谁在发声?
——《达洛维夫人》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研究
蒋 翃 遐,赵 丹 莲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1925年出版的《达洛维夫人》是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代表作之一。该书2005年入选《时代》杂志“百部伟大的英文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上流社会贵妇人达洛维夫人一天的经历,展现出一战结束后个体对时代命运的深切思考。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阐释了《达洛维夫人》,既包含主题,又涉及形式。潘建从女同性恋现象出发,讨论父权社会制度下女性艰难生存的状况[1];吕洪灵等分析了小说中的消费与赠礼行为,挖掘了隐含其中的性别关系与社会阶层关系[2];綦亮借助“对位阅读”,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阐释了文本背后的政治意图[3];沃尔夫(Wolfe)探讨了达洛维夫人形象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和自我书写意识,印证了该书中女性主义创作元素[4];里德(Reed)则通过叙述视角分析,挖掘女性的主体意识[5];兹沃德林(Zwerdling)、隆切提(Ronchetti)则通过分析人物的经历,探寻作者的两性观和社会观[6~7]。虽然相关的期刊论著层出不穷,但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入手,对《达洛维夫人》进行研究的成果却不多。鉴于此,本文借助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框架,从话语表达方式、叙述声音和叙事聚焦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究伍尔夫如何采取性别化的干预手段构建女性意识,发出女性声音,构建写作权威。
一、话语表达方式:再现女性意识
(一)自由间接引语与“模糊”的女性意识
利奇(Leech)和肖特(Short)把言语转述(speech reporting)分为五种类型,其中包括:“直接引语(direct speech)、间接引语(indirect speech)、自由直接引语(free direct speech)、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和言语行为的转述行为(NRSA)。这五种类型在小说中均有体现,且在不同的情境中各显其能。”[8]其中,自由间接引语尤其值得关注,它是一种介于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中的话语表现形式,广泛应用于现代小说。“西方批评家采用了‘双重声音’(dual voice),‘双重观点’(dual perspectives),‘双重眼光’(dual vision)等术语来描写自由间接引语的‘双重性’(duplicing):人物话语+作者(或叙述者)的叙述干预。”[9]自由间接引语往往模糊叙述者的身份,使读者难以确定究竟是故事内的人物还是故事外的叙述者在发表观点。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运用了大量的自由间接引语,使女性人物有机会表达自己观点,同时能够隐藏身份,从而避免读者因为性别身份对其叙述可靠性产生质疑;尤其是涉及到当时社会的诸多敏感话题,自由间接引语的模糊特性,能够较好地保存女性主体意识。
小说中当彼得从印度归来,理查德·达洛维结束午宴回到家中,相聚本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因为她举办的宴会,受到了两位亲密男性不约而同的质疑,达洛维夫人情绪受到了影响,发出如下的感慨:
那么,她应怎样为自己辩护呢?现在找到了原因,她觉得非常快活。他们认为,至少彼得认为,她就爱强加于人;身边总有名人拥着她;大人物,一句话,她干脆就是个势利之辈。咳,彼得可能这样想。理查德仅仅这么认为,她明知热闹对她心脏不好,还那么喜欢热闹激动,实在愚蠢。他认为这样太幼稚了。可他们俩都想错了。她热爱的只是生活本身[10]。
达洛维夫人举办晚会,是其热爱生活的表现,却硬生生遭到曲解。任何人在被误解时都理应为自己辩护,可是正如引言所言,她却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女性的“失语”状态可见一斑。初恋情人彼得认为达洛维夫人喜欢出风头才执着于举办晚宴;丈夫理查德认为热闹对她身体不好,简直是强出头;参加过她宴会的大人物则认为这只是体面运作而已。书中的男性几乎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构造、想象女性,而从未试图真正了解过女性,两性的二元对立在此进一步凸显。仔细阅读,引文具有两层含意:第一,故事内的达洛维夫人因为不被理解而颇感失望,发出“她热爱的只是生活本身”的呐喊为自己辩解;第二,故事外的叙述者深感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为男性所构陷,但囿于性别身份而无力发声,于心不忍,继而为女性慷慨辩护。因此,通过隐藏于自由间接引语的双重身份,女性人物能够扎根于强烈的主体意识,打破失语状态,为自己辩护。综上所述,正是因为自由间接引语模糊了小说人物和第三人称叙述者的身份,女性人物才能够在双重叙述身份中维护话语权,陈述带有女性主体意识的观点,避免陷入他者化的境地。
(二)自由直接引语与“清晰”的女性意识
在《达洛维夫人》中,女性人物时而隐藏在自由间接引语之下发声,时而通过自由直接引语直截了当地表达其所思所想。同自由间接引语一样,自由直接引语也是在直接引语的基础之上,通过省略引述句和引号等形式构成。虽然其形式更为自由松散,但是表达的意义却更为丰富。“自由直接引语是叙述干预最轻、叙述距离最近的一种形式。由于没有叙述语境的压力,它使作者能够自由地表现人物话语的内涵、风格和语气。”[11]鉴于自由直接引语能够直接表现人物思想,凸显人物主体意识,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便将其广泛应用。具体来说,小说中这一引语形式既用于展现女性人物面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思考,也用于描述她们对日常生活的感慨。例如,丈夫理查德给克拉丽莎送了花,却没有说出一直想说的“我爱你”。为此,克拉丽莎发出了关于夫妻关系的感慨:
因为你自己不愿意放弃它,也不愿意违背丈夫的意志去夺取它,否则就会失去你的独立,你的自尊——毕竟这是无价之宝[10]107。
克拉丽莎清醒地意识到她和理查德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给对方留有自由的空间。她执着于维护作为妻子的尊严和独立,而理查德能够让她满意,所以最终选择了他。出乎意料的是,这份尊重、自由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演化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自此我们看到,达洛维夫人在经历了婚姻生活之后,对夫妻关系有了更加成熟的思考,进一步明确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维护作妻子的尊严,尊重彼此。此外,自由直接引语也反映了人物不经意之间对生活产生的感悟,这些感悟通常发生于次要人物,从侧面强化了整部小说的女性主体意识。例如,年迈的邓普斯顿太太看着街边的年轻女孩,回想起了自己如花般的岁月,同时对婚姻和女性关系作了思考:
你会结婚的,因为你够漂亮。邓普斯特太太想。结婚吧。她想道。那时你就明白了。啊,那些厨师啦什么的。每一个男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可是我如果能够预先知道的话,我会作出那样的选择吗,邓普斯特太太想道[10]24。
邓普斯特太太在整部小说只出现了一次,但她关于婚姻的思考却发人深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貌美如花的年龄就应该找个好人家结婚,但是嫁作他人妇并非意味着幸福的开始,而只是为了共同生活、互相磨合。倘若时光倒回,邓普斯特太太会问自己,也会问他人:她是否还会结婚。小说没有给出答案,把问题抛给读者。虽然全书刻画的主要女性角色不多,但是次要女性人物——诸如邓普斯特太太、女仆露茜以及布鲁顿夫人等等——思维的自觉流动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女性主体意识。
综上所述,自由直接引语可以是女性人物的沉思,也可以是不经意的感慨。自由直接引语将女性人物的过去与现在、情感与思考相互交融,真切、生动地展现出其主体意识,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
二、叙述声音:助力女性发声
(一)作家型叙述声音与女性作家的声音
“声音”一词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具有特殊的含义,相较于经典叙事学强调的叙述功能和美学价值,后者更注重声音在文本中所承载的社会意义。长期以来,公众的话语权隶属于男性,男性作家用自己的声音完成了女性的文学想象。因此,女性作家只有依靠自己发声才能打破僵局。
兰瑟(Lanser)在分析了伍尔夫的教育背景和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之后,认为伍尔夫采取了特殊的作家型叙述声音,并指出这一声音“既压制又表达叙述者的立场,在乔治·艾略特式的显露型作者权威和多萝西·理查德森式的作者隐退、人物聚焦之间左右协商平衡,以争得一席之地”[12]。因此,《达洛维夫人》中的叙述者,通过间接的话语表达方式,借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发出了作家型叙述声音。诸如,小说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突然间闪现出关于世界、生死等问题的思考。达洛维夫人走向邦德街时,发出了“没有她而这一切必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感慨[10]8;听到塞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达洛维夫人则宣告“如果现在就死去,现在就是最幸福”[10]164;塞普蒂默斯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高喊“可是他为什么应该为了他们杀死自己呢?”[10]83。“尽管这种情节实在不足为奇,可我们感受到了普通人内心的震颤。那一个个若无其事的心灵里搏动的是同样焦躁的心,他们对生存感到困惑,但又面临着死亡的恐怖。”[13]通过上述表达方式,小说反思了生与死的哲学命题,反思了战后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惑等问题,小说的时代意义得以升华。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型叙述声音并不意味着作家取代叙述者在小说中发挥叙述交流的作用,而是通过特定的叙述策略,使叙述者看上去带有作家声音的某些特征,进而顺理成章地获取叙述权威。正如兰瑟所言:“文本对(隐含)作者和集体的、异故事的主述者之间没有作记号区分的地方,读者即被引入,把叙述者等同于作者。”[12]18换言之,在作家型叙述声音之下,读者倾向于将异故事状态下的全知叙述者当成作者,尽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正是“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的作家型叙述声音”[12]17,使得文本内的全知叙述者带有了文本外作家声音的特点。叙述声音与作家声音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不仅确保全知叙述者获取了类似于作家般的叙述权威,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传递了作家的观点,强化了女性作家的声音。
(二)个人型叙述声音与女性人物的声音
“个人叙述型声音就是‘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事者’,也就是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主角以往的自我。”[12]20个人型叙述声音往往以小说人物为载体,在某些特定的情节中,叙述者与人物合二为一,直接叙述自己的所思所想,与读者对话。
《达洛维夫人》广泛使用了个人型叙述声音,让女性人物直接发声,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小说中彼得和达洛维夫人阔别多年,再次重逢,双方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岁月的痕迹。彼得害怕自己如今的生活受到朋友的鄙夷,“她会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从达洛维家的意义上,我是个失败者”[10]39。另一方面,达洛维夫人虽然因为“不屈不挠的自我中心感”[10]40并没有立刻表现出重逢后的激动心情,但是看到情绪失控而嚎啕大哭的彼得,她主动安慰他,并且闪现出“如果当初我嫁给了他,这样的快乐就整天都属于我了!”[10]42的想法。从这短暂的重逢中,读者可以察觉出彼得和达洛维夫人的差异:虽然两人都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但是彼得更多地考虑自己,而没有真正关心过达洛维夫人;达洛维夫人则体现了女性特有的共情心,看到彼得情绪崩溃便上前主动安慰。个人型叙述声音允许女性人物自如发声,这样针对同一件事情,男女双方能够表达出各自不同的观点,男性一家之言的局面被打破。此外,伍尔夫还创作了众多女性人物,包括出格的莎利、保守的布鲁顿夫人、具有反抗精神的伊丽莎白等等,使人物多重的叙述声音代替单一的叙述者发声,让更多的女性人物成为叙述代言人,言说自己的故事,增强了女性人物的话语权。
三、叙事聚焦:构建女性话语
(一)零聚焦与女性作家的话语权
热奈特将聚焦划分为零聚焦(non-focalization)、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和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三种类型。零聚焦指传统的全知叙述,其典型特征为聚焦者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能够透视人物的内心,并直接向读者传递价值和情感观点。热奈特的零聚焦与凯南(Rimmon-Kennan)的“叙述者—聚焦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凯南认为:“叙述者—聚焦者可以或隐蔽或公开地表达其权威观点。”[14]为此,叙述者采用特定人物的视角,对达洛维夫人的评价能够隐秘地引导读者作出价值判断。小说中彼得、理查德似乎处处在否定达洛维夫人的行为和品格;而在零聚焦的透视镜头下,达洛维夫人则显现出迥然不同的形象:例如,朝夕相处的仆人们都喜欢她,尤其是贴身女仆露茜认为“她的女主人最可爱”[10]34。通过小说中不同人物相左的评价,全知叙述者多维度地透视了人物内心,全面诠释了女性形象;同时也扩大了小说的聚焦空间和话语空间,从而能够从更深刻的层面引导读者思考小说人物真正的面貌。
当小说涉及诸如婚姻、同性恋等敏感话题时,全知叙述者倾向于通过插入语的形式直言不讳地表达其价值判断。当克拉丽莎年少时与莎利谈论结婚的话题,小说写道“他们谈起婚姻时,总把它说成是灾难”[10]31。然而插入语不只是直接评论,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充当叙述者的幌子和借口。当莎利在餐桌上向就座的上流社会人士,询问婚前有过孩子是否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插入语则成了全知叙述者打圆场的手段“在那个时候,在男女都在场的时候,说这种话是很冒失的”[10]53。而关于妇女权利的争论,在插入语的掩护下又成为了“那个古老的题目”[10]65。虽然女性权利在当时已经逐渐兴起,但是男性话语在任何时代都占据主导地位。插入语本身是非正式的表达方式,因此插科打诨式的评论,看似不起眼,但却能够公开而又隐秘地表达“出格”的观点。正如德洛里(Delorey)所言:“插入语本身是停顿的标志,但在伍尔夫的笔下,插入语使呈现一个完整句子成为幻象。在更大范围内,我们可以认为其打破了固定的、预设的文本结构,甚至可以说,打破了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社会结构。”[15]
在思考《达洛维夫人》的创作时,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人真的能够彬彬有礼对待女性,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和男性的关系比起来,女性是多么私密。为什么不能写下来呢?真正地描述这件事?”[16]正如修辞叙述学强调:“叙事的目的是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17]那么,伍尔夫创作的目的就是想要传递出关于两性关系的思考。正是通过零聚焦,伍尔夫不仅透视了人物内心,隐秘地揭露人物真实想法,为小说创造更大的聚焦空间和话语空间;而且直接传递了价值判断标准,增强了女性作家的话语权。
(二)内聚焦与女性人物的话语权
热奈特指出:“内聚焦指的是从小说中人物的视角出发来感知事物发展的情况,此时叙述者知道的和其中某个人物一样多。”[18]内聚焦代入感强,读者能够从人物视角出发,透视故事发展,感受特定情感。因此以女性人物为主体的内聚焦,能够从女性特有的角度观察事件,在话语层面改变女性人物长期被客体化的现实,颠覆凝视主客体的权力关系。《达洛维夫人》同时也采用了内聚焦的方式,其中既包含以彼得、理查德为代表的传统的男性视角,也包含女性视角,这样男女双方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观点得以相互补充。在彼得眼里,达洛维夫人是为了身份地位而抛弃爱情的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但通过达洛维夫人的聚焦,读者知道她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她不得不和他分手,否则会毁了他们,两个人都会毁掉。”[10]7虽然达洛维夫人的决定和行为遭到了身边男性的质疑,但是她没有随波逐流,放弃独立的个体意识,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通过内聚焦,女性人物能够传递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成功避免了在男性视角下的“他者化”。
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认为,“电影研究中的‘凝视’(gaze),带有性别化的影射意义:男性是凝视者而女性则成为了被凝视的对象。而叙事学中,聚焦则承担着相似的功能”[19]。因此,为了颠覆被凝视的状态,女性主义叙事学更多地关注了叙事聚焦和性别政治之间的联动关系,分析聚焦模式下的深刻动机。《达洛维夫人》中存在着传统的男性聚焦者,但是聚焦的效果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彼得的聚焦对象与达洛维夫人息息相关,从最初的重逢到参加晚宴,他回忆了青年时代的爱情,记录了此次重逢的心情,也对自身的性格作了反思。彼得作为聚焦者的功能受到了批评家的关注。“彼得根据克拉丽莎的一言一行,推断了克拉丽莎的精神状态。”[20]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作为聚焦者,彼得显得越来越偏执。在他眼中,达洛维夫人举动可笑,情感冷漠,伊丽莎白模样古怪,海伦姑妈性情乖张。然而,这几位女性人物对他一向友善、关心。因此,通过彼得的视角所呈现出的人物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籍此叙述者否定了彼得的话语权,说出了“至于他自己,他很荒唐。他对克拉丽莎的要求(他现在明白了)是荒唐的”[10]56之类的话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以彼得为代表的男性聚焦在小说中是失败的,其观点不为叙述者所信任。《达洛维夫人》中女性聚焦的可靠性和男性聚焦的不可靠性本质上是叙事聚焦背后两性话语权力地位的转换。
四、结语
肖尔瓦特(Showalter)曾评价说:“伍尔夫的小说将女性创作的准则从自我牺牲转换为破坏叙述本身,将女性主义的文化分析转移到小说中语言的文字、句式以及结构研究。”[21]在《达洛维夫人》一书中,伍尔夫运用独特的女性主义叙述策略,不仅在字里行间中再现了女性主体意识,推动了女性发声;而且成功打破了两性传统的话语权力结构。虽然由于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的局限,伍尔夫没有在叙述中完全消解男性话语,但是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压制和对抗策略,她隐秘地获取了女性叙述的权威。女性主义叙述策略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发展,本质在于女性作家为了获取叙事权威,并非直接僭越传统,而是做出一定的妥协。尽管如此,伍尔夫的小说仍为后来的女性主义小说创作以及叙事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内容。因此,对伍尔夫小说叙述策略的研究对当代女性作家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