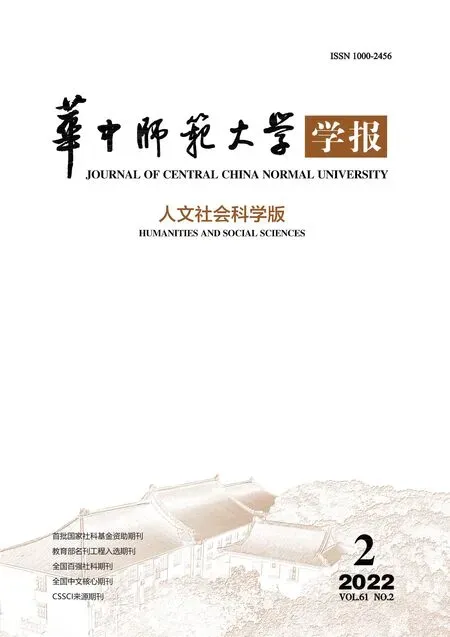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影像书写
彭 涛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48种伟大精神,它们是建党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反映和赓续,彰显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必然反映一个时代的现实使命与理想愿景,影视剧(2)因电视剧文本太过浩繁,本文以电影文本为主展开论述,偶尔兼及重要电视剧文本。作为通过影像书写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既是时代精神气质的反映,也是理解过去、认识现在和畅想未来的重要窗口。中国影视剧在其影像实践中,以其特有的方式再现或表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各种伟大精神。因此,中国电影史,尤其是新中国电影史,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影像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习近平总书记将建党精神高度概括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和起点,是极其精辟而准确的,同时也为我们准确把握“精神谱系的影像史”指明了路径,使我们能够从建党精神的角度,烛照中国影视剧书写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和特点。
一、以建党精神为核心的精神谱系影像书写
鸦片战争以来,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有感于旧中国腐朽衰败的现状,立志于救国图强。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漫漫求索路,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开出一剂剂药方,但依旧未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率先向国人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密码,也成为精神谱系影像书写实践的起点。
直接铆定建党精神的影视剧,在20世纪90年代前基本是阙如的。分别拍摄于1991年、2011年的《开天辟地》和《建党伟业》,是直面这段历史的两部电影。前者是影视作品中首次正面表现陈独秀形象的电影,后者除了直面历史外,还引入商业片的明星制,引发了巨大的观影热潮。2021年前后,在纪念建党百年的氛围下,聚焦建党精神的影视剧空前增多,电影有《1921》《红船》《革命者》《望道》《何叔衡》等,电视剧则有《觉醒年代》《光荣与梦想》《理想照耀中国》《中流击水》《百炼成钢》等。
这些影视剧或影片,大多涉及共产党是如何成立的这一历史进程,创作者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理念,对涉及的中外重大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既有全景式勾勒,又有生动细致的刻画。通过电影的影像书写,历史的前台后景,宏观处,平地惊雷,壮怀激烈;惊险处,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细节处,波澜不惊,余韵深长。这些电影都将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编织进剧情,熔铸到人物的形象与性格中。比如,2021年的现象级电视剧《觉醒年代》,将160多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为刻画的对象,有名有姓者竟达千位。编导以酣畅饱满的激情,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历史,表现了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时代追求,回答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也理清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五四时代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
建党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浴血奋斗中,而且“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奋斗之中”(4)路克利、曲政:《伟大的建党精神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奋斗之中——伟大建党精神的鲜明特征与时代价值》,《北京日报》2021年7月5日,第9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是什么?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5)曲青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人民日报》2021年7月8日,第9版。。当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审视中国电影的精神谱系书写实践时,它的书写传统也就更加源远流长。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党的左翼电影小组就将党的主张融入电影创作思想中,造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左翼电影高峰,《渔光曲》《马路天使》《大路》《桃李劫》《野玫瑰》《十字街头》等电影至今仍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抗战胜利后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影片,或以史诗巨制书写八年离乱,或以横截面表现底层苦难,揭露统治者的黑暗,表达人民对光明的向往,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折射了中国电影人的精神追求。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新中国电影,以马列主义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这样的文艺观指导下的电影事业与电影创作的方针政策,以至审美取向、艺术风格,是电影工作者遵循的‘宪法’”(6)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导言”第2-3页。。因此,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还是儿童题材的电影,虽然书写的主题不一,着墨的人物千姿百态,但在故事背后人物拥有的价值底座、精神向度和行为逻辑,都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凝聚或折射。
“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数量众多,成就巨大,《南征北战》《红日》《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优秀作品,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党的辉煌历史和奋斗精神。同时,电影人还秉持一种“健康实际的现实感、实践感”(7)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423页。,创作了大量“工农兵电影”,如《李双双》《柳堡的故事》等,以高度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礼赞时代新的面貌和气象,书写新政权的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驾轻就熟的革命历史题材,既收获了《西安事变》《风雨下钟山》等宏大叙事佳作,也在《归心似箭》《今夜星光灿烂》《小花》等作品中尝试“小叙事”,表现革命洪流中普通参与者的命运和心路。而刚刚兴起的电视连续剧,则以《虾球传》《敌营十八年》等作品,为书写建党精神开启了新的路径。1987年,“主旋律电影”被正式提出。主旋律电影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建党精神高度契合。“主旋律电影”提出以来,因为其独具一格的意识形态功能,在80年代后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构成的电影版图中受到格外关注,“主旋律不仅作为一种口号,而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中国电影的基本形象”(8)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尽管经受了电影产业化、“入世”等冲击,“但主旋律电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载体的功能始终未变”(9)彭涛:《中国电影史链条上的主旋律电影及其未来走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主旋律电影和与其精神气质一致的主旋律电视剧,共同为书写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发挥着重要功用。
进入新世纪、新时代,某种意义上,“主旋律电影”这个名称被“新主流电影”接棒,创作上更多借鉴类型片的手法,以正剧题材、精良制作、低起点人物、个体视角、国族情怀、认同想象为核心特征,达成了主流价值观和商业价值的合流(10)尹鸿、尹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和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2018年第7期。。代表性作品,如《战狼》系列、《红海行动》《长津湖》等影片,激发了巨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力量,充分展现了影像书写的魅力。
二、 “精神谱系影像史”中的人物画廊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指出:“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可以体现一个时代的特点。黑格尔指出,“艺术是和整个时代与整个民族的一般世界观和宗教旨趣联系在一起的”(1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8页。。影视剧正是围绕人物展开的一种叙事艺术,人是精神的源泉和起点。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中涌现的无数楷范先贤、英雄志士,也为中国电影的影像书写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影视作品塑造的众多共产党人形象灿若星河,构成了绵延不绝的人物画廊。
第一类是领袖人物系列。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人生经历,是中国影视人物塑造取之不尽的宝库。领袖们的形象,是影视剧观赏和接受中的重要要素,极易在观众那里激发向往与崇拜之情。在影像实践史中,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经历了“缺席的神化”、“世俗化”和“泛情化”的过程。1978年以前,领袖们主要是以精神偶像的方式存在于影像当中的,领袖形象按照“缺席的神化”原则塑造。比如1960年拍摄的电影《万水千山》,这部旨在反映工农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取得长征胜利的故事,时时处处都在强调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但领袖的形象却始终没有在电影中出现。直到1978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河奔流》中,才首次出现由演员扮演的领袖形象。著名话剧演员于是之扮演毛泽东,王铁成扮演周恩来。此后,演员出演第一代中共领袖渐成气象,并产生了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特型演员”群体。通过他们的表演,领袖们或是出现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如《四渡赤水》《风雨下钟山》《西安事变》《重庆谈判》《百色起义》《大决战》(系列)等,或是出现在人物传记片中,如《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刘少奇的四十四天》《邓小平》《彭大将军》《青年刘伯承》等。这是领袖形象的“世俗化”塑造时期。领袖不仅可以由演员扮演,而且可以在银幕荧屏上供观众“凝视”,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为破除主旋律影视剧的刻板印象,领袖人物塑造进入“泛情化”时期,作品注重挖掘领袖身上折射的普通人情人性。如在《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一片中,当毛泽东得知儿子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时,他一声长叹:“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痛惜中又自我开释,令人泪目。在电影《周恩来》中,即将手术前,周总理在床上拉着邓小平的手叮嘱:“小平,都托付给你了!”这种伤感的情景,越发让人体会到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情谊和信任。而在影片《刘少奇的四十四天》里,当返回故乡调查研究的共和国主席,看到公社食堂一双双饥饿的眼睛和一张张狼吞虎咽的嘴时,心里交织着痛楚和自责。当这些情节描写出现在电影中时,它们淡化的是领袖的“神性”,丰富的却是领袖的人性,于是也就把领袖与人民呼吸与共、血脉相连的共同情感凸显出来,同时也加深了观众的情感认同。“伦理‘泛情化’策略成为‘主旋律’电影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一条有效通道。……对这一时期电影的题材选择、价值观念的表达、叙事方式以及对人性和世界的表现深度、甚至电影语言本体都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12)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第160页。。
第二类是英雄人物系列。塑造英雄形象,歌颂英雄行为,是世界各国电影共同的偏好和选择,中国电影也不例外。同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在崇拜英雄、认可英雄的观念之外,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还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英雄品格:信仰坚定,忠诚勇敢,不畏艰险,敢于牺牲。
早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起步阶段,创作者们就有意识地塑造了一批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英雄,通过他们来将党的政策主张具化为电影人的实践行动。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了《钢铁战士》和《刘胡兰》(13)1950年版《刘胡兰》由冯白鲁导演,胡宗温扮演刘胡兰。1996年山西电影制片厂重拍《刘胡兰》,池华琼扮演刘胡兰。两部歌颂英雄的著名影片。前者以剧情片的样式,歌颂了以张排长为代表的三位解放军干部战士的钢铁意志,后者则以传记片的样式再现了刘胡兰的生平事迹,生动诠释了毛泽东为其题词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内涵。此后,新中国电影以传记片和剧情片的样式,塑造出一个庞大的英雄系列。传记片秉承了中国史传传统,为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英雄树碑立传。“群英谱”上,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先驱李大钊、夏明翰、江竹筠、林祥谦、施洋、周文雍、陈铁军、向警予,有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有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刘胡兰、董存瑞,有抗美援朝战场上光荣牺牲的邱少云、杨根思、黄继光……剧情片则通过展现时代中的英雄人物,将个人的选择与信仰作为叙事重点,进一步彰显了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比如《钢铁战士》中的张排长,《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玉梅,《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吴琼花,《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刘闯,《红日》中的刘胜、石根东,《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李正、芳林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杨晓东,《小兵张嘎》中的张嘎,《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英雄儿女》里的王成,《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等。这些英雄形象灿烂多姿,其中绝大多数都成为新中国影像史中的经典人物,他们从各自侧面体现了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在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创作者着力塑造的罗霄这个人物,可以看作共和国军事将领走向成长之路的缩影。罗霄从农奴到将军的成长史,也是精神的解放史。在电影《血战湘江》中,陈树湘率领被后世称为“绝命后卫师”的红34师,面对敌我力量悬殊,他率部死战不退,为主力渡江赢得了宝贵时间,解除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他最后伤重被俘,不幸牺牲,年仅29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无数像陈树湘这样的英雄,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前仆后继、敢于斗争、勇于胜利。”(14)《学习时报》评论员:《讲好陈树湘等英雄的故事》,《学习时报》2021年5月5日,第1版。这些熠熠生辉的英雄人物形象在丰富影像书写空间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有力的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狼毒花》《亮剑》《光荣岁月》等。这些电视剧塑造了一批具有时代审美烙印的新英雄形象——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常发等,他们的身上不仅有着传统审美中的智勇双全,还格外强调了英雄人物的成长性和性格的多面性,因此角色的草莽色彩以及某些人性的弱点,不仅没有削弱英雄的崇高感,反而使其显得更加立体和丰富。这些新英雄颇有福斯特称许的“圆形人物”的特点。
第三类是革命和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新人。新中国的成立,激发了广大人民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因此再现和讴歌人民,既是新中国电影应有的政治功效,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举措。比如,“十七年”时期出品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兵新传》《冰上姐妹》《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影片中的新人形象,有着浓烈的时代生活气息以及纯净、美好心灵的共性。他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中,蕴含着热情拥抱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价值立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时刻,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新的历史时期,建党精神被赋予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时代内涵,也使影视塑造的新人充满了新时代的活力与魅力。在《你好,太平洋!》《他在特区》等电影以及《外来妹》《情满珠江》等电视剧中,创作者以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和特区深圳为背景,塑造出一批特区建设的弄潮儿形象。电影《花园街五号》《T省的八四八五年》,通过塑造“被误解的改革者”形象,直面体制沉疴与困境,振聋发聩地为改革开放鼓与呼。而《给咖啡加点糖》《雅马哈鱼档》等影片,则以清新的人物和故事,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经济带来的观念革新和人物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咱们的牛百岁》中的主人公牛百岁,在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心思谋如何带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形象放在当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电影《血总是热的》、电视剧《车间主任》等作品,通过描摹国有企业管理者形象,透视改革的阵痛,探寻改革的出路。而以反映武汉小商品市场在新时期沉浮变迁的电视剧《汉正街》,以及反映知识分子参与市场经济的电视剧《儒商》等,在中国影视人物画廊中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进入21世纪后,以《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功勋》等为代表的影视剧,则以一种无比崇敬的态度,歌颂了当代中国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以七个具有时代感的小故事,讲述主人公们在平凡生活中迸发出的伟大精神。这些人物的原型都来自现实世界,比如在《前夜》这个章节中由黄渤扮演的工程师林治远,他以自己的智慧、坚韧和敢于牺牲的精神,终于赶在开国大典之前完成了国旗升降杆的设计。《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侃爷”张北京,他意外地赢得了一张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本想借此挽救在儿子面前岌岌可危的父亲形象,却又心甘情愿地将门票捐给了汶川地震孤儿。这些人物塑造的方法,体现了时代的审美倾向,同时也更贴近新时代观影群体的审美旨趣。电视剧《大江大河》则通过大学生宋运辉、乡村支书雷东宝、个体工商户杨巡等人物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不同人生际遇和奋斗历程,深刻地刻画了改革者们的奋斗、觉醒和变化。电视剧《山海情》则是近年来扶贫题材影视剧中的佼佼者。剧中村支书马德福、“对口帮扶”教授凌一农等人物,在扶贫一线通过多年的不懈探索和辛勤劳动,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脱贫攻坚战役的生动写照,也是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反映。
第四类是先进典型形象。这些形象的原型,或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劳模,或是基层和一线的普通党员或领导干部,以他们为主人公的电影、电视剧可以视作传记片类型的亚类,因此也有不少人称此类电影为“‘好人好事’电影”(15)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第157页。或“劳模电影”。在这些先进典型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与表现——他们乐于奉献,一心为公,无私无畏,舍小我为大我,不怕牺牲,闪耀着党性的光辉,如《雷锋》《铁人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蒋筑英》《黄大年》等电影,“这些影片并不直接宣传政府的政策、方针,也尽量避免政治倾向直接‘出场’,而是通过对克己、奉献、集体本位和鞠躬尽瘁的伦理精神的强调来为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化’询唤,从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合法性”(16)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第158页。。例如,电影《孔繁森》中,如果说孔繁森在牧区抱起藏族大妈冻伤的双脚放入怀中温暖也是一种“泛情化”策略的话,那么,孔繁森收养的藏族孩子发自内心地称呼他为“冈底斯的神”时,立刻唤起基督教中有关创世传说的互文联想。丹尼尔·贝尔指出,“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在于诱发情感。除了宗教(即战争与民族主义)以外,很少有哪种形式能够把情感的能量诱发出来。宗教符号化了人的情感,使它们枯竭了,把来自现实世界的情感能量通通转化成了祈祷文、礼拜仪式、升礼、信条和宗教艺术。意识形态则使这些情感融合到了一起并将它们引向了政治”(17)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8-459页。。从这点看,《孔繁森》的探索是颇为成功的。它将观影过程变成了一次情感释放的高峰体验,并成为阿尔都塞所谓的一种“召唤”行为:“意识形态是以一种在个体中‘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个体)或把个体‘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个体)的方式并运用非常准确的操作‘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的。这种操作我称之为询唤或召唤”(18)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4期。。
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影像书写的特点
影视艺术是大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视听性、运动性、叙事性和大众性,使其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艺术形式而言,在如实再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时,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特点。
(一)政治性与诗性的高度统一
独特的国情,使中国影视剧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赏,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这是对包括影视艺术在内的文艺政治性提出的明确要求。对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影视剧而言,这种要求不是一般尺度,而是范式的合规性。影视剧在忠实、准确传达精神谱系蕴含的价值内涵的同时,还必须具有观赏性,这样才能提升观众对精神谱系的认同。中国电影人主要通过为电影注入“诗性”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诗性的赋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展示革命历史人物的诗性情怀,歌颂革命浪漫主义。此类影视剧不胜枚举,比如电视剧《血色浪漫》《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通过展示革命之路上的艰难困苦以及人物的苦中作乐,将历史的脉络和人的奋斗与抉择融为一体,生动再现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追求。《开天辟地》《建党伟业》《革命者》三部影片,都写到为躲避军阀的追捕,李大钊雪夜赶马车送陈独秀出城,从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情节。每部影片都用“诗化”的方式浓墨渲染了历史中这个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从而凸显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如《开天辟地》里,马车远去后,雪地里留下深深的车辙,《革命者》里马车前挂着两盏明亮的马灯,《建党伟业》里,是雪地里两位早期领袖紧紧拥抱,然后拉开一个寓意深远的大全景。
第二,通过增加电影的诗性,对事件、情节、人物进行抒情化处理,淡化文本的叙事性,以营造出诗的节奏或韵律,从形式上丰富电影,使文本的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于“诗性”之中,造成强烈的审美效果。在叙事功能上,诗情段落艺术地调控了叙事节奏、延伸了叙述时间,又丰富了叙事内容、增强了叙事的诗意感。它们并不是游离于影片主题之外的情感抒发,而是叙事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一种摇曳变化的美学效果,在严肃深刻的宏大叙事之外,描绘出一幅诗意的画卷。
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相遇》和《白昼流星》是两个最能体现电影“诗性”的章节。《相遇》的故事围绕着公交车上一对男女的重逢展开,女人愤恨而不甘的诘问,男人无措又悲凉的沉默,使得故事被嵌套进一个带有强烈戏剧冲突的结构之中,“相遇”在这里成了互文式的“诗眼”——它既是两性情感错综复杂的再现,又是宏大历史与个人悲欢的辉映。当谜题揭开,男人和女人都消失在庆祝的人群之中时,这个故事在审美上就造成了“此时有声若无声”的怅惘之感,留给观众的心灵震撼就越发强烈,于是无数湮没在历史中的个人情感也就喷薄而出。《1921》里表现杨开慧烈士牺牲的时候,使用杨开慧的主观镜头,并用柔光镜头的形式,回忆了她和毛泽东短暂而美好的爱情,唯美中又令人无比惋惜。
无独有偶的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的《我的诗篇》也延续了这种诗性的风格。通过展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中反复遇挫的一段历史,它将一个母亲的深情和诗意置于茫茫戈壁之中,将爱情、亲情与报国之情都融入“在天上写诗”的浪漫之中。它既象征着一个母亲在人生中的坚守,又象征了一代中国航天人的“初心”——在天上写诗,写一首生生不息的诗。
(二)叙述性与奇观性的有机结合
这里的“叙述”是“特指讲故事的行为本身”(19)申丹:《叙述》,见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736页。,我们将其理解为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在中国电影尤其是主旋律电影中,“说教”是其在叙事上的一个典型特征,以至于一段时间以来,在观众那里形成了对主旋律电影的刻板印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主旋律电影中,创作者们曾以伦理化、泛情化的方式寻求突破,比如《焦裕禄》《周恩来》《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通过它们的尝试使主旋律“从棱角分明到面目模糊”(20)彭涛:《从棱角分明到面目模糊——主旋律电影的形态演变》,《华中学术》(第2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5-284页。,并拉近了主旋律与观众的距离。新主流电影在“讲好故事”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它们大多借鉴类型片的创作模式。比如影片《1921》,创作者通过挖掘史料,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遭到的监视和追捕,以及日本特务暗杀日本共产党人的情节,加入侦探片的类型元素,使其观赏性大为提升。而在《我的母亲赵一曼》这部影片中,全片以“不在场”的儿子作为叙事视角,讲述赵一曼到东北工作直至牺牲的过程,这是一种叙事手法上的革新。影片《革命者》则以新颖的叙事手法,以李大钊就义前38小时作为叙事的起点,将行刑与人生片段进行交叉叙事,并从毛泽东、蒋介石、张学良、报童等八个人物的视角,多维度展现了李大钊先生的性格特点和人格魅力。电影《何叔衡》则将一大代表何叔衡的生平事迹,浓缩在他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四年多时光里,用他人生中的一个片段,折射出他光辉奋斗的一生。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这部影片可以视为建党精神的一部生动教材”(21)王一川:《〈何叔衡〉:生动诠释建党精神》,《光明日报》2022年1月3日,第6版。。
进入新世纪后,“奇观性”又成为中国电影的一大特点。当“奇观”进入精神谱系的影像书写实践中时,它既充实了历史的细节,又丰富了电影的叙事空间。奇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电影文本之外,通过明星效应、大规模的投资使电影本身成为一个奇观,以《建国大业》等电影为代表。它是中国电影史上表现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的产物。它几乎集结了当时中国影坛的所有有名气的演员,并通过声势浩大的媒体宣传,将影片成功运作成为一个社会焦点,此后类似的电影,都是沿着《建国大业》开辟的道路进行自我的“奇观化”。
第二,在电影文本之内,通过场面设计、情景设置强调“奇观”,也就是视觉的奇观化。这种视觉的奇观化倾向在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一片中达到顶峰。在这部电影里,孤胆英雄杨子荣不断化解接踵而至的危机,人物的遭遇在叙事的奇观性中转化为通关游戏式的智斗,在展示他如何落入和逃脱险境的过程里,人物就构成了奇观的一个组成部分。2017年的电影《建军大业》,则通过引入香港黑帮片、警匪片的类型要素使“建军”这一历史事件“奇观化”了。在攻占南昌城门的情节中,叶挺独自一人立于阵前,潇洒又桀骜,身后纷飞的炮火越是激越,他的形象就越发具有香港电影的意味。这种文本内的奇观化改造,在某种意义上是迎合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影群体审美趣味的结果。
威廉·弗莱明说, “现代技术的一切光辉都出现在现代艺术创作中”(22)威廉·弗莱明:《艺术与观念:西方文化史》,宋协立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34页。。电影从无声到有声到杜比立体声,从黑白到彩色到全色域,从小银幕到宽银幕、巨幕,从2D到3D,影视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拓宽了观众的观赏视域与审美空间。尽管卡梅隆认为,“在电影院看到的不是银幕而是影像……一切技术的目的都是让它本身消失不见”(23)萧游:《卡梅隆:精彩的梦,是笔好买卖》,《北京青年报》2010年1月14日,第7版。,但对电影观众而言,电影技术本身就构成了电影观赏的一个部分。比如在电影《集结号》《芳华》《战狼2》《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影片中出现的战争场面,从视觉上和心理上都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而学界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形成了探讨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强烈兴趣(24)参见陈旭光《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等系列论文。。
(三)历史唯物主义理性的复归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革命过程布满坎坷,腥风血雨中,也必然大浪淘沙、披沙沥金。大部分革命者不屈不挠,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但也有人曾经动摇、彷徨,有人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更有少数人背叛。如何表现历史上这些不太“完美”的革命者,考验着书写者是否有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理性。近些年来,在有关历史人物的塑造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复归,也是一个明显特征。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物的影像形象之中,刻画得最为出色的是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他是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绕不过去的人物。在《觉醒年代》《革命者》《1921》《红船》《开天辟地》《建党伟业》等影视作品中的陈独秀,不再是教科书上刻板印象式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筋骨的形象。他身上虽有旧文化人的狷狂傲物,也有小布尔乔亚的冲动与敏感,但更有革命领袖的理想与激情。“这一个”陈独秀是多面、立体的,也是可敬可爱可亲的。自从《大决战·辽沈战役》第一次出现林彪形象,其形象塑造也是一个关注焦点。如果说这部影片中的林彪还有些刻板的话,那么《古田军号》中的林彪形象就更立体。他的思想和主见,他对毛泽东的认同,体现了当代中国影视艺术在认识并塑造历史人物方面的理性与自觉。
当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电影塑造历史人物的基础,既源于历史也源于当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反映出时代的进步与认知,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电影《1921》里,发生在一大代表张国焘和李达之间的争论,具体的历史细节已很难考证,但围绕中共的章程、成立细节,是否应该向共产国际代表汇报的争论,既是电影叙事的需要,同时也暗含着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如何走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道路的现实。《古田军号》里,正面表现的朱毛对改造旧军队理念的激烈冲突,毛泽东对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唯共产国际的反感,这些在过去的宏大叙事中都曾被遮蔽的历史,在作品中被实事求是地再现,这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与真实的回归。
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影像书写实践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影像书写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何在?首先,当我们从影像书写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进行追溯时,就能深刻领会到精神谱系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实践性,理解伟大的建党精神所具有的开天辟地式的意义,以及它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而表现出来的延续性。
第一,精神谱系赋予影像书写实践以深厚的价值和意蕴,影像书写实践拓展并丰富了精神谱系的艺术表达边界。中国电影尤其是主旋律电影通过书写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将抽象的精神内涵具化为生动可感的银幕荧屏形象,而精神谱系恰好是主旋律电影影像合理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所谓影像合理性主要指的是,相较于文学、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影视艺术能够通过视觉化、听觉化的手段将对象形象化,并借助形象化赋予影像以某种意义。这种形象化虽然免不了艺术想象和创造的成分,但更多时候它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的,在主旋律电影中尤其如此。于是,通过在视觉上复归、重设或创造某个时空或人物,在听觉上增强或减弱刺激以形成某种情绪或倾向,影像呈现的效果就能超越影像呈现本身。比如,在《中国机长》《中国医生》两部电影中,创作者通过再造飞机遇险、医院突临疫情的空间,将危机视觉化,再通过混乱的现场同期声、激烈的电影配乐,造成紧张的观影效果,影像呈现的所指就实现了飞跃——它从表现危机本身转向了表现在危机中挺身而出的共产党人及其精神。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电影在呈现历史、表现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也通过这种呈现和表现获得并丰富了内在的价值与意蕴。一方面,百年党史为其提供了生动的创作素材;另一方面,通过书写建党精神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在挖掘和重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影像也更新并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
第二,影像书写实践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增强人们对精神谱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观念的产物,人类的影像实践是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映,同时它又是构成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发挥着宣传教育的重要功能。在列宁看来,“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25)《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94页。。他认为国家的中心工作是生产建设,电影恰好能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宣传和教育,因此要重视电影的生产和管理。因为电影所呈现和传达的观念、思想与价值立场,可以通过影像的合理性,直接或间接地在观众头脑中造成一定的效果,因此电影生产的“源泉”就显得格外重要。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及文艺创作的立场时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2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他针对当时文艺创作普遍存在的脱离实际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看到“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1页。。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凝练出来的观念、精神和价值体系,它源于建党精神,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并通过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而传承至今,因此它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和普遍性。当中国电影以其为源泉开展影像书写实践时,影像呈现所激发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也就更加全面而深刻。此外,精神谱系的传承性,既使中国电影可以反复书写与确认我们的来处——伟大的建党精神,同时又可以在精神谱系的坐标轴中锚定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正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
第三,影像书写实践是形成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之一,并可能沉淀为一个民族的审美旨趣与文化心理倾向。莫里斯·哈布瓦赫在1925年谈及集体记忆时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共有的记忆,它是由群体之中的每一份子共同建构并且传承下去的。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界定,在确认它的来源和构成要素的同时,也突出了其隐匿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集体记忆虽然来自于个人记忆,但它又有其独特之处,它不具备个人记忆那种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零碎性、遗忘性,而是表现出附着在历史或社会发展节点之上,并指向某事、某物或某人的特性,它一经形成就难以改变,进而可能沉淀为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某种文化心理倾向(29)参见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页。。回顾影史,以《英雄儿女》《地道战》《小兵张嘎》等为代表的电影,已经构成并内化进入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而以《觉醒年代》《山海情》《功勋》为代表的电视剧,又成为当代青年的重要影像记忆。通过观众的接受,影像书写实践在构成个体记忆的同时,又升华为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并通过这种记忆将影像书写的意义一代代传承下来。
第四,影像书写实践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辅助教材,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民众对党和国家的热爱。正如前文所述,影像的视听特性使得人们在表现历史事件或人物时能够将抽象的形象或理念具体化,因此蕴含在形象之中的价值理念也就更加容易为人所接受。中国电影史上那些抗日题材、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剧,无疑是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材。最近热映的《长津湖》得到广大青少年的热爱就是明证。像《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等电影,通过塑造乡村教师、驻村扶贫干部、推销员、带货主播等形象,讲述普通人在时代大潮中的初心、抉择和坚守,将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的观念以及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情感有机结合起来,同样也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材。这些影像也在重写当代史的过程中,确认了精神谱系的价值——尊重并认同历史,热爱并建设当下。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30)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作为讲述党的故事的重要阵地,中国电影电视通过其影像书写实践,将共产党人的奋斗史、成长史、精神史以一种生动而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通过塑造人物、再现孕育人物的时代风貌,将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人民选择的必然性、社会演进的必然性注入光影世界之中,于是中国电影的影像书写实践,也就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精神坐标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