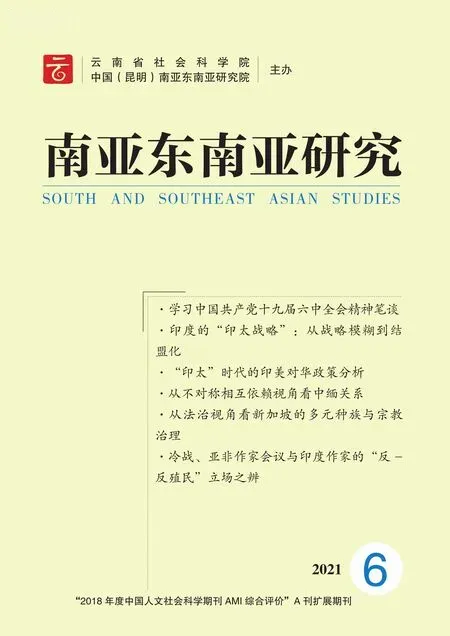天府之国与中印古代文化交流
薛克翘
中印文化交流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天府之国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十分密切。其内容之丰富,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说清楚的,写一部大书也不为过。本文着重讨论如下八点。
一、最早的文字记载
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那一天起,丝绸之路就与天府之国紧密相连,也与中印文化交流紧密相关。这个记载就是大家熟知的《史记·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中的那段故事: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约当今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北部地区)看到了蜀布和邛竹杖。张骞是汉中城固人,当时巴、蜀、汉中几乎是三位一体,而且城固地处成都通往长安的要道上。所以,张骞对天府之国的物产蜀布和邛竹杖很熟悉。当他在被匈奴人羁押十年后,到大夏国见到了蜀布和邛竹杖的时候,感到特别亲切,就要问清楚来历。一问方知,这些物产是从天府之国经云南和印度转口贸易到大夏国的。原来,从天府之国到西域还有一条久已存在的丝绸之路——西南道,又称牂牁道、滇缅道等。这条道上的民间贸易很发达。蜀布(过去或解释为苎麻布,稍偏狭,当包括蜀地的丝绸)就是这条道上最主要的货品。
到公元1世纪,希腊人写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中提到,中国丝和丝织品以印度为转运站,经大夏销往西方。①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86页。这就证明,在张骞以后,这条西南丝路还在正常运作当中。
二、“支那”与丝
张骞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但印度人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就知道中国。他们把中国叫作“支那”(梵文Cina)。这也与天府之国有关。中外学者讨论“支那”一词已经360多年了,多数人认为是“秦”的对音,②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4~69页;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一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3页;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载饶宗颐:《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这里不细说。印度人是从哪里知道“秦”的?无非是三个渠道,即西域道、西南道和南海道。笔者倾向于西南道。因为,据《史记》的《秦本纪》和《始皇本纪》记载,秦将司马错于前316年伐蜀,灭掉蜀国。又于前301年平定蜀侯之乱。嬴政即秦王位时,“秦地已并巴、蜀”。所以,印度人很有可能是从中国西南方得知秦国的,并开始称中国为“秦”(支那)的。这个时间与印度方面的文献记载也对得上。
印度有许多古书都提到“支那”,其中有一部《政事论》(Arthashastra),约作于前4世纪。它不仅提到“支那”,还说到“中国的成捆的丝”(cinapatta),而且他们还知道,丝是“虫子生的”(kitaja)。③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载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有趣的是,在此后几个世纪,当罗马人以穿丝绸衣服为时尚时,他们还以为丝是从树上长出来的。相比之下,印度人对丝的了解显然更准确。
三、蜀丝与蜀锦
至于蜀地养蚕缫丝的历史,则非常悠久,用李白的话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虽然是个传说,“四万八千岁”也未免夸张,但四五千年总是可能的。多年来,学界据《华阳国志》《文选》《艺文类聚》等,对蚕丛做过多方考证,公认他为中国养蚕缫丝的先祖。另外,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正妃嫘祖也教民养蚕,所生二子皆落户四川。又据《淮南子》等书,蜀、蚕二字同义,则蜀国即蚕乡。
养蚕缫丝的目的是纺绸织锦。蜀地既以养蚕缫丝为业,蜀锦则随之名满天下。成都被称为“锦官城”,或简称“锦城”,锦江也因蜀锦而得名。这些都是常识,不必多说。
最近读过一些关于蜀锦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文章,在谈到蜀锦传入中亚、日本等地时,有考古资料为佐证,是有说服力的。谈到蜀锦传到南亚次大陆的情况时,往往只有张骞在大夏见到蜀布的例子,显得很单薄。所以,这里要补充几条早期相关资料。
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建初九年(公元84年),班超派使者“多赍锦帛遗月氏王”。当时月氏人已经建立了贵霜帝国,统治着印度西北部的大片圭地。作为国礼的锦和帛,则是蜀地的特产。尤其是蜀锦,其他地方尚不能生产。
据《魏书·世祖纪上》,太延元年(435年)曾遣使二十辈使西域,二年,又遣使六辈使西域。又据《魏书·西域列传》,太延(435~440年)中,“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这说明太延年间大魏使者曾频繁去西域,所携礼品主要是锦和帛。董琬、高明没有到印度,但的确有大魏使者到过印度,有石刻为证。①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载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12页。
《洛阳伽蓝记》载,北魏神龟元年(518年),皇家派惠生、宋云去印度取经,“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②《洛阳伽蓝记》卷五《城北》。这里的“乾陀”即通常所说的犍陀罗国,在今巴基斯坦境内。这里的幡是丝绸所制,已不用说。锦香袋,当为蜀锦制品。
以上是东汉至北朝的例子。到唐代,例子就更多了,这里仅列两条:(1)据《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赐南天竺使者以锦袍。(2)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玄奘在那揭罗喝国(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一带,玄奘时属于西北印度)“施金钱五十,银钱一千,绮幡四口,锦两端,法服二具。”
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高僧著文,常以蜀锦比喻华美贵重的事物,并时常将蜀锦与“燕缇”或“吴绫”合称。①见《辨证论》卷四、《法苑珠林》卷一百、《兴福部第五》、《古尊宿语录》卷二六等。
四、三星堆的海贝
除了最早的文字记载外,还有考古资料。这要比文字记载早得多。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是20世纪80年代天府之国最重大的考古成就,震撼了世界考古界。人们看到了一种与中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文化。这个文化与海外也有不少关联。当时四川文管会曾对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写出两份发掘简报,②参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其中说到这两个坑里都发现了大量海贝。有考古学者指出,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的年代在殷墟一期和二期之间,即3400年前。③参见陈旭:《夏商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我们知道,四川并不临海,这些海贝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中国东部沿海来的还是别的地方?另外,这些海贝是做什么用的?是用作装饰、观赏还是用作货币?其中有一种虎斑贝,经生物学家鉴定,这种海贝仅产于印度洋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一带。④参见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关于这些海贝的用途,有人持不同看法,以为当时还没有货币经济,这些海贝只是装饰品、观赏品。但这恐怕站不住脚,如果拿同一时期的殷墟作比较,甲骨文的“贝”和“朋”都已出现,作为产品交换等价物的作用已经明显,是最初的货币。三星堆的海贝是大量的,其用途应该是相同的。
五、最早的印度侨民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有“身毒之民”。又说:“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国,见邛竹、蜀布,问所从来,曰:‘吾贾人从身毒国得之。’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徼外是也。”身毒即印度古译。永昌今属云南省,汉代为蜀地边陲。其时,永昌西通缅、印,北接巴蜀,为西南丝路的重要节点和货品集散市场。有身毒国商人长期在那里居住,与蜀商接洽贸易,并将蜀布、邛竹杖等货物转运印度及大夏等地,完全是情理中事。
《华阳国志·南中志》还记载永昌郡“圭地沃腴,宜五谷。出铜、锡、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纹绣。”“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有阑干细布,阑干,獠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又有罽、旄、帛、水精、琉璃、轲虫、蚌珠。”显然,这些物产并不完全是当地特产,而是四方商品的汇集。
六、中国取经僧
佛教在丝路精神文明交流中占主导地位达千余年之久,这正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最大项目。天府之国也曾在这千余年间为中印佛教交流做出过巨大贡献。
最早西行求法而又与天府之国相关的僧人是智猛,据《高僧传》卷三:
(404年),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同侣竺道嵩又复无常。……与余四人共度雪山渡辛头河(印度河)至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复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维罗卫国(又作释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人。……以伪秦弘始六年甲辰之岁迦毗罗卫,在今印度与尼泊尔交界处)。……后至华氏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一带)阿育王旧都。……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余经梵本,誓愿流通,于是便反。以甲子岁(424)发天竺,同行三伴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于凉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七月造《传》,记所游历。元嘉末卒于成都。
智猛取经经历九死一生,15名同伴有9人退缩,4人逝世途中。他在成都期间曾写出一本书《释智猛传》,与《法显传》大约相仿,可惜未得流传。
《釋迦方志》卷二:
宋元嘉(424~453)中,冀州沙门慧叡,游蜀之西界,至南天竺。晓方俗、音义,为还庐山。又入关,又返江南。
关于慧叡,《高僧传》卷七有传,文字略多于此。只知他在蜀之西界被劫掠,被迫牧羊,后被赎,周游诸国,至南天竺。但不知他去南天竺走的是哪条道,似乎并非西南道。照理说,川滇离印度更近,求法者可以选择西南道。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义净法师在印度听到一个传闻: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弶伽河(即恒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钵娜寺(意译鹿园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向莫诃菩提(即大菩提寺,意译大觉寺)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現今地属东印度王。①CBETA,T51,no.2066,p.5,b12.
这段文字中提到“蜀川牂牁道”,似乎有人通过此道去印度瞻礼游学,但字里行间有多重疑问。首先,支那寺的位置殊难确定。沿恒河东下四十驿(约三十里)许,已过千里,又如何礼拜离那烂陀不远的大菩提寺?支那寺若离大菩提寺近,如何又“地属东印度王”?其次,支那寺建成的时间,若距义净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691)五百余年,则至少在191年,即东汉晚期,其时印度并未有室利笈多王。“五百”或为三百之误?又如何有“唐僧”二十许人西去?若“五百”为五十之误,则可能有“唐僧”前往,而其时玄奘正在印度,《西域记》与《慈恩传》为何只字未提?总之,义净的这段记载中疑点很多,也许有义净的笔误?或者有刊刻之误?
大名鼎鼎的玄奘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伟人。他的事迹不仅在中国广为人知,在印度也家喻户晓。他在洛阳净圭寺出家为沙弥,后到长安求学,但因当时大唐初立,长安法师不兴,他便与二兄长捷法师一起来到成都,并在成都空慧寺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法师。这是他与成都的一段因缘。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记载了4名益州僧人西行求法的事迹:
明远法师,益州清城人,由海路经交趾(今属越南)、诃陵国(约在今加里曼丹岛西部),到师子国,受国王敬重,但因盗取佛牙被捉,受凌辱,去南印度,后不知所终。
义朗律师与弟弟义玄,成都人,从广西由海路经扶南(今柬埔寨)到师子国,敬礼佛牙后去印度,之后便无消息。
会宁律师,成都人,由海路前往印度,中途在诃陵国停留,并与当地高僧合作翻译出佛经《大般涅槃经后分》二卷,命小僧回国报送朝廷,故此经现存。会宁本人后来去了天竺,不知所终。
以上四人均为益州人,又都循南海道去印度。他们之所以不取道西南川滇缅道,一是因为他们要在国内周游访学,而是因为当时的西南通道仍然有诸多凶险。
宋代初年,朝廷出面组织一大批僧人西行求法,为中国佛教求法运动的空前壮举。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乾德四年(966),太祖下诏往西天求法,应诏者157人。《宋史·外国传六》记载稍异:“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范成大《吴船录》所记又有异:“继业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三处记载各有不同。也许《佛祖统纪》的记载是正确的。范成大《吴船录》记载他于淳熙四年(1177年)游历成都、登峨眉山、访牛心寺的一段传奇经历。在牛心寺,他不仅观赏到罗汉图,还发现寺中所藏《涅槃经》,僧人继业在经的背面记载了求法行程。范成大把这段记载抄录下来,使后人得知继业三藏的大体经历。继业回国后赶往京城时,宋太祖已过世,太宗即位(976年),也就是说,继业西行回国已经历时十来年。他向朝廷献上西天取回的梵夹和舍利后,皇帝下诏可选择名山修行,继业便选择了峨眉山北边的一处地方,先建庵舍,后建牛心寺。继业留下的西域行程记录对研究中印古代交通很有价值。
与继业同批西行的僧人中还有成都沙门光远。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光远于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983年)到京,向朝廷进献西天竺王子的表文,以及佛顶印、贝多叶、菩提树叶。皇帝命施护三藏译出表文:
伏闻支那国有大天子,至圣至神,富贵自在。自惭福薄,无由朝谒。远蒙皇恩,赐金刚座释迦如来袈裟一领,即已披挂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一切有情,度诸沈溺。谨以释迦舍利附沙门光远以进。
光远为中印文化交流增添了一段佳话。
七、印度来华僧
唐代,有两位印度高僧与蜀地有关,这二人的故事都很神奇,带有民间传说的性质,不妨以中印文学交流视之。
一位是天竺无名僧。据《宋高僧传》卷十九,他在韦皋出生后三日来到韦家,说此子乃诸葛亮转世,将为蜀帅,做剑南节度使二十年,官位极其显贵,会做到中书令太尉。后韦皋于贞元元年(785年)出任成都府尹,有功,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时晋升太尉。天竺无名僧的预言一一应验。
另一位是梵僧难陀,事极诡异,今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全录于下:
释难陀者,华言喜也,未详种姓何国人乎。其为人也,诡异不伦、恭慢无定。当建中年(780~783年)中,无何至于岷蜀。时张魏公延赏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甞入水不濡,投火无灼,能变金石,化现无穷。”初入蜀,与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聚众说法。戍将深恶之,亟令擒捉。喜被捉随至,乃曰:“贫道寄迹僧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曰:“此皆妙于歌舞。”戍将乃重之,遂留连为置酒肉,夜宴与之饮唱。乃假襦袴巾栉,三尼各洞粉黛,并皆列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欲半酣,喜谓尼曰:“可为押衙蹋舞乎。”因徐进对舞,曳练回雪,迅起摩趺,伎又绝伦。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妇女风邪!”喜忽起,取戍将刀。众谓酒狂,坐者悉皆惊走。遂斫三尼头,皆踣于地,血及数丈。戍将大惊,呼左右缚喜。喜笑曰:“无草草也。”徐举三尼,乃筇竹杖也。血乃向来所饮之酒耳。喜乃却坐饮宴,别使人断其头,钉两耳柱上,皆无血污。身即坐于席上。酒巡到,即泻入断处,面色亦赤,而口能歌舞,手复击掌应节。及宴散,其身自起,就柱取头安之,辄无瘢痕。时时言人吉凶事,多是谜语,过后方悟。成都有人供养数日,喜忽不欲住。乃闭关留之,喜即入壁缝中,及牵之,渐入,唯余袈裟角,逡巡不见。来日,见壁画僧影,其状如日色。隔日渐落,经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灭。有人早见喜已在彭州界。后终不知所之。
梵僧难陀的故事首见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传》袭之。《酉阳杂俎》对后世笔记小说、神魔小说的影响亦甚深远。暂不论。
五代时,又有一梵僧来华,亦神奇。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二:
(贞明)四年(918年),西天三藏钵怛罗至蜀。自言从摩伽陀国至益州,途经九万九千三百八十里。时蜀主王建光天元年(918年)也。三藏自言,已二百七十岁。
这里,梵僧钵怛罗的年龄和摩伽陀国①摩伽陀国,Magadha,印度古国名,又作摩揭陀等,疆域历来多变,约指今印度比哈尔邦及其周边地区。至益州的距离都过于夸张。重要的是,他东来的路线正是西南丝路。
元代,有一位名叫指空的印度僧人来华。据称他是摩揭陀国第三王子,周游过印度和斯里兰卡,约于1287年从新疆进入中国,曾于1291至1294年到峨眉山,瞻礼普贤像,并坐禅三年。后至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苏等地传教,1335年受元朝皇帝接见,并被指派至高丽金刚山进香、传教。1329年回大都,1363年去世,享年108岁。②段玉明:《指空——最后一位来华的印度高僧》附录《指空年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94~196页。
八、佛经翻译与刊刻
佛经是印度文化的一座宝库,其内容包罗万象。佛经的汉译与刊刻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重要事项。天府之国于此有过重要贡献。
天府之国人杰地灵,曾出现过费长房这样的译经大德,出现过一些辛勤奉献而默默无闻的翻译家,还曾有印度高僧在此译经。下面只介绍两位译经大德。
据《开元释教录》卷七:翻经学士费长房为成都人,原本出家,北周废佛时还俗,隋朝兴佛,未再出家。又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开皇元年(581)冬,有沙门智周等赍西域梵经260部来长安,文帝下敕翻译。随即,大兴善寺成为全国译经中心,一时间大德汇聚,文士济济,王公宰辅,冠盖相望。其时,大兴善寺不仅汇聚有来自印度的高僧,有寓居华夏的印侨,也有自印度取经归来的汉僧,以及学过梵文的僧人、学士等。其中,来自天竺的主要是“开皇三大士”:那连提黎耶舍(又作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从西域取经归来的中国高僧有宝暹、道邃、智周等十一人。此外尚有内地大德十余人,以及官员和学士等。在大兴善寺的首批翻译家中有多人来自成都,费长房是其中之一。他在译场中担任“笔受”,负责记录和整理翻译出的汉文经文。费长房的主要成就是编纂出《历代三宝纪》(又称《开皇三宝录》)十五卷,于开皇十七年(597年)进献。此书虽属经录,但包括不少中国佛教史内容,历来受到学界重视。
据《续高僧传》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七等,三藏法师阇那崛多来自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国。起初,他与师友共十人一起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于阗,辗转到达青海时,十人中多半亡殁,只剩四人。560年,阇那崛多等到达长安,受到周明帝的高规格礼遇,为便于他居住和译经,特地建造了四天王寺。他在长安译出佛经多部。谯王宇文俭出镇益州,阇那崛多应邀同行。他在益州住龙渊寺,做僧主三年,并译出《妙法莲华普门重诵偈》、《种种杂咒经》和《佛语经》。周武帝灭佛时,他被迫流落甘肃等地,幸好遇见取经僧宝暹、道邃、智周等人,便一起研究佛经。隋朝建立,阇那崛多等来到长安,成为译经场主力。在那连提黎耶舍故后,阇那崛多成为唯一权威,共译出佛经37部(或39部)176卷(或192卷)。
天府之国对汉文大藏经的刊印也曾做出过贡献。
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开封太平兴国寺印经院建成。八年,成都的一大批经板雕成,并送至京城开封开印。这就是中国大藏经史上著名的《开宝藏》。据我国学者研究,《开宝藏》自开印起,经多次增补,直至宋徽宗宣和初年(1119年前后)终止。最后,《开宝藏》收经总数约为1565部、6962卷,分为682帙。学界的评价是,“《开宝藏》是中国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中国刻本大藏经之先河。它的问世无疑是中国刻藏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件。中国佛教典籍的传播从此有了一个可以成批生产的规模化的定本;而中国佛教大藏经的雕造也因为有了《开宝藏》这个标本而一发不可止”。①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83~90页。